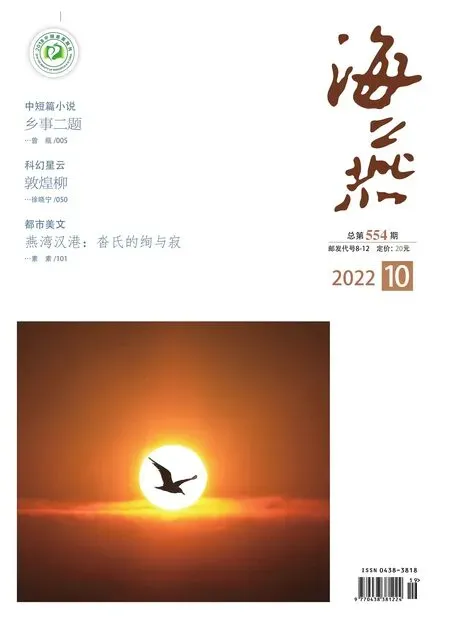燕灣漢港:沓氏的絢與寂
文 素 素
大連建城史,始于燕。
大連設治史,始于漢。
漢以前,中原文化對東北有兩次重量級輸入,一次是箕子東遷,一次是燕國東擴。
箕子東遷,走的是陸路而不是水路,大連地處半島一隅,殷商大族們負笈的經典,未在這里打開一頁。
燕國東擴,因置遼東郡,大連為燕管轄。貊與燕數十年混血,青丘之野,盡染華夏。
然而,燕擴遼東,以及短暫的秦國一統,都只是大戲演出前的墊場。千呼萬喚中,帷幕拉開,真正的主角是漢。滴水穿石,功在不斷,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終將夷地耕成漢土。
一、海邊的牧羊城
公元前1046年,一場牧野之戰,商朝頃刻化為烏有。商亡,周武王將其弟召公奭封于燕。燕是商朝一個侯國,侯是世襲的,也是有名有姓的。變成召公奭封地之后,國名仍叫燕,卻換了姬姓。

這只姬姓的燕在北方飛了800多年,有700多年飛得戰戰兢兢,因為南有齊國,一直對它虎視眈眈;北有東胡,時不時就來一場襲擾。飛得這么窩囊,連老鄰居齊桓公都看不過眼,主動放棄對手思維,出兵助燕,伐山戎,打令支,斬孤竹。收兵南歸之時,齊桓公居然還大大方方割了一塊國土給燕。
幸好有了一個燕昭王,國運總算開始向好。
公元前284年至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派大將秦開北襲東胡,使“東胡卻千余里”,接著東擊箕氏朝鮮,又“取地二千里”。
公元前300年,燕昭王作出兩個大動作,一是設郡置官,以加強政治管理;二是修筑長城,以加強軍事防御。《史記·匈奴列傳》載:
燕亦筑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
正是閃電般的北破東胡、東擊朝鮮、建長城、置五郡、開疆拓土之舉,讓遼東第一次被來自中原的燕納入版圖。
郡是二級政權,治所設在襄平,也就是今天的遼陽。郡對遼東半島南部的大連,只是一種大而化之的管。但有記載說,燕在遼東、遼西兩郡曾設二十九個縣,究竟在大連境內設了幾個縣,叫什么名字,卻未見確切記載。
燕已今非昔比,一下子多了五個郡,翅膀頓時就硬了起來,一時竟出現“士爭趨燕”之盛況,更有大量燕民從薊地遷入遼東。千古夷氛,遂為華風所覆。
燕的國力自此大增,尤其是黃渤沿海盛產魚鹽,簡直給燕打了雞血,助它走出了一條“以鹽興邦”的崛起之路。《史記·貨殖列傳》載:
上谷至遼東……有魚鹽棗栗之饒。
比《史記》更早的《管子·地數》載:
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可以當武王之數。
遼東之煮,就是煮海水取鹽。早在青銅時代,大嘴子先民就曾在大連灣岸邊用海水煮鹽,這個傳承有序的地方產業,讓燕變成一匹黑馬,以遼東之煮當主打商品,去和中原諸國作交易,看得近鄰齊國直眼饞。最后,一直氣虛血虧的燕,缺席了春秋五霸的燕,竟憑魚鹽之利,一躍登上戰國七雄榜。
戰國始于公元前475年,結束于公元前221年。燕據遼東始于公元前300年,亡于公元前222年。就是說,大連被燕管轄的78年,屬于戰國的中后期。
因為是戰國,大連不只是燕的經濟后盾,比經濟后盾更不一般的角色,在于大連是燕的海防前沿,軍事要沖。正因為如此,大連建城的歷史始于燕,準確地說,始于戰國,大連在這一時期所建的城,都叫戰國城。
戰國中期,大連過了一段安寧日子。戰國后期,秦在中原每滅一國,燕就嚇出一身冷汗,于是在半島南部緊要處大興土木,或建管控舟楫往來的關城,或建扼守海防岸線的城堡。
這些關城或城堡,都是普通的土夯,其實是一種急就章。戰爭風云已在不遠處升騰,刀兵未逼近時,它們是城,烽煙一燃,便是防御工事。
《大連通史》載:
大連地區發現的戰國城址主要有牧羊城、黃空亮子城、張店城等。這些城都是始建于戰國后期,西漢甚至東漢仍然沿用。
牧羊城建在將軍山下羊頭洼岸邊,它是遼東半島南部第一座海防城堡,也是戰國城代表作。
將軍山在老鐵山西北麓,面向渤海。處在自由遷徙期的古代先民,已經在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之間摸索了幾千年,因為船小槳陋,他們對海溜子、風向、氣候了如指掌,于是發現渤海是內陸海,又有將軍山擋著南來的風,認為山下的羊頭洼最適合當碼頭。當越來越多的船聚集在羊頭洼,替它們遮寒擋風的將軍山,便在秦漢以前最早有文字記載。為其取名者,或許就是在羊頭洼岸邊建牧羊城的燕人。
羊頭洼之名,來自一個用羊頭祭海的傳說。這個民間傳說,不知始于何時,因為在秦漢以前的文字記載里,只見將軍山,不見羊頭洼。然而,無論它何時有名,將軍山和羊頭洼是亙古就在的。
比較起來,自然是牧羊城來得晚,叫這個名字,與羊頭洼傳說有關,祭海者先是向海里拋真羊頭,后來改用木刻的羊頭,因而牧羊城還有一個土名,“木羊城”。直到現在,仍有人兩個名字混著叫。建城之初,燕人或許給它取過什么名字,或許還未來得及有個名字,就已在戰火中與守城燕軍同歸于盡。
事實證明,再強的燕,敵不過更強的秦。公元前230年,秦始皇在關中平原升帳宣令,正式開始了滅六國之戰。3年后,就發生了那個眾所周知的故事。燕太子丹派俠客荊軻去咸陽獻圖,圖窮匕首現。
正是荊軻的自殺式襲擊,惹得秦始皇怒而起兵,派王翦揮師東來。燕王喜和太子丹爺兒倆驚恐萬狀,急率宗族和衰兵退到遼東,茍延一個國的殘喘。4年后,公元前222年,秦為刀俎,燕為魚肉,歷史給失敗者畫上了句號。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烽煙四起時,青丘舊墟,燕國城堡,皆成斷壁殘垣。戰國城代表作牧羊城,也墻破門壞,狼藉無形。
但是,倒塌的牧羊城,據說曾在秦代重新站立起來。干這個好事的是徐福船隊滯留在半島的能工巧匠們。
《大連通史》載:
秦始皇統治時期,曾派遣方士徐福征三千男女并五谷百工,及大批航海物資,由山東瑯琊港入海,沿廟島群島駛抵旅順(時稱沓津)補充飲水和食物,再沿黃海近岸、朝鮮西海岸,最終抵達日本列島之新宮町熊野灘并留居日本。徐福船隊停泊旅順期間,有數十人因病暈臥船不能繼續隨航而留居大連地區,其中不乏能工巧匠。
但也有人說,牧羊城重建于漢代。遼東“地逴遠”,秦始皇父子兩代的東巡,皆駐蹕于遼東灣岸邊的碣石宮,他們最多朝遼東半島方向瞄了幾眼。再說,即使那些留下來的能工巧匠真這么做了,秦國只有15年,在大連幾乎沒什么存在感,那幾十個秦人很快就被編入漢籍,重建后的牧羊城,就應該算漢城。說到底,漢代偉大,漢城也偉大。
兩漢之世,大連享受和平的時間最長,牧羊城所在位置重要,把它修得多么漂亮都在情理之中。正因為它在將軍山下的羊頭洼,這里自古以來就是個最有名的避風港,東漢末年來遼東避亂的齊魯名士,三國東吳北上勾搭公孫氏的船隊和使臣,隋唐征討高句麗的水路大軍,宋金結海上之盟的間諜說客,明代剿元抗倭的鎮邊將軍,都把這里當作必泊之岸,必駐之所。
然而,它最終還是成了廢墟。有人說,牧羊城被徹底棄用,應該在明末清初。棄用不等于消失,在清初的《盛京通志》里,仍可看出它的綽約姿影:
牧羊城,城西南一百五十里,周圍二百五十步,門一。
牧羊城在金州城西南,能被描述得這么清楚,說明它仍是完整的一座城,因為它是大連戰國史不可忽略的一個地標,清代的志書必須給它記上重重一筆。
如今的牧羊城,城址還在,一塊碑石,伴著幾段夯筑的土墻和城基。不知有多少次走近它,每次都以為穿越到了戰國,明明是莊稼葉子在窸窣,卻覺得那是戰國守城者的竊竊私語。
二、沓氏,沓津,沓渚
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初登大位,就作了一個關乎遼東命運的頂層設計:“筑城廊,立邊堡,移民實邊。”
朝廷的執行方式,就是號令齊魯燕趙子民去遼東墾殖,凡響應者,不但賜給衣物、糧食、種子、牲畜、工具,還派官軍一路護送前往。為招徠更多的響應者,朝廷甚至專出一策,對平民小吏加官進爵遷徙,對罪犯歹徒實行減刑遷徙,以至于每筑一座城廓,都遷徙千戶以上。
對于遼東,人口就是一切。大連更是如此,因為這里到處都是燕秦之戰留下的荒蕪和凄涼,死去的人已成舊鬼,活著的人全部跑光。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彼時的大連,就是這樣的慘象。
移民實邊,其實是一場治愈。大連一掃往日的蒼白和死寂,戰國的牧羊城,已然改頭換面,將軍山下的羊頭洼,日夜迎接著返城者,以及蜂擁而至的遷民。
公元前110年,遼東形勢一片大好,睥睨天下的漢武帝便在秦始皇東臨碣石一百多年后,開始了他此生第一次東巡之旅。然而,天時地利作美,人卻不和。漢武帝在遼東前腳走,后腳就出事了。
公元前109年,衛氏朝鮮右渠王殺了西漢遼東都尉。更惡劣的是,在此之前,衛氏已阻斷真番、辰國與西漢海上通使之路60年。兩件事攢在一起,那就算總賬吧。于是,第一次東巡之后的漢武帝,發起了中原王朝歷史上第一次大軍東征。
當年秋季,漢武帝發兵五萬,派樓船將軍楊仆率一支水軍,從山東半島登萊入海,派左將軍荀彘率一支陸軍,自遼東南下渡鴨綠江,兩面夾擊衛氏朝鮮。
楊仆的水路大軍,曾在遼東半島登陸短暫休整,大連境內的將軍山和三山浦,便是漢軍兵馬糧秣囤駐地。待養足精神、裝備充盈之后,水路漢軍即升帆鳴鼓,鏗鏘東行,直搗衛氏朝鮮老巢。
衛氏被伐,完全是罪有應得。燕將衛滿原是盧綰部下,兩個人背叛漢室,恐遭漢高祖追殺,盧綰北逃匈奴,衛滿東遁朝鮮。箕氏朝鮮第四十代王叫箕準,他不忍看衛滿落魄,好心贈地封官,卻養了個白眼狼,900年箕氏江山,竟被衛氏朝鮮一朝取代。正因為有了這個資本,衛滿便開始與中原的漢朝叫板,他也不看看漢武帝是誰。
這是一場聲勢浩大的討伐之戰,水陸兩支漢軍,聯手打了一年。結局是漢軍攻陷衛氏朝鮮都城,右渠王被部下所殺,存在了90年的衛氏朝鮮,飄成了漢代的一粒灰。
一吐塊壘的漢武帝,隨后就在衛氏朝鮮舊地設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三國志·魏書·東沃沮傳》載:
漢初,燕亡人衛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漢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鮮,殺滿孫右渠,分其地為四郡。
當被衛氏阻斷了60年的通使之路重新打開,漢武帝也因此創造了兩個第一:第一次由中原皇帝下令、開通第一條海上國際航線。
就是說,在此之前也有航線,但它不是中原皇帝欽準的,而是民間自發的,歷史遺留的。性質不同,這是朝與野之分,今與昨之分。漢家史官當然不會偷懶,一定要把此功記給漢武帝。
在這條航線上,大連雖然既不是始發港,也不是終點站,然而雨露均沾,興高采烈,消沉了那么久的半島港灣,終又重現往日的喧響。
公元前107年,收拾完了衛氏朝鮮,漢武帝便把目光內收,正式置郡設縣。有個說法,遼東郡,始于燕,定于秦,臻于漢。遼東郡所跨疆域,北起“遼東故塞”,與夫余、穢貊為鄰;南至遼東半島,隔海與山東半島齊郡呼應;西至醫巫閭山,與遼西郡接壤;東至鴨綠江以東,與樂浪郡相毗。雖只一郡之地,卻廣袤無邊。
《前漢書·地理志》載:
遼東郡,秦置:屬幽州,縣十八。
遼東十八縣,大連有二:文和沓氏。這是大連最早的縣治,也是迄今為止唯一可見的白紙黑字。就是說,大連的面孔由模糊變清晰,以前是被郡宏觀地管,之后是被縣微觀地管。這種由二級下沉至三級的管,這種來到家門口的管,讓大連走到一個陌生的歷史關口,大連也將開始一個簇新的歷史敘事。
兩縣方位,文縣在北,沓氏縣在南。兩縣名字,因水而得。文縣治所前有一條汶水,流入西南方向的復州灣;沓氏縣治所前有一條平陽河,流入西南方向的普蘭店灣。復州灣和普蘭店灣,都屬于誕生于第三紀的渤海。
門前有河,不遠處有海,兩縣五行都不缺水。史書對沓氏闡釋尤多。許慎《說文解字》云:“遼東有沓縣。”《資治通鑒》胡三省注:“遼東郡有沓氏縣,西南臨海渚。”《漢書》應劭注云:“氏,水也。”
沓為多,氏為水,沓與氏連在一起,就是很多的水。也是因為,沓氏縣在半島南部,三面環水,水豈止是多,而是太多。
兩縣治所,沿用燕時舊城,也就是戰國城。漢代那么長,雖然沒挪地方,但一定搞了不知多少次舊城改造。今人對兩縣治所地址的確認,卻費了不少周折,各路史志專家像認祖尋親一樣,遍地去找它們依稀杳然的影子。最后塵埃落定,沓氏縣遺址,是現在的張店漢城,也就是前面說的,靠近普蘭店灣;文縣遺址,是現在的陳屯漢城,即前面說的,靠近復州灣。沓氏對張店,文縣對陳屯,名字有古有今,令人時空難辨,聽著也擰巴。但,這是考古慣例,只能以今名稱之。
沓氏在張店,依據是這里有隱約可見的城垣,而且是大城里面套著小城。據說小城為后來的遼金所建,主要用于屯軍。另外,這里出土了“千秋萬歲”瓦當,一對“馬蹄金”,一方“臨穢丞”封泥。后者與平壤城出土的“沓丞之印”成為一種互證,說明兩個城之間,乃至兩個半島之間,曾有過相當正式的官方往來。
文縣在陳屯,一是城址在大連北境,與張店拉開了必要距離,二是城的規制巨大,出土文物也多,城的四周,還環繞著近兩百座漢墓。只有一個解釋,此乃文縣之所在。
兩縣之外,還有鄉邑。據記載,文、沓兩縣,時有鄉邑51座。有些鄉邑也是城,只是比縣城小些。在漫長的漢代,在僻遠的半島,它們的存在,是對縣城的烘托,最初是星散的種子,后來是葳蕤的綠蔭。
文、沓兩縣,都是大連的子城,如果非要認定一個母城,肯定不是文縣,而是沓氏縣。因為大連現在的主城區,在漢代的沓氏縣境內。沓氏,也可以說是大連的乳名。
沓氏縣沿海有許多港灣,近海有許多島嶼。在漢代記載里,這些港灣和島嶼有一個泛稱,港灣都叫“沓津”,島嶼都叫“沓渚”。津和渚像一群孩子,沓氏是它們的爹,都得跟著姓沓。
最有名的沓津,非羊頭洼莫屬。不管羊頭洼在漢以前和漢以后叫什么,它在漢代的名字,就叫沓津。牧羊城也一樣,不管漢以前和漢以后叫什么,它在漢代的沓津岸邊,它的名字叫沓津城。
有漢一代,羊頭洼是最有故事的沓津,牧羊城是最有故事的沓津城,因為光芒太強,它們把別的沓津和沓津城都給屏蔽了。
論行政級別,沓津城無法跟兩座縣城比;論戰略地位,兩座縣城得給沓津城讓地方。那些數不清的銅鏃,說明沓津城一直具有軍事防御性質;那些“長樂未央”瓦當,說明沓津城與中原關系很密切;那些與身份有關的物件,諸如“武庫中丞”封泥、“河陽令印”、“侯賀私印”之類,說明沓津城的影響力僅次于老上級沓氏縣。
沓津城最顯山露水的一次,借了漢武帝滅衛氏朝鮮的光,一塊武庫中丞封泥,還原了那場浩大的登陸行動。
封泥是把印章蓋在干燥堅硬的泥團上,原印是陰文,鈐在泥上,就成了陽文。武庫中丞是個武官,在朝中專管兵器和軍備,他的封泥遺落在沓津城,只有兩種可能:一是他曾隨軍來到前線,兵器運到岸上之后,他親自鈐印封泥,再向下發送;二是他本人沒到前線,封泥是他在后方兵庫鈐印過的。
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在那場大征討中,樓船將軍楊仆所率的五萬水路大軍,曾在沓津登岸補給,岸上的沓津城,曾是儲運軍械物資的中轉站。
沓氏,沓津,沓渚。呈現的意象,就是很多的水,很多的灣,很多的島。紛至沓來,泱泱如陣。
但是,查看漢代遺存,又有太多缺憾。文、沓兩縣,存續了那么多年,一任一任來了那么多縣官,卻沒能給后世留下一本哪怕很薄的縣志,留下幾頁哪怕只言片語的記事。否則,不知會有多少驚世駭俗的奇聞,多少悲歡離合的際遇,從那些發黃的故紙堆里魚貫而出。
三、埋在地下的繁華
渤海岸邊有個金州灣。灣南岸有個地方叫營城子。
羊頭洼在漢代有名,是因為海邊有一座戰國城,金州灣在漢代應該也很有名,因為海邊有一片神秘的漢墓。回到漢代,金州灣跟羊頭洼一樣,也叫沓津。
其實,漢墓是果,是蓋棺定論,它們所在的沓津是因,是背景和緣起。所以,看漢墓的時候,我常常走神。因為在漢代,半島南部不止金州灣一個沓津,而是一個連一個的沓津,如果沒有這么多沓津,就不會有這么多漢墓。而所有的沓津,都串在古人開辟的航線上。
《大連港史》載:
從距今5000年左右起,大連原始的海上航行活動范圍已擴大到山東的廟島群島,并以廟島群島為中介進而延伸到山東北部沿海地區;到距今約4000年左右,大連與山東煙臺地區的海上航線已相當成熟。
5000年左右,正是大汶口文化與遼東半島相互走動的蜜月期;4000年左右,正是龍山文化與遼東半島你來我往的好時光。因為兩個半島隔海相望,古人走向彼此的方式,唯有“循海岸水行”,卻在不經意間,在海上蹚出了一條看似無痕的古道。
行駛在古道上的大汶口人和龍山人,不但在船艙里裝著各種谷物,還裝著煮食谷物的陶器。行駛在古道上的小珠山人和郭家村人,不但用岫玉打磨出精致的玉斧,還讓那些圓潤的玉玦、玉珮、玉環戴在了大汶口人和龍山人的頸上。
4000年前,在行駛于這條古道的船上,坐著一個國王。他是中國第一個野馬馴養師,第一輛馬車發明者和制造者,也是第一個載入遼東半島史籍的真實人物。《大連通史》載:
先商第三代王相土從今遼東一帶移居河南商丘,因懷戀故土,往返于遼豫之間,開辟了今蓬萊至大連航線,使大連與山東北部沿海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日繁。約公元前十七世紀,商湯滅夏。至帝辛(紂)時期,大連地區社會已由地區性組織轉化為方國。
商初有相土,將商族版圖東擴到渤海兩岸。商末有紂王,親自葬送500多年江山。但是,相土開辟的這條海上航線還在,且一直暢通無阻。
3000多年前,青丘已經由部落而升為方國,青丘國主要去洛陽參加成王之會,應該就是沿著相土當年開辟的航線,往返于遼豫之間的吧?
春秋之世,這條海上航線已然具有了政商交織的色彩。《史記·貨殖列傳》載:
北鄰烏桓、夫余,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
由此可見,燕國東擴,不只是疆域擴大了,海外貿易也賺大發了。燕幣明刀,成了硬通貨,從燕地薊都,到遼東半島,再到朝鮮半島北部,各地都有出土。有錢的地方,就有人在走動,有商品在流動。更重要的是,海上有船在開動。
秦滅燕之后,這條海上航線便被秦人接管。證據也是錢,在平壤附近,出土過罕見的秦半兩。別看秦的歷史短,秦幣卻走得很遠。
然而,經商這件事兒,秦和燕都不是齊國的對手。據記載,5300年前,大汶口人就織出了絲綢。至春秋時代,齊國人織出了“齊紈”,魯國則織出了“魯縞”。齊國和魯國有仇,管仲就給齊桓公出了個主意,用齊紈跟魯縞打貿易戰,結果把魯國打敗了。那么多過剩的齊紈和魯縞,不知道裝沒裝在商船里,循海岸水行,去異地他鄉找買家。
《管子·輕重》載:
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毤服而以為幣乎?……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后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
文皮,即虎豹之皮。聽齊相管仲的口氣,有點仗勢逼迫的意思,如果這兩個國家不前來朝拜,就得用天下皆視之為寶物的皮張和皮服來交換。連接著三個半島的渤海和黃海,已然被齊老大借貿易之名,行朝貢之實。有朝貢,就得有封賞,發和朝鮮貢的是文皮,齊國賞的大概就是齊紈吧?
漢代的驕傲,就是它讓這條海上航線更加繁忙。
彼時,已有三條固定的水路穿過沓津:一條是航至遼東半島之后,或登陸北行,或沿渤海岸北上;另一條也是航至遼東半島,補給之后,沿渤海岸上溯遼河,再入太子河,直至遼東郡所在地遼陽;還有一條是航至遼東半島,然后沿黃海岸北行,入鴨綠江口,再轉至遼東或朝鮮半島。
除此之外,從長江口至遼東半島,也是一條涌動了數千年的海路,且在漢魏之際達到了鼎盛。《三國志·吳主傳》載,嘉禾元年:
三月,遺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冬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稱藩于權并獻貂馬。權大悅,加淵爵位。
遠處江陵的孫吳為了牽制曹魏,經常通過海路與遼東公孫氏勾結,公孫氏則遣使“稱藩于權”。吳軍每次北上,駐泊地就是沓津。據同書載,嘉禾二年:
三月,遣舒、綜還。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
暫且不論公孫和孫吳兩家的關系,光是將兵萬人、九錫備物的壯觀場面,就給我一種眩暈感。如此多的人,重舳巨帆,乘海齊發,航行于如此漫長的千里水道,在中國航海交通史是開篇,在亞洲和世界交通史也罕有。
不管哪一條水路,必經半島南部的沓津,而且,幾乎是約定俗成的習慣,走渤海岸的船多,走黃海岸的少。于是渤海一邊不只人煙村落稠密,墓地也稠密。這也就是為什么,在營城子地下,會有大連乃至東北最大一片漢墓群。
有人說,這里叫營城子,一定是先有城,后有墓,城在中央,墓在四周,一般都是這個邏輯。而且,有這么多漢墓埋在這里,那個城一定很大。有人甚至認為,那個很大的城,極有可能是沓氏縣城。于是,人們就在營城子附近尋找那個大城,城沒找見,卻找到了越來越多的漢墓。
漢代是大連有史以來第一個盛世。營城子漢墓是埋在地下的漢朝,埋在地下的繁華,可以說,它是盛世背書,也是盛世注腳。
上世紀20年代末,施工者在營城子挖出了一座東漢大墓。
首先,它是一座磚式墓。漢以前,大連土著多以石為墓,諸如積石冢、石棺墓、石蓋墓、石棚等等,可謂遍地都是。以磚砌墓,顯然是中原傳統,等于修改了大連原住民的葬俗。據記載,大連早在西漢就有磚窯,制磚技術,各種紋飾肌理,可與中原媲美。東漢再后,墓磚上的羽狀紋、菱形紋、混合紋,更是精致得無以復加。
其次,墓穴的結構奇特,據說在國內屬于僅見。整個墓穴有主室、套室、側室之分,墓頂是曲面球形的穹隆拱式,主室與套室呈上下兩層穹隆頂,如此造型,不只是空間上有一種玄妙,建筑工藝也復雜到家了。記得,第一次走進墓穴參觀,我曾在心里輕嘆了一聲,給逝者造一座墓肯下這等功夫,那么生者居住的屋宇又該怎樣軒敞?
最后,就是壁畫。墓大,室多,畫便不止一幅。亮點在主室北壁,畫面上的墓主是個中年男子,頭戴一頂三山冠,身著一襲漢式長袍,腰佩一柄長劍,腳踏一團祥云,正目光從容地注視著遠方。在他前面,有一個戴方巾、持羽扇的方士。在方士前面,還有一個手持赤草、腳踏云端的羽人,方士和羽人,各以不同手勢,為墓主作引領狀。畫面上下,還有更多內容,上方是傳說中的朱雀和蒼龍,下方則是家眷祭拜送別情景。總體來看,就是一幅典型的中國人都能看懂的“升天圖”,只不過達官顯貴死了,畫在墓壁上,平民百姓死了,畫在棺槨上。
升天圖是司空見慣的題材,讓人高看的是繪畫技巧。據說,此作出自民間畫師之手,畫風卻代表著漢代繪畫的一個重要流派,構圖層次清晰,人物形態生動,線條自如流暢,墨線勾勒,略加一點朱色,整個畫面就呼之欲出了。于是,有專家經過研究認為,它是中國美術史上具有重要價值的代表性作品,在世界藝術史上也占有一席。民間有高手,此話看來也適用于東漢。
本世紀初一個秋天,營城子又因為施工而成了漢墓發掘場。彼時,我正給一部大連歷史紀錄片撰稿,那天正跟著攝像去拍營城子漢墓,現場專家告訴我,站在渤海岸邊向營城子望去,凡是凸起的地方,下面就是漢墓,走在這里,一不小心就可能踩在了漢代的棺蓋上。因為他們在這里一次性發現了一百八十多座漢墓,出土了兩千多件文物。
這次考古最吸睛的,是一座剛剛打開的西漢大墓,里面居然有一條金質十龍帶扣。看它的奢華程度,一百條愛馬仕外加一百條LV都抵不過。扣面上,一條大龍和九條小龍騰空穿行于繚繞的云氣之間,出沒于浩瀚的天穹之上。在龍眼和龍脊上,綴滿了圓形金粒,大者如粟米,小者如莧子。龍身是用金絲編結的,纖細如毫,渾然天成。邊框和畫面,更是鑲嵌了無數菱形或水滴形的綠松石、紅寶石……
對比起來,東漢大墓的壁畫是平面的,西漢大墓的帶扣是立體的。壁畫是藝術,十龍帶扣是工藝。壁畫上的墓主,自非等閑之輩,然而系十龍帶扣的墓主,已不能用非等閑之輩來稱呼,而應該以顯赫和神秘來命名。總之,買得起愛馬仕和LV腰帶的人有可能是土豪,把金龍戴在腰上的人只能是皇親顯貴。
也是,西漢之初,遼東曾是皇子劉建的封地。劉氏子孫曾在遼東做了63年燕王,除了燕王家的人,有誰敢以龍為飾,而且是那么多的龍呢?
其實,營城子已經挖掘出來的漢墓,只是冰山一角,還有數不清的墓仍在營城子地下。
想當年,在漢武帝一聲號令下蜂擁而至的那些實邊遷民,有的是獨自前來,有的是舉家或舉族而來,有的是傾邑或傾城而來。來了之后,就世世代代定居于此。
有生就有死,按照中原傳統,聚族而居的每一家每一族,都會有一片屬于本家本族的墓地。于是,墓與墓皆以血緣為紐帶,家人越多,家族越大,墓地也就越廣。而那些成片的墓,成組的墓,則在說明,那里面埋的是在不同時間、不同年齡消逝的生命,那些生命從生到死,從未離開這個半島。
就是說,人煙的背后是墓地,墓地的背后是人煙。只不過,當漢代走到了最后,屬于漢代的人煙和墓地,也一起作了告別。今天的人,只能從墓里的奢華或簡素,去想象地上的豐盈或閑適。
而且,怎么想象,都不過分。
四、管王之地
本土名士松齋先生曾作《大連賦》,在一段綿密的句子里,不但寫到了許多人,也寫到了許多事。賦曰:
漢武設沓文而人煙麕集,公孫自封侯而賢士紛登。棲止于三山兮,邴原避難;始發于沓津兮,管寧北征。
邴原避難,管寧北征,說的是同一件事,在漢代大連,可謂一件文化盛事,它所產生的影響,超出了大連,遠播整個中原。
此事發生在東漢末年。平庸而可憐的漢獻帝成了個擺設,天下已成三國四方之勢,魏蜀吳三分中原,另外一分在遼東。
彼時,中原戰亂不止,唯有公孫度治下的遼東獨得安寧,于是燕、齊流民紛紛逃向遼東,齊魯名士管寧、王烈、邴原、劉政、太史慈等,也夾雜在熙攘的人群中。
管王,既指管寧和王烈,亦指一眾齊魯名士。他們是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人人都是管王。管王們在將軍山下的沓津上岸,避亂棲身處也是半島南部鄉野,大連因此有了一個別稱:管王之地。
齊魯名士是一組群像。在他們當中,管寧無疑是一號人物。
他有兩個特點:一是人長得帥,身高八尺,且留美髯;二是出身高貴,管仲九世孫,政商細胞卻未繼承分毫,一生甘當隱士。
遼東侯公孫度自詡愛才,曾對管寧多次以官相誘,管寧一概婉拒,獨自在山谷間結草廬而居。彼時,赴遼避亂者眾,得知管寧住處,悉來與他為鄰,主要是想當他的學生。如此,一方僻壤,蔚為村屯。
管寧隱居遼東的日常所為,寫在《三國志·管寧傳》里:
寧往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為廬,鑿壞為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
中國文人也是有福,入世有孔孟,出世有老莊,出與處、仕與隱,全看自己要什么。以至于,大隱于朝,中隱于市,小隱于野,成了中國文人安身立命的三種方式。
大隱最難,西漢有東方朔,魏晉有七賢,只不過前者游刃有余,后者未得善終。
中隱最安全,帶頭大哥是白居易。安史之亂,令唐代文人心灰意懶,白居易一邊在朝里掛職上班,一邊在市井弄園池侍花草,求個魚和熊掌兼得。
小隱最徹底,比如管寧,青壯來,白首歸,隱于遼東之野三十七年。
有人說,三國無圣賢,管寧稱大儒。王夫之和錢穆卻說,三國隱士,管寧是第一人。我自認為,后者對管寧的評價更公道,也更準確。中國不乏大儒,真正的隱士卻并不多見。
正因為如此,我為半島山水倍感自豪,這里曾是三國第一隱士的天堂。雖然不知道管寧所在的山、所居的廬,究竟在哪片溝谷,哪條河邊,但我可以肯定,他在這里過得很自在,否則不會隱了那么久。
可以想象,尋常日子,送走了門徒學生,放下了詩經論語,他便走出灑滿陽光的柴門小院,去看天上的云煙萬狀,去聽樹上的雀鳥百囀。內心的無限快意,便是有幸遠離并拒絕了兩種黑暗,一是戰亂,二是官場。
據記載,管寧出走遼東,令曹操十分不解,忍著滿肚子不高興,給管寧下了個征召令,請他回去做官。只是這個令被公孫度兒子公孫康給截獲了,管寧并沒有看到,但以管寧的脾氣,即使看到了,也不會聽招呼。
有意思的是,公孫康當上遼東太守之后,本想讓管寧輔佐自己,卻終究不敢開口,可見在管寧的高傲里,藏著多么具有殺傷力的高冷。《三國志·魏書》裴松之注引《傅子》:
度庶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為號,而內實有王心,卑己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
管寧如此不近人情,卻享受著公孫氏三世不變的尊崇。公孫氏們也夠執著,給官不做,那就饋贈金銀布帛。管寧自是不改清白,返回故里時,特地叫來一個可靠的人,讓他幫忙把那些饋贈如數奉還給原主。
來時還是東漢,歸時已是曹魏。第一代魏主曹丕學他老爹,力邀管寧入朝。同門好友華歆已做到三公,也幾次推薦管寧,甚至愿將自己的太尉之職讓給他。
管寧素看不起華歆,“割席之交”這個成語,就來自他們年輕時的一次翻臉。即使回到故里,管寧仍做他的隱土,任你是曹丕還是華歆,誰的面子都不給。
之后,太尉華歆故去,太仆桓范接著寫《薦管寧表》《與管寧書》。管寧也只是出于禮貌,回書致謝,堅不出仕。
第二代魏主曹叡向先帝曹丕學習,曾寫一篇《征管寧詔》,為了說動他,不惜甩出各種肉麻大詞:
太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
出于對魏主的尊重,管寧連著寫了《辭辟別駕文》《致明帝疏》。然后,“以禮發遣,寧復不至”。
241年,直到管寧生命最后時日,太仆陶丘一和中書侍郎王基還不死心,又向第三代魏主曹芳奉上《薦管寧書》。當朝臣以詔令行事,“安車蒲輪,束帛加璽”之禮來聘時,管寧剛剛在家里去世,享年84歲。
管寧隱居遼東的日常和裝束,曾被《三國志·管寧傳》用15個字畫出一幅素描:
學行皆高,避亂遼東,常著皂帽,布襦袴。
管寧戴皂帽,與曹操有關。他三番兩次派人來請管寧回去做官,甚至還派來了便衣武士,以死相逼。管寧故意設計了一款與眾不同的高帽,然后找人幫忙制作。管寧本來就個子高大,頭上又戴一頂高帽,使命在身的便衣武士,只好惶然退去。
就是說,管寧的皂帽,其實是高帽。直到現在,高帽這個詞還常會被用到,卻極少有人知道,始作俑者是管寧。
杜甫《嚴中丞枉駕見過》詩云:
扁舟不獨如張翰,白帽還應似管寧。
劉克莊《題張元德著作春秋解二首》詩云:
笑我赭衣鉗楚市,愧君白帽老遼東。
皂為白,管寧戴的皂帽卻是黑。唐宋兩位大粉絲竟統一口徑,把黑說成了白。或許認為,白帽清高拔俗,與管寧這個人更搭。
一字不差的“遼東帽”,最早出自元代文天祥的《正氣歌》:
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
我想,文天祥一定讀過杜甫,讀過劉克莊,但他偏不說白,而說冰雪。管寧的遼東帽,更加有了不可企及的美。而且從文天祥的《正氣歌》開始,遼東帽就是管寧,管寧就是遼東帽。
遼東帽,自此成典。不但成了管寧個人的標識,也成了中國文人和隱士的代稱。
王烈比管寧大17歲。也許因為,齊魯名士群里,管寧最堅執,王烈最年長,故以“管王”并稱。
魏書和后漢書,齊魯諸名士幾乎都有個人傳略。《三國志·王烈傳》載:
王烈通識達道,秉義不回。以穎川陳太丘為師,二子為友。時穎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陳君學,見烈器業過人,嘆服所履,亦與相親。由是英名著于海內。
傳記內容很多,或許見古人如此不吝贊美,網絡百科也給了他一個很高蹈的標簽:三國風云人物。王烈要是活著,說不定要生氣了。
其實,王烈與管寧,三觀一致,學富五車,卻淡名利,遠官場,隱林泉,既是儒家信徒,亦有道家風骨。自避難遼東,日日是好日,與南山朝暮,與東籬朝暮,與園蔬朝暮,與村鄰朝暮,與詩書朝暮,讓自己真正活成了君子。
《三國志·王烈傳》載:
會董卓作亂,避地遼東,躬秉農器,編于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樂,東域之人,奉之若君。
畢竟與西漢朝暮了那么多年,與東漢也朝暮了那么多年,遼東先民還是有眼光的,也是知倫理的,對來此避亂的齊魯名士給了足夠的尊重。而且,如公孫度這樣的狂人,在王烈面前也表現得相當謙遜。《后漢書·王烈傳》載:
接以昆弟之禮,訪酬政事。欲以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穢,得免。
公孫度自己是個野心家,想不到,被他另眼相看的王烈為了找個拒官的托辭,竟不惜以商人自污,只好隨他的意。
曹操給管寧封官,也抓王烈不放,“聞烈高名”,便對其各種騷擾。王烈跟管寧一樣,說破了嘴,亦“屢征不至”。
《后漢書·王烈傳》載:
使遼東強不凌弱,眾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王烈全部心思,都在學問和操行,在教人易俗。所謂春風如貴客,一到便繁華,說的就是他和這群齊魯名士了。
218年,王烈病歿于遼南,終年78歲。本是齊魯名士,卻被后人稱為“遼東名士”。也許因為,別的名士大都相繼歸里,只有他把遼東當成了首丘之地吧?
在管王之后,最有談資的一個人是邴原。
他與管寧同鄉,籍屬北海郡朱墟。風華正茂時,曾與管寧、華歆友善,三人合稱“一龍”,華歆是龍頭,邴原是龍腹,管寧是龍尾。后來人各有志,龍頭去了官場,龍腹和龍尾,結伴共赴遼東。《三國志·邴原傳》載:
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
公孫度對名士的開明和大度,給出的條件和待遇,放到現在也是鳳毛麟角。邴原也不含糊,你投之以桃,我報之以李。在《大連地區歷代詩文一覽表》里,收有東漢末年流傳的一首民謠,作者佚名,題目是《遼東里老誦邴原》,錄自現存的《古謠諺》:
邴君行仁,居邑無虎。邴君行廉,路樹成社。
在大連,這是迄今所見最早記入史書的民謠,也是最早的分行文字。足見管王們在遼東設塾教課,已經初見成果,有人都可以寫出這么有文字功夫的歌謠,而且是給知識分子唱贊歌。
不知民謠在前,還是《三國志·邴原傳》在前。注引《邴原別傳》載:
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系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系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己而成淫祀,乃辯之,于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供。
原之邑落在大連,他在大連的名氣,有點像現在的網紅。當然,他原本就很紅,在故里北海也有許多鐵粉,而且他走到哪里,他們就跟到哪里。說是避亂,其實日子過得并不寂寞:
一年中往返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
然而,當中原趨于安定,見名士們多回原籍,邴原也動搖了:
后原欲歸故里,止于三山。
三山,今指大連灣出口處的三山島,漢代泛指大連。西漢見稱三山浦,樓船將軍楊仆曾在這里儲置軍械。東漢稱三山,應是三山浦另一個叫法。當年齊魯名士們的隱居之所,三山是唯一有確切記載的地名。
邴原止于三山,與孔融有關。孔融是東漢著名文學家,邴原避亂遼東,兩人之間常有書信交流。因為中原仍在斗亂中,孔融勸邴原不要回去:
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棋弈爭梟。
邴原真就聽了孔融的勸,“積十馀年,后乃遁還”。只能說,邴原是名士,但不是隱士,他來遼東,只為避亂。
離開三山,命運就此改變。曹操立即召邴原入幕,讓他給兒子們當老師。邴原顯然是后悔了,厭倦了,那么豪爽的一個人,竟至郁郁寡歡。時過不久,曹操征討孫權,邴原隨軍出發,居然病歿于途中。
邴原離開三山的時候,不知是否征求過管寧的意見,只知管寧仍守在這里。而且,邴原死了,曹操還在。管寧去世時,魏主是曹操的曾孫。看起來,還是隱者壽。
歷史就是這么吊詭,成也公孫氏,敗也公孫氏。
管王之地本是公孫氏成就的好事,且給公孫氏貼足了金,然而管王之地最后的悲劇,竟也由公孫氏一手造成。
管寧是最后一個離開遼東的。彼時,公孫度長子、第二代遼東侯公孫康已死,由其弟公孫恭嗣位。公孫恭有隱疾,不能生育,身體虛到不能問政。公孫淵是公孫康兒子,有躍躍奪位之勢。管寧認為,這里已非凈土,如果叔侄爭權,遼東禍亂必起。于是打點行裝,以魏主又有詔書為由,辭別了公孫氏。
果不出管寧所料,公孫淵踢開叔叔公孫恭,把個好端端的遼東葬送了。他一會兒投吳拒魏,一會兒附魏叛吳,最后徹底惹怒了第二代魏主曹叡。237年,曹叡派幽州刺史毌丘儉率兵屯駐遼東邊界,再以璽書征公孫淵入朝。公孫淵知道是計,遂與魏決裂,兩軍戰于遼遂,也就是今天的海城。因連遇大雨,魏軍失利而返。
238年,曹叡又派太尉司馬懿率四萬大軍再征遼東,雖又遇大雨,魏將紛紛要求遷營避水,太尉司馬懿卻號令三軍:敢有言徙者斬!于是,魏軍一直追到太子河,公孫淵及兒子公孫修悉被司馬懿誅殺。襄平既破,司馬懿遂掠人口三十萬,收樂浪、帶方二郡,將遼東之境盡收魏國。
此前,公孫淵“聞魏人將討,復稱臣于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主孫權居然不計前嫌,派將出兵,走海路北上馳援。然而,吳軍在沓津登岸后,聞公孫淵父子已死,襄平城已破,七千守軍正棄城向文、沓兩縣退卻。吳軍終于醒過神來,自知不是司馬懿對手,卻也不能吃虧,退兵登船之前,擄無數沓氏縣男女青壯,走海路南還。
文、沓兩縣,人去地空。239年,遼東已收歸魏國,將文縣改稱“汶縣”,將沓氏縣改稱“東沓縣”,縣治遷至黃海岸的青云河口。
240年,鑒于僥幸逃生的大連百姓“渡海居齊郡界”,魏國又在齊郡設“新汶”、“南豐”兩縣,以安置文縣籍居民;在淄川設“新沓”,以安置沓氏籍居民。
《三國郡縣表附考證》載:
魏以齊郡立有新沓,故于遼東之沓加東以別之。
遠在齊桓公時代,曾將大批齊國居民移徙遼東半島,想不到900多年后,齊人后裔又以這樣的方式反蹤故里。因此,魏國稱新沓縣治所“故縱城”,齊郡父老則稱“反蹤城”。
新沓縣舊址,在今天的淄博市淄川區羅村鎮,只有一座古城門,一截與城門相連的土城墻。據淄川縣志記載,魏國當局不但為沓氏難民另置一縣,還讓沓氏官員主掌之。在那樣的亂世,也是少有的一縷溫情。
上一次是秦滅燕,這一次是魏滅公孫,都是兵燹之毀。浸潤了幾十年的管王之地,從此風華不再,再陷蠻荒。積聚了300多年的文、沓兩縣,更是一地雞毛,七零八落。
仿佛是一種宿命,上自戰國,下至明清,不論是改朝換代,還是兩軍相爭,大連一直是兵家必爭之地,一直在相似的輪回里周而復始。于是,好不容易播撒下去的種子,一場硝煙過后,即成一片焦土。后世復后世,只能無助且無奈地,在一次次毀掉之后,再一次次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