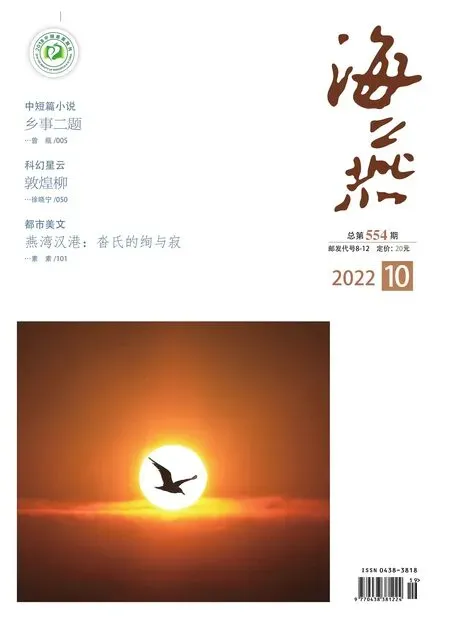敦煌柳
文 徐曉寧

楔子
高仙芝雙手捧著長劍橫置于地,鄭重地系好冠纓,他已決心以死明志,只是對于這位曾經(jīng)閃擊小勃律國、威震西域的悍將來說,被誣陷而死,是不是比下地獄還痛苦?
太監(jiān)邊令誠帶著玄宗皇帝的敕書而來,斥責(zé)他和封常清放棄了陜郡幾百里地,偷偷克扣士兵的糧食和賞賜。而真相是,安祿山叛軍迫近時,高仙芝為鼓舞士氣、不讓庫藏落入叛軍之手,急忙打開太原倉,把庫中的繒布全部分賜給將士,率兵向潼關(guān)方面撤退。
高仙芝望著邊令誠帶來的一百名陌刀手,看來不奉詔自裁,便會被亂刀分尸。他回想起《史記》里趙高偽造詔書命令公子扶蘇和大將軍蒙恬自裁的事,沒想到近千年前的事情會發(fā)生在自己和封常清身上,高仙芝顫抖著雙唇說道:“我退兵是有罪,死罪我不敢否認(rèn)。但認(rèn)為我偷偷克扣賞賜和軍糧,這是誣蔑。上有皇天、下有后土,兵將都在這里,您難道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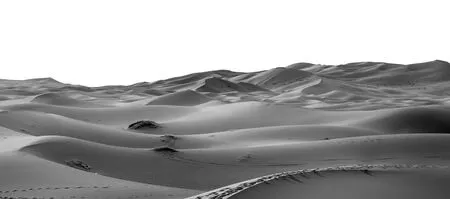
邊令誠只是呵斥他速速赴死,高仙芝又回頭對部下說:“我把你們招募來,當(dāng)然是想打敗叛軍多得重賞,但叛軍鋒芒正盛,所以撤退到潼關(guān)據(jù)守。我如有罪,你們盡可揭發(fā),如果無辜,你們就喊冤枉。”
全軍喊聲動地:“冤枉!”
縱然群議洶洶,邊令誠有唐玄宗的敕書在,高仙芝只能自裁,冰冷的劍刃橫在頸上,頸動脈突突直跳。生死之間,一個念頭不知從何而起:如果柳寧在,是不是另一種局面?
旋即,高仙芝問自己:柳寧是誰?記憶里怎么會有這個名字?
一
時值春末夏初,監(jiān)軍太監(jiān)邊令誠在大泉河碼頭攜男寵尹淼之手,正要登上樓船暢游一番,郁郁蔥蔥的小丘如屏風(fēng)遮住這游船碼頭。忽聞大泉河中流響起“隆隆”聲,狹長的快艇拖著一線黑煙疾馳而來,猛火油氣缸推動兩側(cè)明輪激蕩起白浪,紅色、黑色、碧色的抽象紋樣布滿船身,白色撞角凸起于船首,讓人想起代表司法的獨角獸“獬豸”。
快艇一個漂移動作將邊令誠的樓船卡在碼頭內(nèi)側(cè),水葫蘆濺了岸上人一身。駕船者將黑水晶磨制的風(fēng)鏡往額上一推,犀利的目光掃向岸上諸人,突然猱身而上摁倒尹淼,十字弩抵住尹淼的后腦勺,厲聲喝道:“吾乃敦煌校尉高仙芝是也,以‘干涉官員任免’之罪將汝逮捕,汝有權(quán)保持緘默,汝之言辭將成為呈堂證供。”
尹淼嗚嗚地道:“監(jiān)門將軍救我!”
“小小校尉竟敢在我跟前抓人。”邊令誠手一揮,十來個侍衛(wèi)抽出環(huán)首刀包圍過來。高仙芝抽出一支黃銅小筒、扣動底部的機(jī)簧,一道紅焰拖著尖銳的尾音沖天而起,半空中綻開明晃晃的焰火。
侍衛(wèi)們俱是一怔,只聽邊令誠冷笑道:“周圍都是山,等你的同伙到來,你早就沉到河底喂魚了。”
侍衛(wèi)們十來把利刃就要往高仙芝身上招呼。一片巨大的陰影倏然將眾人籠罩,侍衛(wèi)們抬頭一看,碩大的熱氣球蹭著蒼郁的小丘飛來,六聯(lián)裝火藥弓弩對準(zhǔn)他們,點燃的火繩劈啪作響。邊令誠只能眼睜睜看著尹淼被高仙芝拖上快艇,銬在氣缸邊上。
燃燒的猛火油鼓蕩蒸汽、催動活塞,高仙芝飛快地從二擋掛到五擋,明輪槳片卷起白浪,快艇將咬牙切齒的監(jiān)門將軍拋在身后。
冷汗把尹淼臉上的脂粉沖出幾道小溝:“我暈船,想吐。”
高仙芝冷冷地說:“吐河里罰款五百貫,吐船上就把你扔下去。”
尹淼的腮幫子如倉鼠般鼓起,臉都綠了。
二
將尹淼押進(jìn)敦煌府衙,案卷已移交,尹淼依仗監(jiān)門將軍寵幸而賣官鬻爵、干涉訴訟的案子即將提交皇帝案頭。高仙芝躺在快艇放平的椅子上,湛藍(lán)的天穹在峽谷頂端滑動。
比起擔(dān)心監(jiān)門將軍的報復(fù),他更擔(dān)心另外一件事,最近經(jīng)常夢到另外一個世界,那里沒有猛火油驅(qū)動的快艇,沒有絲綢和牛皮縫制的雙層熱氣球,木船大多靠風(fēng)帆驅(qū)動。年輕時,他二十來歲便當(dāng)上專管敦煌治安的校尉;可后來的三十年里,他追隨安西節(jié)度使四處征伐,甚至自己率領(lǐng)軍隊閃擊小勃律國,威震西域,只可惜最后死于監(jiān)軍太監(jiān)邊令誠之手。不過自己才二十多歲,怎么會有后面三十年的記憶?
那個世界的人寬袍大袖,常用武器是弓箭和彎刀,給帆船命名是“春明”“金池”之類。哪像他,看到百牛之力的氣缸想起“特(巨牛)”字,巡弋長河、逝者如斯取個“斯”字,再加上腦海里不知哪里冒出來的“拉風(fēng)”二字,高仙芝將自己的快艇命名為——特斯拉。
看著船頭自己用暗金漆草書的“特斯拉”三個大字,他靈光一閃:“逝者如斯夫,流逝的不光有大江大河,還有時光,時光也像這大河般有源頭、有支流、奔流入海嗎?”
夢境中的另一個自己嚴(yán)峻刻直,不像現(xiàn)在灑脫不羈,但一樣執(zhí)法嚴(yán)明不避權(quán)貴。夢中那人和他一樣對西域山川地勢表現(xiàn)出極大的興趣,他倒是很佩服另一個自己駕駱駝橫穿沙漠、徒步跋涉于雪山高原的毅力。而“現(xiàn)實”中的他駕駛快艇穿梭于各條河道,也曾于熱氣球上俯瞰山川,比單純騎馬駕車暢快多了。
不過令他有些嫉妒的是,夢中的另一個高仙芝非但坐上河西節(jié)度使、安西四鎮(zhèn)節(jié)度使的高位,還娶妻生子,不像自己現(xiàn)在孤單一人。
不,若是柳寧在,怎會孤單一人?
他想起幾個月前的那個燃燈節(jié),夜的帷幕還未完全落下,莫高窟每一個洞窟內(nèi)點燃燈輪,供奉在佛祖面前。有的燈輪高約一丈,七層輪盤上放置近百盞燈,宛如花樹盛放、灼灼其華。
高仙芝在月牙湖隔岸遠(yuǎn)眺,燈影鋪滿大泉河,猶如懸在河川里的星河,一川星懸。整座莫高窟恍若龐大的夜航船,每個窗口閃爍著燈火,在夜晚的沙海里,載著無數(shù)人的夢想,駛向極樂凈土的彼岸。
半夜他游興不減,獨自攜酒來到月牙湖旁邊的亭子,月上中天,月光將那亭子染上一層輕薄的白釉,他總覺得此處恍如前生的故地,似是夢境中游歷江河的一站。綠柳搖擺著枝葉,夜晚的神靈在絲絳間輪舞,兩岸垂柳有多高探入月光,就有多深映入湖中。亭中已有一人,倚在亭柱上,高仙芝只看到她窈窕的背影。
她聽到腳步聲,轉(zhuǎn)過身子,靈動的眼眸注視著他,挺秀的鼻梁以下被面紗遮住。不知為何,高仙芝感到那目光無比熟悉。女孩也在觀察他,高仙芝左額一簇白發(fā),從左額角梳進(jìn)發(fā)髻,如黛石上一道殘雪。常在大泉河上駕著特斯拉穿梭,幾度寒暑帶給他小麥色皮膚,唯有一笑之際牙齒極白,這是常用青鹽清潔之故。
親自面對本人與置身事外觀測終究不同,女孩忍不住道:“你竟然變成了這副樣子……”
“我一直是這副樣子啊。月牙湖夜景雖美,沒有酒總是少了什么。”
“恰好你帶著酒?”
高仙芝掏出兩個扁酒瓶,遞給女孩一個,笑問:“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女孩沒有摘下面紗的意思,卻將扁酒瓶捧在手里,她的雙眸閃過狡黠:“我叫‘柳寧’,‘垂柳’的‘柳’,‘寧靜’的‘寧’。”
潺潺微波倒映著兩人的身影,雖然與柳寧素昧平生,不過高仙芝感到與她極為投緣,柳寧知道他當(dāng)敦煌校尉,問他最近有什么見聞。
高仙芝遙指遠(yuǎn)處燈火通明的洞窟:“燃燈節(jié)前,《西方凈土變》壁畫上反彈琵琶的‘伎樂天女’天衣飛揚、滿壁風(fēng)動,驚艷眾人。人人都說‘畫天女如宮娃’,可他們并不知道背后的故事。”
“哦,什么故事?”
“有位多情的畫師在酒肆中邂逅一位舞姬,為她學(xué)自長安教坊的舞技而震撼,為她反彈琵琶的身姿而傾倒。舞姬則被畫師的作品吸引,兩情相悅。可惜畫師收入微薄、無法為她贖身,也沒權(quán)勢保護(hù)她不被惡霸騷擾。舞姬不想再受酒肆老板的虐待,只能跟著胡商去了龜茲國。畫師的思念綿綿不絕,只能把戀人最美的身影,一筆一筆描摹在莫高窟的石壁上。”
柳寧悠悠地說:“我在街市上見過那位舞姬,容貌未必是天姿國色,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畫師在腦海里印下她的舞姿,又把這思念留在壁畫中。也許在另一個世界,鐘情于她的畫師有積蓄為她贖身,舞姬嫁人生子,過起了平常人的生活。”
“很有意思,你說的‘另一個世界’是佛經(jīng)中的‘六界輪回’哪一界?”
“只是我的幻想而已。”柳寧有意岔開這話題,“還有什么見聞?”
……
兩人一直聊到更深露重之時,柳寧坐到石桌旁,高仙芝隱約看到她左邊鎖骨上一道傷痕,縱使他將目光飛快地移開,柳寧還是覺察到了,淡淡地說:“商旅跋涉,劫匪四起,難免被卷入其中。”
隔著面紗看不出悲喜,高仙芝暗罵自己遲鈍:或許她不幸在逆旅中臉有微瑕,比鎖骨上的傷痕更嚴(yán)重,不得不以面紗遮面。高仙芝不想引起她更多難受,正想說點別的,只見柳寧站起身:“我在這里太久了,該回去了。”
高仙芝霍地起身:“太晚了,我送你回去。”
“不必了,以后或許還會再見。”
高仙芝正琢磨她模棱兩可的話,柳寧拈出一粒小東西放在他手中。
攤開手掌,掌心有一粒朱紅色緊致果實,高仙芝暗忖:莫非這是她所在世界的紅豆?他用溫厚而有磁性的聲音說:“我會把這粒紅豆刻進(jìn)牛骨骰子,刻骨相思……”
“哦,這個不是紅豆,這個叫做‘枸杞’。”月光在她瞳仁中閃爍,高仙芝被那眼波吸引,情不自禁地顫抖著手指探向面紗。
女孩急忙捉住他的手:“不要摘去這面紗,一旦摘去,你會從這世界脫離,之前……”
柳寧幾次欲言又止,高仙芝心里煩躁,但只要看到面紗之上那雙眼睛,總有萬般柔情將煩躁與不忿融化于無形。
在過去的幾個月,柳寧和他相約在月牙湖碰面,而且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柳寧換過好幾套衣服,胡服漢服都有,面紗換過許多樣式,從夏天薄如蟬翼的絲綢到冬天的提花錦緞都有,柳寧的眉眼鐫刻在他記憶中,他卻始終不知曉鼻梁以下的面容。
枸杞過去幾個月仍未枯萎、仍未褪色,尋常果實不會如此,高仙芝開始懷疑,他所在的世界是不是一直在柳寧注視之下。
若要算出柳寧的來歷,恐怕要找這個時代最擅長推演術(shù)的人了,“特斯拉”的猛火油發(fā)動機(jī)就是他設(shè)計的。
三
“永不朽壞的枸杞?”
寬額頭的老者摘下右眼的單鏡片,換上兩片用微型框架拉開一定距離的鏡片,不斷轉(zhuǎn)動眼鏡框上的旋鈕,調(diào)節(jié)焦距,枸杞的紋理在目鏡中愈發(fā)清晰。老者瞇起左眼、右眼圓睜看了一陣,拿起枸杞轉(zhuǎn)身就跑。
“喂喂,一行先生,你去哪里?”
“跟我來!”
陽光最好的地方有一臺古怪的儀器,半弧架子懸著銅制圓筒,圓筒下端的鏡片正對一小方臺,一行先生將枸杞置于小方臺上,小心翼翼地固定,瞇起左眼、右眼貼著圓筒上端的鏡片,手指微調(diào)圓筒腰部的旋鈕。高仙芝就這樣大氣也不敢喘地等他觀察了一刻鐘,一行先生從圓筒上端抬起頭,眨眨酸澀的眼睛,高仙芝急忙問:“看出什么來了?”
“這紋理太完美了,比普通枸杞完美多了,就好像有人曾經(jīng)將成千上萬顆枸杞展開數(shù)以億計的平面,選取其中最完美的紋理,造出這顆枸杞。”
“你是說,這是人造物?”
“是的,普通果物用藥物處理達(dá)不到這種效果。你從哪里得到這個孤品?”
“一行先生,能不能用你的機(jī)器算一下它的來歷?”高仙芝指指三座并立的方塔,它們的部件在陽光下反射著金屬光芒,齒輪、連桿、鋼絲、曲軸有序和諧地運轉(zhuǎn),運行的聲音在一行先生聽起來像是天籟。
“不行,那是我計算圓周率用的,算不出它的來歷。”一行先生把十幾粒烘焙豆傾入攪碎機(jī),轉(zhuǎn)動把手,黑褐色碎豆帶著焦香從黃銅敞口漏出。這和打孔牘片進(jìn)入差分機(jī),帶著數(shù)據(jù)出來有異曲同工之妙。他經(jīng)常用給差分機(jī)提供動力的鍋爐燒開水,給自己沖一杯“嘉蘇”,這種苦澀的飲料能提神醒腦。
“那么您能不能幫我個忙?”
“不行!”
“我還沒說幫什么忙……”
“你想讓我進(jìn)入朝廷安放在敦煌石窟的數(shù)據(jù)庫,幫你查找枸杞主人的來歷吧?”一行先生臉上浮現(xiàn)出揭破對方小心思的笑容,忽然看到他提折疊凳在手,拿杯子的手一晃,“嘉蘇”在白大褂上氤氳出一大片褐色。一行先生卻顧不上燙,臉色發(fā)白地擺擺手:“把你手里的折疊凳放下,別急著砸過來。聽我說,能制作出完美枸杞的人,會在官方數(shù)據(jù)庫里留下痕跡。而且以你敦煌校尉的權(quán)限,豈能找不到?”
高仙芝被他戳中痛處,“哐當(dāng)”一聲把折疊凳丟在地上,雙手攥住頭發(fā),臉龐埋在陰影中。一行先生走過去拍拍他的肩膀:“是不是一個女孩送你的?別這么看我,怪嚇人的,我就是隨口一說。”
眼睛里的火苗黯淡失色,高仙芝重新低下頭,十指再次和頭發(fā)較勁。一行先生長嘆一口氣,悠悠地說:“最近我一直試圖借助差分機(jī)建立關(guān)于世界運行的模型,我花費三年計算了日月以及金木水火土五星運行的軌跡,在那之后,我發(fā)現(xiàn)一件奇怪的事情。你猜是什么?”
高仙芝沒搭理他。
一行先生惱羞成怒,捏著他的臉頰轉(zhuǎn)向屋里摞到屋頂?shù)谋≈衿瑯拥挠卸噢恳晦數(shù)教旎ò澹科≈衿砻婵逃?024個點陣,有些鉆孔透過,有些沒有。
“刻錄第五版模型整整耗費了9012張牘片,在差分機(jī)運行的四個時辰里用掉的上等無煙煤,足夠二十戶人家用一個月。第五版模型在差分機(jī)里只運行了一次,差點將那寶貝機(jī)器燒了。幸而數(shù)據(jù)保存下來,幸而我推導(dǎo)出結(jié)論,你猜是什么?”
高仙芝茫然地望著近在咫尺的一行先生,不過那眼神仿佛轉(zhuǎn)了彎,鎖定著一行先生身后的枸杞。
“我們的世界是被設(shè)計的。”一行先生那雙深陷皺紋中的眼睛閃著光,“圓周率本應(yīng)是無限不循環(huán)小數(shù),但是差分機(jī)只能運算到小數(shù)點之后十七位,這并非我這臺機(jī)器運算的極限,算到小數(shù)點之后二十位理論上不成問題。然而無論我如何改進(jìn)硬件或是程序,圓周率最多算到小數(shù)點之后十七位,這說明‘那個人’認(rèn)為十七位圓周率足以支撐整個世界運轉(zhuǎn)了。”
“哪個人?”
“創(chuàng)造世界的人。”一行先生揚起厚厚的筆記本,嘩嘩翻著:“還有很多證據(jù),你看日月星辰的運行太過有規(guī)律,‘歲差’(每年地球繞太陽運行一周,不會完全回到上一年的冬至點上,總要相差一個微小距離,大約每年相差50秒)為五十息,‘交點月’(月亮相繼兩次通過黃道、白道的同一交點的時間)為二十七日,諸如此類還有很多,為什么這些數(shù)據(jù)背后的物理常數(shù)都是整數(shù)?是因為創(chuàng)世者太懶,還是他認(rèn)為這些整數(shù)足以支撐起日月星辰的運行?”
高仙芝低聲道:“‘他’?為什么不能是‘她’?”
“你說什么?”
高仙芝難以用語言表達(dá)自己的想法,只能指向差分機(jī)。
“對啊,我怎么沒想到!”一行先生激動地雙手揮舞,“差分機(jī)的運算量是有限的,創(chuàng)世者的‘差分機(jī)’雖然不知道比我這臺寶貝高到哪里去,但運算量是有限的——只能去繁就簡,把無限不循環(huán)小數(shù)取有限位數(shù),把日月星辰運行的規(guī)律去蕪存菁,才能最大限度地留出運算的空間,保證這世界的多姿多彩。高仙芝,你怎么不早來?”
身后無人應(yīng)答,一行先生回頭一看,高仙芝已經(jīng)消失了,一同消失的還有那顆枸杞。
四
特斯拉號在水道上飛馳,高仙芝計劃去月牙湖,下一個月圓之時是與柳寧約定再見的日子。
一行的一番宏論醍醐灌頂,令他想清楚之前的一些事。
如果自己所處的世界是被設(shè)計好的,那么夢境中逼真的世界呢?難道那才是真實的世界?難道自己的真實命運是和素未謀面的封常清一起死于邊令誠之手?
究竟哪個世界的創(chuàng)世者更有黑色幽默感?是那個世界的他,還是這個世界的“她”?高仙芝攥緊那顆紅得灼人的枸杞,萬千思緒灌入腦海,他的目光一會兒狂躁無比,一會兒平靜異常,一會兒明亮如炬,一會兒陰沉如磷火。
停舟換馬,馬蹄在青石板上敲出急促的“嘚嘚”聲,林蔭道兩旁的樹木紛紛向身后倒去,只有搖曳的樹影在他身上不斷劃過。快到了,月牙湖亭子在望,然而亭中沒有熟悉的窈窕身影,只有一支斷裂的短笛留在亭心,亭柱上刻著幾個劍拔弩張的大字——“想見她,來監(jiān)門將軍府”。
手指向湖中一舀,掬起一捧水,清涼的水珠順著指縫流溢而出。高仙芝定定神,清冽的觸感只在幻覺中。千百柳枝如女妖的長發(fā)亂舞,垂柳樹葉痙攣著沙沙作響,他的柳寧從指尖溜走,月光依舊,只是微涼。
五
白色沙洲,柔風(fēng)蹁躚,步搖的碧璽珠子在發(fā)髻上隨風(fēng)搖曳,柳寧一襲水色長裙,纖細(xì)的雙腳踩在細(xì)沙上。她的目光從波光瀲滟的月牙湖回到身前,水浪一來一去,來時為白皙的小腿套上蕩漾的濾鏡,去時留下濕漉漉的腳趾,清涼的觸感也如波浪一陣一陣涌來。
最近有預(yù)警說病毒在各個服務(wù)器間肆虐,柳寧進(jìn)入“敦煌”服務(wù)器之前檢查了幾遍防火墻,應(yīng)該不必?fù)?dān)心這個世界被入侵。她將朱紅色的短笛湊近唇邊,櫻唇雖與笛孔隔著面紗,旋律依然透過短笛流溢而出,這一段新編寫的小程序能給高仙芝帶來什么樣的驚喜?他會循著笛聲找到她嗎?
背后響起腳步聲,柳寧想靜靜地奏罷一曲,誰知兩只長爪如鐵鉗箍住她的雙臂,笛聲戛然而止,邊令誠在恨恨地瞪著她。柳寧低頭看去,邊令誠的手爪比常人長了三倍,而且如蜘蛛的節(jié)肢短刺叢生。
什么時候NPC能有這么大權(quán)限了?柳寧秀眉微蹙,指尖金砂般的一簇光射向邊令誠,若不是為了讓高仙芝感覺這個世界更逼真,她早就刪除這個存在。
沒想到邊令誠身子震了一震,手爪加勁,柳寧痛苦地呻吟一聲,她緊急調(diào)取最高權(quán)限強(qiáng)行抹殺,無數(shù)金色砂礫在邊令誠身上流淌,順著血管勾勒出樹葉筋脈般的圖案。他的身體表面出現(xiàn)雪花形狀的分型,層層疊疊,似乎被分解、銷蝕,但邊令誠又一絲一毫地強(qiáng)行恢復(fù)原狀,狹長的雙眼里滿含譏諷。
邊令誠動作起伏之間帶有紅白的重影,柳寧心里一驚:病毒終究入侵這個世界,以邊令誠為載體,病毒的權(quán)限在不斷擴(kuò)大,她的權(quán)限無法令他湮滅。
“有你在手,不愁殺不了那個家伙。今天就剝了這層皮,看看你究竟長什么樣子。”邊令誠拽住薄如煙霧的面紗向下一扯,面紗沒有動。他的五指如枯葉片片碎裂,又飛旋著聚合在一起恢復(fù)為五指形狀。他的眼前蹦出一組對話框,紅燈與警笛齊飛:“系統(tǒng)警告,冗余數(shù)據(jù)溢出。”
整個月牙湖和岸邊的垂柳劇烈震動,湖面漾起無數(shù)細(xì)碎的波紋,仿佛有人遠(yuǎn)遠(yuǎn)地掀動這綢緞,“邊令誠”驚恐地望著她,剛才差點令一部分世界坍塌,如果不謹(jǐn)慎行事,自己賴以棲身的服務(wù)器會崩潰。那是她在數(shù)據(jù)海洋上設(shè)置的長堤,邊令誠可不想和這世界一起被海嘯吞噬,只能悻悻地住手。
方才邊令誠短暫的受傷,暴露一小段源代碼,柳寧覺察到異常:“你來自‘暗網(wǎng)’,你究竟是誰?”
邊令誠冷笑一聲,白凈的面皮鉆出許多胡茬,扁平的鼻梁驟然拔高,瞇縫的雙眼變得眼窩深陷、眼珠灰藍(lán)。
“竟然是你?”柳寧望著他五官變形的臉,想起一個人來,那人是臭名昭著的文物獵人,打著“探險家”的名號招搖撞騙,掠奪亞洲諸國文物作為自己躋身上流社會的籌碼。
那人又恢復(fù)邊令誠的面孔:“跟我走吧,小姑娘。”
六
邊令誠緊閉府門,深溝高壘,將柳寧囚禁在監(jiān)門將軍府的花廳,自己在花廳前的小湖邊上飲酒。湖邊的屋子里滿是侍衛(wèi)親兵,埋伏窩弓射虎豹,撒下香餌釣金鰲。
高仙芝不過一人一騎而已,能翻起多大浪花?誰會冒著得罪監(jiān)軍太監(jiān)的風(fēng)險幫他?邊令誠正閉目假寐,忽然將軍府后面一陣騷動,他緩緩坐起,后門也布置許多衛(wèi)兵,強(qiáng)弓硬弩,說不定過一刻鐘,衛(wèi)兵會抬著高仙芝被射成刺猬的尸體來請賞。
騷動越來越大,巨大的陰影如烏云從后方籠罩而來,邊令誠抬頭一看,橄欖形狀的飛艇在螺旋槳推動下飛來,特斯拉號吊在飛艇下方,如流焰般熠熠生輝。
高仙芝一扳鐵閘,船體伸出兩扇蝙蝠般的滑翔翼,猛火油喚醒沉寂多日的氣缸,對稱的六排黃銅管放出白瀑般的蒸汽,特斯拉號從飛艇上脫離,憤怒的獬豸高昂獨角,嚎叫著向小湖俯沖而來。
白色撞角在邊令誠眼睛里越來越大,他發(fā)瘋般地大喊:“快放箭!快放箭!”
周圍屋子響起令人牙酸的弓弦繃緊聲和弩箭上弦聲,高仙芝雙手端著六聯(lián)裝轉(zhuǎn)筒弩,一扳唧筒,壓縮蒸汽驅(qū)動短矢“嗤嗤嗤”射出,轉(zhuǎn)著圈掃射,侍衛(wèi)親兵紛紛撲街。
隔著墨鏡,邊令誠都能感受到對方殺氣騰騰的目光。一支火藥箭帶著尖利的唿哨飛來,邊令誠急忙縮在酒桌后面,箭桿上的壓縮火藥忽地爆炸,將金絲楠木桌板炸開焦黑的破洞。
一點紅色閃爍在高仙芝脖子正中,那顆永不枯朽的枸杞被他用鉑金細(xì)鏈穿了,掛在頸前,高仙芝厲聲高喊:“邊令誠,今日必取你的首級!”
要釣金鰲卻來了條鯊魚,還是大白鯊,邊令誠趕緊去找“香餌”,高仙芝緊追著他來到花廳,一火藥箭扎進(jìn)邊令誠后背,高仙芝隨即抱住柳寧就地臥倒,一陣火光,轟鳴過后空氣中彌漫著烤肉味。
高仙芝扶起她,看到柳寧口唇在面紗下一張一翕,而他雙耳嗡嗡作響聽不清,自嘲道:“火藥裝填有點過頭,你在說什么?”
他將耳朵貼近,勉強(qiáng)辨聽出四個字——“他還活著”。
殘破的錦袍掛在炸出窟窿的身體上,邊令誠長發(fā)披散在肩頭,不斷伸長的十指如黑曜石般尖銳。他的嗓音變了:“你只不過是古代死人的殘響而已,再過一刻鐘,你不會留半點痕跡在這世上。”
柳寧疾呼:“當(dāng)心,他不再是邊令誠……”
“只是一堆數(shù)據(jù)而已,和差分機(jī)里運轉(zhuǎn)的二十摞打孔竹片沒區(qū)別。”高仙芝將柳寧護(hù)在身后,射出一箭。弩箭被邊令誠抓在掌中,箭桿兀自不停顫動。邊令誠一口吞掉弩箭,黑火藥爆炸的氣浪將他腦袋撐成球形:“怎么樣,怕了吧?”
高仙芝問柳寧:“你們那個世界的電腦病毒都這么可笑嗎?”
柳寧含嗔帶笑地說:“先把繩子給我解開。”
邊令誠怒道:“我要把你撕成碎片。”
高仙芝橫抱柳寧沖出花廳,將她放在特斯拉號上,他后心毫無遮護(hù),五根黑曜石般的手指從后面刺來。
隨著一聲巨響,螺旋形指尖再也無法穿透,鈦合金盾由兩組伸縮框架支撐,從高仙芝后背探出。
“一行先生那里除了差分機(jī),還有改造機(jī)器的精工車床。”高仙芝笑道,猛火油引擎將澎湃動力注入特斯拉號,數(shù)千個氣壓傳動裝置在鍍鉻合金外殼下運轉(zhuǎn),船舷流線型的金屬板折疊又展開,護(hù)住高仙芝的胸腹、四肢。
“一行可以用他的差分機(jī)改寫程序,特斯拉號機(jī)甲還不錯吧?”
兩注噴泉似的蒸汽從背部噴口激射而出,高仙芝舉起七尺長刀,向邊令誠撲去。兩人動作越來越快,血珠不時濺出圈子。
七
黑煙汩汩的特斯拉機(jī)甲翻倒在地,不時發(fā)出爆炸的悶響,高仙芝努力睜開被鮮血糊住的眼瞼,柳寧正艱難地將他從駕駛艙拖出來。
“邊令誠”半邊身體被火藥弩摧毀,身體的橫截面如風(fēng)中火焰翻卷不休。此刻他難以維系“邊令誠”的偽裝,高仙芝驚詫地望著對方從寬袍大袖、敷粉涂面的太監(jiān),變成頭戴盔形帽、穿著短風(fēng)衣的探險者。那人灰藍(lán)的眼睛與他對望,高仙芝感覺自己被饑餓的孤狼盯著:“你究竟是什么人?”
“鄙人斯坦因。”那人笑了,露出兩排看起來比常人多一些的牙齒:“‘敦煌’服務(wù)器的核心數(shù)據(jù)全部存儲在‘莫高窟’數(shù)據(jù)庫里,我很想作為私人收藏。可是如果揭下這小姑娘的面紗,這個小世界便會坍塌,我想試一試,用她的身體作為鑰匙,強(qiáng)行解碼數(shù)據(jù)庫。”
高仙芝不知道后世的事:“斯坦因?你是什么人?”
“他是來自‘暗網(wǎng)’的病毒,借助邊令誠的軀殼‘移魂’,不過他的秉性和兩百多年前的文物大盜如出一轍。”柳寧急忙將1907年斯坦因巧取豪奪藏經(jīng)洞內(nèi)二十四箱敦煌寫本、五箱絹畫和絲織品的罪行說了。高仙芝目眥欲裂、嘔出一大口鮮血,苦于身受重傷,無法再與斯坦因廝殺。
“接管‘敦煌’服務(wù)器之后,我可以以此為跳板,入侵更大的‘絲路’服務(wù)器。”斯坦因嘲弄地望著手足無措的柳寧和奄奄一息的高仙芝,大度地說:“作為一個有追求的電腦病毒,我可以讓你選擇自己的死法。”
柳寧正要說話,高仙芝示意她噤聲,寬厚的右手和她兩只手握在一起。高仙芝抬頭望向鬼魅般的斯坦因:“當(dāng)真能讓我實現(xiàn)我的死法?我不信。”
“你太小看我了。”斯坦因一指花廳之外,明明是春末夏初,寒風(fēng)卷地而來,絳紅暗紫的云靄沉浮升降,轉(zhuǎn)眼間飄起雪花。
斯坦因哂笑道:“我在逐漸接管‘敦煌’小世界,而你,將無足輕重。”
“你能不能以七尺長為半徑畫一個完美的圓形,讓我們倆葬在里面?”高仙芝在地面上劃出一道七尺長的直線,盯著躍躍欲試的斯坦因。柳寧聽高仙芝這么說,雙手緊緊攥住他滿是傷痕的右手,生怕下一秒就會消失。
“這有什么難度?”斯坦因探出比手術(shù)刀還鋒利的指尖,好整以暇地劃出弧線。柳寧不明白高仙芝的用意,緊張地望著在青石板上劃得吱吱作響的指尖,只要圓形合攏,斯坦因就要動手,不過能和高仙芝一起……
圓弧眼看就要嚴(yán)絲合縫,指尖被看不見的力量彈起,圓形消失了。斯坦因皺皺眉,精密計算一番,再次在地上畫弧,這次和上次一樣,就在圓形即將完成之際,消弭于無形。
“怎么回事?”斯坦因一次又一次將青石板劃得火星四濺,每次都是功虧一簣,咬牙切齒地說:“這不可能,怎么會這樣?”
柳寧將目光投向高仙芝,他輕撫她的長發(fā),壞笑著說:“這得感謝一行先生,他發(fā)現(xiàn)圓周率最多算到小數(shù)點之后17位,這個世界的圓周率是有限位的常數(shù),這說明‘創(chuàng)世者’認(rèn)為17位的圓周率足以支撐整個世界運轉(zhuǎn)了。然而真正的圓周率是無限不循環(huán)小數(shù)——換句話說,想在這個世界畫出完美的圓形,是不可能的!”
柳寧恍然大悟:“他已經(jīng)讓自己運行‘畫完美圓形’的指令,會陷入無窮遞歸之中。”
“請說點我能聽懂的。”
“他會因為陷入無法完成的進(jìn)程而自取滅亡。”
方才詭異的天象漸漸褪去,恢復(fù)一派春和景明,斯坦因望著地上永遠(yuǎn)無法合攏的圓形,一滴冷汗從額頭滴下。
八
蒸汽喧囂,明輪如天鵝雙翼激蕩起水花,留下無數(shù)閃躍的翠藍(lán)色,特斯拉號飛馳在大泉河上。柳寧憐惜地?fù)崦呦芍ド砩系膫冢瑥拇戏鲠t(yī)藥箱給他包扎。
高仙芝淡淡地說:“一行先生的差分機(jī)最初是為計算更加精確的圓周率,后來發(fā)現(xiàn)世界的運行規(guī)律……”
柳寧興奮地說:“是啊,這次多虧了他。”
“我自己演繹了一下,對其他事也能證實或者證偽。”
柳寧縫傷口的動作停滯了。
“我漸漸想清楚關(guān)于‘前世記憶’的緣由,與老搭檔封常清一起死于邊令誠之手。我猜,那才是本體的經(jīng)歷,我是他在這個世界的復(fù)制品——邊令誠也說過,我只是古代死人的殘響。”
“不要相信那個瘋子,你和我都在這里,這個世界無比真實……”
“柳寧,如果我沒猜錯,你為了避免這個世界坍塌,把支撐它運行的密鑰時刻不停地帶在身上,而且只有你自己才能解開。其他強(qiáng)大的存在或許能困住你,但不能解開那密鑰。”
柳寧下意識地雙手交叉遮在面紗上:“你什么時候確認(rèn)的?”
高仙芝平靜地說:“就在剛才。”
“不,你所猜想的無法證實,為什么我們要糾結(jié)于虛妄的爭論?”
“這里是你的小小私服,很美好,但也留下入侵‘敦煌’的缺口,還會有下一個斯坦因循著缺口入侵,為了敦煌,為了整個‘絲路’,我們得想個辦法。”
“我們剛剛逃出生天,今天先別說這些了。”她輕輕地說,“我可以滿足你一個愿望,任何事都可以。”
柳寧羞赧地看他一眼,過了許久,高仙芝故作輕松地說:“能讓我看看你的臉嗎?”
柳寧的瞳孔驟然收縮,急促的喘息令面紗起了漣漪,她緊盯住高仙芝,像盯著一個從未見過的陌生人。高仙芝雙手搭在舵盤上,平靜地望著她:“‘敦煌’保藏的數(shù)據(jù)資料,在‘暗網(wǎng)’那些家伙眼里是無盡的寶藏,不要給他們可乘之機(jī)。”
柳寧凄然一笑,一手將額前的斜劉海撥開,一手摘下面紗,那笑容是他從未見過的瀲滟波光。
高仙芝笑了:“你真美。”
柳寧攬住他,幾縷長發(fā)在額前飛舞。她感受到他的身軀如同化解為數(shù)萬只蝴蝶,碎片翩翩然消逝在風(fēng)里。柳寧咬著下唇,竭力不讓自己哭出聲。
兩行眼淚從高仙芝臉頰上滑落,最后一滴沒有軀體遮擋,飄在柳寧臉頰上,與她的眼淚混合在一起,甲板上只留一線鉑金細(xì)鏈,末端系著一點明紅。
柳寧將那顆永不朽壞的枸杞托在掌心,回想起那一天,她穿過時間的裂隙前往天寶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想在邊令誠逼迫高仙芝自殺之前,為拯救他做些什么。
她計劃在十五秒停滯的時間內(nèi)拷貝他的意識,然而十五秒終究太短,89%,91%,94%……無法全部拷貝高仙芝的意識,給不斷閃回的“前世記憶”留下隱患。
十五秒已到,所有人恢復(fù)動作。在時間的縫隙關(guān)閉之前,邊令誠拔刀向她劈來,刀刃在她左肩留下傷痕,生銹的刀刃和古代的細(xì)菌令她高燒三天。不過她還是苦撐著,將高仙芝的意識上傳到“敦煌”服務(wù)器中,她像一名細(xì)致的外科醫(yī)生,盡量剝離關(guān)于后三十年軍旅生涯與死亡的記憶,保留他擔(dān)任敦煌校尉的記憶,還保留他的性格元素:尋根究底、嫉惡如仇、寧折不彎……
在時空管理局眼中,她僅僅將古人的意識存儲進(jìn)“敦煌”服務(wù)器,歷史線沒有跑偏,而且沒有古人被帶回2121年,時空管理局縱然嚴(yán)酷,卻找不出對應(yīng)的法條懲罰她,此事不了了之。
高仙芝在“敦煌”服務(wù)器中如魚得水,一如他在歷史記載中的瀟灑不羈。然而服務(wù)器中的高仙芝意識尚不穩(wěn)定,剝離不盡的“前世”記憶仍然存在,在他于夢鄉(xiāng)流連時不斷閃回。
敏銳如他是否發(fā)現(xiàn)端倪?她決定“深潛”進(jìn)入服務(wù)器親自查看,她知道高仙芝必去的地點是莫高窟前面的月牙湖。
在此之前她設(shè)置了一道保險,一旦她深陷數(shù)據(jù)之海中難以脫身,可以通過密鑰使得虛擬世界湮滅,促使她強(qiáng)行脫離。但系統(tǒng)將那密鑰設(shè)置為面紗,這如煙似霧的面紗無人可以剝除,除非她自愿。柳寧感到啼笑皆非,莫非這是“主腦”有意橫亙在古人與今人之間的長堤?
初次在“敦煌”服務(wù)器見到高仙芝時,柳寧下意識地輕觸臉頰上方的面紗,暗自告誡自己無論他如何請求,也不能摘下。而高仙芝最后的請求,和保護(hù)“絲路”服務(wù)器而關(guān)閉敦煌入口的決絕,她無法拒絕。
面紗已經(jīng)摘去,敦煌的竦峙巖山變得像奶油般柔軟,莫高窟變得如云霧般縹緲,但江流猶自未竭,算盡這一生,終究夢里身是客。她再也無法見到高仙芝,沒有他的世界在逐漸崩塌,“主腦”強(qiáng)制她脫離虛擬世界。恍惚間,她感到冷風(fēng)颼颼地從另一個世界吹來,伴隨著蝕骨的寒意,將她的靈魂碎作齏粉……
尾聲
兩千年世間如紅塵走馬,舊憶幽深讀盡滄桑變化,塵寰已悄然興衰過手,恍然間此身已非我所有。
前世遺落的幻痛仍在,而這個世界無法讓我愈合。
在偵查邊令誠的老巢時,我找到柳寧被禁錮的地方,望了又望。我確信會救出柳寧,就像我已經(jīng)在另一個世界死亡一樣確信。
我可以枯萎,可以消散,怎樣都行,但我無法永遠(yuǎn)不去摘下你的面紗,我會記住你的面容。
此去經(jīng)年,每當(dāng)我與死神直面,或于地獄中殺上山巔,只要想起你面紗下的容顏,萬般柔情便涌上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