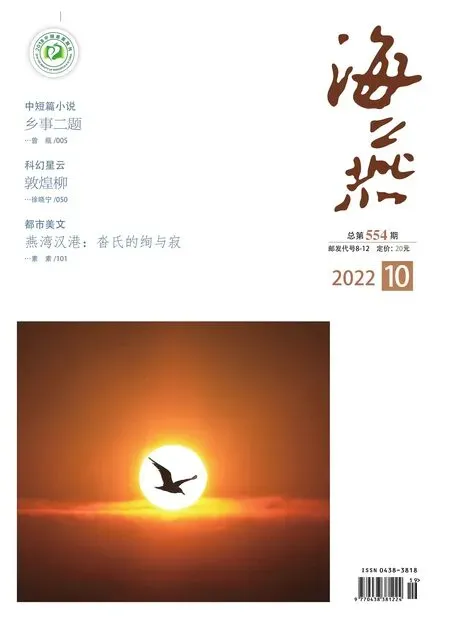相 助
文 杜陽林

一
社區的柳主任枉自姓柳,身材卻與柳條的形狀扯不上關系,是個腰圍三尺八的胖子。天熱,他在紅磚樓下仰起腦袋,認真看了看七樓的窗戶,靠外的玻璃上貼著一張碩大的“喜羊羊”貼紙,像是在熱情招呼柳主任:上來吧,今天跑完黃婆婆這一家,就順利完成任務了。
如果沒有特殊因由,柳主任總將黃婆婆留成最后一個慰問的對象。這不是柳主任不重視黃婆婆,恰恰相反,之所以讓黃婆婆“壓軸”,是因為在柳主任負責的轄區,他覺得黃婆婆是最該被幫扶的對象。七層高的老樓,沒有安裝電梯,幾十年前的泥水工,喜歡將樓梯砌得直而陡,去黃婆婆那兒“家訪”一次,柳主任好比征服半座珠穆朗瑪峰。這幾個月,他上上下下紅磚樓不止三十次,就是想早點做通黃婆婆的工作,讓她答應去養老院頤養天年,也稍減社區工作人員慰老愛老的勞動強度。
黃婆婆既是最后一個慰問對象,柳主任便想著能有充裕時間,可以和黃婆婆好好攀談,做一做她的思想工作。黃婆婆已八十有七,嘴里只有稀稀落落的四顆牙齒,頭上無一絲黑發。她走路時需拄杖助力,有一次柳主任見黃婆婆上公交車,眼看車子已經關門起步,她舉起拐杖勇猛地追攆了幾步,硬是感動得司機剎了一腳。黃婆婆到底是老態龍鐘,生活難以自理,還是老當益壯,在經驗十足的柳主任那里,都一直是個未解之謎。如今他也不想再猜謎了,黃婆婆畢竟年歲爬坡一般,爬到那兒去了,一旦有個三長兩短,社區的“孝敬老人的紅旗”便可能保不住,柳主任也要承擔不大不小的責任,老壽星早一日去養老院,才是放下他柳主任的心頭大石。
柳主任甩了一腦門兒的熱汗,在單元樓門口通風處的小板凳坐下,隨手抄起正在棋盤上對弈酣戰的大爺的蒲扇,呼啦啦地扇起風來。大爺瞅柳主任一眼,眼神向樓上瞄了瞄,知心知肺道:“大熱的天,又來做動員啊?”柳主任從亮晶晶的汗珠子中,咧嘴擠出一臉苦笑,蹦出一個“嗯”字。
社區的困難群眾喜歡柳主任,不僅因為柳主任真的能給大家帶來精米白面、優惠政策,還因為柳主任身上有一股大大咧咧的勁兒。他到哪家,磨盤般沉實的屁股絕不挑三揀四,哪怕家里臟得像狗窩也熟視無睹照坐不嫌,隨手撈過一個鼻涕娃兒來,圈在兩腿間,拇指與食指鉗住娃兒鼻孔,命令道:“我喊一二三,用力擤!”娃兒也就聽話地配合,擠出毛毛蟲一樣的黃鼻涕來,柳主任毫不嫌棄地用衛生紙擦掉,擰開龍頭洗手甩水。回頭撞見這家大人惴惴不安的眼神,大度地笑著擺擺手:“要讓娃兒從小講衛生,咱們社區可是區里的衛生文明標兵哦。”
柳主任在黃婆婆家,一手幫娃兒擤鼻涕的功夫毫無用武之地,倘若黃婆婆的孫子不死,可能家里也會多出一個鼻涕娃兒。可世事誰能料呢,如果這樣推演下去,倘若那孫子還活著,黃婆婆就不是孤寡老人,也不會進入柳主任的幫扶視野。
柳主任及時打住自己忽閃漫卷的念頭,終于成功登頂黃婆婆家門口,嘴里喘著大氣,準備掏出DM單,請黃婆婆看看他新找的這家養老院。這家養老院依山傍水,老人的房屋如別墅一般精致,旁邊設有五星級的醫護中心。可他的手剛探進皮包,像是心有靈犀,大門忽然推開,幸虧柳主任反應及時,否則一準被門彈到鼻梁。黃婆婆拐杖橐橐地點著地,毫不客氣地下了逐客令:“對不起,柳主任,我有事要出門去,咱們下回再聊吧。”
柳主任一臉蒙,他將自己累得氣喘吁吁,中途拿偉人名言自我鼓舞了三次,才頂著桑拿天氣,爬上七層高樓,如今黃婆婆要讓他即時離開?不不不。
黃婆婆急了,拐杖一下一下杵著地,嘴里呼哧呼哧喘大氣:“老五不見了,我要去把他找回來!”
聽說老五不見了,柳主任圓球般的肚子猛一吸氣,熱汗又趁機往外多滲了一層。
老五也是社區的關注對象,柳主任使勁兒撓了撓汗濕的頭皮。
二
老五自然是有名字的,但他自己總是不小心就“弄丟”名字。小時候,頑皮的鄰家孩子捉弄他:“老五,你是不是叫邱少云?”他認真想想,然后鄭重地點頭,頑皮孩子便嘻嘻笑著,將火柴擦燃了扔到他身上,嚇得老五哇哇哭叫。那幫頑皮孩子捉弄了人還振振有詞:“邱少云就是被火燒死的,你莫躲,躲了就不準叫邱少云。下次你當董存瑞吧。”老五不曉得當董存瑞是要挨炸,雖說不會真的背炸藥包,但頑皮孩子們撿石塊打他,讓他在飛舞的石塊中真實模擬烈士被炸藥轟炸后英勇倒地的場景,老五受痛不過,又是一通哇哇大哭。

插圖:李雨薇
在外面挨了惡作劇,回家還有一頓藤條子等著他。老五的爸爸,人稱“邱大眼”,臉上大概二分之一的面積被一雙大眼占據,世人都道眼睛大的人足夠深情,其實不知他們鼓起牛眼來,也比旁人更兇悍十分。老五上面有一個哥哥,三個姐姐,生他時母親難產,不得已動用了產鉗,腦袋挨了夾才拖出娘胎。護士給苦等門外的邱大眼報喜:“是個小子。”邱大眼咧開嘴,還沒來得及好好地樂一樂,產房又亂起來,有尖利的聲音嚷著:“血漿,血漿!”血漿包火速送進來,女人性子太急,已經等不住,瞪著圓圓的眼睛咽下最后一口氣。
老五的生日,成為母親的忌日,這讓邱大眼面對自己的幺兒,肉蟲子般溫嘟嘟一團肉,抱在懷里丟也丟不得,棄也棄不了,總有些憐愛夾雜憎惡的情緒。
老五三歲時報名上廠辦幼兒園,老師說他不正常,執意不肯收下。邱大眼還和人家爭辯,說娃兒就是命苦,出生后沒喝過母乳,反應慢一些,并不是傻子,不肯收下他,是看不起工人老大哥,嫌棄工人階級的革命接班人。幼兒園園長心平氣和地讓邱大眼帶孩子去大醫院仔細瞧瞧,只要拿到一張醫學體檢證明,入學不成問題。
邱大眼氣鼓鼓地帶老五去了醫院,從醫院大門出來,他一張原本昂揚的紫紅臉膛變成了一塊燒焦的黑炭,上面還結著厚厚一層冰霜。老五不會看形勢,拉著他褲腿,昂起小臉,口齒不清地提要求:“爸,餓,餓。”邱大眼忽然發作,一腳將老五踢到一旁,指著他痛罵:“我怎么倒了八輩子的霉,招來你這個喪門星?為生你累死了你媽,卻只得一個傻子!”
此前邱大眼喪妻,因他年富力強,相貌堂堂,來拉媒說親的熱心人不少,他怕后娘進門,虐待了自己五個孩子,一直咬著牙沒答應。如今醫生證實了老五“天生智力發育受限”,他以付出一個老婆為代價換來的寶貝兒子,終究是命中注定的討債鬼,這讓邱大眼怨氣沖頂憤憤難平,破了自己從前嚴守的戒,很快就和食堂幫廚的馬寡婦明鋪暗蓋睡到了一起,打飯時眉來眼去,旁邊排隊的人看得要發嘔,邱大眼只當他人是瞎子,不管不顧地大嚼馬寡婦偏心多給的幾塊肋排,恨不能自己墮落得更徹底一點。
與邱大眼私交甚好的工友溫言勸他,馬寡婦拖著三個鼻涕娃兒,以前聽說她和后勤科長的關系不清不楚,才從農村爭取到指標,進到廠里食堂,這樣一個作風既不正派、身后拖累又大的女人,何必與她攪不清呢?
不知邱大眼是和馬寡婦“一夜夫妻百夜恩”,真正睡出了感情呢,還是如今覺得老天爺與他嚴重作對,他正好自我放逐,破罐子該摔出更大的破聲響,索性將無賴的嘴臉描得再深刻濃黑些,遂不聽旁人好言相勸,敲鑼打鼓風風光光迎娶了馬寡婦。
馬寡婦進門,兩只眼仁兒不一邊高,八個孩子分成了三六九等。姓邱的四個哥哥姐姐受了鄰居點撥,“后媽后媽,要當先人一般敬著捧著,可不能像在親媽面前那么任性。”這四個孩子一開始還不以為然,卻因為喝湯聲音粗魯一點,或者叫了兩聲沒及時應答,馬寡婦立刻垮下臉沖邱大眼道:“反正不是從我肚里爬出去的貨,我管也管不住,說也沒人聽的。”馬寡婦這招“借刀”把戲,拙劣得要死,也只有邱大眼次次上當,眼珠子一瞪,蒲扇般的巴掌立即扇過去,打得親生娃兒嗷嗷叫,娃兒越叫得凄慘,邱大眼越是挺起胸脯,像是立了規矩又長了妻威。四個孩子皮肉吃過幾回虧,曉得在這個家里掌印把子的已變成馬寡婦,斗不過,躲得起,于是紛紛轉了臉孔,一口一個“媽”喊得油爆爆地香。
老五自然沒這份“眼色”,他生下來就沒了媽,嘴里也從未喊過媽,就算馬寡婦想要拿麻花馓子“招安”他,這個半傻子塞得腮幫子鼓鼓地吃了,照樣嘿嘿傻笑著不喊“媽”。老五的“各色”令馬寡婦感到挫敗,長此以往,老五成了家里唯一的眼中釘,于是老五的親兄姊也見風使舵地合起心來,比外人更狠辣地捉弄和欺辱弟弟,以此博得后媽的一點歡心,換來自己碗里多一點肉末,或者學校催交費時少受點夾磨。
工廠家屬區的人,常常見到老五光著腳,不知又犯了哪款天條,被馬寡婦趕到門外,不許他吃晚飯,不給他鞋襪穿。他也不知道反抗,只是一路走一路拿手背抹眼角,小臉臟兮兮地如花貓。心軟的人看到了,拖了聲音嘆道:“可憐的傻子,還知道哭,應該也不是太傻嘛。”
嘆雖嘆,卻沒人管老五,都說他有爹有媽,哪里輪得到外人插手?管多了還要挨邱大眼的罵,說好心人自己家里五行不缺,就缺個傻子,索性就將老五領養了去,免得礙他老邱的眼。人家傻子的親爹既說了這話,老五便成了真正的“邊緣戶”,幸好人傻體壯,冬天凍得滿腳生瘡,也未得過什么病。
馬寡婦進邱家的門,轉眼已過了二十多年,當日受后媽氣的四個兄姊,均已成家,各自埋頭經營自己一份小日子。他們心里天長日久地揣了怨氣,縱然逢年過節也不愛回父母這里假裝闔家大團圓。邱大眼和馬寡婦膝下,漸漸只剩下傻子老五這一個孩子。可這一個,還不如不剩。
三
柳主任攙扶黃婆婆下樓,黃婆婆嫌他動作慢,急急道:“你放開讓我自己走,你這將軍肚頂著礙事得很,和你一路我反倒走得慢。”黃婆婆這樣說,柳主任更要將她攙緊些了,老人家一個趔趄一個摔滑,那就是大事,不只是黃婆婆的大事,還是他柳主任和整個社區的大事。想到這兒,柳主任覺得應該在言語上盡量寬黃婆婆的心,舒緩她的焦灼情緒:“黃婆婆,老五原本就是個沒上籠頭的野馬,到處亂跑慣了,也不是真的丟了,您老莫急。”
“老五絕對不會無緣無故不見的。”黃婆婆又用拐杖頭敲地,一記接一記像是敲打著柳主任的太陽穴:“他和我約好的,就絕對不會失約。”
之前手底下的小姑娘和他說過,老五白天在外面游游蕩蕩,到了夜里睡覺,倒走去黃婆婆家里。柳主任一開始也想過,一個是八十多歲的孤寡婆婆,一個是生下來腦子就缺根弦兒的傻小子,他們咋就湊到一塊了?囑托社區工作的小姑娘暗中觀察,主要怕老五不懂事,給黃婆婆惹麻煩。小姑娘用手機仔細拍了黃婆婆照片,上午老人習慣拄著拐杖到一街之隔的農貿市場買點小菜,自從老五“蹭住”,黃婆婆好像比孫子剛離世時精神好了一些,眉眼也舒展開來,柳主任便想著,說不定是老天爺故意這樣安排,黃婆婆身邊走了一個機靈孫兒,又補償她一個傻孫兒。
饒是這樣,老五也不可替代“真孫子”呀,比如一個傻子,能有啥時間觀念?平時問十句話答不上一句有鹽有味的來,他還懂啥叫守約失約了?
柳主任畢竟做了多年社區工作,明白有些話不能講,講了,這位八十七歲的老人說不定就不準他陪著去找老五了。而讓一個孤寡婆婆頂著炎炎的大日頭孤零零尋找傻子,怎么想都是一樁危險任務。
黃婆婆現在住的房子,是孫兒購買的,當然孫兒手里沒那么多錢,黃婆婆支援了大頭,之前拾撿破爛攢的一點棺材本,悉數拿給了孫兒。她愿意給孫兒支援,這世上,除了孫兒,還有更親的人嗎?一個一個親人都爭先恐后見了馬克思,孫兒是她晚年最后的指望了。
孫兒是個好孫兒,從學校畢業,去廠里找到工作,又從別人手中買了這所二手房,趕緊從老家將奶奶接來,他臉貼著奶奶膝頭:“以后您再也不用撿破爛了,我要讓您體體面面地過上城里老太太的好日子。”
黃婆婆男人去世時,她還是個頭發烏油油的年輕媳婦,丈夫家里的親戚都冷眼看著呢:這么年輕,哪里守得住?豈知她真的守住了,一個人手腳并用,也將獨生兒子拉扯著養大,還給他娶了媳婦。以為兒子成家立業,自己卸下了人生重擔,豈知當年孫兒還在吃奶,兒子出差時乘坐的大巴像被鬼神推了輪子,莫名撞毀橋欄出了車禍,整車掉進江里,撈上來時乘客司機都已腫得發亮。兒媳哭了一氣,竟不聲不響地拿定主意,卷走所有賠償金,只將一個嗷嗷待哺的嬰兒留給黃婆婆。
黃婆婆是用米糊糊將孫兒養大的,她原先有工作,當年一手盤大兒子也有這份“吃公家飯”的底氣,哪知時代浪潮一波接一波地卷來,原以為飯碗賽鐵似鋼的國企也逼得銳意改革。臺上領導眼淚汪汪說什么“斷臂生存”,黃婆婆也聽不大懂,工作幾十年,她一直老實聽話,如果摘下臉皮揣包包里,和領導潑天潑地鬧一場,說不定也能再賴一賴,可惜這不符合黃婆婆的做人原則,她從來不給領導添麻煩,于是干脆利落地買斷工齡下崗,靠著打散工、撿破爛,將孫兒供到了大學畢業。
孫兒真是好孩子,畢業安頓下來,首先就是從老家接奶奶到他工作的城市,孫兒抱著她胳膊說:“我要和奶奶萬萬年在一起!”回頭想想,這“萬萬年”哪里敢亂說呢,這傻小子,沒有這么大的福分,倒狠狠連累了自己。
年紀輕輕的孫兒,應該是臺嶄新的機器才對,腸子咋就出毛病了呀!
大醫院跑了無數次,專家號掛了厚厚一沓,卻沒有一個醫生能說出真正的解救之法,只能眼睜睜看著孫兒的腸子一點一點地爛掉,從他腹腔中打一個小洞引流,流出來的盡是腥臭膿液,厚厚的床墊上從此有了頑固的印跡和味道。一日復一日,一年又一年,祖孫倆期盼的奇跡并未出現,孫兒的腸子徹底壞死,他在萬分痛苦中不甘又不愿地閉上了雙眼。
孫兒死的時候三十多歲,一米七五的個子,瘦得不到八十斤,只剩一把骨頭,皺巴巴的臉皮如同焦炭,像在人世間遭了足足一百年的罪。
黃婆婆當時是想和孫兒一道去的。
孫兒走了,親戚們七手八腳地將單人床豎起來,靠著墻壁放,當時原本說要抬下樓的,畢竟按照本地風俗,放一個“走了”的人的床鋪在屋里,不吉利。但從七樓搬抬一張木床下去,是讓親戚心里都生畏的事,黃婆婆也說將床鋪豎起就好,自家的孫兒,難不成他變成鬼了會對親奶奶耍奸使壞不成?
親戚合力將孫兒的床豎起擺放,草草收拾了一下房子。黃婆婆說自己想靜靜,眾人互相望望,便相繼離開了,黃婆婆便坐下來,想自己是該抹脖子,還是上吊,或者跳樓?她對每一樣死法會呈現怎樣的死貌都想到了,哪種都令她渾身打冷顫,她開始咒罵自己,一把年歲了還貪生怕死,不就是死嗎,腿一伸眼一閉,想那么多干啥?
罵著罵著便罵餓了肚子,身體太過誠實,黃婆婆只能去廚房,打開櫥柜,拿出剩下的兩個已干得起殼的饅頭。溫水瓶里的水也不知哪天燒的,她還是用這稍有余溫的水泡了饅頭,勺子也懶得用,手指劃拉著,囫圇吃喝了大半碗。肚里填了吃食,好歹回過精神頭,黃婆婆驟然想到,她現在喂飽了肚子,孫兒呢?她這個當奶奶的,還沒給孫兒燒過一回紙錢呢,他在黃泉地下,哪有鈔票去買吃的喝的?
黃婆婆頓時感到有點自責。紙錢和元寶都是親戚準備好的,墻腳堆著一只馬夾袋,說好“頭七”過來接黃婆婆,一起上山燒紙,可黃婆婆既已存了今日去死的心,自然要將這燒紙程序提前了。黃婆婆拿過一只菜籃子,放了蠟燭、紙錢、元寶和火柴進去,又顫巍巍地拉開了房門。
雖有兩個干硬饅頭打底,她這段時間畢竟是又勞累又悲愁,虛弱的身體挪到家屬院對門的小山坡腳下,已是臉色蠟黃虛汗淋漓。黃婆婆覺得這里僻靜,燒紙也相宜,燒過了,她也好安靜地選好一種死法,不能再拖延了。
已是黃昏暮色,黃婆婆眼神不濟,劃拉了幾次火柴都沒將紙錢點燃。這時身后傳來驚恐的聲音,喊著:“火,火。”黃婆婆淚眼婆娑地回頭,看到一個大小伙子,一手指著火柴,一手垂在大腿根兒,神經質地抖動,也不知他是怕火還是愛火。黃婆婆腦袋像一盆漿糊,反正是要死的人了,對誰都不存戒心,擺擺手招呼大小伙子:“你過來,幫我擋一下風,我好點火。”
小伙子真的過去了,半步半步地騰挪,腳在前行,屁股卻往后墜,像個失衡的秤砣。到底還是當了黃婆婆的“人肉屏風”,火苗在一堆紙錢上躥起時,他又嚇得雙腳踮起往上一跳。黃婆婆代孫兒向小伙子道歉:“娃兒,你慢慢收錢莫急莫慌,莫嚇到幫忙的好心人了。”
小伙子聽了黃婆婆的話,慢慢蹲下來,雙手抱著膝蓋。黃婆婆遞給他一串元寶,他也敢學著老人的樣子丟往火堆,看元寶化為灰燼,嘴里直發出呀呀的驚叫聲。
燒完紙錢,黃婆婆站起時有些發暈,往前一個趔趄,小伙子及時扶住她,嘴里嘿嘿傻笑。黃婆婆想著自己馬上就要死了,還能遇到這么好的小伙子,也是老天爺可憐她失去了孫兒,派一個好人來幫她最后一程。
黃婆婆鼓起精神,抬頭仔細打量小伙子,這一看,看出問題來。小伙子穿著一套藍白鑲條的運動服,明顯短小了,褲腳在腳腕上方高高吊起,頭發很臟,麻繩一般一綹綹地胡亂纏繞。最讓人訝異的是,如今春寒料峭的季節,他打著一雙赤足滿山跑,黑黢黢的腳背上,有幾道新鮮的口子,血珠已凝固了。黃婆婆心疼地問:“你媽媽呢?”
“媽?媽媽打老五,不準老五在家吃飯,不準睡覺,老五跑,老五快跑。”老五兩只腳彈跳起來,臉上一派驚恐表情。黃婆婆明白,自己是遇到傻子了。她剛隨孫兒搬到七樓房子時,就聽鄰居說過,這里有一個著名的傻娃兒,但自己卻是今日才初次遇到他,和老五在這種奇特的情境下相遇。
黃婆婆嘆口氣,她覺得就算要死,也得先回去給老五找雙鞋,他這樣光著腳到處亂跑,若是腳板扎著玻璃鐵釘,很可能得破傷風的。
老五跟著進了黃婆婆家,她蹲下來在柜里找鞋,老五已自說自話,走進孫兒房間,掄圓胳膊,三下五除二就將床放平整。
黃婆婆提著孫子一雙半新不舊的鞋,顫巍巍走進孫子房間,看到床放平整了,愣了一愣。幾個壯漢親戚摩拳擦掌才把床立起的,怎么又放下來了?床立起來,黃婆婆感到心死了大半,一想著孫子再也不能躺在上面,氣息微弱地喊奶奶,她就感到骨頭縫兒里滲出絲絲疼痛。如今老五莽撞,讓床回歸原狀,鬼使神差般,黃婆婆仿佛覺得這是孫子在天有靈,指使這個破衣赤腳的傻小子這般行事,借了老五的蠻力來告訴奶奶:“您還有壽數慢慢活,不要那么急著來找我。”
鼻頭一酸,黃婆婆嘆口氣,指揮老五從衣柜最上面的格子里取下被褥,鋪在床上。黃婆婆摸著半舊的枕頭、洗得發白的床單,仿佛孫兒一下班就嚷嚷著:“累死了累死了。”鞋也不脫就往床上一趴,等著奶奶拍他屁股,叫他起床吃飯。想起孫兒,令黃婆婆干涸的眼窩滲出兩滴渾濁的眼淚來。
老五讀不懂老人細微的表情,他只由著自己喜歡,四肢攤開往床墊上一倒,床墊像波浪一樣托起他,他高興地哦哦叫:“黃婆婆,老五的床,老五的床!”黃婆婆眼淚落下來,點著頭應和:“就是,就是,老五的床。”
老五傻了三十多年,那天竟破天荒說了句明白話:“老五的床,老五每天都來睡!”
黃婆婆怔了一怔,心頭滾過一陣悶雷,敲擊得肋骨生疼,卻也立刻附和道:“好好,老五夜里來睡老五的床。”
于是,床易了主,一年多了,老五像歸巢的燕兒,白天不管在外面瘋跑成啥樣,晚上到點肯定要回黃婆婆家歇息的。
四
樓下花園沒人,屋后一排平房沒人。眼看黃婆婆要往前面的小山攀爬,柳主任嘴里趕緊喊著:“慢點慢點,莫慌莫慌。”此時已過了晌午,他一上午時間都在忙工作,拖著一個脂肪膨脹的肚子四下奔走,水米未進,如今口干舌燥,四肢乏力,真的快要吃不消了,便掏出手機,給社區另外的工作人員小張與小秦打電話,讓她們火速過來支援。
小張和小秦是年輕女娃,腿腳敏捷,一會兒工夫便跑到山坡下,哼哈二將一般,從柳主任手中接管了黃婆婆,左右攙扶,請示主任:“您是要帶黃婆婆去哪里?”柳主任大口喘氣:“不是我帶黃婆婆去哪兒,是我們一道在找老五。他昨晚沒去黃婆婆家里睡,害得今天黃婆婆等了一上午,過了約定時間也沒出現。這不,老人家擔心老五,拉我四處來找找。”
柳主任愿意陪著自己找尋老五,黃婆婆心里是感激的,抬眼見他累得肚皮上的肥肉一疊一疊地打抖,又暗覺有些好笑,嘴硬道:“我可沒拉你,你自個要跟來的。”
“是,我自己偏要攆您老的路。”柳主任說著,一屁股坐在地上。他很久沒這么“運動”了,感覺自己已有了中暑的預兆,手掌有氣無力地搖動扇風,吩咐兩個女娃:“你們好好陪著黃婆婆,今天勢必要找到老五。”
小張和小秦對看一下,輕松地開了口:“不用找了。”
眼看黃婆婆的拐杖頭又要杵地,小張期期艾艾道:“老五剛剛在社區辦公室,都和我們磨一上午了。”
只要老五沒丟,黃婆婆心頭的大石便平平穩穩落了地。柳主任卻拔高嗓門兒哎呀一聲:“兩個死女子,剛剛為啥不早說?”
“我們也不清楚黃婆婆在心急火燎尋老五啊。”小秦偷偷吐了下舌頭。
黃婆婆擺擺手說趕緊回去看看老五。又自言自語地嘀咕:“老五咋回事,不來我家,倒去你們那兒?”
所有人都認為老五是傻子,只有黃婆婆一個人不當他傻,什么心事都肯絮絮叨叨講給他聽,還拿柳主任留下的養老院畫冊給老五看,聲音凄涼地說:“我不想去養老院,住在這所房子里,到處都有孫兒生活過的痕跡,到了那里,我孤零零的一個人,想著都害怕。”
老五不要黃婆婆害怕,他專門去磨社區的工作人員,就是希望自己也能和黃婆婆一道住進養老院,不用專門給他準備床鋪,他就在黃婆婆腳下的地板上睡覺就好。
老五將自己的想法完整表達出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顛三倒四,又比又劃地說了老半天,小張和小秦連蒙帶猜,才終于明白他的意思。她們覺得和一個傻子是說不清的,他又不是孤寡老人,怎么能進養老院?還要睡人家老太太的床腳下,非親非故的,怎么可能?
小張和小秦不將道理掰碎了說給老五聽,倒是兩人熱熱鬧鬧地聊了起來,邊聊邊用眼角瞥老五,仿佛在懷疑他傻子的外表下,藏著深不見底的陰謀禍心。
老五急了,像動物園困在鐵籠子里的猩猩,咚咚地跺腳,啊啊地吼叫,還圍著辦公桌轉圈圈。
“現在呢?”柳主任打斷這兩個女娃繪聲繪色的講述,急焦焦地問道。
倆年輕女娃鄭重了神色向領導匯報:“現在您不是打電話把我們喊過來了嗎?我們只有請老五到門外去,鎖好辦公室的門,趕緊一溜煙兒跑過來。”
小秦好奇地問黃婆婆:“老五一直嚷著要睡在您床腳,這是為什么呢?”
黃婆婆嘆口氣,稍微放緩了腳步,這話,說來就長。
五
好幾個月了,只要老五后媽不尋他的晦氣,故意將他反鎖在屋里,他每晚都過來睡黃婆婆孫兒的床。老五睡覺從不關門,鼾聲打得震天響,黃婆婆以為他是個從小腦袋就不靈光的傻子,一切都隨他。卻不知老五敞著門,是因為睡夢中還睜著一只眼。
這只眼幫了黃婆婆大忙。
有天晚上,黃婆婆心里忽然不好受,喘不過氣來,竭盡全力,嘴里也只能發出啊啊的聲音。既不能大聲呼救,也沒有力氣去摸枕頭下的速效救心丸。她以為自己這下完了,活到這把歲數,老婆子早就不怕死,可老五還睡在隔壁屋,她怕大清早的嚇著這個傻娃兒,還有點不想死。
柳主任完全不知道,黃婆婆還經歷過這樣一出險事,如果孤寡老人死在家中,傻小子老五受到刺激病情惡化,他也難辭其咎。
黃婆婆抬起長著密密老年斑的手背,擦了一下眼角。沒有經歷過死神敲門的人,很難明白懸在生死一線的人,每一秒都拉得無限長,長得像過了一輩子,今生今世的歡喜事難忘事都在眼前飛舞,她才忽然感悟:這個人間即使有再多不如意,還是舍不得此時咽下最后一口氣。倘若老天爺開恩,希望能再獲得一段光陰,至少將腦子中這走馬觀燈的人與事,再細細憶一次。
黃婆婆在最難受時,朦朦朧朧聽到耳邊響起一串腳步聲,是光腳板敲地的聲音,啪嗒啪嗒響亮得很,一下子就讓她的心安定了下來。老五將黃婆婆從床頭扶起來,喂老人吃了藥,他不肯走,腦袋伏在她胸口,一直緊張地聽心跳。
“這傻娃兒,從哪里學會聽人心跳這一招呢?”黃婆婆笑著嗔著,熱辣辣的眼淚倒搶先涌了出來。
黃婆婆喘口氣,伸手在臉上抹了兩把,腳下步子急急的,倒一點都不耽誤行走的工夫。到了社區辦公室門口,老五果真在那兒。他蜷坐在臺階上,將自己縮成一只球,身上套一件土黃色背心,濕出一個人印子,陽光毫無遮掩地刺向他,頭皮泛著油亮的汗珠,閃著微光。
“老五!”黃婆婆高喊了一聲,老五彈起身子,臉上露出既驚又喜的笑容。黃婆婆甩開小張和小秦的胳膊,向他奔了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