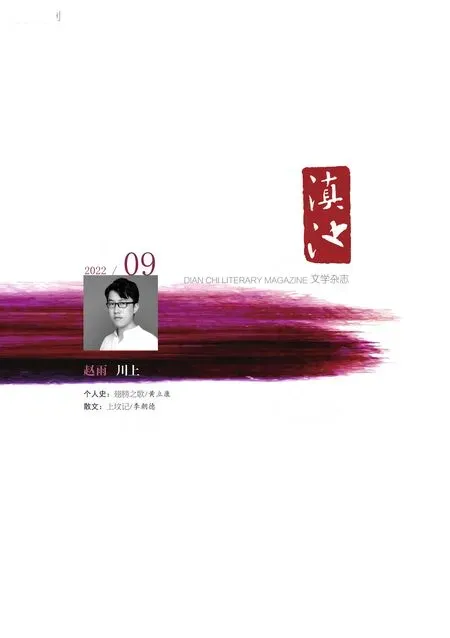手臂長滿苔蘚
組詩 趙俊
跨海大橋
從視覺上,它是一塊韌帶。
在剁碎的肉上頑強粘連。
擺渡船停止了轟鳴的交響樂,
島民因此不再擁有完整的身份。
它無非是一個半島,
那拉伸的鐵索將身份趨同。
需要改造的是它的生態系統,
它需要經歷一次物種的受難。
最先行動的是那些蜥蜴,
在橋墩上緩慢地進軍,
加入海島未知的食物鏈,
卜算著無數昆蟲將進入五臟廟。
大型動物們仍在原地徘徊,
大腦容量讓它們決定等待。
如果數據模型還沒有坍塌,
它們將進駐島上的開闊地。
只是游客們再沒有上島的感覺,
汽笛未在耳膜中蓋上戳印。
縱使有更多的生物在奔跑,
他們依然靜止在原生的想象中。
野生動物調查員
你按照喜好炮制著地名,
野牛溝、狼谷、巖羊灘……
以你貧瘠的想象力,
給地名按上合理的翅膀,
讓它們的羽毛更適合
想象力的滑翔。
你甚至需要為孑遺者造像,
為它們刻上墓碑,
最好能記錄最后的呢喃。
用相機的成像學,
素描出消失的軌跡,
以確定罪與罰的坐標。
但你從未警醒,
在你的上帝視角之外,
它們一直觀察著你,
當你隱藏在草叢的暗格,
它們敞開著交談——
以穿透森林的頻率。
廢棄的代售點
這并非是你要的結局:
窗口荒蕪,手臂長滿苔蘚。
這是無法存續的購買方式,
手工時代的笨拙在消退。
她們的制服繡著藍色的波浪,
讓旅途的褶皺無限延展。
你接過的票據被香水加持,
從此成為這玻璃櫥窗的信徒。
只有在賬單黑暗的修辭中,
才會留存著你名字的偏旁。
它無法勾勒你飛行的軌跡,
讓它消融在眼眶素色的薄膜中。
你曾種植的旅程的胚芽,
是從你心靈溫室中制造的驚喜。
你每天都在調試合適的溫度,
對應著空中小姐訓練過的儀態。
而現在你用手指決定行程,
默然地經過這僅剩的博物館。
幾個老者笨拙地擺弄紙幣,
映照著行程單被忘卻的螺螄紋。
水邊的香樟
雨后,香樟冠以綠意明亮的名諱。
過于頎長的枝葉拂過水的鏡面。
讓人誤以為闖入榕樹碩大的版圖,
樹冠已籠罩住水鄉的低音部,
高蹈中吸納著蜂鳥的翅膀。
東家的族譜一直在男權之中,
炫耀著最新一代的雙胞胎男嬰。
也許是不舍這日益成長的精靈。
樹葉搖晃時眾人在譜曲,
水邊的阿蒂麗娜在聲音中成長。
她將代替一位出嫁的水鄉女子,
看別處的香樟進入門閥之中,
直到變成一張孤單的八仙桌,
那纖維和油漆被囚禁在桌布的下方,
它將兀自擁有更遼闊的語境。
在那里,鴛鴦露宿在濕地之中。
百年好合的祝福只剩下一堆果漿,
作為一個永恒的觀察者,
它忍受著永生的詛咒,
在水鄉的迷宮里延伸著變節的根須。
詩歌鴨
幾只草鴨笨拙地搖動著蹼,
城區的人不再停留于田園的抒情。
味蕾精確的區間捕捉著它,
想象它和醬油在熱鍋中癡戀,
或者讓筍干和它在沸水中相遇。
有人注視于它吞食蚯蚓的姿勢,
這食欲的弧線帶來缺席的正義。
這像是在訴說食物鏈的遞進性,
無人可否定這蛋白質的擊鼓傳花,
除非你想用饑餓為夜晚獻祭。
你在那刻從未想起童年的鋤柄,
曾為它們親手將泥土松開。
當鴨毛在墻角中舔舐著血跡,
眼淚甚至伴隨著美味的圖騰,
在日記本里升騰起往昔的煙火。
那初蹄是否連接著詩的琴弦?
在農業經驗里躺臥著它跛腳的姿態,
多年后,它變成皮肉生意的喻體,
這已超出食欲和情感的界碑,
那異域的酸性腐蝕著城市的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