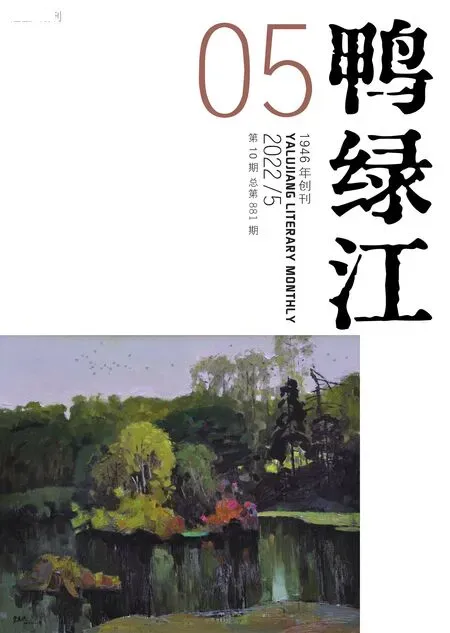考拉的夏天
劉 伊
考拉是一只狗,腿瘸了。它來自廣東省,現在和它的主人江一鳴還有一只叫毛線的貓生活在北京。
天是越來越熱了,北京的端午節便是夏天了。
這一天陽光一如既往的暴曬,把養狗、養貓當成養孩子一樣的江一鳴,真她的是去哪里都要選擇自駕,就為了能帶上她這一對可愛的寶貝。
別人家的貓和狗在一起總打架,生活在一起的兩個物種,各自都不免會動一點兒小心思。一般貓看上去比較高傲,似乎還比較聰明,狗是逗不過貓的。
可是在江一鳴的家里,這一對相處的就如同恩愛的戀人。它們相濡以沫,從來不打架。
考拉和所有的狗一樣,用舌頭排汗,天氣稍微有點溫度,它就會吐著舌頭。它是一條有文化的犬,從來不欺凌霸世。它和毛線相依相伴,一起陪在江一鳴的身邊,給江一鳴枯燥的生活增添了一抹陽光。
江一鳴從廣東自駕到北京,就留下來了,一直住在四環外,離宋莊畫家藝術村不是很遠的地方。時間真快,十年過去了。這是一個陽光晴好的日子,閨密小嫻喊她一起去宋莊參加一個有關端午的詩會。
江一鳴直搖頭:“不去,我還是在家里待著吧,好不容易周六可以休息一下。我還打算帶考拉和毛線出去玩呢。你們宋莊都是搞藝術的,我怕融不進去。再說了,你要是讓我去你家待會兒,那倒是沒問題。見藝術家們,還是算了吧。”
小嫻說:“來吧,啥藝術不藝術的,沒那么深奧。就是一起玩兒。藝術本來就是來源于生活,就算它高于生活,我們畫畫、寫詩的時候,抬高美化了它,可它還不是有生活的底蘊?不來自生活的繪畫作品和詩,那都是沒有筋骨,不痛不癢,沒有靈魂。就比方說我吧,我的職業是畫家,也寫詩,可是你從我頭上到腳下看看我哪里散發著藝術家的氣息?把我放人堆里,還不就是一個普通大姐?”
小嫻比江一鳴大六歲,一鳴來北京多少年,也就和她相處了多少年。那個時候她們是在人民日報老干部處的一個編委會工作的時候認識的。
那個時候的小嫻還做著編輯的活兒,畫畫只是業余愛好,誰又能想到十多年的時間,她從小時候的愛好,直到現在畫成了專業畫家,后來編輯也不做了,不再和江一鳴合租,跑到宋莊租了一個院子做工作室。而江一鳴也在朝陽區買房安家。
江一鳴那個時候做編輯也不是發自心底的熱愛,她是一個文學愛好者,應聘到這家編委會,工作了一段時間。當時每天忙于搶單,天天中午別的公司員工估計都在休息,可是編委會這些姑娘們都跑去朝陽區圖書館查資料,回到公司就開始撥打114查詢電話。就算查到的是對方無人接聽的傳真機號碼,也要趕緊把傳真發過去,就算午休時間對方辦公室里空無一人,沒有人接傳真,這單成與不成也都是這個人的了,其他同事就不允許再打這個單位的電話號碼。反正等到下午兩點上班時可以再追問對方負責人電話,如果沒收到,再發一份就OK。
那一段時間也是讓江一鳴很疲憊。離開老家就是想離開所有熟悉的一切。到一個陌生的城市,就是想讓陌生的城市重新認識她,也讓自己認識一個新的世界。哪怕這個新城市不會再有任何一個人和她有親密聯系,也都無所謂。反正她有考拉,何況來北京以后她又撿到一只流浪貓。每天回到家,她都覺得家里很熱鬧,慢慢地,它們治愈了她,她最初因為疼痛離開老家,后來她變得比之前越來越樂觀。
其實這只貓一點兒不像野貓,之前應該也是一只被寵過的小貓。到底它是怎么和主人走失的,她也不知道,只知道把它帶回家,經過一段時間的照料,它的毛發越來越干凈好看。
最重要的是,她覺得之前有點抑郁的考拉變得有點活潑了,這是她感覺毛線來到她家以后給考拉帶來的最大變化。小嫻不喜歡大型犬,對于考拉,她是愛屋及烏。既然好朋友答應來賦詩會,那她想帶著考拉和毛線一起來參加活動,她也就默許。
那些詩人、畫家,對于江一鳴來說,都是陌生人,除了小嫻以外。之前小嫻沒想太多,說你把它們帶來吧,反正你得拴繩,別把不喜歡小動物的人給嚇著。這一點不用小嫻教,江一鳴心里有數,當下別說像考拉這么大個頭的犬,就是那些小不點狗,如果被大人牽在手里,它都能跟你狂叫好半天。狗仗人勢就是這么來的。要是不拴它們,真要嚇到小孩子和老人,那真是負不起責任。
拴是一定要拴的。按照走進小嫻發來的共享位置,江一鳴來到一家私人美術館。宋莊美術館很多。大多數美術館都是私人的,小型的,不是很大,只有上上美術館規模還可以,這種大型美術館是需要門票的。
小嫻朋友的美術館,當然是私人的,憑著小嫻這張門票,江一鳴和她的考拉和毛線順利走進美術館。考拉牽在她的手里,毛線裝在它自己的太空艙里,就那么背在她的后背上。
見到小嫻,江一鳴嘴角上揚:“我們全家都來了,不會不受歡迎吧?”
小嫻接過江一鳴后背上的包,從包外面就可以看見里面的毛線,一副懶洋洋的模樣,還有一點兒趾高氣揚。小嫻把包挎在自己的肩膀上:“你們全家都來了,這最好了,今天晚上就和我住一起,別回去了。”
江一鳴說:“我也是這么想的,今天就當周末度假了,反正明天星期天我也不用上班。今天我們要和大姨在一起羅。”說著拍了拍考拉的后背。
江一鳴有162的身高,考拉走在她身邊也是很威風,盡管它是瘸腿的。小嫻把江一鳴介紹給出來迎接他們的男士:“許哥,這是江一鳴,我以前和你說過的,我最好的閨密。”
許先生點頭表示歡迎:“很高興光臨寒舍。你這狗是什么品種?是馬犬嗎?”
江一鳴點了點頭:“它叫考拉,男孩boy,毛線也是boy。”
小嫻趕緊把太空艙里的貓展示了一下:“毛線是它。俊男一枚。”
一個男子尖利的聲音傳來:“這么熱鬧?小嫻你來了也不叫上我?自己來的還是和哪個帥哥?”
小嫻沒有抬頭,低頭看著箱包里的毛線,見毛線張著嘴喵了一聲,雖然隔著箱子聽不太清,但是她也跟著喵了一聲。她之所以和貓說話,就是為了不想和剛才嗓音尖利男子搭腔。
江一鳴看出來了,但是這個男人她不認識。小嫻圈子里這些人,她一個都不認識。雖然以前她們兩個在圖書編委會工作,那個時候好賴她還喜歡點文學。越是成長,離文學也就越遙遠。她現在除了正兒八經的工作,根本就沒有了文學細胞,更別說像小嫻一樣去畫畫了。
她們兩個如今雖然干的不是一個行業,可是對于江一鳴來說,或者對于小嫻來說,這一切都阻止不了她們的友誼。
尖利嗓走近了:“小嫻同學越來越漂亮了,眼里都沒我這樣的俗人了。”
小嫻這才開口,但是并沒有看他:“我近視,看不清近處的東西,你走遠點,我興許能看清。”
美術館館長許先生歡迎每一位客人:“大家都進屋里坐吧,別在院子里站著了。”
院子不大,但是有風有水有魚有花有草,一派詩情畫意。不懂詩的江一鳴在來之前聽小嫻說工參加端午詩會,每個人要讀一首小詩。當時她就提醒小嫻,她寫詩的年代早就過去了,那是20歲。那個時候沒有愁事,但是喜歡為賦新詩強說愁。現在她每天都想開心過,所以她不想寫詩也不想讀詩。現在的她早已經沒有詩情畫意了。
當她說她不想讀詩的時候,小嫻說可以,行。她口頭答應,這可不算數,真正把江一鳴忽悠來以后,可由不得她了。每個人都認認真真地讀著詩,大多是你儂我儂情感類的詩歌。
江一鳴聽著,聽沒聽進去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怎么這么討厭這種無病呻吟的文字呢。男男女女情感的詩,她聽起來真是無聊至極。
可是她不能離席,她不能走,至少要等到詩會結束,和小嫻一起去她的住處。她打算今天晚上住在小嫻家里。兩個人雖然都在北京,一年難得見上兩面。
除了那個尖利嗓說話讓人聽著不大舒服以外,其他人,有報社記者、作家、畫家,無論如何都給人一種彬彬有禮的樣子。別說小嫻不愿意搭理那個人,就是江一鳴也覺得那個人的眼神也好、坐姿也好,還有他讀詩的時候,胳膊腿和手比比畫畫的樣子也好,怎么看這人都有點別扭,感覺與眼前的氣場不大協調。
反正無所謂了,江一鳴知道活動快結束了,結束以后就可以去小嫻家,和小嫻一起吃個晚餐,讓兩個毛孩子在寬敞的院子里撒撒歡兒。一直讓毛線在太空艙里待著肯定不行,雖然太空艙的透氣性不錯,可是江一鳴心疼它。而考拉的脖套一直沒有解下來,把它拴在院子里的鐵欄桿上,太難為它了。
許先生點名了:“江,哦,江一鳴,你看大家都讀詩了,你也讀一首吧。”
被美術館館長點名,江一鳴有一點不知所措,只好回復:“我和小嫻說了,我不懂詩。真的,我寫詩的時候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也沒準備啊。”
許先生繼續說:“你看今天這么多朋友,每個人都準備了一首詩,讀一首,不用是自己寫的。”
小嫻也用眼神示意她:“沒事,你準備準備,在網上找一首,朗讀詩你還不是小菜一碟?當年江一鳴可是電視臺主播。”
許先生說:“那更應該讀一首了。我說你的聲音怎么這么好聽。”
聽小嫻出賣她,江一鳴只好拿出手機,勉為其難地說:“那我找一首。”
她很快就找到了一首詩歌,這不是一首情感詩。之前各位朗誦的都是情愛的詩,而江一鳴讀的卻是一首有關狗的詩。她照著手機讀著:“殺狗的過程……”讀著讀著,江一鳴說:“算了,就念到這吧。”
此時江一鳴的聲音變了音兒,她不想再讀下去了,她真的是讀不下去了。她覺得自己的眼睛生疼生疼的,有什么東西狠狠地扎了進去。
她這才發現,所有人仿佛都沒有被感動,只有小嫻,她的閨密認真地看著她,那雙眼睛充滿了情感色彩,在和江一鳴產生著共鳴。
尖利嗓說:“狗就是狗,狗就是殺來吃肉的。狗肉可太香了,就著二兩牛欄山,配上一碟油炸花生。”
江一鳴非常反感地把頭扭到一邊去。
詩會還在繼續。善男信女們都喜歡寫愛情詩讀情感詩,對江一鳴血淋淋地殺狗不感興趣,甚至覺得她讀的詩大煞風景。江一鳴不想坐下去了,她從落地大玻璃看向窗外,考拉一定是渴了,它看向室內。然后她又聽到來自太空艙的毛線球的喵喵聲。
她從另一個包里拿出水瓶和一個空碗,直接走向外面,向考拉走去,給它倒了水。考拉看見主人到面前,愉快地搖著尾巴,開心地喝著水。想不到尖利嗓在身后把江一鳴嚇了一跳:“這狗肉肯定好吃,啊,都瘸了,你還留著它?你真是愛狗,你老公愿意你養狗嗎?不是說男不養貓,女不養狗嗎?”
江一鳴通過自我介紹,已經知道他曾經是一個狗販子,也許因為人在宋莊,就開始了他的畫畫生涯。難怪他經過考拉身邊的時候,本來在江一鳴面前性情很是溫順的考拉會對他汪汪大叫。
江一鳴很反感:“我愛養什么養什么,誰又能管到我呢?”
尖利嗓說:“看來你沒有小嫻開放,你看小嫻畫的畫,嘖,每幅畫都那么性感。總讓男人有非分之想,渾身的化學反應。我也想畫,就是畫不來。還是她有好身體才能畫得這么好。我們老爺們想畫自己的身體,也沒有人愛看。能和你交個朋友嗎?做我的脫衣模特咋樣?我要是有模特,肯定畫的比小嫻還好。”
小嫻喜歡畫女性裸體。她從來不畫男人,只畫女人。她畫的女人柔美,其實她畫的并沒有眼前這男人說得這么露骨。
江一鳴非常討厭這個人,何況他說的話已經不是友好地聊天了。江一鳴很想把喂考拉的水潑他一臉一身。他是怎么混到畫畫的隊伍里來的呢?
江一鳴不想在別人家失態,畢竟這里不是尖利嗓的地盤,如果是他的地盤,她肯定立刻離開這種惡心境地。她快速走向室內。原來朋友們近乎要散場了,江一鳴背著毛線也打算離開。
拉著考拉背著毛線,江一鳴連小嫻的家都不想去了。小嫻拉著她的手說:“怎么了?讀了那首詩你的情緒就不對勁,是不是又想他了?”
就這一句話讓江一鳴的眼淚沖出眼眶:“小嫻,我給你丟臉了,你們都讀情詩,就我讀寫狗的詩。”
小嫻說:“你看你想的可真多。沒事,這首詩我也喜歡。我也喜歡小狗小貓。我知道你肯定是想哥哥了。別這樣,你這樣,考拉是不是也會覺察到,它該傷心了。”
看向考拉,江一鳴把眼淚抹去:“小嫻,今天我們就不去你家了。我心里有點煩,你說的對,我想他了。”
尖利嗓從江一鳴身邊走過,吹了聲口哨,然后感覺要去投胎一樣飛車離開美術館門口。
江一鳴以要趕回家接一份傳真為由,帶著兩個毛孩子開車回家。
車行至北關環島的時候,發現前面擁堵。經過車禍現場,看著車眼熟,她趕緊把車靠邊停下,把毛孩子鎖在車內趕過去看到底是誰。原來是尖利嗓,江一鳴的胃淺,看著他臉上的血,差點吐出來。
尖利嗓的聲音不太尖利:“快送我去醫院,撞我的人逃逸了,我要死了。”
這求救的聲音無法忽視,江一鳴趕緊把他扶向自己的車,把他塞進車里。聞著尖利嗓的血腥味,考拉大聲叫著。江一鳴吼了它一聲,才停下來。在開車送他去醫院的同時,她給110打了報警電話。
經過醫院及時搶救,尖利嗓沒有生命危險。江一鳴就守在醫院的走廊里,等尖利嗓醒過來以后,她走過去,站在他面前,一聲不吭。
尖利嗓沒有了囂張氣焰:“妹妹,謝謝你。要不是你,我可能命都沒了。120也不知道都去哪了,等了太久了。”
江一鳴始終不說話,嘴角在抽動著,想說,又忍住。
尖利嗓不知道江一鳴為什么不說話,他想搜索所有最美的語言贊美江一鳴,可是他一開口,剛被手術針縫過的嘴巴就疼:“妹妹,你說說,我怎么謝你,你才能原諒我今天下午的出言不遜。”
江一鳴說:“起床,去我的車里,向我的考拉道歉。”
尖利嗓一愣:“考拉?就是那只狗?我道什么歉?”
江一鳴說:“它是退役犬,是我丈夫當年當緝毒警察時的忠犬。你說你道什么歉,你下午羞辱它,你說你道什么歉。我只要一個道歉就好。你道完歉,我們就立刻離開這里。”
尖利嗓說:“那你丈夫呢?”見江一鳴表情痛苦,他趕緊收住話,“對不起。我混蛋。”
尖利嗓嘴巴張嘴說話費勁,畢竟醫生給他縫了好幾針,因為費勁,嗓子也不再尖利。但是這一切并不影響他走路,他走到江一鳴的車前,向考拉敬禮,向它道歉:“對不起,我下午說錯話了,我不該說吃狗肉,我還不如狗。”
江一鳴說:“你向考拉保證,你永遠不販賣它們,永遠不吃它們,永遠不歧視它們。守住你為人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