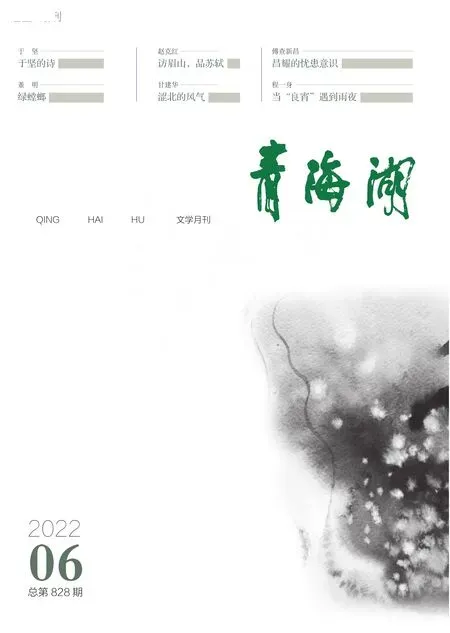綠蔭中冒出的紅頂房
李本才讓
黎明初曉,微露柔光,當第一縷陽光灑向雪山之巔時,也照亮了牧人一天的生活。輕輕的馬蹄踏著亮晶晶的晨露,微風吹拂草原的褶皺,原野盡顯無邊無際的遼闊,一首悠揚的民歌飛入彩云間。夜幕降臨,裊裊炊煙從帳篷天窗中緩緩升起,以嬌柔的姿態,去觸摸心愛的晴空。念“瑪尼”的老阿媽閉著眼睛一動不動,喃喃的誦經聲纏繞著炊煙沖散了白天的憂愁。拉下帳篷前的門簾,灶臺里牛糞燃燒的火焰舔食著鍋底,仿佛夜幕送來的一幅油畫。
一頂帳篷,默默無語,它是游牧民生存發展的歷史見證。取牦牛身上之毛,精心編制而成,是牧民家庭生息繁衍的堡壘,血脈延續的殿堂。不僅是牧人棲身于帳篷躲雨避雪的安全島,也是安身立命的溫暖家園,更是照看、保護牛羊的前哨陣地。牛羊在反復的咀嚼聲中酣然入睡,整個草原在夜色中蒼茫無際。
千百年來,隨著四季更替,逐水草而居的牧人,將帳篷馱在牛背上,如一道游動的風景,在廣袤的草原漂泊遷徙。帳篷是牧人住宿文化的濃縮,也是牧民歷史傳統與戰天斗地精神的彰顯。
歲月更替,四季輪回,又是一年草原繁華之際,伴隨著和煦春光,游牧定居項目如期而至,不分窮富貴賤,不分厚此薄彼,全村的牧戶都在籌劃修建一座獨特石木結構的藏式紅頂房,讓牧人告別黑帳篷入住石木房。黑帳篷曾是牧人主要居住形式,曾在風霜雨雪的歲月里,為牧人遮擋風寒,是他們溫暖的家。他們的人生命運,幸福苦難,歡樂憂傷,都與這座帳篷難以割舍。游牧生活方式逐步被現代文明所代替的說辭讓牧人有些難以接受,篤守古學古道的他們,在從四處聞訊趕來,老人們內一圈外一圈密密麻麻聚集起來,你一言我一語排斥著紅頂房,其實在內心深處已不得不接受時代發展帶來的變化,真正令他們難以割舍的是取牦牛之毛親手精心編織的黑帳篷。
然而,眾人并非眾口一詞,異口同聲,個別家境較為貧寒的牧戶就是懷著試一下紅頂房的想法,阿克阿貝家選用圈窩子,不切草根,不大興土木,石料與石料相砌,木料與木料榫孔相嵌,散發著新鮮的氣味。柴爐燃起熊熊火焰,暖氣融融,望著窗外飄搖的雪花,漸漸靜穆下來。
益民之事總會到來,雖晚,也不失為一種驚喜。牧人逐漸撥云見日,心慕手追紛紛在圈窩開發人間新樂園。站在山巔,看草原朝暉夕陰,云來霧往,鳥鳴蟲唧,還有牧人期待的神情。看綠浪翻滾的草原上一排排錯落有致的紅頂房映襯著藍天,生機蕩漾,像天上撒落的紅瑪瑙,晶瑩璀璨。
陽光晴好,潔凈如洗的天空瓦藍碧亮,九曲縈繞的河溪似緞帶飄逸,詩人眼中的“雪牡丹”悄然盛開,原野上燃燒的火焰,生命萌動的暖。羊群和牦牛悠然吃草,一雙犄角拱起一輪草原的紅日,牧民的日子從此紅紅火火。
甘冽的山泉水再無需借用“雪舟”堅韌的脊梁和背水姑娘那艱難步履,而順著管壁溢滿心窩,轉經路上的鵝卵石驅散了昔日飛揚的塵埃。昔日的夜幕下,沒有光的安慰,只有一閃一閃的手電筒是草原唯一的眼睛,內心深感悲傷,而今,月亮害怕路旁那一盞盞路燈灼傷眼睛而蒙上一臉輕紗。
牧場承包到戶,家家戶戶用鋪天蓋地的鐵絲網將牧場織成了天羅地網,野生動物難逃厄運,連看家的狗都自投羅網,幸免的幾只狗自然成為瀕危動物。
“丹懷”(藏語“諺語”)在大腦心田中已成了悠久的回憶,被淹沒在歷史大潮中,生命在歲月的風沙中飄散了,但那一份美好的情結永遠活著。
有些人才從母體中探出生命的頭,一些人已登仙而去。哭聲與笑聲有新有舊,總有人跟著羊群上山下坡,如趕集的商戶,趕往天葬臺;總有人裹著皮襖依偎在鍋臺旁,借蒼茫歲月的暖,扶住日漸陡峭的年紀,打個盹從夢里置換出真身。
羊群是村莊的一部分,狗是夜晚的一部分,“丹懷”與帳篷是我寂寞的一部分。風在經幡上詠誦,在草尖上彈奏,讓靈魂回到草原的懷抱,站得比太陽還高,比月光還潔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