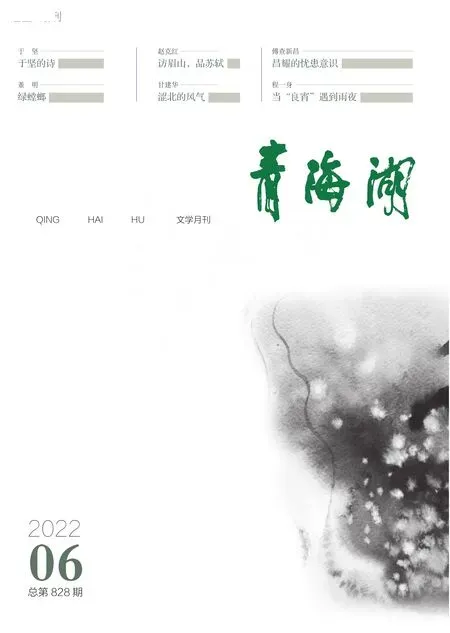風物
錦 梅
讓冬日山川,一點點豐盈起來的,一定是雪。風,不再是龐然大物或神秘巨人,倒像一位凌厲精明的小婦人,藏在山雪的折線里,偷著吹口哨。有時呼嘯中,還夾著一兩聲詭異的媚笑,像鬼故事里無處不藏妖嬈的女巫。
夜里一場封門大雪,馬路兩邊的小溪水溝,被掩隱得一如平地。大雪沒膝,一腳踩下去,輕巧的雪粒子倏地鉆進褲腿,刺骨冰涼。拔腿像拔蘿卜,“窟嗵,窟嗵”,只有深一腳,沒有淺一腳。干凈的風忽遠忽近,大河堰對面學堂大殿里的合唱,格外受聽。一定是王老師在拉手風琴,一張一翕,幽幽地穿越。飄蕩的歌聲,恨不得馬上生出一對翅膀。腳下的雪,一腳一腳鉆進褲管。強烈的雪光中手搭涼棚舉目,去路更遠,只好再踩了來路的那些雪窟窿折返回家。
次日村里就傳聞令人膽寒的消息,昨天要不是楊父忐忑不安,一路追蹤,陷于雪路的女兒蓮,差點凍死在雪窩里。
雪留下了平生唯一一次逃課記錄,想起來并不后悔。如果沒有那場大雪,童年該多么驚慌。
雪野中,萬籟俱靜,只有麻雀不甘寂寞,在花樹間啄來啄去雀躍。藍綠長尾的喜鵲卻一味地淡定,在青楊的高枝上,或長滿了蒿草的莊廓墻頭上瞭望,“喳—喳—喳”,從容報告風吹草動的消息。有時屋里寂寞,聽聲出門看動靜,什么也沒有。只有樹枝一陣微晃,襯出一片疏朗的藍天。雪洗過它們聲音,或細碎清脆,或嘹亮直白。
有孩子莫名哭鬧的人家,趁雪后人靜,懷抱了愛哭的孩子,早早出門走到馬路撞姓。也不知什么時候留下的一種鄉(xiāng)俗,說清早出門第一個撞上誰,哭鬧的孩子就姓誰。從此,孩子就可安生無憂不再哭鬧。實在無人可碰,平日懶惰的豬,討嫌的雞,也成為撞姓的對象。村中張五豬,雞頭保的乳名,就是這樣得來的。
有一年,書記家女人,也抱了大女兒去撞姓。運氣有點背,一路無人,大巷口走出來一頭豬,于是女兒長大都傻傻的有些木訥,只好招了女婿。
雪霽后的山野,山脊峻峭,脊線蜿蜒,山南山北青白分明,看上去像一個清癯矍鑠,又豁達的老人。歲月消減了他的肌理,但風骨還在。騎了自行車沿湟水岸穿行,南面的山巒披了雪,染了一絲嫵媚,北面的雪化了,蒼莽曠遠高古,又枯瘦嶙峋落寞。
車子奔馳,筆直的路剪開原野,兩岸的一切像正在播放的復古膠片。
總是那些路邊筆挺的白楊迎來送往,雪野朦朧。風偶然驚起路兩邊田野里一群迷失的鴉雀,噗嚕嚕飛起又落地,耐不住覓食的欲望。只有湟水一如既往地如影相隨,或坦坦蕩蕩或期期艾艾,既無聲寂寞,又充滿渴望,像藏了一份憂傷,人就想迎風落淚,停了車子,駐足觀望一陣,趁著無人大喊一聲,看一陣俊朗山野,想擁抱那份壯美呢,又不可盈手掬,無所適從,心里隱隱感到一種無以言說的疼痛。好在有凌厲的風,隨時會過濾掉那些不可名狀的隱痛,和即將逝去的傷逝。
雪是高原情感生命里的蒹葭,潔凈空靈,又豐茂葳蕤得常常使人傷懷。
后來冬季去過南方,看到植物依然翠綠,但萎靡不振的闊葉,高高伸向天空的火焰花,煙霞似的三角梅,一路的扶桑,總有時令淪陷,季節(jié)癱瘓的錯亂與不適感覺。于是領會遼闊的高原,因為裸露的遠山,疏朗的樹枝,高遠的天,廣漠的大野,而心胸闊展,也適宜滋養(yǎng)蒼涼與悲情,更貼近冬的內涵。總覺得花紅葉綠的南方冬天,少了一份壯美和期盼,而多了一份頹靡。于是臆想,一個熱愛遼闊又習慣了隨節(jié)令看風物的人,長期置身四季曖昧的南方,也會無所期待而郁悶發(fā)瘋的吧!
風雪迎春歸。紅底墨字的楹聯(lián),對了雪野剛嶄嶄新了半月,湟水兩岸遠遠近近的山野,林地,河谷好像都打開了氣孔,到處都是空穴,風開始作惡。
樹梢是風信子,鳥雀的翅膀是風在加速度,風卻看不見。哨子般吁吁竄起一股聲響的時候,瞬間天地像抖動起一件隱形的大氅,之后黃土揚塵,遮天蔽日。一些聲浪,像大河的濤聲,一浪高過一浪,又似千軍萬馬,卷著黃土層層奔騰。天地混沌啦,宇宙洪荒啦,不用念叨,小孩子都見過的奇觀,曠日持久地彌漫。之后樹枝的殘骸,甚至齊刷刷吹折的樹干,甚至炎炎夏日,也有風摧枯拉朽的杰作。而更高的風,卻常常在月黑夜里。遠遠地聽著一陣叮呤咣啷,像誰的腳步鬼祟地無意觸碰,接著像一個無形魔獸,漸漸逼近,近處物品七零八落,恣肆掃蕩。最后門被三番五次地抽打,像剝繭。風聲大得想要掀開泥皮屋頂,人頭皮發(fā)麻了縮在被窩里等動靜時,半天風卻悄無聲息地走了,如抽絲一般,世界出奇地靜。
風卷殘云只是天象,在高原卻是一道驚心動魄的奇觀。高原風實在像來去無蹤而直爽耿介的俠客,從不粘連,渾身充滿神秘的豪氣。
從月暈觀測來日風的大小,是夜里寒暄無聊時的日常。鄉(xiāng)土俗語落地生根。“月暈午時風”,“牛碾場,亮晃晃,草圈圈”,像童謠,反復地唱,唱暈了會唱反。
高原,人們既厭惡春風的暗無天日,又替它辯解說,一場春風化一寸凍土。只有強勁有力的風,才能化凍等著耕作的厚土。
一物降一物呢。一場夜里下過的雪,悄然之間神奇地收斂起風的虎口,人稱壘春雪。這正是人們春天最盼望的。
道路卻泥濘難走。一天下來,布鞋走成了一對灰老鼠,人們并不抱怨。土地開始變得柔軟,鳥雀重振精神,抖擻翅膀,溝渠潮濕,春三月的一切,好像空氣都突然有了活力。犁溝里奔騰的春水,最能夠激發(fā)希望,農夫為了澆灌正排水溝。一些溝渠里的枯葉,還沒有排凈,“頭把水”已經(jīng)渾濁地順溝渠淌下來了。雖然纖弱,卻有一股子一往直前的沖勁,遠遠地看著“水頭”流下來,小孩子們沿溝渠奔跑,內心受了撞擊,不由怦然心動,繼而欣喜。理解只有孩童和農夫,面對自然的那份敏感與呆癡,是多么難得的天真爛漫和赤誠。
二月的剪刀,大概從立春開始,已剪開了飛蟲的翅膀,剪開河谷山野的混沌懵懂,草尖萌動。三月,蒲公英鋸齒形的葉子沿石墻的裂縫,舉起第一朵羞赧的黃花時,終于草色遙看近卻無了,終于絕勝煙柳滿河谷了。
一個蠢蠢欲動的季節(jié),春風和凍土的較量,春水和人的言和,一切受了鼓舞,春心活泛起來,急吼吼脫去笨重鎧甲的春天,終于輕快地翻了一個身。
夏天。四歲的小弟和幾片樹葉,安靜地玩鬧了一個下午。心形的葉片和葉脈,像極了他的小手和掌紋,翻來倒去地查看手與樹葉的秘密。或許還有很多說給葉子的話。南風,調皮地輕吹一口氣,葉子翻飛于地面,沾上一絲灰土,終于惹惱了小弟,通紅了臉正和風置氣。于是跑到門前的小溪流,搭建他的那些橋梁。
溪流好像有意考驗著孩子的耐心。那條我們常常挑水澆菜或洗衣寬不過一米的溪流,有天突然拓寬。流水任性,小弟昨天在河床窄處精心搭建的小橋,了無蹤跡,是人畜車馬無意中做了水的幫兇。
與旁邊寬闊的馬路和田野相比,那橋本來就小得可憐而孤單,小到讓人熟視無睹。誰會在意它的存在呢?小橋正對了巷口,早出晚歸的牛羊,進出巷道拉麥捆的馬車,還有灌溉的水壩,都可能將剛剛搭建一新的橋梁毀于一旦。執(zhí)拗的小弟非但沒有因此沮喪,反而樂此不疲,小橋毀一次再搭一次,天天毀,天天搭,倒?jié)q了一些技藝,堅固得讓人知道了他的礙事。被水滋潤的創(chuàng)造力是旺盛的。
游戲里果然藏了命運,小弟后來從業(yè)橋梁與建筑,河溝水的起落,功不可沒。
火的世界不及水靈動,卻很炫耀。
陽光下一種黑黃相間叫‘尕喇叭’的野蜜蜂,出入花叢或花墻。一對兒透明的翅膀交叉震動,激起空氣,忽高忽低,垂直升降,像螺旋槳飛機旋在空中,一刻不停地發(fā)出嗚嗚飛旋的聲音。突然身子一縮,鉆進豁口的孔眼里去了。
虔心舉了大拇指和食指,等在“尕喇叭”蠶豆大小的洞口,不敢眨一下眼睛。“尕喇叭”一旦飛出,就可以毫不費力地落入大拇指和食指彀中。裝進事先備好的青霉素玻璃瓶里,迅速擰上蓋子,看野蜜蜂在瓶子中四處碰壁。想它的眼睛大概沒有視力的吧,可捉它的時候,一不小心“嗚”的一聲,猛然躥高的樣子,人就癡了。
有時來不及裝瓶擰蓋,幾只“尕喇叭”就握在拳頭里,左突右圍嗡嗡欲裂,刺得手心癢癢難耐,一種征服的快感,一番手心與內心的掙扎,痛苦著快樂著,忍耐著也不愿輕易放飛。
總不知太陽何時落山。南風習習,門前樹蔭下的晾臺,一片清涼。正是晚飯后左鄰右舍的大人孩子閑聊的好時候。巷口老樹上,歸巢鳥雀的響動,朦朦朧朧。高空中,繁星閃爍,一陣窸窸窣窣的碎響,微風拂動青楊,像碎銀清脆。月輝灑了一地,斑斑駁駁。
風裹了土皮上殘留的熱氣熏來,門前田野里大片的麥穗正揚花,墨團般黑漆一片的豆花馥郁飄香,連空氣都是香甜的。一里外三城大水潭邊的蛙鳴,此起彼伏,像和聲的練唱。浩渺星夜下,有一搭沒一搭閑聊的婦孺,醉心于薄暮下迷人的氣息,戀戀不舍,直到黑夜完全吞沒了單薄身影。
星夜空闊,遠山朦朧。高樹直刺青天,樹葉如流水作響。月亮爬過樹梢頭的時候,夜深人靜。月光灑滿院子,灑滿酣睡了一屋的人。村深處偶爾狗吠嗚咽,莊廓外高樹旁遞渠里的水,日夜不息。
鄉(xiāng)野里,這世俗不能湮沒,木欣欣向榮泉涓涓始流的悵然風情啊,像一支經(jīng)典老電影里的歌,唱啊唱,單曲回放,唱到入秋。
秋陽下的山墻,蠅蟲制造了它千瘡百孔的臉。炙烤的陽光,像冒著火焰。結對出行的螢蟲,在山墻的火焰上,屢屢練習蛾子撲火的游戲。藍頭紅尾的,紅頭綠尾的,一身火紅或孔雀藍。也許因為小,一個個煥發(fā)出迷人的光彩。魅惑,攝人心魂,魂不守舍,毒辣的陽光讓人眼冒金星。
我無師自通地排列組合,集齊了所有看見過的色彩種類,幻想夜色中集體舞動的剎那,多么炫幻。當然那時村里并沒有這個外來詞。
遠處的蛙鳴也有點鬧心。晚嵐中或濃郁或清淡的豆花香,也折磨人。螢火蟲舉了燈籠在夜色中飄舞,一個個像得了夜游癥。
我沒有能力理解,太過一廂情愿的愛會成為一種謀殺。讓那些本來可以夜里舉著燈籠四處游走的生靈,慘死在秋陽殘酷的封殺之中,渾然不覺。可那又怎么樣呢。
游戲會上癮。僅僅為了一個單純的心愿。五年級時學校舉行一次長途拉練,目的地湟中水峽,一個世外桃源。
高海拔的大山里,草甸柔軟如毛毯,溪流清泉清澈得激動人心,大葉白杜鵑花正競相盛放,手掌般徐徐展開的大朵的花,潔白如玉,鵝黃似綢,彩蝶蹁躚,清脆鳥聲充盈了山谷。
愛的謀殺再次上演。山里不論是蝴蝶的數(shù)量,還是種類,都出乎意料得多。綺麗的花紋,巨大的身形,枯葉蝶家族才是我的真正目標。但它們太敏感又易于高飛,難以捕捉。只好降低標準,蠱惑幾個同齡的女孩,重蹈覆轍螢火蟲的游戲。打算用兩百只普通蝴蝶的蹁躚飛舞,抵消對枯葉蝶家族的覬覦。
生活的無聊和樂趣,是因為重復和健忘。捉來的蝴蝶多達一百九十多只時,即便吸取了以前的教訓沒有封閉袋口,但經(jīng)過一天一夜的窒息,口袋完全打開的時候,蝴蝶們并沒有我們料想的那樣,遮蔽頭頂?shù)奶旃狻A阈堑仫w動,也搖搖欲墜不盡如人意。大部分奄奄一息,慘不忍睹。
這場慘殺,只因為純粹對美的攫取或掠奪,人只能躲在一棵高大杜鵑的背后,借樹茂盛的遮蔽檢討自己,悄聲抽泣。
其實野營拉練人員上的選拔,我并不夠格。路途有些遙遠,老師怕我們太小走不了遠路,實際上也因此吃盡了苦頭。但野營太有誘惑,母親們像對父親們出遠門那樣,為我們所做的準備,果然有些被重視的優(yōu)越和自豪,虛榮由此叢生。課間或上下學的路上,為各搭伙小組同伴之間,交流各家準備的信息而興奮不已。無非一些平日各家母親們舍不得做、這會兒換著花樣制作的干糧及油鹽。
萬花家卻很令大家失望,依然是難吃的青稞面餅,吝嗇得連一點香豆都不擦。大家只好在她拾柴火時,心照不宣地分食那些各家準備的誘人吃食,比如謝珍姐妹的棋子豆,英子爺爺合作社(代銷點)里幾粒蜜棗等。回家說給各自的家長,女人們憤憤地議論了好幾天,紛紛說,都是一個村里的,也不知道可憐自己的孩子,心腸也太狠了點。
我們做飯不像大人,手頭沒卡瑪(標準),好多小隊的食用油不夠了,老師們領著去山里人家換食油,才知道山里人家不通電,并且那些名字古怪的孩子很深奧。一個叫鐵勺的男孩,領了四五個同伴來營地看西洋景,見誰出神,就喊人家“盤山”了,弄得我們莫名其妙,明明在帳篷里嘛。原來山里孩子知事早,女孩十四五歲已許了婆家或出嫁。又粗通人事,“盤山”原來指想家或心上人,聽得圍了一圈的我們很羞怯。
水峽之行,像做了一場結實的夢。而高原秋季,更是一場接一場的夢魘,動人心魄。
麥黃時站在半山坡,團團云朵逐浪一樣飄來,撒下一大片一大片陰涼,夠一群人乘涼。山鷹嘯叫,遼闊而空曠。山地層層纏繞,油菜金黃,小麥吐穗,大豆揚花,人們淪陷于近乎失真的畫卷。風翻動一樹樹青楊的金葉子,獵獵作響,也只有習習涼風才能被翻動的山川,驚擾了人的迷夢。
收割了一半的金黃原野,彎腰收秋的人,像米勒的畫,只是沒有長裙和晚鐘。一行人字大雁,遠遠發(fā)出木輪車的聲響。有人抬頭就喊叫“雁兒雁兒一溜兒”。雁叫聲有些蒼涼,天藍得人失心瘋,像掉進了夢的深淵。
一切淪陷于情不自禁,迷失于經(jīng)年天高任鳥飛,海闊任魚游的夢魘。鄉(xiāng)村太寂寞,又太豐富。而感同身受自然萬物的神奇與美妙,好像是與生俱來、義不容辭的稟賦。
突然非常懷念那時的大黃風。像一位遠走他鄉(xiāng)的老朋友,希望重逢或邂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