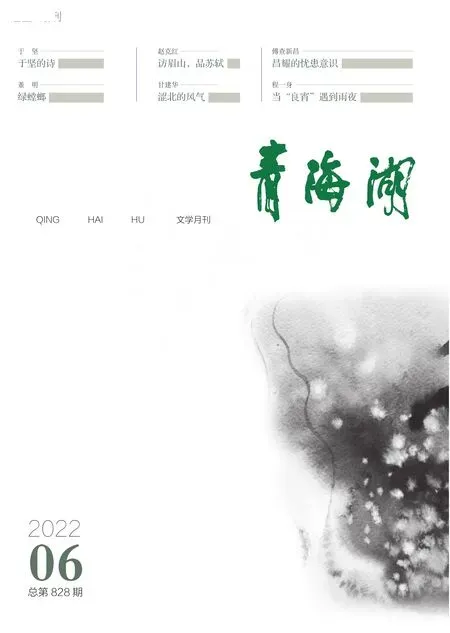程集往事
菡 萏
寒雨天。老人老門(mén),濕漉漉的街巷,封火墻上方蒼灰的天,這便是程集了。
這樣的青石板街,在江漢平原,我見(jiàn)過(guò)不少。她們懨懨在林立的高樓之間,衰敗老朽,又波瀾不驚獨(dú)守著自身秘密。
一條近乎失語(yǔ)的街巷,想為自己的祖先留塊地,抑或回家之路。但確實(shí)老了,你能感覺(jué)到,她慢慢矮化,歸于泥土的姿勢(shì)。那一座座落鎖的空屋,勾著糯米漿的青磚殘墻,四分五裂,架空騰起的樹(shù)根,長(zhǎng)滿荒草、油菜花的庭院,都陳述著人煙散盡后的凄涼。
就像春天的休止符,由無(wú)數(shù)個(gè)感嘆號(hào)和句號(hào)組成。往事落盡,海市蜃樓般的勝景,虛無(wú)又真切。
年輕人是不屑于此的,只有倚門(mén)望風(fēng)的老人和幾桌慢悠悠的麻將。
這時(shí)光,真像剪不斷的風(fēng)箏,獨(dú)自飄著。一放手,便萬(wàn)般惆悵。
一
雷瓊姐打著傘,帶著我們沿街慢慢走著。雨花砸在青石板上,綠苔爬滿青磚,多么古雅的一條街。一座座陳舊發(fā)黑的門(mén)楣,鏤花的窗,熏焦的桐油板壁。臨街的閣樓,沒(méi)有咯噔咯噔上樓的小腳聲,沒(méi)有待嫁的小姐,潘金蓮從紙窗落下的竹竿。妖冶與端淑皆歸塵土,活色生香的市井真是遠(yuǎn)去了。
雷瓊姐的外婆家,居于此。他的外公姓程,程集的程,是程家的香火血脈。他們的祖先,要追溯至南宋。800 多年前,這里原本荒蕪,是江漢平原大自然水文化的一個(gè)小小村落。程家兄弟從蘇州,順長(zhǎng)江,乘船而至,在這片荒僻美麗之地扎下根。他們的后人是勤勉的,一步一個(gè)腳印往前走,修了這條街,建了一所所連環(huán)套式的縱深院落。
他們守著浩瀚的長(zhǎng)江,與外界通聯(lián)。一船船茶葉、絲綢、瓷器,源源不斷抵達(dá)這兒。酒旗招搖,店鋪林立。代乳粉的廣告,與賣(mài)糯米沉漿的吆喝并不違和,多元的經(jīng)濟(jì)形態(tài),讓這個(gè)古鎮(zhèn)充溢著異國(guó)情質(zhì),又具本土寫(xiě)實(shí)。
鐵匠鋪燒著紅紅爐火,赤膊的匠人一錘錘輪下,細(xì)密的汗珠,古銅色肌膚,火星四濺的當(dāng)當(dāng)聲。先人們有使不完的勁。篾匠店掛著籃子筲箕篩子,沒(méi)塑料制品的年代,被純情手工壟斷。那些具有技術(shù)靈魂,泛著竹木清香的器物,喑啞在櫓聲灶間,質(zhì)樸而純粹。
現(xiàn)今依舊能看到“朱記紙?jiān)辍薄叭接浂垢边@樣的招牌。
古人們?cè)臀覀兩钤谕豢臻g,遙遠(yuǎn)親密,豐盈空落,像時(shí)光深處的老種子。
程集是程家人的,也是外來(lái)者的棲息地。一股股春風(fēng)吹拂著,她海綿般汲取著營(yíng)養(yǎng),既有儒雅之風(fēng),亦有豪爽之氣,更具市井之樂(lè)。
二
夜深人靜時(shí),一輪孤月懸于魏橋上空,又倒映水中。欸乃聲搖破寂靜水面。老長(zhǎng)河流過(guò)一座座白墻黛瓦的屋后,彎過(guò)魏橋,涌入長(zhǎng)江。
有人說(shuō),雖是平平凡凡的相貌,細(xì)看時(shí),有一股秀氣逼出來(lái),便是美人了,此言也適合程集。被清水擁過(guò)的街巷,既有古樸之氣,又多了幾分靈秀。
接新娘的船,吹著喇叭,搖進(jìn)來(lái)。掛紅的酒壇,一箱箱嫁妝。外來(lái)說(shuō)書(shū)人、游方郎中、騷人、俠客、手藝人,立于船舷;或從艙內(nèi)挑起藍(lán)花布簾,探出頭,遙望著魏橋上方如夢(mèng)似幻的喧鬧街景。
外來(lái)者的加盟,使其逐步繁茂壯大,成為陸路地鎖三縣;水路西進(jìn)蜀黔、北通漢口的門(mén)戶(hù)重鎮(zhèn)。人稱(chēng)“小漢口”。也體現(xiàn)了程集人的格局心胸,氣魄與涵養(yǎng)。
魏橋是座石拱橋,倒映水中的拱洞,是另一輪明月。
魚(yú)行、當(dāng)鋪、錢(qián)莊、郵局、客棧、武館、疋頭店、老酒館,多么熱氣騰騰的生活。南貨鋪是雷瓊姐喜歡之地,時(shí)鮮果品,蝦子魚(yú)生,黃草紙包著糕餅,頂著紅紙,系著麻繩,一層層解開(kāi),鼻子湊近一聞,香噴噴;籮筐里裝著蜜餞、炒貨、醬菜。作坊里的綠豆糕、薄荷糕、茯苓糕,何其誘人。
雷瓊姐的曾外公開(kāi)著一爿棉行,是地地道道的生意人,也是鄉(xiāng)紳。
家里三進(jìn)院落,商住兩用。門(mén)臉為鋪面,中進(jìn)作坊,后進(jìn)住房、貨棧兼曬場(chǎng)。每進(jìn)間,有隔板,獨(dú)立又暢通。家不斷打開(kāi),像一條幽深的隧道。鏤格門(mén)窗后面,閃著花影和青春年少的臉。登樓眺望,街景水系,一覽無(wú)余。
雪白的棉花,由棉農(nóng)之手,一朵朵摘下,裝進(jìn)麻袋,賣(mài)到棉行,再運(yùn)至沙市洋碼頭的外資打包場(chǎng)。壓實(shí)后,由水路輻射全國(guó)。
經(jīng)濟(jì)起源勞動(dòng),順著長(zhǎng)江的雙翼,展翅翱翔。
雷瓊姐的祖上,吃的便是這碗飯。不難看出,程集生意的興隆,很大一部分源自甲午戰(zhàn)爭(zhēng)后,沙市的開(kāi)埠。
三
跑日本那年,雷瓊姐的曾外公,連夜上了門(mén)板,用繩索綁了籮筐,一邊挑著行李,一邊挑著雷瓊姐的外公,順?biāo)范阃瞬JD月,寒風(fēng)呼嘯。家里積攢的一箱子銀元,無(wú)處安放,怕日本人擄走,也怕鄉(xiāng)人惦記,遂裝進(jìn)麻袋,沉入屋后的老長(zhǎng)河邊的水中。
幾個(gè)月后返回,滿目瘡痍,門(mén)板七零八落躺在街心。程集這只精美的匣子,滿是刀剁斧鑿的痕跡。住過(guò)兵的家里,柜子?xùn)|倒西歪,衣服揚(yáng)了一地,吃剩的罐頭,歪斜著淌著汁。煙蒂酒瓶,醬壇子成了夜壺,曾外婆喜歡的四屜雕花凳燒壞一角,幾扇鏤花格子門(mén)被折斷。
像一場(chǎng)噩夢(mèng),被不同語(yǔ)言者入侵。
黑乎乎的夜色里,雷瓊姐的曾外祖,穿過(guò)水庫(kù),鑿開(kāi)冰,下河去撈銀元。怎奈冰天雪地,水寒徹骨,接連幾夜沒(méi)撈到。曾外婆默坐在堂屋里,聽(tīng)著自鳴鐘當(dāng)當(dāng)幾下,想勸,欲言又止。曾外公受了傷寒,一病不起。昏暗油燈下,年輕的曾外婆端著藥守在床前。曾外公發(fā)著高燒,說(shuō)著胡話,腦門(mén)搭著毛巾。走之前,看了眼站在床邊的愛(ài)兒,拉起他的小手,交到妻子掌心,囑咐她好生把兒子養(yǎng)大。任何人不要再下河去找那袋銀元。不祥之物,權(quán)當(dāng)沒(méi)有。
曾外公很愛(ài)曾外婆。當(dāng)年,大紅花轎抬進(jìn)門(mén),堵塞整個(gè)街巷。曾外婆的一雙小腳邁出轎門(mén),一汪水色,天空碧藍(lán)。
一個(gè)婦人,便是一個(gè)家的靈魂。曾外婆穿的衣料,是曾外公從沙市買(mǎi)回來(lái)的,有進(jìn)口的,也有本土老蠶繭。曾外公每次去沙市送貨,總是給曾外婆帶些稀奇古怪之物。小鏡子,小提包。國(guó)門(mén)洞開(kāi),洋貨不斷涌入。真正意義上的旗袍尚未面世,但已有很時(shí)尚類(lèi)似旗袍的衣服,曾外公購(gòu)回,又帶回進(jìn)口西洋傘。曾外婆打著果綠色蕾絲花傘,裊裊婷婷,穿過(guò)古街,走上魏橋,去文昌宮進(jìn)香。是怎樣的風(fēng)姿綽約,楚楚動(dòng)人。
正午的太陽(yáng)孤零零掛在天空,整個(gè)程集屏住了呼吸。挑擔(dān)的、推車(chē)的、擺攤的,無(wú)不側(cè)目。很多婦人爭(zhēng)相效仿,成為摩登對(duì)象。
這樣華麗的生活畢竟遠(yuǎn)去了。
四
曾外公走后,曾太婆獨(dú)自拉扯著八歲的兒子過(guò)生活。日子蕭條,卻樸素殷實(shí)。家里除了收棉花,兼做秤生意。她是大家小姐,知書(shū)識(shí)禮,打得一手好算盤(pán)。
她的文化情結(jié)默默影響著外公,加之私塾教育,外公的思想逐步開(kāi)化。讀《四書(shū)五經(jīng)》,迷楚腔漢調(diào)。外公野,不拘泥祖上留下的尺幅店面。乘船遠(yuǎn)游,足跡踏遍三山五岳,流連瓦市勾欄、酒樓茶肆。
即便回至古街,也是坐在茶館的臺(tái)面上說(shuō)書(shū)。臺(tái)子高出地面半尺,外公頭戴瓜棱小帽,腳蹬青布鑲鞋,一襲灰藍(lán)袍子。人儒雅漂亮,又帶著幾分市井的平庸喜樂(lè),抑或憂郁。說(shuō)秦漢、大唐,說(shuō)張飛、小喬,說(shuō)秋風(fēng)高起,人世離亂。緊要處,“啪”地一拍驚堂木。長(zhǎng)嘴茶壺,隔空沖水,落入杯盞,不濺落一滴。絞好的熱毛巾把子“啪”地甩過(guò)去,那邊雙手接住,用完再甩回來(lái),像空中飛碟來(lái)回穿梭。
茶館里座無(wú)虛席,人們嗑著瓜子,搖著折扇。過(guò)道里站滿了人,連門(mén)口街心皆擠滿看客。老翁孩童婦孺,伸脖引頸。引車(chē)賣(mài)漿者,駐足觀摩。趕驢人喊著讓路讓路,卻停下來(lái)聽(tīng)上一段。
哪根煙囪最黑,哪家就是茶館,雷瓊姐指著一座老屋的灰黑屋頂說(shuō)道。她兒時(shí),常去聽(tīng)外公說(shuō)書(shū)。外公已換了新式打扮。灶房的爐子很大,火苗很旺,無(wú)數(shù)個(gè)紅紅灶眼,跺著數(shù)不清熏黑的一尺多長(zhǎng)的長(zhǎng)嘴銅茶壺。壺嘴刀削一般,尖尖的,也叫長(zhǎng)流壺,或長(zhǎng)銅壺。這個(gè)提走,那個(gè)跺上;這個(gè)滾邊,噗噗冒著熱氣,那個(gè)在缸邊嘩嘩舀著水。
客堂明亮,掛著馬燈,老板娘和穿短打的堂倌提著壺,一刻不停地加茶碗續(xù)水。客人悠閑地端著三件套蓋碗茶杯,輕輕一刮,啜一口,蓋上蓋子,再放下。茶館開(kāi)得一本正經(jīng),每天門(mén)口牌子上,輪換著書(shū)目和請(qǐng)的角兒。
有熱氣,便有生意;有生意,便有源源不斷的精神食糧和物質(zhì)財(cái)富。茶只是個(gè)引子,涓涓細(xì)流里,流淌的是祖輩的故事。過(guò)去的茶館,在一定程度上,等同現(xiàn)今媒體,說(shuō)書(shū)人用聲音、腔調(diào)、動(dòng)作、表情,傳播二手文化。
在程集,外公是個(gè)人物,雷瓊姐如是說(shuō)。
五
曾外婆年輕守寡,一生未嫁。長(zhǎng)壽,深居簡(jiǎn)出,晚年幾乎與世隔絕,獨(dú)自住在家中三進(jìn)院落的最深處。從后門(mén)出去,是廁所,兩邊菜地,一條小路直通老長(zhǎng)河。老長(zhǎng)河的水,清亮亮,在她夢(mèng)里嗚咽了一生。她枕著汩汩流淌的水聲,直至深眠。
像一樹(shù)好看的花,春天過(guò)去了,也就落寞了。
曾外婆干凈仔細(xì),身上房里,纖塵不染。雷瓊姐兒時(shí),叫她老爸爸。老爸爸與眾不同,一身黑衣,安靜古老,充滿神秘。她的衣襟一年四季都是香的。房里幽暗,擺著她喜歡的器物——結(jié)婚時(shí)的雕花床、腳踏、烏沉沉厚實(shí)的老松木柜。她不聞人間事,也不知外面事。重孫輩喜歡去她屋里打探秘密,聽(tīng)她講《白蛇傳》,一段段,一套套。雷瓊姐的父親不讓講,怕傳出去。
外面是個(gè)新鮮世界。舅舅是個(gè)朝氣蓬勃,俊朗的青年,看書(shū)、寫(xiě)作、朗誦,登臺(tái)表演。四個(gè)姨媽唱歌跳舞,參加各種活動(dòng)。外婆的六個(gè)子女,個(gè)個(gè)灑脫快活。
老爸爸一生內(nèi)斂,風(fēng)度,孤獨(dú),慈愛(ài)。眼神里滿是動(dòng)蕩后的平靜。她走的那天,嗩吶一起,雨簾順著黑瓦傾聲而落。
多么悲傷的女人,生于斯,長(zhǎng)于斯,逝于斯,一生沒(méi)有走出這條街。
她用過(guò)的老物件,散落在后人手里,成了古董。
美國(guó)在《Mobility 2000》中對(duì)交通管理系統(tǒng)的定義強(qiáng)調(diào),監(jiān)視、控制和管理交通。“監(jiān)視”交通的關(guān)鍵是采集、存儲(chǔ)和傳輸交通信息。隨著科學(xué)技術(shù)的發(fā)展,采集、存儲(chǔ)、傳輸交通信息的方法越來(lái)越智能化,智能交通管理系統(tǒng)應(yīng)運(yùn)而生。智能交通管理系統(tǒng)是利用先進(jìn)的信號(hào)檢測(cè)手段和相關(guān)交通控制模型,通過(guò)檢測(cè)到的交通信息,制定有效的交通控制方案,并將成熟的方案通過(guò)多種方式傳遞給交通參與者和管理者,目標(biāo)是提高交通管理和運(yùn)輸效率。
六
雷瓊姐兒時(shí),最盼望寒暑假。母親把她送到外婆家。她家住在堤頭古驛鄉(xiāng)下,吃返銷(xiāo)糧。母親早先在沙市電池廠上班,父親是沙市農(nóng)校的學(xué)生,兩人在監(jiān)利至沙市的輪船上相識(shí)相愛(ài)。父親分到輕工業(yè)局上班,被政治運(yùn)動(dòng)所累,下放回鄉(xiāng)。母親帶著孩子,跟了回來(lái),成為農(nóng)村人。外婆罵雷瓊姐的母親,不該回農(nóng)村,害得孩子們受苦。
外婆家吃商品糧,有各種物資供給,每每接濟(jì)他們。
外婆是郊區(qū)好人家的女兒,會(huì)做各種吃食。軟甜的糯米酒,是雷瓊姐的最?lèi)?ài)。爛豆腐、炸胡椒、泡洋姜,壇壇罐罐清清爽爽。外公買(mǎi)回來(lái)糍粑、糯米包油條、米圓子、鐵盒餅干,一些鄉(xiāng)下無(wú)法見(jiàn)到之物。外婆變著法子改善伙食。
孩子們過(guò)節(jié)一般。
“三進(jìn)房屋,中間堂屋,兩邊臥室,外公外婆一間,舅舅一間。”外婆的房間藏了許多的糖果,空氣都是甜的。雷瓊姐去后,和小姨們住在兩邊的廂房,里面有很多漂亮東西。
最有意思最難忘的是和小姨一起,躲在街后河邊荒屋看《紅樓夢(mèng)》。繁體字,繪著繡像,沒(méi)皮,頁(yè)面殘缺。雷瓊姐看不懂,小姨教她按偏旁部首猜。即便如此,她讀得津津有味,和小姨討論著里面的人物,黛玉、寶釵、湘云,就像討論自己。書(shū)藏在柴垛里,一次次偷偷跑去。
那樣的秘密,當(dāng)時(shí)只她倆知道。
書(shū),是小姨弄到的,小姨比她大四歲,梳著兩根到腰的麻花辮,一走一搖,好看的燈芯絨衣褲。雷瓊姐跟在她身后,像個(gè)小跟班。
光從墻高處的小窗射進(jìn)來(lái),擴(kuò)散成渾濁的一束。小姨低頭看書(shū)的樣子極美,小巧的鼻子,膚色白凈,浮著層細(xì)細(xì)的絨毛。她們倚著柴垛,身旁堆放著凌亂的農(nóng)具。
街面朱紅板墻上,寫(xiě)著一心為革命的白漆大字;穿灰藍(lán)制服的人,行色匆匆。
在那個(gè)充滿革命氣息的年代,這條老巷的后面,依舊藏著一個(gè)大觀園。
多么美好的詮釋?zhuān)@片古老嘈雜的土地,從沒(méi)有對(duì)文化泯滅;一個(gè)少女心中從沒(méi)斬?cái)鄬?duì)美好人性的渴望。
七
雨后的石板最好,脊背樣慢慢彎成美麗弧度,人稱(chēng)鯽魚(yú)背。雷瓊姐趿著銅油木屐在上面“嘚嘚嘚”,發(fā)出清脆的好聽(tīng)聲,充盈著少女的輕盈喜悅。獨(dú)輪車(chē)剛好從中間的青石板推過(guò),吱呀呀。
舊時(shí)的青石板整齊有序,銜接自然,不像現(xiàn)在這般凹凸不平。這條街,性質(zhì)上很像沙市的九十埠;外貌現(xiàn)狀又似三義街。但沒(méi)限量版一說(shuō),每條街都是獨(dú)特的。程集的下水道很特別,那時(shí)便有地漏。五條青石板,中間高高隆起,是為了便于排水。水排到老長(zhǎng)河,再歸入長(zhǎng)江。
河霧彌漫的清晨,一家家卸下門(mén)板。
睡在幽深的板壁房里,每每被嘈雜的市聲吵醒。獨(dú)輪車(chē)?yán)χi崽,嗷嗷叫著推過(guò)街門(mén);挑擔(dān)賣(mài)菜的,吆喝著剛出塘的茭白菱角。屋后老長(zhǎng)河,白鵝游動(dòng),發(fā)出“嘎嘎嘎”的歡叫。石埠上的婦人高舉著棒頭,篤篤搗衣。在五光十色的聲音里,程集開(kāi)始了新的一天。
夕陽(yáng)西下,裸背男子擔(dān)水的沉默背影,也都是生機(jī)勃勃的。夜晚時(shí),伙計(jì)們咔咔上上門(mén)板。日復(fù)一日。
春天,飽滿的河水,流經(jīng)一片片金黃的油菜花田。秋天,鵝黃的稻谷垂?jié)M河岸。
每家后面的石埠,可以停船、洗衣、淘米。像一個(gè)天然大水池,又似一個(gè)個(gè)微型碼頭。水鄉(xiāng)是濕潤(rùn)的,女孩的辮子垂在胸前,吊腿褲露出一截瓷白的小腿和彎曲的腳踝。斜欠著身子,兩手嘩啦,嘩啦搖著擼。
程集兩條路,一條旱路,一條水路。每家兩個(gè)門(mén),前門(mén)與后門(mén)。
那些熱鬧的古人,老長(zhǎng)河里穿梭的商船、貨船、漁船;石板街上的馬騾驢,都移除了這條街。大戲謝幕,觀眾卻久久不愿離去。
在這兒,很多文字同樣會(huì)移除我們的身體,掏空和遇見(jiàn)都是幸福的。空蕩蕩,有多好,像風(fēng)刮過(guò)的原野,看似什么都不曾留下,卻存儲(chǔ)在另一個(gè)優(yōu)盤(pán)里,等待回憶或開(kāi)啟。
每一次重新辨識(shí)都是新鮮的。
八
雷瓊姐外婆家的老屋,盡管還在,已面目全非,老長(zhǎng)河也淺了濁了。
記憶是看不見(jiàn)的,殘破也是一種美。附了時(shí)間的魂魄,生成新的藝術(shù)品,幽遠(yuǎn)、孤獨(dú)、深靜。
右邊第一家——冉記豆腐店,是名副其實(shí)的老店,依舊沿襲手工制作。堂屋幽深,拆下的雕花門(mén)扇,放在高高的頂棚。
大鍋大灶,陰滿綠苔的水井。一中年女子,穿著套鞋襖罩,拿著塑料筐,彎腰洗著泥鰍。水很冷,手凍得紅彤彤的。江漢平原鄉(xiāng)下的女子,多半如此,但一定燒得一手好菜。豆腐早已賣(mài)完,喜歡吃,得提前定。
“我的莓楂炒韭菜最好吃了……”這樣的吆喝,你還能聽(tīng)見(jiàn)嗎?
家里人曾認(rèn)為外公是一個(gè)離經(jīng)叛道、不負(fù)責(zé)任的紈绔子弟,現(xiàn)今才理解他是個(gè)被時(shí)代拋棄,憂傷的,精神生活的追隨者。他用另一種方式,解讀自己,引領(lǐng)著后代;雷瓊姐年少時(shí),也曾不理解母親,在那么困苦的環(huán)境,依舊唱呀跳呀。母親說(shuō),想活著有意義,就要盡力去愛(ài)一件事。
歲月擦肩而過(guò),茶館已然變味。前幾年,有押寶的,雷瓊姐也會(huì)壓上一把,試下手氣。更多時(shí),在自己的文化園里,鋤草、種花、插花、看書(shū)、彈琴。
時(shí)代一層層脫繭,化蝶時(shí),除了新生的喜悅,亦有無(wú)數(shù)失落。就像春天,無(wú)法阻擋秋天的腳步。程集鎮(zhèn)的后人,多半去了沙市和監(jiān)利,亦如都市人北漂、留洋一樣。但精神文化的種子依舊在。
程集因商業(yè)發(fā)達(dá),人口流動(dòng)而興;又隨商業(yè)發(fā)達(dá),人口流動(dòng)而衰。日月無(wú)邊,生命的循環(huán)生生不息。老長(zhǎng)河這條故道河通著長(zhǎng)江,通著萬(wàn)里之遙的外部世界。而碼頭,是經(jīng)濟(jì)的命脈與歸屬地。碼頭文化帶來(lái)的繁榮,進(jìn)入多軌的今天,必然消退。從宋至今,近千年的街巷,依舊是輝煌的地標(biāo)。即便那些古人蒸發(fā)了,亦是歷史云端里一條笑語(yǔ)喧嘩的老街。
我們懷念著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