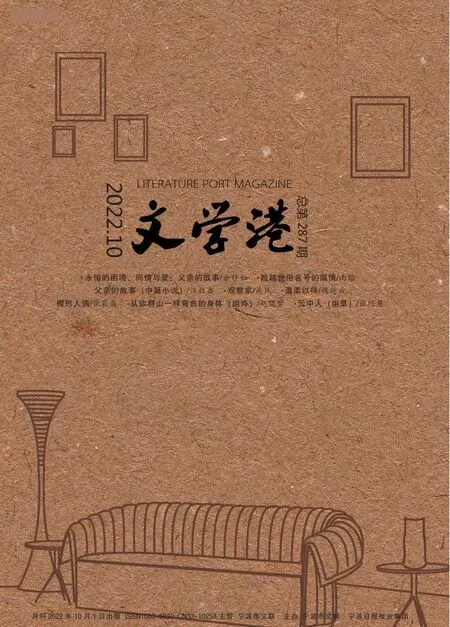詠春三題
□沈學東
春 雪
是彤云和狂風催生了這澄澈透明的晶體,就像在沙子的刺激下,粗糙的蚌殼內孕育了璀璨的珍珠。
開始,天空布滿戾氣,黑壓壓的云層就像整日板著的包公臉。漸壓漸低的云腳,幾乎已經踩著了村西殘破的籬笆墻。狂風是他掄起鞭子不斷甩動的聲音,呼呼地響。本來以為就要下點雨,可是雨水化為精魂,那雪就自然而然地來了。
晦曚的天空幾乎就是白色的顆粒重疊起來的,一片片纖巧的白雪旋轉著,就好像美女優雅的舞姿,劃出一道靈動的光影,就像春日岸邊漂浮的柳絮,親昵地黏著游客的頭發,就像成熟的菖蒲花被風吹散后,在田野的上空無拘束地飄揚,就像岸邊的蘆花,在晴朗的日子里,在青黃交接的葉子里停留。
可是狡獪的風就像一個頑劣的小子,兀自不放棄它的捉弄,它以為雪是一個嬌小而漂亮的女生,纖柔,沒有力量,是可以欺負的,跟在輕盈的雪的后面,呼呼地喘氣,于是白雪翻卷起來,腳步踉蹌。
雪卻不理睬他,她聰明地離開了烏云,靈巧地避開了風的追逐,要尋找一個高潔的地方落腳。如果運氣不好,不幸落入濕潤的坑洼,或者是積水的石凼,就速速地融解;如果碰到了高燥的屋頂,清干的巖石,那雪便漸漸地積聚起來。你看她悠游自在,在海堤的上面,看潮浪,聽潮音;在寂靜的山坳,安寧,就像一個淑女,側耳聽松濤,享受那一份寧靜;在田岸的茅草稈上,頑皮地壓著不怕寒冷的青綠的葉子,順著風,蕩啊蕩的,好像坐秋千,待風住了,她就圈著茅稈的脖子,或者挽著茅稈的腰,緊緊地黏貼著,不愿意松手。
她愿意把枯枝裝扮成春天來臨的樣子,于是快樂地落在樹枝上,光禿禿的枝條,點綴上素華的花,“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便有了暖意。
她希望看見莊稼的種子萌芽,于是溫厚地落在被翻耕過的田野上。勤勞的農家用厚厚的干草覆蓋著,她便伸展四肢,擁抱著大地,用身體來溫暖那些地底下的生靈。犁過的泥土平鋪著,她便順著細碎的裂縫偷偷張望,然后融化了身體,就像母親清涼的乳汁,慢慢地滲透。她似乎聽到種子爆裂的聲音,看到苗頭緩慢地從苞溝里伸出手來,她感覺那些稚嫩的孩子在貪婪地吮吸著乳汁,吱吱著響,于是不由自主地升起了母親的情懷。
她已經感受到春天的氣息了,你看山茶開得正艷,青青的梅枝雖然不見葉子,可是細小的米粒狀花朵密密地擠在樹枝的骨節里,爭先恐后地窺探春天的奧秘。綻放的花瓣是樹枝的舌頭,吻著清涼的雪水,春雪羞澀了,情不自禁地升起了一股情欲,感受到那股暖,使身體融解得更快了。
她甚至著迷清澈的流水,著迷于它嘩嘩地自由奔騰。她希望水位更高一些,流速更快一些,于是奮不顧身地躍入小溪,或者就貼在岸邊,鋪在薄薄的冰層上,她看到了小魚就在巖石的縫隙里靜浮著,瘦瘦的,便有點不舍;她看到了水草不怕冷,調皮地打著手勢,招呼自己,便有點興奮。她甚至看到了獨自坐在岸邊垂釣的漁夫,披著厚厚的蓑衣,暈紅的,粗糙的,像件古董,于是紛紛地黏結上去,讓他成了一座塑像。她還想著自己應該做點什么,可是因為熱情,身體融化得更快了。
風停云霽,可雪漫山遍野都是。遠望山峰,銀裝素裹,雪如粉,如沙,映著綠,映著黃,映著紅,清淡的畫面,滿含著活力。村莊外邊的海堤被遮蓋了,成為長長的痕跡。村莊里,茅屋蓋上了棉被,顯得有點臃腫。茅稈折斷了,枯黃的莖衰敗無力。青翠的竹林里,雪從葉子上悄悄地滑落,沙沙地響。清幽的松林里,一塊一塊的積雪,有的厚厚的,有的露著泥土。角麂張著水靈靈的眼睛,謹慎地沿著小徑走過來,踩裂了冰凍的雪塊,吱嘎吱嘎地響。素潔的土地上,麻雀飛來,興奮地找食,只要得到了一顆果粒,就抑制不住快樂,呼朋引友,嘰嘰喳喳地叫。
人們也從屋子里走出來。孩子們打雪仗,壘雪球,堆雪人,玩得不亦樂乎,大人們頭上戴著皮套子,穿著棉襖,戴著手套,拿著掃帚,提著鏟子,在道路上掃雪。路邊的雪積得很厚,大家充滿了快樂,瑞雪兆豐年,確實是個好兆頭。
春 雨
風水論者說:“東陳有風無水。”這很切合實際。
東陳中學的校園兀然突立在曠野之中,后院是大片的荒地,一無阻擋,風,橫沖直撞,從三樓玻璃窗的細縫里直灌進來,嗚嗚作響。雖然感覺朔風凜冽,但是四周環繞的小山恰如天然的城墻,風只能在高空穿過,風聲好像大噸頭的貨車壓過馬路,好像戰機低空掠過,似乎不在氣勢上壓倒你,決不罷休。然而躺在被窩里,也感覺不出冷。
東陳地處城郊,靠海。校園新建在幸福塘里。塘田是土改時圍成的。1956 年一次臺災,潮水曾經侵襲這里的田地,淹死過兩個瓜農。也許條件惡劣,很多人僅僅把它作為進城工作的跳板。然而我卻不以為然,我在這里蹲了6年,感覺生活很是美好,長久地呆在這里,直到退休,也是一件稱心如意的事情。
不僅是我,就是春天也似乎特別留戀這個美麗的地方。假如說雪是冬天的名片,那么雨水就是春天的笑容。從冬天至春天,就好像運動員50 米跑步,快速,只是一眨眼的時間。這邊風過后,雪還未融化,老天爺就迫不及待地邁過冬的門檻,下起雨來,把天地洗個徹凈,從而宣告春天的來臨。
堆積了這么多天的厚雪,雖然也漸漸地露出一塊塊空地,露出暗黃的地衣,還有黛色的巖石,但是在隱晦的地方,陽光化不開它。可是雨水一來,雪就被洗了個干凈。黑夜里,我仿佛聽見雨水輕輕撫摸厚雪的聲音,錯誤地以為又得落一場新雪,然而拉開窗簾,發現近處隨風搖動的樹葉如此光滑而清爽,而遠處的山峰,就像剛剛洗過臉一樣,深綠及至黛黑。怪不得春汛來臨,水位增高了,小溪口的水奔騰著,跳躍著,像活潑快樂的小鹿,從山谷里飛奔下來。
雨絲似有似無。有,嫩白如陽光映照的蠶絲;無,飄蕩如絲網之間的空隙。人們行走在道路上,卻不打傘,江南的冬天,其實干燥,即使是那雨也是干燥的,灑落在頭上,糾結著的雨珠,顆顆光亮的,伸手就可以抹去。
那雨分明是暖和的。特別是麻雀,已經清醒地感知春天的來臨,總是在雪后幾天,或者雨水剛停,陽光清淡的日子里,在露出的幾塊空地里高興地跳躍。有的蹲在電線桿上,把一雙翅膀包裹得緊緊的,有的啄食地面上的草籽,人影掠過,竟然也不害怕,好像小孩子,并且是個機靈鬼,帶著狡黠的眼光,勇敢地和你對望。空氣十分清新,聲音十分清脆。
地氣也返暖了,很明顯地長出了小草,當地人稱為“青衣”,大地穿上了衣服,這多么富有創意啊,人們對土地總是情不自禁地附加上自己的情感。“草色遙看近卻無”,雖然切合,但是這個詞組更形象;《滿井游記》 里說,“淺鬣寸許”,雖然形象,可是這個詞組更人格化。走近看時,細如牛毛的草尖黏著珍珠一樣的水珠,晶瑩澄澈。
深秋撒下的種子,這時候應該爆出了嫩芽,卻藏在雪被下,在裂開的縫隙里,黃綠的嫩芽在偷偷地張望。干黃的枯茅,萌發的新芽包裹在芯子中。花草樹木喝飽了汁水,顯得鼓脹欲滴。雁來紅抽出的嫩枝如花朵一樣嫣紅,好像喝醉了酒的少女,酡紅的臉一片光亮。山茶的落紅鋪滿地面,可是枝頭上仍然有密密麻麻郁結著的蒂頭,包裹著的深紅,粉紅,爭奇斗艷。
江南二月,是春的發端。暮色初合時的那聲春雷,大家都說是驚蟄,是蒼龍醒來睜開眼睛時呼出的第一口氣息。室內的滴水觀音,由于沒有及時澆水,缺少甘露,萎靡不振已久,這時候也恢復了生機勃勃的景象,葉子綠油油的,葉子的邊沿又有了流淌的水跡。
這春天卻流連人間,久久地不愿意離開。雨水的情感也細膩,她經閩廣,至滬浙,在秦嶺掉頭向南,又情不自禁地回到這里。“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在早春時,我曾經拉著兒子去嶺下桃花渡,那時寒流陣陣,桃枝上結滿了骨朵,卻不開放,花苞呈現暗紅色,顯得秾艷而深沉,大概環境越是惡劣,性格就越顯得剛正,越不易散敗,所以現在開放得如此熱烈奔放。
忽然覺得朱仕玠隱居楊林,結廬授徒,雖生活困頓,但是巧洋之涵澹蕭瑟,也確實是吸引他的根本。其他如彭息庵,獨居小齋,一爐香,一瓶插花的水,安心于鄉村抄書,雄心不就,蝸居于一室,實在是生活中有使精神專一的東西。至于謝南岡,雖然詩文高邃古澀,包孕深遠,卻因屢次落第,屢次被嘲笑而目盲身死,覺得又欠缺點什么了。

春 曉
黎明驅趕黑暗的腳步總是如此神速。
太陽還未升起來,地平線下已經泛起溫暖的光,云朵被渲染得金碧輝煌。隨著天空射下五彩的光線,第一滴雪水順著瓦壟,在屋檐際滴落,伴著清晨的靜寂,臺階上一聲響,清脆而明晰。
是誰最先感知春曉的快樂?
是溪澗的清水跳躍著來報告喜訊,你看他正滿溢過低矮的壟,帶走溪澗洄漩里累積的雜木和漂浮的泡沫,對冬季的殘骸做一篇哀悼的祭文。還是寒雪里的紅梅,第一朵花苞被驚醒。
是公雞在寂寥的黑暗里觸摸到了夜靜,嗅到了黎明的氣息,在人們還沉浸在甜甜的夢鄉里,就開始心動。高昂的激啼聲,在夜空里,如波浪的漣漪一圈圈地蕩漾開來。還是枝頭的烏鵲,月明星稀產生的錯覺,繞樹三匝后,回到象征性的窩,虬曲的腳爪緊扣樹枝,再重新打個盹。
是披上綠衣的大地睜開惺忪的眼,還是鄉間老農播下一壟地的種子,悄悄地拱開了泥土的裂縫。
是裹著羽絨的鴨子感知水的溫暖,還是魚兒領會到春的快樂,你看它在水底下嬉戲,翻轉柔軟的身體,炫耀一身的銀鱗白,或者悄悄地浮上水面,嘴唇翕合著吞下一顆泡沫,轉身時尾翼閃著一縷晶亮的紅。
是燕子從北方歸來,惦念著燕窩里的孩子,在原野上空盤旋,尋找冬眠中醒來的蟲子;還是臭鼬從地洞中鉆出來,在嫩綠的小草中穿梭,或者在太陽底下慵懶地曬肚子。
是山地堆積的厚厚的樹葉,一冬的腐爛,滲入地底,化為養料,為母樹光禿的枝條,發出生的氣息而自豪;還是柴梗子上的苞芽、貼地的竹筍鉆出嫩黃的簇,在唱著一首新生的歌曲。
我在春曉里獨自行走,心不存濁氣,輕松自在。春曉在鄉野的每個角落里。
森林的破曉,是晨嵐氤氳。白色的山霧,上下升騰,把山尖包裹起來。似乎是美女梳洗,長長的頭發順風飄拂,在撩開的隙縫里,我看到楓葉的那一抹姹紅,就像美女醉酒時酡紅色的臉,或者是山體黛綠,好像是剛剛吃飽了桑葉的蠶蛹,嘴里吐出的蠶絲,在風中一絲絲搖曳。
河流和田野的破曉是水霧云騰。稻谷經過一夜的呼吸,身體內部的熱量醞釀成熱烈的情感,化作水汽在葉子里纏繞。即使是河道,整個水面如仙宮,云霧妖嬈。小草被水汽纏繞,好像被母親的手撫摸,溫暖的、潤澤的、細膩的、親親的。
村莊的破曉是炊煙。燈光次第亮起來,窗口里透露出來,黃紅色的,漸漸地隱于曙光。悠長的巷弄,隱隱的輪廓明了起來,腳步聲輕輕的、散散的、雜亂的,貪睡的孩子,靠著枕頭,數落著腳步聲,從少到多的變化。漁人碼頭,在田坎下,圍城的塘岸吻著起伏的潮汐。小船在晃動,蕩漾的海水泛起粼粼的波光。船槳搖動,頓起欸乃之聲。其實鴨子比人還勤勞,早浮在水面上,也像一只小船,伸著的脖子,翹起的尾巴刷,順著波浪的褶皺起沉。它見慣了碼頭的熱鬧,一點也不驚慌,沉穩的眼光盯著人們忙亂的手。小雞也起得早,從窠里出來,開始是悠悠然在道地里東蕩西逛,后來,它扇一下翅膀,就邁出門檻,也不叫喚,專注地在碎石子堆里玩耍。
喜鵲的黎明在屋檐頭。旭日早升,朝霞燦爛。天空中的雞蛋黃和薔薇紅,一點也不刺眼,而且還有溫暖的感覺。有人還縮在被窩里酣睡,它們已經密密麻麻地站立在屋檐上,高聲歌唱,歌聲里充滿了重見天日的歡樂。它們也會相互打鬧,嘰嘰喳喳的,一只鳥的翅膀打著了兄弟的翅膀,于是開始互相追逐。一只鳥的嫩喙在啄搜女兒身上的蟲子,小鳥卻不耐煩,瘦小的身軀在瓦楞上跳了幾跳,躲得遠遠的。
春天的黎明啊,有誰能夠理解我對你的渴望,渴望你帶給我的快樂,從秋的干旱冬的寒冷一路走來,看見一片汁水欲脹破的嫩葉,墨綠而豐腴;一朵雨露滋潤的鮮花,肌理柔潤;一條蟲子從睡夢中醒來,在低低地呻吟;一只鳥兒在清新的空氣里舒放心靈,自由歌唱;甚至一群麻雀目中無人,一隊白鵝邁著八字步,打著官腔,都讓我沉睡的心開始復蘇,從此干渴的心底鮮潤,久已麻木的雙手撥拉出那一串和諧的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