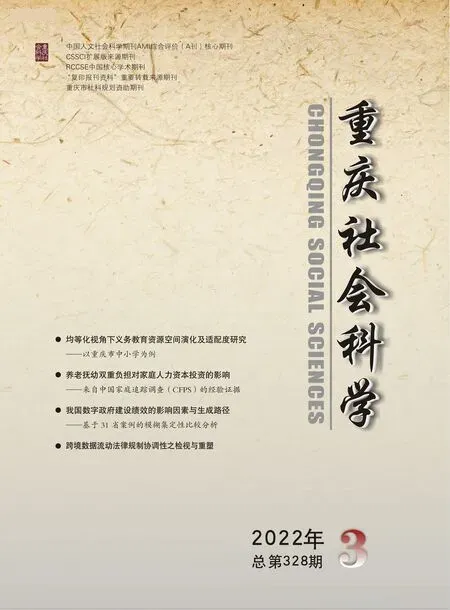試論康德《法權論》之闡釋路向
——兼評契約論與自然法闡釋
20 世紀后半葉,西方學界重新燃起了對康德法哲學的興趣。 學界對于康德法哲學的理論推進以及批判,大多以1797 年出版的《法權論》
作為核心文本,但就目前來看,學者們對《法權論》的闡釋路向的判定存在較大爭論,難以形成共識,這直接影響了后續理論的解讀方向。
法權(Recht)是康德法哲學的核心概念,它不單指主體擁有的具體的權利(right),而是意味著一種外在合法則性的整體公民狀態
。 《法權論》不單是對法律的討論,而且是一種政治學說,對它的闡釋包含著對康德關于政治合法性之形式與范圍的理解
。就政治合法性之形式而言,學界的闡釋路向大體包括以墨菲、凱爾斯汀為代表的契約論闡釋
與以路德維希、馬爾霍蘭為代表的自然法闡釋
,兩者的分歧在于,康德的法權思想更接近于社會契約論傳統還是諸如格勞秀斯的自然法傳統。 契約論闡釋路向采取的是經驗主義視角,顯然與康德哲學的“先驗性”相悖,并且在康德文本的處理上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自然法闡釋路向雖然選擇了意志作為法權之根據,但其論證是從細節入手,鮮有提及康德關于人的先天實踐能力的批判性預設,缺乏整體性關注。 對康德而言,實踐領域的批判對象是人的欲求能力
,目的是為人的先天實踐能力重新劃定界限,并試圖在意志(Wille)與任意(Willkür)的實踐的自由的劃分基礎上展開道德學說的演繹。 法權與德行同屬道德問題,都建立在實踐的自由的基礎上,因此,康德《法權論》的闡釋無法繞過這一前提,應當采取一種先驗路向。
本文嘗試闡明康德《法權論》之闡釋路向,擬從實踐的自由著手,厘清它在康德法哲學語境下的功能定位與準確含義,隨后說明契約論闡釋與自然法闡釋的局限性,以及何為先驗闡釋路向,它在何種意義上實現了對意志論與理性主義的超越。 由于主題所限,本文主要探討《法權論》關于政治合法性之形式的闡釋,政治合法性之范圍(即“永久和平”)僅在文章最后一部分有所提及。
一、實踐的自由:法權何以可能的先天條件
康德的《法權論》是對外在合法性行為之形而上學的要素闡明,對它的闡釋首先找到它的邏輯起點,也就是法權之所以為法權的先天條件。 實際上,法權可以被視為一種先驗的實踐知識,并且實踐的自由,更確切地說,自由的意志充當了其演繹的最終根據。
(一)法權本質上是一種先驗的實踐知識
康德哲學是批判哲學,批判的本質就在于獲悉關于人的諸先天能力的來源、范圍以及種類的先驗知識。 “先驗”(transzendental)在一般意義上與“先天”(a priori)相同,指先于經驗的(邏輯上而非時間上在先)。 但康德明確指出,“先驗”與“先天”這兩個術語是有區別的:“不是說任意一種先天知識都須稱為先驗的,只有那種使我們認識到某些表象(直觀或概念)只是先天地被運用或只是先天地才可能的、并且認識到何以是這樣的先天知識,才稱之為先驗的(這就是知識的先天可能性或知識的先天運用)。 ”(A56=B80-81)
先驗知識也是先天知識,但先天知識并不都是先驗知識。先天知識指那些沒有摻雜任何經驗性的,具有普遍性的知識。 先驗知識是對先天知識本身加以研究的知識,探究這些知識成為知識的條件,即必須運用于經驗之上,以及如何運用于經驗之上
。
先驗知識在理論領域的考察對象是人的先天認識能力,在實踐領域則是人的先天實踐能力,前者回答“這是什么”的問題,后者回答“這應當是什么”的問題
。 經過康德批判的人的實踐能力作為實踐行為的先天根據,是他的整個實踐哲學的根基,那么,依據其所確立的實踐法則,也就是最高的道德法則,自然而然應當適用于法權與德行領域,這也是《道德形而上學》由《法權論》與《德行論》兩部分構成的原因之一。 但有學者質疑,法權并不建立在道德法則的基礎之上,《法權論》可獨立于《道德形而上學》
。 這一觀點(分離命題)有兩個最主要的論據:其一, 法權的最高原則是 “分析的”(analytisch), 而德行的最高原則是綜合的 (synthetisch)(6:396)。 “分析的”指法權原則可以從法權概念(外在自由概念)中直接推導出來,無須借助其他東西,因此,法權獨立于康德的道德理論。 其二,康德在“法權論導論”中指出,法權的普遍原則是一個“根本無法得到進一步證明的公設”(6:231)。 這意味著,法權的普遍原則自身構成了一個獨立的體系,它無需道德法則即可證明自己。 那么,是否康德的法權就具有完全的獨立性呢? 下文的觀點將表明,康德的法權的確一定程度上獨立于道德理論,但它的有限的獨立性并不能消除其終究是以道德為基礎的事實。
第一,根據《道德形而上學》的結構安排,康德在導論中提出了一些法權與德行共有的“預備概念”,例如,自由、義務、法則等,這些概念內在于(廣義的)道德之中。 根據法權與德行領域的性質差異,自由被劃分為外在的自由與內在的自由,兩者都屬于道德形而上學的整全性的自由。 此外,康德由自由概念引出了義務、法則,自由主要表現為一種普遍性的義務,普遍性指的是法則的普遍性。 自由或道德的普遍性法則,即意志的普遍立法法則,被視作法權義務與德行義務共同遵循的道德領域的最高法則。
堤防工程中首先要進行地基鋪填,碾壓好的合成土料鋪在第一層,然后分段之后在地基上鋪一層土料,碾壓一層鋪一層,層層鋪填層層碾壓,鋪填好地基之后還要對側面進行防水防滲處理,構筑混凝土防滲墻,注意地基鋪填的寬度、厚度都要滿足施工要求。
7.2.13炭疽葉枯病是近年來我國蘋果廣泛發生的突發性新病害,在貴州中部蘋果產區已經發現有該病危害。炭疽葉枯病在高溫高濕的氣候條件下發病較重,葉片和果實都會受害,且傳播速度很快,炭疽病菌在病果、落葉和病枝上越冬,來年降雨后傳染開來,比其他葉部病害更難防治,目前處于可防不可治的階段,主要本著預防控制為主,防治為輔的方針。
第三,所有外在的法權以自由或者道德為最高標準,還表現在康德對法權的類型劃分上。康德首先在形式上對法權作出了一般劃分:“法權分為自然法權和實證法權,前者建立在全然的先天原則之上,后者來自立法者的意志。 ”(6:237)在康德看來,法權的劃分還能在“功能”上進行闡明:“作為使他人承擔義務的(道德的)能力,亦即作為對他人的一個法律根據的法權,其上位的劃分就是生而具有的法權和獲得的法權,前者是不依賴于一切法權行為而自然歸于每個人的法權;后者是需要這樣一種法權行為的法權。 ”(6:237)“生而具有的法權”和“自然法權”,“獲得的法權”和“實證法權”分別有一種對應關系。 “生而具有的法權”也就是內在的“我的”和“你的”的法權,這種法權只有一種,即自由
。 自由(法權)就是所有具體的、實證的法權的最終標準,“一旦對獲得的法權發生了爭執,出現了問題,誰有責任作出證明……可以在方法上像依據不同的法權條文那樣援引生而具有的自由法權”(6:238)。 “生而具有的法權”是更為內在的、出于本心的,它意味著一種主體的能動性,而“獲得的法權”,也就是實證法權,是更為外在的,它意味著一種被動的“束縛”。 因此,可以認為,康德試圖通過法權的形式與內容的劃分來追溯法權的道德根基,自由是法權成立的最高標準。
簡而言之,法權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但它僅限于規范范圍上的行為合法性
。 康德從先驗的角度,將法權之為法權的先天條件,以及它的規范力來源,都建立在其道德理論之上,法權法則最終指向的是道德法則。 那么,康德對于人的先天實踐能力(實踐的自由)的定義是適用于法權領域的,對《法權論》的闡釋自然應當以準確把握實踐的自由的內涵為前提。
(二)意志(Wille)與任意(Willkür)
自然法闡釋路向將關注點轉向了法權原則的形式性,也就是自由主體之間的關系,僅就這一點上來說,它也可以被稱為先驗闡釋路向,任何經驗性的內容并不是其考慮的重點。 先驗闡釋路向的獨特意義不僅在于如何理解財產權的成立,還能看出經驗在康德法權學說中的地位。 經驗主義始終是康德哲學的批判對象,在法哲學中,這種批判反映在康德對于近代自然法學或者說意志論的超越上。 康德首先接受了霍布斯關于自然狀態的描述,指出“自然狀態其實是一種戰爭狀態,也就是說,盡管并非一直有敵對行為之爆發,卻不斷有敵對行為之威脅”(4:349)但康德認為人們簽訂契約并進入公民狀態,并不應當以自身的利益為動機,后者的社會契約思想是經驗主義的。 近代的經驗主義來自從神學形態向世俗形態轉化的意志論傳統,意志論強調人的主觀意志,具體指每一個公民本人的意志,但問題在于,它沒有區分、排除經驗的理性與情感,使得人們對意志的理解陷入經驗主義。 先驗闡釋路向在公民狀態的論證上選擇了排除一切經驗的意志,公民狀態的建立不以其他經驗內容為目的,因而不是偶然的,它作為純粹實踐理性的演繹結果,其本身就是目的。在這里,“先驗”的意義就在于對經驗主義的超越,人作為自由主體必然進入公民狀態,法權關系的形成并不來源于我們“選擇”簽訂的社會契約。
康德首先定義了人的任意,并將其與動物的任意進行比較:“在實踐理解中的自由就是任意性對于由感性沖動而來的強迫的獨立性。 因為一種任意就其(通過感性的動因)被病理學地刺激起來而言,是感性的;如果它能夠成為在病理學上被迫的,它就叫動物性的。 ”(A534=B562)人和動物的活動都是一種任意并且是帶有感性的。 動物的任意完全受到病理學因素的強迫,是被動的,而人的任意是一種自由的任意,代表著自由選擇的能力,能夠獨立于“由感性沖動而來的強迫”。 動物的任意對應著本能,自由的任意對應著一般的實踐理性,在康德看來,兩者都有著專屬于自身的使命。 本能的使命就在于追求幸福,這是大自然的本來目的,“因為比起每次都通過理性才能做到,這種被造物必須在這一意圖中實施出來的所有的行動,以及他的行為的全部規則,若有本能來給他擬定將會更為準確得多”(4:395)。康德在此處接受了由盧梭開啟的浪漫主義的觀念,即對幸福的追求不需要理性的干涉。 但不同的是,康德并沒有因此貶低理性,而是進一步挖掘理性自身的價值。 在康德看來,“理性必定具有其真正的使命,這絕不是產生一個作為其它目的的手段的意志,而是產生一種自在的本身就善良的意志”(4:396)。 對理性的使用也有層次之分,如果僅僅將理性作為手段而追求其它目的,那么我們能夠掌握的只是“技術上實踐的規則”,盡管屬于一般的實踐理性,但它不屬于實踐哲學。 然而,一般的實踐理性已經暗含著純粹實踐理性的種子,我們只要把任意完全置于理性規則之上,不是為了其他感性的目的,而是使得一切感性都服從于純粹實踐理性自身的要求,那么,就能直接反映出人的意志(自由意志)的存在。
康德進一步區分了意志與任意。 貝克認為:“康德并未挑出這兩個概念, 然后形式性地展開它們的彼此關系。 他對它們加以一并處理,而從未清晰地表明哪一個才是他正在討論的對象。 ”
但通常來看,康德在“意志”概念的使用上有著狹義與廣義之分。 狹義上,意志與任意分別承擔著立法的機能與執行的機能。 意志為任意提供規定根據,它本身是絕對的,不再有任何其他的規定根據。 任意直接與行動相關,它既能夠因感性刺激而產生行為,也能夠以純粹意志作為行為的規定根據。 這樣我們就能夠理解康德為什么宣稱:“只與法則相關的意志,既不能被稱為自由的也不能被稱為不自由的,……只有任意才能被稱作自由的。”(6:226)意志不關注行為本身,注重為行為的準則立法。 任意之所以是自由的,就在于它是一種自由選擇行為的能力。 廣義上,意志代表著一種統合立法與執行的整體能力,只有廣義的意志才具有“自律”的特性,這種意義上的意志才能說為自己立法
。
第二,法權成立的最高標準是道德的,而非自然的。 根據康德的闡述:“就這些法則僅僅涉及純然外在的行動及其合法性而言,它們叫作法學的;但是如果它們要求,它們(法則)本身應當是行動的規定根據,那么,它就是倫理的。 這樣一來,人們就說:與前者的一致叫作行動的合法性,與后者的一致叫作行動的道德性。 ”(6:214)就規范的對象而言,在法權的領域中,行為的允許無關乎道德與否,只需要符合法權法則的規定。 然而,法權的規范有效性,也就是其強制力的成立,是建立在行為的道德性基礎上的。 如果一個行為,它是一個自然而非自由事件,即它不具有道德意義,那么,法權就無法對其產生規范力,進而無法將這一行為歸責于任意主體。 人區別于自然界的其他事物的關鍵就在于,他是一個自由的存在者,是可以為其行為承擔責任的存在者。 人之所以是自由的存在者,就在于他是理性的,服從于理性的法則,其行為表現為“應當”。 因此,盡管法權僅要求外在行為的合法性,但法權最終是道德的,是人的自由本質賦予其規范性。
在康德看來,盡管意志與任意同為實踐的自由,真正嚴格意義上的自由并不是能夠自由選擇行為的、任意的自由,而只能是具有超越一切感性欲求之上的,能夠自我立法的意志的自由。 因此,法權與德行同屬自由的實踐領域,真正探尋《法權論》之闡釋路向,需要回到康德所設立的人的實踐行為的先天標準,從實踐的自由,尤其是意志著手,方可得出結論。
二、契約論闡釋路向:任意(Willkür)作為道德之本質
討論實踐的自由概念的目的是厘清康德對于作為自由主體的人的道德本質的理解, 這直接關系到《法權論》闡釋路向的選擇。 不同闡釋路向的差異取決于對實踐的自由概念的取舍,究竟是意志還是任意決定了人的道德本質。 因此,要判斷哪一種闡釋路向符合康德文本的論證邏輯,并且能夠內在地一以貫之,首先必須清楚闡釋的邏輯起點是什么,進而分析其闡釋依據。
(一)基于理性選擇的社會契約
契約論闡釋路向認為,應當將康德解讀為一個社會契約論者,顧名思義,康德關于公民狀態建立的形式基礎在于社會契約的簽訂,而社會契約是體現人的理性選擇的理想模式
。契約論闡釋路向的代表人物是墨菲與凱爾斯汀,之所以如此理解康德的《法權論》,其原因就在于他們都強調康德語境下的道德之本質應當是人的自由選擇行為的能力,即任意,而非具有立法能力的意志。 實際上,兩位學者都缺乏對康德關于實踐的自由概念的整體關注,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本選擇以及關注點的局限性所造成的。
[3]王磊,姚駿.基于HTML5的移動病房WebApp的設計與實現[J].工業控制計算機,2017,30(05):143-144+148.
當今社會是一個多元的社會,具象美術、意象美術都得到了較好的發展,抽象美術還是個弱項。這個弱項由弱變強的時候應該就是陶瓷美術面貎發生根本改變之日。我們期待這個春天早日到來。
同樣采取契約論闡釋路向的凱爾斯汀關注的主要文本是《道德形而上學》,他的《良好的自由秩序》是全面研究康德政治法律思想的重要著作。 凱爾斯汀較為注重《道德形而上學》自身的論證邏輯,但他在處理文本中某些含混之處時,轉而訴諸了大量康德為澄清其思想而準備的預備性筆記。 實際上,這些預備性筆記的時間跨度長達30 年之久,以至于并不能完全保證康德思想的連貫性
。 預備性筆記著重提到了關于外在對象占有的正反命題,正命題支持一種理智性占有的觀念,反命題支持一種經驗性占有的觀念
,而在這些筆記中并沒有提出任何有效的解決辦法。 凱爾斯汀的方法是支持正命題,即理智性占有,并進而形成了一種規定主體—客體關系的財產權觀念。 凱爾斯汀認為,康德正是基于這種財產權觀念展開了政治合法性之形式的論述,主體間的政治義務就是通過達成一致的同意來約束選擇自由,“一個契約的必要性源自這樣一種要求,即使得對于外在對象的單方面的占有能夠與所有人的立法意志相一致”
。 顯然,凱爾斯汀將公民狀態的形成建立在人們的理性同意的基礎之上,同意的目的就在于保護個人的自由選擇,而這也是所有人的聯合意志的立法對象。
墨菲的《康德:權利哲學》一書是英美世界中具有代表性的闡釋康德法哲學的著作,他在康德文本的選擇上主要集中于《實踐理性批判》與《道德形而上學奠基》,而《道德形而上學》則處于次要位置。 墨菲的論證始于對兩個問題的關注,其一,康德在討論自由與道德法則關系時的“循環論證”;其二,自黑格爾開始的對絕對命令的批判,他們認為康德的最高道德法則是一種空洞的形式主義,沒有任何實質內容。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學奠基》的第三章中“承認”了他的循環論證:“人們必須坦率地承認,這樣一種循環看起來是無法擺脫的。 我們假定自己在起作用的原因的秩序中是自由的,是為了在道德法則之下的目的秩序中設想自己,接著,我們把自己設想為服從這些法則的,是因為我們把意志自由賦予了自己。 ”(4:450)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假定自由是為了道德,但我們服從道德法則又是為了自由,自由與道德法則互為根據,在邏輯上這顯然就是一種循環論證。 墨菲在解決這一困境的時候并沒有采取康德的“綜合”方法,而是提出了一種實質性而非形式性的自由概念。 墨菲認為:“如果我們能夠證明是任意,而非意志賦予人以尊嚴,那么我們將使康德對于道德的刻畫免于循環論證的指責。 因而人的尊嚴將不再源于他能夠成為道德存在者的能力, 而是源于他選擇任何行為過程的自我立法的能力。 ”
墨菲以康德描述意志的話語來定義任意,賦予人以尊嚴的是自由的任意,道德之本質就在于“個人自由選擇行為的能力”,而非立法的能力。 此外,墨菲指出,個人自由選擇的目的是“人性的本質性目的”,即幸福和完善,其來源于絕對命令的第二項變形公式
,而正是這一目的構成了絕對命令的實質內容,因此,針對康德最高道德法則的形式主義批判并不成立。 可以看出,在墨菲那里,并不是具有普遍性的法則限制著個人的選擇,而是個人的選擇及其本質性目的決定了哪些法則是可以被普遍接受的,政府、法權是理性同意的產物,社會契約正是為了滿足這一需求而設立。
墨菲與凱爾斯汀盡管在文本的選擇以及闡釋的起點上有所差別, 但兩者關于政治合法性之形式的闡釋都是建立在基于有限選擇的契約觀念之上的。 他們的解讀都傾向于將體現人的自由選擇能力的任意作為康德語境下法權狀態的核心觀念,法權概念在這并不具有無條件的有效性,也不是純粹實踐理性的一種先天主張,其論證邏輯是通過訴諸基于人的理性選擇的社會契約來回答政治合法性之形式的問題。
(二)一種經驗主義的自我消解
對經典文本的闡釋,應當首先回到文本自身,盡量遵循作者本人的論證邏輯。 契約論闡釋路向的問題就在于它對一些關鍵問題的處理并沒有關注康德本人的解釋,而是試圖以完全悖于康德哲學基本特征的方式來探尋一條全新的解釋路徑,因而,所得出結論的合理性是不無疑問的。
目前來看,康德法哲學研究的經驗主義徑路并不少見,而這也是對康德產生懷疑的重要來源。部分學者認為《道德形而上學》的寫作是“不純粹的”(impure),與康德早期的批判性作品的形而上學特征大相徑庭
。 然而,康德始終都強調意志與任意的劃分,真正的自由就是自我立法,就是自律。 如果不是自我立法,那么自由就不再是自由,任意只是行為選擇上的自由,它表面上看起來是自由的,若不以意志作為規定根據,僅僅只是為了更大的、長遠的利益,那么這種自由馬上就會自我取消,終究是被外在的其他目的所決定的。 康德主張:“法權的普遍法則……盡管是一條賦予我責任的法則,但卻根本沒有指望、更沒有要求我為了這種責任而把我的自由限制在那些條件上,而是理性僅說,我的自由在其理念上被限制在上面,而且事實上它也可能受到他人的限制;而且理性把這說成是一個無法得到進一步證明的公設。”(6:231)盡管法權僅考慮外在的合法性問題,并不要求主觀上的動機,但就其要求的限制而言,是來自于純粹的實踐理性,即意志的理念自身的
。 如果法權的成立是建立在有條件的契約觀念之上,那么法權就不是自在地就存在的,因而也不是一個“無法得到進一步證明的公設”。 契約論闡釋路向以任意作為道德的本質,進而也作為法權的本質,顯然難以符合康德自己的主張,經驗主義闡釋的最終結果將是不可避免地自我消解于某一外在的有限目的之中。
凱爾斯汀將康德視為一位嚴肅的政治哲學家, 但他本人對康德文本的處理可能是不嚴肅的。 凱爾斯汀注意到了財產權觀念之于康德《法權論》的重要意義,進而重點討論了理智性占有的命題, 但問題仍在于他對外在對象占有的二律背反的解決上是非康德式的。 康德認為,“理智性占有的正命題與經驗性占有的反命題都為真”(6:255),這一判斷的根據依然是物自體與現象界的劃分。 經驗性占有僅在現象界成立,并且體現的是人與物的關系,理智性占有“必須從實踐理性的公設中得出……實踐理性不需要直觀,乃至先天直觀,僅通過自由法則所授權的對經驗的排除來擴展自身,這樣就能提出先天綜合的法權命題”(6:255)。 理智性占有表面上與財產權相關,毋寧說是對法權何以成立的先驗演繹,本質上,法權成立的先天條件考慮的是排除一切經驗性條件的意志與意志的關系,也就是作為自由主體的人與人的關系,這種關系實際上就是實踐理性的公設。凱爾斯汀籠統地否定了經驗性占有,并將理智性占有乃至財產權觀念解釋為人對物的關系,與墨菲類似,“限縮”了康德的論證邏輯,以“經驗”去理解康德的“形而上學”。
根據隸屬函數值的大小可以得出不同辣椒資源的耐鹽性,10個耐鹽性強的辣椒資源中,其中87號自交混收(ZY16-15)的隸屬函數值最大為0.92,說明耐鹽性最強,其他的隸屬函數值依次為0.92,0.91,0.91,0.88,0.86,0.85,0.84,0.83,0.83;26號自交混收(華混5-5)的隸屬函數值最小為0,說明26號自交混收(華混5-5)極不耐鹽。
墨菲在處理康德的循環論證時所采取的辦法是將重心轉向任意, 從人的自由選擇能力及其本質性目的來論證政治合法性之形式的問題。 然而,康德只是表面上承認了自己的循環論證,經過“綜合”辦法的解讀,其論證顯然是成立的,并且意志仍舊是人之道德行為的本質。 康德認為,“自由和意志的自我立法都是自律,因而是可互換的概念,但正因如此,一個不能用來解釋另一個,且提供論證上的根據,而最多只能為了邏輯的意圖,把同一對象的那些顯得不同的表象歸結為一個唯一的概念”(4:450)。 在這里,自由指的是自我立法的能力,而自律就是道德律,那么自由和道德律就等同了,因而涉及自由與道德律的關系也是循環論證。 但康德強調這種等同只是“為了邏輯的意圖”,這就是說循環論證只是對于形式邏輯而言的,只關系到概念間的邏輯關系,并沒有考慮到本體論的關系。 形式邏輯的自相矛盾或循環論證,在其他方面(例如本體論)上是有意義的,這在康德那里并不少見,《純粹理性批判》中的二律背反采取的就是這一解決思路,即“同一性命題在形式邏輯上是分析的,但在先驗邏輯中卻是綜合的,具有重要的認識論意義”
。 就此而言,自由和道德律雖然在形式邏輯上可以互換,但在本體論的意義上仍有不同。 我們為了道德律而假定自由,此時的自由作為一種消極的自由,它停留在智性世界(intellektuellen Welt)
中,而我們服從道德律是為了自由,這說明此時的自由是一種積極的自由,它是要影響感性世界(Sinnenwelt)的。因此,康德采取了物自體與現象界的不同立場,在認識論的意義上假定一種先驗的自由,在實踐論的意義上,我們的道德行為需要以實踐的自由為基礎,進而“綜合”智性世界與感性世界,這基本上就是康德在第三個二律背反上所采取的思路。 墨菲從一開始就接受了康德在討論自由與道德法則關系時循環論證的“錯誤”,在他看來,如果康德不采取一種經驗主義的論證方向,那么這一“錯誤”就是無法避免的。 物自體與現象界的劃分在墨菲那是不存在的,或者是無需考慮的,唯有完全根植于經驗世界的任意才是人之為人的本質所在。 但是,物自體與現象界的劃分正是康德哲學的根本,人的道德行為之所以可能的先天條件就在于物自體的超越性,墨菲站在經驗的視角上的闡釋是與康德哲學難以相容的,因而不得不說是難以讓人接受的。
三、先驗闡釋路向:基于意志(Wille)的法權演繹
據前文所述,康德哲學的關注點始終是“形而上學”,它在理論與實踐維度一以貫之的是其批判與先驗的“方法論”,這一標準在如此“實踐”的法哲學中也完全適用。 法權本質上是一種先驗的實踐知識。 先驗闡釋路向之于康德《法權論》的意義就在于其“先驗性”:一方面,它對法權的演繹是基于排除一切經驗的意志的, 得出的是關于法權的具有普遍性的知識; 另一方面,先于經驗的知識并沒有脫離人的認識范圍,也就是說,“先驗”仍然是與經驗相關的,人的(自由)意志是能夠被“反思”到的。 概言之,先驗闡釋路向是完全康德式的闡釋路向,通過它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康德的法權學說是在與何者的“對話”中形成的,以及在哪些方面作出了改進。
(一)先驗維度的社會契約
先驗闡釋路向的“先驗性”首先在于對人的先天實踐能力,即實踐的自由的關注。 康德的法權以人的意志而非任意為最終根據,整個法權體系的論證是在“先驗”的維度上進行的,這主要反映在財產權的演繹中。 盡管較少提及康德關于人的實踐的自由的預設,與契約論闡釋路向相對立的自然法闡釋路向在理智性占有的論證中著重提到了意志,在這一點上遵從了康德原本的論證邏輯。 自然法闡釋路向的代表人物路德維希在其修訂的1986 年版 《法權論》中指出,由于一些印刷上的錯誤,需要重構該文本的體系結構
。 路德維希將《法權論》第2 節的內容移到了第6 節“純然的合法占有(本體性占有)的概念的演繹”中,并且指出正是第6 節關于理智性占有(本體性占有)的演繹揭示出《法權論》并不是一本實用的法律手冊。 不同于凱爾斯汀,路德維希保留了理智性占有的主體——主體向度,理智性占有之所以必然是可能的,不是因為主體對外在對象的一種支配權主張,而是如果沒有理智性占有的觀念,就不能對主體與主體間的外在自由進行規制。 在路德維希看來,理智性占有或者法權關系源自純粹實踐理性,“如果它們(法權原則)是從純粹實踐理性推演出來的話,那么法權原則必定是形式的。 ”
法權關系就是依據純粹實踐理性原則本身的形式約束所展開的本體論關系,它所反映的是主體間的意志的關系。 依照這種闡釋路向,理智性占有反映的是整體的意志的演繹,意志為自身提供行為根據,而從自然狀態到公民狀態的轉變所依據的應當是純粹的意志,因而這種轉變是先天必然的,所謂契約只是預設的政治合法性的形式的理念
。
自由概念是貫穿康德三大批判的核心概念,它分為先驗的自由、實踐的自由與自由感
。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完成了對先驗的自由的設定,并進一步過渡到了實踐的自由。 《純粹理性批判》的第三個二律背反的正題指出:“自然律的因果性并不是世界的全部現象都可以由之推出的唯一因果性。 有必要假定一種由自由而來的因果性來解釋這些現象。 ”(A444=B472)自然因果律需要追溯更早的原因,而這種追溯是無止境的,為了滿足充分理由律,進而能夠解釋這個世界的現實存在,我們必須假設一個純粹自發的自由因。 為此,我們同樣可以為人的因果序列設定一個先驗的自由理念,給人的經驗性行為提供可歸責性(自由選擇的能力,即任意)的真正根據,這對于實踐的自由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這樣先驗的自由理念在另一種意義上(實踐意義)具有了實在性,康德將關注點從人的認識能力轉向了人的實踐能力。
(二)認知主義的自由概念
先驗闡釋路向強調從先于經驗的純粹理性的實踐自由出發, 排除一切經驗內容構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法權,進而運用于現實經驗中,這是基本符合康德本人的論證邏輯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實踐的自由對康德的法權,以及公民狀態的闡釋并不是單向性的,在這之中,人自身能夠通過反思來“認識”到純粹的自由意志,這種闡釋應當是雙向互動的。
我們把建立在人的反思的基礎上的意志歸為認知主義的自由概念。有學者認為,康德實際上是一名道德實在論者,在康德看來,“道德的基礎存在于一種已經被確立起來的結構——理性存在者基于本性就擁有的結構——之中”
。 根據道德實在論,道德或者自由之存在,獨立于任何一個有可能受制于他們的人。 如果我們接受了道德實在論的觀點,道德—自由—行為(選擇)的關系就會是單向的,既然道德本身就已經存在了,自由所呈現給我們的是一種確定了的指令,我們也必然會這樣去行動。 然而,這種觀點盡管可以滿足先驗闡釋路向的必然性要求,但卻忽視了“先驗”的認識論特征,即人的自我批判的認知活動。 如果接受道德實在論的論證邏輯,自由就不再是實踐的,它只是懸掛于人的理性范圍之外的超驗理念,人的行動只能是被動地服從指令。
認知主義的自由概念并不是說康德試圖獲得任何有關自由的理論知識, 只意味著人能夠通過自我反思“認識”到超出經驗的自由的存在,并且使其在實踐領域證明人這一主體的道德性。 康德主要在三個方面提到了主體的反思。 其一,康德認為,我們能夠通過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行為來反思自由,“認識”到自由存在的理性“事實”。 當一個人在任何時候意識到道德行為的可能性時,他就可以“認識”到自由在實踐中的實在性,“他能夠做某事是因為他意識到他應當做某事, 他在自身中認識到了平時沒有道德法則就不會知道的自由”
。 其二,個人在行使權利時,同樣能夠反思到自由的存在,權利的有效性依托于自由,唯有自由概念的普遍性才使得權利的自由行使得以可能。 布朗特就指出,康德引入許可法的目的除了為滿足法權原則的普遍性要求外,還在于反映人的反思性承認
。 個人通過主張權利,能夠意識到具有普遍性的意志本身,從而承認自身對其他每個主體所負有的責任。 公民狀態的聯合意志正是通過人的自我反思得以形成,每一個人都將意識到建立法權關系的先天義務。 其三,理性不僅具有通過概念進行認識的功能,它還有通過意志而行動,并且形成實踐法則的功能。 現代社會都是建立在法則之上的,如果沒有這些法則,我們的生活就會立即瓦解,社會不再是人的社會,生活也不再是人的生活。 理性之所以能夠形成法則,正是因為理性是自由的,在意志自由的基礎上,才會有法則,如果人不是自由的,法則就將失去規范的效力,是毫無意義的。 法則在人類社會的客觀有效性,使得自由具有了客觀實在性,在這個意義上,生活在法則社會的人可以透過法則反思到意志的自由,認識到一切法則其實都是建立在意志之上的。 可以看到,上述三種“反思”都指向純粹的實踐的自由,某種意義上是對康德法權理論的一種“反向”闡釋,即從法則、自由權利的主張返回到自由的任意與意志。 因而,從另一方面來看,公民社會中的法權法則既是人們行動的信任標準,也是認識主體的自由本質的媒介,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就在于這些法則是基于普遍聯合的一般意志,是以人的具有普遍的、無條件性的意志為根據的。
先驗闡釋路向忠實反映了康德法權學說的“先驗”特征,任何經驗性的內容在這都是偶然的、有限目的。 然而,對經驗的排除并不代表理性就是萬能的,可以論證一切的。 在康德的時代,萊布尼茨-沃爾夫的理性主義哲學在德國各個大學中占據著支配性地位,這種理性主義哲學的基本思想就是打破人的理性有限性,進而形成了理性的獨斷論。 對于康德而言,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依照理性主義所設立的“自然法”標準是超出我們的認識范圍之外的。 認知主義的自由概念表明意志是可以被實踐、認識的,并且依據其所建立的法權、公民狀態并不是一種“已經確定了的結構”,而是訴諸人類之認知能力與反思能力的實踐理性標準,盡管它在知識的認識論上與我們無關,但在實踐的意義上是我們能夠反思到的。 因此,可以說康德實現了對以往的理性主義傳統的超越,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調和了可知論與不可知論的緊張關系。
四、先驗、法權與永久和平
康德《法權論》的闡釋路向不僅涉及政治合法性之形式,還指向政治合法性之范圍,后者即“永久和平”,也就是康德的世界公民主義。 盡管《法權論》中沒有深入討論與“永久和平”相關的國際法權以及世界公民法權的問題,但康德在前言中作出評論:“在本書結尾處,有幾章我處理得不夠詳細,不及人們與前面幾章相比所可能期待的: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我覺得它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從前面幾章推論出來。 ”(6:209)康德在論證法權時依據的是已經確立的先天自由理念,它是貫穿私人法權、國家法權、國際法權以及世界公民法權的一條紅線。 康德之所以將“永久和平”稱為一項哲學性規劃,因為它是康德法哲學所面對的終極問題,相應地,《法權論》的闡釋路向也應當與“永久和平”的問題導向相契合。
赫費對于康德《法權論》的政治合法性之范圍的闡釋具有代表性。 赫費反對將“永久和平”視為一種“政治烏托邦”,并明確指出:“和平的概念并不局限于《論永久和平》,而是系統貫穿于康德的整個批判哲學。 ”
某種程度上,“永久和平”確實可以說是貫穿三大批判的核心規劃,赫費的判斷僅在這一點上是符合康德哲學的基本要旨的。 和平就在于消除戰爭,后者的必要前提是在世界范圍內建立具有普遍性的法權關系, 而法權僅涉及主體間的外在關系,“永久和平” 也就是康德所構想的一種旨在處理外在沖突問題的特定方式。 赫費對于“永久和平”的動機的解讀是霍布斯式的,他認為現代國家乃至“永久和平”的形成都是基于人對戰爭的厭倦
。事實上,正如上文所言,康德接受了霍布斯關于人類自然狀態的戰爭的描述,但在公民狀態的論證中并沒有采取霍布斯式的經驗主義視角,自利在康德那是不被考慮的。赫費正確地指出了“永久和平”之于康德哲學的重要意義,但卻將康德解釋為一名政治現實主義者,這不得不說是與“永久和平”的先驗特征相悖的。 基于“厭戰”或自利的考慮,休戰協議的達成只是臨時性的,戰爭任何時候都可能再次發生,“永久和平”將不會達成。 盡管赫費的解讀是基于對康德文本的全面考察,從結果來看他并沒有充分理解何為“一項哲學性規劃”,而這也是契約路闡釋路向的問題所在,以至于對康德法權學說的把握在整體性上略有不足。
(3)提高落實工作的能力。進一步探索建立廣西財產行為稅分稅種專業骨干團隊,組建財產行為稅人才庫,為推進新時代財產行為稅工作提供人才支撐。要有側重地抽調人才庫人員分稅種組織研究政策、征管問題,承擔相應的課題研究和重點難點項目攻堅等工作。對現行稅制存在的突出問題,各基層地稅機關要主動參與進來,抓住千載難逢的立法調研、政策規范、強化征管機遇,將真正肯干事、能干事、會干事的專業人才集中起來,上下聯動、協同推進財產行為稅重點工作,發揮分稅種專業骨干團隊集體攻關的作用,使專業人才在干事創業、攻堅克難中鍛煉能力、提升素質、實現價值。
2.3.1 定植。定植是栽培管理中的關鍵環節,對于整體栽培效果影響極大。定植之前,種植人員需嚴格執行相關標準及工作流程,挖好坑穴并合理施肥與灌溉,確保定植工作能夠順利開展,進而保障定植質量。定植時,棗樹樹冠矮小,適宜進行合理密植,但過于密集不利于棗樹生長和管理,因此需要根據棗樹的品種和冠幅確定種植密度。長期棗糧間作行距8.0~15.0 m,株距4.0~6.0 m,定植采用南北行。定植穴的大小一般為80 cm×80 cm×80 cm,并施10 kg以上的農家肥。冬小麥、夏大豆等與棗樹的間距需要保持在2 m以上才可以實現增產,2 m以內易出現減產現象[1]。
在全面深化改革新時期,改革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留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單純地“摸著石頭過河”已經不再適應時代要求。雖然全面深化改革是在走前人未走過的路,“摸著石頭過河”仍有合理性,但必須將“摸著石頭過河”和“頂層設計”結合起來,堅持趨利避害,讓“頂層設計”緩沖“摸著石頭過河”的風險。
如何理解康德的法權與“永久和平”的關系,存在正向演繹與人的“反思”的雙重視角,這也是先驗闡釋路向的基本要旨。 從正向演繹來看,康德指出:“公共法權這一普遍概念使人不僅想到國家法權,而且還想到國際法權;由于大地是一個自我封閉的表面,公共法權必然把二者引向一種多民族的國際法權或者世界公民法權的觀念。 ”(6:311)一國之內的國家法權的建立是以實踐的自由意志為根據,法權普遍化的結果是消除人與人之間的沖突。 如果僅從自由的理念來看,避免沖突的最好辦法是盡量減少來往。 但康德在這里還考慮到了自然目的的闡釋,有限的地球表面以及語言、文化的差異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來往、沖突無法避免,因此,社會需要一種更大范圍的法權關系來調和沖突,正是先天的自由意志與自然目的結合使得全球性的法權關系得以必然。 依照這一邏輯,國家法權、國際法權以及世界公民法權缺一不可,三者具有統一的理念前提,“只要有一種缺乏由法律限制外在自由的原則,其余兩種形式的大廈就必定會被削弱,最終坍塌”(6:311)。 從人的“反思”來看,康德認為,人的理性與知性之間存在著一種判斷力,它在認識領域里是規范性的,在實踐領域里是反思性的。規范性的判斷力能夠將特殊歸攝到已被給予的普遍中, 反思性的判斷力則從特殊中尋求普遍,人們可借此在客體對象上設定一個目的,從而達成一種統一性
。 從公民狀態的建立到社會的逐漸文明化,人們通過一種道德的眼光來審視社會生活中的法律、權利,可以反思到自身的自由本質,以及最終的共同道德理想——人類的永久和平。 人在不斷反思、認識主體的自由本質與道德目的的過程中,轉而將其貫徹到現實的社會生活,這使得“永久和平”的達成成為可能。
“永久和平”是康德在先驗視角下提出的人類政治制度的構建方案,其論證邏輯始于康德的法權學說
,更確切地說,是始于康德對于實踐的自由的意志與任意的劃分。 《法權論》的先驗闡釋路向既抓住了具有立法機能的并且以自身為目的的意志,將任何經驗的內容排除在外,同時強調了人的“反思”,即自由并不是超然于人之外的存在,它是能夠被我們所“認識”的,通過對自身道德目的的“認識”,現實的法權關系才是可能達成的。 因此,先驗闡釋路向契合于“永久和平”的政治道德理想,而唯有以先驗的視角審視康德的《法權論》,才能明晰“永久和平”何以必然的終極問題。
但式(1)中沒有考慮泄漏對于活塞運動速度的影響。泄漏將降低實際進入液壓缸流量的大小,進而影響液壓缸速度,因此泄漏對于液壓系統特別是在高壓精密系統中動態性能的影響不可忽略。
五、余論
康德法哲學以《法權論》為依托,對后者的理解決定了理論發展的基本方向。 康德《法權論》之闡述路向的判定,需要從康德哲學的批判本質來整體把握,其批判對象是人的諸先天能力,在實踐領域中,則是對人的自由的實踐能力,也就是對欲求能力的批判。 法權本質上是先驗的,對它的解讀應當以實踐的自由為前提,實踐的自由意味著先天的自由能力,它在邏輯上是先于經驗的,并最終要運用于經驗之上。 康德將人的欲求能力劃分為意志與任意,意志具有立法機能,它自在的就是目的,任意具有執行機能,僅與行動相關,真正嚴格意義上的自由是意志的自由。 《法權論》的先驗闡釋路向的重要意義就在于,一方面,將意志作為法權演繹的出發點,人類社會從自然狀態到公民狀態的轉變不以任何經驗內容為目的,是人為實現其自由本質的必然階段;另一方面,將實踐的自由視為一種認知主義的自由,先于經驗并不代表脫離人的認識結構,盡管不同于知識意義上的認識,但人類可通過對現實的法權的“反思”來認識到自由的存在,人的本質特征就在于他的自由屬性。 通過對這兩個方面的把握,先驗闡釋路向對國家法權的解讀,可進一步推論出國際法權以及世界公民法權,三者在體系上缺一不可,這也是康德論證“永久和平”的先驗邏輯。 本文將康德《法權論》的闡釋置于“先驗”的層面上,并不代表要破除康德關于法權與倫理(德行)的區分,法權依然只關注外在行為而非主觀動機的合法性。 先驗闡釋路向僅意味著使對法權何以成立、法權的規范效力等問題的解答盡量符合康德哲學的批判本質,并且契合康德對于“永久和平”的“哲學性規劃”的定位。
[1] FLIKSCHUH K. On Kant's Rechtlehre[J].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10: 5(1).
[2] Mark Timmons. Kant's Metaphysics of Morals: Interpretative Essay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3] 湯沛豐.康德法哲學中的人權、所有權與國家[J].中國人權評論,2018(1):15-33+178-179.
[4] 鄧曉芒.康德自由概念的三個層次[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2):24-30.
[5] Lewis White Beck. A Commentary on Kant'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198.
[6] 邵華.論康德的社會契約論[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17-24.
[7] Jeffrie Murphy. Kant: The Philosophy of Right[M].Berlin: Mcmillan, 1970.
[8] Wolfgang Kersting. Wohlgeordnete Freiheit: Immanuel Kant's Rechts-und Staatsphilosophie[M]. Berlin: De Gruyter, 1984: 356.
[9] 楊祖陶,鄧曉芒.康德《純粹理性批判》指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50.
[10] 方博.自由、公意與社會契約——關于盧梭和康德的一個政治哲學的比較[J].哲學研究,2017(10):102-110.
[11] 卞紹斌.走出自然狀態:康德與公共法權的證成[J].學術月刊,2019(6):13-31.
[12] IMMANUEL KANT. Die Metaphysischen Anfangsgründe der Rechtslehre [M]. 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1986:5,113.
[13] IMMANUEL KANT.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x.
[14] LESLIE A, MULHOLLAND. Kant's System of Rights[M].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111.
[15]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M]. Hamburg :Verlag von Felix Meiner,1974:35.
[16] OTFRIED H?FFE. Einleitung: Der Friede - ein vernachl?ssigtes Ideal[M]. Berlin, Boston: Akademie Verlag,2015:12,16.
[17]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nteilskraft[M]. Hamburg:FelixMeiner Verlag, 1924: 15-17.
[18] 洪濤.論康德的永久和平理念[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3):133-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