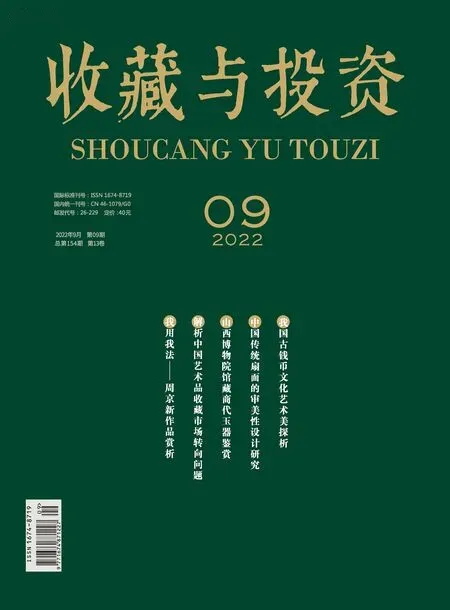古埃及墓室壁畫中圖像與碑銘體的關系探究
史雅楠(太原師范學院,山西 太原 030002)
一、古埃及墓室壁畫
(一)古埃及墓室壁畫溯源
古埃及享地緣優勢,少外敵入侵和異族文化影響,歷史進程較連貫,依傍尼羅河,原始農業發展。古埃及共歷經三十個王朝,分九個時期,以法老為首的中央集權占主導地位。
在傳統生死觀的指引下,有關陵墓的建設及裝飾在統治者眼中尤為重要。死亡被視為生命從一個世界向另一個世界轉移的過程,陵墓作為通往下一世的“裝置”,展現了其生前的生活場景與死后的美好期盼。統治者更希望將現世的財富和權力延續到下一世,故墓室壁畫程式化且理念保守。加之古埃及人民極其信奉神靈,相信靈魂不滅,因此,墓室壁畫內容與形式一脈相承。
(二)古埃及墓室壁畫特征
古埃及歷經的九個時期在藝術風格方面兼具繼承性和創新性,從程式化發展到多樣化,從符號趨向寫實,其間亦有世代傳承的特征。普蘇森尼斯一世是于公元前1047至前1001年統治塔尼斯的古埃及二十一王朝第三位法老,他被埋葬于下埃及的塔尼斯編號為3的陵墓,該陵墓于1940年被發現。陵墓中冥神奧西里斯的局部壁畫反映了古埃及壁畫的特征。
其一,壁畫以豐富的視覺藝術來表達情感,包含宗教、哲學思想。圖1是以古埃及的宗教神話為背景,描繪了死者在復活過程中死亡審判的環節。奧西里斯是冥界的主宰和死亡判官,決定人死后是否可得到永生,是保護死者的神。
其二,繪制人體時采用“正面律”的程式化表現手法,將正側面、寫實與變形結合,旨在追求完整,使靈魂能回到一具完好無損的尸體中。
其三,多點透視構圖方式近三千年未變。
其四,夸張與放大的表現形式,有意將重要人物、權貴形象放大,周遭圍繞著形象較小的家人、奴隸等,體現出森嚴的等級制度和社會秩序。圖1中冥神奧西里斯形象占比最大。

圖1 冥神奧西里斯(左三)
最后是秩序化。在法老的統治下,壁畫整體莊嚴肅穆,構圖上從未出現過大量留白。圖1右上角采用橫帶狀的排列結構繪制奴隸形象,用水平線劃分畫面,整體順序有致,繪制過程中以“格層法”區別遠近關系,更有縱深感。壁畫中色彩的使用也有固定規范,每種顏色所代表的意義不同,適用范圍也不同。
二、古埃及碑銘體文字
(一)古埃及文字溯源
1.古埃及文字產生背景與構成規律
“Hieroglyph”來自希臘語,字面意思是“神圣的刻符”,指整個字符集。周有光先生提出“圣書字”狹義上指碑銘體,廣義上指古埃及三種字體的總稱即碑銘體、僧侶體和人民體。王海利先生指出“古埃及象形文字”與“Egyptian Hieroglyphs”不能對譯,且圣書字在構成和組合方式上與漢字迥然不同,故采用“圣書字字符”一說更準確。
迄今出土最早的古埃及刻符約在公元前3150年,是前王朝晚期阿拜多斯地區(Abydos)u-j號墓的骨制和象牙制標簽上的符號。涅伽達文化Ⅰ末期出土的一些陶片及希拉康坡里出土的納爾邁調色板上的少數符號與后來的字符相似,可作為圣書體字符的緣起。
圣書字字符較西周金文的造型更具象寫實,單個圖符所表達的含義更局限,通過對現有的圖符進行組合、變形和限定可達到記錄語言的目的。圣書字字符由近千個基本圖符組成,常用符號多達700個,由意符、音符和定符三部分組成。意符是用圖符來表示所指具體存在事物的含義。音符中單輔音音符共25個,表發音且對應一個字符,記錄時通過“語音補充”方法,一能提示前面的字符為音符,并附其讀音;二可使字符書寫更靈活、美觀。因為古埃及碑銘體不記錄元音,所以以定符或部首符號來限定詞匯具體含義,置于詞尾且不發音,用于表明詞義范疇。由于這種獨特的構成規律,碑銘體在書寫時多個字符表達一個含義,且字符有方向、可疊放。
2.古埃及文字的三種書體
隨著字符增多,書寫目的、材質轉變,書吏不斷簡化書寫方式,陳永生先生將古埃及文字的三種書體命名為碑銘體、僧侶體(見圖2采自James P.Allen Middle Egyptian,p.6)和民書體(見圖3采自James P.Allen Middle Egyptian,p.7),三種書體曾同時并行使用。碑銘體從公元前3000年一直使用到公元1世紀左右,這種符號系統占據埃及語言文字歷程的3/4。最初在多種場合擔任多種用途,并不限于莊重神圣的場合,手寫與雕刻形式并存,且兩種形態相差無幾。碑銘體由書吏墨書,工匠比照雕刻,后逐漸退出日常生活,只銘刻、涂繪于圣廟、陵墓、紀念碑及金字塔銘文中,較易識讀。長銘文常在歷史性、自傳性的文本中出現,亦用于宗教性的贊美詩或葬禮咒語。

圖2 碑銘體(上)與之對應的僧書體(下)

圖3 民書體
“Hieratic”即“僧書字”“僧侶體”“僧書體”,在希臘羅馬時期一般僅埃及僧侶使用。僧書字與圣書字幾乎同時出現,從古王國時期使用到公元3世紀,以蘆葦筆和墨寫于莎草紙、皮革、木頭上,常用于臨時性信件、賬本等,是圣書字的草體形式,大量連寫使象形性減弱,更簡略、圓潤,較難識讀。“Demotic”為平民大眾使用,稱為“民書字”“民書體”“人民體”“大眾體”“世俗體”“書信體”或“土俗體”。民書字形體上與圣書字相去甚遠,脫胎于僧書字但是其更草率的手寫形式,在早期只用于行政法律和商業文獻。
選取我院2016年1月—2018年1月收治的80例白血病PICC導管瘤患者作為研究對象。根據護理的不同可以分為實試驗組和常規組,每組患者40例。納入標準為:符合白血病臨床診斷,需靜脈化療,生命體征在正常范圍;排除標準:不愿參加本次實驗患者,合并腎肝肺等嚴重疾病患者,精神、心理疾病患者。實驗組中,男性患者26例,女性患者14例,年齡15~65歲,平均年齡(43.92±3.25)歲;常規組中,男性患者25例,女性患者15例,年齡為16~66歲,平均年齡(44.12±4.86)歲。兩組患者的一般資料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二)古埃及碑銘體特征
寫實性、圖畫性造型原則始于古埃及史前刻符階段,自然主義特征突出,藝術性極強,字符形態規范成定式。碑銘體主要為來世書寫,體現古埃及人注重畫面敘述性。為了來世的幸福生活、靈魂和肉體的完整性并幫助死者復活,墓室內雕像與繪畫都須詳盡精微,逼真寫實,文字按照標準范式書寫得一絲不茍。其中一些示意危險的字符需抹去一些部分,防止傷害死者。
碑銘體文字形態固定化,與古埃及人生死觀中對永恒和穩定的追求以及宗教思想中“逼真”意識的追求相吻合。古埃及人認為字符被賦予生命,在墓葬文化中承擔延續現世、通向永恒的重要作用。


圖4 箭頭指向為圣書字書寫方向
書吏的工具箱中調色板一般配有紅、黑兩種顏料,黑色用于正常書寫,紅色用于標注開頭、結尾或其他特殊提示。
三、古埃及墓室壁畫中圖像與碑銘體關系分析
(一)壁畫圖像與碑銘體相輔相成
1.壁畫圖像與碑銘體的共生
中國有“書畫同源”之說,在古埃及陵墓壁畫中也有體現。最初,人們使用一些形象、直觀的圖形來表現和代表具體的物品和存在物,處于原始層次;當這些圖形中的一部分經過聯想層次的簡化加工后,它們就具有了物品與存在物形象擴展后與之相近概念的含義,這種擴展與不確定性成為具有多重延伸含義的文字畫,與圖像發展為兩種不同路徑。文字畫逐步簡化規范后形成圖畫文字,在古埃及文字中由意符、音符、定符組合成完整可讀的語言。碑銘體經歷了從最初的圖形到符號的簡化,繼而逐漸形成特有的語言語意系統,基于古埃及文字與圖像同源原因,讓二者具備了統一的具象思維及寫實性特征。
碑銘體由圖像產生,又為其釋義,在表意與布局上與壁畫圖像成互補關系。古埃及陵墓中部分壁畫由圖像與碑銘體共同組成,一方面,部分圖像描繪死者生前所經歷和享受的世俗生活,其周圍的碑銘體用以記載墓主人的豐功偉績和現世場景;另一方面,圖像與碑銘體相組合還具有加強王權、傳播宗教神學思想的政治功能。古埃及人受宗教思想影響相信靈魂不滅,亦有對來世的期待,將碑銘體融入其中有解釋、擴展圖像含義之用。圖1中作為冥府之主的奧西里斯是死亡審判的主持者,無論是國王、王公貴族,還是下層平民百姓,都希望自己死后可以順利地通過審判,如此便可以順利到達永生之地,所以才會利用碑銘體在對應的圖像周圍來記錄贊美詩、咒語和祈禱文,分別用于贊美神、驅除邪惡、祈禱美滿的重生生活。此外,碑銘體在與圖像的組合中還擔任裝飾作用,與墓室壁畫相互輝映。
3.壁畫圖像與碑銘體彼此構建的思維模式
古埃及墓室壁畫中圖像均采用“正面律”法則,手法寫實如同碑銘體構形。以網格法確保圖像中人物與動物形象比例正確、形象完整,繪制前畫好網格,按照規定的范式繪畫圖像,規范書寫碑銘體,確保死者經過重重考驗能以完整的軀體到達下一世,兩者均體現埃及藝術“規范的傳統”特征和寫實主義的藝術精神。
圖像與碑銘體的同質性源于思維一致性。古埃及人的藝術創作皆以“萬物有靈”觀為基礎,他們崇拜一切自然事物,崇拜動植物、“復合神”以及人格化的神,他們利用圖像和文字將所崇拜的事物具象化,將其宗教思想寫實化,這種形象思維,以及黑格爾提到的“象征首先是一種符號”代表的象征性思維是圖像與文字同質性的深層原因。
(二)壁畫圖像與碑銘體疏密節奏關系
碑銘體與圖像的組合以大團塊的圖像為主體,其間用橫帶狀結構留白小,有疏簡之意。碑銘體字符多,緊湊繁密,與圖像呈疏密對比、主次分明的關系,增強裝飾藝術感染力,充分利用墓室內的展示面積。這種布局疏密、塊面大小、著色輕重的多重對比頗富視覺沖擊,賦予壁畫整體生命力,氣息貫穿其間,具有韻律感、流動感。圖像與文字組合的表現手法在內容與形式上互補,產生新的視覺張力和欣賞視角,使古埃及壁畫始終具備繪畫的可讀性與文字的繪畫性,這種平衡感是古埃及人藝術創造的直觀體現。
(三)壁畫圖像與碑銘體共賦色彩關系
圖像與碑銘體共賦色彩,其一,生產力低下,取色工藝煩瑣,著色豐富可彰顯王權至上;其二,畫面整體更和諧,動感十足。圖文和諧也體現了古埃及人對自然崇拜的藝術精神,強烈的來世觀念表現在墓室壁畫藝術臻于完美的內容、形式與色彩范式中,圖文著色豐富更具視覺沖擊力,也更貼近現世豐富的生活場景,這種所見即所得的寫實主義與古埃及人對規范、自然的追求一直貫穿于墓室藝術始末。
四、結語
古埃及墓室壁畫中圖像與碑銘體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和諧平衡,體現了思維一致性,這種圖文組合的表現形式能更透徹地分析古埃及人的思想精神及藝術追求,有助于為藝術創作在汲古道路上提供更多出新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