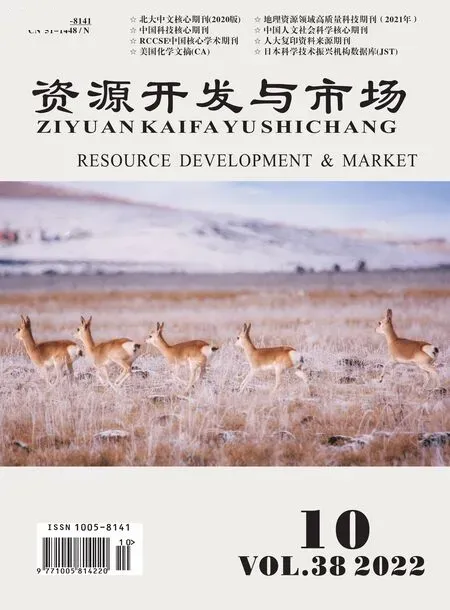新疆農業面源污染的時空分異及動態演進
——基于特色畜牧視角的再分析
夏文浩,潘生亮,霍 瑜,馬義光,孫超俊
(1.塔里木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南疆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新疆 阿拉爾 843300;3.云南大學滇池學院 經濟學院,云南 昆明 650228)
0 引言
農業面源污染又稱“非點源污染”,是指在農業生產和日常生活過程中產生的未經凈化處理的各種污染物對土壤、水體和大氣等環境造成的污染[1]。由于農業面源污染具有分布區域較廣、覆蓋面積大、隨機性強和污染源分散程度高[1]等特征,成為農業現代化進程中實現“2030 年前碳達峰,2060 年前碳中和”雙重目標[2]和綠色農業發展[3]新的重難點之一。在中央農業可持續發展政策的指導下,新疆經濟快速發展,綜合實力明顯增強,經濟結構逐漸優化,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加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顯著增強,但農業生產過程中特別是農村超量和不合理施用化肥、農藥等造成的農業污染日益嚴重,威脅著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加劇了生態環境的脆弱性,進而減緩經濟增長速度,降低人們的生活水平。《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公報》顯示,2017年畜禽養殖、農村生活污染排放量分別占全區農業面源污染物排放量的67.7%和31.2%。2018 年,新疆化肥施用量比2009 年增長了100 萬t,農用塑料薄膜使用量擴大了近2 倍,農藥使用量增加至3.04萬t,農業面源污染排放量年均增長率達2.903%[4]。新疆作為我國種養殖大省之一,其單位面積農作物產量大、規模化養殖程度較高,目前已成為我國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攻堅克難主戰場。
縱觀近年國內外對農業面源污染的研究,國外學者集中于水質監測與污染源研究[5,6]、農業面源污染模型模擬技術的使用和拓展[7,8]、BMPs 效益及環境治理政策[9,10]等方面,國內學者對農業面源污染的研究包括農業面源污染的內涵[11]、調控策略[12]、污染量測算[13]、空間區域差異及特征[14-18]、影響因素[19-21]、與經濟增長的關系[4]等方面。就農業面源污染的核算和評價方法而言,國內外研究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賴斯蕓[22]運用單元調查法,借助地圖可視化對我國及部分地區的農業面源污染進行了測算,并進一步展示了其空間差異及分布特征;二是熊昭昭等[14]、楊永健等[15]通過排污系數法分別對三峽庫區重慶段、江西省和黑龍江省的農業面源污染排放情況進行了考察;三是陳敏鵬等[16]、謝文寶等[4]和林江彪等[23]利用清單分析法計算了我國及各省份農業面源污染的排放量和排放強度;四是王思如等[17]通過輸出系數模型法估算了洞庭湖和全國的COD、TN、TP的農業面源污染負荷量;五是賈陳忠等[18]借助等標污染負荷法對2016 年山西省農業面源污染負荷進行了計算,認為該省農業面源污染嚴重,尤其是COD 排放量最大,污染物來源主要為畜牧養殖污染和農村生活污染。
綜上所述,學者們在農業面源污染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后續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在文獻總結過程中,仍存在以下不足:①從研究內容看,已有文獻多考察常見農作物、禽畜類型的污染排放,未將區域特色種養殖單元納入其中;②從研究區域看,多以全國、中部和東南部地區經濟發展較好的省份為主,而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不同地州市的研究較少,忽略了少數民族地區不同區域區情所造成的差異;③從研究方法看,目前多以單一計量方法為主,未考慮到區域內環境條件的復雜性、調查數據的稀缺性和數學模型本身存在的局限性。
基于此,本文采用清單分析法,以2000—2019年為研究時段,嘗試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14 個地州市的農田化肥、農用固體廢棄物、禽畜養殖、水產養殖和農村生活5 個產污核算單元造成的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進行測算。在此基礎上,引入Dagum 基尼系數分解法和Kernel 核密度,借助ArcGIS 揭示新疆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的空間分布、區域差異及動態演進特征。對比以往的研究,本文主要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一是在對農業面源污染強度進行核算時,從新疆區域實際出發,在“禽畜養殖”核算單元中引入新疆特色畜牧養殖清單,譬如牛、馬、駱駝等;二是在進行實證分析時,利用Dagum 基尼系數分解和非參數估計,借助ArcGIS 與三維視圖,多維度把握新疆農業面源污染排放的時空分布特征及變化規律,深入分析其現狀原因,以期為新疆地區農業面源污染的治理提供參考。
1 研究區概況
新疆位于我國西北地區,地處73°40′—96°23′E、34°22′—49°10′N之間,國土面積166.49 萬km2,是我國陸地面積最大的省級行政區,約占我國國土總面積的六分之一(圖1)。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自治區常住人口為2559 萬人。新疆地處亞歐大陸腹地,與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印度、阿富汗8 個國家接壤,歷史上是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

圖1 研究區區位Figure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新疆是我國農業大省,2019 年糧食種植面積為220.36 萬hm2,糧食產量同比增產了1.5%;豬牛羊禽肉產量160.6 萬t,同比增長了2.2%;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056 元,同比增長了7.1%。但新疆農業經濟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的環境污染問題。經計算,2019 年新疆農田化肥、農田固體廢棄物、畜禽養殖、水產養殖和農村生活污染物的排放量分別達到4056.58t、29789.30t、158041.38t、213152. 71t、1694.3t,較 2000 年 分 別 增 長 了162.44%、95.06%、40.2%、175.81%、68.3%,農業面源污染物排放總量同比2018 年增長了6.13%。由此可見,農業面源污染是新疆生態環境綜合治理、打贏“藍天保衛戰”和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障礙。
2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 研究方法
清單分析法:基于新疆農業污染現狀,本文選擇農田化肥、農田固體廢棄物、禽畜養殖、水產養殖和農村生活排污5 個產污單元,利用清單分析法構建新疆農業面源污染排放測算與評估的5 層結構,包括污染來源、調查單元、調查指標、單位HE 排放清單(表1)。

表1 新疆農業面源產污單元清單Table 1 List of agricultural non- point source pollution production units in Xinjiang
參考陳敏鵬等[16]、賴斯蕓[22]的研究,對新疆農業面源污染的排放量及排放強度進行測算,計算公式為:

式中:E 表示新疆農業面源污染排放量;PEn表示新疆農業面源污染的產生量;σn表示單元中第n種污染物的產污強度系數;ηn表示各種相關資源利用效率的系數;ωn表示第n 種污染物的流失系數,該系數由污染源本身及空間特征(S)決定,表征為新疆地區異于內地的地理特征、降水量、水質、地表徑流、復種指數和人為管理措施等復雜因素對農業面源污染的綜合影響;EUn表示第n 種污染物指標的統計數量;EI 表示新疆地區農業面源污染的排放強度;AL 表示新疆年末耕地面積。
Dagum基尼系數分解法:借助Dagum 基尼系數分解法對新疆地區農業面源污染的區域差異考察,計算公式為:

Dagum[24]將基尼系數GN 分解為地區內差異GNw、地區間差異GNb和超變密度差異GNt3 個模塊,三者的關系滿足GN = GNw+ GNb+ GNt。具體如下:


公式(9)—(11)中:djh為各地州市污染強度的差值;pjh為超變一階距;Fj、Fh分別表示區域j 與區域h 的累計密度分布函數。
Kernel 密度估計:核密度估計采用連續密度曲線繪制隨機變量分布形態及特征。基于其可使研究對象擺脫未知參數影響的非參數估計方法優點[25],本文將使用該方法進一步分析新疆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的動態演進。假設隨機變量X的密度函數為:

式中:N 為樣本的數量;h 為帶寬;K 為核函數;Xi為獨立同分布的樣本值,x 為均值。本文中,X1,X2,…,Xi表示各地區的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f(x)是Kernel密度估計。由于核密度估計對帶寬h較為敏感,故本文選擇小帶寬以提高估計精度。同時,采用較為常見的高斯核函數,計算公式為:

2.2 數據來源及參數選擇
本文使用的新疆農業面源產污單元清單列表數據來自于《新疆統計年鑒》和《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對于缺失值首先找尋地區統計年鑒、公報進行數據填補,然后采用均值替換法進行處理。農業面源污染排放測算中使用的各產污強度系數、排污系數等參數取值通過大量的文獻調研和綜合比對所得,重點參考陳敏鵬等[16]、賴斯蕓[22]、潘丹[26]、梁流濤[20]、丘雯文等[27]的參數取值,同時還參考了《污染源普查農業源系數手冊》分省份參數取值,以此為基礎建立新疆地區的相關影響參數數據庫(表2)。

表2 新疆農業面源污染影響參數Table 2 Impact parameters of agricultural non- 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Xinjiang
3 結果與分析
3.1 污染排放量及時序分布特征
從圖2 可見,在南疆、北疆、東疆(南疆包括喀什地區、阿克蘇地區、和田地區、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北疆包括烏魯木齊市、克拉瑪依市、阿勒泰地區、塔城地區、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東疆包括哈密市、吐魯番市)分布中,北疆的污染物排放量最高(72.3%),南疆次之(21.5%),東疆的污染物排放量最少(5.7%)。通過查閱數據資料,發現北疆地區中經濟發展排名靠前的地級市數量較多,如烏魯木齊、阿勒泰地區、克拉瑪依市等地,此類地區人口數量多、密度大、分布密集,導致農村生活類污染排放較其他地區較多。調研發現,北疆地區養殖以散養為主,規模化養殖程度不高,大部分養殖戶無資源集約化、循環利用的思想,導致禽畜糞便污染比其他地區高。而南疆有著大面積的耕地,意味著化肥、農藥投入的不可或缺,化肥量從2001 年的330561t(折純)增加到2016 年的1188166t,增長了2.6 倍,使用密度達到347 kg/hm2,超出國際公認安全上限的38.8%,但化肥利用率較低,富余的化肥殘留在土壤中成為農業生產和土壤的污染源。平均每年農藥使用密度達到3.36kg/hm2,超出農藥使用的重度污染線。年均農用地膜使用量達到692582t,20%以上的廢棄地膜殘留在土壤中,造成非常嚴重的”白色污染”。此外,南疆農業機械化作業水平較高,農用柴油消耗量由14.5 萬t 增加到32.17 萬t,增漲了2 倍以上。各種農資投入量的增加,是導致南疆農業生態環境惡化的主要原因。東疆地區由于氣溫高、蒸發量大,故不種植水稻、甜菜等含水量較高的作物,農田固體廢棄物污染物排放量不高,其水產養殖面積也不高。通過數據發現,該地區禽畜養殖量較其他地區相比數量極低,因此污染程度不高。2019 年,新疆COD、TN、TP 3 類污染排放量較2000年分別增長了102363.2t、81876.3t、14664.9t,平均增長速度為0.033%,但在2014—2015 年間增長率高達22%;北疆地區COD、TN、TP 3 類污染排放量較2000年分別增長了67763.31t、41759.89t、4733.43t,同在2014 年,3 類污染物排放量較2013 年分別增長了174418.85t、231707.93t、25810.27t,翻了2.2 倍;南疆2019 年COD、TN、TP 3 類污染排放量較2000 年分別增長13775.42t、- 5690.7t、2148.32t,但僅2014年,3 類污染物排放量較 2013 年分別增長了173773.65t、230680.62t、25785.43t,翻了3.69 倍;東疆2019 年COD、TN、TP3 類污染排放量較2000 年分別增長了3134.59t、- 208.5、387.03t,增幅不明顯,但在2014 年,3 類污染物排放量較2013 年分別增長了25706.59t、34343.02t、3746.60t,翻了9 倍。新疆各地區在2014 年均實現了污染物排放量翻倍增長,可能存在的解釋是:隨著各地區農業人口的不斷增加,農業種植技術和農業機械技術的發展,導致農民對耕地的需求量不斷增加,加之2014 年政府鼓勵農民開發戈壁、河灘等不易利用的土地類型發展農業,農業播種面積和耕地面積隨之迅速增長,為提高農業產量,對化肥、農藥的需求不斷增加。而大量使用化肥和農藥不僅會破壞土壤有機質,土壤中的污染殘留還會隨農田排水和地表徑流流入江河湖海,擴大了農業面源污染的面積。

圖2 2000—2019 年新疆各地區農業面源污染物排放量時序分布特征Figure 2 Time series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non- point source pollutant emissions in various regions of Xinjiang,2000-2019
3.2 污染排放強度的空間分布特征
李海鵬等(2009)[1]在進行農業面源污染排放的空間分布研究時,按照一定標準將污染強度劃分為輕度、中度、重度污染區3 種類型。本文在研究新疆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的空間分布時,考慮到新疆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民族的多樣性、思想的復雜性和脫貧攻堅成果的不穩定性,根據自治區的實際情況,將污染物排放物強度劃分為5 個等級,并以此為基礎,結合AirGIS 10.8 軟件繪制空間差異分布圖,具體如圖3 所示。

圖3 2000—2019 年新疆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空間分布Figure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non- point source polluti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Xinjiang,2000-2019

(續圖3 2000—2019 年新疆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空間分布)
從圖3 可見,2000—2019 年新疆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呈“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曲折下降態勢,空間差異明顯。較高值主要出現在阿勒泰地區、烏魯木齊市、喀什地區、吐魯番市、哈密市,較低值主要分布在克拉瑪依市、塔城地區、阿克蘇地區,說明新疆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由南北兩端向中心逐漸遞減,治理效果沿著天山山脈,由中心向南北兩端逐漸凸顯。具體來看:2000 年排放強度最高的是阿勒泰地區,為25.43t/km2;其次是烏魯木齊市,為22.57t/km2;最低是克拉瑪依市,僅為1. 44t/km2。2005年排放強度排名前三位的分別是吐魯番市、烏魯木齊市、哈密市,分別為25.55t/km2、22.59t/km2、20.42t/km2;排名最低的是克拉瑪依市,僅為2.25t/km2。2010年排放強度排名前三位的分別是烏魯木齊市、和田地區、喀什地區,分別為 21. 56t/km2、10.10t/km2、9.52t/km2;排名最低的是克拉瑪依市,僅為1.15t/km2。2015 年排放強度排名在前三位的分別是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烏魯木齊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分別為215.49t/km2、79.66t/km2、39.95t/km2;排名最低的是克拉瑪依市,僅為0.98t/km2。2019 年排放強度排名在前三位的分別是烏魯木齊市、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分別達到68.64t/km2、44.40t/km2、9.48t/km2;排名最低的依舊是克拉瑪依市,僅為1.43t/km2。
3.3 新疆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的空間差異
根據相關計算方法,分別計算得到2000—2019年新疆及各地區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的基尼系數,結果如表3 所示。新疆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的空間差異具體體現在總體差異及其分解、地區間差異兩大方面。

表3 新疆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的基尼系數及分解結果Table 3 Gini coefficient and decomposition results of agricultural non- 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tensity in Xinjiang

(續表3)
新疆農業面源污染的總體差異及其分解:新疆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總體Dagum 基尼系數及其動態演變如圖4a所示。

圖4 新疆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差異動態演變Figure 4 Dynamic evolution of differences in agricultural non- pointsource polluti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Xinjiang
觀測期內,新疆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總體基尼系數以2009 年和2013 年為拐點表現出“增加—減少—增加”的“N”形變化趨勢,觀測期末的排放強度差異較2000 年期初不斷擴大。①從差異來源的變化趨勢來看,2000 年新疆地區內差異對總體差距的貢獻率為38.14%,2019 年增長至41.38%,其年均增幅為11.17%;同時,2000 年新疆地區間差異對總體差距的貢獻率為24. 64%,2019 年增長至46.22%,年均增幅為87.6%。超變密度反映了新疆地區間交叉重疊對總體差距的影響,觀測期內表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②從差異來源的貢獻來看,地區內差異是總體差異的最主要來源,觀測期內貢獻率位于30.97%—43.38%之間;其次,超變密度是第二來源,貢獻率在12.40%—47.92%之間;新疆地區間差異對總體差異的貢獻最小,觀測期內貢獻率位于10.97%—46.22%之間。③從均值來看,地區內差異、地區間差異和超變密度對總體差異的貢獻率分別為37.8748%、27.1536%、34.9716%,驗證了新疆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差異來源的貢獻程度為地區內差異>超變密度>地區間差異。
新疆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地區內Dagum 基尼系數及其動態演進如圖4b所示。①從均值看,北疆和南疆地區的排放強度基尼系數較高,分別達到0.4354、0.2297,排放強度內部不均衡現象明顯。相較而言,東疆的排放強度基尼系數較低,為0.0753,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內部差異較其他地區相對較小,與空間分布動態特征結果相一致。②從增長態勢看,北疆地區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的地區內差異存在曲折上升趨勢,2019 年達到最高點0.6170,年均增長率達3.00%;南疆地區污染排放強度基尼系數呈現升降交替的動態波動增加變化趨勢,2015 年達到峰值0.5596,該年度南疆地區內污染物排放強度差異最大,年均增幅為9.8%;東疆地區相對于其他地區而言,其污染物排放強度區域內差異呈現曲折下降的趨勢,2019 年基尼系數較2000 年降低了0.0738,但在2005 年、2018 年出現驟增的變化趨勢,兩年年度增長幅度分別高達14.05%、16.76%。
新疆農業面源污染地區間差異:新疆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地區間Dagum 基尼系數及其動態演進如圖5 所示。①從均值看,北疆和南疆的污染物排放強度差異最為明顯,觀測期內基尼系數均值達0.4099;其次是北疆和東疆,系數均值為0.3884;南疆與東疆之間的污染物排放強度差異最小,其系數均值為0.2904。②從變化趨勢看,觀測期內北疆和南疆之間的污染物排放強度差異增幅最為明顯,年均增幅為8.11%,呈現出以2015 年、2016 年為拐點的“N”字形增長態勢,且觀測期末較期初有所增加。2013年之前北疆—東疆的污染物排放強度差異變化趨勢較為穩定,無較突出的波動,但在2014 年及之后的觀測期內,該地區間差異增長態勢差異極為不穩定;而南疆、東疆之間的污染物排放強度差異增幅最小,觀測期末較期初而言無太大的差距,除個別年份外,該地區間的差異呈現波動減少的趨勢。

圖5 新疆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地區間差異動態演變Figure 5 Dynamic evolution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agricultural non- point source polluti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Xinjiang
3.4 污染排放強度的動態演進
基于Dagum 基尼系數分解法的研究雖然呈現了新疆不同地區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差異的大小及其來源,反映出新疆地區農業面源污染強度的相對差異,但是無法刻畫農業面源污染強度絕對差異變化的動態演進過程。因此,本文利用Kernel 密度函數進一步分析新疆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的動態演進(圖6、表4)。

表4 新疆農業面源污染強度分布的動態演進特征Table 4 Dynamic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non- 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tensity distribution in Xinjiang

圖6 新疆各地區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的動態演進Figure 6 Dynamic evolution of agricultural non- point source polluti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various regions of Xinjiang
具體來看:①分布位置。觀測期內新疆總體核密度分布曲線隨著時間的推移整體呈現小幅度左移趨勢,表明新疆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逐漸減少,治理有一定的效果,但效果不明顯。南疆、北疆、東疆地區均出現左移趨勢。其中:東疆左移幅度最大,表明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降低最多,治理效果顯著;南疆和北疆的左移幅度比較小,說明治理效果不明顯。②分布形態。觀測期內新疆總體核密度分布曲線表現為主峰高度下降而寬度減小趨勢,表明新疆總體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總體離散程度呈縮小趨勢。各地區中,南疆地區核密度分布曲線表現為主峰高度先降低后升高、寬度變小的趨勢,表明南疆地區內部農業面源污染強度的絕對差異呈現擴大趨勢;北疆和東疆地區的核密度分布曲線均表現為主峰高度曲折降低、寬度變小的態勢,表明北疆和東疆地區內部農業面源污染強度的絕對差異呈現擴大的趨勢。③分布延展性。新疆總體和各地區核密度分布曲線均存在顯著的右拖尾現象,但延展性有所差異。新疆總體和北疆地區核密度分布呈現拓寬趨勢,表明農業面源污染強度與平均水平之間的差距持續增大;而東疆地區核密度分布呈現顯著的收斂趨勢,表明該地區內部農業面源污染強度較高的地州市同平均水平的距離有所縮減;南疆地區的分布延展趨勢不明顯。④極化特征。觀測期內新疆總體和各地區核密度分布曲線均呈現多峰或多峰現象,表明新疆總體和各地區的農業面源污染強度的發展存在兩級或多級分化的現象。北疆和東疆地區核密度分布曲線主峰核側峰間的距離從期初較小變化為后期的較大,說明前期北疆和東疆地區內部的農業面源污染強度差異不明顯,到后期差異逐漸增大。南疆地區觀測期內個別年度出現了單峰現象,此時極化現象不顯著,較緩和。除此之外,南疆地區還表現為雙峰特征,污染物排放強度仍然存在較小程度的空間極化現象。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針對新疆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的時空分異,本文利用14 個地州市2000—2019 年的面板數據,在利用清單分析法測算新疆農業面源污染排放量及排放強度的基礎上,結合Dagum 基尼系數分解和Kernel核密度估計考察了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的空間差異及動態演進。主要結論如下:①新疆農業面源污染排放主要集中于農田固體廢棄物和禽畜養殖污染。2000—2019 年,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呈曲折下降態勢。在南疆、北疆、東疆分布中,北疆污染物排放量最高,南疆次之,東疆污染物排放量最少。同時,空間差異也非常明顯,污染物排放強度較高值主要分布在北疆和東疆地區,排放強度較低值主要分布在克拉瑪依市、塔城地區和阿克蘇地區,說明新疆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由南北兩端向中心階梯式遞減,治理效果沿著天山山脈,由中心向南北兩端逐漸凸顯的分布特征。農業面源污染雖然得到了一定的治理,但是總體來說形勢依舊嚴峻。就已有文獻看,大多數文獻在研究時缺乏“因地制宜”,更多的是“一刀切”。大多數學者對污染物排放強度進行計算時,使用污染排放量與土地總面積作比,但新疆區域面積居全國第一,過大的分母導致新疆污染物排放強度計算偏低。此外,就目前新疆農業經濟發展狀況來看,農業經濟在快速增長的同時帶來的是農藥、化肥等污染物的高投入與農田固體廢棄污染物、禽畜養殖污染物的高產出,農業面源污染仍是新疆農業現代化發展中亟需解決的一個重要障礙。農戶對資源集約化、循環利用、養地護地、秸稈還田等認識不足、規模化養殖程度低等因素導致新疆農業面源污染問題依舊嚴峻。②2000—2019 年,污染物排放強度總體基尼系數以2009 年和2013 年為拐點表現出“N”形變化趨勢。地區內差異是總體差異的最主要來源,觀測期內貢獻率位于30.97%—43.38%之間;其次,超變密度是第二來源,其貢獻率在12.40%—47.92%之間;新疆地區間差異對總體差異的貢獻最小,觀測期內貢獻率位于10.97%—46.22%之間。即,新疆農業面源污染排放強度差異來源的貢獻程度為:地區內差異>超變密度>地區間差異。③觀測期內新疆總體核密度分布曲線隨著時間的推移整體呈現小幅度左移趨勢,農業面源污染逐漸緩和,南疆、北疆、東疆地區均出現左移趨勢,左移幅度東疆>南、北疆;觀測期內新疆總體分布曲線表現為主峰高度下降、寬度減小的趨勢,污染物排放強度離散程度呈減弱的趨勢;新疆總體和各地區分布曲線均存在顯著的右拖尾現象,但延展性有所差異;觀測期內新疆總體和各地區分布曲線均呈現多峰或多峰現象,新疆總體和各地區的農業面源污染強度發展存在兩級或多級分化現象。
4.2 建議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①充分發揮高校在“科技發明的最初一公里”的牽引作用,力求科技發明落地,將論文和發明應用到大地上,充分解決新疆地區因科技含量低造成的污染問題。②充分發揮科技特派員作用,借助農民夜校、知識大講堂、農民技工培訓學校、農牧民培訓中心,帶動知識水平較高的農戶由傳統農業向綠色農業轉變,通過“傳、幫、帶”形式,帶動區域整體農業轉型,如綠色農業的重要性教育、新技術宣傳應用教育、秸稈還田教育、養地護地教育等。③減少化肥、農藥和塑料薄膜等化學物質的使用,加強生物農藥等生物資源的應用,避免因過度使用化肥和農藥造成的化學物質殘留污染。④加強規模化養殖,提高農家肥的使用率;通過精細化飼料分配,加強控制牛、羊等大牲畜的碳排放。⑤當地政府在制定農業面源污染防控及治理措施時應因地制宜,充分結合各區域農業經濟發展趨勢、氣候環境等制定相應的管控措施。此外,農業面源污染較重的地區應加強與內地的交流與合作,引進新型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與管理經驗,逐步縮小差距,實現面源污染治理與農業增長共贏。
4.3 討論
本文結論可為新疆各地區定向制定專項治理政策時提供借鑒與參考。事實上,農業面源污染不僅受到區域內種養殖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影響,還會受到相鄰區域的影響,本文在進行研究時未對其空間溢出效應進行檢驗。近年來,國家將治理面源污染擺在重要的位置上,下一步應著重對新疆各地區農業面源污染排放量的趨勢預測、空間溢出效應與治理效率上作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