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早期血清IL-33和sST2及其比值與妊娠期糖尿病的相關性
李秀娟,張林林,于志娟
(1.赤峰市醫(yī)院產科,內蒙古 赤峰 024000;2.阿魯科爾沁旗婦幼保健計劃生育服務中心產科,內蒙古 赤峰 025550)
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是妊娠期常見的合并癥之一,相關流行病學調查顯示我國GDM的發(fā)病率約為17.5%[1]。GDM不僅影響母胎安全,增加早產、難產、巨大兒、新生兒低血糖等不良妊娠結局的發(fā)生風險,也顯著增加了孕婦遠期罹患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風險[2]。目前,GDM的診斷主要依賴于孕24~28周時口服葡萄糖耐量試驗(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OGTT)檢查,缺乏早期評估GDM發(fā)病的有效手段。近年,多項國內外隊列研究對孕早期孕婦進行了隨訪觀察,發(fā)現(xiàn)孕早期血常規(guī)指標及生化指標對GDM的發(fā)病具有預測價值,但不足之處是預測效能較差、靈敏度和特異度均較差[3-5]。因此,尋找孕早期預測GDM的標志物不僅有助于GDM的早期篩查及干預,也有助于深入認識GDM的發(fā)病機制。
微炎癥反應的持續(xù)激活在GDM及2型糖尿病的發(fā)病中均起到重要作用,多種炎癥細胞因子的分泌紊亂介導了胰島素抵抗,進而參與了GDM及2型糖尿病的發(fā)生發(fā)展。白介素(interleukin,IL)-33屬于IL-1家族,其生物學功能是通過識別膜受體腫瘤抑制素2(suppression of tumorigenicity 2,ST2)抑制炎癥反應;可溶性ST2(soluble suppression of tumorigenicity 2,sST2)通過與膜受體ST2競爭性結合IL-33的方式起到促炎作用[6]。有基礎研究報道,外源性給予IL-33可顯著改善糖尿病小鼠及糖尿病前期小鼠的糖代謝,提示IL-33在糖尿病發(fā)病中起保護作用[7];但IL-33和糖尿病相關的臨床研究結果與基礎研究報道并不一致,GDM患者血清中IL-33水平均顯著升高[8],異常升高的IL-33在糖尿病發(fā)病中起促進作用還是代償性保護作用并不清楚。因此,為了系統(tǒng)地認識IL-33/ST2軸在GDM發(fā)病中的作用及評估價值,本研究以血清IL-33、sST2作為標志物,分析孕早期母體血清IL-33、sST2水平及其比值與GDM的相關性。
1 研究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擇2017年4月至2020年12月期間在赤峰市醫(yī)院定期產檢的孕婦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孕8~12周時在本院早孕門診建檔,完成血常規(guī)及生化檢驗;②單胎妊娠;③定期產檢,孕24~28周時完成75g OGTT;④臨床資料及樣本完整。排除標準:①既往有糖尿病、高血壓、貧血、甲狀腺疾病等病史;②妊娠期合并妊娠期高血壓、肝內膽汁淤積癥等并發(fā)癥。本次共納入244例孕婦,根據(jù)OGTT結果、參照《妊娠合并糖尿病診治指南(2014)》[9]中GDM的診斷標準進行分組,其中GDM組40例、正常葡萄糖耐量(normal glucose tolerance,NGT)組204例。本研究獲得醫(y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倫理[2017]第46號)。
1.2 方法
1.2.1 血清IL-33和sST2水平的檢測
孕早期建檔時,采集空腹外周靜脈血5~6mL于生化采血管內,靜置30min后凝血,以3 000r/min離心10min后分離上層血清,采用酶聯(lián)免疫吸附法試劑盒(上海西唐生物公司)檢測IL-33和sST2水平。
1.2.2 臨床資料的收集
孕早期建檔時,收集臨床資料:孕婦的年齡、孕次、產次、孕前體質量指數(shù)(body mass index,BMI)、孕早期增重、收縮壓(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舒張壓(diastolic blood pressure,DBP)、血紅蛋白(hemoglobin,Hb)、紅細胞計數(shù)(red blood cell,RBC)、白細胞計數(shù)(white blood cell,WBC)、血小板計數(shù)(platelet,PLT)、谷丙轉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谷草轉氨酶(aspartate transaminase,AST)、堿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γ-谷氨酰基轉移酶(γ-glutamyl transferase,GGT)、甘油三酯(triacylglycerol,TG)、總膽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
孕中期時,收集OGTT資料:空腹血糖(fasting plasma glucose,F(xiàn)PG)、空腹血胰島素(fasting insulin,F(xiàn)-Ins),參照穩(wěn)態(tài)模型計算胰島素抵抗指數(shù)(homeostatic model assessment for insulin resistance,HOMA-IR),HOMA-IR=FPG×F-Ins/22.5。
1.3 統(tǒng)計學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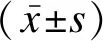
2 結果
2.1 GDM組與NGT組的一般資料
本研究共納入244例孕婦,有40例發(fā)生了GDM,發(fā)生率為16.39%。
GDM組的年齡、孕前BMI、孕早期增重均顯著高于NGT組(P<0.05),而孕次、產次≥1次的分布與NGT組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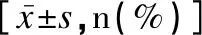
表1 GDM組與NGT組一般資料的比較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between the GDM group and the NGT
2.2 GDM組與NGT組孕早期的實驗室指標
GDM組孕早期的IL-33/sST2比值低于NGT組,Hb、RBC、WBC、TG、TC、GGT、ALP、IL-33、sST2水平均顯著高于NGT組(P<0.05),而PLT、ALT、AST與NGT組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GDM組與NGT組孕早期實驗室指標的比較Table 2 Comparison of laboratory indexes in the first trimester of pregnancy between the GDM group and the NGT
2.3 GDM組孕早期血清IL-33和sST2水平及其比值與孕中期OGTT結果的相關性
在GDM組,孕早期血清IL-33水平與孕中期OGTT時的FPG、HOMA-IR均呈負相關(r=-0.434,P=0.005;r=-0.391,P=0.013),孕早期血清sST2水平與孕中期OGTT時的FPG、HOMA-IR均呈正相關(r=0.373,P=0.018;r=0.343,P=0.030),孕早期IL-33/sST2比值與孕中期OGTT時的FPG、HOMA-IR均呈負相關(r=-0.546,P<0.001;r=-0.534,P<0.001),見圖1。
2.4 GDM相關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
以是否發(fā)生GDM為因變量,以兩組間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的因素為自變量,在Logistic回歸模型中進行分析,采用逐步回歸法篩選變量,最終IL-33、sST2、IL-33/sST2、孕前BMI、孕早期增重、Hb、TC、GGT納入模型,分析結果顯示:IL-33、IL-33/sST2、Hb、TC均是發(fā)生GDM的影響因素(P<0.05),見表3。

表3 GDM相關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Table 3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GDM related factors
2.5 血清IL-33水平及IL-33/sST2比值預測GDM的ROC曲線分析
血清IL-33水平及IL-33/sST2比值兩項指標對GDM具有預測價值(P<0.05),ROC曲線見圖2A、圖2B、表4。根據(jù)Logistic回歸分析得到回歸方程:-31.119+0.377×IL-33-24.840×IL-33/sST2+0.073×Hb-1.496×TC,以該方程為聯(lián)合指標預測GDM的ROC曲線見圖2C,聯(lián)合指標對GDM具有預測價值(P<0.05),見表4。
3 討論
GDM的發(fā)病機制未明,也缺乏孕早期評估GDM發(fā)病風險的標志物[10]。本研究以IL-33/ST2軸為切入點,以孕中期(24~28周)時75g OGTT作為診斷GDM的金標準,分析GDM孕早期的篩查標志物,旨在為臨床上孕早期評估GDM發(fā)病風險并進行干預提供參考依據(jù),也為今后深入認識GDM的發(fā)病機制提供思路。本研究共納入244例孕婦,有40例發(fā)生了GDM,發(fā)生率占16.39%,接近相關流行病學調查報道17.5%的GDM發(fā)病率[1]。
3.1 IL-33/ST2軸的研究現(xiàn)狀
IL-33/ST2軸具有抗炎活性,IL-33與細胞膜受體ST2結合后,通過調控下游叉頭狀轉錄因子p3(forkhead box protein 3,F(xiàn)oxp3)、腫瘤壞死因子受體相關因子6(TNF receptor associated factor 6,TRAF6)、髓樣分化因子88(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 88,MyD88)、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等表達的方式,減少促炎因子釋放、增加抗炎因子釋放,進而在炎癥反應的激活中起抑制作用[11]。Hasan等[12]研究顯示,糖尿病前期及2型糖尿病患者脂肪組織中IL-33和ST2表達降低與炎癥基因TRAF6、MyD88、NF-κB等,以及促炎因子CCL2、IL-1β表達增加有關,提示IL-33/ST2軸在糖尿病的發(fā)病過程中起抗炎作用。sST2是膜受體ST2裂解后釋放進入血液循環(huán)的產物,能夠與ST2競爭性結合IL-33,拮抗IL-33/ST2軸的抗炎作用,進而介導促炎效應,并參與胰島素抵抗的發(fā)生[13]。多項臨床研究證實,血清中sST2的增多與2型糖尿病及相應的大血管并發(fā)癥、微血管并發(fā)癥發(fā)病有關[14-16]。
3.2 GDM發(fā)病過程中IL-33/ST2軸的變化
GDM的發(fā)病與2型糖尿病及肥胖存在共同的病理、生理特征,即胰島素抵抗,炎癥反應的激活是影響胰島素敏感性、加重胰島素抵抗的關鍵生物學環(huán)節(jié)。已有研究證實,2型糖尿病及肥胖患者血清IL-33和sST2均有增加,但在相關性分析中顯示,具有抗炎作用的IL-33與胰島素抵抗程度呈負相關,具有促炎活性的sST2與胰島素抵抗程度呈正相關[13,17]。另有妊娠相關研究證實,孕早期sST2的檢測可作為評價子癇前期的標志物[18-19]。本研究將IL-33、sST2作為孕早期篩查GDM的標志物,與NGT孕婦比較,GDM患者孕早期的血清IL-33和sST2水平均明顯升高,且孕早期血清IL-33水平與孕中期OGTT時血糖水平及胰島素抵抗程度均呈負相關,孕早期血清sST2水平與與孕中期OGTT時血糖水平及胰島素抵抗程度均呈正相關,提示孕早期血清IL-33和sST2水平的增高與GDM的發(fā)病及胰島素抵抗的程度有關。
3.3 IL-33/ST2軸與GDM病情的關系
Pavlovic等[7]研究顯示,IL-33具有改善炎癥反應及胰島素抵抗的生物學活性。本研究中血清IL-33水平與血糖水平及胰島素抵抗程度均呈負相關的結果符合IL-33的生物學活性,基于此推測GDM患者孕早期血清IL-33水平升高可能是機體自身代償?shù)恼{控機制,通過代償性增加IL-33水平的釋放來減輕炎癥反應及胰島素抵抗。已有研究證實了sST2的促炎活性,妊娠過程中sST2生成增加可能與肥胖因素、飲食因素等有關,孕早期增多的sST2水平通過其促炎作用影響胰島素敏感性,并在孕期逐步加重胰島素抵抗,最終導致GDM的發(fā)生[13]。因為IL-33的抗炎作用和sST2的促炎作用相互影響、相互調控,所以本研究通過IL-33/sST2比值來反映IL-33抗炎作用與sST2促炎作用的平衡關系。GDM患者孕早期IL-33/sST2比值低于NGT孕婦,且與血糖水平及胰島素抵抗程度均呈負相關,表明雖然GDM孕早期血清IL-33、sST2水平均有增加,但通過比值的分析可以推測sST2的增加程度較IL-33更為顯著,IL-33/sST2的平衡向sST2所介導的促炎作用偏移;隨著IL-33/sST2平衡向sST2偏移的加重,IL-33/sST2比值降低且胰島素抵抗程度加重。
3.4 IL-33/ST2軸預測GDM的價值
有研究顯示,孕早期血常規(guī)指標Hb、RBC、WBC,以及生化指標TG、TC、GGT、ALP的異常均與GDM的發(fā)病有關[3-5,20]。本研究比較了GDM患者與NGT孕婦孕早期的臨床資料,結果顯示GDM患者的年齡、孕前BMI、孕早期增重及Hb、RBC、WBC、TG、TC、GGT、ALP均與NGT孕婦存在顯著性差異,與已有研究結果一致。本研究進一步在Logistic回歸模型中分析GDM的影響因素可知,IL-33、IL-33/sST2、Hb、TC均是發(fā)生GDM的影響因素;經ROC曲線驗證,單一使用IL-33和IL-33/sST2檢測均對GDM的發(fā)病具有預測價值,但預測效能較低,曲線下面積均不足0.70;根據(jù)Logistic回歸分析得到回歸方程,將該方程作為檢測IL-33、IL-33/sST2、Hb、TC的聯(lián)合指標,其對GDM的發(fā)病具有預測價值,且預測效能理想,曲線下面積接近0.85,靈敏度和特異度均超過80%。
綜上所述,孕早期母體血清IL-33、sST2水平及其比值的變化與GDM的發(fā)病有關。GDM患者孕早期血清IL-33和sST2水平增加、IL-33/sST2比值降低,結合IL-33與胰島素抵抗程度呈負相關,sST2與胰島素抵抗程度呈正相關的相關性結果分析,GDM孕早期血清IL-33水平增高是自我保護的代償機制,代償性分泌不足會使其代償妊娠過程中胰島素抵抗的功能減弱,進而造成GDM的發(fā)生。同時,本研究還初步探索了GDM的預測模型,聯(lián)合使用IL-33、IL-33/sST2、Hb、TC指標,根據(jù)回歸方程對GDM進行預測,具有較好的預測效能和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