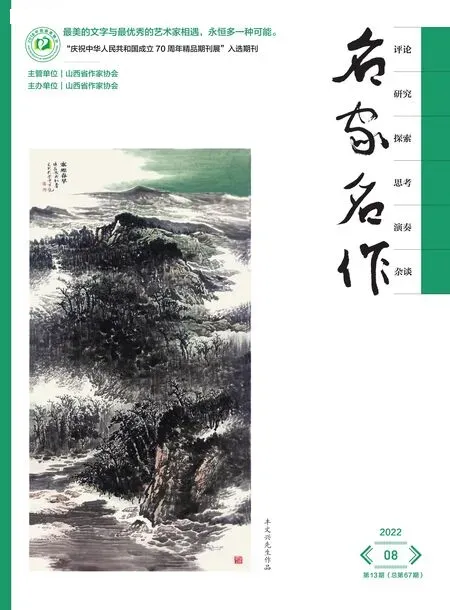音樂演繹中“理解”的若干思考
——讀郟而慷《音樂演繹的忠實性與創造性研究》有感
2022-09-08 05:57:32何冰鈺
名家名作
2022年13期
何冰鈺
一、《音樂演繹的忠實性與創造性研究》基本概述
郟而慷博士在《音樂演繹的忠實性與創造性研究》一書中運用現象學原理,輔以釋義學、符號學、社會學,探究作品的本質特征在何處。首先,作者從作品的“在世存在”出發,以作為作品信息表象的樂譜文本和直觀表象的音響作為探究作品本質的切入口,先對其表象進行分析。其次,作者將音樂的運動形態與語言的運動形態相比較,從音樂的運動方式分析音樂語言與普通語言的相似之處,采用“家族相似”“類加種差”“格式塔質”以及伽達默爾的“視界融合”等前人觀點做引證,闡釋主體對作品對象的忠實是在不斷理解中生成的,并且確定了原作的存在方式——存在于每一次正確的、不同的形態中。再次,作者通過對貝多芬《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不同演奏版本的考查和分析,化抽象為具體,發現主體對客體的創造性存在于主體時刻變化的意識和理解中,而產生的創造性存在一種普遍規律,這種普遍規律作者用“類加種差”進行解釋,無論從縱向還是橫向角度,最終生成的創造性一定暗含了某種規律,而這種規律必然包含了差異的、具體的同一性。最后,作者將文章的整體思路和核心概念用六個小標題進行總結,將文章中探究出的結論整理出一條完整的邏輯思路,為讀者對音樂演繹中忠實性和創造性的學習提供清晰豐富的理論成果。
其中,音樂演繹中的“理解”問題貫穿全文,也是主體探究音樂作品本質規律過程中時刻需要思考的問題。……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南大法學(2021年3期)2021-08-13 09:22:32
阿來研究(2021年1期)2021-07-31 07:39:04
小天使·一年級語數英綜合(2020年3期)2020-12-16 02:56:12
中國自行車(2018年9期)2018-10-13 06:17:10
藝術啟蒙(2018年7期)2018-08-23 09:14:16
兒童繪本(2017年24期)2018-01-07 15:51:37
東方藝術·大家(2016年6期)2016-09-05 07:30:56
金色年華(2016年13期)2016-02-28 01:43:27
山西大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6期)2015-01-22 07:22:22
外語學刊(2011年3期)2011-01-22 03:4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