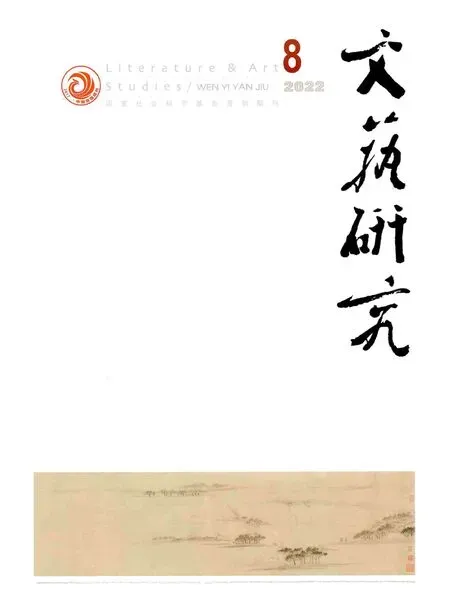北宋“太學(xué)新體”考論
——以張方平慶歷六年科舉奏章為中心
林 巖
慶歷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作為同知貢舉的張方平向朝廷上了一份奏章。此時省試閱卷剛剛完畢,而殿試尚未舉行。他說:
未盡詳之。伏乞朝廷申明前詔,更于貢院前榜示,使天下之士知循常道。臣典司憲度,復(fù)預(yù)文衡,敢此敷聞,伏候進止。
按照宋代慣例,一般多在科考之前發(fā)布詔書,提醒舉子在科場寫作中要避免出現(xiàn)哪些情況,但此份奏狀卻是提交于省試閱卷結(jié)束之后,難免令人疑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奏章中,張方平不僅將那些違背科場程式的文風(fēng)稱為“太學(xué)新體”,而且將其形成的源頭直接歸咎于太學(xué)官員石介,為了杜絕太學(xué)新體”的出現(xiàn),他甚至請求朝廷將申誡詔書張榜于貢院之前。張方平批判的矛頭指向如此明確,且如此大張旗鼓,顯然已經(jīng)超越了科舉,而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張方平的這篇奏章因為首次提及“太學(xué)新體”,故引起了一些學(xué)者的關(guān)注。人們在討論北宋古文運動的曲折進程時,常常把“太學(xué)新體”作為一環(huán)討論。盡管有一些學(xué)者注意到“太學(xué)新體”的出現(xiàn)與“慶歷新政”存在關(guān)聯(lián),但是,張方平的這篇奏章本身卻沒有引起足夠重視,人們只是將其作為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知貢舉時打擊“險怪”文風(fēng)(或稱之為“太學(xué)體”)的一個前奏曲,給予正面評價。本文則嘗試聯(lián)系當(dāng)時“慶歷新政”失敗不久的政治情勢,從新政反對者(張方平即是其中一員)的角度來審視他們?nèi)绾慰创疤珜W(xué)新體”的形成,以及為何要清除其影響。
一、天圣詔書與“景祐變體”
據(jù)祝尚書考證,張方平奏章中所說“景祐元年有以變體擢高第者”,乃是景祐元年的狀元張?zhí)魄洌?dāng)年殿試的題目是“房心為明堂賦”“和氣致祥詩”“積善成德論”。根據(jù)韓琦所撰墓志銘,張?zhí)魄洳粌H與石介、韓琦有著密切的交往,而且他還得到了范仲淹的賞識:
文正范公亦知君為深,常與余評論人物,喟然謂余曰:“凡布衣應(yīng)科舉,得試殿廷下,必婉辭過謹,以求中格,人情之常也。而張某者為《積善成德論》,獨言切規(guī)諫,冀以感寤人主,立朝可知矣。使今而在,必以直道為一時名臣。”其推重如此。
上述史料值得注意者有二:一是景祐元年狀元張?zhí)魄渑c后來的慶歷改革派官員有著密切的人際交往;二是他受到激賞的科場文章并非律賦而是論,因為寓含諷諫而獲褒獎。范仲淹、石介一直主張在科舉考試中應(yīng)重視策論而不是詩賦,而張?zhí)魄淝『靡陨瞄L策論而中了狀元,此中緣由,耐人尋味。
(一)作為轉(zhuǎn)折點的天圣七年(1029)詔書
景祐元年之前的一次科考,發(fā)生在天圣八年,即歐陽修登科中進士的那一年。按照慣例,此科的選拔性考試——解試應(yīng)在前一年的秋季舉行。但在天圣七年五月二日,朝廷下了一道詔書:
俊,以助化源。而褒博之流,習(xí)尚為弊,觀其著撰,多涉浮華。或磔裂陳言,或會粹小說,好奇者遂成于譎怪,矜巧者專事于雕鐫。流宕若茲,雅正何在。屬方開于貢部,宜申儆于詞場。當(dāng)念文章所宗,必以理實為要,探典經(jīng)之旨趣,究作者之楷模,用復(fù)溫純,無陷偷薄。庶有裨于國教,期增闡于儒風(fēng)。咨爾多方,咸體朕意。
這道詔書的頒布,顯示朝廷不滿于當(dāng)時科場的浮華文風(fēng),而其矛頭所指,顯然就是風(fēng)行一時、注重駢儷和典故堆砌的西昆體文風(fēng)。
天圣八年登科的歐陽修,以親歷者的身份對這道詔書產(chǎn)生的效力給予了充分肯定,多次在著作中提及。如景祐四年,他在所作《與荊南樂秀才書》中說:“天圣中,天子下詔書,敕學(xué)者去浮華,其后風(fēng)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為,彬彬有兩漢之風(fēng)矣。”皇祐三年(1051),他在為蘇舜欽文集所作序言中寫道:
天圣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xué)者務(wù)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以相夸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后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xué)者以近古,由是其風(fēng)漸息,而學(xué)者稍趨于古焉。
嘉祐五年,他在舉薦蘇軾的奏狀中也說:
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xué)者以近古,蓋自天圣迄今二十余年,通經(jīng)學(xué)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shù)。
南宋人對天圣下詔也給予了高度評價,如呂中說:
祐之時,實萌于天圣之初矣。唐文變于韓、柳,我朝之文雖倡于歐陽,而實變于仁宗。
根據(jù)這些記述,天圣七年詔書顯然意味著一個轉(zhuǎn)折點的出現(xiàn),至少它代表了一種試圖轉(zhuǎn)變科場文風(fēng)的官方意志。
(二)科舉考試中策論地位的提升
伴隨著天圣七年詔書的頒布,科舉對策論給予了越來越多的重視。此后,朝廷幾乎在每次開科之時,都會發(fā)布詔書,要求重視策論考校。
約真宗朝末期,已有知貢舉官員以策論成績決定士人登科與否。西昆體的代表人物之一劉筠就是一個典型。《宋史·劉筠傳》載:
筠,景德以來,居文翰之選,其文辭善對偶,尤工為詩。初為楊億所識拔,后遂與齊名,時號“楊劉”。凡三入禁林,又三典貢部,以策論升降天下士,自筠始。
按,劉筠,大中祥符八年(1015),同知貢舉;天圣二年、天圣五年兩任知貢舉。作為重視駢儷文的西昆體代表人物,他竟然也重視以散體文為主的策論,這是文風(fēng)轉(zhuǎn)變的一個信號。
從天圣五年開始,朝廷陸續(xù)發(fā)布詔書,要求貢院在省試中注重考校策論。當(dāng)年正月,省試開始之前,朝廷發(fā)布詔書:“詔禮部貢院比進士以詩賦定去留,學(xué)者或病聲律而不得騁其力,其以策論兼考之。”《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下文簡稱《長編》)卷一一三載,明道二年(1033)十月“辛亥,上諭輔臣曰:‘近歲進士所試詩賦多浮華,而學(xué)古者或不可以自進,宜令有司兼以策論取之’”。可見,在科舉考試中重視策論,乃是為了促使士人去除浮華轉(zhuǎn)而學(xué)古。次年即景祐元年三月一日,朝廷再次下詔:
貢院所試進士,除詩、賦依自來格式考定外,其策、論亦仰精研考校,如詞理可采,不得遺落。賦如欲不依次押官韻者聽。
這些一再發(fā)布的詔書,顯示從天圣年間開始,策論在科舉考試中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雖然律賦仍在科場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但策論成績無疑也會影響到應(yīng)考士子能否被錄取。這顯然是對天圣詔書的一個有力回應(yīng)。
(三)“景祐變體”出現(xiàn)的意義
天圣詔書的頒布、科場中策論地位的提升,都是朝廷為了轉(zhuǎn)變科場風(fēng)氣而實施的舉措,這構(gòu)成了景祐元年張?zhí)魄涞弥袪钤臍v史語境。反過來說,張?zhí)魄湓诘钤囍幸哉擉w文表達時事關(guān)懷,且能獲取高第,正表明科場風(fēng)氣已然發(fā)生轉(zhuǎn)變,政策舉措取得了預(yù)期效果。
不應(yīng)忽視的是,此一時期恰好也是古文逐步得到認可的時期。《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二引蔡寬夫《詩話》云:“景祐、慶歷后,天下知尚古文。”這說明,到了景祐年間,古文的影響力在士人階層中逐漸擴大,所以,張?zhí)魄淠芎头吨傺汀⑹檫@樣的古文家建立起密切的關(guān)系。這并非偶然事件,而是意味著具有共同政治傾向和文學(xué)追求的士人開始有意識地集結(jié)。
張?zhí)魄涫艿酵浦氐摹斗e善成德論》無疑是用散體文撰寫的,而且表達了對時事的關(guān)懷,這都符合古文家的主張。張方平之所以稱其為“景祐變體”,或許意在指出,古文家的影響不僅滲透到科場文風(fēng)中,而且他們已經(jīng)開始通過科場文章來表達政治見解與時事關(guān)懷。
更重要的是,張?zhí)魄浣煌哪切┕賳T士大夫如范仲淹、韓琦、石介,都是當(dāng)時政治改革的積極倡導(dǎo)者,更是后來“慶歷新政”的主導(dǎo)者和參與者。他們都鼓勵士人通過古文寫作來議論時政、改造社會。張?zhí)魄滹@然受到了他們政治熱情的影響,才會在殿試文章中寓含諷諫。而這,在張方平看來,則是一種不良傾向。
二、“太學(xué)新體”與“慶歷新政”
張方平在慶歷六年的科舉奏章中特別指出,自景祐至慶歷的十余年里,科場文風(fēng)有一個逐漸演化的過程,而太學(xué)的建立以及太學(xué)直講石介的推波助瀾,造成了科場文風(fēng)的惡化。他說:
顯然,張方平將石介視為“太學(xué)新體”形成的一個主要推動者。那么,石介何以能夠促成一種科場文風(fēng)的形成,有沒有外部條件的刺激?這是一個必須探討的問題。
(一)石介與慶歷年間的太學(xué)
自宋初立國至慶歷三年,長達八十余年的時間里,國子監(jiān)是京城唯一的中央官辦學(xué)校。其下按專業(yè)分設(shè)三館:廣文、太學(xué)、律學(xué),“廣文教進士,太學(xué)教九經(jīng)、五經(jīng)、三禮、三傳學(xué)究,律學(xué)館教明律”。原則上說,國子監(jiān)招錄的學(xué)生主要是“京朝官七品以上子孫”,但實際上執(zhí)行并不嚴(yán)格。慶歷三年二月,又設(shè)立了四門學(xué),“以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孫補充學(xué)生”。無論國子學(xué)還是四門學(xué),招錄學(xué)生的人數(shù)都相當(dāng)有限。
慶歷四年三月,作為新政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朝廷頒布了鼓勵州縣興建學(xué)校、改革貢舉考試規(guī)定的詔令,特別要求學(xué)生須在學(xué)校聽讀一段時間才具備參加解試的資格。于是一個月后,判國子監(jiān)王拱辰等官員請求在錫慶院興建太學(xué),由此確立了太學(xué)的獨立地位。太學(xué)校址的選擇有點波折:慶歷五年正月,朝廷下詔要求太學(xué)放棄錫慶院校址,二月另選定馬軍都虞侯公廨作為校址。
據(jù)陳植鍔考證,石介在慶歷二年六月?lián)螄颖O(jiān)直講,至慶歷四年十月才離開國子監(jiān),赴任濮州通判。也就是說,石介前后在太學(xué)的時間不到兩年半,但恰好碰上了太學(xué)興建的好時機。與此同時,經(jīng)由石介推薦,孫復(fù)也于慶歷二年十一月?lián)螄颖O(jiān)直講。
曾任國子監(jiān)長官的田況對慶歷初年國子監(jiān)講學(xué)的盛況有如下記述:
漸不可遏。
根據(jù)這段記述,生員具備一定聽讀時間才可參加科考的規(guī)定導(dǎo)致國子監(jiān)入學(xué)人數(shù)暴增,于是才有了占用錫慶院擴充太學(xué)的舉措。正是借此契機,石介擁有了面向眾多學(xué)生講學(xué)的機會。歐陽修在為石介所撰墓志銘中說的“及在太學(xué),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眾,太學(xué)之興自先生始”,顯然應(yīng)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理解。
石介在太學(xué)講學(xué)之所以能造成轟動性影響,無疑與他對時政的關(guān)切和議論直接相關(guān)。除了田況明言石介喜議時事、造成“群謗喧興”的局面外,慶歷七年,御史何郯在論及石介時也有如是評價:
緣石介平生,頗篤學(xué)問,所病者,道未周而好為人師,致后生從學(xué)者多流蕩狂妄之士。又在太學(xué)日,不量職分,專以時事為任。
由此可以推測,石介在太學(xué)直講任上經(jīng)常面向太學(xué)生評論時事政治。
石介喜議時政的一個直接證據(jù),就是他在太學(xué)任教期間撰寫的與時局變動緊密相關(guān)的《慶歷圣德頌》,時在慶歷三年四月。此前不久,仁宗皇帝將范仲淹、富弼、韓琦引入權(quán)力中樞,同時任命歐陽修、余靖、蔡襄等為諫官,而呂夷簡則離開朝廷,夏竦的樞密使職務(wù)被罷免,這一切預(yù)示著“慶歷新政”的帷幕即將拉開。石介《慶歷圣德頌》就是對此事件的記述,詩中甚至使用了“退奸進賢”等帶有強烈褒貶色彩的語言,引發(fā)了一場風(fēng)波。同時人田況說:
范仲淹、富弼初被進用,銳于建謀作事,不顧時之可否。時山東人石介方為國子監(jiān)直講,撰《慶歷圣德詩》以美得人,中有“惟仲淹、弼,一夔一契”之句,氣類不同者,惡之若仇。未幾,謗訾群興,范、富皆罷為郡,介詩頗為累焉。
顯然,作為慶歷改革派官員的支持者,石介試圖利用太學(xué)制造輿論,通過向太學(xué)生發(fā)表自己對于時事的看法,以影響士人階層的政治傾向。或許正是因為他強烈支持政治改革,所以新政派官員一度有舉薦他任諫官的打算,后來考慮到他激進的行為方式,最終放棄了。
(二)慶歷年間的貢舉新制
作為“慶歷新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州縣興學(xué)與貢舉改革緊密相關(guān)。除了規(guī)定舉子必須在學(xué)校聽讀一段時間才可應(yīng)舉之外,科舉內(nèi)容方面的新規(guī)定也值得留意。
慶歷四年三月,圍繞貢舉改革,一些官員討論后提出了一個綜合意見。他們認為:
專分析這些建議,可以看出:第一,他們凸顯了策論的重要性,建議在科舉考試中先根據(jù)策論成績進行篩選,合格者才能進入下一輪考試;第二,放松了對詩賦聲律方面的要求,以使考生有更大的發(fā)揮余地。因當(dāng)時的主政者是范仲淹等改革派官員,這些主張隨即被朝廷全盤接受,并發(fā)布了正式的詔令:
進士試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jīng)墨義。又以舊制用詞賦,聲病偶切,立為考式,一字違忤,已在黜格,使博識之士,臨文拘忌,俯就規(guī)檢,美文善意,郁而不伸。如白居易《性習(xí)相近遠賦》、獨孤綬《放馴象賦》,皆當(dāng)時試禮部,對偶之外,自有義意可觀,宜許仿唐體,使馳騁于其間。
從這道詔令來看,天圣年間以來重視策論的呼聲得到了高度重視并落實。雖然律賦仍是考試內(nèi)容之一,但放松了原先十分嚴(yán)苛的聲律要求,且允許仿照唐人寫賦的體式,以便考生自由發(fā)揮。
對于貢舉新制頒布后的影響及其在新政失敗后的命運,田況做了如下描述:
詔既下,人爭務(wù)學(xué),風(fēng)俗一變。未幾,首議者多出外官。所見不同,競興譏詆,以謂俗儒是古非今,不足為法,遂追止前詔,學(xué)者亦廢焉。
也就是說,貢舉新制的頒布對當(dāng)時的科場文風(fēng)確實發(fā)生了不小的影響。但是,到了慶歷五年初,隨著改革派主要官員陸續(xù)被逐出朝廷,貢舉新制也就被停廢了。《長編》卷一五五載:
(慶歷五年,三月己卯——引者注)詔禮部貢院進士所試詩賦,諸科所對經(jīng)義,并如舊制考校。先是,知制誥楊察言前所更令不便者甚眾,其略以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故祖宗莫能改也。且異時嘗得人矣,今乃釋前日之利,而為此紛紛,非計之得,宜如故便。上下其議于有司,而有司請今者考校,宜且如舊制,遂降此詔。
當(dāng)時停廢貢舉新制的理由,主要是為了便于考校,對科場文風(fēng)并沒有太多指責(zé)。這與后來張方平的嚴(yán)厲批評有顯著區(qū)別。
由此可見,作為“慶歷新政”下的產(chǎn)物,太學(xué)內(nèi)部的教學(xué)方式與科舉考試規(guī)定都發(fā)生了顯著變化。這無疑提高了便于古文寫作的策論的地位,也鼓勵了議論時政的風(fēng)氣。“太學(xué)新體”正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出現(xiàn)的。
三、何謂“怪誕詆訕”
張方平奏章嚴(yán)厲批評了當(dāng)時的科場文風(fēng),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他使用了“以怪誕詆訕為高,以流蕩猥煩為贍”這樣的評語。此語究竟應(yīng)作何理解,張方平是基于何種理由做出如此評判的,這樣的評判是否合適?凡此種種,頗值得深究。惜乎已有研究多未論及,故這里擬作詳細考察。
(一)何謂“怪誕”
既然張方平認為是石介助長了這樣的風(fēng)氣,那么,我們應(yīng)該首先從石介身邊的朋友著眼,看有沒有稱得上“怪誕”的人物。石介所賞識的杜默,似乎算一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征引《隱居詩話》載:
東坡云:石介作《三豪詩》,略云:“曼卿豪于詩,永叔豪于文,杜默豪于歌也。”永叔亦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之歌少見于世,初不知之,后聞其篇云:“學(xué)海波中老龍,圣人門前大蟲,推倒楊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識也。永叔不欲嘲笑之者,此公惡爭名,且為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是京東學(xué)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后發(fā)者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
從蘇軾所引杜默的詩歌來看,杜默顯然有著強烈的衛(wèi)道意識,這與石介本人的價值理念頗有契合之處,但在表達方式上有些不倫不類、虛張聲勢,故而蘇軾覺得怪奇至極,對于石介為何欣賞表示不解。
此外,在慶歷四年十一月發(fā)生的“進奏院案”中,也能發(fā)現(xiàn)一些此類人物的影子。《長編》卷一五三載:
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同執(zhí)政,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而舜欽仲淹所薦,其妻又衍女也,少年能文章,議論稍侵權(quán)貴。會進奏院祠神,舜欽循前例用鬻故紙公錢召妓女,開席會賓客。拱辰亷得之,諷其屬魚周詢、劉元瑜等劾奏,因欲動揺衍。事下開封府治。于是舜欽及巽俱坐自盜,洙等與妓女雜坐,而休復(fù)、約、延雋、延讓又服慘未除,益柔并以謗訕周、孔坐之,同時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為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wǎng)盡矣!”
這個事件完全是改革派的政敵們借題發(fā)揮,意在搖撼范仲淹等人的政治地位,王益柔這個人物尤其值得注意。他本是寇準(zhǔn)的外孫,卻因為寫了一首《傲歌》而遭到貶逐。而據(jù)《長編》所引《王拱辰行狀》,其《傲歌》詩中有這么兩句:“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qū)為奴。”與杜默詩歌在風(fēng)格上極為相似,不僅語言夸張,而且思想也相當(dāng)怪異。這似可視為“怪誕”的一種表現(xiàn)。
杜默、王益柔詩歌都以一種夸張的方式顯露出故意迥異于常人的特征,而這,與歐陽修描述的“慶歷之學(xué)”具有某種相似之處。歐陽修《議學(xué)狀》說:
以怪異的思想、出格的言論博取關(guān)注,在常人看來無疑有點“怪誕”,卻也反映了慶歷年間言論較為自由的時代風(fēng)氣。這種風(fēng)氣隨著古文運動的展開,也滲透到了科場文章的寫作之中。蘇軾登科后在寫給歐陽修的《謝歐陽內(nèi)翰書》中說:
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風(fēng)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嘆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于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樸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余,而漸復(fù)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dāng),求深者或至于迂,務(wù)奇者怪僻而不可讀,余風(fēng)未殄,新弊復(fù)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zhuǎn)相摹寫,號稱古文。
因此,張方平所謂的“怪誕”,極有可能是指科場文章寫作中存在的一種思想怪異、語言浮夸晦澀的風(fēng)氣。
(二)何謂“詆訕”
“進奏院案”發(fā)生之后數(shù)天,朝廷突然發(fā)布詔令,指斥朋黨現(xiàn)象、按察使派遣和文壇風(fēng)氣。《長編》卷一五三載:
(慶歷四年十一月——引者注)己巳,詔曰:“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為朋黨,君明臣哲,垂榮無極,何其德之盛也。朕昃食厲志,庶幾古治,而承平之弊,澆競相蒙,人務(wù)交游,家為激訐,更相附離,以沽聲譽,至或陰招賄賂,陽托薦賢。又按察將命者,恣為苛刻,構(gòu)織罪端,奏鞫縱橫,以重多辟。至于屬文之人,類亡體要,詆斥前圣,放肆異言,以訕上為能,以行怪為美。自今委中書、門下、御史臺采察以聞。
朋黨問題是慶歷改革派遭到攻擊的一個最主要的罪名,按察使派遣也是“慶歷新政”的一項重要舉措。單從這兩點,足以看出詔令是針對改革派而發(fā)的。而此時,除了杜衍仍在朝中獨自支撐外,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都已被調(diào)離朝廷,“慶歷新政”實際上已經(jīng)宣告失敗。不過,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詔書還專門批評了當(dāng)時的文壇風(fēng)氣,尤其是“詆斥前圣,放肆異言,以訕上為能,以行怪為美”一句,幾乎就是張方平“以怪誕詆訕為高”一語的翻版。顯然,“慶歷新政”在文化方面的舉措及其影響,也引起了反對派的敵視。
隨著改革派官員被逐出朝廷,抨擊他們的言論也多了起來。概括起來,這些抨擊言論主要指責(zé)改革派官員喜歡攻擊他人、言辭過激、沽名釣譽。如曾經(jīng)是王拱辰下屬、參與“進奏院案”的監(jiān)察御史劉元瑜,就指斥慶歷時期以歐陽修為首的諫官,說他們“以進退大臣為己任,以激訐陰私為忠直,薦延輕薄,列之館閣,與相倡和,扇為朋比”。又《長編》卷一五四載:
圖自進,賴陛下圣明覺悟,比來此風(fēng)漸息。”上因言攻訐之弊曰:“凡此皆謂小忠,非大忠也。”
“慶歷新政”推行時期,改革派官員大膽進言與彈劾,現(xiàn)在都成為喜好攻訐、沽名釣譽的證據(jù)。
面對攻擊,歐陽修一直采取強硬的回擊姿態(tài)。如他在范仲淹去世后所寫《祭資政范公文》中說:“公曰彼惡,公為好訐;公曰彼善,公為樹朋。公所勇為,公則躁進;公有退讓,公為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就意在為范仲淹洗刷污名。而當(dāng)歐陽修晚年重回朝廷之后,他也試圖解釋慶歷改革派官員何以會蒙上喜好攻訐的壞名聲。他在《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中說:
國家自數(shù)十年來,士君子務(wù)以恭謹靜慎為賢。及其弊也,循默茍且,頹惰寬弛,習(xí)成風(fēng)俗,不以為非,至于百職不修,紀(jì)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并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shù)大臣,銳意于更張矣。于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jì)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為公相傾陷,或謂沽激(邀——引者校)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群言百端,幾惑上聽。
從歐陽修這些嚴(yán)肅的回應(yīng)和辯白可以想見,喜好攻訐已經(jīng)成為政敵加諸改革派官員的一項重要罪狀,而極力洗刷這種不白之冤,也成為改革派官員不得不承擔(dān)的一項重負。
因此,張方平奏章中所說的“以怪誕詆訕為高”,似可從兩個方面理解:一方面是“怪誕”,主要指思想的怪異和語言的浮夸晦澀;另一方面是“詆訕”,主要指喜好評論時事、議論人物,對政治弊端進行批判。這正是慶歷時期言路大開的自然結(jié)果。它們反映了“慶歷新政”下的兩種風(fēng)氣:一是在文章著述中,出現(xiàn)了一些迥異流俗、頗為另類的奇特思想,以及過于標(biāo)新立異而顯得浮夸的表述方式;二是在政治實踐中,表現(xiàn)出一種積極進取、毫不妥協(xié)而顯得具有攻擊性的斗爭姿態(tài)。這些都滲透到了科場寫作之中。
四、所謂“流蕩猥煩”
研究北宋“太學(xué)體”,無論是“景祐變體”,還是慶歷“太學(xué)新體”,抑或是嘉祐“險怪”文風(fēng),最令學(xué)者們感到頭疼的是,找不到一篇文本作為印證,這就使立論有鑿空的危險。
關(guān)于慶歷“太學(xué)新體”的特征,張方平奏章有描述:
稍作分析,即可發(fā)現(xiàn),這實際上是他對“以流蕩猥煩為贍”這一評語展開的闡述。所謂“流蕩”,即是說拋開題目,完全自由發(fā)揮,泛濫而無歸;所謂“猥煩”,即是指文章篇幅過長,字數(shù)太多,逾越規(guī)制。那么,是否有符合慶歷“太學(xué)新體”的科場文章作為印證呢?有學(xué)者注意到,歐陽修慶歷二年撰寫了一篇《進擬應(yīng)天以實不以文賦》,與張方平指斥的文風(fēng)若合符契,進而認為歐陽修就是“太學(xué)新體”的有力推動者。下面對歐陽修的這篇科場擬作,試作分析。
首先,這是一篇科場律賦,根據(jù)慶歷二年殿試賦題“應(yīng)天以實不以文”而擬作,賦題之下標(biāo)注了應(yīng)押的八韻:“推誠應(yīng)天,豈尚文飾。”歐陽修嚴(yán)格遵照用韻要求,依照“誠、應(yīng)、推、式(飾)、天、尚、文、豈”的用韻次序,將全文分為八個段落,各段落之間層層遞進,具有明顯的說理特征。
其次,此賦字數(shù)約八百字,其中一些對句確實過長。如有每句十九字者:
又有每句十四字者,加上發(fā)端詞有十六字之多:
這些長對句,幾乎都采用了散體文的句式,明顯受到古文影響,這是天圣以來古文滲透到科場文體之中的一個有力證據(jù)。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此篇賦作明顯有借題發(fā)揮、議論時政的用意,迥然有別于科舉程文套路式的寫法。其實,這在歐陽修隨賦進獻的引狀中已有交待:
蓋自四年來,天災(zāi)頻見,故陛下欲修應(yīng)天以實之事。時謂出題以詢多士,而求其直言者。外議皆稱,自來科場只是考試進士文辭,但取空言,無益時事。亦有人君能上思天戒,廣求規(guī)諫以為試題者。此乃自有殿試以來,數(shù)百年間最美之事,獨見于陛下。然臣竊慮遠方貢士乍對天威,又迫三題,不能盡其說以副陛下之意。臣忝列書林,粗知文字,學(xué)淺文陋,不自揆度,謹擬御題撰成賦一首。不敢廣列前事,但直言當(dāng)今要務(wù),皆陛下所欲聞?wù)摺?/span>
這種借科場題目議論時事的寫法,顯然符合張方平所說的“妄肆胸臆,條陳他事”。文中,歐陽修對社會現(xiàn)實的揭示不留情面:
這段文字,除了押韻還能體現(xiàn)出律賦的聲律特征之外,基本是在用古文筆法批判時政,甚至可以說,這幾乎就是一篇文賦。有學(xué)者認為歐陽修“把律賦當(dāng)成章奏來寫”,確為允當(dāng)。
這篇擬作的科場律賦寫于慶歷二年,正好處于“景祐變體”到“太學(xué)新體”嬗變的過程之中,而歐陽修既是古文家,也是慶歷政治改革的倡導(dǎo)者,且與石介有著密切的交往。他寫出吻合“太學(xué)新體”特征的文章,完全在情理之中。這明白無誤地顯示出“慶歷新政”的改革派官員在倡導(dǎo)什么樣的科場文風(fēng)。
余論:張方平科舉奏章背后的政治意圖
通過上述考證,有理由相信,張方平此篇科舉奏章的批判矛頭,指向的是“慶歷新政”改革派。那么,張方平本人又持何種政治立場,他向朝廷呈遞這篇奏章的意圖何在呢?
不妨重新回到慶歷四年十一月的“進奏院案”。《長編》卷一五三載:
讒者益深,而益柔亦仲淹所薦。拱辰既劾奏,宋祁、張方平又助之,力言益柔作《傲歌》,罪當(dāng)誅,蓋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及輔臣進白,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為《傲歌》可見也。”上悟,稍寬之。
這里透露出一個重要信息,即在“進奏院案”中,御史中丞王拱辰為了搖撼范仲淹的宰執(zhí)地位,對寫作《傲歌》的王益柔進行彈劾,而張方平則與王拱辰站在一邊。也就是說,從政治立場來說,張方平處于慶歷改革派官員的對立面。改革派陣營的韓琦已經(jīng)明確指出,王拱辰等人之所以極力要給王益柔治罪,絕不僅僅是因為《傲歌》本身,而是要攻擊改革派官員中的重要人物范仲淹,這早已成為“慶歷新政”反對派慣用的政治伎倆和手腕。
關(guān)于張方平的政治立場,葉夢得《避暑錄話》提供了一則材料:
張安道與歐文忠素不相能。慶歷初,杜祁公、韓、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為。文忠為諫官,協(xié)佐之,而前日呂申公所用人多不然。于是諸人皆以朋黨罷去,而安道繼為中丞,頗彈擊以前事,二人遂交惡,蓋趣操各有主也。
這段文字進一步證實,張方平與歐陽修分屬不同的政治陣營。而改革派陣營中的石介,更是遭到張方平的憎惡。蘇象先《魏公譚訓(xùn)》卷六載:
張安道雅不喜石介,以為狂譎盜名。所以與歐、范不足,至目以為奸邪。一日,謁曾祖,在祖父書室中案上見介書,曰:“吾弟何為與此狂游?”
可見,張方平對石介充滿敵意。與張方平交往密切的蘇紳,也站在慶歷改革派官員的對立面。《宋史·蘇紳傳》說:“王素、歐陽修為諫官,數(shù)言事,紳忌之。”說明張方平與蘇紳在政治立場上頗為接近,甚至被視為同黨。
一直與張方平保持良好關(guān)系的蘇轍,在《龍川別志》中也引述了張方平的話,這表明張方平對慶歷改革派官員的政治作風(fēng)很是不滿:
國朝自真宗以前,朝廷尊嚴(yán),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lián)u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為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它矣。諺曰:“水到魚行。”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shù)馭下……仁宗初年,王沂公、呂許公猶持此論。自設(shè)六科以來,士之翹俊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既罷,則輕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為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為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盛矣。許公雖復(fù)作相,然不能守其舊格,意雖不喜,而亦從風(fēng)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為之稱首。其后許公免相,晏元獻為政,富鄭公自西都留守入?yún)⒄拢罴苍S公,乞多置諫官,以廣主聽。上方向之,而晏公深為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并為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猶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帥成風(fēng)。上以謙虛為賢,下以傲誕為高,于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
這一段文字極其重要,它反映了站在慶歷改革派官員對立面的張方平,如何看待仁宗朝政治風(fēng)氣的變化。顯然,在張方平看來,是慶歷改革派官員的出現(xiàn),帶來了朝野上下輕議朝政的風(fēng)氣,對此,他是明確反對的。相反,他對昔日宰相呂夷簡的執(zhí)政風(fēng)格倒是頗為欣賞。根據(jù)王鞏所撰張方平的《行狀》,張方平在入仕之初曾受到宰相呂夷簡的賞識,而呂夷簡恰恰就是改革派官員極力攻擊的對象。另外,張方平同知貢舉,恰好是在被任命為御史中丞不久。《行狀》說他“遷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甫受命,即知貢舉”。這個御史中丞身份,正好給了張方平對慶歷改革派官員發(fā)動攻擊的一個有利地位。聯(lián)系張方平當(dāng)時的政治立場和身份來看,他將批判矛頭指向慶歷改革派官員不足為怪。
“景祐變體”“太學(xué)變體”的出現(xiàn),實際上反映了慶歷改革派官員在文化方面所造成的深刻影響。表現(xiàn)在科場風(fēng)氣上,就是不顧科場文體原有的程式限制,以一種較為激進的態(tài)度來議論時政,臧否人物;有時還會以一種夸張晦澀的語言來表達一些另類、特異的思想觀點。這即是張方平所謂的“怪誕詆訕”“流蕩猥煩”。張方平之所以對此種科場文風(fēng)進行嚴(yán)厲抨擊,其真正意圖是要消除在政治上已經(jīng)失勢的改革派官員在文化上的遺留影響,具有政治攻擊之目的。因此,就不應(yīng)將張方平對慶歷“太學(xué)新體”的抨擊,與歐陽修嘉祐二年對“險怪”文風(fēng)的打擊視為一個先后貫串的連續(xù)體,而應(yīng)注意其性質(zhì)的差異。
注釋
① 張方平:《貢院請誡勵天下舉人文章》,鄭涵點校:《張方平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78—279頁。按,此篇奏章收入張方平《樂全集》,亦見于《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五八(李燾著,上海師范大學(xué)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范大學(xué)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821—3822頁)、《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之三〇(劉琳、刁忠民、舒大剛、尹波等點校:《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之三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5300—5301頁),但文字互有出入。《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文字最簡,《宋會要輯稿》稍詳,但也有刪節(jié);兩者都未出現(xiàn)“太學(xué)新體”的說法。
② 最早論及“太學(xué)體”者,是曾棗莊《北宋古文運動的曲折過程》(《文學(xué)評論》1982年第5期)。此后,葛曉音《歐陽修排抑“太學(xué)體”新探》(《北京大學(xué)學(xué)報》1983年第5期)進行了專門探討。繼而,日本學(xué)者也發(fā)生了興趣,如東英壽《“太學(xué)體”考——從北宋古文復(fù)興的角度》(東英壽:《復(fù)古與創(chuàng)新——歐陽修散文與古文復(fù)興》,王振宇、李莉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141頁)、高津孝《北宋文學(xué)之發(fā)展與太學(xué)體》(高津孝:《科舉與詩藝——宋代文學(xué)與士人社會》,潘世圣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6頁),都進行了更為深入的考察。隨后,中國學(xué)界有了更多關(guān)注,成果有祝尚書:《北宋“太學(xué)體”新論》,《四川大學(xué)學(xué)報》1999年第3期;朱剛:《“太學(xué)體”及其周邊諸問題》,《文學(xué)遺產(chǎn)》2007年第5期;謝琰:《歐陽修排抑“太學(xué)體”發(fā)覆》,《安慶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2008年第10期;張興武:《北宋“太學(xué)體”文風(fēng)新論》,《文學(xué)評論》2008年第6期;許瑤麗:《慶歷“太學(xué)新體”新論——兼論歐陽修對慶歷“太學(xué)新體”的促進》,《四川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2008年第6期;許瑤麗:《再論嘉祐“太學(xué)體”與“古文”的關(guān)系》,《西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2011年第1期;許外芳:《北宋仁宗朝科舉改革與“太學(xué)體”之興衰新探》,《學(xué)術(shù)研究》2013年第4期;雷恩海、劉巖:《北宋“太學(xué)體”事件覆議》,《河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2021年第2期。這些成果一方面糾正了某些錯誤認識,另一方面也存在較大的意見分歧。不過,其關(guān)注點多落在嘉祐二年歐陽修排斥“險怪”文風(fēng)的舉措上,唯有許瑤麗之文對慶歷“太學(xué)新體”的考察,與本文在考察對象上略有近似之處,但切入點、行文思路和結(jié)論都有顯著差異。
③ 參見祝尚書:《北宋“太學(xué)體”新論》。
④ 韓琦:《故將作監(jiān)丞通判陜府張君墓志銘》,李之亮、徐正英箋注:《安陽集編年箋注》卷四七,巴蜀書社2000年版,第1500—1501頁。
⑤ 劉琳、刁忠民、舒大剛、尹波等點校:《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之一六,第5293頁。按,《宋會要輯稿》系為天圣七年正月二日,但對勘《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〇八(第2512頁)天圣七年五月己未朔之記載,知文字抄寫有誤,“正月”應(yīng)為“五月”。
⑥⑦???? 洪本健:《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4頁,第1064頁,第897頁,第1231頁,第1945—1947頁,第1945—1946頁。
⑧?? 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1698頁,第1673頁,第1693頁。
⑨ 呂中著,張其凡、白曉霞整理:《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類編皇朝中興大事記講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1頁。
⑩??[53] 《宋史》,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0089頁,第3910頁,第9634—9636頁,第9813頁。
???????????????? 李燾著,上海師范大學(xué)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范大學(xué)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續(xù)資治通鑒長編》,第2435頁,第2639頁,第3564頁,第3589頁,第3735頁,第3747頁,第3877頁,第3563頁,第3565頁,第3761頁,第3715—3716頁,第3716頁,第3718頁,第3744頁,第3746頁,第3716頁。
? 劉琳、刁忠民、舒大剛、尹波等點校:《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之一七,第5293頁。
?? 胡仔纂集,廖德明點校:《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頁,第174頁。
?? 關(guān)于宋初國子學(xué)及后來太學(xué)建立的情形,參見朱瑞熙、張邦煒:《論宋代國子學(xué)向太學(xué)的演變》,鄧廣銘、酈家駒等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9—240頁。
? 劉琳、刁忠民、舒大剛、尹波等點校:《宋會要輯稿·崇儒》一之三〇,第2743頁。
??? 陳植鍔著,周秀蓉整理:《石介事跡著作編年》,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110、126頁,第114頁,第118—119頁。
??? 田況著,張其凡點校:《儒林公議》,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29—30頁,第6—7頁,第82頁。
? 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423頁。
?? 參見許瑤麗:《慶歷“太學(xué)新體”新論——兼論歐陽修對慶歷“太學(xué)新體”的促進》。
?劉琳、刁忠民、舒大剛、尹波等點校:《宋會要輯稿·選舉》七之一六,第5396頁。
[51] 葉夢得:《避暑錄話》,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第2編第10冊,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289頁。
[52][54] 蘇頌著,王同策等點校:《蘇魏公文集》,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160頁,第1158頁。
[55]蘇轍著,俞宗憲點校:《龍川略志·龍川別志》,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81—82頁。
[56][57] 鄭涵點校:《張方平集》,第783—815頁,第7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