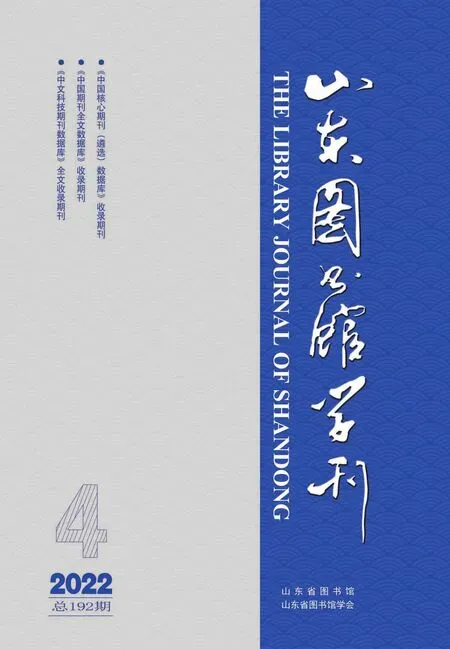歷算分途:中國古代“數學”分類演變路徑分析*
張晚霞
(淮北師范大學圖書館,安徽淮北 235000)
中國古代眾多的科學技術與學術思想成就無不蘊藏于浩瀚的經典之中,其中,數學是最為發達的基礎學科之一,傳統中諸如九數、算術、數術、數學等術語都是與這一知識領域相關的名稱,論其淵源,則從周代“數”成為一門學科到19世紀初“算術”匯集于世界數學潮流,歷經三千多年的漫長路徑 。人與物發展到一定程度便出現“算數之事”[1],如傳說中的“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大橈作甲子,隸首作算數”[2]等,易卦也源于數,我國科學史上的第一部經典著作《周易》,認為人類在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的實際體驗中掌握了天地運行的規律,總結出了陰陽八卦,其他像《山海經》《管子》等典籍中都有關于數起源問題的記載。相傳虞、夏時已有學校,西周時有大學、小學之分,于貴族子弟“教之以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3],“九數”在西周時已成為一門學科。
盡管在先秦典籍中尚未發現有關數學的專門著述,但在夏、商、西周三代數學史料最集中的《周髀算經》中,記載有周公與商高關于“數”的起源問題的討論[4],證明“數”在當時已得到廣泛應用。先秦時“數”與其它學術一樣呈多樣化發展趨勢,或有相關典籍出現,現存最早的數學著作《九章算術》是先秦以迄西漢中國古代數學的總結與升華,劉徽在《九章算術注·序》中說:“往者暴秦焚書,經術散壞。自時厥后,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張蒼等因舊文之遺殘,各稱刪補。”[5]張蒼“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6],入漢后又任計相,蒼等所刪補的“舊文”是《九章算術》文本的前身,為后世多數學者所認可。劉徽《序》中梳理了數的起源:
昔在包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暨于黃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于是建歷紀,協律呂,用稽道原,然后兩儀四象精微之氣可得而效焉。……按: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7]
《九章算術》是“九數”之流,東漢鄭眾“注”《周禮》“九數”為:“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8],也是《九章算術》的主要方法和基本框架。《周易》或是數學的源頭,但《周易》并非專門數學的著作,如汪辟疆所言:“《易》雖一書,而學有十六,學有傳學,有注學,有章句學,有圖學,有數學,有讖緯學,不得總言《易》。”[9]而《周易》作為儒家經典卻對古代數學的產生具有開啟之功,秦九韶“大衍之術”就源于《周易》:“圣有大衍,微寓于《易》。”[10]因此,中國古代數學并不是固定的科學概念上的一個分支學科,其內涵豐富,領域廣闊,傳統目錄分類中,并沒有現代科學意義上“數學”的正位,往往與其它學科內容特別是天文、歷法雜糅于一體,其相互間的離析分合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過程。
1 古代數學與“數術”融為一體,依附于天文、歷譜
“數術”是中國古代科學產生的主要知識氛圍,“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11],“此明數術之學,出于古史。則今之江湖醫卜星相之流,皆其苗裔也”[12],“數術”為“占卜之書”(師古注)[13],“藝謂書、數、射、御,術謂醫、方、卜、筮”[14](李賢等注),“數”“術”有相通之處,由此,以星占歷算、醫藥方術為基本涵義的“數術”于兩漢時較為興盛,“術數之興,多在秦漢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陰陽五行,生剋制化。實皆《易》之支派”[15]。
1.1 “數術略”歷譜中的“外算”
群書皆文,“六藝”為宗,劉向、劉歆整序文獻,經義為準,《七略》是最早著錄數術類典籍的目錄著作,二書雖佚,成就體現于《漢書·藝文志》(簡稱《漢志》)。《漢志》“六略”之錄萬三千篇,涵蓋當時所有學術,“術數雖居六藝之末,而施之人事,則最為切務”[16],“數術略”190家2528卷,總數居“六略”之首,包括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六類。一為占星術,類似于古天文學,以觀星象云氣占驗吉兇;二為推歷之術,關乎古歷算,天文、歷譜關涉國政,“所謂紀吉兇之象,圣王所以參政者”[17];三為陰陽、五行災異術,包括堪輿、刑德等;四為龜卜、筮占之預測法;五為物驗雜占,是對人鬼、異夢等怪異現象的驅邪之術;六為形法,包括異域地理、相宅相物等相術。可知,“數術”在漢代既包羅萬象又流傳廣泛,涉及大量的自然科學知識,用途卻偏于神鬼迷信,與現代科學截然不同,但無論如何,算術知識是它們共同的基礎,通常被作為“術”的運算法則而融入各類,統系其運作。
南宋數學家秦九韶把算術分為“通神明,順性命”的“內算”與“經世務,類萬物”的“外算”兩種:“今數術之書尚三十余家,天象歷度謂之綴術,太乙壬甲謂之三式,皆曰內算,言其秘也。九章所載,及周官九數系于方圓者,為叀術,皆曰外算,對內而言也。其用相通,不可岐二。”[18]“內算”包括綴術和三式,為大數術,是一種秘不外漏只許師徒間傳習的方術;“外算”則是“九數”“方圓”的小數術,類似于今天所說的數學,宜公開傳授。秦氏的數學觀與北宋科學家沈括之說相契:“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算家謂之叀術,叀心文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綴術。謂不可以形察,但以算術綴之而已,北齊祖暅有《綴術》二卷。”[19]“叀術”與測量、幾何相關,“綴術”與天文歷法相連,即探求天體運行,推導節氣朔望盈縮之變化,不可以形考察,惟以算數法連綴推衍而知。沈、秦二者的論述表明了古代數術包含了天文歷法計算的歷史事實。
《九章算術》是以田畝、賦稅等實用計算為主的“外算”,卻不見載于《漢志》,“數術略”中附于“歷譜”而又類似于數學的著作有《許商算術》《杜忠算術》(已佚),李學勤先生認為:“《許商算術》《杜忠算術》,猶如《毛詩》《左氏春秋》之類,只是推衍《九章算術》的兩部作品。”[20]郭書春說:“劉徽關于《九章算術》的編纂的論述是完全正確的。”[21]《九章算術》因先秦“九數”遺文由張蒼、耿壽昌先后增補而成。許商、杜忠皆西漢后期人,據《廣韻》卷四(1)《廣韻》“筭”字注云:“又有九章術,漢許商、杜忠,吳陳熾,魏王粲并善之。”見《四庫全書》第236冊《原本廣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知二人都曾推衍過九章之術,與耿壽昌“增補”年代相去不遠。漢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命陳農廣求遺書,詔光祿大夫劉向主持并校定經傳等書,太史令尹咸校理數術時收錄了許、杜的《算術》,他們當是最早研究過《九章算術》文本的數學家,其著作是在該文本的基礎上完成的,屬于“外算”。
1.2 “數術之書,更為一部”之專目
算學亦儒學之事,劉徽《九章算術注》以類似于經注的方式研究數學經典,發展了《九章算術》中的率概念和齊同原理,將古代的算法提升到理論的高度,形成較為完整的數學理論體系。至南北朝,數學進入輝煌期,算學大師輩出,南有祖沖之、祖暅父子,他們在圓周率等問題上所取得的成就是數學史上的驕傲。北朝也不乏算學之士,公元525年,祖暅被北魏俘獲,授數法于信都芳,令其數學水平大長(2)參見李延壽撰《北史》卷八十九《藝術上·信都芳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933頁。。北周數學家甄鸞整理并注釋了貫穿于《詩》《書》《易》等儒家經典中的天文、數學內容,撰成《五經算術》,同時,北方還出現了一批普及性的數學著作,如《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等。阮元等《疇人傳》所收歷算家人數中,北多于南,《顏氏家訓·雜藝篇》云:“算術亦是六藝要事。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歷者,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江南此學殊少,唯范陽祖暅精之……河北多曉此術。”[22]數理科學服務于經學,儒者須通曉,即便不能“專業”,必以“兼明”。
魏晉以降,歷朝整理典籍,“荀勖、李充、王儉、任昉、祖暅,皆達學多聞,歷世整比,群分類聚,遞相祖述”[23],南朝各朝政府藏書與官修目錄至梁時達到極盛,“目錄之學,創始于兩漢,改進于魏晉,極盛于六朝”[24],四部法為其主流,而《古今書最》載有《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錄》,《隋志·序》或以為梁有《五部目錄》者:
梁初,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內列藏眾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梁有秘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為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錄》。[25]
《七錄序》云:
齊末兵火,延及秘閣,有梁之初,缺亡甚眾,爰命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內別藏眾書,使學士劉孝標等重加校進,乃分數術之文,更為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錄。其尚書閣內別藏經史雜書,華林園又集釋氏經論,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逾于今者也。[26]
孫振田認為,《隋志·序》據《七錄序》修改而來,“五部目錄”既不是任昉、殷鈞《四部目錄》之“四部”與祖暅所撰《術數書目錄》之“一部”的合稱,也不是將書籍分為五個部類的目錄著作,更不是指梁撰有五種目錄書;“五部目錄”實際上是對《七錄序》及《古今書最》的誤讀。余嘉錫先生考證兩《唐志》所載《天監四年四部書目》,“實即《隋志》之劉孝標《梁文德殿四部目錄》”[27],為《七錄序》所言“文德殿目錄”,也即《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錄》之《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書目錄)》部分,其中并不包含祖暅《術數書目錄》,祖暅《術數書目錄》當在流傳的過程中佚失,唐初已不存,故《隋志》既不可能對其進行單獨著錄,也不可能按合題名著錄,那么,《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錄》應是《術數書目錄》與《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書目錄)》二者的合稱。(3)見孫振田《〈隋志序〉“梁有五部目錄”再考釋——兼釋“任昉、殷鈞〈四部目錄〉”》,《文史哲》,2015年第1期,第140-143頁。
據此,梁朝的成就還在于對專門目錄的編撰,一則梁有釋氏專目,“由漢至東晉,目錄無專類。至梁始別行,阮氏《七錄序》所謂華林園又集釋氏經論是也”[28];又“殷鈞字季和,……歷秘書丞,在職啟校定秘閣四部書,更為目錄。又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跡,列為品目”[29],殷鈞不只撰有綜合目錄,還編有藝術品法書的專門目錄,如姚名達所言:“當梁武帝極盛右文之際,秘閣四部之外……令劉孝標撰《梁文德殿四部目錄》。僧紹、寶唱先后撰《眾經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為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而書畫已有目錄。”[30]姑不論“五部”之說,梁初學士劉孝標校文德殿藏書,由祖暅負責整理術數之書,并撰成專目《術數書目錄》,像宗教、書畫各撰有目錄一樣,梁編有數術書專目已是共識,現存最早的佛經專門目錄(釋僧祐)《出三藏記集》也是梁朝所為。
另外,依梁元帝江陵校書,“王司徒表送秘閣舊事八萬卷,乃詔比校部分,為正御、副御、重雜三本”[31],則知“正御本”是選擇最精善的標準本政府藏書,它的建立“是完善藏書體系的一項重要措施。正御本目錄的編撰當以此為開端,是南朝目錄事業中的重大貢獻”[32]。梁朝由中書省建成專藏文德殿正御本的藏書處,令深通其學的數學家祖暅校勘整理術數書而編成專目,說明這一時期數術文獻典籍的繁盛及當朝對該類知識的高度重視。梁阮孝緒《七錄》總集眾家分類體系,將經史至術伎合為五錄成內篇,佛、道二錄為外篇,共錄圖書3453種,5493帙37983卷,內篇“術伎錄”較文德殿“術數書”有所擴展,分為天文、緯讖、歷算、五行、卜筮等十類,計492種,601帙3733卷,阮氏著錄了自己見聞的所有圖書,是當時學術思想和文化典籍的現實反映。
2 天文、歷算的離析分合
《隋書·經籍志》首次明確以經、史、子、集為四部,將《漢志》“諸子、兵書、數術、方伎之略,今合而敘之,為十四種,謂之子部”[33],遂成定制。汪辟疆說:“迄于《隋書·經籍志》,而此三部之書,完全并入子書,一合而不可復分。蓋以三部本為專家,與諸子之學,可相附麗。”[34]直至清末,凡以四部為依歸者,之前數術各類及之后析出的天文、歷算等均未出子部范疇。
2.1 算術因歷術而發達,并入“歷數類”
古代數學涉及天文、歷法的各種運算法,蔡邕說:“先治律歷,以籌算為本,天文為驗。”[35]我國從西周厲王、幽王時(前9世紀-前8世紀)已有世代相承掌管天文歷法而通數學的“疇人”,“幽、厲之世,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36]。如李約瑟說:“在整個中國歷史中,數學的重要性主要是在于他與歷法有關。《疇人傳》中很難找到一個數學家不受詔參與或幫助他那個時代的歷法革新工作。”[37]日本學者的理解則更深刻:“中國之算學,因歷術之關系而發達者,甚多。以算家見稱之人,大概精歷術……歷術上之事,其供給算學之問題,及為算學方法之創意者,必多也”,并舉例說“《授時歷》中有招差法之三差,此亦算學方法由歷術發達之一例。祖沖之為歷術大家,招差法或與歷術有關聯也……何承天用強弱二法于調日法,可視為在歷術創算學之方法也。”[38]因此,古代目錄分類中,數學始終與天文關聯,與歷法相通。
《隋志》四分法融合《七錄》之“子兵”“術伎”為子部,保留原數術中天文、歷數、五行三類,并卜筮、雜占、形法入五行類,不再以“數術”之稱,附佛、道二錄于四部末,將歷法、算術并入子部“歷數類”,該類錄入“外算”與普及性數學著作約30部,包括隨佛經傳入中國的印度歷法及數學著作《婆羅門算法》《婆羅門陰陽算歷》等。《隋志》雖以“歷數”為主而附算法,但此時天文、歷術、算術三者均已析出以卜筮為主的數術范疇,《舊唐志》亦然。不僅如此,就隋唐時傳入日本的中算書在《日本見在書目》中,歸類亦效仿《隋志》《舊唐志》,附于“歷數家”門下(參見《中國科學技術史·數學卷》),以此門目所有書名來判斷,大概有一半以上為純算學書,據當時傳入日本的中國典籍中,天文、歷算書籍為最多,天文85部461卷,歷數55部167卷;《隋志》中天文97部675卷,歷數100部263卷;《舊唐志》中天文26家260卷,歷算58部167卷,三種書目均為國家政府所為,編纂年代也相近,同時,隋唐時的數學教育制度也被傳入日本。總之,日本官方幾乎全面引進和移植了古代中算體制,并相互滲透,成為整個日本民族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2.2 “算術”出“歷數”而獨立,或附于它類
盡管天文、歷法、算術內容相近關系密切,但它們本該是屬于不同知識范疇的三種學科,北宋《崇文總目》子部二級類目在《舊唐志》十七類的基礎上調整至二十類,改“天文”為“天文占書”,合“經脈”“醫術”為“醫書”,增算術、卜筮、道書、釋書四類,首次將算術及其相關文獻從“歷數”中析出,設“算術”專類,自此,“外算”在子部中爭得一席之地。歷、算各立門戶,學科分化漸趨明朗。但稍后的《新唐志》“歷算類”中,將歷、算二類相雜著錄,混然不清。鄭樵質疑:“有歷學,有算學,《隋志》以歷數為主而附以算法,雖不別條,自成兩類。后人始分歷數為兩家,不知《唐志》如何以歷與算二種之書相濫為一?雖曰歷算同歸乎數,各自名家。”[39]鄭氏主張把學科內容不同的書籍區分開來,包括內涵相近,而實屬不同學科者,其《通志·藝文略》近百家十二大類,第七“天文類”統系天文、歷數、算術三種,又各分子目,天文分八,歷數為五,算術分為算術、竺國算術二種,算術雖未脫離天文科學之大范圍,但將其移出歷數,與天文、歷法并列,已是學科門類日趨細化的必然趨勢,所謂“類例不患其多也”。
“算術”不再依附于“歷數”,但天文、歷法、算術三門學科的獨立性尚未成公論,后來的《文獻通考·經籍考》《宋史·藝文志》等仍保留著前人歷、算合一的認知。私家目則有所不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衢本”子部分“天文”“星歷”兩類,“袁本”為“天文歷數”一類,錄天文歷法,兼陰陽、五行等。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子部設“歷象類”著錄天文歷法,另列陰陽家、卜筮等類,而在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附“四部分類源流一覽表”中,誤將“歷象類”分標“天文”“歷算”兩目,實際晁、陳二人均將算術書歸子部“雜藝”,陳氏《直齋》并在《應用算法》解題中略作說明:“前《志》在歷算類。案:射、御、書、數均一藝也;不專為歷法設,故列于此。”[40]在他們,認為“數”亦一“技藝”,不只與天文、歷法關系密切。同樣,尤袤《遂初堂書目》中算術亦歸“雜藝類”,原數術其余各類并入子部“數術類”,但此“數術”范圍已縮小,算術已不在其內,卻將算術入“雜藝類”,頗為不妥。清初《千頃堂書目》與《明史·藝文志》仿宋人做法,從天文、歷數中析出算術,附于“小學”,大概以算學為“六藝”之附,但“小學”從來屬于經部,算術則另當別論。
2.3 子部“天文算法類”,后置“術數類”
《四庫全書總目》兼顧學術發展與圖書量遞增之實情,將墨、名、縱橫諸家并入“雜家類”,子部含儒、兵、天文算法、術數等十四類,合數術其他分支于“術數類”,并天文、歷算為“天文算法類”,以實學為重,“小序”指出:
三代上制作,類非后世所及,惟天文算法則愈闡愈精……洛下閎以后,利馬竇以前,變化不一。泰西晚出,頗異前規,門戶構爭,亦如講學。然分曹測驗,具有實征,終不能指北為南,移昏作曉。[41]
“天文算法類”又以“諸家算術為天文而作者”和“其專言數者”[42]為立類依據,下設推步、算書兩小類,推步之屬31部429卷,存目23部127卷,凡推測天文歷象者入本類,首列《周髀算經》為現存最早的天文歷法之瑰寶;算書之屬25部210卷,存目4部23卷,專講數學算法者入本屬,首列《九章算術》為古算學之鴻寶。館臣們認為:“天文無不根算書,算書雖不言天文者,其法亦通于天文,二者恒相出入,蓋流別而源同。”[43]該類與以往天文、歷算類所含內容不盡相同,并接受歷算大師梅文鼎的進步觀點,收錄明后期利瑪竇以來的西洋算法,以示中西學術之異同。
至若“術數類”,將以往“數術略”下附會巫術迷信的部分歸入本類,分為數學、占侯、陰陽五行等五目,加上存目所附雜技術,共七個三級類目,“中惟數學一家,為《易》外別傳,不切事而猶近理。其余則皆百偽一真,遞相煽動”[44],該“數學”與今數學全然不同,是附以雜說的《易》之分支,即李零所謂《易》學中的圖數之學的《易通便》之類,與秦九韶所言“內算”相關聯。
“術數類”辨義、分類精細,屬子部中三級類目之最,凡196部1427卷,如將其與“天文算法類”合為一處,數量亦相當可觀。因此,李約瑟說:“如果有一個漢學家兼通數學,那末,通過對隱晦難解的中國中世紀占卜術著作的探索,他在這方面是會大有收獲的。”[45]術數文化一經產生,內涵豐富而流傳廣泛,是傳統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隨著文化的演進,術數自身也歷經裂變,天文歷算超自然科學領域發展,命相占卜漸次萎縮,體現了科學與迷信間相互消長的淵源關系。從《七略》“術數略”到《總目》重現“術數類”,其內部發生較大的分化,《總目》置“術數”于“天文算法”之后,留以陰陽五行為基礎的占術、相術等內容,意味著數術中科學與偽科學的徹底分離,書籍隸屬的科學性增強,以便學術的系統發展。
3 設立“數學”專類,確定“數學”科名
古代數學經歷了先秦、兩漢、魏晉、宋元幾個比較突出的發展階段后,在明末進入一個新時代,西學東漸,數學會通,外算數學真正居于算學主導地位,數學逐漸獨立為大類。
3.1 “數學”一詞的出現
傳統數學發展的全盛期當數宋元時期,此時雕版印刷術發達,數學經典大量刊刻流傳。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秘書省刊刻“算經十書”,是世界文明史上首次印刷數學著作,后得南宋數學家鮑澣之翻刻,或有孤本流傳至今,成為目前所知中國數學最早的印刷本。三上義夫曾說:“及宋元之際,算學發達上,及發生一大變化,構成前代未聞之新算學。若干人物與宋元新算學組織有關系者,……如宋之秦九韶、楊輝,元之李冶、郭守敬、朱世杰等即是……即僅有五十七年之成績……在此極短期間,中國算學,別開新面最為發達,乃一極顯著之現象也。”[46]“數學”一詞也隨之出現,秦九韶所撰《數學九章》,當是最早以“數學”作為書名關鍵詞的著作,同時代的楊輝也使用過這一名稱:“夫六藝之設,數學居其一焉。”[47]“數學”一詞自宋末開始逐漸流傳開來。
經宋元時期數學理論的大發展,明代數學進入以應用為主的“技術化”時代,典籍洋洋大觀,分類體系的變革已成必然趨勢,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始以“算法”為一級類目,令私家目錄引以為范,晁瑮《寶文堂書目》新增“算法”專類,尤其是,崇禎間茅元儀《白華樓書目》首次以“數學”為類名,獨立大類。
3.2 《白華樓書目》創設“數學”大類
明萬歷末至崇禎年間,西方傳教士孟三德、利瑪竇、熊三拔等先后來華傳播先進的科學技術,激發了中國自然科學的復興,出現了徐光啟、宋應星、李時珍等杰出的科學家,他們譯介并編著了《幾何原本》《天工開物》《本草綱目》等一系列科學名著,有些甚至成為自然科學界的不朽之作,梁啟超贊:“明末有一場公案,為中國學術史上應該大筆特書者,曰:歐洲歷算學之輸入……中國知識線和外國知識線相接觸,晉唐間的佛學為第一次,明末的歷算學便是第二次。”[48]隨著西學的融入,中國傳統數學所代表的知識體系也發生變化,算法數學逐漸獨立,數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傾向得以不斷增強。中西知識線交匯結碩果,不少新的學科門目出現,目錄著作專立門類予以反映,趙琦美《脈望館書目》子部“大西人術”專錄西方傳教士著譯之作,茅元儀《白華樓書目》創設文學、兵學、數學等許多新學科類目。范鍇輯《吳興藏書錄》記載:
鹿門茅先生藏書甲海內……其孫大將軍止生(元儀),編為《九學十部目》,自述云:“九學者,一曰經學,二曰史學,三曰文學,四曰說學,五曰小學,六曰兵學,七曰類學,八曰數學,九曰外學。十部者,即九學之部而加以世學。”[49]
茅坤祖孫三代近百年書香家風,繼起不衰,家藏以論世務實學見長,居多的兵書為茅元儀編撰被譽為古代“軍事學百科全書”的《武備志》奠定了基礎。與學科演進相同步,茅元儀改“兵書”為“兵學”,直延用至近代,創“數學”大類,與今數學學科名稱亦絕非偶然巧合,而是與所藏“數”類文獻內容及數量的相匹配,也是對中西會通后數學書籍的集中反映。此前(公元1545年)有瑞士人蓋士納(Conrad Gesnner 1516-1565)《萬象圖書分類法》,分圖書為字學、數學、修養、高等學科四大部和語言學、辯證學、詩歌、算學、天文學等二十一類,該分類法被譽為歐洲第一個正式圖書分類法,大、小各類基本以“學”為類名。茅元儀應受其影響,《白華樓書目》九學十部中除“世學”不足為典則外,其余九類皆以“學”作類名,為歷代書目所僅有,該目雖已佚,但茅氏獨能以學科屬性為標準改舊創新,類目之清晰無人能出其右,堪稱明代書目之佳品,姚名達稱贊:
一掃雜稱,于諸家中獨為明潔,有似乎現代之十分法焉……向來目錄之弊,惟知類書,不知類學……今茅元儀獨能以學術為分類之標準,且劃一其名稱,整齊其部次,賢于往哲多矣。[50]
之后,“數學”一詞即以獨立的類目名稱或學科名稱而頻頻出現,清代錢曾《讀書敏求記》、王聞遠《孝慈堂書目》等均將數學、天文、歷法等反映自然科學的小類或子目提升到一級類目,盡可能讓其擺脫與其他學科的附庸而獨立發展。
總之,到近代,中國知識逐漸學科制度化,有了清晰的門類種屬,并建立起具有西方科學意義上的學科分類體系及知識系統,“學”亦成為多數類名的固定匹配,甚至后來以“學”為后綴的部分類名直接成為該科的學科名稱。《涵芬樓新書分類目錄》(約1914年)以近代學科分類整理中西文獻,新書分哲學、文學、數學等十四部,“數學部”含算術、代數、幾何、三角、高等數學五目,“數學”成為該類文獻的類名通稱。而“數學”作為今天本學科的代名稱,則始于1939年,由教育部確定將英文mathematics一律譯為“數學”,是現代漢語數學詞匯中唯一由行政行為手段規定的學科名詞,正所謂“數學本身是一個歷史概念,數學的內涵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給數學下一個一勞永逸的定義是不可能的”[51]。當代《中國圖書館分類法》中,“數學”作為“數理科學和化學”的組成部分之一,包含了數學理論、古典數學、中國數學等十五目,既容納了古今中外的文獻,又涵蓋了前沿新增科學,奠定了數學知識體系框架,體現了科學發展的動態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