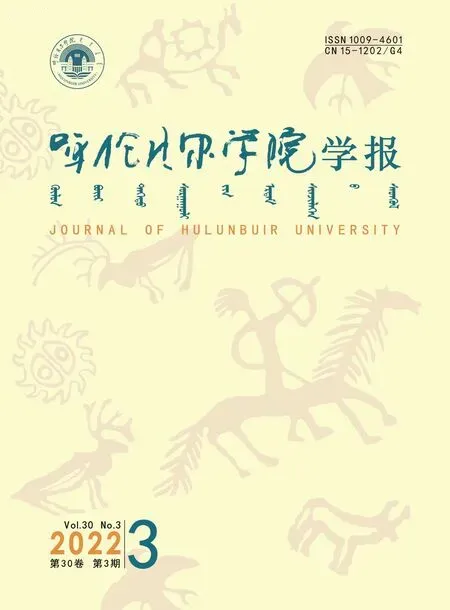試論嘎仙洞石室祝文與東漢刑徒磚的相同之處
楊文賓
(呼倫貝爾學院 內(nèi)蒙古 海拉爾 021008)
嘎仙洞石室祝文于1980年7月30日為時任呼倫貝爾盟文物站站長的米文平先生發(fā)現(xiàn),[1]發(fā)現(xiàn)伊始即備受學術(shù)界的關(guān)注。其內(nèi)容如下:

石室祝文刊刻的原因、目的和過程《魏書·禮記》有載:
“魏先之居幽都也,鑿石為祖宗之廟于烏洛侯國西北。自后南遷,其地隔遠。真君中,烏洛侯國遣使朝獻,云石廟如故,民常祈請,有神驗焉。其歲,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曰:‘天子燾謹遣敞等用駿足、一元大武敢昭告于皇天之靈。自啟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歷載億年,聿來南遷。惟祖惟父,光宅中原。克剪兇丑,拓定四邊。沖人纂業(yè),德聲弗彰。豈謂幽遐,稽首來王。具知舊廟,弗毀弗亡。悠悠之懷,希仰余光。王業(yè)之興,起自皇祖。綿綿瓜瓞,時惟多祜。敢以丕功,配饗于天。子子孫孫,福祿永延。’敞等既祭,斬樺木立之,以置牲體而還……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3]
石室祝文刊刻于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摩崖石刻,劉濤先生《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將其歸類于隸書。依其字形來看,并非狹義的隸書。
東漢時期,帝王更替現(xiàn)象尤為顯著,皆因外戚與宦官爭權(quán)之弊。其間假借帝王詔令修建自家官舍者,不乏其人。刑徒參與工程建設可視為朝廷勞教刑徒的一種手段,且可以通過這種方式節(jié)省財政開支,刑徒于“工作”過程中,飽受刑罰折磨。這些刑徒是從全國各地的獄所押送到司隸校尉、將作大匠等管轄工地,替封建統(tǒng)治者做修砌陵墓、建造宮苑、筑城、開鑿棧道、漕運、伐木、采礦等重體力勞動。[4]刑徒在繁重的勞作過程中飽受摧殘和壓迫,往往在刑滿釋放前即不堪重負而殞命,刑徒死后,為方便親屬將尸骨遷回故鄉(xiāng),往往在統(tǒng)一埋葬死者時以建筑等殘舊廢磚書刻死者犯罪時批復的所屬地、所犯罪責、姓名等內(nèi)容。因為只是作為死者的“標簽”,書寫者又并非專業(yè)書家,書刻材質(zhì)有限等原因,所以文字相對隨意,并非當時官方的標準八分書。
雖然《嘎仙洞石室祝文》與東漢刑徒磚的刊刻時空跨度較長,且主要功用與刊刻目的不同,但不乏其相同之處,茲闡述如下:
一、書刻者的不確定性
《嘎仙洞石室祝文》的書刻者《魏書》中無考,祝文中也未明確。欒繼生《大興安嶺嘎仙洞北魏石室祝文瑣談》一文推斷:“《祝文》雖刻于大興安嶺,但其作者,應出于祭祖官員,可作為北魏前期北方地區(qū)書風的代表。”[5]通過查校《魏書》等相關(guān)文獻,結(jié)合石室祝文的相關(guān)內(nèi)容,所涉及的官員有:謁者仆射,其職責在于引見臣下、傳達使命外,還掌朝靴賓饗及奉詔出使等職。[6]可見“謁者仆射”并沒有書寫詔書或碑文的職責。


“東作帥使”史籍無載,祝文中明確了他的職責是“鑿”,刊刻祝文前的石壁修整和刊刻文字是他的職責所在,“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作為祭祖的石室祝文不可能不作書丹而直接刻,如果直接刻,文字必然遠不如現(xiàn)有祝文工整規(guī)范,所以祝文的書丹和刻石必然是分開的,而“東作帥使”的“鑿”只是“物勒工名,以考其誠”的職責所在。
關(guān)于刑徒磚的書刻者,歷來難以定論。筆者依據(jù)有關(guān)文獻記述及前人推論,大致可分為兩種:
第一種:疑為“書佐”所為。“書佐”處于官員的最底層,對其任職要求不高,人員的選擇也不嚴格,“可以不要求精通儒家經(jīng)典,只要能很好地弄懂法律條文,處理好各種文件,盡其力奉侍其主就可以了。”[13]張志亮《洛陽東漢刑徒墓磚概說》一文有“書者系當時左校或右校里面從事書寫或刻辭的書佐”[14]的推測。
第二種:疑為服刑人員所為。漢代刑徒不單有平民,亦有粗通文墨者及因罪入獄的官員,[15]黃展岳《早期墓志的一些問題》中提到:“筆者認為,秦始皇陵西側(cè)役徒墓瓦文和洛陽出土的東漢刑徒墓磚文比較,確實存在一些差別,例如瓦文沒有部署、獄名、郡名、死亡時間以及‘死(尸) 在此下’等語,但都是信手刻寫,字劃草率,大小行距不勻,估計都是服刑同伴或監(jiān)工所刻寫。”[16]
《嘎仙洞石室祝文》因皇家祭祀祖先的特殊性,臣子是不能僭越禮志而刊刻書刻人姓名的;刑徒磚出于對逝者的忌諱或其“標簽”的功用,也不會將刻者的相關(guān)信息加刻在內(nèi),即便有些磚文后部留有大面積空白。
二、書體的宏觀統(tǒng)一性
劉濤先生在《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中將《嘎仙洞石室祝文》的書體歸類于隸書。唐代以前對隸書的界定是相對寬泛的,從石室祝文的表現(xiàn)形式來看,并非標準的八分,也非“古隸”,隨時代的發(fā)展,新書體未能成為官方規(guī)范,舊書體在當時的傳播中尚有殘存,因而,在《嘎仙洞石室祝文》中,往往表現(xiàn)為有篆書的用筆、篆書部件的殘留、初期楷書的雛形等形式。因此從宏觀來看將其歸類于寬泛意義上的隸書最為穩(wěn)妥。
現(xiàn)代學者界定隸書時,根據(jù)《漢書·藝文志》“施之于徒隸”之說,胡樸安先生《文字學ABC》、丁易《中國文字與中國社會》中進一步發(fā)揮此說,稱隸書為“專供獄吏隸人用的字”“是官府衙門里差人皂隸用的字”,依此論,將刑徒磚文字厘定為隸書,更加“名正言順”了。隸書分為古隸和八分,關(guān)于兩者之間的區(qū)別,多采用裘錫圭先生的解釋:“一般把隸書分成古隸和八分兩個階段。八分指的是結(jié)體方整,筆畫有明顯的波勢和挑法的隸書,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漢隸。八分形成以前的隸書就是古隸。”[17]依此說,刑徒磚文字中既沒有明顯的“波勢和挑法”,結(jié)體也因形生字,可見,若將刑徒磚文字定義為“古隸”是合乎情理的,且可以將其宏觀的歸類為隸書。
三、文字應用的不規(guī)范性
《嘎仙洞石室祝文》中部分文字摻雜篆書的部件或用筆習慣,如“祐”字的右偏旁“右”撇上保留短橫,“玄”字形態(tài)類似于小篆的寫法,“帥”字寫法與小篆寫法十分相近。在刑徒磚中也可以找到類似的痕跡,如“卻成磚”中的“鹿”字保留有篆書的用筆,“樊平磚”中的“故”右部作篆書的寫法等。
《嘎仙洞石室祝文》和刑徒中還存在有些字作筆畫的省減現(xiàn)象,如《嘎仙洞石室祝文》中的“緜”字左部“系”省去下部,“臣”字中間作一豎貫穿;刑徒磚中多出現(xiàn)在上下部首同時出現(xiàn)“口形”時,左豎上下一筆貫穿,如“昌、副、會、堅”等。
《嘎仙洞石室祝文》書刻于北魏拓跋氏漢化初期,對漢文化和漢字尚未形成規(guī)范的認識,故而太武帝于始光二年(公元425年)春,“初造新字千余”,并下詔:
“在昔帝軒,創(chuàng)制造物,乃命倉頡因鳥獸之跡以立文字。自茲以降,隨時改作,故篆隸草楷,并行于世。然經(jīng)歷久遠,傳習多失其真,故令文體錯謬,會義不愜,非所以示軌則于來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成,此之謂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頒下遠近,永為楷式”。[18]
張金龍先生認為,“太武帝下令所造新字千余,其具體情形今已無從所知,從其頒布的詔令來看,他是想通過統(tǒng)一文字來實現(xiàn)文化上的統(tǒng)一,將文化的控制權(quán)掌握在北魏手中”。[19]
王元軍先生《書寫規(guī)范與書寫之美》一文中考究曰:“總而言之,漢人用字,有通用者,有假借者,有奇古者,有省減者,有增筆者,此種情況十分普遍,以至于形成風俗。”[20]刑徒身處社會底層,其身份與生活的環(huán)境造成了他的“墓志”不可能被書刻者重視,因而為書寫的方便快捷,不規(guī)則漢字的產(chǎn)生與運用也就順理成章了。
由此可見,二者相距百余年,文字應用的不規(guī)范性的原因也不盡相同,但文字不規(guī)范的表現(xiàn)形式有著跨越百年的“傳承”。
四、獨特的藝術(shù)性
《嘎仙洞石室祝文》書刻在摩崖石壁之上,因書丹方式受客觀條件影響的必然性,或石面的不均勻性,以及當時社會文字書寫可能未落實于具體的統(tǒng)一要求,整個祝文文字大小不一,且重心難以保持在一條垂直線上,形成一種無行無列、一任自然的藝術(shù)特色。
刑徒磚可視為早期墓志的前身,死者身份的標識,并未形成標準的書寫格式和文字要求,書寫者也多是粗通文墨的官吏、刑徒或書佐。刑徒的身份,決定了他的“墓志”不可能有人先為其書丹,而后再作細致的刻劃修整。刑徒磚多采用廢棄建筑用磚,大小、形狀不一,且都是干刻,故而,文字大小、行距、行與行之間文字的多少等多是隨體附形,不作人為的刻意安排。
清方朔《枕經(jīng)堂金石書畫題跋》在評論刑徒磚書法時稱“結(jié)構(gòu)淳古、風神飄逸、隸中佳品,可愛也”。借此評《嘎仙洞石室祝文》的藝術(shù)價值亦是妥帖的。
五、相同的價值性
侯開嘉先生將中國書法發(fā)展史劃分為官方和民間兩條脈絡,[21]前期多數(shù)書家關(guān)注于世家大族的經(jīng)典之作,難免將書體的轉(zhuǎn)化,劃分的過于“生硬”,缺失中間環(huán)節(jié)的歷史史實圖錄作補充。正如沃興華先生《敦煌書法藝術(shù)》一書中談及敦煌書法的價值時,對當時學術(shù)界研究狀況有如下分析:
“以現(xiàn)代學術(shù)的眼光來看,書法史研究有三大任務:一是描述字體和書體的演變過程,二是揭示這種演變的原因,三是對演變過程中的種種現(xiàn)象加以評論,使后人有所借鑒。在這三大任務中,最基本的是描述演變過程。然而,目前所有的書法史著作,幾乎都是篆書、隸書、楷書、顏體、歐體、柳體的分別介紹,斷爛朝報,充其量只能算是一部比較詳細的書法辭典。造成這種落后狀況的主要原因是真實可靠的歷史記載和當時的書法作品實在太少,‘史不足證’,孔子也是無可奈何。”[22]
近年來,人們的關(guān)注范圍更為寬泛,從之前多關(guān)注于官方書家、書作中抽身出來,轉(zhuǎn)而對整個書法史中的書寫進行全面的探索。《嘎仙洞石室祝文》書刻于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正處于隸書體向楷書(魏碑)遞變的時期,祝文的發(fā)現(xiàn)再一次印證了前人的論述,將真實的歷史“痕跡”呈現(xiàn)在世人眼中。刑徒磚在東漢時期屬于下層民眾的日常書寫,更能夠直觀體現(xiàn)出當時人們解散規(guī)整“八分”的全過程,清晰地展現(xiàn)了從八分向初期楷書過度的中間環(huán)節(jié)。
同時,二者隨體附形的技法表現(xiàn)、古拙的用筆、生動的字形結(jié)構(gòu)也為現(xiàn)代展廳效果和材質(zhì)多樣化的表現(xiàn)形式提供了可資借鑒之處。
藝術(shù)性是在實用性的基礎之上表達人們對于“美”的追求。《嘎仙洞石室祝文》是帝王祭祀祖先的詔令,用于宣揚祖宗和自己的功德,其書刻的前提是可識讀。刑徒磚為早期“墓志”,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方便刑徒親屬對刑徒身份的確認,不在于書刻技法的表現(xiàn),書刻者的隨意而就,只是為了逝者親屬遷墳時的可識。二者都是以實用為前提。
概而言之,《嘎仙洞石室祝文》和刑徒磚無論在書刻者、文字規(guī)范性、藝術(shù)性、價值等方面都存在諸多相同性,對他們的進一步對比研究可以使我們更為深入地了解書體發(fā)展演變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