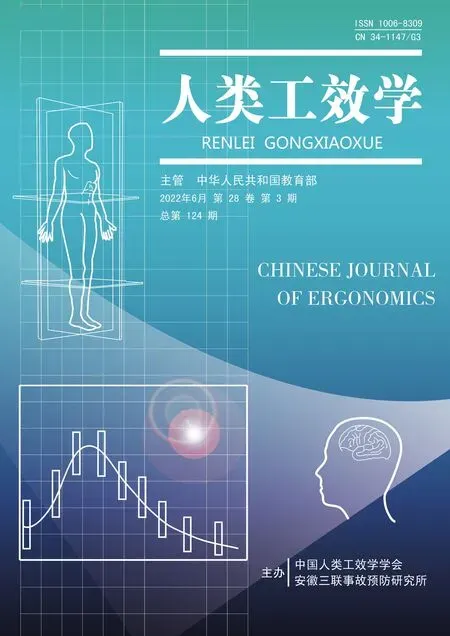12-16歲少年認知共情與欺凌角色行為的關系: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
徐霜,劉泓妤,郝澤生,葉逢璐,洪芳,牛玉柏
(浙江理工大學心理學系,杭州 310018)
1 引言
校園欺凌(School Bullying)也稱霸凌或欺負,最早由Olweus提出,是指對無力保護自己的弱小的學生造成身體或心理傷害的反復的攻擊性行為[1]。校園欺凌現象普遍存在且十分嚴重。日本超過一半的學校存在校園欺凌現象[2],美國36%的6-12年級學生報告遭受過欺凌[3]。校園欺凌會造成嚴重的后果,欺凌者會有更多的酗酒、家暴和犯罪的風險,受害者會經歷更多的抑郁和焦慮[4],以及各種心理健康和學業適應的問題[5]。此外,僅僅目睹欺凌事件就可能對旁觀者的心理健康造成嚴重的消極影響[6]。因此探討中小學生欺凌角色行為的現狀及發生機制對于預防欺凌的發生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校園欺凌事件中存在著不同的角色,過去二十年相關研究的關注點從欺凌者和受害者轉移到旁觀者[7]。旁觀者分為不同的角色,包括:跟隨者,指協助、跟隨欺凌者的兒童;強化者,指通過某些行為方式來強化欺凌者的兒童;助人者,指幫助受害者的兒童;局外人,指什么也不做,回避欺凌情境的兒童[8]。盡管參與欺凌事件的方式不同,但無論是欺凌、協助欺凌還是制止欺凌,都與個人的情感和認知因素有關,如共情、道德敏感度、道德推脫等[9]。
共情是指理解和感受他人情緒的能力[10],包括認知共情與情感共情兩個維度[11]。認知共情著重于推斷他人的情緒狀態[12];情感共情則是對他人情緒狀態的體驗和反應[13]。神經生理學的研究證明,情感共情與認知共情是兩個相互獨立又相互補充的成分,它們在發展趨勢[14]、個體差異[15]以及影響機制[16]等方面有差別,同時認知共情是情感共情發生的先決條件,情感共情可以看作是認知共情的深入[17],它們在欺凌中的作用也并不相同[18]。
根據社會認知理論的觀點,欺凌行為是一種有意識的決定,幾乎所有的欺凌都是由于欺凌者錯誤的歸因所導致的[19]。而認知共情較低的兒童少年不能很好地理解受害者的處境,他們更可能通過重新定義不道德行為來推卸責任,擺脫內疚和自責感,實施欺凌行為。因此,提高認知共情能力會促進青少年公正動機和道德意識的發展[20],從而使兒童少年表現出更多的幫助行為與更少的欺凌行為[21]。元分析的結果也支持認知共情與攻擊態度、攻擊行為之間顯著負相關的結論[22]。那么認知共情與欺凌角色行為是否也存在這種關系呢?這是本研究試圖探討的第一個研究問題。
此外,在個體認知因素中,道德控制的失敗也是青少年攻擊行為出現的重要風險因素,它主要是由道德推脫引起的[21]。道德推脫是指個體脫離道德標準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認知重建,以減少負性情緒的產生。道德推脫水平高的青少年會有更多的欺凌和促進欺凌行為[23],以及更少的內疚感和幫助行為[24]。研究者還發現,共情與道德推脫之間相關顯著,即共情能力越強,越不容易產生道德推脫[25]。而道德推脫作為一種認知機制,僅有情感共情并不會使個體的道德推脫水平明顯下降,認知共情在其中的作用更大[26]。并且道德推脫在認知共情與身體、言語和關系欺凌等不同欺凌形式之間均存在顯著的中介作用[21]。那么,道德推脫是否在認知共情與欺凌角色行為之間起著中介作用呢?這是本研究試圖探討的第二個研究問題。
根據共情的多維取向理論,除了個體的認知因素外,共情的情感維度以及它們的相互作用也會對預防欺凌行為的發生產生重要影響[9]。共情利他假說認為,共情引發的情感(如同情、憐憫、擔心等)會喚起人們的利他動機[27],使人們更少卷入到欺凌事件中[28]。并且情感共情可以調節道德推脫與攻擊行為之間的關系,即情感共情較高的學生,他們的道德推脫對攻擊行為的影響會更小[29],此時情感共情起抑制效應。情感共情還可以調節認知共情對網絡欺凌的影響[15],此時情感共情起促進效應。那么情感共情在認知共情、道德推脫與欺凌角色行為之間是否也存在著調節效應?這是本研究試圖探討的第三個研究問題。
2 對象與方法
2.1 研究對象
方便選取杭州市某兩所九年制公立學校的六、七和八年級學生242人,回收有效問卷221份,有效回收率91.32%。其中六年級學生76人,七年級學生79人,八年級學生66人,年齡范圍在12-16歲之間,平均年齡13.48±0.82歲。
2.2 測量工具
2.2.1 基本共情量表
由Jolliffe和Farrington于2006年編制[30],李晨楓,呂悅,劉潔等人于2011年修訂[31],包括認知和情感兩個維度。5點計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完全同意”,分數越高表明認知和情感共情能力越強。本研究中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75和0.72。
2.2.2 道德推脫量表
由Bandura,Barbaranelli,Caprara等人于1996年編制[24],王興超和楊繼平于2010年修訂[32],包含道德辯護、委婉標簽、有利比較、責任轉移、責任分散、扭曲結果、責備歸因和非人性化八個維度。5點計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分數越高表示個體道德推脫水平越高。本研究中各分量表Cronbach's α系數為0.74~0.81。
2.2.3 欺凌參與角色行為問卷
由Demaray,Summers,Jenkins等人于2014年編制[33],邱小艷,楊偃成,劉小群等人于2020年修訂[34],包括欺凌行為、促進欺凌行為、受害行為、捍衛行為、事不關己行為五個分量表。5點計分,0表示“從不”,4表示“7次以上”,分數越高表明該分量表的行為出現越多。本研究中各分量表Cronbach's α系數為0.83~0.91。
2.3 數據處理
采用SPSS 19.0對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相關分析、回歸分析和有調節的中介效應分析等。
3 結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n 單因子檢驗法檢驗數據的共同方法偏差[35]。結果發現,共有3個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且第一個因子的解釋率為36.62%,小于40%的臨界值,說明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
在控制年級和性別后,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和偏相關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結果表明,道德推脫與捍衛行為、情感共情的相關性均沒有達到顯著水平(Ps>0.05),與其他變量均呈顯著相關(Ps<0.05);認知共情與受害行為的相關性沒有達到顯著水平(P>0.05),與其他變量均呈顯著相關(Ps<0.05);情感共情與認知共情呈顯著相關以外(P<0.05),與其他變量相關性均沒有達到顯著水平(Ps>0.05)。

表1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與偏相關分析結果(r)
3.3 道德推脫在認知共情與欺凌角色行為之間的中介作用
首先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的模型4檢驗道德推脫在認知共情與五種欺凌角色行為之間的中介作用[36]。結果表明,在控制了性別和年級的影響后,認知共情可以顯著預測道德推脫,a=0.15,t=-2.14,P=0.034;之后分別以五種欺凌角色行為作為因變量,將認知共情和道德推脫同時放入回歸方程。結果發現,以欺凌行為作為因變量時,認知共情和道德推脫的預測作用顯著,c’=-0.07,t=-2.27,P=0.024,b=0.24,t=8.20,P<0.001。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表明,道德推脫的中介作用顯著,ab=-0.04,95%的置信區間為[-0.076,-0.003];以促進欺凌行為作為因變量時,認知共情和道德推脫的預測作用顯著,c’=-0.07,t=-3.15,P=0.002,b=0.14,t=6.41,P<0.001。Bootstrap結果表明,道德推脫的中介作用顯著,ab=-0.02,95%的置信區間為[-0.046,-0.002];以事不關己行為作為因變量時,認知共情和道德推脫的預測作用顯著,c’=-0.10,t=-2.85,P=0.049,b=0.14,t=4.04,P<0.001。Bootstrap 結果表明,道德推脫的中介作用顯著,ab=-0.02,95%的置信區間為[-0.051,-0.001];以受害行為作為因變量時,道德推脫的預測作用顯著,b=0.18,t=2.97,P=0.003,而認知共情的預測作用變得不再顯著,c’=-0.07,t=-1.20,P=0.232。Bootstrap結果表明,道德推脫的中介作用不顯著,ab=-0.03,95%的置信區間為[-0.073,0.001];以捍衛行為作為因變量時,認知共情的預測作用顯著,c’=0.28,t=4.04,P<0.001,而道德推脫的預測作用不顯著,b=-0.08,t=-1.13,P=0.260。Bootstrap結果表明,道德推脫的中介作用不顯著,ab=0.01,95%的置信區間為[-0.006,0.038]。
3.4 情感共情在認知共情與欺凌角色行為之間的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由3.3的結果可知,道德推脫在認知共情與欺凌行為、促進欺凌行為和事不關己行為之間存在中介作用,為了進一步檢驗情感共情對中介作用的調節效應是否顯著,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的模型1和模型59檢驗情感共情的調節作用。檢驗有調節的中介模型需要建立三個回歸方程:(1)方程1估計調節變量對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調節作用;(2)方程2估計調節變量對自變量與中介變量之間的調節作用;(3)方程3估計調節變量對中介變量與因變量以及自變量對因變量的殘余效應的調節作用[36]。分別在三個因變量上建立這三個回歸方程,檢驗結果見表2-表4。由表2-表4可知,方程1中認知共情可顯著反向預測欺凌、促進欺凌和事不關己行為,而認知共情和情感共情的交互項對這三種行為的預測作用不顯著,說明情感共情不能調節認知共情對三種欺凌角色行為的直接作用。方程2中情感共情與認知共情的交互項對道德推脫的預測作用顯著,并且方程3中道德推脫可以顯著正向預測三種欺凌角色行為,根據Hayes的觀點,情感共情對道德推脫在認知共情與三種欺凌角色行為之間中介效應的調節作用顯著,情感共情在模型的前半路徑上起調節作用[37]。而方程3中情感共情與道德推脫的交互項對三種欺凌角色行為的預測作用不顯著,說明情感共情在模型后半路徑上的調節作用不顯著。

表2 情感共情在認知共情與欺凌行為之間的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表3 情感共情在認知共情與促進欺凌行為之間的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表4 情感共情在認知共情與事不關己行為之間的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為了進一步考察情感共情是如何調節認知共情與道德推脫之間的關系,將情感共情按照正負一個標準差的上下分成高、低兩組,并進行簡單斜率檢驗(simple slope test),檢驗結果見圖1。結果表明,當情感共情較低時,認知共情對道德推脫的預測作用并不顯著,Bsimple =-0.04,t=-0.49,P>0.05;當情感共情較高時,認知共情可以顯著負向預測道德推脫水平,Bsimple =-0.35,t=-3.25,P<0.01。

圖1 情感共情在認知共情對道德推脫影響中的調節效應
4 討論
4.1 認知共情與校園欺凌角色行為之間的關系
本研究發現,認知共情與欺凌、促進欺凌和事不關己行為呈顯著負相關,這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一致[38-39]。雖然以往有研究者認為認知共情水平高的欺凌者更加擅長“讀心術”,更容易掌控他人,表現出更多的欺凌行為。但本研究卻發現,認知共情水平低的少年更有可能會出現欺凌和促進欺凌行為。這可能是因為他們的觀點采擇能力較差,不容易理解自己的行為給他人帶來的痛苦,更容易實施欺凌行為,或是更熱衷于協助欺凌者實施攻擊行為,或者裝作沒看見,拒絕幫助受害者。旁觀者介入模型認為,旁觀者介入共包含了五個階段,分別是注意發生什么事、解讀事件是否緊急、認同干預是一項責任、知道必要的干預策略以及實施干預行動[40]。這其中的三個階段都與認知共情能力有關,這可能是認知共情水平低的旁觀者沒有采取幫助行為,甚至還協助欺凌者侵害的原因。
此外,認知共情與捍衛行為呈顯著正相關,這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一致[41],即認知共情越高的旁觀者越可能在欺凌事件中采取幫助行為,這表明培養少年的認知共情能力有助于促進他們親社會行為的發展。
4.2 道德推脫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發現,道德推脫在認知共情與欺凌、促進欺凌和事不關己行為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這表明,認知共情水平低的少年更可能通過道德推脫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認知重建,避免出現內疚、自責等負性情緒,從而實施欺凌或協助欺凌者實施欺凌行為,這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一致[42-43]。本研究結果支持了道德推脫理論,即道德推脫合理地切斷個體行為或決策與其內在道德標準之間的聯系,使得個體在欺凌中不但不實施幫助行為,甚至在做出不道德的攻擊行為時,也能輕易擺脫內疚與自責[19]。在欺凌事件發生時,認知共情水平低的少年可能較少考慮受害者遭受的痛苦,將自己的欺凌行為解釋為“男性力量的象征”,從而造成更嚴重的欺凌;旁觀者也可能采用“責任轉移”的道德推脫機制,從而允許自己不卷入到欺凌事件當中。
4.3 情感共情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還發現,少年的情感共情可以調節道德推脫在認知共情與欺凌、促進欺凌以及事不關己行為之間的中介作用,該調節作用發生在中介路徑的前半段,即情感共情調節了認知共情對道德推脫的影響。該結果支持了情感共情對認知共情的促進作用[15],即對于情感共情水平較低的少年,他們的親社會動機很弱,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受害者的處境,都會表現出明顯的道德推脫現象,此時認知共情無法預測他們的道德推脫;而對于情感共情水平較高的少年,他們的親社會動機更強,當注意到受害者的不利處境時,更可能遵循道德標準的要求,采取相應的幫助措施,而不會置之不理,此時認知共情可以顯著改善他們的道德推脫現象,產生促進效應。
此外,情感共情不能調節道德推脫對欺凌角色行為的影響,這可能是因為道德推脫對欺凌角色行為的影響更大[19],無論情感共情是低或是高,道德推脫的少年都更可能參與欺凌行為,研究結果也支持了道德推脫理論的觀點。因此,為預防校園欺凌事件的發生,教育工作者既要加強對少年認知因素的關注,保證他們能夠理解欺凌中受害者的不利處境;同時也要注重對少年共情關注能力的培養,促進他們親社會動機的發展,并傳授合適的干預方法,從而使少年能夠更加嚴格地按照道德標準正確地應對校園欺凌。
4.4 不足與展望
第一、本研究在調查對象選取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推廣研究結論需要更加慎重;第二、本研究采用自我報告法測量欺凌角色行為,未來可以采用行為觀察法和社會測量法等多種研究方法來補充和豐富相關研究;第三、家庭和社會因素也會對少年的攻擊行為產生影響[44],未來可以更深入探討外界環境和個體內在因素是如何共同影響少年的欺凌角色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