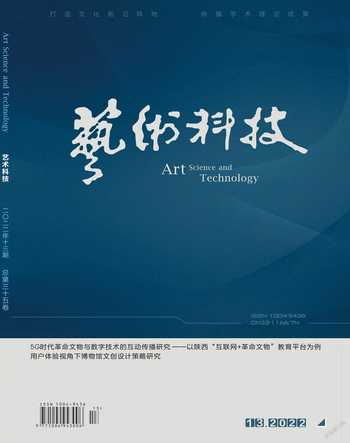古籍點校成果的法律保護(hù)研究
摘要:隨著時代的發(fā)展,網(wǎng)絡(luò)通信愈發(fā)便捷,古籍點校成果面臨侵權(quán)的問題也逐漸引起學(xué)者的注意。作為古籍原文的“注釋”,古籍點校如果蘊(yùn)含點校者獨(dú)創(chuàng)性的表達(dá),一般都可以作為演繹作品保護(hù),但對單純的點校而言,點校成果因為無法受到著作權(quán)的保護(hù)而面臨巨大的挑戰(zhàn)。因此,古籍點校者的智力勞動是否應(yīng)當(dāng)受到著作權(quán)保護(hù),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對于無法定為“作品”的點校成果,可以設(shè)立特殊的鄰接權(quán)保護(hù)制度。
關(guān)鍵詞:古籍點校;獨(dú)創(chuàng)性;演繹作品;鄰接權(quán)
中圖分類號:D923.41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2)13-0-03
1 問題的提出
關(guān)于古籍點校成果侵權(quán)的經(jīng)典案例當(dāng)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有限公司訴人民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侵害其對《鏡花緣》校注版一書的專有出版權(quán)一案。案件的關(guān)鍵點在于,對于這本清代小說家李汝珍撰寫的長篇小說《鏡花緣》,經(jīng)張友鶴標(biāo)點和校注后,是否屬于獨(dú)創(chuàng)性表達(dá)。1955年,張友鶴校注的《鏡花緣》在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出版,1977年張友鶴去世后,其后人又將該書的專有出版權(quán)授予該出版社。但2017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和張友鶴校注版別無二致的《鏡花緣》,其中注釋幾乎沒有差別。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有限公司訴求法院,要求對方道歉并給予賠償。
法院審理認(rèn)為,古籍點校者對古籍所做的標(biāo)點分段注釋等是集自己的智力成果為一體而形成的區(qū)別于“原本”的獨(dú)創(chuàng)性表達(dá)。正如張友鶴校注的《鏡花緣》,應(yīng)當(dāng)視為演繹作品而受到著作權(quán)法的保護(hù)。最終法院一審判決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有限公司勝訴,人民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應(yīng)當(dāng)停止出版發(fā)行此書,并賠償勝訴方經(jīng)濟(jì)損失300萬元。
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中華文明成果根本的創(chuàng)造力,是新時期創(chuàng)新與改革的源泉,而古籍在其中發(fā)揮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而要傳承古籍中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古籍點校是一項基礎(chǔ)工作。
古籍點校是對古籍進(jìn)行編輯加工,或分段或加標(biāo)點或補(bǔ)充或刪減或修改,前提是結(jié)合客觀的歷史事實,加之綜合點校者的歷史文化水平、價值判斷等因素而開展的一項古籍整理工作。“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不僅古籍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yùn),對這些古籍的點校,也需要耗費(fèi)點校者很大的精力,花費(fèi)自己的心血注釋而成。然而,對古籍點校成果的保護(hù)存在爭議,古籍點校成果頻頻出現(xiàn)被侵權(quán)的現(xiàn)象。在司法實踐中,點校成果真的無法納入著作權(quán)法的法律保護(hù)羽翼之下嗎?
2 古籍點校成果能否被認(rèn)定為作品
2.1 案例對比
上述《鏡花緣》一案,法官對張友鶴的智力成果給予了肯定的判決,認(rèn)為其最后著作的新版本具有獨(dú)創(chuàng)性,能構(gòu)成演繹作品,這無疑給了許多古籍點校者信心和鼓勵。其實在此之前的許多案例中,針對同一個焦點問題,不同的法官作出了不同的判決。
中華書局訴北京國學(xué)時代文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點校本“二十四史”與《清史稿》等電子產(chǎn)品侵權(quán)案,終審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將點校智力成果視為作品。這個古籍點校“世紀(jì)第一案”中法官指出,古籍點校工作專業(yè)性較強(qiáng),并非非專業(yè)的普通人可以完成,這需要長久以來的文化積累和扎實的文學(xué)功底。若只是將點校行為視作一種“機(jī)械行為”,相信所謂的點校版本會無人問津。國學(xué)時代公司電子產(chǎn)品中“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內(nèi)容與受著作權(quán)保護(hù)的中華書局點校本的內(nèi)容差異很小,構(gòu)成實質(zhì)性近似,所以侵權(quán)。該案雖歷經(jīng)兩審,但各審法官的觀點基本一致,即充分認(rèn)可點校成果的可版權(quán)性。獨(dú)創(chuàng)性體現(xiàn)在從事古籍整理的工作人員所具備的成熟的業(yè)務(wù)技能以及豐富的文史知識儲備,簡言之,古籍點校成果是點校人基于自身的國學(xué)素養(yǎng)對古籍底本獨(dú)立作出的現(xiàn)代化詮釋,符合著作權(quán)法對作品的定義和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應(yīng)當(dāng)納入著作權(quán)法的保護(hù)中。由此,法院將“二十五史”定義為“經(jīng)整理產(chǎn)生的作品”,雖然并未就“二十五史”的作品屬性作進(jìn)一步認(rèn)定,但法院基于此判決明確了保護(hù)的態(tài)度。
周錫山訴江蘇鳳凰出版社有限公司等侵害作品復(fù)制權(quán)、發(fā)行權(quán)糾紛一案中,一審和二審判決給出了不同的答案。判決指出:當(dāng)點校成果目的在于復(fù)原古籍原意、點校者僅是按照語法規(guī)則揭示了客觀事實時,點校成果不構(gòu)成著作權(quán)法意義上的作品;古籍點校有個明顯的特殊之處,就是古籍點校在先者和在后者,因為古籍文獻(xiàn)的有限和歷史的客觀現(xiàn)實,后面的點校存在與之前相似的表達(dá)是十分正常的現(xiàn)象,如果以此為依據(jù)認(rèn)定其不具有獨(dú)創(chuàng)性,未免牽強(qiáng)。換言之,不能因為一項成果的來之不易和千頭萬緒,進(jìn)而撬動我國著作權(quán)法的理論根基,任何方式的法律保護(hù)都應(yīng)當(dāng)回歸至理性,著作權(quán)法保護(hù)更是如此。
然而,該案在再審中發(fā)生了反轉(zhuǎn),再審法官認(rèn)為點校為古籍原文帶來了不同的閱讀感受,發(fā)生了實質(zhì)性變化,符合作品的特征,受著作權(quán)法保護(hù)。基于以上的案例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古籍點校成果納入著作權(quán)法保護(hù)受到更多司法界人士的支持。所以縱觀司法實踐,不同法官給出的裁判理由主要圍繞古籍點校成果能否受到著作權(quán)法保護(hù),歸根結(jié)底還是看其是否能被認(rèn)定為作品。如果能,作品的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又如何在“古籍點校成果”上形成邏輯自洽?如果不能,又該如何保護(hù)點校者的成果呢?
2.2 學(xué)術(shù)爭議
基于上述三個案例可以看出,學(xué)界和司法實踐中,對古籍點校成果是否形成新的作品存在不同的觀點。
肯定者認(rèn)為,古籍點校可以形成新的作品,因為古籍點校凝結(jié)了點校者的智慧與汗水,是以其廣博的歷史文獻(xiàn)知識和大量的研究探討為基礎(chǔ)的高難度工作,點校者創(chuàng)作的點校讀本,是全新的演繹作品。支持者認(rèn)為也可以在著作權(quán)法中找到相應(yīng)的法律依據(jù):著作權(quán)法第12條明確指出,“改編、翻譯、注釋、整理已有作品而產(chǎn)生的作品,其著作權(quán)由改編、翻譯、注釋、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權(quán)時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權(quán)”。同時,也有支持者指出,古籍點校工作需要點校者有深厚的文化積累和個性化理解,并且將這種理解融入古籍點校中。比如在進(jìn)行標(biāo)點和給段落分段的時候,學(xué)者就會根據(jù)自己過往的經(jīng)歷以及文獻(xiàn)的閱讀習(xí)慣,作出不同的選擇,這也是因為某些古籍雖然標(biāo)點斷句不同,但都能自然通順,更何況部分古籍保存得不完整,對那段歷史的多樣化解釋也會導(dǎo)致最終的注釋不同。因而,不能因為部分內(nèi)容相似,就不認(rèn)可古籍點校者的智力成果。這樣既會導(dǎo)致古籍點校者心有余而“力”不足,也不利于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與發(fā)揚(yáng)[1]。
否定者則持完全不同的觀點。他們認(rèn)為這種針對古籍文獻(xiàn)本身的注釋行為,只是一次技術(shù)處理,不能被視為作品,也自然不能受著作權(quán)法保護(hù)。在這些觀點持有者看來,古籍點校是基于原作的,為了還原古籍內(nèi)容的原貌,追求客觀事實本身,而不是把自己的創(chuàng)作技巧、方法、風(fēng)格等融入進(jìn)去,形成新的作品。同時,在認(rèn)定“作品”的范圍內(nèi),有許多客體,只存在唯一表達(dá)形式,若是用著作權(quán)保護(hù)這類客體,就會妨礙科學(xué)與文化的發(fā)展,比如美國將這類作品稱為“事實作品”,德國將其定義為“自然科學(xué)作品”[2]。因為在古籍原文的基礎(chǔ)上,對其加標(biāo)點、分段、補(bǔ)充或刪改內(nèi)容,都有一定的規(guī)范性、習(xí)慣性和歷史淵源性,后人開展同樣的校對工作,不可避免地具有極大的近似性。若是認(rèn)定點校成果為新作品,不利于后人再次進(jìn)行古籍整理,讓人望而卻步,又何談對古籍內(nèi)容真?zhèn)蔚淖非螅灰f傳承正確的經(jīng)典著作了。
筆者認(rèn)為,古籍點校成果是否構(gòu)成演繹作品不能一概而論,對其是否受著作權(quán)法保護(hù)更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根據(jù)著作權(quán)法關(guān)于著作權(quán)作品的規(guī)定,作品的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包括智力成果和獨(dú)創(chuàng)性兩個重要因素。
首先是對“智力成果”的解讀。一方面,“智力成果”在這里的表述,筆者認(rèn)為有待商榷,思想亦是一種智力成果,公式也是一種智力成果[3]。所以此處不適合用“智力成果”作為“作品”的法定標(biāo)準(zhǔn),將“作品”限定為“智力表達(dá)”更為恰當(dāng)。古籍點校成果凝聚了點校者的智力創(chuàng)造,在充分發(fā)揮其所學(xué)的基礎(chǔ)上,用能夠為外界客觀感知的外在表達(dá)表現(xiàn)出來,理應(yīng)屬于“智力表達(dá)”。
其次是對“獨(dú)創(chuàng)性”的解讀。獨(dú)創(chuàng)性又可以分解為“獨(dú)立完成”和“創(chuàng)造性”。“獨(dú)立完成”即非抄襲、非剽竊。但這并不是構(gòu)成作品的必要條件,僅僅自己動手,還不一定能形成作品,重點在于“創(chuàng)作性”。這就要求作者在創(chuàng)作時,要將具有一定高度、個人特色的表達(dá)體現(xiàn)在創(chuàng)作之中。部分古籍內(nèi)容容易點校,僅需簡單的標(biāo)點和斷句即可完成,想要構(gòu)成獨(dú)創(chuàng)性比較困難[4],加之點校工作的創(chuàng)作空間極為有限,對古籍內(nèi)容真?zhèn)蔚淖C明材料也只會讓這份古籍點校成果更加接近事實,“創(chuàng)造性”中的個性和高度就更加難以體現(xiàn)。《著作權(quán)法》保護(hù)古籍點校成果的最大呼聲,是來自對點校者的專業(yè)知識和淵博學(xué)識的尊重。在《鏡花緣》一案中,認(rèn)定點校成果構(gòu)成新作品的一大理由也是對點校者積極性的鼓勵和對古籍點校行業(yè)形象的維護(hù)。
可以發(fā)現(xiàn),這種出于還原經(jīng)典著作目的的古籍點校,表達(dá)的內(nèi)容確實傾向于事實,形式也比較單一。古籍點校同時也有一個很大的特點,一旦有通行版本,就很少有學(xué)者或出版社重新對同樣的古籍進(jìn)行點校,因為缺少了新意和含金量。而對于古籍點校成果的獨(dú)創(chuàng)性認(rèn)定,不僅不易,且一旦將此種點校成果認(rèn)定為作品,會使得點校市場趨向衰弱,反而有悖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的立法初衷。
綜上所述,這些通行版本的古籍點校成果,因為缺乏獨(dú)創(chuàng)性,很難被稱為作品,更不要說以著作權(quán)的名義為其提供法律保護(hù)。2002年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quán)法實施條例》后,刪除了“整理”的定義,缺少了“‘整理’能夠產(chǎn)生新作品”這一直接的法律依據(jù)。在立法演進(jìn)的過程中,“整理”的含義從開始的明確可適用已經(jīng)轉(zhuǎn)變?yōu)槟:豢芍由弦?guī)范性文件效力的存廢不定帶來的干擾因素影響,點校行為是否還能被解釋為“整理”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由此給司法實踐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困擾[5]。縱觀司法實踐可以發(fā)現(xiàn),不同的法官在主觀上對作品的獨(dú)創(chuàng)性有不同的認(rèn)識,往往作出的判決也有所不同。
3 古籍點校成果保護(hù)路徑
基于上述分析展開思考,市場上大量盜版、剽竊的點校讀本該如何處置才能維護(hù)點校者的合法權(quán)益呢?
第一,完善著作權(quán)法司法解釋,對古籍整理作出規(guī)范解釋,在復(fù)雜的司法實踐與抽象的法律規(guī)定之間,讓保護(hù)點校成果有法可依。但此方法仍然是在特殊情況下,認(rèn)定古籍點校成果為作品,并沒有直面否定者“古籍是基于原作進(jìn)行的一種客觀現(xiàn)實的技術(shù)處理”“不利于后人的更新、整理工作”的觀點,現(xiàn)在看來頗為勉強(qiáng)。
第二,將點校成果納入民事權(quán)益保護(hù)范圍,基于古籍點校所投入的資金與人力支持,應(yīng)當(dāng)合理保護(hù)古籍點校者的權(quán)益,讓侵權(quán)者承擔(dān)停止侵權(quán)、賠償損失等法律責(zé)任,給文獻(xiàn)工作提供適當(dāng)?shù)募睢1娝苤偶c校耗時耗力,非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尤其是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更被稱為“史上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所以選擇此種路徑也有弊端,容易增加古籍點校的成本。
第三,對于無法認(rèn)定為作品的古籍點校成果,可以借鑒德國和意大利的著作權(quán)法制度,為古籍點校設(shè)立特殊的鄰接權(quán)保護(hù)制度,將點校成果納入鄰接權(quán)保護(hù)范圍內(nèi),比如以專有權(quán)的形式,將那些明顯區(qū)別于他人點校的作品納入合理的法律保護(hù)范圍內(nèi)。并且從發(fā)揚(yáng)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角度來看,鄰接權(quán)的保護(hù)制度涉及古籍點校范圍,保護(hù)期限較短,既能平衡經(jīng)濟(jì)發(fā)展與文化傳承的關(guān)系,又能激勵廣大古籍文化愛好者,積極參與到古籍整理工作中。
4 結(jié)語
“文以載道,文以化人”,幾千年來,中國豐富的古籍文獻(xiàn)資料給后人留下了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其中蘊(yùn)含的思想觀念、人生哲理、道德規(guī)范是值得永久傳承下去的,而古籍點校工作則讓這些古籍文獻(xiàn)變得更加通俗易懂,能夠得到更好的傳承和發(fā)揚(yáng),點校者的貢獻(xiàn)必須得到重視。保護(hù)古籍點校成果,不僅僅是為了那些已經(jīng)點校過的巨作,更是為了中華文明源源不斷的傳承。點校行為的目的雖為釋讀古籍原意,但因古籍點校者知識積累、占有資料和主觀認(rèn)知程度的差異,必然會表現(xiàn)為不同風(fēng)格、水平的個性化判斷。點校者綜合完成標(biāo)點、分段、注釋的智力成果整體產(chǎn)生的新版本作品應(yīng)當(dāng)根據(jù)是否符合獨(dú)創(chuàng)性標(biāo)準(zhǔn)而得到不同保護(hù),對符合著作權(quán)法“作品”標(biāo)準(zhǔn)的點校成果予以著作權(quán)法的保護(hù),對于無法定為“作品”的點校成果可以設(shè)立特殊的鄰接權(quán)保護(hù)制度,將點校成果納入鄰接權(quán)保護(hù)范圍內(nèi),賦予其合理的法律保護(hù)。
因而,面對古籍點校成果侵權(quán)事件,不能忽視點校者耗時耗力完成的成果面臨被侵害的風(fēng)險,又要在進(jìn)行文化保護(hù)的同時,認(rèn)識到經(jīng)濟(jì)效益的重要性。這是一個需要雙向均衡的論題,筆者認(rèn)為著作權(quán)法第四次修訂時,應(yīng)當(dāng)將保護(hù)古籍點校成果納入其中,探討對古籍點校成果更加恰當(dāng)、長久的保護(hù)途徑。
參考文獻(xiàn):
[1] 龔浩鳴.古籍點校成果構(gòu)成演繹作品[J].人民司法,2020(29):90-93.
[2] 張彥民,鄭成思.《版權(quán)法》探微[J].中國出版,1991(7):52-54.
[3] 何懷文.古籍點校本的法律保護(hù):特設(shè)民事權(quán)益與著作權(quán)之外第三條出路[J].中國出版,2013(13):25-27.
[4] 王雅宇.網(wǎng)絡(luò)時代如何保護(hù)古籍點校成果的著作權(quán):以獨(dú)創(chuàng)性分析為視角[J].傳播與版權(quán),2018(6):198-199.
[5] 劉玲玲.古籍點校成果的法律保護(hù)研究[D].武漢:中南財經(jīng)政法大學(xué),2020.
作者簡介:李若(1995—),女,安徽蕭縣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法社會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