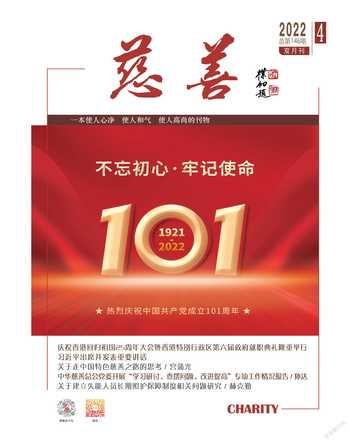我的老師公木先生
2022-07-15 16:11:53周凡愷
慈善
2022年4期
周凡愷
1979年全國高考的徹底結束,是7月9日,那個傍晚,我也徹底釋然了。我馬上跑到野外的一處小湖,不停歇地暢游了一個多小時,后來累了,就頭枕一塊石頭,看著一群群小魚兒在清澈的水中撒歡兒。我仔細地想了想三天來的考試,覺得上個普通大學,還是十拿九穩的,現在的關鍵,不是考上考不上的問題了,而是去選擇一所什么樣的院校。
如果按著我內心的真實想法,我是更愿意去讀美術學院的,當然最好是中央美術學院。但學美術,是要提前報考的,除了全國的文化統考,還需參加專業考試,也即是到設在吉林市的考場畫幾幅畫,而這些事情,我都錯過了。因為我的母親一直固執地認為:當一個小畫匠是難以養家的。她希望我繼承祖父和父親的衣缽,將來最好做個醫生,這才是正經的營生。但我最終還是讓母親失望了,因為我報考的是文科,即便分數再高,醫學院也是不可能錄取我的。
那么,我究竟應該報考一個什么院校什么專業呢?這的確是個問題。
高考成績公布之后,我考取的分數,竟然比我料想的還要高出許多,按著老師們的說法,我完全可以去報考當年的那二十幾所國家級重點大學了。
可我仍是十分糾結。
有一天,我實在閑得無聊,便逛到了我一中的語文老師于澄之家里去借書。于老師是山東人,畢業于東北師范大學中文系,對古典文學造詣頗深。他從書架上隨手抽出一本《詩經》遞給過來,說我看你干脆報考吉林大學中文系吧,去做張松如先生的門徒。……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