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鐘擺”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園圃”比喻
付來友
摘要:在云南傣族村寨的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當(dāng)?shù)氐奈幕冞w呈現(xiàn)了一種“鐘擺”現(xiàn)象。隨著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信息傳播、族際通婚等因素影響,人們?nèi)諠u融入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一體化進(jìn)程中。但在此基礎(chǔ)之上,人們又在新的意義上開始注重民族文化特色。這種變化預(yù)示著中華民族共同體中“一體”與“多元”的關(guān)系發(fā)生了微妙變化。隨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加深,“一體”的社會(huì)基礎(chǔ)正日漸牢固,但與此同時(shí)民族的“多元”文化也獲得了新的時(shí)代形式。這種“多元”的綻放不會(huì)損害“一體”的基礎(chǔ),而是在更高層面上使“一體”得到強(qiáng)化。
關(guān)鍵詞:一體多元;文化變遷;中華民族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hào):C956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0-5099(2022)04-0050-06
一、引言
費(fèi)孝通先生在著名的《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一文結(jié)尾提到“中華民族將是一個(gè)百花爭(zhēng)艷的大園圃”。之所以將中華民族比喻成一個(gè)“園圃”,我們可以在上文發(fā)現(xiàn)費(fèi)先生如此表述的原因:“在工業(yè)化的過程中,各民族人民生活中共同的東西必然會(huì)越來越多,比如為了信息的交流,必須有共同的通用語言,但是這并不妨礙各民族用自己的語言文字發(fā)展有自己民族風(fēng)格的文學(xué)”。按照費(fèi)先生所言,隨著工業(yè)化的進(jìn)行,各民族共性增加,將更為緊密地團(tuán)結(jié)在中華民族的大“園圃”之中,但是另一方面各民族共性的增加并不影響各民族特色的繼續(xù)存在,從而大“園圃”中不同民族文化也會(huì)出現(xiàn)“百花爭(zhēng)艷”的局面。
費(fèi)先生對(duì)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園圃”比喻涉及到各民族文化的共性與個(gè)性之間的辯證關(guān)系。作者在云南兩個(gè)傣族村寨的考察中,發(fā)現(xiàn)其文化變遷十分符合費(fèi)先生的這種表述。這兩個(gè)村寨位于云南省昌寧縣,名為帕旭、芒石。在1949年之前甚至1978年之前,這兩個(gè)村寨與外界的聯(lián)系相對(duì)較少。1978年之后,尤其是2000年之后,這兩個(gè)村寨與外界的聯(lián)系逐漸增多。與外界聯(lián)系的增加也是“各民族人民生活中共同的東西必然會(huì)越來越多”的過程。然而,在共性逐漸增多的基礎(chǔ)之上,這兩個(gè)傣族村寨反而開始強(qiáng)調(diào)其民族特色。比如人們開始在其房屋設(shè)計(jì)中增加傣族的文化元素,而這在其傳統(tǒng)建筑樣式中是沒有的。
這兩個(gè)傣族村寨的文化變遷說明現(xiàn)代化過程中,民族文化變遷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發(fā)展之間存在一種呼應(yīng)關(guān)系,這種呼應(yīng)關(guān)系涉及到了文化與共同體認(rèn)同的一般性問題。下文先從這個(gè)問題說起,然后再對(duì)這兩個(gè)傣族村寨的文化變遷進(jìn)行描述,最后再討論其對(duì)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發(fā)展所具有的個(gè)案意義。
二、文化與共同體認(rèn)同
共同體認(rèn)同的形成有多種方式,文化無疑是一個(gè)重要要素。格爾茲(Clifford Geertz)將文化看作“意義之網(wǎng)”,是外在于個(gè)體且不依賴于個(gè)體的一種延續(xù)性。格爾茲對(duì)文化的界定一方面受到了韋伯(Max Weber)的影響,另一方面又有一些現(xiàn)象學(xué)的色彩。按照現(xiàn)象學(xué)的觀點(diǎn),每個(gè)人都擁有一條與他人永遠(yuǎn)無法相交的意識(shí)流,因而從絕對(duì)意義上來說,“人與人的悲歡并不相通”,任何人的感受都無法超出皮膚的邊界。或許在“腦機(jī)接口”技術(shù)成熟之后,我們可以將一個(gè)人的感覺精確復(fù)制到另外一人的頭腦中,但在此之前,人與人之間是無法實(shí)現(xiàn)真正意義上相互理解的。所謂的理解,不過是人們回憶自己的類似感受,從而對(duì)別人的感受做出設(shè)想,而不是直接意義上感受別人的感受。這種設(shè)想要成為可能,文化的意義之網(wǎng)就成為了必要。語言符號(hào)作為文化的重要構(gòu)成部分,使得人們的相互理解成為可能。比如當(dāng)一個(gè)人說道自己“悲傷”的時(shí)候,我們就可以調(diào)動(dòng)起“悲傷”所對(duì)應(yīng)的內(nèi)在體驗(yàn),從而對(duì)別人的感受做出揣測(cè)。身處同一個(gè)文化中,人們對(duì)語言的意義有著共同的約定,從而使得彼此的溝通成為可能。除了語言,各種儀式、信號(hào)、標(biāo)志等其它符號(hào)類型都具有這種功能。
在對(duì)文化進(jìn)行定義后,格爾茲又將宗教、意識(shí)形態(tài)等看作“文化體系”,如此類推下去“文化體系”的概念還可以進(jìn)一步涵蓋泰勒(Edward B.Tylor)的文化定義中所羅列的“知識(shí)、信仰、藝術(shù)、道德、法律、風(fēng)俗”等等。所有這些文化要素,都具有一種符號(hào)化的存在狀態(tài),構(gòu)成了某個(gè)群體共享的意義世界。按照一般的劃分,這些文化體系可以分為三種類別:一種是認(rèn)知的,即關(guān)于人類自身以及世界的各種知識(shí);一種是道德的,即關(guān)于價(jià)值與行為方式的各種觀念、規(guī)范;最后一種是審美的,即藝術(shù)的文化創(chuàng)造。比如宗教的“文化體系”既包含認(rèn)知要素,又包含道德要素。宗教信仰一方面提供了一套關(guān)于這個(gè)世界的基本看法,這些看法可能與自然科學(xué)的認(rèn)知不相符,但卻被信徒們信以為真。以對(duì)世界的特定知識(shí)為前提,人們又發(fā)展出與之相適應(yīng)的行為方式,這就屬于道德的范疇。
身處同一個(gè)文化中的人們,通過不同的符號(hào)系統(tǒng),共享著認(rèn)知的、道德的、審美的各種文化要素,從而處于一種共同的精神世界中。如此人們才能夠在個(gè)體孤立的意識(shí)流之間建立聯(lián)系,實(shí)現(xiàn)文化意義上的“感同身受”,一種認(rèn)同意識(shí)由此形成。文化與共同體認(rèn)同的這種關(guān)系在赫茲菲爾德(Michael Herzfeld)的“文化親昵”概念中得到了精妙表達(dá)。當(dāng)兩個(gè)人意味深長(zhǎng)地眨一下眼或者說出類似“你懂得”的表述時(shí),相對(duì)于第三者的一種親密感就建立起來。相對(duì)于共同體外部的成員來說,人們分享了大量彼此都“懂得”而外人“不懂得”的符號(hào)意義。這種文化共性越多,“意義之網(wǎng)”的連接就更為牢固。
當(dāng)下中華民族的發(fā)展正處于“各民族人民生活中共同的東西必然會(huì)越來越多”的進(jìn)程中。不同民族共享的文化要素變得越來越多,對(duì)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rèn)同也隨之增強(qiáng)。各民族文化共同性的增加一方面得益于國(guó)家有意識(shí)的培育,另一方面也是社會(huì)交往自然而然的結(jié)果。從國(guó)家角度來說,通過學(xué)校教育、官方媒體等手段,培育著人們的歷史與社會(huì)認(rèn)同。從社會(huì)交往角度來說,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的迅速發(fā)展以及通信技術(shù)的日新月異使得各民族之間的交往與交流越來越多,從而使得彼此的生活日益相互交融。在這些變化中,最矚目的當(dāng)屬最近十幾年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的快速進(jìn)步。中國(guó)強(qiáng)大的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能力使4G網(wǎng)絡(luò)進(jìn)入了最偏遠(yuǎn)的地區(qū),將14億人口更緊密地聯(lián)系在了一起。4G技術(shù)的普及使得人們的信息交流從文字與語音為主的時(shí)代轉(zhuǎn)向了視頻為主的時(shí)代。視頻所傳遞的信息量遠(yuǎn)超出了文字與語音,使得人們對(duì)不在場(chǎng)的場(chǎng)景獲得了在場(chǎng)般的體驗(yàn)。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的發(fā)展促進(jìn)了平臺(tái)經(jīng)濟(jì)的發(fā)達(dá),使得各民族之間的經(jīng)濟(jì)聯(lián)系也變得更緊密。
然而,所有這些社會(huì)交往的強(qiáng)化卻伴隨著一種相反的趨勢(shì)。人們?cè)谌谌胪獠渴澜绲耐瑫r(shí),對(duì)自己的地方性的、民族性的文化特色也變得更為珍視。比如張文瀟、趙旭東對(duì)一個(gè)河北村莊的研究中提出了“鐘擺現(xiàn)象”的概念。在這個(gè)河北村莊,板栗種植曾在二十世紀(jì)九十年代構(gòu)成了村民經(jīng)濟(jì)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遺產(chǎn)繼承中“爭(zhēng)樹”構(gòu)成了一種常見的糾紛。隨著打工經(jīng)濟(jì)興起,村民們有了更好的收入渠道,于是紛紛“棄樹”,板栗園被荒廢。然而,在最近幾年村民們又因各種原因出現(xiàn)了返鄉(xiāng)趨勢(shì),人們重新發(fā)掘板栗的價(jià)值,又開始“守樹”。從“爭(zhēng)樹”到“棄樹”再到“守樹”的變化也是人們與家鄉(xiāng)的聯(lián)系從緊密到松散再到重新連接的變化。人們重新回歸家鄉(xiāng)并不意味著返回一種傳統(tǒng)的封閉狀態(tài),而是一種“否定之否定”的更高層次回歸,是已經(jīng)融入外部世界的前提下對(duì)傳統(tǒng)紐帶的重新發(fā)掘。面對(duì)一個(gè)充滿風(fēng)險(xiǎn)的外部世界以及個(gè)體化的生存狀態(tài),人們重新開始向傳統(tǒng)資源需求幫助。
如果我們將這種“鐘擺現(xiàn)象”加以擴(kuò)展,就會(huì)發(fā)現(xiàn)除了村莊共同體的變遷中存在這種變化,民族共同體生活中也存在這種變化,本研究在云南傣族村寨的考察中就發(fā)現(xiàn)了類似現(xiàn)象。通過對(duì)民族文化“鐘擺現(xiàn)象”的描述,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中華民族共同體格局中“一體”與“多元” 的關(guān)系所具有的新的時(shí)代含義。
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傣族村寨
帕旭、芒石是云南省昌寧縣灣甸傣族自治鄉(xiāng)的兩個(gè)傣族村寨,兩村寨共計(jì)有84戶,300余人。在二十世紀(jì)70年代,帕旭寨遭遇洪水災(zāi)害,災(zāi)后村址發(fā)生遷移,使得原本相鄰的兩個(gè)村寨進(jìn)一步靠近。現(xiàn)在兩個(gè)村寨在居住空間上已經(jīng)分辨不出彼此,很多公共活動(dòng)也共同舉辦,故而本研究將兩者作為一個(gè)共同單位展開研究。兩個(gè)村寨所處的灣甸鄉(xiāng)是一處被群山環(huán)繞的山間壩子,在壩子四周的山腳,分布著各個(gè)村寨,宛如一串項(xiàng)鏈上的寶石。這個(gè)壩子與周邊其它地區(qū)被群山阻斷,交通不便,在長(zhǎng)期歷史發(fā)展中形成了一個(gè)相對(duì)獨(dú)立的社會(huì)單位。
從明朝開始,灣甸土知州在此地進(jìn)行了長(zhǎng)達(dá)540多年的封建世襲統(tǒng)治。1924年灣甸土知州隸昌寧縣府轄,但是土司衙門一直存在,土司仍在沿襲。直到1950年4月第28代土司景功同向政府移交了印信、家譜和具有權(quán)力象征的寶劍等,灣甸鄉(xiāng)的土司統(tǒng)治制度才最終結(jié)束。結(jié)束土司統(tǒng)治后,土地等生產(chǎn)資料回到了人民手中,人民生活開始有了改善。經(jīng)過農(nóng)業(yè)集體化改造,帕旭、芒石進(jìn)入了人民公社時(shí)期。十一屆三中全會(huì)之后,人民公社制度在全國(guó)范圍內(nèi)被撤銷,灣甸公社改區(qū),設(shè)置灣甸區(qū),1988年灣甸區(qū)改鄉(xiāng)成立灣甸傣族鄉(xiāng)。
在歷史沿革中,灣甸鄉(xiāng)逐漸打破了一種相對(duì)封閉的狀態(tài)。據(jù)村中老人回憶,在1949年之前,在周邊地區(qū)看來,灣甸鄉(xiāng)是充滿“瘴氣”的蠻荒之地。灣甸之外的人從不會(huì)在此過夜,因?yàn)榕率艿健罢螝狻钡挠绊懚静 J聦?shí)上,古代“瘴氣”的說法實(shí)際上反映了地域偏見和文化歧視,而非一種自然的疾病。外界認(rèn)為灣甸存在“瘴氣”實(shí)際上是交往匱乏的結(jié)果,以致外界產(chǎn)生了一些不合理的想象。彼時(shí)除了外界對(duì)灣甸充滿偏見,灣甸的人們似乎也不愿意與外界產(chǎn)生過多的交往。最典型的體現(xiàn)就是1949年之前灣甸的傣族群眾反對(duì)與漢族通婚。80多歲的村民楊某向我們講述了自己年輕時(shí)的婚戀經(jīng)歷,當(dāng)時(shí)他與一名漢族姑娘正處于戀愛之中,但是由于父母堅(jiān)決反對(duì)娶漢族姑娘,兩人最終沒能走在一起。
現(xiàn)如今,楊某的戀愛悲劇已經(jīng)不可能在灣甸鄉(xiāng)的村民身上發(fā)生了,灣甸鄉(xiāng)的年輕人已經(jīng)能夠與漢族的年輕人自由通婚。根據(jù)村民回憶,二十世紀(jì)六七十年代與漢族通婚的案例開始慢慢出現(xiàn),但仍舊較少。到九十年代,村民與漢族通婚才多起來。現(xiàn)如今帕旭、芒石共有30對(duì)夫妻是跨民族婚姻,在兩個(gè)村寨一共80多戶人家中已經(jīng)占了不小的比例。同時(shí),外界也不再將灣甸鄉(xiāng)看作充滿“瘴氣”的蠻荒之地,并與灣甸鄉(xiāng)的人民產(chǎn)生著頻繁的人員、商品和信息交流。從1949年前后到如今的變化是一個(gè)緩慢的過程,中間的細(xì)節(jié)難以描述清楚。如果進(jìn)行一個(gè)大致的階段劃分,1978年可以看作一個(gè)關(guān)鍵節(jié)點(diǎn)。在人民公社時(shí)期灣甸與外界的交往雖然增加,但是還不夠充分。在1978年之后尤其是21世紀(jì)以來,灣甸鄉(xiāng)與外界的交往呈現(xiàn)了加速態(tài)勢(shì),這種變化主要得益于以下幾個(gè)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灣甸鄉(xiāng)在進(jìn)入21世紀(jì)之后,開始發(fā)展起了反季節(jié)蔬菜水果種植,深度融入了與外界的經(jīng)濟(jì)交往之中。灣甸鄉(xiāng)蔬菜水果種植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得益于外部市場(chǎng)環(huán)境的變化以及自身獨(dú)特的氣候條件。從整個(gè)中國(guó)消費(fèi)市場(chǎng)的變化來說,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飲食從糧食為主轉(zhuǎn)變?yōu)榱艘怨呷馇轂橹鳎a(chǎn)生了巨大的消費(fèi)需求。灣甸鄉(xiāng)地處低緯度、低海拔地區(qū),冬季依舊保持著較高的氣溫,于是灣甸鄉(xiāng)的傣族群眾利用這一獨(dú)特優(yōu)勢(shì)發(fā)展反季節(jié)果蔬種植,并遠(yuǎn)銷北方地區(qū)。現(xiàn)在果蔬種植已經(jīng)成為了帕旭、芒石村民最主要的經(jīng)濟(jì)收入來源。每年冬季,外部的客商就會(huì)來到灣甸鄉(xiāng),將一車車的豆角、苦瓜、辣椒、西瓜等產(chǎn)品運(yùn)往外地。這使得灣甸鄉(xiāng)與外界產(chǎn)生了更緊密的聯(lián)系,與外部人員發(fā)生了更頻繁的交往。
通訊技術(shù)的發(fā)展是帕旭、芒石的村民與外界產(chǎn)生更緊密聯(lián)系的另外一個(gè)重要原因。在最近10年,中國(guó)4G技術(shù)和智能手機(jī)全面普及。除了老年村民和兒童,帕旭、芒石寨的村民幾乎每人都有一部智能手機(jī)。微信朋友圈、抖音視頻、淘寶購(gòu)物、網(wǎng)絡(luò)游戲成為了村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發(fā)展使人們接受了更多的外部信息,與其他民族的群眾產(chǎn)生了更多共同話題。在調(diào)查過程中,我們與當(dāng)?shù)氐哪贻p人相互交流,可以隨時(shí)討論網(wǎng)絡(luò)上的熱點(diǎn)話題,并在交流“王者榮耀”等網(wǎng)絡(luò)游戲中發(fā)現(xiàn)共同的愛好,一種“文化親昵”感由此產(chǎn)生。
最后,帕旭、芒石村民與漢族通婚的增加既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結(jié)果,也是進(jìn)一步促進(jìn)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原因。過去村民不同意與漢族結(jié)婚,主要原因是語言溝通問題。老一輩村民不會(huì)說普通話,只會(huì)講傣語,找了漢族的媳婦或女婿后,在日常生活中就難以溝通。除了語言不通,風(fēng)俗差異也增加了兩個(gè)民族間通婚的困難。后來村民們開始慢慢接受漢傣結(jié)婚,主要原因是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增多,使得彼此之間在語言、風(fēng)俗上的隔閡減弱。比如隨著義務(wù)教育的普及,村里上學(xué)的孩子越來越多。在學(xué)校里,不僅有傣族,還有漢族、苗族等等。在學(xué)校生活中不同民族的交往增進(jìn)了彼此的了解,民族間的通婚也成了自然而然的結(jié)果。在最近幾年,網(wǎng)絡(luò)的迅速普及更進(jìn)一步推動(dòng)了這一變化。無論是微信還是抖音,都極大程度了豐富了當(dāng)?shù)厝说囊娮R(shí),讓他們接觸到了更多與本民族不一樣的東西。所有這些變化使得漢傣之間的通婚障礙減少,反過來通婚的增加也進(jìn)一步增強(qiáng)了民族之間的相互了解。
總而言之,在以上幾個(gè)原因影響下,帕旭、芒石寨的村民已經(jīng)深度融入了外部世界,融入了中華民族的“一體”格局之中。人們與外界在經(jīng)濟(jì)聯(lián)系上更為緊密,在信息交流上更為頻繁,在消費(fèi)娛樂上也逐漸同步。然而,在融入“一體”的基本格局之下,我們發(fā)現(xiàn)帕旭、芒石寨的村民對(duì)村寨的認(rèn)同,對(duì)民族文化的認(rèn)同并沒有下降,而是呈現(xiàn)了一種新面貌,也即出現(xiàn)了上文所謂的“文化鐘擺”現(xiàn)象。
四、文化的“反嵌”與“發(fā)明”
在此處,所謂的“文化鐘擺”是指小群體文化在日漸融入更大的共同體之后,出現(xiàn)的一種反方向的對(duì)本群體文化的強(qiáng)調(diào)或認(rèn)同。小群體生活融入更大的共同體是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通信技術(shù)、交通運(yùn)輸、大眾文化等因素影響的結(jié)果,上文所描述的帕旭、芒石寨的文化變遷就是鮮活的例子。與這一大潮流相反的對(duì)本群體文化的強(qiáng)調(diào)則是在這一大趨勢(shì)之下,小群體文化的一種重新“發(fā)明”或“復(fù)興”,但并不意味著回到一種與外界孤立的封閉狀態(tài),而是可以看作一種與外界互動(dòng)的新姿態(tài)。
通過對(duì)帕旭、芒石寨的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這種文化的反方向回歸可以分為兩種形式,其一可以稱之為文化的“反嵌”,其二可以稱之為文化的“發(fā)明”。“脫嵌”與“嵌入”等概念因?yàn)椴ㄌm尼(Karl Polanyi)、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人的使用而變得廣為人知。這里采用文化的“反嵌”主要是指小群體的成員在融入更大的社會(huì)生活之中時(shí),因面臨的外部世界風(fēng)險(xiǎn)增加,而返回傳統(tǒng)文化資源尋求幫助的現(xiàn)象。前文所提到的河北村莊的“守樹”現(xiàn)象就是如此。“發(fā)明”這一概念則因?yàn)榛舨妓辊U姆(Eric Hobsbawm)主編的《傳統(tǒng)的發(fā)明》而廣為人知,此處這一概念的使用與霍布斯鮑姆的含義基本一致。
帕旭、芒石寨存在著較為明顯的文化“反嵌”現(xiàn)象,其中重要的體現(xiàn)是在面對(duì)外部風(fēng)險(xiǎn)過程中,人們對(duì)村寨傳統(tǒng)社會(huì)關(guān)系與文化資源又開始重視起來。帕旭、芒石寨村民的生活中,村寨一直占據(jù)著顯赫地位。在長(zhǎng)期歷史生活中,村寨是抵御外部社會(huì)風(fēng)險(xiǎn)與自然災(zāi)害的重要單位,是各種公共活動(dòng)的重要組織載體,同時(shí)村寨也構(gòu)成了人們社會(huì)交往的重要邊界。與村寨在人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相對(duì)應(yīng)的是圍繞著村寨的一系列信仰與儀式活動(dòng)。村寨是一種抽象組織,人們需要一種具體的形象來表達(dá)對(duì)村寨的依賴。在帕旭、芒石寨,社林與寨心亭就構(gòu)成了這一具體形象。社林中的社神是村寨的人格化形象,村民們出遠(yuǎn)門都要先祭拜社林,從外地返回村寨也要先向社神“報(bào)道”。寨心亭則是空間意義上的村寨中心,圍繞著寨心亭也有一系列的祭祀活動(dòng),強(qiáng)化著人們的村寨認(rèn)同。
隨著社會(huì)生活的現(xiàn)代化,村寨已經(jīng)很大程度失去了防御外敵入侵、應(yīng)對(duì)自然災(zāi)害等傳統(tǒng)風(fēng)險(xiǎn)的作用,但是在應(yīng)對(duì)新的社會(huì)風(fēng)險(xiǎn)方面,卻發(fā)揮了新的作用。最典型的體現(xiàn)是年輕人在外出務(wù)工時(shí),面對(duì)社會(huì)支持較弱的外部世界,會(huì)尋求村寨傳統(tǒng)社會(huì)關(guān)系的支持。在外出務(wù)工過程中,同一個(gè)村寨的人往往結(jié)伴而行以“抱團(tuán)取暖”。同時(shí),年輕人在外出務(wù)工幾年之后,往往最終會(huì)返回村寨生活。根據(jù)調(diào)查過程中的統(tǒng)計(jì),村中50歲以下的人口中有打工經(jīng)歷的共計(jì)78人,實(shí)際上只有17人仍在外務(wù)工,大部分人結(jié)婚后選擇回家務(wù)農(nóng)。年輕人往往完成初中學(xué)業(yè)之后就不再繼續(xù)學(xué)習(xí),懷著對(duì)外面世界的向往外出務(wù)工。在外面生活一段時(shí)間之后,大部分年輕人發(fā)現(xiàn)還是留在村寨熟悉的環(huán)境中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更為穩(wěn)定。實(shí)際上,打工收入相對(duì)在家務(wù)農(nóng)收入要稍高,但是在熟悉的村寨中生活人們可以獲得更多的社會(huì)支持,傳統(tǒng)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了更為穩(wěn)定的基礎(chǔ)。
傳統(tǒng)的村寨組織不僅為個(gè)體所面臨的新社會(huì)風(fēng)險(xiǎn)提供幫助,也為村寨整體層面面臨的風(fēng)險(xiǎn)提供了一種解決之道。在調(diào)查過程中,帕旭、芒石寨分別舉行了一場(chǎng)“送禍”儀式。“送禍”儀式是一種凈化村寨的儀式,在儀式過程中,人們制作一個(gè)大竹筐,被稱作“邦禍”。“邦禍”內(nèi)放置著貢品,每家都用舊衣服的布料裹在傣香或夾竹桃葉子上做成一個(gè)物件放入其中,象征著帶走家中的污穢。在請(qǐng)佛爺念過一番經(jīng)書之后,人們將“邦禍”抬到村寨邊界之外,象征著將村寨中的污穢之物清除出去。據(jù)說“送禍”儀式已經(jīng)幾十年沒有舉行了,之所以要舉行這次“送禍”儀式,是因?yàn)樽罱逭钤庥隽艘恍┎恍摇1热绱逭i瘟流行給村民造成了很大損失,蔬菜市場(chǎng)不景氣使得村民收入下降,以及幾個(gè)月之前村寨中發(fā)生的一次車禍一下帶走了三個(gè)小伙子的生命。凡此種種,使得村民們認(rèn)為村寨中可能有一些污穢之物給人們帶來不幸,于是又想起了這一古老的儀式,祈求能給村寨帶來平安。
除了文化的“反嵌”,文化的“發(fā)明”構(gòu)成了文化“鐘擺”的另外一種形式,這方面最為明顯的例子是帕旭、芒石寨近幾年建筑風(fēng)貌的轉(zhuǎn)變。帕旭、芒石寨傳統(tǒng)建筑為土木結(jié)構(gòu),裝飾比較簡(jiǎn)單,并沒有體現(xiàn)出“濃郁的民族風(fēng)情”。然而,在近幾年新修的磚混結(jié)構(gòu)房屋上,都被裝飾了具有傣族特色的精美屋檐和屋頂。這種對(duì)傣族民族特色的強(qiáng)調(diào)有著其時(shí)代背景。隨著旅游業(yè)的逐漸繁榮以及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的推行,民族鄉(xiāng)村地區(qū)通過旅游實(shí)現(xiàn)鄉(xiāng)村振興成為一條重要途徑。強(qiáng)調(diào)民族特色,“發(fā)明”更多的民族文化元素就成了吸引游客,發(fā)展旅游經(jīng)濟(jì)的一種手段。這種對(duì)傳統(tǒng)元素的強(qiáng)調(diào)并非是對(duì)傳統(tǒng)封閉狀態(tài)的回歸,而是試圖通過強(qiáng)調(diào)自己的特色獲得外部世界的認(rèn)可,故而是一種與外部世界互動(dòng)的新方式。
這種對(duì)民族特色文化元素的強(qiáng)調(diào)不僅僅體現(xiàn)在村寨的集體面貌改造中,也體現(xiàn)在了村民個(gè)體的生活中。每當(dāng)村寨中舉行各種傳統(tǒng)的節(jié)日或集會(huì),村民們都會(huì)紛紛拿手機(jī)拍照,并在微信朋友圈或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臺(tái)展示。村民知曉在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tái)上,凸顯自己生活中的民族風(fēng)情會(huì)受到更多關(guān)注。強(qiáng)調(diào)民族的特色,就可以獲得更多的“流量”,這種模糊的“實(shí)踐意識(shí)”是村民在與外界的互動(dòng)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在田野調(diào)查期間,帕旭、芒石寨的村民舉行了一次“采花節(jié)”,村中的男男女女上山采摘鮮花以用于供奉佛祖。在“采花節(jié)”當(dāng)天,村寨中聚滿了外來的攝影愛好者,他們對(duì)“采花節(jié)”充滿了濃厚的興趣,全程拍攝記錄著活動(dòng)過程。村民們?cè)谶@樣的場(chǎng)景中也逐漸意識(shí)到了外界的興趣之所在,從而更積極地展現(xiàn)著自己的民族特色。
可以看出,日漸融入外部世界的同時(shí),帕旭、芒石兩個(gè)村寨文化的“反嵌”與“發(fā)明”使得民族文化又獲得了新意義。外出務(wù)工面臨的社會(huì)風(fēng)險(xiǎn),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帶來的收入波動(dòng),人流物流的頻繁帶來的豬瘟傳播,以及現(xiàn)代交通工具產(chǎn)生的車禍,這些都不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災(zāi)禍。然而,傳統(tǒng)的村寨社會(huì)紐帶與信仰觀念在應(yīng)對(duì)這些風(fēng)險(xiǎn)過程中,仍舊發(fā)揮著作用。這種文化的“反嵌”是對(duì)傳統(tǒng)的重新發(fā)現(xiàn),而文化的“發(fā)明”則意味著一種新的創(chuàng)造和轉(zhuǎn)化。在這種“發(fā)明”的過程中,帕旭、芒石寨的群眾更加強(qiáng)調(diào)自己的民族特色,以在與外界的交往中獲得某種新的認(rèn)同感。
五、討論
這兩個(gè)傣族村寨發(fā)生的文化變遷很大程度上是有普遍意義的,通過這個(gè)案例我們可以回到費(fèi)孝通對(duì)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園圃”比喻。正如帕旭、芒石寨的變化所表明的,在當(dāng)下社會(huì)環(huán)境中,“一體”基礎(chǔ)正在變得越來越牢固。在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信息傳播、族際通婚等因素影響下,當(dāng)?shù)卮鲎迦罕姷纳钆c外界產(chǎn)生了更為緊密的聯(lián)系。相信這一過程不僅僅在帕旭、芒石寨的傣族群眾身上發(fā)生,在其他民族群眾的生活中也發(fā)生著這一變化。各民族之間隨著聯(lián)系的日漸緊密,必將在文化上產(chǎn)生更多共性,建立更多的“文化親昵”感,從而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建立更牢固的基礎(chǔ)。
另一方面,在各民族共性增加的基礎(chǔ)上,民族文化特色在人們的生活中獲得了新含義。為了應(yīng)對(duì)新的社會(huì)風(fēng)險(xiǎn),以及在與外界的交往中展現(xiàn)出某種新姿態(tài),帕旭、芒石寨的村民又返回傳統(tǒng)文化資源尋求幫助,并對(duì)其進(jìn)行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然而,這種對(duì)傳統(tǒng)文化資源的強(qiáng)調(diào)不是返回過去的封閉和隔閡,而是在牢固“一體”基礎(chǔ)之上的“多元”綻放,并不會(huì)破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發(fā)展,反而會(huì)增進(jìn)各民族的相互欣賞和了解,讓各民族群眾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獲得更高的存在感。
在這種民族文化“鐘擺”運(yùn)動(dòng)中,“多元”與“一體”之間的關(guān)系正在發(fā)生微妙變化。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fā)展面臨的一個(gè)重要問題是如何讓“多元”之間的聯(lián)系更為緊密,從而為“一體”建立更為牢固的根基,費(fèi)先生“多元一體”的論述也有這方面的考慮。隨著各民族交融日益加深,我們現(xiàn)在似乎已經(jīng)到了一個(gè)臨界點(diǎn),即“一體”的社會(huì)基礎(chǔ)日漸牢固,我們對(duì)“一體”的信心也日益增強(qiáng)。在此基礎(chǔ)上“多元”的綻放則是“在一體不變的總格局之下族群與社會(huì)多元分化成長(zhǎng)的滋生過程”。牢固的“一體”基礎(chǔ)與繽紛的“多元”綻放并存,如此費(fèi)孝通的“園圃”比喻就從愿景變成了現(xiàn)實(shí)。
參考文獻(xiàn):
[1]費(fèi)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J].北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1989(4):3-21.
[2]格爾茲.文化的解釋[M].韓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
[3]胡塞爾.純粹現(xiàn)象學(xué)通論[M].李幼蒸,譯.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4.
[4]舒茨.社會(huì)世界的意義構(gòu)成[M].游淙祺,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7.
[5]泰勒.原始文化[M].蔡江濃,編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6]赫茲菲爾德.文化親昵[M].納日碧力戈,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
[7]張文瀟,趙旭東.鐘擺現(xiàn)象中的循環(huán)與融合:由栗樹糾紛看中國(guó)鄉(xiāng)村社會(huì)轉(zhuǎn)型[J].中國(guó)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0,37(4):31-40.
[8]張文.地域偏見和族群歧視:中國(guó)古代瘴氣與瘴病的文化學(xué)解讀[J].民族研究,2005(3):68-77.
[9]黃宗智.中國(guó)的隱性農(nóng)業(yè)革命[J].中國(guó)鄉(xiāng)村研究,2010(2):1-10.
[10]波蘭尼.巨變:當(dāng)代政治與經(jīng)濟(jì)的起源[M].黃樹民,譯.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3.
[11]格蘭諾維特.鑲嵌:社會(huì)網(wǎng)與經(jīng)濟(jì)行動(dòng)[M].羅家德,譯.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5.
[12]吉登斯.現(xiàn)代性的后果[M].田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
[13]霍布斯鮑姆,蘭杰.傳統(tǒng)的發(fā)明[M].顧杭,龐冠群,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20.
[14]布迪厄,華康德.實(shí)踐與反思[M].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15]趙旭東.一體多元的族群關(guān)系論要:基于費(fèi)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構(gòu)想的再思考[J].社會(huì)科學(xué),2012(4):51-62.
(責(zé)任編輯:王勤美)
Cultural “Pendulum” and the Metaphor of “Garden” of the Chinese Nation
FU Laiyou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China,400715)
Abstract:The investigation of Dai ethnic villages in Yunnan Province found out the “pendulum” phenomenon represented in the local cultural change.Though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arket economy,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inter-ethnic marriage and other factors,people are increasingly involved in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people also started to emphasize ethnic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a new sense.This change indicates a subtle chang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versity” and “integration” in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With the deepening of association,communication and blending among all ethnic groups,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integration” is increasingly consolidated,while “diversity” is getting a new form.The blooming of “diversity” will not damage the foundation of “integration”,but strengthen it at a higher level.
Key words:diverse integration; cultural change;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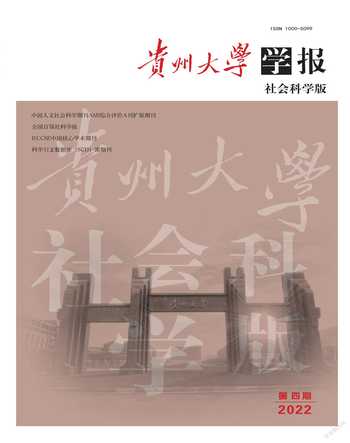 貴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2年4期
貴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2年4期
- 貴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國(guó)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一項(xiàng)基礎(chǔ)性工程
- 增進(jìn)共同性: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學(xué)理
- 洞見與偏見:美國(guó)輿論關(guān)于“五四”反日運(yùn)動(dòng)的認(rèn)知
- 檢察消費(fèi)民事公益訴訟的實(shí)踐考察與理論反思
——基于貴州省(2017-2021)司法實(shí)踐的分析 - 環(huán)境公益訴訟中的行民交叉問題研究
——以行政附帶民事訴訟“參照”適用為中心 - 從算法黑箱到算法透明:政府算法治理的轉(zhuǎn)軌邏輯與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