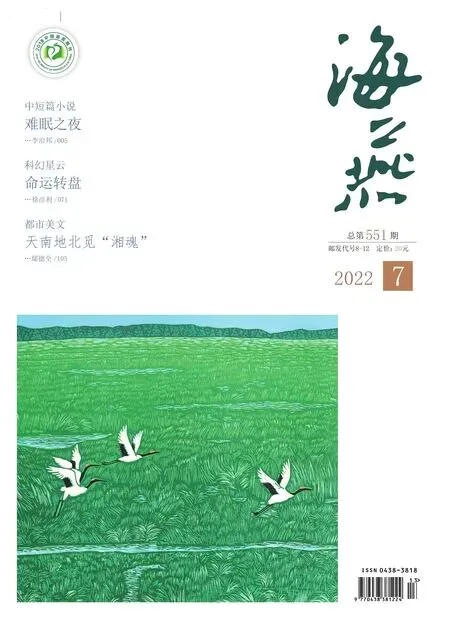退成一座島嶼
文 王冠一

世無好茶
有人愛茶,有人則無感。剛認識韓先生的時候,邀他來家中做客,不想傍晚,風雨琳瑯。我拿出最后一泡“牛肉”存貨,好巖茶跟壞天氣,仿佛富家女與街頭痞子的愛情,有種毫無道理的匹配感。當然,亮出牛欄坑肉桂,也有在他面前炫耀的意思。牛肉金貴,加之閑談間我扯出每年跑去天心村收茶的經歷,為茶加持,更顯這一盞茶滋味非凡。
沏茶前差點沒沐浴更衣,以示鄭重。我擼起袖子,一招一式地忙活起來,他看得倒認真,接過茶盞,沒等他喝完,我便問,這茶好不好?
他笑笑,答:比中藥好一點,卻不如白開水甜。
這可是牛肉,很貴的,我親自看著做的……如果當時有彈幕,我大概要打上這些吐槽,并義憤填膺。
送他上車后,雨已經停了,風鼓著潮濕的空氣直往衣縫里鉆,落紅一片。我坐在長椅上,許久,琢磨著韓先生評茶的話。是一句實在話,實在話最能戳破屏障,使人望見遠山。我之于茶,因為愛,所以情深。對他人而言,不過飲品,牛肉也好,虎肉也罷,或許真沒白水來得暢快。

好茶的概念經不起推敲。或者說世間本沒有絕好的茶,人不同,人站的立場不同,人的口味亦不同。白水為什么不能是好味呢?好茶,由人厘定。世間的絕好之處,亦在于每個人皆能自由選擇。選擇不分好壞,選擇只關乎個體意愿。
我們習慣于把一些事物變成生命的自負。那次小聚,似當頭棒喝,給了我一番開示。就拿喝茶這件事來說,愛茶者往往將不喝茶的人排除在階層之外,常喝圈子里公認“好茶”的,又剪掉其他“不入流”茶客。
很多時候,茶不再是草木的藝術。它更像一則廣告,所謂茶人,在階層、圈子、流派中各懷鬼胎。那算不得喝茶。
我一度困于此結界,竟然被“門外漢”點醒。那句“比中藥好一點,卻不如白開水甜”乃我之偈語,比阿彌陀佛還要實惠呢。尊重每個人對茶的選擇和情感,不把茶事淪為一場精致的平庸,才好關起門來,獨自抑或二三摯友,在清茗流轉間,恣意歡喜。
后來,韓先生經常做客我家,我也換著茶給他喝,卻打消了洗腦模式。我只管泡,不言茶;他只管喝,不問茶,仿佛成就了另一種高山流水。微黃燈光,兩個人對茶而坐,聊中醫,聊北京哪里好吃,聊香山的桃花。
趕上落雨,他便掏出陶笛,即興吹奏一曲。那嗚咽綿細的音符,把房檐與未露面的月亮也變成笛聲,蕩向歲月里。歲月有了遠意。
可人到底是追尋意義的物種,人生亦由無數意義壘疊完成。那么,盞中一捧茶,它的意義究竟在哪里呢?
靜水流深
從某種維度講,我完全可歸為“茶香世家”行列。打小看著爸媽喝茶——喝“勞保茶”長大的……實錘“茶根世家”了。估計那白瓷缸勞保茶的底子過分濃烈,慫恿我后來鐘情于茶,且一往而深。
二十青春,是看燕子歸來也要落淚的年紀。那時讀須蘭小說《銀杏,銀杏》,有句“茶已涼了”著實驚艷,大約它激活了沉于生命角落的濃烈情愫。我不瘋魔不成活,迅速置辦齊整喝茶的家伙,品嘗父親來路不明的茶們。
那會兒,我常去一位忘年朋友店里蹭茶吃。素秋季節,風戲弄路邊梧桐,梧桐枝丫前仰后合,飛起漫天昏黃。他的茶店就在梧桐深處,粉墻黛瓦,是特地從皖南請的匠人修葺建成,好不風雅。
我想,若非它隱匿了起來,在這座北方城市,如評彈般溫軟的茶店會害羞吧。
我坐在圈椅上,身體稍微前傾,直勾勾盯著小巧玲瓏的紫砂。陶壺里燒著水,水開了,他將壺放于金絲楠大案上,之后停下所有動作。我不解,以為有什么事要宣布,挑著眉毛問道:咋啦,怎么不倒水呢?
他說,等水靜。他是一個很有做派的老人家。我把“做派”解釋為,不做作的講究。生活中到底需要一點講究,讓紅塵滿衣的我們不那么將就。
跟他一起等水靜,我竟聽到壺內水泡爭相破裂,繼而波搖蕩漾又漸漸平穩安寧地起伏。起伏定了,他才緩緩提壺,注水。
陳年白茶的香,在紫砂里打幾個滾沖將出來,我忽然涌起莫名的感動。是從那時起,我漸漸摸到了一點茶的門楣。茶自然具有飲牛飲騾的功能,也解人之渴,但它還要我們懂得“品”。
品茶,被世世代代文人墨客渲染,早跟華夏文明諸多哲學符號聯袂,匯流成浩瀚而精深的文化長河。古今多少人,在這條河流上,尋到自己的一葉扁舟。有的畢生泛舟水波之間,有的登了岸。
于我的體驗,品茶是一個過程,從啟開茶葉罐,“品”的意義已經上線。現實中我不太理解復辟繁縟禮節的華麗茶會,但抱以善意和觀望。我比較偏愛簡單清爽的小飲。天下茶被天下人喝,茶是很包容的,很隨便的。很不計較的。
什么人喝茶,茶就是什么。水開了,我把陶壺放到一邊。等著,等靜水流深,沏出的茶分外平穩。抱歉,這個環節不必科學前來指手畫腳。品茶的標準是沒有標準。
沒有標準的事情,全憑心境,和成全心境的信仰。
一直以來,我總不肯輕信外部世界,世事無常,變數如影隨形,所以只能在心里打造天堂。這是我的小信仰。而品茶成全了我的小信仰,我也賦予了它意義。
與其說忘年友人教會我品茶的過程,毋寧說我從他那兒接過一支拐杖,讓我于無垠的時空中行走,腳步和心都穩當。
品茶,安的是心。心安了,茶有滋味。老套的雞湯話,是我真實感受。
如今,我已不是溫潤如玉的少年郎,那位老友也拋棄了人間。茶店改頭換面,不復從前。可我每每經過,總下意識地停上一停,想起他。一個人,是否只以肉身的存在而定義為存在?我承認因果,卻對來世存疑。興許,一個人在另一個人的生命中留下過記憶,被念著,這個人就不曾真的消逝。
再往后,我也轉身離開了北方的家鄉,來到一座大城——北京。
天涯道路
臨登機前,我還在讀齊邦媛的《巨流河》,把情緒放進已過的洪荒風浪里,權當沉浸式緩釋。不然無法說服自己為什么要拖著三十多歲高齡擠入北漂大軍,跟95后爭食吃。為什么呢?促發動因有無數個,正當理由亦很多,但果真邁了出去,忐忑盡裝在左右兩邊碩大無比的箱子之中。
左邊的箱子,塞滿了書和茶、茶器。非必需品,之于背井離鄉的人,成為心靈上的必需品。這讓我想起古人行囊里要裝一把故鄉的土,誠然有治療功效,但精神的意義大于實際療效吧。
于北京的第一年,我施行“限茶令”。因為餓。
這個年代外出打工能餓著自己?沒錯。造成困頓的原因,全怪我選擇不打工。
我當時想法執拗,在家鄉給單位打工,好不容易出來,為什么要做同樣事!難道只為從海濱轉移到首都嗎?既然打破了舊世界,不如徹底粉碎它。
小小房間,兩扇不大的窗。窗外蟬鳴紛紛,原來北京的蟬蟲跟家鄉叫聲不同。我坐禪般整日不出屋,窗外另一棟相似的老式居民樓是唯一風景。北京夏日的黃昏,像歸寧的小媳婦,羞著眼,紅著臉。每至黃昏,我最饞茶。
那是孤獨在召喚。孤獨這個詞充滿游俠氣及與宿命過招的力度,不至于熱愛孤獨,可人得先承認了孤獨,方能遠走他鄉。而這份孤獨在油水不多的現實條件中暫時妥協,喝茶促進消化,很快會餓。奈何銀行卡余額日趨萎縮,房東又鐵面無私,房租仍需按時交付,我只好把錢省在吃穿用度上。
一小碗粥一點青菜便是一天的伙食。有次去超市,聞見燒雞香味,不自覺地聚過去,繞著柜臺走了好幾圈,最終也沒舍得買……其實家里經濟不至我如此,可堂堂男兒,雄心壯志地出來了,不想父母援助。
他們甚至不清楚兒子忍饑挨餓。哪里來的倔強,我現在想想也可笑。
北京的夜晚太長了,我思來想去,還是撬出幾塊陳年普洱,投入汝窯壺內。那把從寶島臺灣買來的壺,賣價也夠幾頓美餐。當初真是鮮衣怒馬,驕奢得可以,我不禁連連后悔,若把錢攢下來該多好。
外在的雪月風花,難免須支付物質成本。靈魂清雅,不需要后臺。
很早接觸普洱,起先遇到貴人王先生,肯帶我從低年份茶一路喝至高年份,遂對普洱有了系統認知,而后秦先生把我拽進老茶疆域,即便這疆域深廣,毀譽摻雜,但普洱如情人,還是老的好。清代,乃消耗普洱之大時代。《紅樓夢》中賈寶玉過生日吃了面怕停住食,林之孝家的就建議:該沏些個普洱茶吃。
我推測那時的普洱,應幾乎都不“新鮮”。畢竟交通阻隔,山路迢迢自云南進貢而來,不老也難。
天空略深一度,呈墨藍顏色。我沒開燈,微光和大面積的影鋪陳于茶器之上,我意外獲得陰翳侘寂的美好。沏罷茶,茶湯似乎承襲了夕陽,透著沉醉的紅。嘗一口,被時光打磨過的茶,味道并不模糊,相反更清晰。只是那味道淘氣,與人捉起迷藏。它隱于悠悠年歲背后,要人尋覓。
喝普洱,樂趣在尋覓它隱藏的滋味。
痛追少年樂,不許俗人知。找著找著,就找回了自己。倘若你問我,在北京這些年得到了什么?名利嗎?見識嗎?一段一段悲欣交集的閱歷嗎?
是,也不是。
我從不否認,選擇來到大城市,真實目的是為了賺錢博名。但京城四時風物,壓根沒燃起我熱淚盈眶的奮斗史。卻見天高地厚,掂量出了自己的斤兩。我那些不切實際的欲望剝落,胸口的火焰弱了,慢慢退成一座島嶼,堅硬,坦然平淡也不失希望。從此茶的意義也變了。
之前它是拐杖,在跌跌撞撞的日子里,我仰賴它撐住不著邊際的心。社會分秒變革,思想觀念、技術網絡、新聞舊聞……像西洋鏡,輪番變換。一介凡人,又怎抵得住多變的大環境。茶,草胎木心,雖不堪遮風擋寒,亦不能阻止我不停摔倒,但它至少使我擁有足以爬起身,抖抖灰塵,繼續行走天涯的支點。
向自身缺陷投誠,接受不能抵達的山峰和不完美的人生,所謂支點便光榮退役了。茶回歸于茶,現在它只是我每天的私情。補充一句,這般豪橫地吃茶,表明溫飽問題得以解決。何止,昨日低頭,驚見微微隆起的小肚腩,它賣萌似的上顫下抖,頓時容貌焦慮,默默下單一張瑜伽墊。
大雪春色
人有嗜好,并不是什么壞事。也許嗜好,會拼湊成一個人最后的烏托邦。現實世界不具備美感,多令人疲倦。我們需要烏托邦,在其中唱支歌,或吃口茶。
將入夜,亂云低暮,不久便飛雪風中轉。這場大雪到底來了,雪片敲擊窗戶發出蝴蝶震動翅膀的聲響。我取出冰箱里“霄坑五隊”的茶,咦?這個時候不正該喝陳年普洱、武夷巖茶,實在沒有,祁門紅茶也是好的,它們溫經補氣抵抗苦寒,為什么選“綠茶”!
隆冬季節,綠茶自帶意想不到之高光。故而我的綠茶,專為過冬儲備。
捏一小撮茶投入蓋碗,也不拘究竟幾克,太嚴絲合縫,反倒失去了與味道不期而遇的怦然。蓋碗亦隨心,我常用的兩只,一只粉彩梅花圖樣的,手上這只甜白釉,據說制作師傅出自早年毛瓷廠,胎極薄,又樸拙,暗夜以手電照之,可透光。當水咕嘟咕嘟涌起無數魚眼水泡,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故意把壺擎得高一些,往蓋碗里澆水。瞬息春光。那綠茶芽頭隨水從碗底滾滾而上,綠意波濤水中搖,清香浮蕩,十分風流。茶湯翠色,入口生甜,鮮爽得剛剛好。這是谷雨前后,自九華山脈海拔八百米處采下的茶。
許南華《茶疏》寫著:清明太早,立夏太遲,谷雨前后,其時適中。喝茶不必緊攥古書不放,但許次紓先生的話與我心意相合。過早,茶的滋味略顯輕浮;太晚難免昏濁。恰到好處的徽風皖韻,最可愛。
佛家常言“心能轉物”,我看茶亦可。眼下即是憑一茶之力,破除時間與空間的執念。人間紛紛大雪,屋內片片春情。是多么神奇,又平常的法門。
大雪過后,春天又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