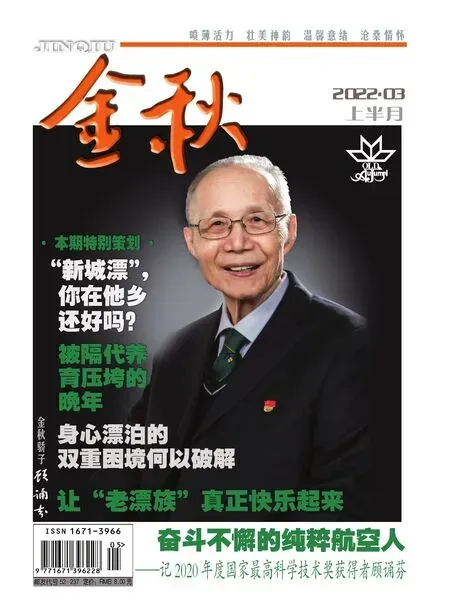漢江拉纖
※文/王凱利
1970年盛夏,被列為國家重點戰備工程的襄渝鐵路陜西段全面開工建設,我和西安市萬名69級初中畢業生一道奔赴施工一線。
我們乘車到達安康后,方知我們連的施工工地還遠在漢江上游。第二天早晨,我們連一百多人在安康縣城西的一座小碼頭登上了接送我們的一艘木制大帆船。開船后,只見3個船工幾乎赤裸著全身,一人在船尾掌舵搖櫓,另兩個各在船舷的一側,用長篙頂住江底,在船上一步一步艱難地推動著大船逆水而行。木船緩緩地行進在洶涌的江面上,我們則貪婪地欣賞著漢江兩岸的旖旎風光:青山滴翠,山花簇簇,還不時望見一條條瀑布從高崖上漂落而下。木船行駛到一個叫火石巖的地方,突然猛的一震停住了。這里兩岸荒蕪,不見人煙,漢江水在這里轉了個大彎兒,江面變寬,河水漸淺,水流湍急,形成了漢江上游的一個激流險灘。這時,扳船的艄公急切地大聲喊叫:“學生娃,下去拉船!快點兒!都下去拉船!”艄公邊喊邊把一卷竹皮編就的粗壯纖繩,用力甩到了岸上。
這時木船離岸還有四五米遠,船幫高有四五尺,船下是湍急的江水,同學們見狀個個面露難色,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該怎么下船。當時我是連里的3排排長,我覺得自己應該起個帶頭作用了,便噗通一聲跳到水里,江中濕滑的鵝卵石把我滑了個趔趄。緊接著,又噗通噗通地跳下來十三四個同學。我們在江灘上撿起粗糙的竹皮纖繩時,一個個顯得束手無策,因為我們誰都沒有拉過纖。船上的艄公卻不把我們當孩子看,依然大聲地催促著。情急之下,我們十幾個人只能學著像《伏爾加河上的纖夫》那樣,排成一隊,把粗糲的纖繩搭在了稚嫩的肩上。纖繩上每隔一段有一個環形的套,同學們也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只是個個肩搭纖繩,手挽環套,身體前傾,有了個拉纖的模樣。這時艄公收起鐵錨,威嚴地命令道:“拉!”我們十幾個同學一起用力,船終于緩緩起動了。
由于我們沒有經驗,不懂得喊號子,都是各拉各的,形不成合力,所以拉起船來特別費力。這時,又隱約聽到艄公在船上大聲喊話,可“嘩嘩”的江水聲淹沒了他的聲音。后來我們才知道,他是讓我們把纖繩上的環套挎在肩上拉。年少無知的我們只是拼了命地拉纖,個個臉掙得通紅。粗糲的纖繩幾乎勒進了肉里,刺的肩膀疼痛難忍。船到急彎處,艄公緊張地避讓礁石急流,不停地發出吼聲,但洶涌的江水死死地攔住了船頭,帆船像釘在了江心一樣,同學們拼命地拉著,誰也不敢有絲毫的松懈。大家知道,只要稍一松勁兒,船就會像斷了線的風箏,順水倒流,造成“溜船”。無舵的船一旦碰上礁石,就有船毀人亡的危險。豆大的汗珠模糊了我們的雙眼,順著臉頰一滴滴的跌落在江邊滾燙的沙石上,發出“滋滋”的響聲。大家強忍著肩上鉆心的疼痛,前傾的身體幾乎貼到了地面,口里喘著粗氣,一步一步艱難地向前掙扎。當時的情形,正如一首詩中描述的那樣:“一條長長的纖繩,把從心頭迸發的聲音勒出了血。那些沉重的腳步,踩碎了嶙峋的山巖。”
在難以忍受的煎熬中,我們個個咬緊牙關,一步步向前挪動,終于把大船拉過了“漫長”的急流險灘。當艄公把船定在了一個迴水彎上時,我們十幾個拉纖的同學,累的癱軟在了滾燙的沙灘上,大口大口地喘著粗氣。我仰面朝天躺在地上,遙望蒼穹,陜南8月熾烈的陽光刺得我睜不開眼睛。恍惚間,感到江對面高聳入云的巍巍山峰,似乎正向我傾來,使我感到了一種無形的壓力,它仿佛在向我們昭示著未來的艱辛與磨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