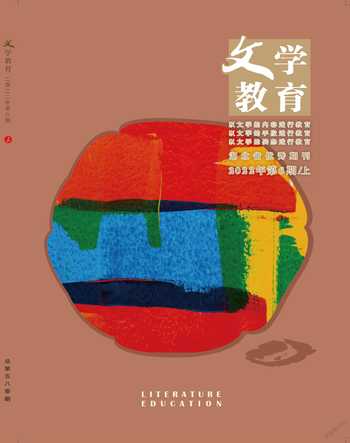寫詩帶來“隱秘的歡樂”

秦立彥是一位勤奮的詩人,因為她對詩人們所保有的“詩歌的能力”有著清醒的認知。她知曉大多數人作詩靠不了天賦,而主要是靠后天習得得來。近些年來,她對詩歌一直保持著一種孜孜以求的態度,也因此給人留下了“沉深好學,孳孳不倦”的印象。
秦立彥對詩歌有一種敬畏,同時也對詩歌充滿信心。一方面,她相信詩不會死,另一方面,她將詩歌作為自己“活著”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她認為,生活中如果沒有詩,就僅僅只是“活著”,人生的大部分都是如此。而有了詩則不同,“詩是平淡中的光”,所以異常珍貴。按常理而言,詩歌并不能給寫詩的人帶來什么“好處”,相反,還可能“有礙正常生活”。秦立彥根據寫作的經驗指出,之所以還有這么多的人寫詩,“也許因為詩有一種好處,是寫詩的人立即得到的。那是一種隱秘的歡樂。”(《隱秘的歡樂》,《詩刊(上半月)》2021年第8期)這種隱秘的歡樂深深地植根于詩人的寫作過程之中,起始的時候,你產生一種寫作的沖動;中間的過程里,你獲得一種自由的氣息和自我“掌控”的愉悅感;終了,面對一首嶄新的詩歌,面對這“不曾有之物”,你生出一種像上帝“創造世界”的感覺。秦立彥非常深刻地體味到了這一點。當然,出于“情動于中而形于言”的需要,詩歌也達成生命本身的訴求,秦立彥把它概括為“說出自己,留住生命”,在某種意義上,這已經是人類高層次的需要,類似于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的“自我實現”這一歸屬。不過,要真正達成這種“隱秘的歡樂”并不容易。它需要詩人有對詩歌理想的追求,有自己獨覺的發現,有對藝術經驗表達的高潮技能。
秦立彥對于詩歌品質的最高追求是“真”。她從中國古詩追求“情真意切”得到啟示,認為“‘真’是語言作為交流工具的基本要求,也是詩有別于小說、戲劇等虛構文類的最大特點。”(《我相信的詩》,《詩刊(下半月)》2017年第11期)這一的判斷無疑是正確的。無論是抒發情感,還是表達經驗,甚至是打開想象,如果失去了內心的誠與真,詩歌將毫無立足之地。詩歌與“虛構文學”不同,它從不借助虛構成為理解世界的方式。尤其是秦立彥把“詩的語言”當作是“天下之公器,不是詩人的自言自語”,這就把詩歌提升到一個很高的位置。為此,她重視詩歌的倫理,尤其是對古典詩學中的那些偉岸的存在,那些把詩的境界與人的境界合一了的大詩人,如陶淵明、杜甫、蘇軾,她認為他們是世界詩歌中“最獨特的存在”,“是最好的詩人,也是最好的人。”因為“他們的詩最終是對世界的肯定,是容納了矛盾與悲傷的動蕩的智慧。”(《隱秘的歡樂》)在秦立彥看來,詩人要看到這個世界“合理”的成分,要將個人的“動蕩”與人類的矛盾和悲傷形成共振,讓整個世界與自己一同顫抖。當然,這需要詩人通過對詩歌的創造來達成一種共情的力量,這種共情的力量能夠使他與人類成為一體,所謂“沉入自己”即“沉入人類”,“關進自己的房間”即“走入了眾人共有的廣大國土”。秦立彥將之形象地表述為“說出那共通之物”。詩人要有這樣對世界的貢獻,才能稱之為詩人。放眼寰宇,世界上的那些大詩人之所以能成為大詩人,無不是因為如此。退一萬步講,即使你的詩歌只是表達私人情感,提供私人經驗,與人交流,“真”也是基礎,因為你期望通過文字得到別人的理解與同情。秦立彥把這一點也表達得很形象,她說:“詩是對他人的渴望,是向他人伸出的手,是寫給他人的信。”并且指出,“詩人以為獨有的許多私人情感與思緒,其實很可能是人所共有。”(《我相信的詩》)為此,如果失去了真,交流也不復存在。
當然,現代詩的最大功用仍是最大限度、最大范圍地表達現代經驗。但由于“現代”是一個變動不居、常在常新的領域,它的很多“經驗”尚未被詩人發現。或者已經被發現,而尚未被表達;或者已經被表達,但沒有達成效果。因此,現代詩人的使命,一是發現經驗,二是對經驗進行有效的達成。這種有效性,一方面與現代詩的形式密切相關,同其他藝術建立的互文性質素(如音樂性、繪畫性、對話性等)也不無關系。但首要的任務,還是應該去發現,去創造,去抵達,一如秦立彥從古詩那里發現的可能性:“詩是自我的,同時也是公共的,是服務于人的。詩中所描述的經驗未必是完全私密的,詩的效果來自于言人所未言,此言未曾被他人道出。而說出眾人的情感,說出眾人想說而未說出的公共經驗,追求共鳴,抵達尚未有語言抵達之處。”(《“拿來”自己的傳統》,《詩刊(上半月)》2019年第3期)秦立彥的創作大都是朝著這些方向努力的。
趙目珍,青年詩人,批評家。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教育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