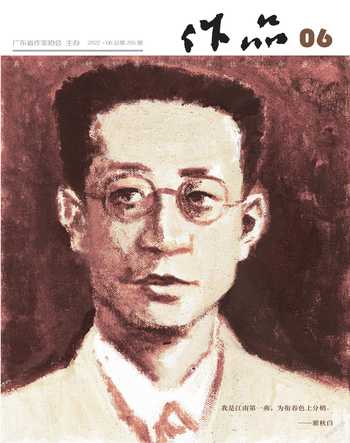韓愈與孟郊
彭玉平
所謂“韓孟”,就是韓愈與孟郊二人的并稱。在中國詩歌上有個“韓孟詩派”,韓愈與孟郊兩個人在唐代領頭形成了一個流派,這足以說明這兩人的影響有多大了。
韓愈(768-824年),字退之,自稱“郡望昌黎”,河南河陽(今孟州南)人。韓愈從小志向特別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欲自振于一代”(《舊唐書·韓愈傳》),可見他的不凡志向,要成為一個時代的引領者。他虛歲25(貞元八年,792年)的時候考中進士。韓愈的詩歌當然寫得不錯,但散文更有名,“唐宋八大家”,說的就是散文八家,韓愈名列第一。他的《師說》也收在中學語文課本里,非常有名,“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這已經成為名句了。
孟郊(751-814年),字東野,湖州武康(今德清)人。可能有人不大知道孟郊的名字,但他有一首詩歌,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就是這首《游子吟》:
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這首《游子吟》是孟郊擔任溧陽縣尉時寫的,把深厚的母愛和親情寫得非常傳神,順便也把一個江南小城“溧陽”的名氣帶了出來。
孟郊年長韓愈17歲,從年齡上說,他們其實是忘年交。因為兩人的詩歌在當時很有特色,所以才世稱“韓孟”。因為年齡的原因,孟郊詩歌出道早,并影響到韓愈;但韓愈后來居上,影響更大,而且一直在大力推崇孟郊的詩歌,所以他們首先是詩人與詩人的關系。
更直接地說,韓愈與孟郊其實是生死之交。
元和九年(814年),受山南西道節度使鄭馀慶奏薦,孟郊為興元軍參軍,他從洛陽往興元,八月間,他走到今天的河南靈寶縣,突然生病,而且沒幾天就去世了。我曾經想弄清楚孟郊到底生的是什么病,但一直沒有找到答案。孟郊妻子鄭氏第一時間就告訴了當時在長安的韓愈,韓愈聞訊大哭,走到張籍那里。張籍也是韓愈和孟郊的好朋友,三人關系就像鐵三角。韓愈與張籍坐在一起,說不出一句話,兩人就是號啕大哭,哭了很久很久。
韓愈知道孟郊家貧窮,第二天,就派人送了一筆錢,讓孟家準備孟郊的后事。長安與洛陽又有比較遠的距離,韓愈就在長安的家中專門設了孟郊的靈位,那些在長安與孟郊有過交往的人都來韓愈家憑吊。因為靈位設在韓愈家中,韓愈就像孟郊的至親一樣接受各方人士的哭吊。
那一年是閏八月,孟郊要在這個月下葬,孟郊的另外一個朋友樊宗師來韓愈家悼念,說起墓志銘的事情。樊宗師說:“孟先生一生與您最為知己,您也最了解孟公的為人。這篇墓志銘只有勞駕您了。我想孟先生冥冥之中應該也是期望您來寫的。”
韓愈邊哭邊說:“我哪里忍心來寫這篇墓志銘啊,我知道我一動筆,真是一字一傷心的!”
這個時候山南西道節度使鄭馀慶也來到韓愈家里,一起商量孟郊后事的細節。樊宗師再次催促說:“沒有您這篇情深意長的墓志銘,怎么能安慰大家對孟公的悲痛之情呢?”
話說到這個份上,韓愈當然也就不能再推辭了,很快就寫出了這篇《貞曜先生墓志銘》,這也是一篇對孟郊研究十分重要的文獻。
你看,孟郊去世,韓愈的家成為商量孟郊后事的中心。韓愈不僅出錢,而且撰寫墓志銘,更在家中專門為孟郊設立靈位。這都不是一般的朋友關系能做到的。
所以,我說韓愈與孟郊是生死之交。
這個生死之交是怎么形成的?我稍后再說。我要先說什么呢?韓愈與孟郊兩人交情深厚,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與韓愈對孟郊的極度崇拜有關系的。大家可能奇怪了,在文學史上,好像韓愈的地位遠在孟郊之上,怎么一個地位與成就高的人反而去崇拜一個不如自己的人呢?這個問題問得好,因為這樣的現象在中國古代雖然不能說非常普遍,但還真不是個別的。如大名鼎鼎的歐陽修就同樣欽佩并大力推薦梅堯臣的詩歌,但事實上,梅堯臣的地位遠不能與歐陽修相比。那么,這種看似“反常”的現象,背后究竟有著怎樣的原因呢?
說起來,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一個詩人的成長需要一個過程,而在他還沒有成長為一代名流之前,有些在我們現在看來名氣不怎樣的詩人,可能在當時已經聲名顯赫了。這樣的特殊“崇拜”,也就有了可能。
大概是貞元十四年(798年)某一天,地點是汴州,也就是現在的河南開封,天越來越昏暗了。但有三個人喝酒喝得正酣,空置的酒瓶在旁邊已經排成一排了。哪三個人呢?韓愈、孟郊、張籍,這三個人的關系就像鐵三角,關系好得就像一個人。三個詩人,酒喝多了,能干什么呢?當然是寫詩了。孟郊先寫了一首《與韓愈李翺張籍話別》,其中兩句真的不是深情之人不可能寫出的句子:“遠游起重恨,送人念先歸。”因為要去遠方,所以要跟好朋友離別了,引發了內心巨大的愁情。被送的人其實雖然行走在即,但他想的是怎樣早點回來與兄弟們相聚呢?你看,離別之惆悵,相聚之期待,就這樣直接連在了一起。人還沒走,感情已經被渲染得十分濃厚了。
其實那天喝酒喝得最多的還不是孟郊,而是韓愈。韓愈讀了孟郊的詩歌,對這位年長自己17歲的老大哥突然起了無限崇拜之心,揮筆寫下了這首《醉留東野》:
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
吾與東野生并世,如何復躡二子蹤。
東野不得官,白首稱龍鐘。
韓子稍奸黠,自慚青蒿倚長松。
低頭拜東野,愿得終始如弡蛩。
東野不回頭,有如寸莛撞巨鐘。
吾愿身為云,東野變為龍。
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何由逢。
我不知道韓愈在晚年地位崇高的時候,還愿不愿意寫這樣的詩,但當年30歲的韓愈,就是把自己內心最真實的對詩歌的傲氣和對孟郊的折服之心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我想這首詩雖然是醉后寫的,但想法應該是醉前就有的。
為什么說這首詩有逼人的傲氣呢?因為看開頭四句:“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并世,如何復躡二子蹤。”仔細想想,這幾句真是不得了,了不得。他說我以前因為讀了李白、杜甫的詩歌,總是遺憾我和孟郊沒有與他們生活在同一時代。那么我與孟郊怎么才能追蹤他們詩歌的步伐和境界呢?你看,韓愈就是把他與孟郊兩人比作是當代的李白與杜甫。這種傲氣厲害吧?而且在稱贊孟郊的同時,也直接把自己帶了進去。
從第五句開始一直到結束說什么呢?就是說對孟郊的各種崇拜,簡直是無條件的崇拜。
孟郊中了進士后,等了兩年也沒有得到官位,不僅深感郁郁不得志,連身體也感到年老體衰了。韓愈說,我比孟郊要狡猾一些,做了官,但在孟郊面前我就好像是地上的青蒿,而孟郊則是高大的松樹。我們兩人在一起,我真是又卑微又渺小,真是慚愧。你看韓愈這比方,硬是要把自己比下去才舒服。
“低頭拜東野,愿得終始如弡蛩”兩句,翻譯過來,情感也是濃得化不開的感覺了。韓愈說我因為崇拜孟郊,所以愿意像弡、蛩兩種小動物一樣,既形象相似,又形影不離。
“東野不回頭,有如寸莛撞巨鐘”,但孟郊傲氣啊,不過傲氣的孟郊讓我韓愈服的,像我這樣才疏學淺的人去向孟郊發問,就好像用一根短草去撞擊巨大的鐘,肯定是一點聲響也沒有的。你看,孟郊在當時的韓愈眼中,就是一種高大的存在。而自己呢?反而是一種可以忽略的存在。
最后韓愈說,我多么希望自己變成云,而孟郊變成龍,圍繞著龍,我這云四方上下追隨著他,龍與云雖然會有短暫的離別,但我們一定會有重逢的時候。因為云與龍一直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
如果大家不了解韓愈與孟郊當時的地位差異及一生關系,對韓愈用這樣極致的語言來贊美、推崇孟郊會覺得奇怪。
那孟郊對韓愈有怎樣總的評價呢?元和八年(813年),孟郊63歲了,當時他在洛陽,寫了《贈韓郎中愈二首》,其一:
何以定交契,贈君高山石。
何以保貞堅,贈君青松色。
韓愈30歲的時候寫詩直接說“低頭拜東野”,而63歲時的孟郊其實也是“低頭拜退之”的,說你韓愈好像就是高山之石,非常銳利,又好像是獨立之青松,如此堅貞挺拔。而這就是我們成為至交的原因。
像孟郊這樣性格孤僻的人,一般不大愿意直接表達對他人的感情,但你看他對韓愈,那是用語唯恐不盡,是要用一種極致的語言去表述他的感情的。
正是因為兩人互相有這樣的真心崇拜,才能將兩人的關系維持一生,并成為真正的生死之交。
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能稱為生死之交。那么,韓愈與孟郊的這種生死之交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我覺得與韓愈深刻地理解孟郊有關。
孟郊與韓愈最初其實是考友。貞元七年(791年),當年秋開科進士試,兩人都是考生。韓愈應該就與孟郊認識了,面對詩壇前輩孟郊,韓愈應該是非常恭敬的。第二年放榜,25歲的韓愈考中了,但42歲的孟郊卻落榜了。42歲還落榜,心情肯定不好,孟郊本來就是一個喜歡發牢騷的人,他不認為是自己的水平不夠,而是沒有貴人推薦,所以牢騷就更大了。你看他的《長安道》詩怎么說:“家家朱門開,得見不可入。”在長安街上,王公門第一座連著一座,但我孟郊一個也不認識,我進不去。唐代的科舉制度有“行卷”的風俗,也就是應舉者在考試前把自己所寫的優秀詩文寫成卷軸,投送給當時的權貴,如果得到賞識,并愿意積極推薦,那成功率就高了很多。但行卷也要有人推薦才行,不是你見誰家門開著,闖進去自薦就可以的。
但孟郊真是屬于一點人脈也沒有的人,他在長安街上轉了一圈又一圈,實在是沒有敲門的勇氣,所以失望中帶著憤懣。他不知不覺來到韓愈住處,韓愈見到前輩孟郊來了,當然大喜過望,趕緊請坐。看著孟郊略顯疲憊的面容,就問孟郊:“見您愁容滿面,不知有何心事?”
孟郊沉重地嘆了一口氣說:“我的心事你懂的,苦讀幾十年,但苦于無人推薦,京城權貴之家對我來說,都是高不可攀,看來希望通過科舉改變我的命運是沒可能了。”
韓愈走到孟郊身邊,剛想開口說話,但一時也覺得語言好蒼白,就說:“我還是寫首詩送給你吧!”韓愈果然寫了一首《長安交游者一首贈孟郊》詩送給孟郊。詩歌比較長,主要內容就是韓愈安慰孟郊,什么貧富、賢愚,都是相對的,你總放在心里,就總是擺脫不了,不如把它放下,所有的差別也就不存在了。
孟郊有沒有聽進去?這當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作為相識不久的朋友,韓愈奉上了真摯的情義。
貞元十二年(796年),46歲的孟郊在第三次參加進士考試后,終于一掃此前數十年的陰霾之氣,寫下了他平生的第一首快詩《登科后》:
昔日齷齪不足夸,今朝放蕩思無涯。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
一個長期有點抑郁的人能寫下這樣的詩歌,真是非常難得。以往黯淡無光的日子不去說了,今天終于揚眉吐氣,可以盡情綻放美麗的心情,盡情遐想美好的未來了。唐代一般是春天放榜,所以在春風里,我騎著馬,因為高興,馬也跟著高興,在一天之間把長安的花都看了個遍。孟郊其實有沒有真的騎馬奔馳在長安的街上,是不是去看長安各地的花卉,這其實都不重要,但孟郊的人生在46歲這年,終于像鮮花一樣開放了一回,這個才重要。他憋了那么多年,可以理解那種需要強烈釋放的沖天豪情。
但孟郊其實并沒有興奮多久,接下來居然是長達近四年的等待官職任命。貞元十六年(800年),孟郊已經50歲了,他先是居住在常州,當年冬天赴洛陽應“銓選”。什么叫“銓選”呢?在唐代,五品以上官員由皇帝直接任命,六品以下的文官一般由吏部——相當于我們現在的組織部任命,按照相關規定,凡是經過科舉考試的進士,先要經過審查資格,然后根據官職分布的情況,由吏部負責統一授予官職,這個制度稱為銓選。
那么,孟郊被授予什么官職呢?溧陽縣尉。“縣尉”就是負責地方的治安、司法方面的職位。溧陽是個小地方,縣尉是九品官職中的最低一品了。沒想到等了四年,就等到了一個墊底的官職,孟郊心里是失望的,他可是進士啊,再說也已經50高齡了。
孟郊不高興了,他不甘心,不想去,但也沒有辦法。在這個時候,誰是可以一訴衷腸的人呢?當然是韓愈了。孟郊洋洋灑灑地寫了一封信給韓愈,現在這封信雖然已經看不到了,但里面肯定是滿紙的牢騷。韓愈呢?我估計是收到信,很快復了信。
其實,孟郊在等候朝廷授官的時候,就經常給韓愈寫信,訴說自己內心的不平。韓愈有一封《與孟東野書》至今還在,這信寫得怎樣?你能想象朋友之情能有多深,韓愈的這封信就有多深。
信的開頭就說:“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于吾也。”文言文我們讀著感覺好像還不怎么強烈,我一翻譯過來,你就知道真正的友情是怎樣的了。韓愈說:我們已經很久很久沒相見了,從我怎么時時刻刻地想你,就知道你是怎么分分秒秒地想著我的。所謂“懸懸”,就是心好像總拎著,一刻也不停息的意思。翻譯過來,是不是情感很洶涌,很厲害?關鍵是韓愈對于孟郊與自己的友情,因為了解,所以自信。
這信寫得真是情真意切。韓愈繼續猛烈抒情:你不在,我說話誰聽呢?我寫詩誰來和呢?說話沒人聽,寫詩沒人和,世界那么大,但我怎么感覺好像舉目無親呢?您知道我內心肯定不快樂的啊。
讀了這樣的信,我們應該知道,這孟郊其實成了韓愈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依賴的一部分。換句話來說,他們雖然是兩個人,但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就像一個人。
其實,當時的韓愈也很狼狽,他剛剛從動亂不堪的汴州逃出來,去徐州找徐泗節度使張建封,所以也就暫時在徐州留了下來,當了張建封的幕僚。自己的人生也在動蕩不安中,但他更為孟郊的遭遇感到不平。他說:“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與孟東野書》)韓愈真是太懂孟郊了,他知道孟郊這個人辛勞艱苦,但在這個混濁的世界上,哪里能夠得到回報了。而孟郊的內心一心想追隨古人,事實上就形成了追心古人與混混濁世的矛盾,有沒有辦法解決這個矛盾呢?肯定沒有,所以,韓愈才感到一種透骨的悲涼,為孟郊悲,其實也是為自己悲。
所以在這封信的最后,韓愈希望孟郊來徐州聚聚,雖然路途有點遠,但交通還是暢通的,而且希望孟郊越早動身越好。韓愈很迫切地要見到孟郊。
這一次知道要出任溧陽縣尉,孟郊又給韓愈寫了信,韓愈回信一番安慰,才使得孟郊放下不滿,同意出任。孟郊大概在第二年春夏之間到達溧陽,同年迎養其母于溧陽,寫了那首著名的《游子吟》詩歌。
孟郊帶著情緒到溧陽,也把這個情緒帶到了工作中,有點消極怠工。溧陽是典型的江南水鄉,高高低低的丘陵與大大小小的湖泊河塘交錯其間。丘陵地區樹木蔥蘢,而山腳往往有湖泊,坐在那里發發呆,寫寫詩,絕對是很享受的。晚唐詩人陸龜蒙說:我小的時候在溧陽聽老人說,孟郊因為家窮,所以接受了溧陽縣尉的官職。唐代以前的溧陽叫平陵,在唐代溧陽縣城(今溧陽舊縣)南邊十二三里遠的地方有以前的平陵城故址,當年城墻的地基還在,大概有三四尺高,草木繁盛,有很多粗大的櫟樹,都是那種幾個人都合抱不過來的大樹,樹下幽靜,近處就是一些河面,應該是當初的護城河了。孟郊發現了這個好地方,三天兩頭騎著小驢過來,到了就在臨近水面的大櫟樹下面坐著,苦吟寫詩,一直到太陽西下的時候,才坐著小毛驢回城(參見陸龜蒙《書李賀小傳后》)。陸龜蒙的這一番話,可以得到《新唐書》的證明,《新唐書·孟郊傳》說“郊間往坐水旁,徘徊賦詩,而曹務多廢”(《新唐書·孟郊傳》)。所謂“曹務”就是官署分科掌管的事務,也就是把工作丟在了一邊。
這樣縣令就不高興了,你一個縣尉不履行職責,整天就是出游、寫詩,你自在了,工作怎么辦呢?孟郊也不管你高興不高興,詩人嘛,難免有點任性,他依舊是騎驢去平陵故城賞玩,有時運氣好,還能射殺幾只野鴨帶回城里打打牙祭。縣令沒辦法,就另外找個人來幫孟郊干事,當然把孟郊的一半工資給代理人。孟郊本來就窮,現在工資就剩一半,怎么辦呢?只有辭職了。正好一個任期也結束了。
除了尋幽探勝,臨水賦詩,孟郊在溧陽應該呆得總體不開心,與縣令的矛盾可能是關鍵,當然這個矛盾的根源與孟郊也有關系。說到底,是孟郊對這個小小的溧陽縣尉感到不滿意,所以工作不投入。
在溧陽的孟郊與在外地的韓愈,聯系一直沒有中斷,孟郊在溧陽的種種不快樂,也都通過信件和詩歌寄給了韓愈。韓愈當然關心這個老朋友的。大概是貞元十九年(803年),這一年冬韓愈被貶為連州陽山縣令。韓愈自己的人生雖然也處于低谷,但他收到了孟郊的信,最關心的還是孟郊的心情,他趕緊寫了一篇《送孟東野序》。在這篇文章的最后,韓愈特地說:“東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聽說孟郊在溧陽,好像很不開心,我呢就專門寫這篇文章開解他,告訴他一切都是天命,我們能做的就是怎么順應并且利用好天命而已,可見這篇序文也是專門慰問孟郊的。
他說這個世界很有意思,“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水、金石這些東西,平常都沒有什么聲音,但一旦有風或者有人擊打金石,就會發出聲音。這就是“不平則鳴”了。人也是這樣,那些名家經典著作,都是屬于“善鳴”者。唐詩的情況怎樣呢?李白、杜甫當然是一流的,而當下的詩人呢?韓愈認為孟郊就是一個“善鳴”的詩人。韓愈只是困惑,到底是讓這些詩人“鳴國家之盛”呢,還是詩人“自鳴其不幸”呢?問題當然是沉重的。這篇文章,我沒辦法在這里詳細給大家分析,但核心意思就是人生的磨難,也可以化為一筆財富,不僅對創作有益,而且對調整自己的心態很有作用。
你看,在孟郊每一個重要的人生關頭,幾乎都有韓愈的身影,這樣的朋友當然是貫穿一生的。
我剛才不是說韓愈在詩歌里說“低頭拜東野”嗎?孟郊不是在詩歌里說“何以定交契”嗎?到底是什么原因,讓這兩個詩人如此地將命運息息相關在一起呢?我覺得原因至少有以下三點:
第一,相似的貧困經歷,讓他們有同病相憐之感。
韓愈三歲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只能依靠哥哥嫂嫂生活。但不幸的是,在韓愈十歲的時候,哥哥在嶺南的貶所也去世了,韓愈就跟著嫂嫂,度過了一個十分艱難的童年和少年。但貧困的生活磨煉了他的意志,都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韓愈從小就特別能吃苦,努力讀書,根本不用人在后面督促。
孟郊呢?從小家境清貧,一路上也是苦讀過來,后來考進士,也是考了三次才考上,考上的時候已經46歲了。
兩個同樣經歷過貧困的人,在對生活的體驗和對人生的價值認同上,肯定容易取得共鳴。
第二,相似的性格特征,讓他們從對方身上看到真實的自己。
孟郊的性格如何呢?《新唐書》孟郊傳說他“性介,少諧合”,就是說性格耿介直率,用土話說就是認死理,一根筋,所以與周圍人很難相處。
那韓愈的性格究竟是怎么樣的呢?韓愈也同樣耿直,說話不轉彎,他在《潮州謝上表》中用兩個字形容自己的性格“狂直”,也就是狂妄而率直。我們都知道狂妄不是一種好的性格,其實,率直也經常會出問題。所以韓愈在官場上也是吃盡了苦頭。唐憲宗派人到鳳翔迎佛骨到宮中,連著供奉了三天,當時的王公士人都放下手頭的工作,紛紛來拜。這韓愈就看不下去了,就上書皇帝,說你一個帝王怎么能放下政事,這么過度地奉佛呢?然后就說歷史上誰誰誰奉佛,結果沒活多久就死掉了。憲宗一拿到這奏折,就拿給宰相看,說:“你看看,這樣說話,應該是死罪吧?”宰相和大臣大概都知道韓愈就這性格,就對皇帝說:“這韓愈說話有失分寸,確實應該受到嚴懲。但如果他內心不是對這個國家滿懷著忠誠,大概也不會語言這么急切,希望能稍微寬免一下他的罪行。”憲宗說:“他韓愈說我奉佛太過,我沒什么話好說,但居然說什么從東漢以后,凡是信佛的皇帝都短命,哪有一個臣子這樣說話的?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結果最后韓愈被貶為潮州刺史。所以韓愈其實一生中也因為這種狂直的性格吃盡了苦頭。
人以群分,物以類聚。韓愈與孟郊這兩個在別人看來性格有問題的人,但在他們彼此的眼中,卻是最好的知己。《舊唐書》孟郊傳怎么說他們?“(孟郊)性孤僻寡合,韓愈一見以為忘形之契”。也就是說孟郊這人性格孤僻,不合群,但這種性格正是韓愈喜歡的性格。貞元八年(792年),韓愈考中進士,孟郊落第,韓愈有《孟生》詩說孟郊“異質忌處群,孤芳難寄林”,說孟郊天性跟別人就不一樣,他是人群中的另類,樹林中的別枝,注定是很特別的。你看看,什么叫緣分?這就是緣分,在韓愈看來,孟郊的這種性格,那是最好的性格,也是最有魅力的性格,所以他一見孟郊就仿佛見到了另外一個自己。
第三,相似的審美追求,讓他們的詩歌形成了一種風尚。
韓愈推崇孟郊,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此前的大歷詩歌,風格偏于弱,是典型的軟體詩,但孟郊的詩歌呢,則是典型的硬體詩,清奇瘦硬,而且古樸。李肇的《唐國史補》說,在元和以后的詩歌“為文筆學奇詭于韓愈”“詩章則學矯激于孟郊”,所謂“元和體”的內容當然要更廣泛一些,但韓愈的文章和孟郊的詩歌一定是其中的主要內容了。他們代表了一個時代的風格。
孟郊的詩歌因為基本是寫“士不遇”的情懷,也就是不受重視、前路茫茫的感覺,再加上特別的窮困,所以他的詩歌“讀之每令人不歡”(《唐才子傳》),如“借車載家具,家具少于車”(《借車》),“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謝炭》)。前者說家里窮得空空蕩蕩,后者說天冷都凍得彎腰了,太陽曬了一會,身體暖一點,腰才能直立起來。這樣的詩歌讓有的讀者讀得不開心,但韓愈不這樣認為,韓愈《醉贈張秘書》,說“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對孟郊的詩歌的不同凡響和特殊韻味非常贊賞。
《新唐書》孟郊傳說“郊為詩有理致,最為愈所稱”,用了這個“最”字,可見他們惺惺相惜的情感。當時很多人對韓愈那么用力地稱道孟郊詩不能理解,韓愈越推薦,他們就越是譏笑孟郊的詩,所以韓愈對孟郊詩歌的推崇,在當時也確實帶來了一些反作用。但韓愈不可能管這個輿論的過度反應,他的詩歌其實跟孟郊的詩歌,在總體風格上,也是相似的,所以這才形成了所謂“韓孟詩派”。這說明他們兩人對詩歌共同的追求要多于各人獨特風格的追求。
相差17歲的兩個詩人,本來應該有代溝,有隔閡,但韓愈與孟郊因為有太多的生平、性格和詩歌的相似之處,讓他們在艱難的時代,相擁以取暖,在開心的時刻,拍手來稱快。世界再大,一個人能擁有的空間也很有限。在這樣有限的空間里,遇到投緣的人,無疑是人生的大幸福。我覺得無論韓愈與孟郊兩人詩歌地位誰高誰低,這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因為他們遇見了對方,而且一生相伴,為各自的人生帶來了巨大的幸福。這才是重要而珍貴的人生體驗。
責編:梁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