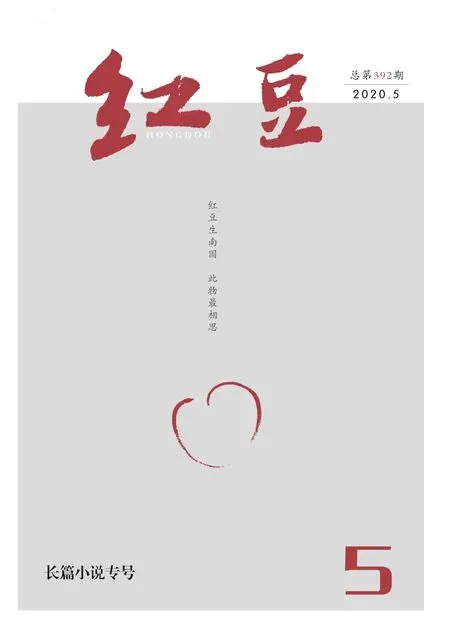珠市口
邱振剛
在北平很多市民的記憶里,二十世紀(jì)初丁丑年(1937年)的臘月是最冷的一個(gè)臘月。這一年,日本侵略軍打進(jìn)北平,占領(lǐng)了這座古都。
在這一年的五月廿九,也就是公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駐扎在豐臺(tái)的日軍進(jìn)行夜間軍事演習(xí),地點(diǎn)選在宛平縣城外的盧溝橋附近。
在這次演習(xí)中,日軍借口一個(gè)日本士兵失蹤,要求進(jìn)入宛平城搜查,被中國駐軍嚴(yán)詞拒絕,日軍開始籌備攻城。其實(shí)那天深夜,那個(gè)“失蹤”的士兵已自行歸隊(duì),但蓄謀已久的日軍仍然對(duì)宛平城發(fā)動(dòng)進(jìn)攻,隨后又從四面八方進(jìn)攻北平城。當(dāng)?shù)刂袊v軍奮起反抗,全民族抗戰(zhàn)由此爆發(fā)。
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國發(fā)出通電:“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shí)行抗戰(zhàn),才是我們的出路!”一場決定中華民族命運(yùn)的殊死大搏斗拉開帷幕。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蔣介石發(fā)表廬山講話。他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講,隨著電波傳遍了全國,但這并不能阻擋日軍的攻勢(shì)。
開戰(zhàn)后,日軍很快擊潰了北平守軍。一九三七年八月八日,日軍在永定門等處舉行入城式,大批日軍耀武揚(yáng)威進(jìn)入北平。
北平,這座千年古都,就此翻開了歷史上最恥辱最黑暗的一頁。但是在日軍鐵蹄的踐踏之下,仍然有許許多多人,為了黎明的到來,咬緊牙關(guān),昂起頭顱,奮力抗?fàn)帲I(xiàn)出了一切……
多災(zāi)多難的丁丑年終于過去了。除夕這天,除了極少數(shù)人家,因?yàn)榧依镉腥送犊苛巳毡厩致哉撸@得了種種好處,興高采烈地放起了鞭炮煙花之外,全城的老百姓都是沉默著度過了這一晚。這些響聲和煙火在漆黑的夜空中消散后,整座城市愈發(fā)顯得蒼涼沉寂。
除夕如此,年初一、年初二,直到年初五,都是如此。按照北方民俗“正月里頭都是年”,如果一切如常的話,到了年初六,城里應(yīng)該都是熱熱鬧鬧的年景。可如今到了這一天,城里僅有的一點(diǎn)過年味道,也無影無蹤了。
這天早上六點(diǎn),天還沒亮,日軍重兵把守的永定門,已經(jīng)有一雙雙馬靴重重踩踏臺(tái)階的磚石,登上了城樓。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個(gè)身材粗壯、挎著腰刀、身披軍用大氅的日軍軍官。在他身后是整整一個(gè)排的衛(wèi)兵。城樓下停著三輛轎車和兩輛軍用卡車,這幾輛車都沒有熄火,排氣管都在寒風(fēng)中噴著熱氣。八個(gè)日軍士兵端著步槍,排成整齊的圓圈,槍口朝外保衛(wèi)著這幾輛車。
偶爾有三兩個(gè)早起遛鳥的市民,一看這陣勢(shì),都提心吊膽地低下頭,快步遠(yuǎn)遠(yuǎn)繞開這里,仿佛看一眼這些兇神惡煞的侵略者,就會(huì)生一場大病似的。
能夠這樣肆無忌憚地消耗寶貴的汽油,還擁有自己的衛(wèi)隊(duì),這個(gè)軍官的身份一定不簡單。他上了城樓,原本端端正正站在那里的十幾個(gè)日軍士兵,馬上舉手敬禮。
“喜多將軍!”他們齊刷刷地往兩側(cè)退讓,把城樓正前方的位置讓了出來。這個(gè)將軍扶著垛口,臉上浮現(xiàn)出躊躇滿志的神情,嘴角露出了一絲得意的笑。他俯視這座城市的神情,就像一只貓正在玩弄?jiǎng)倓傋降降睦鲜蟆?/p>
他就是日本華北派遣軍特務(wù)機(jī)關(guān)長喜多誠一。此時(shí)的北平城里已經(jīng)成立了臨時(shí)政府,但所有人都知道,這個(gè)臨時(shí)政府里的各個(gè)要員,不過是一群傀儡,真正控制全城的就是這個(gè)五短身材的日軍軍官。
在他的視線里,古城北平還在沉睡著,全城只有三兩處地方閃動(dòng)著還算連成片的燈光。其中最大的一片,在他的右前方。他知道那里是東交民巷,各國駐華大使館所在的地方。此時(shí)英美國家對(duì)于日本侵華都奉行中立政策,所以日本沒有去動(dòng)那些大使館,以及在北平居住的那些國家的公民。
這些駐華官員也就得以在這座已經(jīng)更換了主人的城市里,繼續(xù)過著和從前一樣的歌舞升平的日子。
鼠目寸光之輩!喜多誠一心里想。他相信,大日本帝國的軍威,終究要把這些國家吞噬掉!
在他的正前方不遠(yuǎn),順著永定門下方的這條路,直著向北,不過一公里處是一個(gè)名叫珠市口的地方。來到中國十多年的喜多誠一,知道那里原本是北平城里最熱鬧的地方。但是自從日軍進(jìn)城后,城里像樣些的商鋪基本上都關(guān)了,四處一片蕭條,哪里有半點(diǎn)“大東亞共榮圈”的樣子?他下令一定要這些商鋪恢復(fù)營業(yè)。可那個(gè)剛剛當(dāng)上臨時(shí)政府頭頭的王克敏,在民間毫無威信可言,那些商鋪根本不聽他指揮。這些都是小事,影響不了這個(gè)北平統(tǒng)治者的心情。喜多誠一自從去年進(jìn)城后就非常喜歡這種感覺,那就是來到某個(gè)高處,俯瞰著這座臣服在自己面前的城市。
他曾經(jīng)到過景山。站在山上朝南望去,直接映入眼簾的就是故宮。他很想帶領(lǐng)大隊(duì)人馬闖進(jìn)這座宮殿。他早就從內(nèi)部文件里讀到自己的同僚在占領(lǐng)南京后,如何在南京城里為所欲為的信息。可是故宮畢竟是一座舉世聞名的古建筑,要闖進(jìn)故宮的話,他還是不敢擅作主張,必須發(fā)電報(bào)向東京大本營請(qǐng)示。令他沮喪的是,大本營在回電中斷然否決了他的提議。
后來,他在大本營的朋友告訴他,他的提議遭到否決,是因?yàn)槿哲姽ハ荼逼胶螅莻€(gè)被日本侵略者扶持登上滿洲國皇帝寶座的溥儀,就急匆匆向東京哀求,一定要保護(hù)好故宮,否則他無顏去見自己的列祖列宗,唯有自盡。
這件事也讓他對(duì)這個(gè)清朝末代皇帝多了一點(diǎn)點(diǎn)敬意。不久前,他一手操辦的臨時(shí)政府舉行了成立大會(huì),行政委員會(huì)委員長王克敏、北平特別市市長江朝宗、內(nèi)政總長王揖唐、治安總長兼華北治安軍司令齊燮元……那些中國人穿著長袍馬褂站在主席臺(tái)上,一個(gè)個(gè)看上去志得意滿、春風(fēng)滿面。他會(huì)面帶笑容地和臨時(shí)政府的這些首腦打交道,但心里卻對(duì)他們鄙視至極。他尊重的恰恰是那些拼命和自己對(duì)著干的人,他們?cè)谶@座城市里刺殺和日軍合作的中國人,竊取軍事、政治、經(jīng)濟(jì)情報(bào),還炸毀了日軍的軍火庫。自己的特工抓住他們,即使打斷了一根根皮鞭,用烙鐵燙、放狼狗咬,他們都不肯吐露一丁點(diǎn)秘密。也正是因?yàn)檫@些中國人的存在,北平的治安始終不能徹底穩(wěn)定下來,大本營要求他盡快在北平建立的“大東亞共榮秩序”更是無從談起。
想到這里,他心里又是一陣惱恨,不由得舉起右手,伸向漆黑的夜色,仿佛要一把將這些不肯合作的中國人統(tǒng)統(tǒng)抓進(jìn)手心。這時(shí),他身后傳來一陣急促的馬靴聲。這人走得很快,腳步聲很快到了身后。他聽出來了,這是他的副官松崎葵。
“將軍,大本營密電!”
他猛一揮手,城樓上的士兵紛紛轉(zhuǎn)身,邁著正步離開,到了城樓的另一側(cè)。他正要伸手去接過密電,松崎葵又說:“將軍,這是特一級(jí)密電!”
“特一級(jí)密電”意味著他必須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才能閱讀這封密電。在他的軍人生涯里,這還是他第一次收到特一級(jí)密電。
喜多誠一的車隊(duì)離開永定門,飛馳穿過天橋、珠市口、前門時(shí),這一帶的街面上一個(gè)人影都沒有。又過了半袋煙的工夫,珠市口天祥泰綢緞莊的門板才被人從里面卸下來一塊。一個(gè)裹著件灰棉襖、留著板寸頭的瘦小的伙計(jì),先是探出頭來飛快地掃了一眼大街,把一只腳伸過門檻,又厭惡地朝門側(cè)插著的日本國旗吐了口唾沫。他拎著一把大號(hào)掃帚從門板縫里走出來,開始打掃店門前的地面。
掃著掃著,四周又有幾家店鋪也像這家一樣有伙計(jì)出來打掃自家門口。往年的大年初六,正是各家店鋪開門重新營業(yè)的日子,可這一年,從前門到珠市口、天橋,沒幾家店鋪開始營業(yè)。
“行啊,雙林哥,又是你最早。”這個(gè)伙計(jì)正掃地,身后傳來甜軟的女聲。他不用回頭就知道,這是天祥泰綢緞莊穆老夫人的貼身丫鬟袖兒,她正要出門去不遠(yuǎn)處的二葷鋪?zhàn)訒?huì)仙居買早點(diǎn)。
這伙計(jì)名叫周雙林,是城南南池子五河莊人氏,今年三十四歲。從他來到天祥泰當(dāng)學(xué)徒算起,今年已經(jīng)是第十五個(gè)年頭了。
因?yàn)榕従╃埽搴忧f的傳統(tǒng)是男丁長到十八九歲,就要送進(jìn)北平城里的某個(gè)字號(hào)里當(dāng)學(xué)徒。去年日軍進(jìn)城后,天祥泰的伙計(jì)走了一大半,周雙林念著東家一家人只剩下老太太和老爺太太,兩位少爺都不在,就和另外幾個(gè)伙計(jì)留了下來。
周雙林轉(zhuǎn)過身,咧嘴笑笑,說:“袖兒,你也挺勤快的,今天又是這么早,每回都是買第一鍋的豆腐腦。”
“嗐,老太太就好這口,我無非就是圖她高興。”袖兒嘆口氣,拿手絹抹了抹眼角說,“昨晚上老太太又是一宿沒睡著,斷斷續(xù)續(xù)哭了好幾次。”
周雙林問:“又想大少爺、二少爺了?”
“除了這個(gè)事,還能因?yàn)槭裁矗窟@兩個(gè)少爺——唉!”袖兒搖搖頭說。大少爺、二少爺畢竟是自己主子,縱有千般不是,也不是她一個(gè)丫鬟該議論的。她端著食盒,嘆著氣,朝著鮮魚口方向走去。
他們說的大少爺、二少爺,就是天祥泰綢緞莊的少東家穆興科、穆立民。從道光七年(1827年)到如今,天祥泰綢緞莊已經(jīng)經(jīng)營了一百一十一年,傳了四代。如今的東家穆世軒,有兩個(gè)兒子,長子穆興科,次子穆立民。穆世軒的母親穆老夫人也在世,只是常年吃齋念佛,連飯都不和別人一起吃,更不過問綢緞莊的事。
十年前,北伐軍從廣東起兵后,節(jié)節(jié)勝利,一路打到了北平(當(dāng)時(shí)叫北京)。當(dāng)時(shí)穆興科剛滿十八歲,已經(jīng)中學(xué)畢業(yè),他本來在店里好好地學(xué)做生意,都已經(jīng)把穆世軒的本事學(xué)了個(gè)三四成。那天他也和城里的年輕人一起,揮舞著旗子去歡迎北伐軍進(jìn)城。當(dāng)天晚上回到家里,一家人正吃著飯,他忽然把筷子撂下,說要去參軍,說國民革命軍是國家的希望,自己不想賣一輩子布,要去參軍,以后干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yè)。
當(dāng)時(shí),北伐軍趕跑了和日軍合作的奉系軍閥,在北平城里正得人心。穆世軒看了看大兒子說:“興科,你不懂軍事,即使加入了國民革命軍,也不過是當(dāng)個(gè)普通士兵。你留在家里搞實(shí)業(yè),一樣是為國出力。”穆興科說:“爹,誰也不是天生就會(huì)開槍放炮的。更何況男兒志在四方,等到天下太平了,可再也沒有建功立業(yè)的機(jī)會(huì)了。”穆夫人在一旁說:“如今北伐成功,軍閥被打倒,你父親打算再開一家織布廠、一家印染廠,到時(shí)你們把廠子經(jīng)營好了,為國家作出的貢獻(xiàn),不比參軍入伍小。”
穆興科不再說話,只是悶著頭吃飯。他弟弟穆立民那年不過十二歲,還聽不太懂父母和哥哥在說些什么,但也聽出他們?cè)捓镉袪幷摰囊馑迹宦暡豢缘乇牬笱劬粗麄儭R娝麄儾粻幜耍诺拖骂^吃飯。
穆家的格局,是店鋪在前,坐落在珠市口大街上。而店鋪的后門外,隔了一條胡同則是穆家人住的宅院。這處宅院是北平殷實(shí)的商賈人家常用的三進(jìn)四合院。外院是傭仆住的,中院一左一右兩處廂房是兄弟倆住的,穆老夫人和穆世軒、穆夫人則住在里院。
那天晚上,一家人吃過晚飯,穆興科又去里院,陪奶奶說了好一陣子話才回房。但是到了第二天,穆興科卻不見了蹤影。他的床鋪收拾得整整齊齊,可見他是連夜離開的,覺都沒睡。
穆家在北平雖然算不上是第一等的頭面大家族,但也有頭有臉,尤其是在珠市口這一帶,穆世軒算得上是商界領(lǐng)袖。十年來,穆世軒不知道花了多少錢、托了多少人到處打聽,可始終沒有穆興科的任何消息。
穆家托的人已經(jīng)把當(dāng)初進(jìn)到北平的北伐軍所有的連隊(duì)都問過了,可是沒人見過穆家這位大少爺。穆家還是不死心,繼續(xù)花錢托人打聽,可始終杳無音信。
穆家大少爺就這么一走了之,穆家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二少爺身上。二少爺穆立民,比大少爺小六歲,一直平平安安上學(xué)。到了辛未年也就是民國二十年(1931年),日軍在東北挑事兒,三十萬東北軍愣是一槍一炮都沒放,就把東北丟給了日本侵略者。全中國民怨沸騰,各地學(xué)生游行示威不斷,報(bào)紙上也天天罵國民政府、罵日本侵略者。在這種社會(huì)氛圍下,二少爺?shù)臅闶遣缓米x了,他每天回到家,就給家人說在學(xué)校里聽到的事情。全家人整天心驚肉跳地盯著他,生怕他學(xué)他大哥離家出走。
穆老太太對(duì)穆世軒說,要是這個(gè)二孫子也離家干革命,自己就一頭撞死在穆家列祖列宗的靈位前。在穆立民每次出家門時(shí),無奈的穆世軒只好派兩個(gè)伙計(jì)緊緊盯著他。好歹三四年過后,二少爺算是慢慢安穩(wěn)了下來。
可好景不長,日軍占了整個(gè)東北還是貪心不足,到了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要“滅亡中國”的跡象越來越明顯。這一年,全家人的心思都在這個(gè)二少爺身上,店里不準(zhǔn)有一份報(bào)紙,誰也不能議論國事。本來穆立民這一年中學(xué)畢業(yè)后,穆世軒計(jì)劃讓他到店里學(xué)做生意,可穆立民說對(duì)做生意沒興趣,自己想考大學(xué)。穆老太太、穆世軒、穆夫人商量來商量去,覺得上大學(xué)終究也是好事,況且如果硬逼他學(xué)做生意,說不定他也一走了之。
穆立民整天在家溫書備考。轉(zhuǎn)眼間到了這年十二月十六日,這天一大早,穆世軒就感覺不對(duì)勁。那天,許多一看就是大學(xué)生的年輕人在店門口的街面上,成群結(jié)隊(duì)地走著,路上這樣的人越聚越多,大部分學(xué)生還舉著旗,喊著口號(hào)。
后來人們才知道,這一天有上萬名學(xué)生先是在天橋聚集,接著舉行游行示威,步行經(jīng)過珠市口、前門,一直到了天安門。學(xué)生的游行隊(duì)伍在天祥泰綢緞店門口經(jīng)過時(shí),發(fā)出震耳欲聾的吶喊,喊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jié)h奸賣國賊”“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對(duì)外”之類的口號(hào)。二少爺穆立民扔了書本,到了店里從門縫朝外面仔仔細(xì)細(xì)地看著。一開始他只是光看著,到了后來他也跟著不停地?fù)]著拳,跺著腳,嘴里反復(fù)喊著愛國口號(hào)。
他說得最多的一句是“華北之大,已經(jīng)安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了”。
在他身后,穆世軒夫婦面面相覷。他們看得出來,二兒子人在店里,心早就飛到外面的游行隊(duì)伍去了。
對(duì)于這天北平城里的情況,后來的新聞報(bào)道說得很準(zhǔn)確:在長達(dá)半個(gè)月的一二·九運(yùn)動(dòng)中,十二月十六日這天的愛國大游行,是規(guī)模最大、影響最大、持續(xù)時(shí)間最長的。當(dāng)天清晨這場游行從天橋開始,一萬多名愛國學(xué)生、市民聚集起來后,一路向北前進(jìn),經(jīng)過珠市口、大柵欄,到了前門后,游行隊(duì)伍遭到反動(dòng)軍警的鎮(zhèn)壓。這場運(yùn)動(dòng)極大地喚起了全國人民的愛國情感,點(diǎn)燃了國人團(tuán)結(jié)一致、共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熱血。
這天上午,穆世軒夫婦一直心驚膽戰(zhàn)。幸好學(xué)生們的游行隊(duì)伍經(jīng)過店門口后,穆立民一句話也沒說,更沒提要離家的事兒,就安安靜靜地回到自己的房間里繼續(xù)讀書。一家人連續(xù)十多天對(duì)他嚴(yán)加看管后,逐漸有些放松了。終于在元旦前的一個(gè)下午,穆立民借口去東安市場買書,也一去不復(fù)返了。
就在袖兒侍奉穆老太太吃完早點(diǎn)的時(shí)候,喜多誠一已經(jīng)回到位于東城煤渣胡同日軍特務(wù)機(jī)關(guān)的駐地,在他的辦公室讀完了那封特一級(jí)密電。
在密電里,東京大本營命令他即刻籌集大批軍火,用來支援正在徐州北部作戰(zhàn)的日軍。目前,日軍兩個(gè)南下的精銳師團(tuán)——板垣師團(tuán)和磯谷師團(tuán)在滕縣、臨沂一帶,遭到中國第五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李宗仁所指揮的第三、第二十二集團(tuán)軍的頑強(qiáng)阻擊,還有大批中國軍隊(duì)正開赴此地。這兩個(gè)師團(tuán)如果不能及時(shí)獲得支援,不但無法繼續(xù)前進(jìn),還有被圍殲的危險(xiǎn)。電報(bào)里還附有一份清單,這份清單里列了迫擊炮、加農(nóng)炮、輕重機(jī)槍、手榴彈等各種軍火,這批軍火必須火速備齊,隨時(shí)準(zhǔn)備沿津浦線運(yùn)往前線。
大日本帝國的軍隊(duì)里,也有這樣的蠢貨!滕縣和臨沂,這兩個(gè)小小的地方都拿不下來!
喜多誠一露出輕蔑的冷笑,大步走到鋪滿整面墻的華北軍用地圖前,目光從北平城一路向下,終于在地圖的下方,找到了徐州以北的山東、江蘇交界一帶。
他一向以滿腹韜略、軍事眼光高人一等自居,他也的確一眼就看出,滕縣、臨沂,還有南邊的臺(tái)兒莊,這幾個(gè)小小的地方,對(duì)于日軍半年之內(nèi)“滅亡中國”的戰(zhàn)略計(jì)劃而言,重要性的確非同小可。研究了一番雙方的作戰(zhàn)態(tài)勢(shì)后,他覺得,如果這場戰(zhàn)役由自己指揮,他早就率領(lǐng)華北派遣軍打敗了李宗仁,和華東派遣軍勝利會(huì)師,順利打通了中國的陸地交通。到了那時(shí),中國的華北、華東一帶,就像是被兩只鐵鉗牢牢鉗住的一塊肥肉,把這塊肥肉撕下來,占領(lǐng)整個(gè)中國也就指日可待了。
盡管對(duì)自己沒能指揮這場舉世關(guān)注的大戰(zhàn)極不甘心,他還是下令籌集軍火。這一批軍火能否及時(shí)運(yùn)抵前線,不但和這場大戰(zhàn)的勝負(fù)密切相關(guān),還左右著整個(gè)侵華戰(zhàn)爭的走勢(shì)。想到這里,他又有些得意。
但是自從入城以來,每天都有日軍或者和日軍合作的中國人被暗殺,軍糧被焚、彈藥庫被炸的情形也發(fā)生過。這說明隱藏在北平城里的中國特工還為數(shù)不少,要完成密電中的任務(wù)必須要徹底消滅中國人的地下情報(bào)網(wǎng)。幸好自己早已提前布下一張巨網(wǎng),如果行動(dòng)順利的話,國共兩黨在北平的地下組織很快就會(huì)被一網(wǎng)打盡。
“通知森本嶠來見我!”他朝自己的副官喊道。
他所要見的這個(gè)人,就是他手下的特工頭目、情報(bào)課課長。日軍占領(lǐng)北平前,森本嶠一直在東北活動(dòng),多年來以冷酷陰險(xiǎn)、殺人無數(shù)而出名。他破獲過國共兩黨在當(dāng)?shù)氐亩鄠€(gè)地下組織,同樣也是靠他搜集來的情報(bào),日軍才逮捕、殺害了抗日隊(duì)伍的多名領(lǐng)袖。
現(xiàn)在喜多誠一要把他叫來,讓他把這個(gè)搜捕北平地下組織的計(jì)劃,再仔仔細(xì)細(xì)地推敲一遍,確保萬無一失。為了完成這個(gè)計(jì)劃,他已經(jīng)命令森本嶠啟動(dòng)了一枚埋下多年的棋子——代號(hào)為“佩劍”的特工。
養(yǎng)兵千日,用兵一時(shí),這是他最喜歡的一句中國諺語。如今這個(gè)計(jì)劃不僅關(guān)系到能否破壞國共兩黨的地下組織,也決定了能否把前線急需的軍火安全送達(dá),所以那枚棋子也到了派上用場的時(shí)候了。
“森本君,我們的那位‘佩劍’已經(jīng)完全做好出擊的準(zhǔn)備了嗎?”喜多誠一對(duì)一個(gè)剛剛走進(jìn)來的外形干瘦、面色慘白的日軍軍官說。
“請(qǐng)將軍放心,我剛剛和‘佩劍’重新推演了一遍整個(gè)計(jì)劃,絕對(duì)萬無一失!”森本嶠低下頭,恭恭敬敬地說。
“吆西,吆西。”喜多誠一笑了,仿佛看到了自己抓獲大批國共兩黨地下組織成員,城里各種各樣的叛亂從此煙消云散的情形。他可以確信,到了那時(shí),自己就真正成了這座城市的主人,自己在天皇眼中的地位也將達(dá)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這天早上,穆世軒吃罷早飯,才想起今天是大年初六,就走出家門,到了大街上。他發(fā)現(xiàn)街面上比前一陣更加冷清了。若在往年,珠市口這一帶自然是極熱鬧的,可今時(shí)今日,穆世軒卻希望整個(gè)珠市口,越冷清越好。
他知道,北平每個(gè)商號(hào)都是有祖宗定下的規(guī)矩的,每年從正月初六開始,一定要開門迎客。但是他也知道,自己這一次沒有打開店門正式營業(yè),并不算違背祖訓(xùn),因?yàn)樽孀趥儺?dāng)年定規(guī)矩時(shí),絕對(duì)不會(huì)想到有如今的局面。他們?nèi)f萬想不到,這堂堂的北平城,竟然能讓東洋人給占了!
庚子(1900年)那年,數(shù)都數(shù)不過來的洋鬼子兵,打著各種各樣的旗號(hào)進(jìn)了北平——那時(shí)還叫北京,自己剛剛學(xué)會(huì)看賬本。那些說著不知道是哪國話的洋鬼子兵,成群結(jié)隊(duì)地在前門、大柵欄、珠市口這一帶洗劫店鋪。開著門的店鋪,他們直接進(jìn)去搶,沒開門的,就拿槍托砸開門。店鋪里的伙計(jì),自然早就逃了。天祥泰和別的店鋪不一樣,穆世軒平時(shí)待人仁義,店里的伙計(jì)誰也不肯走,都說要豁出命來保護(hù)東家。伙計(jì)們上了好幾層門板,又把門板頂?shù)镁o緊的。最后還是讓洋鬼子兵砸破了門板,闖進(jìn)來把成千匹綢緞?chuàng)尮饬恕:髞沓⒑屯鈬炗喠恕缎脸髼l約》,從那之后,洋鬼子兵就能在北京城里城外駐扎著。翻遍史書,哪里有過這么喪氣丟臉的事兒!
如今日軍占領(lǐng)了北平,看情況可和從前不一樣。日本兵滿城都是,這陣勢(shì),明擺著是要長駐下去。難道這次中國真的要亡在日軍手里?
穆世軒這么想著,又盤算了一會(huì)兒自家的家底,覺得街面上的寒氣有點(diǎn)重了,也就回到了自家院子。
也是從去年日本兵進(jìn)城之后,每月初六,珠市口這一帶幾個(gè)大鋪面的老板,都會(huì)輪流做東,大伙兒互相通通氣、交流交流信息。大伙兒心里都明白,在兵荒馬亂的年月里,要是早點(diǎn)知道某一件事,說不定一家人的性命就得救了。所以天祥泰綢緞莊、正和居飯莊、豫豐銀樓、廣順源南貨行、奎明戲院、永和車廠等珠市口一帶十來家大店鋪的老板,都把這頓飯看得挺重。
這天晚上,大伙兒正好是在正和居飯莊吃這頓飯。席上豫豐銀樓的東家范長安說了一條爆炸性消息。
日本人剛扶上來的臨時(shí)政府行政委員會(huì)委員長王克敏,還沒把那把官椅坐熱乎,今天就險(xiǎn)些被人刺殺了!
當(dāng)時(shí)這頓飯大家吃得都很憋屈,正和居的幾道拿手菜——扒熊掌、柴把鴨子、白切羊羔,都沒人動(dòng)筷子。十幾位大老板除了范長安,其余的都到了。但大家都悶著頭吸煙,議論了幾句范長安為何遲遲未到,就再也沒話可說了。
這天的正和居,整個(gè)樓上樓下也沒幾桌人。要是在往年,這正月時(shí)節(jié)正是一年里生意最好的時(shí)候,包間自然是要在臘月提前訂才訂得上,就連散座也坐滿了人。如今北平城讓日軍占了,自然誰也不會(huì)沒心沒肺地大吃大喝。如果不是為了互通消息,為了在亂世里保住身家性命,這十幾位老板,也沒心思來這里吃飯。
這頓飯尷尬地吃了個(gè)把時(shí)辰,有一半人先告退了,席上只剩六七個(gè)人。穆世軒正要告辭,忽然原本冷冷清清悄無聲息的走廊上,響起一陣急促的腳步聲,而且腳步聲越來越近,肯定是沖著這個(gè)包間來的。
桌旁的幾個(gè)人迅速互相看了看,不知道這是兇是吉。幾秒鐘后,包間的房門突然被人推開,一個(gè)人影裹著一身寒氣沖了進(jìn)來。
眾人定眼一看,此人正是范長安。在珠市口這一帶,各家字號(hào)基本上都是只有一家店鋪,畢竟這里已經(jīng)是全北平一等一的繁華地界了,在這里把生意做好了,比在別處開多家分店還賺錢。可這豫豐銀樓在珠市口的店面太小,只好在東城的東安市場和西城的琉璃廠各開了一家分店。這天正是范長安到兩家分店巡店查賬的日子。
正月寒冬里,范長安竟然滿腦門子細(xì)汗,還一直喘著大氣。眾人正要問他是怎么回事,他先開了口:“老哥兒幾個(gè),今兒咱們這北平城里出了件大事,你們聽說了嗎?”
眾人一起搖頭,范長安正要開口,正和居老板潘廣仁為人精細(xì),示意范長安先別說話。他轉(zhuǎn)身開了房門,先瞅了瞅走廊上有沒有閑雜人等,接著把跑堂伙計(jì)叫進(jìn)來,又給范長安加了幾個(gè)菜,然后掩好了房門,這才回到座位上,朝范長安點(diǎn)點(diǎn)頭。
范長安找了個(gè)座位坐下,從桌上拿起手巾擦擦汗,喘息聲稍稍平息了一些,才說:“老哥兒幾個(gè),我老范這條命,今兒差點(diǎn)丟在煤渣胡同。好家伙,那子彈,嗖嗖地擦著我的耳邊飛過來飛過去。我老范活了這大半輩子,啥風(fēng)浪沒遇見過?今兒這種事兒可真是第一次碰見!”
其余人不知道發(fā)生了何等大事,讓他別賣關(guān)子,有話趕緊說。他這才壓低嗓門說,今天下午,他帶兩個(gè)伙計(jì)去東安市場的分店查賬,他坐了一輛黃包車,兩個(gè)伙計(jì)步行。仨人剛到東華門,就看到有兩輛嶄新漆黑的高檔汽車開出了煤渣胡同。這時(shí)有輛原本停在路邊的汽車突然起步,竄上馬路,擋住了那兩輛汽車。
剛開始范長安還有些納悶,一看那兩輛車的車牌號(hào)碼才知道,那正是北平城名義上的最高長官王克敏的座駕。誰的膽子這么大,敢攔住他的車?
說是“名義上”,自然是因?yàn)橥蹩嗣舻墓巽暎强恐犊咳哲姄Q來的。他的烏紗帽、他的小命,完全掌握在日軍手里。
那輛小車逼停王克敏的車隊(duì)后,數(shù)名蒙面黑衣刺客跳下車,他們每人都是手持雙槍,左右開弓,同時(shí)向兩輛高檔汽車開火。王克敏的司機(jī)、日語翻譯,還有三名保鏢,都身中十多槍,當(dāng)場喪命。
“那王克敏呢?死沒死?”奎明戲院的老板阮道謀是出了名的急性子,還沒等范長安說完就急不可耐地問。
范長安嘆口氣說:“也真是邪門了,王克敏平時(shí)坐車,都是靠右坐,他的翻譯靠左坐。可今兒也不知道王克敏哪根筋搭錯(cuò)了,他非要和翻譯換個(gè)位置。結(jié)果是他的翻譯被打成了篩子,他雖然也中了兩槍,可沒一槍打中要害。他這條狗命,就這么保住了。”
眾人一片嘆息,有人還重重一拳砸在桌上。阮道謀搖搖頭說:“真是好人不長命,禍害遺千年。對(duì)了,那幾位行刺的好漢都脫身了嗎?”
范長安說:“這幾位好漢,個(gè)個(gè)都訓(xùn)練有素,他們一打光子彈,馬上一扭頭,就上了汽車,汽車馬上就開走了。”
廣順源南貨店老板鄒潤德說:“他們一共有幾個(gè)人?有人受傷嗎?”
范長安說:“開槍的一共四個(gè),要是把車?yán)锏乃緳C(jī)也算上,那一共就五個(gè)人。王克敏的保鏢臨死前開過一槍,打中了一個(gè)刺客的右胳膊,還在地上留下一攤血。”
阮道謀說:“真是好漢!哎,出了這么大的事兒,日軍怎么沒滿城搜捕?”
范長安說:“這幾個(gè)人都蒙著面,別人根本看不出他們長怎么樣,憑什么搜啊?”
鄒潤德說:“不是有人胳膊中了一槍嗎?”
范長安說:“他們那輛車,飛似的就開跑了,往哪兒找去?”
“真是高手,這就叫神龍見首不見尾。”幾個(gè)老板紛紛感慨著。
說到這里,范長安的呼吸才平穩(wěn)了些。他摸出煙斗,裝上煙葉,點(diǎn)著,重重吸了一口,說:“這幾位好漢,個(gè)個(gè)身手不凡,而且行動(dòng)統(tǒng)一、計(jì)劃周密,他們肯定不是一般的江湖好漢。”
阮道謀低頭一尋思,說:“那他們會(huì)不會(huì)是國民政府派來的?”
范長安還沒回答,鄒潤德?lián)屜日f:“打鬼子的,又不是只有老蔣。”他伸出手掌,擺出個(gè)“八”的手勢(shì),試探性地看著范長安說,“會(huì)不會(huì)是——”
阮道謀說:“你覺得,他們是八爺?”
鄒潤德點(diǎn)點(diǎn)頭。
阮道謀說:“何以見得?”
鄒潤德說:“我也是胡亂猜的。對(duì)了,王克敏這么大張旗鼓地到煤渣胡同去干什么?”
范長安說:“日本鬼子的特務(wù)機(jī)關(guān),就在那兒。這王克敏啊,每天都要去見那個(gè)日軍特務(wù)頭子喜多誠一,比見他親爹還勤。”
鄒潤德說:“這回行刺王克敏這個(gè)漢奸頭子沒成功,讓他有了提防,以后再想刺殺他,就更難了。”
范長安說:“鄒兄說得對(duì)。日本人如今正格外高看王克敏,在特務(wù)機(jī)關(guān)不遠(yuǎn)的地方發(fā)生這種事兒,日本人的面子也掛不住,馬上把煤渣胡同、東華門那一帶封鎖起來,只許進(jìn)不許出,我和兩個(gè)伙計(jì)就被關(guān)在封鎖線里面。幸好我們都帶著證件,加上有分店里的伙計(jì)作證,日本人也找不出茬來。”
阮道謀說:“那日本人到底有沒有抓住那幾個(gè)刺客?”
范長安搖搖頭說:“沒有。這會(huì)兒封鎖線內(nèi)少說還有千把號(hào)人,要是抓著了,封鎖線還不早就撤了?”
一聽說刺客已然逃脫,包間里的氣氛頓時(shí)輕松了不少。范長安說:“那幾位好漢,個(gè)個(gè)都會(huì)一身好功夫。那個(gè)中了一槍的雖然蒙著臉,但身高腿長,腰身挺拔,眼神里自始至終帶著一股子狠勁。而且他中了槍還臨危不亂,跑起來啪啪響,渾身上下不帶打晃的,真有種!”
鄒潤德一拍腦門說:“那位好漢右胳膊中了槍,怪不得,剛才我來的路上時(shí)不時(shí)就有巡警讓年輕小伙子露出右胳膊來,敢情是在查找刺客。”
這時(shí)跑堂伙計(jì)端著新加的四個(gè)菜——涼菜是醉鵝和醉蟹,熱菜是翡翠蝦仁、九珍燴肝腰,進(jìn)來,又快步退出。等伙計(jì)走遠(yuǎn)了,“只是——”范長安從盤子里拈起蝦仁,嚼了幾下,有些欲言又止。
他這神情被旁人看到眼里,旁人都說:“范老板,你還有什么話,盡管說。”
范長安說:“要說是有點(diǎn)兒邪門。那個(gè)帶頭的好漢,一直蒙著臉,就露出一雙眼來。可也怪了,那雙眼我總覺得在哪里見過。”
幾個(gè)人又陸續(xù)給范長安敬酒壓驚。這頓酒席,吃了一個(gè)多時(shí)辰才吃完。
第二天,北平城的市民一覺醒來,發(fā)現(xiàn)滿大街已經(jīng)貼滿了通緝令。通緝令上的畫像正和范長安在正和居的酒桌上說的一模一樣,是個(gè)高大健壯的年輕人,雖然蒙著面,但劍眉星目,長方臉型看起來頗為英俊。
通緝令上并沒有說這個(gè)通緝犯具體犯了什么罪,只是籠統(tǒng)地說他在鬧市行兇,殺傷無辜,右臂有傷,任何人給警方提供重要線索或者抓獲了此人,都有五百塊銀圓的懸賞可拿。
初七這天,正是天祥泰綢緞莊的穆老太太和穆夫人按慣例去城外臥佛寺進(jìn)香還愿的日子。可如今兵荒馬亂,城里城外人心惶惶,穆老夫人、穆夫人自然也不敢出城,就派了周雙林帶了香火錢,代她們?nèi)ヅP佛寺給佛爺磕頭。
周雙林是綢緞莊的伙計(jì),并非穆家的傭仆,照理說,穆家宅子里的事兒,自有男女傭仆辦理,可如今穆家的仆人只剩下五六個(gè),各有各的事情要忙活,反正綢緞莊也沒恢復(fù)營業(yè),只好由周雙林去了。
天祥泰綢緞莊位于城南正中,而臥佛寺出了西直門,還有足足三十里路,這三十里路都是在荒郊野外,平時(shí)人就少,這時(shí)候自然更沒人了。但凡城里的汽車、黃包車,基本上都不敢出城了。本來穆世軒不想讓任何人去臥佛寺,早在過年前他就對(duì)自己母親和夫人說,哪怕是自家的傭人、伙計(jì),也是父母生父母養(yǎng)的,仙佛鬼怪的事兒,終究不可信,犯不著為了還愿讓人冒這么大的風(fēng)險(xiǎn)。
穆世軒說得鄭重,穆老太太和穆夫人自然也沒再說什么。可兩人那天一口茶沒喝,一口飯沒吃,一直在各自屋里,坐在床頭撲簌簌掉眼淚。
全家人都有些慌了。周雙林知道,當(dāng)初穆夫人在生大少爺?shù)臅r(shí)候,起初有些難產(chǎn),穆老太太為此當(dāng)場許愿,說如果大少爺平安落地,就每年給臥佛寺供奉一大筆香火錢。結(jié)果大少爺順利降生,母子平安。二十八年來,這筆香火錢一直沒斷過。
周雙林找到穆世軒,說自己愿意替東家去還愿。穆世軒當(dāng)場拒絕。周雙林說,三年前是東家出錢請(qǐng)大夫、買藥,才治好自己老母親的病,這回如果不讓自己去,自己就沒臉活在世上了。穆世軒被他說得萬般無奈,只好答應(yīng)了。
這天早上,天還沒亮,周雙林隨身帶上八十塊銀圓,吃完早飯就動(dòng)身了。穆世軒還額外給了他三塊銀圓的車費(fèi),告訴他要早去早回,可以先坐黃包車到西直門,到那兒之后,再租一頭好牲口出城。如果真不走運(yùn)碰到劫匪,就把錢都給他們,千萬要保住性命。
周雙林出了綢緞莊,天色還漆黑一片。他站在珠市口往四下里一望,整條前門大街和珠市口大街都不見人影,更不用說黃包車了。這個(gè)點(diǎn)兒,再肯吃苦的黃包車夫,也還沒出門拉活兒。
周雙林緊了緊包袱,邁開腿往北走去。他估摸著,自己一個(gè)多時(shí)辰準(zhǔn)能走到西直門,到那兒租一匹騾子,再有個(gè)把時(shí)辰就能到臥佛寺。這么一算,天黑前自己就能回到西直門了。
這天計(jì)劃進(jìn)行得很順利,他中午前就到了臥佛寺,給佛像磕了頭,把八十塊銀圓交給了住持。以前他到臥佛寺,寺里寺外擠滿了上香的善男信女,可這天,不但寺外山路上空無一人,寺里也只有寥寥幾個(gè)香客。
住持細(xì)細(xì)問了城里和店里的情形,說自己一直在給店里的幾位施主誦經(jīng)祈福。他送給穆老夫人和穆世軒夫婦各一串佛珠、兩盒素點(diǎn)心,又命知客僧請(qǐng)周雙林進(jìn)廂房吃了一頓素齋。
周雙林吃飽了飯,出了臥佛寺,抬頭一看,日頭不過稍稍偏西,心想天黑前不但能回到西直門,說不定都能回到店里。
他牽著騾子從山門向官道走去,走著走著,總覺得道旁樹林子里有人在朝自己這邊打量。剛才在寺里,自打進(jìn)了大雄寶殿他就覺得身后一直有人盯著自己,就連在廂房里吃素齋,似乎都有人在門外向房內(nèi)打量。
他勒住騾子的韁繩,朝樹林仔細(xì)看了一番,倒是看不到人影。山道一片寂靜,周雙林豎起耳朵,除了自己的呼吸聲,什么聲音也聽不到。他猜想自己大概是疑神疑鬼了,一牽韁繩準(zhǔn)備繼續(xù)趕路。忽然,只聽見一聲脆響,樹林里不遠(yuǎn)處傳出踩斷樹枝的聲音。
“什么人?”周雙林喊了一嗓子,攥緊拳頭背靠騾子,緊緊地盯著樹林。
“雙林,是我。”十多米外的樹林深處,一個(gè)瘦高人影從樹后轉(zhuǎn)了出來。這人戴著一頂厚呢料子的鴨舌帽,帽檐下的陰影遮住了大半張臉。
“大少爺,是你!”
這人走出樹林,周雙林看清了這人的五官,渾身哆嗦起來,失魂落魄一般,手里的韁繩都松開了。大黑騾子一看沒了束縛,本想縱蹄跑開,可山道的臺(tái)階陡峭,沒人牽著,自己非得摔個(gè)骨折筋斷不可,只好一仰脖子向著天空,大聲啾啾地叫了起來。
眼前這人穿著一身北平有點(diǎn)身份的男人常穿的長袍馬褂,帽檐下露出一張清瘦的長方臉。無論是臉型,還是兩道濃黑的劍眉,都是穆家男人代代相傳的印記。周雙林上前一步,想抱住這個(gè)男人,可伸出手去卻又有些不敢。雖然在這個(gè)男人還是個(gè)小男孩的時(shí)候,自己就曾經(jīng)抱著他去東華門看花燈,去天橋買糖葫蘆,去看雜耍。他伸出袖子擦擦眼淚,哆嗦著說:“大少爺,這些年,你都去哪兒了?”
這個(gè)男人自然就是北平城天祥泰綢緞莊的大少爺,離家出走已經(jīng)十年的穆興科。他拍拍周雙林肩膀說:“雙林,我奶奶、我爹我娘,他們身體都好吧?”周雙林點(diǎn)點(diǎn)頭說:“老太太這兩年有些見老,出門少了,老爺和夫人身體都好。大少爺,你快點(diǎn)跟我回家看看吧,他們都惦記著你呢。”
穆興科微微一笑說:“行,雙林,咱們先下山再說。”
周雙林挽起韁繩,把眼淚擦干,二人順著山道下山。此時(shí)正值午后,是北方一天中最暖和的時(shí)候,陽光從樹尖上照射下來,布滿了整條山道。周雙林心里暖烘烘的,覺得這是入冬以來最暖和的一天。
穆興科一步一級(jí)臺(tái)階地走著,周雙林看著他說:“大少爺,你真是長大成人了。我記得你小時(shí)候,和老太太、太太來這兒上香,這條山路不好走,我本想背著你走,可你非得自己走。那時(shí)你上下臺(tái)階都是蹦蹦跳跳的,哪像現(xiàn)在這么沉穩(wěn)?”
穆興科笑著說:“對(duì),雙林,我也記得那些事。對(duì)了,我弟弟該上大學(xué)了吧?他上的哪所大學(xué)?”周雙林遲疑了一下,腳步也慢了。穆興科臉上的笑意消失了,問,“雙林,我弟弟出事了嗎?”
周雙林趕緊說:“大少爺,二少爺他兩年前也離家出走了。”
穆興科說:“兩年前?鬧學(xué)潮的時(shí)候?”
周雙林點(diǎn)點(diǎn)頭。穆興科笑了,說:“這臭小子,年紀(jì)不大就學(xué)別人離家出走。倒也好,在外面吃兩年苦,就更知道家里好了。”
周雙林也笑了,說:“大少爺,我記得你是十八歲那年走的,兩年前二少爺離家的時(shí)候,也是十八歲。”
穆興科說:“雙林,我們哥倆的事兒,你記得還真是清楚。我們老穆家有你,真是全家人的福氣。”
周雙林撓撓頭,臉一紅說:“其實(shí)我也沒記得那么清楚,可架不住老太太和太太整天念叨你們哥兒倆。家里每頓飯,都給你們擺上筷子、碗,每年你們生日那天,家里都準(zhǔn)備了長壽面。”
他們二人邊走邊聊,很快到了山下官道。二人在道路旁找了一處賣大碗茶的茶攤,挑了個(gè)僻靜處坐下。穆興科又聽周雙林細(xì)細(xì)講了家里和綢緞莊的情形,這才壓低嗓子說:“雙林,今兒你先自個(gè)兒回去,我還得過一陣子才能回家,你也別給我奶奶他們說見過我。”
周雙林端起茶碗剛要喝,一聽這話馬上放下茶碗,脖子都急紅了,說:“大少爺,老太太、太太整天惦記著你們哥兒倆,每年一到你們生日,還有你們離家那天,她們都是水米不進(jìn),整宿整宿地哭。老太太有兩回哭得都背過氣去了……”
穆興科笑道:“你不是說他們都挺好的嗎?”
周雙林愣了愣,說:“剛才我那不是怕你擔(dān)心嗎?我還以為你這就跟我回去……”
穆興科伸手拍了拍他的手背,說:“雙林,你放心,過一陣子我肯定回去,但今天不行。”
“那你到底什么時(shí)候回去?自打日軍進(jìn)了城,老太太、老爺、太太他們更擔(dān)心你們了,每天都要念叨好幾回。”
“雙林,我這回回來,就不再走了,到時(shí)我一定好好陪陪他們。你看,我今兒就是因?yàn)橹牢夷棠獭⑽夷锼齻儠?huì)來臥佛寺還愿,就特意來這兒,打算遠(yuǎn)遠(yuǎn)瞅她們幾眼。今兒雖然沒見著她們,但見著你了,知道家里一切都好,我就放心了。”
周雙林點(diǎn)點(diǎn)頭,兩人又喝了幾碗茶。周雙林盯著穆興科看了一會(huì)兒,見他一直都在用左手端茶碗,說:“大少爺,離家十年,你倒成了左撇子了。”
穆興科笑笑沒回答他,轉(zhuǎn)而說:“好了,雙林,時(shí)候不早了,你趕緊回城吧,再晚了路上不太平。”
“你連城都不進(jìn)?”周雙林問大少爺。
穆興科點(diǎn)點(diǎn)頭,摸出幾張鈔票放在桌上,轉(zhuǎn)身離開了官道,進(jìn)了樹林子。一眨眼工夫,人影就不見了。
這天晚上,周雙林回到店里,把上香還愿的經(jīng)過給穆老太太和穆世軒夫婦說了,但沒提遇到大少爺?shù)氖隆H私o了他賞錢,就讓他吃飯休息去了。
周雙林吃喝完畢,和平常一樣,在店里平時(shí)睡慣的地方打開鋪蓋卷。這時(shí)別的伙計(jì)早都睡著了,但爐子里的煤球燒得很旺。在畢畢剝剝的聲音中,他望著黑漆漆的天花板,回想著今天和大少爺見面的經(jīng)過,總琢磨不透這位十年沒見的大少爺,怎么變成了左撇子。這一天他一直在趕路,的確累壞了,胡思亂想了一會(huì)兒,就翻了個(gè)身,睡著了。
通緝令已經(jīng)貼出幾天了,刺客始終沒抓到。北平城不時(shí)有人因?yàn)楹屯ň兞钌系漠嬒裼幸稽c(diǎn)兒像,或者右胳膊有傷,就被巡警或者特務(wù)抓走了。
這天清晨,在北平前門火車站,一個(gè)年輕人從剛剛抵達(dá)的火車上跳下來。他二十出頭的年紀(jì),手提行李箱,身穿藏青色毛料學(xué)生裝,圍巾雪白,皮鞋锃亮,劍眉英挺,整個(gè)人看起來精神極了。四周的女乘客,不斷地扭頭朝他打量著。
這個(gè)年輕人夾在乘客里出了站,馬上有一堆黃包車朝他們圍了上來。有錢的乘客都上了黃包車,他看起來雖然也是富家子弟,卻從黃包車中穿了過去,徑直步行沿著前門大街快步朝南走去。
此時(shí)正值北方最冷的時(shí)節(jié),地面凍得硬邦邦的,灑點(diǎn)水上去馬上就會(huì)結(jié)成冰。這個(gè)年輕人因?yàn)樽叩每欤~頭上竟微微冒汗。他顧不得擦,只是大步流星地往前走著。他很快就穿過鮮魚口、大柵欄,走到了珠市口,到天祥泰綢緞莊那緊閉的店門前停了下來。他仰頭看著高大的店門,眼圈漸漸紅了。
“哎呀,這不是穆家二少爺嗎?你走了有兩年多了吧?你奶奶、你娘可想死你了!”街面上一個(gè)五十多歲的女人,身穿一件破破爛爛的舊棉襖,拉著一個(gè)三歲多的孩子,看到他站在門前,慢慢湊過來說。孩子手里緊攥著半個(gè)沾滿土的凍柿子,腮幫子凍得通紅,身上的棉襖棉褲都臟得看不出本色了,好幾個(gè)腳趾頭也從鞋里露了出來。倆人的手上都長滿了凍瘡。
年輕人扭頭看著她說:“我是穆立民,您是……”
那女人擺擺手說:“我是住施家胡同的孫老六家里頭的。喏,就是在會(huì)仙居包包子的孫老六,平時(shí)你見了,叫他六叔,叫我六嬸。這是我孫子,你以前見過他。”
穆立民說:“對(duì),對(duì),我記得,你是孫六嬸。這是孫哥的孩子吧?孫六叔還有孫哥孫嫂都好吧?”
一聽此話,那女人登時(shí)流下淚,說:“你說的這仨人,如今都已經(jīng)……唉——不在了……”
穆立民吃了一驚,說:“六叔我記得今年也就六十出頭吧,孫哥就更年輕了,怎么就……”
那女人臉色變得慘白,接著說:“他們都是去年沒的。去年日本兵攻打北平城,城外四面八方都是日本兵,咱們自己的兵,只能指望二十九軍了。眼瞅著二十九軍頂不住了,城里的老少爺們也有不少報(bào)名要去打仗。你六叔他們爺兒倆,這輩子連槍長什么樣都沒見過,也跟著報(bào)了名,被派到了南苑,管著送水送糧食。他們這一去,就沒回來。后來聽和他們一道去的蔡家胡同的趙二喜說,你六叔是讓日本兵拿刺刀捅死的。我那傻兒子呢,抓之后,又被日本兵拿鐵絲和別的俘虜綁在一塊,澆上汽油,活活給燒成了炭……后來日本兵進(jìn)了城,有人給日本兵告密,說了我們家這爺兒倆的事兒,就有三個(gè)日本兵上門來了,說是要搜捕二十九軍士兵家屬。我這媳婦不肯去,還讓他們給……媳婦就在胡同里那棵老槐樹上上了吊……”
孫六嬸一手抹著眼淚,一手摸著那孩子的頭頂說:“唉,要不是因?yàn)檫@個(gè)小東西,我也不想活了……”她說著就抽泣起來。
穆立民一掌重重拍在面前的石墻上,咬著牙說:“這群侵略者,真是禽獸不如!”
這時(shí),綢緞莊的門板被卸下了一塊,一個(gè)十八九歲、學(xué)徒模樣的人露出臉來,打量了一下穆立民說:“這位爺,本店暫緩營業(yè),您要買綢緞布匹,請(qǐng)去別處。”說完,就要關(guān)上店門。
“三亭子,你真是有眼不識(shí)泰山!這是你們家二少爺!”孫六嬸忙說。
“二少爺?”這個(gè)叫三亭子的伙計(jì)從門后鉆了出來,站到門外細(xì)細(xì)瞅了瞅穆立民,半信半疑地問,“您尊姓大名?”
“我叫穆立民,穆世軒是我爹。”
“哎喲喂!”這個(gè)伙計(jì)一拍大腿,又卸下兩塊門板,鞠躬請(qǐng)穆立民進(jìn)去,說,“二少爺,您可回來了!您快請(qǐng)進(jìn),老太太、老爺和太太他們整天念叨您呢!我是去年剛來的,叫韓山亭,排行第三,您叫我三亭子就行,老爺他們都這么叫!”
穆立民點(diǎn)點(diǎn)頭,把學(xué)生帽和圍巾摘下來遞給三亭子,邁步走了進(jìn)去。三亭子按亮了電燈,店里那些布滿了金絲銀線的綾羅綢緞,一下子鋪陳在面前,像珍寶一樣閃耀起來。
這是穆立民從小到大再熟悉不過的場景了。
“老太太、老爺、太太,大吉大利,給您幾位道喜了,咱家二少爺回來了!”三亭子在他身后大喊起來。
穆家的三進(jìn)四合院在店面后面,穆老太太、老爺和太太是住在四合院深處,三亭子喊得聲音再大,他們也聽不見,但喜訊很快傳到他們耳朵里。
“二少爺回來了,二少爺回來了!”喜訊在店堂里回蕩著,也傳進(jìn)了后院。穆立民穿過店堂,進(jìn)了自家院子,他看到由貼身丫鬟袖兒攙扶著的奶奶,還有父母,都已經(jīng)站在二進(jìn)院門那里。他鼻子一酸,快走幾步,跪在奶奶面前。
“兩年多了,你這孩子一聲不吭,一走就是兩年多……”穆老太太把他摟進(jìn)懷里,捶打著他的肩背,已是老淚縱橫。袖兒也跪在穆老太太面前,說:“恭喜老太太,二少爺平安回家,大吉大利!”
幾個(gè)人進(jìn)了穆老太太的正房,穆立民先給祖宗牌位磕頭上香,然后恭恭敬敬地站在長輩面前,把自己離家后的情形細(xì)細(xì)說了一遍。
兩年前穆立民受到一二·九運(yùn)動(dòng)的影響,離家出走。他先是四處參加愛國運(yùn)動(dòng),在全國各地漫游了幾個(gè)月后,來到了武漢,正好趕上國立武漢大學(xué)招生。他成功考入武漢大學(xué)物理系。上了一年大學(xué)后,日軍全面侵華,戰(zhàn)火波及武漢,當(dāng)?shù)卮髮W(xué)紛紛內(nèi)遷,他起初也跟著老師同學(xué)一起內(nèi)遷。但出城沒多久,他就染上了瘧疾,等病好后已經(jīng)無法追上師生隊(duì)伍,只好返回北平。
“這兩年,你一直在武漢?”穆世軒問。
穆立民點(diǎn)點(diǎn)頭,說:“我有武漢大學(xué)的證明信,可以憑此信件轉(zhuǎn)入國立大學(xué)繼續(xù)讀書。”說完,從懷里掏出一封信遞給父親。
穆世軒打開信,只見滿紙是極清秀的行楷小字,寫明穆立民是本校物理學(xué)二年級(jí)學(xué)生,尊師重義,勤學(xué)敏行,為可造之才。穆君因病未能與校本部同遷,請(qǐng)接到此信件的高校酌情準(zhǔn)其入學(xué)。落款是國立武漢大學(xué)校長王星拱。
穆世軒冷笑道:“清華和北大,都南遷了,這北平城里,還有什么國立大學(xué)!可惜王校長這一手好字了!”
穆立民說:“爹,國立武漢大學(xué)是著名學(xué)府,按照教育界的慣例,武漢大學(xué)的學(xué)分學(xué)籍,燕京大學(xué)之類的教會(huì)學(xué)校一般也會(huì)承認(rèn)。”
穆世軒臉色緩和了一些,點(diǎn)點(diǎn)頭說:“燕京大學(xué)學(xué)風(fēng)端正,師資頗佳,何況這是美國人辦的學(xué)校,日本人也不敢輕舉妄動(dòng)。”
穆立民說:“那我明天就拿著王校長的親筆信,去燕京大學(xué)看看能否入學(xué)。”
穆老太太在一旁越聽越著急,說:“你們說的這個(gè)燕京大學(xué),到底是在哪兒?”
穆夫人說:“娘,這個(gè)燕京大學(xué),在西郊海淀呢,就是從前老佛爺?shù)念U和園那一片。”
“那么遠(yuǎn)?”穆老太太急得一跺腳,說,“立民,你這剛回來,別急著去上學(xué)。現(xiàn)在城里城外都不太平,我看啊,你就別上這個(gè)學(xué)了。”
穆夫人連忙說:“立民,你也是,剛回來就說要上學(xué),你先在家待幾天,好好陪陪奶奶。”
穆世軒問他在外面這兩年,有沒有聽到他哥的消息。穆立民說,自己當(dāng)初到了武漢,就到處打聽有沒有一個(gè)叫穆興科的人。原來,當(dāng)初北平全城參加北伐軍的年輕人有很多,被編進(jìn)國民革命軍不同的隊(duì)伍。自己在武漢這段時(shí)間,一有空就到國民革命軍駐地探聽情況,后來找到幾個(gè)北平同鄉(xiāng),他們都沒聽說過穆興科。
聽到這里,穆老太太又流下淚來。袖兒趕緊給她擦了眼淚,捶她的背說:“您兩個(gè)離家的孫子,今天回來了一個(gè),還上了大學(xué),個(gè)子長高了、模樣長俊了,另一個(gè)肯定很快也會(huì)回來的。大少爺回來時(shí),一定好事成雙,他準(zhǔn)能給您帶回來一個(gè)又俊又賢惠的孫媳婦,說不定還有一個(gè)大胖重孫子呢。”
穆老太太這才破涕為笑,擦擦眼淚,說:“你這妮子,就是嘴甜。要真能抱上重孫子,就是死了,我也樂意。”
這天晚上穆家上上下下熱熱鬧鬧、喜氣洋洋,穆老太太給家里的仆人、店里的伙計(jì)每人賞了兩塊銀圓。家宴上自然是擺滿了穆立民平常愛吃的各種菜肴,穆世軒還讓人在頭進(jìn)院子的廂房里給伙計(jì)、仆人們也擺了兩桌酒席。穆老太太想起來周雙林剛替自己去臥佛寺上香還愿,二孫子就回家了,真是佛祖顯靈。這周雙林功勞不小,穆老太太給了他加倍的賞錢。
這天的家宴一直到了將近午夜才散,穆立民回到自己從前在中院的西廂房休息。綢緞莊的伙計(jì)們回到店堂里,他們還都沉浸在整個(gè)宅院的鬧騰氣氛里,相互打鬧著,對(duì)比著各自銀圓的成色。周雙林在老位置鋪開被褥,仰面躺下,心想我先見到的是大少爺,結(jié)果卻是二少爺先回家了。大少爺那天在臥佛寺外面說過幾天就回家,他應(yīng)該很快就回來了。
第二天一早,穆世軒命周雙林出門去煤市街的永和車廠雇來了一輛帶司機(jī)的汽車,先送穆立民去燕京大學(xué)問能否入學(xué)的事情,又派三亭子上街采買了些香燭供品。從燕京大學(xué)回來后,他帶著穆立民和周雙林去了右安門外穆家的祖墳,給穆家列祖列宗掃墓上供。
這天是陰天,氣溫驟降,北風(fēng)裹著鋪天蓋地的寒氣,席卷了北平城。一陣陣的寒風(fēng),從前門直沖過來,形成一股股穿堂風(fēng),尖嘯著穿過前門大街,直撲向永定門那高大厚實(shí)的城墻。前門大街上自然是空無一人,大柵欄、珠市口、天橋一帶的商家,也都緊閉了大門。人們躲在房里,圍在煤爐旁聽著門窗被吹得噼啪作響,想著眼下這國土淪喪的境況不知何時(shí)才是終了,心里更是一陣陣沒著沒落的。城里一片嚴(yán)寒,若是到了城外,四下無遮無擋,更是寒風(fēng)刺骨,讓人苦不堪言。
穆家祖墳所在的這塊墳地,是珠市口一帶的大店鋪合伙買的,誰家有人過世,都可以安葬在這里。這也是北平城里殷實(shí)的店鋪常用的法子。這天是日軍占了北平城后,穆世軒半年來第一次出城。他下車一看,只見這里已經(jīng)比半年前添了不少新墳。有的新墳立了墓碑,墳頭也很平整,四周圍了磚廓,一看就是富裕人家的墳。有的只是一個(gè)土堆,墳頭插了紙幡,一看就知道埋的是窮人。這些窮人自然是沒有自家的墳地的,他們死了,家人在城外隨便挖個(gè)坑埋掉。
有的墳連土堆都沒了,尸體因?yàn)槁竦脺\,棺材薄,被野狗拖了出來。至于那些連棺材都沒有,只是裹在破草席里的尸骨,更是早就被野狗啃食干凈,只剩下幾塊殘骨。
半年間添了這么多新墳,這是往年沒有過的事。任憑誰一看都猜得出,這些尸骨一定是去年日軍攻城時(shí)死的老百姓。
穆世軒鐵青著臉,一句話沒說。他和穆立民兩人在穆家?guī)孜蛔嫦鹊膲炃吧狭斯┢罚瑹^了黃紙,磕完頭,就回到城里。
汽車剛剛開到天祥泰綢緞莊門口,兩人在車?yán)锞涂吹酵饷嬲局鍌€(gè)人。其中一個(gè)是負(fù)責(zé)珠市口這一帶巡邏的巡警翟二,另一個(gè)膚色白凈,穿著藍(lán)布長衫,外面罩著一件棉馬褂,看起來很面生。后面一個(gè)則西裝筆挺,頭發(fā)梳得整整齊齊,面孔又白又瘦,眼鏡戴在這張臉上,就像掛上兩個(gè)墨水瓶瓶底。西裝男人身后一左一右,則是手持步槍的日軍士兵,他們的步槍都上了刺刀。
穆世軒父子和周雙林下了車,周雙林對(duì)那個(gè)巡警說:“翟二,這兩位是?”
翟二扭過臉,堆出一臉笑,說:“穆老爺,周二哥,二位好。”接著,他笑瞇瞇地看著穆立民,說,“這位是二少爺吧?真成大人了。”接著他指著身后的兩個(gè)人說,“這位關(guān)孚仁關(guān)先生,是治安委員會(huì)的。這位是稻口德夫先生,是皇軍特務(wù)機(jī)關(guān)處的,在情報(bào)課任職。”
日軍占據(jù)北平后,扶持大漢奸王克敏成立了臨時(shí)政府,治安委員會(huì)是其中極有權(quán)勢(shì)的要害部門,動(dòng)輒以通敵為名,把市民抓走拷打,不少市民最后莫名其妙失蹤,活不見人死不見尸。
日軍的特務(wù)機(jī)關(guān)處,更是整個(gè)北平城實(shí)際的統(tǒng)治中心,機(jī)關(guān)長喜多誠一手下的情報(bào)課課長森本嶠是不折不扣的殺人魔頭。早在盧溝橋事變前,森本嶠就派出特務(wù)混進(jìn)北平,搜集駐守北平的二十九軍兵力部署、武器配備等各種絕密情報(bào),暗殺了二十九軍多名軍官。日軍進(jìn)城后,他更是四處搜捕抗日志士。特務(wù)機(jī)關(guān)處所在的煤渣胡同,總是徹夜傳出拷打的慘叫聲,把周圍百姓嚇得心驚肉跳。
這個(gè)稻口德夫,看到穆世軒他們回來,先是緊緊盯了一會(huì)兒穆立民,然后一指那輛黑色轎車,嘴里嘰里呱啦說了起來。等他說完,關(guān)孚仁說:“穆老先生,稻口先生說,皇軍有命令,凡是從外地返回北平的市民,一律要由特務(wù)機(jī)關(guān)處情報(bào)課進(jìn)行甄別,然后才發(fā)良民證。您這位二少爺不是剛從外地回來嗎?就請(qǐng)跟我們走一趟吧。”
穆世軒冷冷地說:“北平又沒有封城,從外地進(jìn)城的,如今是比以前少了,但每天少說也有上千人。特務(wù)機(jī)關(guān)處要把這些人都抓進(jìn)去嗎?”
關(guān)孚仁說:“穆老先生,令郎和別人不一樣,我們知道,他是早就離開北平了,孤身在外多年。這種情況,皇軍肯定要詳細(xì)了解他這幾年的情形。您放心,他到了情報(bào)課,只要如實(shí)供述,我可以打包票,他一定能平平安安地回來。”
穆世軒還要再說什么,穆立民說:“爹,你別擔(dān)心,我就跟他們?nèi)ァN疫@幾年的經(jīng)歷,就是昨晚我說的那些。”說完,他轉(zhuǎn)身走向那輛黑色汽車,打開車門坐了進(jìn)去。
稻口德夫點(diǎn)點(diǎn)頭,但他并沒有回到汽車,而是繼續(xù)對(duì)穆世軒嘰里呱啦說了一陣。關(guān)孚仁翻譯說:“按照特務(wù)機(jī)關(guān)處的慣例,還要搜查穆立民的住處。”穆世軒剛要擋在門前,心里又想,這會(huì)兒母親和夫人都去東安市場了,家里沒女眷。還不如趁著這會(huì)兒,讓他們搜完,這件事就算過去了。
“得罪了!”關(guān)孚仁見他一遲疑,馬上朝他一拱手,帶著稻口德夫和那兩個(gè)日本兵從店門鉆了進(jìn)去。
翟二也想跟進(jìn)去,但一看到穆世軒冷冷的神情,笑了笑,呆立在一旁。
過了十幾分鐘,這幾個(gè)人出來了。關(guān)孚仁臉色有些尷尬,朝穆世軒拱拱手,說:“穆老先生,得罪了。”稻口德夫和兩個(gè)日本兵在穆世軒面前趾高氣揚(yáng)地走過去,稻口德夫鉆進(jìn)汽車,那兩個(gè)日本兵則一左一右站在汽車兩側(cè)的踏板上。
穆世軒心想,自己和臨時(shí)政府從無交往,要救兒子,還得指望這個(gè)關(guān)孚仁。他從懷里掏出一沓鈔票,塞到關(guān)孚仁手里。關(guān)孚仁一看票面上的數(shù)字和中央銀行字樣,心里一喜,微微做了個(gè)揖,壓低聲音說:“我一定不讓二少爺受罪!”
汽車發(fā)動(dòng)起來開走了。穆世軒回到店里,看到店里倒是一切如常。可等他回到家中,卻發(fā)現(xiàn)不但穆立民的臥室里各種書籍衣物都被扔了一地,就連穆老太太和自己的臥房,還有堂屋、廚房各處都被翻得亂七八糟,凡是被褥都被刺刀捅了很多窟窿。
一陣哭喊聲從院中傳來,穆世軒趕緊跑出去。只見穆老太太正在院子里拿拐杖用力杵著地面喊:“我的二孫子,是誰把我孫子抓走了?”
穆世軒不敢直說是日本特務(wù)抓走了穆立民,只得說臨時(shí)政府派人請(qǐng)穆立民去登記,好給他發(fā)良民證。
穆老太太自然不信,說家里就像是遭了土匪搶劫一樣,如果是規(guī)規(guī)矩矩把人請(qǐng)去,怎么會(huì)弄成這樣?“伙計(jì)跟我說了,是日本特務(wù)沖進(jìn)來到處搜查的,立民是讓這些禽獸抓進(jìn)特務(wù)機(jī)關(guān)去了。那可是個(gè)地地道道的閻王殿啊!去了那里,人還活得了嗎?我這孫子好不容易才回來,要是有個(gè)好歹,我也不活了!”
穆夫人在一旁也不停地抹眼淚。她打發(fā)袖兒給老太太換上一套新被褥。
當(dāng)天晚上,穆世軒夫婦坐在桌邊,愣愣地看著飯菜,誰也沒心思動(dòng)筷子。眼看飯菜全涼透了,穆世軒嘆了口氣,剛要說點(diǎn)什么,袖兒忽然闖進(jìn)來說:“老太太原本坐在床邊掉眼淚,忽然一頭歪過去,就說不出話來了!”幸好永和車廠那輛汽車還在,穆世軒趕緊把她送進(jìn)協(xié)和醫(yī)院。洋大夫先是給她吸痰,接著給她輸了液。這幾天她一直在病床上躺著。穆立民到了第三天才回來。他聽說奶奶進(jìn)了醫(yī)院,趕緊趕到醫(yī)院。穆老太太一看見他,就把他摟進(jìn)懷里,大哭了幾聲,又把他從頭到腳看了一遍,確信他安然無恙,這才放心。她當(dāng)天就出了院。
回到店里,穆世軒夫婦一是因?yàn)槔咸桨渤鲈海且驗(yàn)槟铝⒚衿桨矚w來,又給伙計(jì)和仆人們發(fā)了賞錢。穆立民說:“被抓到煤渣胡同后,日本特務(wù)先是審問我,讓我招供這兩年多在外漂泊的經(jīng)歷,重點(diǎn)問的是遇見過哪些人、有沒有參加各種組織,連審了兩天兩夜才讓睡覺。最后一天則是讓寫良民狀子,大意是愿意效忠大日本帝國、效忠臨時(shí)政府、效忠北平特別市之類。”穆老太太問他有沒有被特務(wù)拿皮鞭抽、拿烙鐵燙,他說那倒沒有,一批接一批被抓進(jìn)去的人很多,他們顧不上都細(xì)細(xì)審問每個(gè)被抓的人,他只是因?yàn)槌鲅皂斪玻淮蜻^幾記耳光。穆老太太和穆世軒夫婦這才放了心。
在外院廂房里,穆世軒也給幾個(gè)伙計(jì)開了一桌。周雙林一邊抿著酒,一邊盤算著時(shí)間,心想在城外遇見大少爺已經(jīng)過去六天了,他為何還遲遲不回來。
第二天早上,一家人吃罷早飯,仆人過來收拾了碗筷桌椅,穆世軒接過手巾擦好了手臉,對(duì)穆老太太說:“娘,我?guī)Я⒚竦浇稚献咦撸俚降昀锶タ纯础!?/p>
穆老太太知道這是要給孫子講生意上的事,點(diǎn)點(diǎn)頭,說:“你們有正經(jīng)事,我不攔著。可外面街上也不太平,讓雙林他們跟著你們?nèi)ァ!?/p>
穆立民給奶奶端上茶,就跟著父親出了家門。周雙林、三亭子和另外一個(gè)伙計(jì)則在后面緊緊跟著。
他們到了街面上,珠市口這邊有寥寥幾家店鋪開門營業(yè)。灑水車在路中間慢悠悠地開著,行人大都面帶愁容,衣衫破舊。也有幾人身穿新長衫或者西裝大衣,他們的大衣還帶著毛皮翻領(lǐng),臉上泛著紅光,顯然是在日本人手下做事。
有一個(gè)女人,兩只手都是通紅的,一只生滿了凍瘡的手里,緊緊端著一個(gè)粗陶大碗,碗里的粥早沒了熱氣,一看就知道她是從天橋那邊的粥廠里剛領(lǐng)到了救濟(jì)粥,要端回去給一家人喝。女人身后跟著一個(gè)孩子,孩子餓得哇哇直哭,女人只好蹲下,把粥碗湊到孩子嘴邊。孩子吸溜了一兩口,女人就把碗拿開。那孩子哭得更厲害了,伸手去抓,結(jié)果那碗掉在地上,摔成幾塊,粥也流了一地。女人愣了愣,立刻跪在地上大哭,孩子卻不懂事,趴在地上伸出手指,撮起米粒放到嘴里。
穆世軒搖搖頭,低聲對(duì)一個(gè)伙計(jì)說:“你帶他們娘倆到家里拿幾個(gè)饅頭,再拿只燒雞給他們。”
那伙計(jì)帶著那對(duì)母子走了,穆世軒指著那幾個(gè)開門營業(yè)的店鋪說:“你們看那幾家店。有的店是架不住日本人和臨時(shí)政府的人整天去威脅才開店的。有的店有人被抓進(jìn)憲兵隊(duì),不開店就不放人,東家實(shí)在沒招了,這才開了店,不過也是開得晚關(guān)得早。也有幾家店,是實(shí)在沒進(jìn)項(xiàng)了,家里坐吃山空,只好開門做點(diǎn)生意。有的藥店、糧食店開了門,是因?yàn)榭腿穗x不了,誰家能不吃藥、不吃飯?這些都是沒辦法的事,誰也不能怨他們。”
穆立民說:“爹,那咱家……”
穆世軒說:“咱家自從日軍進(jìn)了城,就沒正式開過店門。可咱家的生意還在照做,這天祥泰的招牌,畢竟立了一百多年了,那些老主顧信得過咱們,他們來進(jìn)貨,我隨身帶幾塊貨樣子,請(qǐng)他們到正和居喝兩盅,或者去長清池泡個(gè)澡,他們就肯要貨。這陣子,我做成了好幾宗大生意。所以咱家雖然散客的生意做不成了,但還能撐得住。”
三亭子在旁邊說:“二少爺,老爺這招太厲害了,既沒開店門,不讓日本人臉上有光彩,還照顧了老主顧,店里也有進(jìn)項(xiàng)。”
穆世軒說:“日軍進(jìn)城前,天祥泰的生意也這么做,只不過當(dāng)時(shí)既做大宗生意,又做散客生意。立民,這做生意,可不光是店里面的事,還得知道店外面的事,知道天下大勢(shì)。你看現(xiàn)在窮人多,進(jìn)貨的時(shí)候,就不能光進(jìn)綾羅綢緞、呢子毛皮,要多進(jìn)一些經(jīng)穿耐用的,價(jià)格還不能高,這樣窮人才用得起,咱們也對(duì)得起自己的良心。而且便宜布料走貨走得快,不占本錢,這要是進(jìn)上一庫房的貂皮,一時(shí)又出不了手,店里就周轉(zhuǎn)不開了。”
穆世軒帶著他們沿著前門大街一路走著,邊走邊說各個(gè)字號(hào)經(jīng)商的竅門。快到鮮魚口時(shí),周雙林壓低嗓子,指著旁邊一條胡同的深處說:“老爺,這里面有家鐵匠鋪,您記得吧?”
穆世軒點(diǎn)點(diǎn)頭說:“我記得,他家打的鐵器不錯(cuò),可惜那個(gè)鐵匠是個(gè)啞巴,他在這里租房子打鐵,干了有三四年吧,咱們連他姓什么都不知道。最近可有日子沒他的消息了。”
“他不是鐵匠,他是——”周雙林把頭湊得更近些,聲音也壓得更低,“有人說他是日本特務(wù)。剛?cè)肱D月那陣子,有人發(fā)現(xiàn)他死在西便門外的荒地上。聽說他是被人反綁了雙手,腦門中了一槍。”
“日本特務(wù)?啞巴也能當(dāng)特務(wù)?”穆世軒雖然見多識(shí)廣,但聽到這里也吃了一驚。周雙林說:“前幾天,我不是替老夫人、夫人去臥佛寺還愿嗎?那天我和幾個(gè)客商一起出西直門,其中有個(gè)做山貨生意的客商,他平時(shí)老從山里買些野兔山雞之類的到城里賣。他說那個(gè)鐵匠經(jīng)常在房山、門頭溝一帶的山里轉(zhuǎn)悠,那邊煤礦多,他把各處煤礦都畫進(jìn)了地圖。日軍進(jìn)城后,他把地圖交給了日軍。而且他也不是啞巴,日本話說得可溜了。”
穆世軒說:“怪不得這家鐵匠鋪以前就時(shí)常歇業(yè)。日本為了‘滅亡中國’,早已處心積慮。中國各處有什么資源,哪里出煤,哪里產(chǎn)糧食,哪里宜駐兵,哪里宜開礦,地方首腦的賢愚忠奸,早已被他們查得清清楚楚。可我們這個(gè)國家里那些掌握重兵大權(quán)的,只會(huì)鉤心斗角、爾虞我詐,誰真正愿意為國家的事操心出力?山東那個(gè)韓復(fù)榘,明明有黃河天險(xiǎn)作為防線,他都怕?lián)p失實(shí)力,帶著隊(duì)伍逃跑了,把整個(gè)山東,把幾十萬濟(jì)南百姓扔給日本人,真是民族敗類!照我說,這條前門大街上,日本特務(wù),肯定不止這個(gè)鐵匠,還有一些人。”
“雙林哥,那誰殺了這個(gè)特務(wù)?”三亭子問。
周雙林說:“這誰知道啊?那肯定是高人干的。而且這位好漢對(duì)北平城一定非常熟悉。從西便門出城往房山、良鄉(xiāng)方向,有片樹林是一處偏僻地方,別處都是大路。在那里行兇,完事后再回城里,來回用不了一頓飯的工夫。”
三亭子一拍大腿:“咱這北平城里,日軍安插了不少特務(wù),可咱們的人也不少!”
他們幾人在前門大街結(jié)結(jié)實(shí)實(shí)地轉(zhuǎn)了一圈,回到店里,已經(jīng)是飯點(diǎn)了。一家人吃了午飯,穆世軒陪母親說了一會(huì)兒話,就回到房里休息。這兩天因?yàn)槔咸≡骸⒛铝⒚窕丶业氖拢倭瞬簧傩模@會(huì)兒精神有些倦怠,很快就睡著了。
這一覺他睡得很沉、很長,斷斷續(xù)續(xù)做了幾個(gè)夢(mèng),并且結(jié)結(jié)實(shí)實(shí)扎進(jìn)最后一個(gè)夢(mèng)里。等他醒過來,發(fā)現(xiàn)窗臺(tái)上已經(jīng)布滿了夕陽金黃色的光線。他準(zhǔn)備起床,卻發(fā)現(xiàn)頭怎么也抬不起來,滿枕頭都是汗?jié)n。他摸了摸自己的額頭,水淋淋的,還很燙。這時(shí),穆太太端了杯水進(jìn)來,嗔怪著說:“立民在店里等你教他看賬本,都等了一個(gè)多——”穆太太話沒說完,臉色就變了,說,“老爺,你臉色怎么這么差?”穆太太伸手來摸他的額頭,他覺得太太的手涼得很。他知道自己這是病了,努力想坐起來,可身上一點(diǎn)勁都沒有,身子又一歪,暈了過去。
穆世軒被送進(jìn)了協(xié)和醫(yī)院。這次住院一連住了三天,燒才退了下來,一家人連元宵節(jié)都沒得正經(jīng)過。這天醫(yī)生查完床,說他下午就可以出院了。中午他正準(zhǔn)備打個(gè)盹,卻影影綽綽地看到病床邊站著個(gè)年輕人。他乍一看,以為是穆立民。可再仔細(xì)一看,這年輕人雖然長得和穆立民很像,但留起了兩道小胡子,下巴也更方一些,個(gè)子也比穆立民高了一兩寸。穆立民雖然在外面闖蕩了幾年,但二十出頭的年紀(jì),臉上還是有些嬰兒肥。這人的臉卻更瘦一些。
“立民怎么一下子長了好幾歲?”他沒想到的是,年輕人在他床頭慢慢跪了下來。
“爹,是我,我是興科,我回來了。孩兒不孝,這些年讓奶奶,讓您和我娘,都為我擔(dān)心了。”這年輕人流著眼淚,隔著棉被趴在他膝蓋上。
“回來了就好,回來了就好。”他大病初愈,心里再激動(dòng),也沒力氣表示什么,只好摸著年輕人的頭,慢慢地說。病房門口,他的太太正靠在門框上,用手帕擦著眼淚,用哭得通紅的眼睛看著他們。
下午穆世軒出了院,一家人回到家里。穆興科重新給奶奶、父母磕頭,又在飯桌上說了自己這十年來的經(jīng)歷:“當(dāng)年北伐軍打到了北平,孩兒見國民革命軍軍容整齊、士氣高昂,就一門心思想入伍。我離家后,真的加入了國民革命軍,但我萬萬沒想到的是,南京政府只是在名義上統(tǒng)一了中國,軍閥混戰(zhàn)的局面并沒有根本改變。蔣介石以‘國軍編遣會(huì)議’的名義,要所有地方軍閥交出兵權(quán),好建立他的獨(dú)裁統(tǒng)治。擁兵自重的軍閥自然不答應(yīng),他們又打起了‘中原大戰(zhàn)’,互相攻擊起來,這下老百姓又遭了殃。我看透了這幫軍閥的嘴臉,看出來他們個(gè)個(gè)只在乎自己的地盤,誰不也真正拿國家民族的前途當(dāng)回事。那時(shí)知識(shí)界很多人都在思考,同樣是國家,日本為什么能這么快富強(qiáng)起來?為此那幾年去日本留學(xué)的年輕人很多。我一氣之下也脫下軍裝出國留學(xué),到了日本。后來日軍占領(lǐng)了東三省,在日本的中國留學(xué)生更是經(jīng)常被日本人嘲笑毆打。日本的報(bào)紙上整天都在說要‘滅亡中國’,很多中國留學(xué)生忍不下去,不少都回國了。但我想,日本越是要‘滅亡中國’,我越是要在日本待下去,要弄清楚他們的底細(xì),弄明白他們究竟在哪里比中國強(qiáng),為什么比中國強(qiáng)大。一直到了前年,眼看日本要全面侵華,每天都有留學(xué)生同學(xué)被日本警察抓走,我才決心回國。回國后,我先去南京國民政府,把我在日本了解到的情況告訴他們。他們根本不相信我,還要把我當(dāng)共產(chǎn)黨抓起來。我趕緊逃跑。后來我在全國各地周游了幾個(gè)月,到處都在說延安的共產(chǎn)黨是真抗日,國民黨是消極抵抗,是假抗日。我本想去投奔共產(chǎn)黨,可我好不容易到了西安,因?yàn)閼?zhàn)事交通都中斷了,再也沒法往前走了。我在西安待了一陣子,就回來了。”
穆老太太說:“我的孫兒,你當(dāng)初從家走的時(shí)候,都沒帶多少錢,這么多年你是怎么過來的?”
“我去日本時(shí),考取的是官費(fèi)留學(xué)生,自己不用花錢。后來回了國,我在廣州、西安、青島這些地方給有錢人當(dāng)家庭教師,也能掙到錢。奶奶,你放心吧,這些年雖然兵荒馬亂,但我沒吃什么苦。”穆興科說。
穆世軒聽完以后,說:“袖兒,前幾天二少爺剛一到家就被日本特務(wù)抓走了,你給大少爺預(yù)備一下衣物,日本特務(wù)大概很快就要上門了。”
穆立民搶著說:“爹,你住院這幾天,我哥已經(jīng)在日本特務(wù)機(jī)關(guān)里待了兩天了。”
見穆世軒愣住,穆興科說:“爹,我是三天前回到家的。當(dāng)時(shí)我去醫(yī)院里看您,您一直在昏迷。我剛從醫(yī)院回家,就被日本特務(wù)抓走了。我?guī)Щ丶业男欣睿脖凰麄兺绷藗€(gè)稀巴爛。我的被褥都被日軍拿刺刀捅了幾十個(gè)窟窿。”
穆立民說:“爹,我遭過的罪,我哥都已經(jīng)挨過了。以后啊,他就可以安安生生地在家待著了。”
穆興科說:“爹,剛才在汽車上我就該給您說的,不曾想您一路上一直惦記著這件事,飯都沒吃好。”
穆世軒點(diǎn)點(diǎn)頭說:“那就好,那就好。”
穆老太太見飯吃得差不多了,說:“興科、立民,你們哥倆送你們父親回房歇息吧。”
穆興科、穆立民起身伺候穆世軒洗漱完畢,就陪他回房了。看著父子三人的背影,穆老太太又抹開了眼淚:“都是祖宗保佑,穆家算是一家團(tuán)圓了。”
穆夫人眼圈也是紅紅的,說:“娘,我陪您給祖宗上炷香吧。”
穆興科的臥房,在二進(jìn)院子的東廂房,和穆立民的臥房正對(duì)著。這天晚上,穆興科回到自己房里,他雖然已經(jīng)回家三天,可因?yàn)閯傔M(jìn)家門就被日本特務(wù)抓走,這還是第一天在自己臥房睡。他看著房里的陳設(shè)還和自己離家前的一樣,只有被褥因?yàn)楸蝗哲姶唐屏耍謸Q了一套新的。自己桌上的幾件破了的擺設(shè),一個(gè)鐵皮文具盒,一個(gè)竹子筆筒,都用膠布細(xì)細(xì)粘好了。
“大少爺,您可算回來了!自打那天在臥佛寺外頭見著您,這幾天我一直盼著您呢。”周雙林端著火盆進(jìn)來說,“大少爺,晚上冷,得用火盆烤火。”
穆興科點(diǎn)點(diǎn)頭,蹲下來烤火。周雙林說:“對(duì)了,屋里生了火,您肯定會(huì)口渴,我端杯茶來。”說著他也不等穆興科答應(yīng),轉(zhuǎn)身就出了門。很快他端了杯茶進(jìn)來。穆興科接過茶杯喝了幾口,就把茶杯放在桌上,蹲下來繼續(xù)烤火。周雙林也蹲了下來,看著穆興科的每一個(gè)動(dòng)作。穆興科被看得有些不太自然,說:“雙林,你盯著我看什么?”
周雙林一咧嘴說:“大少爺,您胳膊上的傷看來一直沒好利索,咱家旁邊的長春堂,大柵欄那兒的葆順堂,這陣子都有名醫(yī)坐診,明兒我陪您去瞧瞧?”
穆興科停下手上的動(dòng)作,說:“雙林,你怎么知道我胳膊上有傷?”
周雙林嘿嘿一笑,說:“大少爺,您是我從小看著長大的,您打小都是用右手,這回成了左撇子,肯定是因?yàn)橛腋觳彩軅恕!?/p>
“我離家都十年了,這么長時(shí)間,人是會(huì)變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慢慢就變成了左撇子了。”穆興科說。
“大少爺,您瞞不了我。您是十八歲那年離家的,那時(shí)您都成大人了,哪能說變就變?而且我特意細(xì)看了,您這右胳膊,不是不如左胳膊好用,而是壓根兒沒法用。那天您無論端茶碗,還是從兜里拿錢,甭管多么不得勁,您用的都是左手。”周雙林說。
穆興科沒說什么,繼續(xù)烤著火。周雙林笑瞇瞇地湊近他,低聲說:“煤渣胡同那個(gè)案子,大少爺,是您干的吧?”
穆興科頭一扭看了他一眼,從桌上抄起本書往床上一躺,看著書,說:“煤渣胡同出了什么案子?我怎么不知道?是哪個(gè)大戶人家被搶了還是被偷了?”
“這通緝令都貼得滿世界都是了,全北平城里,哪條街哪條胡同不貼個(gè)十張八張的?您還裝糊涂?”周雙林臉上笑意愈發(fā)濃了,他朝穆興科豎起大拇指,說,“大少爺,我敬您是條漢子,是英雄!您放心,這事我誰都不說!”
穆興科聚精會(huì)神看著書,隨口說:“編,你就編吧。”
“我周雙林這雙眼,給我塊布頭,我就能知道是哪個(gè)織造廠的貨。我看布從來沒錯(cuò)過,看人啊,也錯(cuò)不了!”
第二天早上,天色又陰沉起來,還下起了雪。穆家兄弟二人進(jìn)了里院。陪穆老太太和穆世軒夫婦吃過早飯后,穆世軒說:“興科,前幾天我已經(jīng)把店里店外的情形給立民說了,我如今大病初愈,精神還不甚好,立民,你今天就把那天我給你講的,再給你哥哥講一遍。”
穆老太太叮囑兄弟倆說:“外面正下大雪,你們爹這次得這么重的病,就是那天上午在街上著涼了,你們可得多穿點(diǎn)。”
兩人點(diǎn)頭答應(yīng),各自回屋穿上厚實(shí)衣服,就出了店門。兩人沿著前門大街往北走,穆興科已經(jīng)離家十年,街兩旁的鋪面有不少已經(jīng)換了,他們走到鮮魚口,穆立民又把日本特務(wù)在這里假扮鐵匠的事兒講了一遍。穆興科沉默片刻說:“日本侵略中國,早就蓄意已久,好幾代日本人都是這么想的。當(dāng)初我在日本留學(xué)時(shí),每個(gè)中國留學(xué)生,日本軍部都會(huì)派人來細(xì)細(xì)詢問,把學(xué)生的家庭、籍貫、性格、志向等情況一一記錄在案。日本的報(bào)紙也經(jīng)常對(duì)中國各地地方官進(jìn)行考評(píng),連中國各地的礦產(chǎn)資源也被日本報(bào)紙逐一分析能給日本帶來哪些好處,好像中國已經(jīng)被納入他們的版圖一樣。眼下國民政府內(nèi)遷到了武漢,我看武漢很快也保不住了,政府還得繼續(xù)西遷。”
穆立民說:“聽說日本有兩個(gè)師團(tuán),在徐州以北的滕縣、臨沂一帶被國軍攔住了,進(jìn)退不得,說不定這次咱們能打個(gè)勝仗。”
穆興科搖搖頭說:“那里的國軍是好幾支雜牌軍湊成的,蔣介石的嫡系部隊(duì)都打不過日軍,雜牌軍還能指望得上?”
“哥,你多給我講講你這些年在外面見過的事吧,尤其是你在日本看到的事。”穆立民說。
穆興科警惕地掃視著四周,只見漫天雪花里,只有稀稀落落幾個(gè)行人,每個(gè)人都在快步疾行,身后大柵欄東口那兒,有幾個(gè)黃包車車夫正縮著肩膀,佝僂著身子,滿懷期待地看著這邊。他想了想,一拽穆立民的胳膊,大步流星地踏上一輛黃包車,對(duì)車夫說:“去陶然亭。”
陶然亭就在永定門西側(cè),黃包車只需十多分鐘就跑到了。這時(shí)雪越下越大,整個(gè)公園杳無人跡,兩人站在陶然亭里,只見亭外湖面已經(jīng)被大雪覆蓋。幾只野鴨躲在湖邊僅有的幾根搖搖晃晃的蘆葦里,緊緊挨在一起。寒氣從湖面襲來,穆立民連打了幾個(gè)噴嚏,穆興科一看,從懷里掏出酒壺遞給他。兩人輪流喝了幾口酒,只覺得一陣暖意從腹中升起,幾乎凍僵的四肢也慢慢暖和了起來。“你還記得咱們最后一次到這里來是什么時(shí)候嗎?”穆興科望著雪景,拿酒壺朝四周指點(diǎn)著說。
穆立民撓撓頭說:“我記得咱們從前常來這兒,最后一次是什么時(shí)候,我還真忘了。”
“那是十三年前,當(dāng)時(shí)這一帶到處是窮人的窩棚,很多無家可歸的人都住在這兒。那年我十五歲,你九歲,當(dāng)時(shí)咱們一起逃學(xué),去天橋看耍把式的。咱們覺得那個(gè)練八卦掌的一定是武林高手,就跟著他到了這兒,要拜他為師。”穆興科說。
“咱們那時(shí)候一門心思想當(dāng)個(gè)武林高手,四海為家,到處行俠仗義、除暴安良。”穆立民說。
穆興科搖搖頭:“不是。咱們那時(shí)覺得中國人被人叫作東亞病夫,是因?yàn)榇鬅煿矶啵烈叩教幜餍校瑖梭w質(zhì)太差。如果能在全國普及武術(shù),國人就能強(qiáng)身健體,國家也就不受人欺負(fù)了。”
穆立民笑了說:“咱們那時(shí)年紀(jì)小,不懂事,不知道國家積貧積弱、國人貧病交加,根源在于國家政體,和武術(shù)普及不普及,實(shí)在沒有太大關(guān)系。”
穆興科看了他一眼說:“你小子,離家出走了兩年,還真長見識(shí)了。”
穆立民說:“哥,你在日本留了幾年學(xué),比我見識(shí)多,你覺得中國要強(qiáng)大起來,到底應(yīng)該效仿哪國政體?”
穆興科說:“這個(gè)問題,我在十年前離家時(shí)就在想,后來到了日本也一直在想。直到有一次我站在一張世界地圖前,看著世界各大強(qiáng)國,終于明白……”
這時(shí),他們身后傳來一陣喊叫聲:“大少爺,二少爺——燕京大學(xué)的錄取通知書寄到了!”
他們回頭看去,只見周雙林站在湖邊,手里正揮舞著什么,站在大雪里朝這邊喊著。
雖然隔著密密麻麻的雪花,兩人仍然能看到他滿臉激動(dòng)的神情。
“哪天開學(xué)?”穆立民隔著湖大聲問他。
周雙林打開手里的信件,看了看,喊:“正月廿二!”
一家人吃晚飯時(shí),兄弟二人一左一右坐在穆老太太旁邊。穆老太太把錄取通知書翻來覆去瞅了一陣子,又直掉眼淚,說:“你這孩子,怎么就這么不顧家呢?這才回來幾天,就要去那么遠(yuǎn)的地方上學(xué)。聽說日本兵凈闖到學(xué)校里抓鬧事的學(xué)生,海淀那么遠(yuǎn)的地方,你要是讓日本兵抓走了,我們連個(gè)信兒都得不到!”
穆立民說:“奶奶,您放心,日本是和中國開戰(zhàn)了,但還沒和美國開戰(zhàn)。我上的這個(gè)燕京大學(xué),是美國人辦的,日本兵根本不敢進(jìn)去。”
“這北平城里還有日本兵不敢進(jìn)的地方?”穆老太太半信半疑。
穆興科盛好一碗銀耳羹放到她面前,說:“奶奶,這是真的。日本兵是占了北平城,可這城里還有一大堆別的國家占領(lǐng)的地方。日本還沒對(duì)這些國家宣戰(zhàn),所以日本兵就不敢進(jìn)這些地方。”
穆老太太還是不放心,說:“這燕京大學(xué)在海淀那么遠(yuǎn)的地方,離這二十多里遠(yuǎn),路又偏僻,那也容易出事兒。”
穆太太說:“娘,您放心吧。到開學(xué)時(shí),世軒會(huì)去永和車廠再雇一輛汽車,把立民送去。”
這頓飯吃完,已經(jīng)是深夜。兄弟倆回到中院,只見周雙林正在掃院里的雪。北平城里,深夜歷來有叫賣宵夜的商販,這時(shí)人們就聽到一陣陣吆喝聲,先是有人喊“蘿卜——賽蜂蜜——蘿卜——賽蜂蜜——”,接著又有人喊“熏魚兒——好下酒——”。穆興科仔細(xì)聽了聽,說:“賣熏魚兒的和賣蘿卜的碰上了,真巧。”穆立民說:“這個(gè)賣蘿卜的真怪,別人吆喝,都是喊蘿卜賽鴨梨,他喊賽蜂蜜,這也太沒譜了。”
兄弟二人離家已久,這次重新聽到聽?wèi)T了的吆喝聲,都是感慨萬千。北平冬夜苦寒,店鋪打烊甚早,天黑后人們沒有別的去處,那些有點(diǎn)閑錢和閑心的,到了深夜如果還不想睡覺,也都愛買點(diǎn)熏肉鹵肉之類下酒小酌。但按照不知何時(shí)起源的規(guī)矩,那些叫賣熏肉鹵肉的,吆喝里卻不帶一個(gè)“肉”字,都喊成“熏魚兒”。
穆興科回到自己屋里,洗漱后熄了燈平躺下,心里想著自己離開家后多年的經(jīng)歷,再想到穆立民在外面漂泊了兩年,如今還能繼續(xù)讀大學(xué),百感交集。過了十多分鐘,剛才的叫賣聲重新喊了起來:“蘿卜——賽蜂蜜——蘿卜——賽蜂蜜”“熏魚兒——好下酒——”那賣熏魚兒的和賣蘿卜的竟然又轉(zhuǎn)了回來。穆興科索性翻身而起,穿好衣服,抄起手電筒到了院外。
“賣熏魚兒的!”他站在臺(tái)階上,朝路對(duì)面一個(gè)背著大紅柜子的人說。那人踩著滿街的雪,大步跑了過來。
“小心滑倒!”穆興科說。那人到了店門外,把紅漆柜子放下,打開柜門,豬蹄、豬頭肉、豬心、排骨,各式各樣的熏肉露了出來。
穆興科稱了一斤熏排骨,用油紙包了快步往家里走。他進(jìn)了大門,把油紙包放在門口的長凳上,騰出手安上了門閂。他轉(zhuǎn)過身剛要去拿油紙包,卻看到了一張笑瞇瞇的人臉。
他嚇了一跳,好在馬上看清了這張臉,他鎮(zhèn)定地說:“立民,這都快到半夜了,你不睡覺在這里干什么?”
“你還問我干什么。你出去干什么了?這是什么?”穆立民指著油紙包說。
“晚上睡不著,買了點(diǎn)宵夜,本來我正打算叫你一起來陪我喝兩盅。”說完,穆興科抓起油紙包,就要從他身旁穿過去。
“哥,我的好大哥,你就告訴我,你離開家去外面,究竟干了些什么吧。”穆立民趕緊跟過來說。
穆興科嘆了口氣,把油紙包往他面前一遞,說:“我到家門外面去,不就是去買了些熏排骨嗎?”
二人進(jìn)了穆興科的屋子,穆立民故意做出一副很夸張的架勢(shì),掀開床單,拉開衣柜,又彎下腰往床下看了看。
穆興科又好氣又好笑地說:“你這臭小子,半夜三更不睡覺,到我這兒來出什么洋相?”
“哥,”穆立民笑容滿面地湊過來說,“你就招了吧。你當(dāng)時(shí)用的那把槍藏在哪里了?你的那幾位同僚都在哪兒藏著?你們組織叫什么名?你是怎么加入的?能讓我也加入嗎?”
穆興科瞪了他一眼說:“臭小子,胡說八道什么呢?我不知道你在說什么。”
穆立民嘿嘿一笑,朝外面指了指,說:“‘蘿卜——賽蜂蜜——’,這就是你們的暗號(hào)吧?”
穆興科繼續(xù)瞪著他,說:“你是不是沒好好讀書,凈看歪門邪道的書了?什么暗號(hào)不暗號(hào)的?”
穆立民大大咧咧地坐在床上,東翻一下西翻一下,說:“哥,你別不承認(rèn),我告訴你,你的身份啊,在我這兒已經(jīng)完全暴露了。我要是把你舉報(bào)到煤渣胡同去,還能從日本特務(wù)機(jī)關(guān)處領(lǐng)到五百塊銀圓的賞錢呢。”
“沒閑工夫理你。”穆興科在桌前坐下,把油紙包鋪開說,“在外漂泊多年,這北平城里,我最想念的就是這京華美食。”他剛要下手去抓排骨,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打開行李箱,從最內(nèi)層摸出一瓶酒來。
“哥,你別裝了。”穆立民從床上站起來,筆直站著,雙目炯炯地盯著他說:“第一,你的樣子和通緝令上的畫像一模一樣;第二,你右臂受傷——”
“我胳膊沒受傷。”穆興科伸出抓著酒瓶的右臂,大幅度揮舞著。
“雙林說他在臥佛寺外遇見過你,你當(dāng)時(shí)只能用左手。你明明早就回到北平了,卻不回家來看奶奶和爹娘,就是因?yàn)槟愀觳灿袀M(jìn)城怕被鬼子發(fā)現(xiàn)。”
“你這也太牽強(qiáng)附會(huì)了。還有第三嗎?”
“不用第三條,我說的這兩條,每一條都不是特別有力,但兩條加在一起,我覺得就八九不離十了。哥,你到底是不是國民政府的人?你就告訴我實(shí)話吧,我是你親弟弟,我保證誰都不說。”
穆興科瞟了他一眼,慢條斯理地抿了一口酒,又從排骨上撕下一塊肉,嚼了一陣子,才抬起頭,望著他,說:“你猜對(duì)了。我現(xiàn)在的身份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huì)調(diào)查統(tǒng)計(jì)局北平第九特遣隊(duì)負(fù)責(zé)人。”
穆立民眼睛里閃動(dòng)著興奮的神采,他試探著問:“哥,那上次煤渣胡同行刺王克敏,真是你們干的?”
穆興科點(diǎn)點(diǎn)頭。穆立民激動(dòng)得站起來說:“哥,你太棒了!和你一起行刺的那些同事都去哪兒了?能讓我也見見嗎?”
穆興科慢慢搖頭:“按照我們的紀(jì)律,每次刺殺行動(dòng)結(jié)束后,不管是否成功,所有人員都必須分散躲藏,等待下一步指令。”
“這么說,你還不知道自己的下一個(gè)任務(wù)是什么。”穆立民問。
“我知道。”
“你知道?你什么時(shí)候知道的?”
“就是剛才。”
“剛才?”
“對(duì)。就在剛才,那個(gè)賣熏魚兒的把下一步的行動(dòng)告訴我了。”說著,穆興科從褲兜里拿出一小沓鈔票,朝穆立民晃了晃,說,“本來里面有張紙條,告訴我下一個(gè)任務(wù)是什么。”
穆立民想了十幾秒,猛地一拍腦袋,說:“我明白了,那個(gè)賣蘿卜的和賣熏魚兒的同時(shí)出現(xiàn),賣蘿卜的吆喝聲與眾不同,這就是你們的暗號(hào),對(duì)吧?”
“基本對(duì)了,但還不精確。在這個(gè)計(jì)劃里,賣蘿卜的總是和賣熏魚兒的同時(shí)出現(xiàn),真正的情報(bào)卻是在賣熏魚兒的那里。這樣一來,就算別人聽到賣蘿卜的吆喝聲不對(duì),在他身上也搜不出什么。”穆興科說。
“這招數(shù)太高了。這么一來,就算有人覺得那個(gè)賣蘿卜的可疑,也絕對(duì)想不到真正重要的,其實(shí)是他旁邊那個(gè)賣熏魚兒的。”穆立民喃喃說著,往后一仰,倒在床上。
“你這傻小子,腦子轉(zhuǎn)得還挺快。”穆興科不動(dòng)聲色地打量著他,說,“既然你是一二·九運(yùn)動(dòng)時(shí)離家出走的,那你也算是個(gè)愛國青年了。怎么樣,你愿意不愿意加入抗戰(zhàn)的隊(duì)伍,為國家、為民族出一份力?”
穆立民一骨碌爬起來,抓住穆興科的手,說:“哥,你是說我能加入你們的組織嗎?”
穆興科慢吞吞地說:“我只是問你愿不愿意加入,你要是愿意呢,我就考察你一下。你如果通過考察了,就可以加入了。再經(jīng)過一些訓(xùn)練,你就可以執(zhí)行任務(wù)了。”
穆立民興奮地說:“沒問題,沒問題,怎么考察我都行。”
穆立民纏著穆興科,讓他告訴自己一些特工如何執(zhí)行任務(wù)的事。穆興科說今天太晚了,改天再說,讓他趕快回去睡覺。穆立民只得答應(yīng),但還是興奮得直攥拳頭,兩只眼睛里的光越來越亮了。他正要出門,坐在椅子上的穆興科忽然扭過臉,沖著他的背影說:“立民,幸虧你答應(yīng)加入我們。”
穆立民轉(zhuǎn)過身,笑嘻嘻地說:“哥,如果我不加入你們,按照組織的紀(jì)律,你怎么辦?”
“很簡單,把你殺了。既然你已經(jīng)察覺到我的身份,那么我就必須殺了你,這是組織的規(guī)定。”穆興科不動(dòng)聲色地說。
“啊,這么殘忍?”穆立民直吐舌頭。
“這是情報(bào)工作的需要,必須如此。”
“我的老天爺,可怕,太可怕了。不過,這才過癮!”穆立民打開門,輕聲哼著歌,踩著落滿整個(gè)院子的雪花,快步走回自己屋子。
穆興科熄了燈,躺在被窩里,回想著穆立民答應(yīng)加入組織時(shí)的激動(dòng)神情,長長地出了一口氣。
正月廿二這天,燕京大學(xué)正式開學(xué),穆立民去學(xué)校時(shí),穆世軒雇了輛汽車,把穆立民的行李裝上,然后叫穆興科和穆立民一起上車。穆老太太和穆夫人正準(zhǔn)備上車,但穆世軒告訴她們:“如今路上不太平,女眷還是少出門為好。”穆老太太說:“坐在車上沒有什么可擔(dān)心的。”穆世軒說:“如今城外盜匪橫行,別說行人,他們連汽車都敢劫。他們只要先在路上撒上鋼釘或者砍倒一棵樹擺在路上,就能把汽車逼停。荒郊野外的肯定是叫天天不應(yīng),叫地地不靈了。”
穆老太太和穆夫人只好作罷。他們父子三人上車遠(yuǎn)去。當(dāng)天晚上,穆世軒和穆興科回來后,穆老太太自然刨根問底,把燕京大學(xué)里的情形,比如學(xué)校里到底安不安全,女生多不多,食堂里的飯菜豐盛不豐盛,問了個(gè)清清楚楚。穆興科告訴她:“燕京大學(xué)是美國傳教士辦的大學(xué),日本人要是敢進(jìn)去抓人,美國大使館一定會(huì)抗議的,非得引起外交糾紛不可。穆立民在那里上學(xué)比在城里安全多了。”對(duì)于女生多不多的問題,穆興科是這么回答的:“奶奶,燕京大學(xué)里女生可是真不少,而且能把女孩兒一直供讀大學(xué)的,家里肯定非富即貴,跟咱們家倒是門當(dāng)戶對(duì)。他們學(xué)校里提倡自由戀愛,憑立民的條件,交個(gè)女朋友那是不在話下。可有一樣,奶奶,我得給您提個(gè)醒,那里的女大學(xué)生個(gè)個(gè)都新派得很,個(gè)個(gè)英語說得呱呱叫,都想著以后去美國留學(xué)。她們要是非得讓立民陪著去美國,那他們到了美國那個(gè)花花世界,百分之百就不想回來了。到了那時(shí),您就算有了重孫子,可隔著千山萬水的,您想抱也抱不著,這不就成了遠(yuǎn)水解不了近渴嗎?”
穆老太太開始還是眉開眼笑,越往后聽越擔(dān)心,聽穆興科說完,已經(jīng)是心驚膽戰(zhàn),不停地絞著衣角了。穆夫人笑著在穆興科脖子上掐了一把,說:“你這孩子,別貧嘴,凈嚇你奶奶。我可告訴你,你也快三十了,過一陣子,等城里的形勢(shì)安穩(wěn)些了,可得請(qǐng)媒人給你說一房媳婦了。”穆興科嚇得趕緊低頭吃飯。穆老太太又琢磨了一陣子,才納悶地說:“那些女孩子要去美國留學(xué),又不是去英國,干嗎把英語說那么好?能管用嗎?”
三天后,穆興科奉穆老太太和穆夫人之命去燕京大學(xué)看望穆立民。穆立民卻不在宿舍,他舍友說他和一群同學(xué)去了頤和園。穆興科趕過去時(shí),穆立民正在昆明湖上溜冰。穆立民遠(yuǎn)遠(yuǎn)看到穆興科沿著湖岸走過來,便踩著冰刀飛快地溜了過來。
兄弟二人踩著滿地的荒草和積雪,一起朝燕京大學(xué)的方向走著。開始還能看到幾個(gè)行人,等二人越走越遠(yuǎn),周圍漸漸寂靜下來,就再也看不到人影了。穆興科低頭沉思了一陣,說:“你的同學(xué)對(duì)你挺親熱的,看不出你小子這么快就能混出好人緣來。”
“抗戰(zhàn)爆發(fā)后,他們一直在北平,不知道城外的情況,就一直纏著我問。你放心,對(duì)那些同學(xué),我什么也沒說。”穆立民說。
穆興科點(diǎn)點(diǎn)頭。西郊這一帶遠(yuǎn)離市區(qū),本來就荒僻,如今天寒地凍,加之兵荒馬亂,四周更是一片空曠。偶爾有只小獸,也看不清楚是黃鼠狼還是貍貓,在他們面前倏忽而過,轉(zhuǎn)瞬間就進(jìn)了荒草叢。
“穆立民,你真的愿意加入組織?”穆興科問。
穆興科停下腳步,雙目炯炯地盯著穆立民。穆立民使勁地點(diǎn)點(diǎn)頭。穆興科說:“好,現(xiàn)在國家處于危難之中,正是用人之際。組織章程里本來就有一條,凡是組織成員,在執(zhí)行任務(wù)過程中,須以完成任務(wù)為最高宗旨,若為完成任務(wù),可以隨時(shí)發(fā)展臨時(shí)成員。既然你已下定決心,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huì)調(diào)查統(tǒng)計(jì)局北平第九派遣隊(duì)負(fù)責(zé)人穆興科,現(xiàn)根據(jù)任務(wù)需要,發(fā)展北平市民穆立民為本派遣隊(duì)臨時(shí)隊(duì)員,考驗(yàn)期自即日起開始計(jì)算,為時(shí)三個(gè)月。”
穆立民興奮得攥緊拳頭,說:“哥,既然你同意我加入組織,你就盡管給我安排任務(wù)吧。”
“你剛剛加入組織,組織里的各項(xiàng)條例,我會(huì)一一介紹給你。但現(xiàn)在我們有個(gè)緊急任務(wù)需要完成。”
穆興科說著,從懷里取出一張照片。穆立民接過來,只見上面是一個(gè)身穿西裝打著領(lǐng)結(jié)的男人。穆興科說:“這人名叫路文霖,男,三十七歲,現(xiàn)任北平治安委員會(huì)行動(dòng)處處長。他就是我們下一個(gè)清除的對(duì)象。”
“一個(gè)處長?”穆立民問,“咱們?yōu)樯恫恢苯尤?huì)長?”
“傻小子,你猜會(huì)長是誰?”穆興科摸出打火機(jī),把照片燒掉,望著照片上徐徐燃燒的火苗說,“就是現(xiàn)在的北平特別市市長江朝宗。”
穆立民眼睛更亮了,說:“那咱們干脆去殺江朝宗!”
穆興科瞪了他一眼,說:“從事諜報(bào)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嚴(yán)格執(zhí)行上峰命令,絕不能自作主張。這一條你要牢牢記住,絕不能忘。”
穆立民趕緊連連點(diǎn)頭,穆興科又遞給他一沓文件。這是一沓影印件。這些文件都沒有抬頭,第一份文件上,只有一行字:
茲有治安委員會(huì)行動(dòng)處張華定、李金海,奉命處決匪諜謝大壽、韓茂,尸體現(xiàn)場照相后就地焚燒掩埋。
落款是北平治安委員會(huì)行動(dòng)處處長路文霖。
穆立民又翻了翻后面的文件,內(nèi)容大同小異,有的處決的是一個(gè)人,最多的是一次處決五個(gè)人。他算了一下,在這一沓文件里,已經(jīng)有三十多個(gè)人的性命煙消云散。
“這只是一周內(nèi)他簽發(fā)的處決令。被處決的都是國共兩黨的地下情報(bào)人員。這個(gè)路文霖,自從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臨時(shí)政府成立那天,就開始擔(dān)任這個(gè)行動(dòng)處處長。你想想,他手上有多少血債。”
“這個(gè)大漢奸,真是心狠手辣!”穆立民重重一拳砸在墻上。
穆興科說:“不過你的問題也不難回答。江朝宗是大漢奸,作惡更多,上峰肯定不會(huì)放過他,但要找一個(gè)合適的時(shí)機(jī)。所以我們目前清除的對(duì)象還是那些直接殘殺愛國志士的兇手,或者是那些直接為日本人服務(wù)的漢奸,比如幫日本人搜刮軍糧的、掠奪資源的。接下來,你去查清楚路文霖的活動(dòng)規(guī)律,查清他在哪里住和什么人住在一起,還有上班下班的路線。一周后,你進(jìn)城來,咱們?cè)诤蠛D羌铱救怵^子見面。”
穆立民稍一猶豫,還是點(diǎn)點(diǎn)頭。穆興科注意到了他的神情,說:“怎么樣?一周的時(shí)間夠嗎?”
“夠!”
穆興科的語氣冷淡下來,說:“我覺得不夠,因?yàn)槟氵€要上課。再說這里這么偏僻,連輛黃包車都沒有,你怎么進(jìn)城?明明完成不了的任務(wù),你為什么要接受?穆立民,作為情報(bào)人員,一定要以完成任務(wù)為最高宗旨,絕不能意氣用事!”
穆立民一梗脖子,說:“你放心,我有辦法!”
“你有辦法?你有什么辦法?”穆興科問。忽然,他指著兩人身后不遠(yuǎn)處的一處野樹林,壓低聲音急促地說:“那里有人!”
“我去看看!”穆立民說,他轉(zhuǎn)身朝樹林跑了幾步,然后故意大聲喊著,“哥,你等我一下,我去樹林里撒泡尿。”穆興科微微一笑,心想,這小子的確聰明,還知道不能打草驚蛇。
穆立民裝出一副內(nèi)急的神情進(jìn)了樹林。只見這里除了幾個(gè)枯枝敗葉堆成的土堆,什么都沒有。忽然,他看到某個(gè)土堆在陽光的照射下似乎反射出一道銀色的亮光。他小心翼翼地走過去,只見樹枝下面,似乎掩埋著什么物件。他慢慢提起一根樹枝,看到的是一輛嶄新的自行車。
“試試看好不好騎。”穆興科已經(jīng)走到了他的身后。
兄弟二人踱回到校門外,穆興科上了那輛等候已久的洋車,返回城里。穆立民扶著自行車望著漸漸遠(yuǎn)去的洋車變成了一個(gè)小黑點(diǎn),才騎上車朝著自己的宿舍——未名湖北岸的德才均備齋騎去。
一周后。
北平后海邊上的那家烤肉館子,從樓上樓下的格局來看,它像是一家只賣炒菜、不辦酒席的二葷鋪?zhàn)樱鸵话愕亩濅佔(zhàn)硬灰粯拥氖牵锢锿馔庵挥幸坏啦耍褪强救狻_@天下午,兄弟二人分別從燕京大學(xué)和珠市口趕來,在二樓僻靜處找了一靠窗的桌子坐下。伙計(jì)把烤肉炙子支好,把大盤腌好了的肉片擺在炙子上,點(diǎn)燃松枝木炭,就下樓了。穆立民等腳步聲在樓梯上消失,才說:“哥,我都打聽好了。路文霖平時(shí)住在寬街,司機(jī)也住在同一間宅子里,每天早上七點(diǎn)三十分左右他坐汽車離家上班。正常情況是每天下午五點(diǎn)四十分左右下班,六點(diǎn)左右到家。他禮拜天基本不出門,都待在家里。”
穆興科說:“你說正常情況下他五點(diǎn)四十分下班,那是不是還有不正常的情況?”
“他每周六會(huì)提前三個(gè)小時(shí)下班。”
“他提前下班后,大概不是直接回家吧?”
“他每次提前下班后,都會(huì)去六國飯店。在那里他總是住進(jìn)四層的十八號(hào)房。他進(jìn)了房間后,會(huì)有一輛汽車來到六國飯店,車上會(huì)下來三名女子。這三名女子來到他的房間后,他留下其中一人,也可能會(huì)留下兩人或者三人。周六下班后,他一般都會(huì)在那里待到第二天上午或下午才回家。”
穆興科鄙夷地說:“這個(gè)色鬼有保鏢嗎?”
“他的司機(jī)就是他的保鏢,司機(jī)身上有槍,他自己平時(shí)也帶槍。”
穆興科眉毛一挑,看起來頗為喜悅,他打量了一下穆立民,說:“行啊,你查得還挺細(xì)。這些情報(bào)都很管用。說說看,你是怎么查出來的。”
穆立民得意地笑了笑,說:“其實(shí)也不難。我先到他的住處四周觀察,看到他家宅子對(duì)面就是個(gè)二葷鋪?zhàn)樱匈F友居。這種鋪?zhàn)右话愣际羌尜u早點(diǎn)的。五天前我特意在早點(diǎn)的時(shí)間到了貴友居,和店里的幾個(gè)老主顧聊天。我說我前兩天早上八點(diǎn)在這里過馬路,差點(diǎn)讓里面出來的一輛黑色汽車給撞死,當(dāng)時(shí)被撞倒在地,沒看清車牌。聽說這里面住著位治安委員會(huì)的大官,不知那輛車是不是他的。那幾位老主顧都是常年在貴友居吃早點(diǎn)的,他們聽我說完一起搖頭,都說大官那輛車一般都是早上七點(diǎn)半這個(gè)時(shí)間出門。我說自己記得撞人那輛車的樣子,你們知道這胡同里那輛車是什么時(shí)候回來嗎?我到時(shí)看看那車,就知道是不是撞自己那輛。他們說,那得等到晚上六點(diǎn)了。后來我按照這個(gè)時(shí)間去蹲了兩天,發(fā)現(xiàn)路文霖回到家的時(shí)間都沒什么變化。”
“他每個(gè)周六都去六國飯店的事,你怎么打聽出來的?”
“當(dāng)時(shí),我問貴友居的那幾位老主顧,路文霖他是每天都六點(diǎn)回來嗎?他們都說周六這天不是。”
“六國飯店呢?你怎么查到的?”
“我覺得,他周六提前下班,肯定是去吃喝玩樂了,就拿著他的車牌號(hào)碼到城里高級(jí)一些的飯店打聽。在六國飯店,那里的門童說經(jīng)常見到這輛車。當(dāng)時(shí)那個(gè)門童看到這個(gè)車牌,露出有些曖昧的笑意。我猜肯定有原因,就拿了一塊銀圓給他,他就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我。”
“好,我回去擬定一個(gè)行動(dòng)計(jì)劃,三天后再來找你。記住,你剛才提到的這幾個(gè)地方,寬街、六國飯店,都別去了,記住了嗎?”
穆立民點(diǎn)點(diǎn)頭。穆興科滿意地說:“那就好。趕緊吃烤肉吧,都烤煳了。”
這天下午,路文霖坐在寬敞明亮的辦公室里,看著面前的處決令,心緒頗為復(fù)雜。這已經(jīng)是他第三十次在處決令上簽名了。庚子那年,他出生在沈陽東北郊外渾河邊上的一個(gè)小地主家庭。他家里有一大片水澆地,雇了十四個(gè)長工來種。因?yàn)榧揖澈茫诒敬遄x了私塾后,又在縣城上了小學(xué)和中學(xué)。后來他和很多同學(xué)一起去報(bào)考奉天法政學(xué)堂,他還真的考上了。在那里讀了兩年,還沒畢業(yè)就有同學(xué)說要去考張作霖大帥當(dāng)校長的東北講武堂。他也跟著去考,竟也考上了。等畢了業(yè),他自然而然和所有同學(xué)一起進(jìn)了奉系,當(dāng)上了軍官,拿起了短槍。總之,他總是隨波逐流的,別人去哪里他也跟著去哪里。后來老大帥被日軍炸死了,他的同僚都嚷嚷著要給老大帥報(bào)仇。但他卻沒說什么。他覺得老大帥已經(jīng)死了,活著的人應(yīng)該繼續(xù)活好才是最重要的。再后來,日軍在東北到處找碴兒挑釁,他的同僚又?jǐn)x掇少帥和鬼子真刀真槍地打。等日軍真的占了東北,東北軍大部隊(duì)隨著少帥入了關(guān)。他呢,舍不得老家的好地,心想日本人來了也總要吃米,自己把軍裝脫了,好好種地,日本人也就不會(huì)為難自己了。可是日本人來了之后,村里有人眼饞他的水澆地,去報(bào)告他在東北軍里當(dāng)過軍官。日本人來抓他,他起初很怕,就主動(dòng)說自己愿意把糧食獻(xiàn)出來當(dāng)軍糧。東北軍入關(guān)前,在當(dāng)?shù)剡€留下不少特務(wù),他也愿意指認(rèn)這些人。日本人對(duì)他是滿意的,讓他去新成立的滿洲國當(dāng)個(gè)官。就這樣,他在滿洲國的文教部里當(dāng)了一個(gè)小官。這個(gè)官自然沒半分實(shí)權(quán),他也就這么當(dāng)著,還娶了妻,有了孩子。安安穩(wěn)穩(wěn)過了五年后,他看新聞知道日軍又占了北平,但他萬萬沒想到,這件事也會(huì)和自己有關(guān)系。去年底,臨時(shí)政府成立了,因?yàn)楸逼绞谴蟪鞘校枰墓俣啵毡救艘娝@幾年一直謹(jǐn)小慎微,就把他調(diào)了過來。
到了北平,他接到了委任狀,上面的官銜嚇了他一跳,是“治安委員會(huì)行動(dòng)處處長”。后來他進(jìn)了臨時(shí)政府,發(fā)現(xiàn)自己除了在處決令上簽字外,其他什么事情都沒有。他也就明白了,自己是一個(gè)傀儡。他當(dāng)然知道,這個(gè)處經(jīng)常有行動(dòng),行動(dòng)的內(nèi)容是抓人、拷打、殺人,他還知道處里有二十多號(hào)人,這些人、這些事,都是那個(gè)副處長在管。他知道自己“手下”那個(gè)名叫江品祿的副處長,是北平特別市市長江朝宗的侄子,他卻從沒見過這個(gè)人,不知道這人長什么樣子。
他還知道,這個(gè)治安委員會(huì)里,還有情報(bào)處、機(jī)要處、調(diào)查處等好幾個(gè)處,這些處的處長,和他一樣,整天僅有的事情就是坐在辦公室里喝茶、看報(bào)、簽名。
他知道了自己的命運(yùn)后,就托人賣了老家的地。他拿了其中的一小筆,分別以老婆和兒子的名字在銀行里開了戶頭,剩下的錢,還有日本人給他發(fā)的薪水,他天女散花一般地花著。快活了兩個(gè)多月后,賣地的錢都快花完了,但他也不在乎。
這個(gè)臨時(shí)政府本來就是日軍的傀儡,自己顯然是傀儡中的傀儡。一想到這里,他就覺得自己實(shí)在可笑。臨時(shí)政府里陸續(xù)有人被暗殺,他知道,自己也活不了太久了。只要出了家門,他就覺得每個(gè)迎面走來的人,隨時(shí)都有可能從懷里抽出一把手槍朝自己開一槍。
這天又是周六,他來到六國飯店,進(jìn)了那間包房。他想著即將到來的快活時(shí)光,伸手去拉燈繩時(shí),卻拉了個(gè)空。這時(shí)他才看到對(duì)面的沙發(fā)上有人坐著。從窗縫透進(jìn)來的燈光,把那人的黑影拉得很長。他長嘆了一聲,慢慢放下公文包。“你要?dú)⑽遥俊彼麊枴?/p>
黑影沒有回答他,站起身來往手槍上擰著消音器。他心想,真是高看我了,只有最高級(jí)的特務(wù)才有這東西,想不到殺我這樣一個(gè)螻蟻都不如的人,還需要出動(dòng)這樣的高手。
那黑影悄無聲息地朝路文霖快步走來。路文霖雖然早就知道自己隨時(shí)會(huì)死于非命,但這時(shí)一種求生欲突然迸發(fā)出來,他還想繼續(xù)活著。“你們找錯(cuò)人了,我只是替死——”他飛快地說著,“鬼”字還在他的喉嚨里,槍口已經(jīng)頂在他的胸口上。隨著“噗”的一聲悶響,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穆興科下樓來到大堂,先在前臺(tái)取了自己的皮衣,出門后坐上了第一輛來到面前的黃包車。“快,東興樓,快了有賞!”穆興科說。那車夫甩開步子跑了起來。
黃包車開始還跑得很快很穩(wěn),可到了北河沿大街上,這里因?yàn)榭拷辖堑淖o(hù)城河筒子河,寒氣格外重,晚上一個(gè)行人都沒有。這時(shí),那車搖搖晃晃起來。穆興科看到,車夫的小腿在顫抖,他知道北平的車夫跑上十里八里都不會(huì)這樣的。他慢慢抽出手槍,擰好了消音器。那車夫看到槍投在地上長長的影子,忽然輕聲說:“哥,別開槍,是我!”說完,他把車慢慢撂下,然后摘下氈帽,轉(zhuǎn)過身來。
是穆立民。穆興科把槍插回懷里,擺了個(gè)要揍他的姿勢(shì),說:“臭小子,我差點(diǎn)一槍把你崩了!”
穆立民在洋車車把上坐下,揉著自己的兩條小腿,笑嘻嘻地說:“哥,我這一路從六國飯店跑到這兒,都快累死了。”
穆興科啐了他一口,說:“從六國飯店到這兒,壓根兒沒幾步路,看你累成這熊樣兒。”
“不行,我累了,我要吃西餐,去華美餐廳!你今天順利完成任務(wù),本來就該請(qǐng)客!”
“不行,華美在西交民巷,離六國飯店太近了。”
“那去天橋的東方飯店,那里也有西餐。”
“那里可以,離家也近。”
兄弟二人到了東方飯店,侍者給他們端來咖啡和菜單,穆興科要了一份烤牛排,穆立民要了一份奶油蒜香烤大蝦。這時(shí),早已過了晚餐時(shí)間,偌大的廳堂里,只剩下兩三桌客人。穆興科板下臉,壓低聲音說:“按照組織的紀(jì)律,特工在執(zhí)行任務(wù)期間,沒有任務(wù)的特工,絕對(duì)不能加入任務(wù)中。如果你不是我的弟弟,我甚至有可能擊斃你。”
穆立民歪著腦袋品了品咖啡,說:“哥,不至于吧。”
“穆立民同志,我不是和你開玩笑。對(duì)于一名特工,尤其是在執(zhí)行任務(wù)中的特工,完成任務(wù)就是他的第一天職,對(duì)于任何介入者,他都可以當(dāng)場擊斃。”
“我是想幫——”
“一名職業(yè)特工,必須在執(zhí)行每次任務(wù)前,把所有因素都考慮到,詳細(xì)做好任務(wù)規(guī)劃。這也就意味著,他不需要任何計(jì)劃外的幫助。無論什么樣的幫助,其實(shí)都是干擾。既然是對(duì)任務(wù)形成了干擾,當(dāng)然可以當(dāng)場擊斃干擾者。而且你今晚突然出現(xiàn),我有理由懷疑你是不是叛變了,正帶領(lǐng)敵方特工來抓我。”
穆立民嚇得吐了吐舌頭,一聲也不敢吭了,扯過來一塊面包,蘸起盤子里的奶油和蒜末來。這時(shí)餐廳里愈發(fā)安靜,只有幾個(gè)等著他們離開好打烊的侍應(yīng)生,聚在吧臺(tái)后面輕聲聊著天。
兄弟二人不出聲地吃了一會(huì)兒,穆興科說:“好了,這次任務(wù)畢竟順利完成了,在接到下一個(gè)任務(wù)前,參與這次任務(wù)的特工之間都不能再聯(lián)系了。咱們雖然是兄弟倆,也不要談?wù)撨@次任務(wù)了。”
穆立民看看四周,說:“哥,你的上級(jí)同不同意我加入你們組織?”
穆興科說:“不用上級(jí)同意。我這次來北平前已經(jīng)獲得授權(quán),為了完成任務(wù),遇到合適的人,可以直接招募。”
“哥,你上次說你是第九派遣隊(duì)的,是不是北平城里,咱們至少有九支派遣隊(duì)?”
“立民,兵法上說,兵不厭詐。北平城里的派遣隊(duì),每一支都有任務(wù),可能有一支,也可能有兩支,還可能有一二十支。這些數(shù)字都是用來迷惑日本人的,除了組織里的最高長官,誰也不知道北平城里到底有多少我們的人。”
兄弟二人約定,關(guān)于下一次任務(wù),周六下午穆立民上完課后,二人在西直門外見面再談。
三天后。
這天晚上,穆立民去食堂打了晚飯,正和幾個(gè)同學(xué)一起在宿舍里吃著,忽然舍友徐念國裹著一身寒氣推門進(jìn)來。他神情嚴(yán)肅,眼圈通紅,坐在自己的床上一言不發(fā)。穆立民問:“念國,你不是說你娘病了,今天回城里看父母嗎?我還以為你會(huì)在城里住幾天呢。”
徐念國搖搖頭:“我剛進(jìn)家門那會(huì)兒,來家里給我娘看病的大夫正好剛開了藥方。上面的藥,需要去前門那邊的長春堂藥店去抓,我自告奮勇去抓藥。我剛坐洋車出了前門,就看到一大群人圍在五牌樓前看著什么。我一時(shí)好奇,就過去看了看,結(jié)果就看到三顆人頭從五牌樓上掛下來,犧牲的三個(gè)人都是年輕人!”
穆立民也嚇了一跳,他從小就常在這前門五牌樓下玩,這里離天祥泰綢緞莊只不過八九百米。他趕緊問:“這是怎么回事?這三個(gè)是什么人?”
“你們還記得一個(gè)月前,那個(gè)大漢奸王克敏遇刺的事兒嗎?”
“記得,當(dāng)時(shí)那幾個(gè)刺客打死了王克敏的保鏢和翻譯,后來他們都逃跑了。”
“他們都被抓住了,正掛在五牌樓示眾的,就是他們的人頭!”
穆立民只覺得全身都要爆炸了,他忽地站起來說:“他們被抓了幾個(gè)人?叫什么名?”
“他們是兩男一女,女的叫宋茗,男的一個(gè)叫孔人亮,一個(gè)叫杜新川。最可恨的是旁邊還有張臨時(shí)政府的布告,說這幾個(gè)人是匪諜,蓄意破壞北平治安,阻礙大東亞共榮,特將他們的頭顱掛在這里示眾,以儆效尤。最后簽字的是王克敏,蓋著臨時(shí)政府的大印。”
“王克敏這個(gè)賣國賊!”幾個(gè)同學(xué)憤憤不平地說。
到了周六,穆立民一下課就騎上自行車往城里趕。快到西直門城樓下時(shí),他看到不遠(yuǎn)處穆興科正倚在一棵樹下,慢慢抽著煙,心事重重的樣子。
他慢慢推著車走過去,到了穆興科面前,輕聲說:“哥。”
穆興科扔掉煙頭說:“你跟我來。”
兩人進(jìn)了城,穆興科還是一言不發(fā)地走著,一直走到積水潭邊的雜樹林里。他停下腳步,面對(duì)著結(jié)滿了薄冰的湖水說:“我們這支派遣隊(duì),一共六個(gè)人,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三個(gè)人被逮捕殺害,這說明組織里一定有叛徒。這個(gè)叛徒可能是我,也可能是別人。”
“哥,我相信你。”
穆興科打斷他的話說:“這個(gè)時(shí)候,你誰也不能信。就算你是我推薦加入組織的,你也不能完全相信我。我為什么就不能叛變?萬一我也是日本特務(wù)呢?從現(xiàn)在開始,我的一舉一動(dòng),你也要高度懷疑。立民,我之所以沒有懷疑你,絕不是因?yàn)槟闶俏业艿埽膊皇且驗(yàn)槲叶嗝戳私饽悖瑑H僅是我知道你完全不了解這三個(gè)人的下落,所以他們被人出賣也就和你沒有任何關(guān)系。你懂了嗎?”
穆立民點(diǎn)點(diǎn)頭。
穆興科望著遠(yuǎn)處的德勝門城樓,慢慢地說:“當(dāng)初,我離開家之后,參加了國民革命軍。我穿上了軍裝,領(lǐng)到了一桿漢陽造,成了‘革命軍人’。那時(shí)我本來想為國家做一番事業(yè),唯一擔(dān)心的就是北伐成功后,國家統(tǒng)一了,沒有仗可打了。后來我很快就接到命令,要去山西打仗。開始我很納悶,不知道敵人是誰。但我終歸是高興的,覺得自己能給國家做點(diǎn)事了。可到了山西,我才知道,我們要打的是閻錫山。可是我們的隊(duì)伍和山西的隊(duì)伍,在北伐時(shí)還明明是戰(zhàn)友。后來我才知道,這是蔣介石要和閻錫山、馮玉祥搶地盤。那時(shí)我所在的那個(gè)連,除了我就只有一個(gè)人讀過書。他比我大五歲,他告訴我,舊軍閥雖然被打倒了,但新軍閥之間還要互相打,搶錢、搶人,最主要的還是搶地盤,老百姓還是沒好日子過。”
穆立民不知道穆興科為什么在這個(gè)節(jié)骨眼上提起這些事,但他一直聽著。
“再往后,這位老大哥勸我,說我還年輕,不應(yīng)該給軍閥當(dāng)炮灰,說我應(yīng)該出國留學(xué),去學(xué)習(xí)真正的富國強(qiáng)兵之道。這樣我才去了日本。從日本回國后,我又聯(lián)系上他,他這時(shí)已經(jīng)加入了組織,還把我也引薦進(jìn)去了。我在組織里成長得很快,執(zhí)行了十幾次任務(wù)后,他主動(dòng)去找上級(jí),說我的能力已經(jīng)超過了他,我的頭腦比他更冷靜,制訂行動(dòng)計(jì)劃時(shí),心思也比他更縝密。總之,他想方設(shè)法說服上級(jí),把他的職務(wù)讓給了我。這次組織派人到北平來執(zhí)行任務(wù),第一個(gè)要?dú)⒌木褪侨A北頭號(hào)大漢奸王克敏。誰都知道這次任務(wù)很危險(xiǎn),很可能會(huì)把命搭進(jìn)去,他也主動(dòng)報(bào)名要求參加。”
穆立民心里一陣顫抖,他說:“哥,你說的是……”
兩道淚水從穆興科臉上流下來,他說:“我這個(gè)老大哥,名叫孔人亮,那三顆被示眾的人頭里,有一顆就是他的。”穆立民剛要說些什么,穆興科繼續(xù)說,“杜新川本來是東北軍里的一個(gè)排長,日本占領(lǐng)東北后,他很多上司、同僚、部下都逃到了關(guān)內(nèi),他硬是咬牙留了下來,單槍匹馬在暗地里殺日本兵、殺漢奸。后來有一回他正好救了一個(gè)去破壞日本軍械庫的特工,這個(gè)特工是組織派去的,就是孔人亮大哥。孔大哥被他救出來之后,告訴他一個(gè)人單干沒用,必須把不愿意當(dāng)亡國奴的中國人的力量匯集起來,才能干成大事。他明白了這個(gè)道理后,就加入了組織。
“宋茗是大家閨秀,本來是滬江大學(xué)的大學(xué)生,三年級(jí)那年,她交了個(gè)男朋友,那人是藍(lán)衣社的,后來就發(fā)展她進(jìn)了藍(lán)衣社。九一八事變后,她男朋友被派去東北執(zhí)行任務(wù),在那里殉國了。去年日軍占領(lǐng)上海后,她一個(gè)大小姐,為了刺探情報(bào),心甘情愿進(jìn)了那些漢奸常去的窯子,去結(jié)交那些漢奸。最后她不但搞到不少情報(bào),還殺了三個(gè)大漢奸。掛在前門五牌樓的其中一個(gè)人頭,就是她的。”
穆立民用袖子擦擦眼淚說:“哥,我懂了,咱們一定要查出是誰出賣了他們,給他們報(bào)仇!”
穆興科半晌不語,慢慢緩和著情緒。過了一陣子,他才說:“給他們報(bào)仇最好的辦法,就是繼承他們的遺志,完成他們沒有完成的任務(wù)。我們這個(gè)第九派遣隊(duì),目前只剩下你、我和另一位同志了,但我們下一個(gè)任務(wù)非常重要,是竊取日軍往徐州戰(zhàn)場運(yùn)輸軍火的計(jì)劃。按照組織的規(guī)定,這時(shí)我如果需要有足夠的人手完成任務(wù),最可靠的辦法就是到武漢找到組織,請(qǐng)組織加派人手。但是這樣一來,等我們回到這里,日本人的這個(gè)計(jì)劃大概已經(jīng)執(zhí)行完成,大批日軍軍火也已經(jīng)運(yùn)到了前線。”
“發(fā)電報(bào)也不行嗎?或者在報(bào)紙上登個(gè)什么啟事,用暗號(hào)告訴組織你需要幫助。”
“發(fā)電報(bào)是需要電臺(tái)的,我又沒有電臺(tái)。在報(bào)紙上登啟事,這倒的確是一個(gè)特工和組織進(jìn)行聯(lián)系的好辦法,但這個(gè)辦法有一個(gè)缺點(diǎn),就是只能進(jìn)行非常簡單的聯(lián)絡(luò)。比如用某個(gè)暗號(hào)表示任務(wù)完成或者任務(wù)失敗,或者表示出現(xiàn)了叛徒。但這次我要通知給組織的,是非常復(fù)雜的內(nèi)容,根本不可能用暗號(hào)很準(zhǔn)確地表示出來。”
“那上次賣熏魚兒的和賣蘿卜的呢,能讓他們把情況傳遞給組織嗎?”
“那也不行。我只能被動(dòng)地接受他們發(fā)給我的通知,我完全不知道他們的落腳點(diǎn),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他們,更不知道他們下一次會(huì)在什么時(shí)候出現(xiàn)。”
此時(shí),天已經(jīng)全黑了,遠(yuǎn)處的德勝門城樓只剩下一個(gè)黑魆魆的模糊輪廓,積水潭四周的民宅里,也逐漸亮起了黯淡的燈光。穆興科輕輕拍了拍湖邊的一株樹干,點(diǎn)燃了一支香煙,慢慢吐出煙霧后,才說:“我還有一個(gè)辦法。”
穆立民上前走了一步,問:“什么辦法?”
穆興科說:“唯一的辦法,是我們即刻和延安方面安排在北平的特工取得聯(lián)系,雙方共同完成這項(xiàng)任務(wù)。我這次回北平前,上級(jí)就告訴我,眼下國共合作抗日,共產(chǎn)黨方面已經(jīng)同意,不但在戰(zhàn)場上合作,在情報(bào)方面也準(zhǔn)備跟我們合作。到時(shí)如果我們需要,可以調(diào)動(dòng)他們?cè)诒逼降奶毓ぁ.?dāng)然,目前我還沒有見到延安方面情報(bào)人員的代表,自然更談不上合作了。”
“共產(chǎn)黨也往北平派來了特工?”
“那當(dāng)然。共產(chǎn)黨抗日,這些年來一直比國民政府積極得多。日本占領(lǐng)了東北之后,你知道日本人最頭疼的是什么嗎?就是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東北抗聯(lián)!算了,給你說這些也沒什么用,共產(chǎn)黨的特工不可能突然出現(xiàn)在我面前。明天你回家嗎?”
穆立民點(diǎn)點(diǎn)頭。
“好,明天早上我陪奶奶和娘去雍和宮,咱們明天還能在家里見上面。”穆興科說完,在樹皮上重重地按熄了煙頭,轉(zhuǎn)身離開了,很快就消失在夜色里。
“延安方面也往北平派來了特工,只有盡快和他們?nèi)〉寐?lián)系,國共合作才能竊取到這份情報(bào)。”穆立民想著他的話,低頭騎上車,慢悠悠地朝城外騎去。
第二天是周日,穆立民一早就騎車回家,剛到門外,正好見到周雙林送二葷鋪?zhàn)痈T凭拥幕镉?jì)從家里出來,心想:“晚上有炒肝吃了。”
珠市口一帶不僅商戶云集,各種飯店飯鋪更是一家挨著一家。既有全北平赫赫有名,能承辦上百桌酒席的大飯莊天壽堂、同興堂,也有稍小些,只有幾十張桌子的飯館,比如兩益軒、厚德福,至于那些只能炒些家常菜的二葷鋪?zhàn)樱谶@一帶大大小小的胡同里更是到處都是。因?yàn)楦偁幖ち遥@些館子無論大小,都有自己的拿手菜,福云居的炒肝就獨(dú)具特色。這家鋪?zhàn)拥睦习濉⒄乒裢瑸橐蝗耍驗(yàn)槟c子只選用厚薄均勻的中段,而且洗得干凈,加之用上等口蘑湯來勾芡,一碗炒肝毫無異味,吃起來鮮香醇厚,在北平的好吃之徒中頗負(fù)盛名。日軍占據(jù)北平后,福云居也閉門歇業(yè),但店中的老板、廚子、伙計(jì)畢竟要養(yǎng)家糊口,進(jìn)了貨就暗暗開了伙,但門板依然緊閉,并不正式營業(yè),只給老主顧登門送貨。平時(shí)哪怕并不愛吃這口的市民,也偶爾在他家訂貨。
穆立民進(jìn)了家門,周雙林告訴他,穆世軒按老習(xí)慣去長清池泡澡了,穆老太太和穆夫人早早由穆興科陪著去了雍和宮上香,大概很快就回來了。
此時(shí)距離吃午飯還早,穆立民沒吃早飯,也沒心情吃飯。他在里院的葡萄架下坐下,周雙林去廚房給他盛了碗炒肝,又給他沏了茶。家里空無一人,他慢慢地用小勺舀著炒肝,心里一陣茫然。
他昨晚回到燕京大學(xué),在食堂里和同學(xué)聊起時(shí)局,有同學(xué)剛好在外籍教師那里看了國外的報(bào)紙,報(bào)紙上說日軍在南下時(shí)被中國軍隊(duì)攔截在臺(tái)兒莊一帶,雙方已經(jīng)形成大戰(zhàn)態(tài)勢(shì)。如果日軍取勝,就能徹底打通津浦線,相當(dāng)于中國的腹地被重重刺進(jìn)一刀,就會(huì)讓日軍獲取極大的戰(zhàn)略優(yōu)勢(shì)。這名同學(xué)說:“國外報(bào)紙的消息里說,日軍在裝備、訓(xùn)練上的優(yōu)勢(shì)太大,而李宗仁所指揮的是大拼盤的雜牌軍。去年李宗仁的老部下黃紹竑,受命指揮娘子關(guān)保衛(wèi)戰(zhàn),就是因?yàn)檎{(diào)動(dòng)不了閻錫山的部隊(duì),才在山西大敗,接連丟了娘子關(guān)和太原。照這么看,這次的臺(tái)兒莊也是兇多吉少了。”
女同學(xué)曲蝶心是中美混血兒,父親是協(xié)和醫(yī)院的美籍醫(yī)生,母親是中國籍的護(hù)士。她說:“我家訂了多份美國報(bào)紙,這些報(bào)紙代表美國不同的社會(huì)階層,談起美國國內(nèi)的事務(wù)來,觀點(diǎn)都是互不相讓,唯獨(dú)對(duì)中國戰(zhàn)場形勢(shì)的估計(jì)完全一致,他們都覺得徐州以北的這場戰(zhàn)役將以日軍的勝利告終。”
但是也有同學(xué)看好國軍。鄭國恒是華僑子弟,兩年前父輩特意送他回國讀書。他說:“李宗仁的資歷遠(yuǎn)非黃紹竑可比,而且蔣介石剛處決了不聽號(hào)令擅自撤退的韓復(fù)榘,參戰(zhàn)國軍雖然是雜牌軍,來源復(fù)雜,但卻不用擔(dān)心指揮不靈,這樣一來,國軍在人數(shù)上的優(yōu)勢(shì)就可以體現(xiàn)出來。而且國軍的裝備也不是不堪一擊,國軍裝備了購自德國的150毫米重型榴彈炮,這批大炮可是鼎鼎大名的克虜伯公司制造的,世界一流,就算數(shù)量不多,但現(xiàn)都集中在徐州以北的運(yùn)河沿線,那威力可是非同小可。”鄭國恒說著在書包里抽出一張地圖,鋪在石凳上。幾個(gè)男生圍著地圖指指點(diǎn)點(diǎn),大聲議論。
忽然,他們像剛剛發(fā)現(xiàn)新大陸一般,看到站在一旁的穆立民,說:“穆立民,你是在前線見過日本兵的,你說說看,在徐州的這場仗,我們到底能不能打贏。”
穆立民說:“對(duì)日本來說,打輸了的話,無非是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的時(shí)間推遲了一些,等他們獲得補(bǔ)給,補(bǔ)充了兵員后,很快就能卷土重來。但對(duì)于中國來說,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如果國軍輸了,華東、華北兩個(gè)方向的侵華日軍在徐州一帶會(huì)師,不但整個(gè)華東、華北盡入敵手,而且日軍能將津浦線沿線作為后勤補(bǔ)給基地,撲向中國的華中腹地。目前國民政府和整個(gè)中國的精華都在武漢一帶,根本來不及再次轉(zhuǎn)移,就會(huì)被日軍圍殲。”
幾個(gè)同學(xué)聽他說完,面面相覷。過了一陣子,鄭國恒才說:“那這一場仗,中國可不能輸。”
“中國是不會(huì)輸?shù)模 闭f完,穆立民夾了夾胳膊底下的書,大踏步地走了。
穆立民從回憶中走出,這時(shí)他也吃完炒肝,只聽見一陣說笑聲從外院傳來。他抬頭,只見穆興科正陪著奶奶和母親進(jìn)來。袖兒一看見他,馬上笑盈盈地說:“老太太和夫人特意去雍和宮給二少爺求了根平安簽,等二少爺回學(xué)堂,就把簽帶上,準(zhǔn)保出入平安。”
穆夫人說:“我和你奶奶去雍和宮上香,本來想早去早回,可日軍把前門車站這一片兒都給封鎖起來,禁止通行。聽說是運(yùn)什么要緊貨物。”
說話間,穆世軒也回來了。他一進(jìn)門就吩咐關(guān)好房門,誰敲門也不開。接著他又吩咐周雙林給他在里院中間擺好香案,香案上擺了香爐和幾種果品。他進(jìn)了自己的書房,片刻間拿著幾張長長的寫著名字的紙條出來了。穆老太太問他怎么回事,他嘆了口氣說:“我在長清池里面,正搓背呢,聽說前門五牌樓上掛出來三顆人頭。我趕緊過去看,因?yàn)楦舻眠h(yuǎn),我看不清人臉,但聽說了這三位英雄的尊姓大名。我可得好好給他們上一炷香。”說著他朝周雙林使了個(gè)眼色,周雙林點(diǎn)點(diǎn)頭,出了里院,到外院那里去看著大門。穆世軒扭過臉看著穆興科、穆立民,表情異常嚴(yán)肅說:“這三位英雄,是為國捐軀的,你們都過來,和我一起祭拜。”兄弟倆站在他身后,穆世軒先是把三張紙條壓在香爐下面,在香爐里點(diǎn)了三炷香,接著三人每人朝香案三鞠躬,然后把紙條焚化了。
一家人開始吃午飯,飯后穆立民陪著奶奶、母親說了一會(huì)兒話,長輩們自去午睡,他騎車回了燕京大學(xué)。第二天一早,別的同學(xué)剛剛經(jīng)歷了一個(gè)喧鬧的周末,仍然在沉沉睡著,他已經(jīng)開始沿著未名湖跑步。
六點(diǎn)鐘的北平城還籠罩在夜色中,湖邊空無一人。第一圈、第二圈、第三圈,等跑完第三圈,穆立民又鉆進(jìn)了博雅塔,沿著螺旋式鐵梯一直爬到塔頂。在這里,此時(shí)如果朝東望去會(huì)看到東方的天空那原本渾然一體的黑色,慢慢松裂出一道窄窄的縫隙,那里將漸漸露出一道深紫色的朝霞。隨著天幕被晨曦一點(diǎn)點(diǎn)撕開,城市的輪廓慢慢變得清晰,等到朝霞漸漸布滿東南方的天空,哪怕仍然是隆冬,城市的色彩也會(huì)變得豐富起來,蒼灰色的城墻,金黃色的宮殿,暗灰色的民房,反射著銀亮光線的湖泊,成片成排地在視線里延伸著。這時(shí)如果在塔里的最高處朝西看,目光越過塔下結(jié)滿厚冰的未名湖湖面,會(huì)看到遠(yuǎn)處頤和園里因?yàn)檫^于寬闊而只在岸邊結(jié)了冰的昆明湖,和更遠(yuǎn)處玉泉山連綿起伏的峰巒。
下了塔,他做著擴(kuò)胸動(dòng)作慢慢走向德才均備齋——燕京大學(xué)的男生宿舍。每次走過未名湖東岸的這條小路,他都會(huì)想起在武漢生活的那兩年。他在武漢最大的收獲,其實(shí)并不是成為國立武漢大學(xué)的學(xué)生。
一九三六年夏天,他考入國立武漢大學(xué)后,也經(jīng)常沿著東湖跑步、讀書。東湖比未名湖大多了,他每次只能跑完湖岸的一小段。那時(shí)班上的每一個(gè)學(xué)生幾乎都不同程度地經(jīng)歷過一二·九運(yùn)動(dòng),他們談?wù)撈饑聛恚偸歉裢饧?dòng)、興奮。南京政府的影響在這里比在北平大得多,穆立民知道,校園里除了學(xué)生還有大批特務(wù)在活動(dòng),時(shí)常有同學(xué)在教室、寢室中被帶走。
初秋的一天傍晚,他正沿著東湖跑步,忽然聽到一聲英語:“穆立民同學(xué),你好!”
他扭頭看去,看到站在身后的是一個(gè)熟悉的身影。
高銘志是他從前在北平讀中學(xué)時(shí)的英語教師。那時(shí)在他們班里,這位高老師是最受學(xué)生歡迎的。高老師除了上課,還會(huì)給他們講世界各地發(fā)生的事。有的學(xué)生在向他請(qǐng)教功課時(shí),在他的宿舍里還可以借到書店里很難買到的書。后來他也去過高老師的宿舍,發(fā)現(xiàn)屋里擺滿了書。有一次,在一個(gè)周日下午,學(xué)校里靜悄悄的,他去找高老師還書,結(jié)果剛到高老師宿舍門口,還沒來得及敲門,就聽到里面?zhèn)鱽硪魂囕p微的讀書聲。這聲音他聽得不是特別清楚,但聽得出不是英文。后來在高老師的書架上,他竟然看到了幾冊(cè)俄文書。他那時(shí)剛開始學(xué)了一些簡單的英語語法,對(duì)俄文一竅不通,這些書上的字母他一個(gè)都不認(rèn)識(shí)。其中有一本書是包在厚厚的報(bào)紙里,被放在書架的最內(nèi)側(cè)。他問高老師這是什么書,高老師告訴他這是《共產(chǎn)黨宣言》。
穆立民激動(dòng)地打開書,可里面都是他不認(rèn)識(shí)的俄文。高老師見穆立民很失望,想了想說自己有一本油印的中文版《共產(chǎn)黨宣言》,借給別的同學(xué)了。等這本書還回來,就給他看。終于有一天,高老師在下課后把穆立民單獨(dú)留下,告訴他中文版《共產(chǎn)黨宣言》已經(jīng)送回來。穆立民馬上說想看。等穆立民看完這本書,去找高老師還書時(shí),發(fā)現(xiàn)這間宿舍已經(jīng)上了鎖。透過窗戶望進(jìn)去,能看到里面的東西被翻得亂七八糟的。后來他聽同學(xué)說高老師是共產(chǎn)黨地下工作者,在軍警上門抓他前逃跑了。
這次,在武漢再一次見到高老師,他喜出望外。高老師說,自己已經(jīng)知道了穆立民這半年來的經(jīng)歷,也通過武漢大學(xué)里的其他人,了解了他平時(shí)的表現(xiàn),覺得他比以前成熟多了。后來,高老師又陸續(xù)和他見了幾次面,詳細(xì)了解了他的家庭情況,問了很多他對(duì)時(shí)局的看法。終于有一天,高老師告訴他,自己的真實(shí)身份是共產(chǎn)黨的地下工作者,問他愿不愿意加入地下組織,為國家和人民做一些貢獻(xiàn)。穆立民喜出望外,馬上就答應(yīng)了。從那之后,高老師開始對(duì)他進(jìn)行培訓(xùn)。有時(shí)是在東湖的蘆葦深處,有時(shí)是在郊外某處農(nóng)家院落,有時(shí)還會(huì)來到武昌或者漢口最熱鬧地段的某個(gè)旅社里。高老師除了自己教他,還找不同的人教他不同的內(nèi)容。他學(xué)得很快,收發(fā)電報(bào),跟蹤和反跟蹤,使用槍械等,他都學(xué)會(huì)了。高老師對(duì)他也非常滿意。終于在一年之后,高老師告訴他,他已經(jīng)具備了成為一名紅色特工的基本能力。高老師給他分派了幾次簡單的任務(wù),他都順利完成了。最近一次,則是派他去東北,讓他聯(lián)系上當(dāng)?shù)氐牡叵曼h組織。
一個(gè)多月前,侵華日軍在血洗南京后,開始調(diào)集兵力進(jìn)攻中國腹地,國立武漢大學(xué)準(zhǔn)備內(nèi)遷。高老師又交給他一項(xiàng)新的任務(wù),為了完成這項(xiàng)任務(wù),他必須離開校園,回到北平。
這天深夜,朔風(fēng)勁吹,德才均備齋的門窗被吹得嗚嗚作響。穆立民剛要睡著,卻聽到輕輕的嗒嗒聲,窗戶似乎被誰有規(guī)律地敲響了。這是他和穆興科商量好的接頭暗號(hào)。穆立民心里微微顫抖著,慢慢穿好衣服,悄無聲息地在舍友的鼾睡聲中走出宿舍,走到樓外。
在樓門外,穆興科從一株大樹后看到他出來,就轉(zhuǎn)了出來,一言不發(fā)地朝南走去。穆立民在他后面遠(yuǎn)遠(yuǎn)跟著,兩人一前一后,隔了幾十米,一直走到了博雅塔下。在塔身粗大的陰影下,穆興科停下了,他等穆立民走到面前,說:“我給你說過,組織交給我的下一個(gè)任務(wù),是毀掉日軍即將運(yùn)往徐州戰(zhàn)場的這批軍火,至少也要獲取日軍軍火運(yùn)輸方案。目前因?yàn)槿耸植蛔悖瑹o法完成任務(wù),我決定到武漢去,面見上級(jí),請(qǐng)求加派人手。”
穆立民靜靜地看著他,一言不發(fā)。此時(shí)狂風(fēng)正吹動(dòng)著一團(tuán)團(tuán)烏云,烏云在天空中翻滾,枯樹的殘枝則被風(fēng)吹得不停地發(fā)出吱吱呀呀的暗響。過了一會(huì)兒,穆立民說:“哥,如果對(duì)于日軍這批軍火在哪里儲(chǔ)存,又怎么運(yùn)往前線,咱們一點(diǎn)兒頭緒都沒有,那么即使有了足夠的人手,咱們又怎么能毀掉這批軍火呢?”
穆興科微微一笑,說:“你還記得昨天奶奶和娘說過的那句話嗎?”
“哪句話?”
“她們說,在前門遇到交通封鎖。”
“前門火車站那里經(jīng)常封鎖啊。”
“不,我已經(jīng)查清楚,那里最近幾天封鎖得格外頻繁。”
“你覺得,日本人要通過鐵路運(yùn)輸軍火?除了津浦線,他們還可以通過運(yùn)河水運(yùn),或者用飛機(jī)空投。”
“肯定是用鐵路運(yùn)。我已經(jīng)打聽到,最近幾次封鎖,那里還只是演習(xí),并沒有任何軍火裝運(yùn)上車。可見目前日軍還沒把軍火籌集好。我不能繼續(xù)等下去了,我準(zhǔn)備采用目前最保險(xiǎn)的方法,就是到武漢去向組織求援!我估計(jì)來回大概需要一周的時(shí)間,這段時(shí)間里,你要抓緊調(diào)查日軍究竟把軍火存在哪里,怎么運(yùn)往前線。”
穆立民鎮(zhèn)定地說:“哥,你不用去武漢,我這里就有延安方面在北平的特工名單。”
穆興科擺擺手,說:“立民,你別開玩笑。”
穆立民沒繼續(xù)解釋,突然用力往前一沖,眼看就要撞到穆興科了,他突然停下了,伸出手,從穆興科的肩膀上輕輕拿下一枚細(xì)細(xì)的草莖。穆興科下意識(shí)地回退了半步,卻看到穆立民微笑著攤開手,在他的手里正握著自己的那支手槍和消音器。
沒等穆興科做出任何反應(yīng),穆立民已經(jīng)快速裝好了消音器,然后一揚(yáng)手,朝大概十五米外一株懸鈴木的樹冠連開兩槍。第一槍打斷了一枚懸鈴木果實(shí)的細(xì)梗。懸鈴木剛剛下落,他的第二槍又擊中了果實(shí),在噗的一聲悶響后,懸鈴木果實(shí)變成碎屑四散飛揚(yáng),被狂風(fēng)吹得轉(zhuǎn)瞬就不見了。
穆興科又驚又喜,說:“這么好的槍法,你從哪兒學(xué)的?你真的是共產(chǎn)黨?”
穆立民點(diǎn)點(diǎn)頭,說:“哥,我現(xiàn)在就可以把共產(chǎn)黨特工的名單給你。”說著他從懷里拿出一個(gè)信封。
穆興科興奮得雙眼發(fā)亮,他接過信封,馬上打開,拿出一張暗黃色的信紙。這時(shí)他臉上的神情由興奮變成了驚訝和失望。因?yàn)檫@張紙很薄很脆,已經(jīng)泛黃透明,一看就是年頭不短了。
凡我中國之國民,不可不以驅(qū)除列強(qiáng)為宗旨,凡我中國之青年,不可不以報(bào)效國家為己任。如今遍觀世界,處心積慮攫我資源,侵我國土者,當(dāng)以東洋為最。凡甲午以來,日頑兇焰倍長,驕心漸橫,憑吾國之賠款,上下齊心,貴賤通力,興工業(yè),增國力,槍炮艦船日夜趕造,以圖吞并我國。若吾國人再懵懂萎靡,外不識(shí)敵寇之禍心,內(nèi)不修清廉之政體,我中華必將淪為萬劫不復(fù)之地也。
就在穆興科用手電筒照著信紙,看里面的內(nèi)容時(shí),穆立民一字不差地把上面的內(nèi)容背了下來。穆興科默不作聲地聽著,臉上看不出任何表情。穆立民背完了,說:“哥,你還記得這篇文章嗎?這是你十多年前的作文。”
穆興科把胳膊垂下來,任憑風(fēng)把信紙吹得嘩嘩直響。他說:“那時(shí)我年輕氣盛,對(duì)軍國大事似懂非懂。你給我看這個(gè)干什么?立民,共產(chǎn)黨在北平的地下黨名單,如果你能弄到就給我,弄不到的話,我也不怪你。”
穆立民靜靜地看著他,對(duì)他的話仿佛一句也沒聽見似的,繼續(xù)說著自己的話:“哥,你這篇文章,十年前你離家出走的當(dāng)天,我就在你的抽屜里找到了。這兩年來,我無論去哪里都會(huì)帶著,到今天我背了不知道多少遍。”
穆興科看著他說:“立民,現(xiàn)在這個(gè)時(shí)候,你說這些干什么?對(duì)了,趕緊把槍還給我。”
穆立民看了看手槍,慢慢地把槍塞進(jìn)自己的腰間。穆興科看他的眼神變得復(fù)雜起來,有了些許戒備的意味。穆立民輕聲說:“哥,上次刺殺路文霖之前,你要我?guī)湍阏{(diào)查他的行蹤,其實(shí),那一次你的目的不是要考察我,而是要在我面前證明你自己,對(duì)嗎?”
“立民,你在說什么?”
“哥,你是日本特務(wù),對(duì)嗎?”
“立民,別開玩笑了,我必須提醒你,在執(zhí)行任務(wù)的過程中,我們是絕對(duì)不允許開玩笑的。趕快把槍給我!”
“哥,孔人亮、杜新川、宋茗,他們的藏身地點(diǎn),也是你告訴日本人的,對(duì)嗎?我是共產(chǎn)黨的地下組織成員,你也早就知道了,對(duì)嗎?”
“穆立民,你這玩笑開得有些過分了,你再這么不分輕重,我隨時(shí)可以把你開除出組織!”
“哥,國民黨的軍事調(diào)查局給了你任務(wù),讓你毀掉日軍要運(yùn)往前線的軍火,但日本人也給了你任務(wù),就是查清共產(chǎn)黨在北平的地下黨組織。你當(dāng)初行刺王克敏功敗垂成,是因?yàn)橥蹩嗣粼缇偷玫较ⅲ藕腿照Z翻譯交換了位置。那一次雖然也有日本人被打死,但那是為了讓你成為別人眼里的抗日英雄,對(duì)日本特務(wù)機(jī)關(guān)來說,這些代價(jià)也是值得的,對(duì)嗎?”
“刺殺行動(dòng)哪里會(huì)百分之百成功?難道一次不成功,行刺的人就是民族罪人,就是給日本人賣命?”
“那次行刺,還有一個(gè)重要目的,就是讓別人覺得你的胳膊受傷了。其實(shí),我猜想你并沒有真的被子彈擊中,你只是在衣服里裝了些染料,再裝出一副鮮血直流的樣子。而這一切,都是為了騙取我的信任。”
“騙取你的信任?現(xiàn)在我都不信你是共產(chǎn)黨在北平的地下黨成員,更不用說那時(shí)候!”
“你當(dāng)然知道,共產(chǎn)黨對(duì)于國共合作抗日是有著最大的誠意的,我的上級(jí)早就通知了你們,將派遣我方特工到北平,協(xié)助你們的工作。但是你的上級(jí)不知道,你其實(shí)早就被日本人拉下水了,是一把日本人安插在國民黨內(nèi)部的匕首。”
穆興科搖著頭說:“立民,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說什么。你是不是前兩年在外面受到過什么驚嚇,以至于腦子出問題了?”
“哥,出問題的,不是我,是你。好吧,現(xiàn)在我就告訴你,你的破綻究竟是怎么被我察覺的。如果我沒猜錯(cuò),你應(yīng)該是在日本留學(xué)時(shí)被日本人吸收成為間諜的。你回國后,加入了國民黨的軍事調(diào)查局。后來你的上級(jí)派你到北平來執(zhí)行任務(wù),你真正的上級(jí),也就是某個(gè)日本情報(bào)官員,知道國共兩黨的特工在北平活動(dòng)頻繁,就希望利用你,把國共兩黨在北平的特工一網(wǎng)打盡。你們的計(jì)劃,應(yīng)該很早就啟動(dòng)了。當(dāng)初,我的上級(jí)已經(jīng)把我將要來到北平和你們合作的情況通知了你的上級(jí)——軍事調(diào)查局的某位高級(jí)官員,他又把情況告訴了你。于是你和你的日本上司很快就設(shè)下了一個(gè)個(gè)圈套,希望利用我破壞共產(chǎn)黨的地下組織。你為了騙我,讓我覺得你是抗日志士,才裝作右臂負(fù)傷。但是這樣一來,你身上有傷的話,如果被抓進(jìn)日本人的特務(wù)機(jī)關(guān)后還沒有被發(fā)現(xiàn),就說不通了。所以你就先讓日本人把我抓進(jìn)去,并且故意不檢查我的身體,于是你被抓進(jìn)特務(wù)機(jī)關(guān)后也沒有被檢查,就可以解釋了。當(dāng)初你在雙林替奶奶他們上香時(shí)突然出現(xiàn),也是為了讓他以為你胳膊受了傷,覺得你是刺殺王克敏的抗日志士。因?yàn)橛伤堰@件事轉(zhuǎn)述給我,比我自己去猜,說服力大多了。但是無論你做多少鋪墊,我被抓進(jìn)特務(wù)機(jī)關(guān)而沒有被搜身,也是說不過去的。那時(shí)你還沒回家,我還不清楚日本人這么做究竟是何用意。后來雙林把你,就是行刺王克敏的刺客的事兒告訴了我,我就開始有了懷疑。后來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在加深我的懷疑。”
“你別忘了,我可是真的殺過北平治安委員會(huì)的行動(dòng)處處長!這總不會(huì)是在演戲吧?”
“刺殺行動(dòng)處處長路文霖,這就是你的另一個(gè)煙霧彈!他只不過是一個(gè)負(fù)責(zé)在處決令上簽字的傀儡,真正抓捕、拷打、殺害抗日志士的,是行動(dòng)處副處長江品祿!上次日本人在前門車站搞封鎖,也是在演戲,是演給奶奶和娘看的。你們這樣做,是為了讓我覺得時(shí)間緊迫,大批軍火即將運(yùn)往日軍前線,從而把共產(chǎn)黨在北平的地下黨名單告訴你。哥,我的上級(jí)的確給了我這個(gè)名單,派我負(fù)責(zé)和國民黨方面在北平的特工建立起聯(lián)系。但是我必須要在對(duì)國民黨方面的聯(lián)系人完全信任的時(shí)候,才能交出這份名單。”
穆興科一時(shí)無語,但過了一會(huì)兒說:“立民,我沒想到,我和森本嶠,還有情報(bào)課幾名經(jīng)驗(yàn)最豐富的日本特工,一起設(shè)計(jì)出的圈套,竟然被你看穿了。共產(chǎn)黨啊,共產(chǎn)黨,我真是佩服你們,能把我這個(gè)本來連家門都沒出過的弟弟,栽培成這么成熟的特工。立民,我的一切秘密都被你識(shí)破了,這樣也好,省得我費(fèi)口舌向你解釋了。”
穆立民激動(dòng)地說:“哥,你怎么會(huì)變成這樣?剛才那篇文章寫得多好,你明明是愛國的,現(xiàn)在怎么成了……”
“成了漢奸,對(duì)不對(duì)?”穆興科雙手抱在胸前,望著不遠(yuǎn)處隱藏在漆黑夜色中的未名湖說,“我在日本留學(xué)時(shí),我和別的留學(xué)生,每天花費(fèi)時(shí)間討論最多的不是學(xué)校的課程,而是怎么樣能讓中國富強(qiáng),什么才是最適合中國的優(yōu)良政體。有一次,在教室里,我和同學(xué)們剛剛結(jié)束了討論,別人都離開了,整個(gè)教室里就剩下我自己。我望著教室里那張巨大的世界地圖,反復(fù)地想,世界這么大,有這么多國家,有的國家富強(qiáng),有的國家弱小,到底是什么原因,能讓一個(gè)國家變得強(qiáng)大?我去日本前,親眼看到國民黨的軍隊(duì)有多么黑暗、多么腐敗。怎么才能讓中國從這種黑暗和腐敗中走出來?那天,我看著地圖,忽然明白了,東方的日本,西方的德國,這兩個(gè)最近五十年才崛起的國家,才是中國應(yīng)該效法的榜樣!我們要富國強(qiáng)兵的話,最簡單最直接的道路就在我們面前!日本已經(jīng)是世界強(qiáng)國,我們只需去學(xué)習(xí)他們——不,直接加入他們,不就可以了嗎?到那時(shí)我們奉行日本的制度,兩個(gè)國家變成一個(gè)國家,中國的人口、資源,再加上日本的政體,到那時(shí),我們這個(gè)嶄新的國家,必然將是世界頭號(hào)強(qiáng)國!”
“哥,日本是窮兇極惡的侵略者,你覺得他們會(huì)平等對(duì)待中國人嗎?你知道日本占領(lǐng)了東北后,屠殺了多少中國人,掠奪了多少中國的資源嗎?他們血洗了一個(gè)又一個(gè)村莊,制造了一個(gè)接一個(gè)慘案,還日夜不停地把東北的煤、礦石、糧食運(yùn)往日本!所謂的東亞共榮,只是他們欺騙中國人的口號(hào)!”
“他們殺掉那些反抗他們的中國人,是為了盡快實(shí)現(xiàn)和平!如果我們都不反抗了,中國和日本變成一個(gè)國家,他們也就不會(huì)再殺人了!立民,我問你,當(dāng)今世界第一強(qiáng)國是哪個(gè)國家?”
“大概是美國吧。”
“對(duì)。我再問你,美國在建國之前,曾經(jīng)是英國的殖民地,美國現(xiàn)在的制度,基本都繼承英國,這你也知道吧?”
穆立民點(diǎn)點(diǎn)頭。
“那就好。美利堅(jiān)合眾國,如今鋼材產(chǎn)量世界第一,石油產(chǎn)量世界第一,糧食產(chǎn)量世界第一,汽車產(chǎn)量世界第一,他們就是完全效法英國的政體,才有了今天!當(dāng)今世界,誰敢因?yàn)樗麄冊(cè)?jīng)是英國的殖民地而歧視他們?我們想要獨(dú)立,沒問題,完全可以等我們強(qiáng)大起來再去獨(dú)立!”
“哥,你真的是中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毒,你被徹徹底底地洗腦了!你說的這些,都是日本人的謊言!他們對(duì)中國,只有掠奪和殺戮,哪里會(huì)幫助中國建立什么優(yōu)良政體!”
“立民,看來我和你是誰也說服不了誰。現(xiàn)在我的槍在你的手里,我的計(jì)劃又被你完全識(shí)破了,我問你,你是我的親弟弟,你真的要?dú)⑽覇幔俊?/p>
“哥,你為什么要去當(dāng)漢奸?為什么?!你腦子里面的東西,錯(cuò)了,全錯(cuò)了!”穆立民早已熱淚盈眶。在淚光里,他還是抽出那支手槍,裝上了那只消音器,把槍口指向穆興科的額頭。
“好吧,我早應(yīng)該知道,你是一個(gè)合格的特工,一定會(huì)執(zhí)行清除漢奸的命令的。”說著,穆興科轉(zhuǎn)過身,背對(duì)著穆立民說,“你見到了奶奶和爹娘,為了別讓他們太難過,幫我撒一個(gè)謊,總可以吧?你告訴他們,我其實(shí)前幾年就加入了國民政府的特務(wù)組織,如今突然接到組織召喚,必須馬上回到組織,按照組織規(guī)定,不能向他們辭行了。”
穆立民點(diǎn)點(diǎn)頭,說:“我是受組織派遣的,公事我不能答應(yīng)你,必須要得到組織的批準(zhǔn)才行。家里的事我答應(yīng)你。”
“那就可以了。”穆興科指了指自己的后腦說,“朝這里開槍吧,枕骨下方一點(diǎn)五厘米處,槍口向下十五度,這樣子彈將擊穿我的腦干,我會(huì)在一瞬間毫無痛苦地死去,流出來的血也不會(huì)太多。而且子彈會(huì)從我的口中飛出,我這張臉也就保住了。對(duì)了我的尸體,請(qǐng)你一定要火化,再把我的骨灰埋到穆家的祖墳。記得一定要火化,再裝到一個(gè)結(jié)實(shí)的骨灰壇里,我可不想變成野狗的食物。”
說完,他松開了右手。那張泛黃的信紙,一下子就被夜風(fēng)吹上了半空,飛得又高、又遠(yuǎn)……
兩天后的深夜。
在煤渣胡同的日本特務(wù)機(jī)關(guān)處,四下里一派陰森,拷打聲、慘叫聲在走廊里此起彼伏。在一處鋪著精致地毯的辦公室門口,情報(bào)課課長森本嶠脫下軍帽,走進(jìn)喜多誠一那間寬大的辦公室。“將軍,‘佩劍’已經(jīng)連續(xù)兩天失去聯(lián)系了!”他站在正在觀看軍事地圖的喜多誠一身后,深深彎下了腰,頭也垂了下來。
喜多誠一回頭瞥了他一眼,臉上的肌肉憤怒地抽動(dòng)著。他讓自己冷靜下來,這才淡淡地說:“森本君,失去一名培養(yǎng)多年的特工,你我的確有負(fù)天皇重托。但是我們沒有時(shí)間遺憾,從今天起必須全力以赴,把軍火順利運(yùn)往前線,確保皇軍在徐州方向的勝利,以此向天皇謝罪。”
“嗐!”森本嶠雙腿并攏,頭垂得更低了。
“目前軍火已經(jīng)籌集完畢,請(qǐng)你盡快擬定一份運(yùn)輸計(jì)劃,確保這次任務(wù)萬無一失。”喜多誠一走到辦公桌旁,從兵器架上抽出了自己的武士刀。他看了看武士刀那閃著寒光的刀刃,雙手握著刀,走到森本嶠面前,緩慢地說,“如果這次任務(wù)再次失敗,導(dǎo)致皇軍在徐州方向失利,我們就必須剖腹向天皇謝罪了。”
“誓死向天皇效忠!”森本嶠頭朝著地面,嘶啞地喊道。
日軍這批軍火,最后并沒有運(yùn)到臺(tái)兒莊,原因還是與穆立民以及他所在的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有關(guān)。這又是另外一個(gè)故事了。那兩個(gè)沒能及時(shí)得到軍火支援的日軍精銳師團(tuán),在臺(tái)兒莊遭到了中國軍隊(duì)的圍殲和重創(chuàng),這就是名垂史冊(cè)的臺(tái)兒莊大捷。對(duì)于這場勝利的意義,著名的戰(zhàn)地記者羅伯特·卡帕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在美國《生活》雜志上的報(bào)道,再準(zhǔn)確不過了:
歷史上作為轉(zhuǎn)折點(diǎn)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鐵盧、葛底斯堡、凡爾登,今天又增加了一個(gè)新的名字——臺(tái)兒莊。
責(zé)任編輯? ?練彩利? ?藍(lán)雅萍 梁樂欣? ?符支宏
特邀編輯? ?張?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