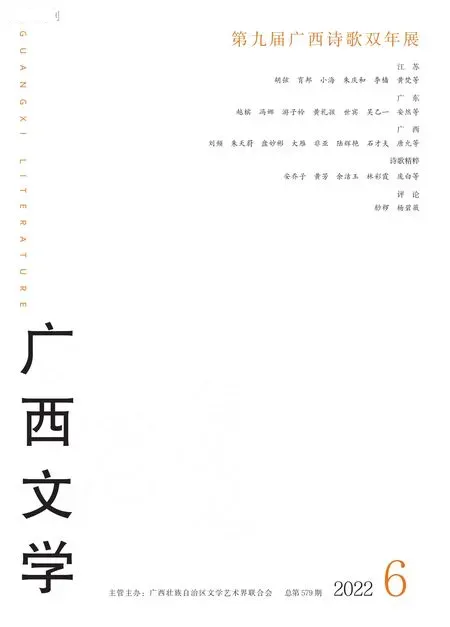在光陰木刻坊的交談(組詩)
天堂來信
在天堂里
他說,他戒酒了,肝功能在慢慢恢復
平日里多吃黃花菜,西紅柿
每天保持一個雞蛋,一杯牛奶,一袋麥片
但還是感到疲倦,那種人間帶來的累讓他
老打瞌睡
一本書從藤椅的陰影區經常滑落
半睡半醒之間,雨燕的糞便一顆顆落到頭上
地上解決不了的問題,他帶到天上繼續思考
他說他堅持散步,但歧路越來越多
一雙鞋子總是和一張遺像結伴而行
他說他很想念我們,包括莫干山那次最后
的聚會
他一生只關心詩歌,鳥,和鐵門
遺憾啊,他所深愛的女人還在愛他
到現在,他都沒能為她寫出一首像樣的情詩
他說,他窗外的湖水太干凈
但他身上的灰塵太多,不敢去那兒洗澡
他仍保持著巖礁的孤憤和晚燈的悲憫
在這封帶著初夏涼風的信里
他習慣性地抿著嘴,還在為受屈者打抱不平
他勸我們珍重,他的目光垂落下來——
“那夕陽的余火,還在為人世間慢慢熬藥”
深夜刻鋼板的人
深夜刻鋼板的人
壓低高度近視眼鏡,那熬紅的眼睛像受傷
的狼
在一塊又冷又硬的鋼板上
他在刻著一首明天排練的大合唱歌曲
鐵筆,以進行曲的速度在鋼板上勻速行進
吱吱的響聲,仿佛樂曲的節奏
一個個工工整整的楷體字,有如一顆顆釘子
打進他隱隱作痛的坐骨神經深處
夜寒中,那是一桿鐵筆和鋼板的對抗與合作
他不能力透紙背,也不能蜻蜓點水
在一張薄如蟬翼的蠟紙上,他把控著力度
小心翼翼平衡著大半生的輕重
一支合唱曲像洶涌的河水,從細密的格子
涌出
淹沒了一盞十五瓦白熾燈投下的暗影
當他刻完那個休止符時,長長地打一個哈欠
一個年代多聲部的激情,夾著他的煙草味
唰唰唰地油印出來。他的鋼板和鐵筆
像船和槳,靜泊在從窗外透進來的晨光里
萬家燈火是一條安謐而忐忑的河流
萬家燈火
是一條安謐而忐忑的河流
仿佛失而復得的愛,用舊帆船
運回了從郵箱走失的情人
燈光扛著梯子走過一條條大街
連人世間的強人,都逆著光陸續回到了家
一朵漣漪在打撈另一朵漣漪
那燈河的骨折處,歲月的沉船想浮起來
想用鐵銹去取悅今夜啤酒的泡沫
光影在一個人的左臉上重新劃分生活的邊界
在明暗的指縫間,有人在給一襲旗袍放生
最幽魅的那一盞,是城市肺部的航標燈
對應著時間下面低燒的黑礁石
廣告燈在練習組裝一雙雙翅膀,那時
我還在反復修葺著一朵朵發光的浪花
在擦傷的暗影拐角處,一個尋虎者
從虎骨酒里猛地跳了出來
羊角錘
我可以寬恕,一只鐵器
擊碎愛情的雙層玻璃
我也可以寬恕,尖嘯的玻璃
以慢鏡頭的方式,從心口處劃出一個人的血
我甚至可以寬恕,一個人流出的血不夠純潔
那是歲月入侵他的血里,秘密產下了蠅卵
但是我不能寬恕,那揮舞在我們頭上的
一把羊角錘,包括它橫暴的名字
我不知道
羊角,這羊身體中善良的偏旁部首
從何時開始,跟一塊冷硬的鐵媾和起來
那是誰,讓羊角進化成為一把鐵錘,成為
用釘子擊穿我們靈魂的工具
當一個人像羊一樣逃出命運的擊打聲
在呻喚中垂下眼瞼,那把羊角錘
依然在薄光的圍欄上旁敲側擊
描述一次被雷電擊中的遭遇
那時我感到自己儼如坦克一樣勇敢,在雷
雨中
青春是身體里的避雷針
一個人像穿著長筒水靴的近衛軍,一路穿過
帶電的建筑、樹林、積水、高壓線
甚至吹著口哨,爬上了尖塔形狀的山頂
那山體下面有一條湍急的礦床,在吐出火
光的蛇芯
就是那一次,隨著頭頂的一聲爆響,我被
雷電擊中了——
我的頭部、頸部,以及手臂
有一萬只螞蟻在爬走,仿佛在繪制著電的
地圖
我的頭發豎起,像厲鬼一樣,驚恐的呼喊
響徹山谷
一個蔑視常識的人,絕望的呼叫聲被暴雨
拖遠,稀釋
——這是雷電給我上的致命一課
至今,每到雷雨季我沉郁的靈魂仍在戰栗
當歲月的滾滾奔雷涌過頭頂,請原諒我變
得怯弱
請原諒我,學會了在閃電欺身時的自我保
護——
兩腳并攏,身子下蹲,雙手抱膝,像命運
一樣低下頭
在強力的震懾中,正如一個失去反抗的被
俘者
有限度的贊美
新的一天開始了
電動窗簾把一個人平生的一頁徐緩打開
世界像一頭猛獸,在伸懶腰,打哈欠
它夢中抖下的灰塵落滿我的亂發
當露珠還沒來得及晨禱
萬物已經開始搶著發言,甚至爭吵
我在一杯牛奶里,區分青草和商業的味道
帶甜味的晨風,是否也為窮人遞來了陽光
早餐
一個綠色郵差穿過紫荊花的河流
郵包里的早報從印刷廠的氣味探出頭來
飛跑的單車比新聞還快
快得連早操都跟不上愛情的節拍
那個作家開始繼續寫一篇連載小說
我猜測在今天的章節里,我還是不是主角
但我習慣性地準備好出門的行頭
試圖幫助生活完成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
當天空把大地推向地平線那邊
而我,竟還觸摸不到一個微小靈魂的邊際
我知道新的一天還在昨日的鏡子里比畫
歲月,依然保持著半翅飛翔的姿勢
此時一只鳥跳出籠子,向我道聲早安
那真實而單調的聲音,正如
我對新生活,保持著有限度的贊美
【劉頻,上世紀60年代出生,柳州市作家協會主席。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文學雜志持續發表大量詩歌,出版詩集《浮世清泉》《雷公根筆記》,作品入選國內權威詩歌選本及其他數十種優秀詩歌選本。近年來詩歌獲廣西文藝創作銅鼓獎、廣西首屆年度作家獎,先后三次獲《廣西文學》年度優秀作品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