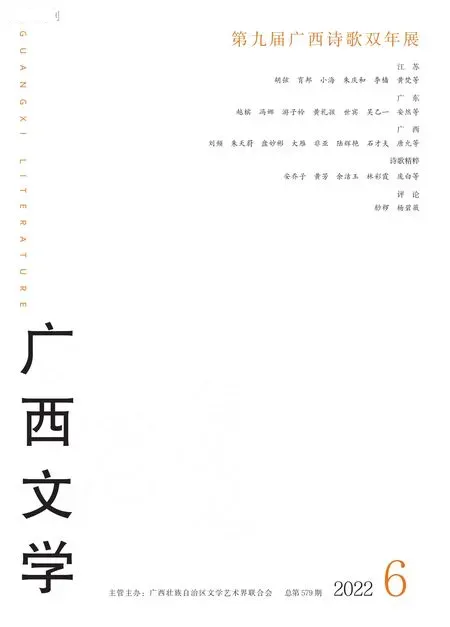馮娜的詩
雙河溶洞
太久了!七億年
“水滴石穿”不是時間的修辭
不是面壁者不可參破的奧義
而是熔巖之火,和一個詩人語言內部的癲狂
地表的頌詞來自繁衍
穿越地心的陰性之美
脫離了肉身所能承受的孕育
它用匕首的鋒利,在自己的身上雕刻
——光線沿著鈣化的模子
幽暗中,一只蛹還來不及羽化
暗河封印了鳥的振翅
和巖羊咀嚼蕨類植物的沙沙聲
太久了,絕壁之上的開鑿
注定也要鏨出一句詩的刻痕:
那荒野的眼睛、雄性的蠻力
匍匐于寒武紀、白堊紀的脈動
要跋涉多久
才能在沉積的體溫中豎起一壁石幔?
要浸泡多久
才能在母體的淚泉中結晶成花?
當幽簾蟲、蝙蝠和人,這些有限的肉身從
中穿過
黑暗便有了新的名字
洞窟也不再僅僅屬于雙河的漲落
在它的穹頂,星斗在旋轉
——世人將它視為浩瀚奇景
詩人則將它稱為時間之詩
蝴 蝶
雙翅間,藍色的光脈涌動
翠蛺蝶、嘉翠蛺蝶、蛇神黛眼蝶……
博物學家的凝視讓它們擁有石化的瞬間
那楔狀的鱗翅目,猶如鐘乳石垂懸
這天黃昏,詩人李元勝的鏡頭捕捉著溪中蝶
它們歡快地振翅,抖動著雙河洞口的風
沈葦想起懷中還有一只西域之蝶
它的斑紋是沙麗纖維,曾在哈薩克人的宴
飲中現身
“碧溪潮生兩岸”
陳先發的蝶,是否也在此地找到了前身?
好在詩人們只是美的采集者
捕掠蝶翅的納博科夫仿佛從石階上趕超了
他們
“暮色中眼狀花紋的蝴蝶翅膀從四面盯著
他看”
——那“欲念之火”便是蝶的軟喙
那“生命之光”,白令海峽失事的船只
標本柜中再也無法訴說的故事
當我彎腰,入侵者的氣息讓蝴蝶驚起
但不遠飛
鴿 子
特拉法加廣場的鴿子和我父親養的一樣
毛翼灰白、雙爪纖細
眼珠骨碌碌轉動,映出褐色的屋頂
廣場的鴿子,繞著歷史書中的建筑飛
羽毛干凈、見過世面的鴿子
踱著方步,啄食人們手中的面包屑
有時歪著頭,打量著黃皮膚的來客
廣場上永遠不會有父親的鴿子
它們膽怯、卑微而警覺
即使被賣給遙遠城市的客人
三個月后也會飛回自己家中
來自小地方的鴿子
一定不習慣在游客手中進食
它們能飛過山峰,卻留戀著自己小小的鴿籠
寬敞的廣場上,鴿子簇擁著我
我與它們一樣,羽翼清晰、爪子輕靈
而我,懷揣著一顆饑餓的胃
想起了小小的鴿籠
姆比拉
姆比拉,來自非洲的拇指琴
用指頭叩出礦石的裂痕
尼羅河,也曾流淌過沙質的圣歌
——摻雜著麋鹿的膻氣
雌獅咀嚼骨頭的聲音
姆比拉,金屬從杯子中飲酒
羚羊群躍過巖洞
裸著上身的人,邀請赤道舞蹈
姆比拉,坦桑石在融化
風暴和烈日在沙漠中炫耀
白晝堆滿異國的緞子和蠟燭
姆比拉,一棵可可樹折斷自己的樹冠
夜晚白白等待著陌生人的身體
他用手抹去灼燙的水汽
在他干旱已久的眼睛里
貧瘠的姆比拉,正下起大雨
愛 墻
蒙馬特高地半山腰的一個小公園里
一面藍色墻上
用311種語言書寫著“我愛你”
——人類是多么渴望愛啊
從城市、部落到偏僻的海灣
混雜著大多數人終生不會精通的語言
從生澀的語法中得到愛
比起砌一面愛墻,更加艱辛
每個人尋找自己熟悉的語言
他們默讀著自己的心
——但我知道這不是愛
太過秘密的事物,不再需要愛的軀殼
我寄望讀出陌生語言中的“我”
那是看不見的陰影旅行中的濃霧
是我感到悲傷時“你”的音節
是建造者未完成的遺愿
我坐在一個無人說話的公園里
我替你感到悲傷
——我知道,這也不是愛!
【馮娜,1985年出生于云南麗江,白族。畢業并任職于中山大學。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廣東文學院簽約作家,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創意寫作中心特聘導師。著有《無數燈火選中的夜》《尋鶴》等詩文集、譯著十余部。作品被翻譯成英語、俄語、日語、韓語等多國文字譯介到海外。曾獲中國少數民族駿馬獎、華文青年詩人獎、美國The Pushcart Prize提名獎等獎項。參加詩刊社第二十九屆青春詩會。首都師范大學第十二屆駐校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