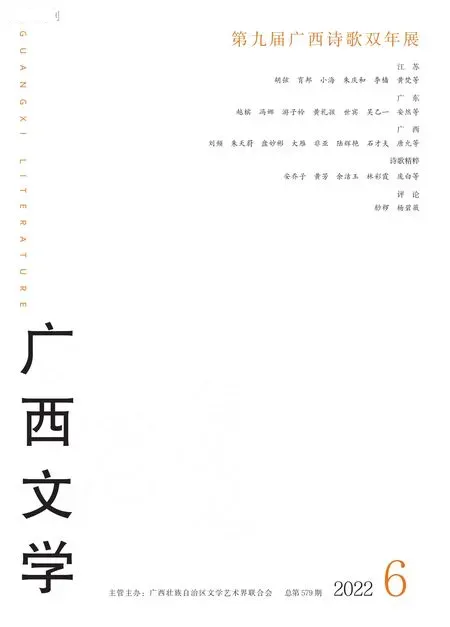越檳的詩
鮭魚夜溯
圣物不傷,只在全無和全有中
游動,詞語敞開了它的小傳達室
而大月亮輕運著它幽靈的百貨
世界是只剛剝好的蛋,緊挨著它
蛻下的一小堆碎殼,在莫之能御的
每個激流中,我參與了我的誕生
我們在詞的大霧中緊抓著周圍
三米的生活不放,像極了異教徒
緊抓著他隱蔽的神,只有大融大化
發生時,才能找到與宇宙十分鐘
宏偉的共生感。夜只是一小間沒有
神父的告解室,入夜不亞于入藥
每處黑暗中都備好了一本打開就是
合上的圣經,而且很像我們自己
幾乎在任何情況下都能點得著
我已在人何以不死的那根刺上
學過百種戰栗,也不止一次見過
您火焰中的死友。正如能不斷證實
自身的水才是浪,不去創造一個
全新的秘密,您就什么也無法占有
再次受傷、變得更少直至璀璨
而完全的沒有就是見神的唯一方式
于是我們開始洄游,在克服引力
的漲潮計劃中,沒有游出來的部分
才是鮭魚,我無法抵抗它,它也
吞噬不了我。其實游和不游都一樣
危險,因為水全漫上來了,游得
過快或過慢,就什么地方也去不了
我們游著,但并非只用鰭和尾而是
用全部自我在游,只在能夠藏得
更深的地方才會現身。所有鹽都在
閃耀的貧瘠性中經過暴烈的重組
我們必須靠活不過今晚的東西活著
更多時候我們在舞著,一切獨舞
毫無例外都是和看不見的自己共舞
怕不怕?舞完了就是換他來生活
鮭魚夜溯,不過是為了重新成為
鮭魚,在逼近那個迫切的開端途中
我們不得不首先成為一種新河水
游到后面根本不是為了抵達,只是
為了能繼續游著,游著恰恰不是
因為我還在,而是因為我已經不在
游著首先是種很深的愛,否則就
只是在宇宙中多弄出幾個水花而已
實際上誰也無法游近誰,我最多只能
讓你游近你自己,我也不在你能
找到我的地方,在小毀滅到來之前
我根本沒有可能完全理解我自己
水對于你來說太深太急而且太冷了
我這就連夜游過去,不需要擔心
我的身體,游過去了,才會有身體
重看穆勒咖啡館
當一個人滿身是夜,開始跳舞
再怎么孤獨也是不夠的
跳之前她是皮娜·鮑什
跳起來后理應一無所是
跳,就是不求存在地去成為
正如自轉之甜供應著天體
一圈又一圈無我的神圣空行
當舞者不斷從伴侶身上滑落時
滑落成為我學會的首個與愛
有關的德語。音樂里也有這樣
奇怪的律法:在神的管口最細的
地方,都應該只由人來充滿人
任何想要觸摸我的手,無一例外
必須是從我自身中伸出的才行
屬于火焰的時間不是太少就是
太多,不止一次了,她和毀滅
在同一軀體里共度過兩個鐘頭
這已經不是舞蹈了。但只有這樣
才沒有一種痛苦可以壓倒一切
單獨成為皮娜·鮑什。這正是舞蹈
還沒有跳,她就已經在里面了
在她肉身沉降的枯瘦皮下,明顯
有幾條命互不相讓地擰在一起
除了她,還有人在順著這條繩索
往上爬。還是那句話,人除了跳舞
與不跳舞根本不應該有其他分類
無遮蔽頌
那些辨認過我天性的火,現在
只是遠遠地在城外燒著,再也不
考驗什么,像個小地方來的神
只帶著一小塊任人消耗的夜
想要從此躲在幽暗中,我必須
以滿月為約束,以不可能性為夜
夜才會更接近湖底,再撥一撥
冰冷的水,我這就躍入湖水中的
自己。人都是按照他堅決不去
打開的門窗在死亡的,活下來的
全活在遠遠的水下,并且帶著
不可抗拒的島的強烈天性,終于
與細浪的知覺形成了堤岸似的同謀
想必你也料到了,我一直都在
逃離,實際上又沒奔向任何一處
正如不可見之物騎著可見之物
飛行以制造良夜,所有詞都過著
這種不會落下來的生活,除非
換一條真命。假如良夜也有底部
我想這就是了,像一條真正的沉船
那樣,波浪要如何沖擊我都可以
每一次愛的鐘聲都是從這里發出的
你一定要敲敲我的,真的,我比
其他的更空、更深、更有回響
水畢竟有肉身可近而火只有靈魂
我總是先從另一個人那里得到
火焰,再從這點火焰中得到自己
之所以長久望著星辰,一定是
因為自己也燒起來了,這一次我
不必再從枯枝敗葉中尋找前身
也不打算用燈籠紙來做任何抵擋
更不會化成余燼后才為你所見
這一次愛的煙霧更加早慧地升起
我是真的燒起來了,四周空無一物
不必再用別的東西來隱藏我自己
【越檳,1993年生于廣東汕頭,寫詩,現居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