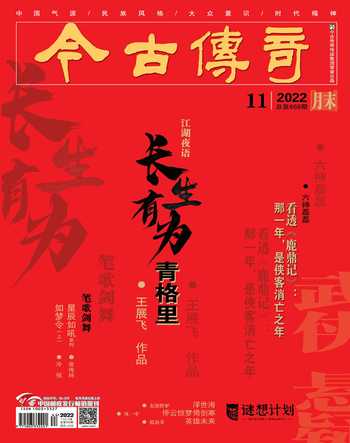看透《鹿鼎記》:那一年,是俠客消亡之年

一
金庸的最后一部書,是《鹿鼎記》。
在這部書里,有一回特別重要,就是第三十四回,讀《鹿鼎記》要特別注意這一回。該回出現在全書大約三分之二處,回目詞叫做:“一紙興亡看覆鹿,千年灰劫付冥鴻”。
這一回的大致情節是韋小寶從云南出使回來,行至柳江,和師父陳近南、天地會英雄吳六奇等人相會,又遇上了大風雨。眾英雄在柳江上冒雨泛舟而歌,很有詩意,可以說是整部書中最有詩意的一回。
群雄泛舟的那一幕,天上風雨大作,江中白浪洶涌,一艘小船載著眾多豪杰,外加一個膽小如鼠、一直嚷嚷著怕被淹死的韋小寶。生角和丑角鬧哄哄一堂,好笑之余,又有豪情蓋天,氣勢如虹。
韋小寶的膽怯,正襯出天地會英雄們的豪邁灑脫,視生死如同兒戲。這些都是好情節、好文字。然而,所謂的“壯志豪情”,不是這一回的真調子,只是個幌子,是金庸故意設的幌子。就好像所謂的“鮮花著錦、烈火烹油”,也不是紅樓夢的真調子一樣。
《鹿鼎記》這一回的真調子,是壓抑、悲愴、大勢已去、壯志難酬。
這一回里,吳六奇在江上唱了一首曲子,是大名鼎鼎的《桃花扇》里的《古輪臺·走江邊》:“走江邊,滿腔憤恨向誰言?老淚風吹,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盡殘兵血戰。跳出重圍,故國悲戀,誰知歌罷剩空筵。長江一線,吳頭楚尾路三千,盡歸別姓,雨翻云變。寒濤東卷,萬事付空煙。精魂顯,《大招》聲逐海天遠。”
這才是這一回的真調子,也是《鹿鼎記》全書的真調子。“寒濤東卷,萬事付空煙”,是陳近南的結局,是吳六奇的結局,是天地會事業的結局,是《鹿鼎記》的結局,是一切俠客的結局。
二
這一回里,處處是讖,韋小寶便是出口皆讖。
柳江中的船上,有兩撥人在說話,一撥是天地會群雄,一撥是韋小寶。
表面上看,天地會群雄如陳近南、吳六奇、林興珠、馬超興等,說的都是英雄語、英雄話。他們形象正面,白馬銀槍,逸興遄飛,舉手投足都是英雄之氣。唯獨韋小寶一人是丑角,滑稽搞笑,膽小怕死,一直胡言亂語、插科打諢、大驚小怪。
然而真相卻是,群雄說的話盡是幌子,韋小寶說的話才是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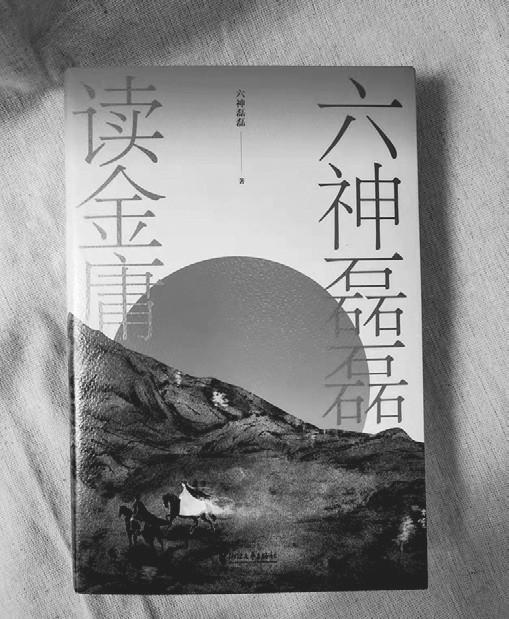
比如天象要變了,大風大雨將至了,第一個說破、說穿的就是韋小寶。他說:“那邊盡是黑云,只怕大雨就來了”。
韋小寶是對環境、對未來最憂心忡忡的人,也是全場對“黑云”“大雨”最敏銳的人。好一個“那邊盡是黑云”,不但“是”,而且“盡是”,再聯想天地會群雄后來的命運,豈非“盡是黑云”?
再看一個情節——大英雄吳六奇藝高膽大,提議把船駛到江心,要到大風大雨中暢飲。韋小寶卻怕死,一再說:“這艘小船吃不起風,要是翻了,豈不糟糕?”
這話當然不夠體面,英雄好漢豈能怕船翻了?
然而最后,天地會的船不是翻了嗎?吳六奇最后不是身首異處了嗎?反清復明的大業最后不正是“吃不起風”,終于傾覆了嗎?
那一日,那一刻,韋小寶說的每句話,回頭看都是讖語:“乖乖不得了!”“啊喲,不好了!”“什么戲不好唱,卻唱這倒霉戲?”“你要沉江,小弟恕不奉陪。”可謂句句應驗。
吳六奇最終蒙冤橫死,韋小寶卻安然得脫,豈不是正應了“你要沉江,小弟恕不奉陪”?
莎士比亞筆下的大劇里,總會安排一個伶人、小丑,動輒說破天機。韋小寶,就是這個說破天機之人。
三
除了韋小寶的“讖”,這一回里還有陳近南的“老”。
你會發現陳近南在這一回里突然老了,“心死著寒灰”了。他是大英雄,江湖上聲望卓著,所謂“平生不見陳近南,便稱英雄也枉然”,什么時候憔悴過?
可這一回里,大英雄陳近南突然現出了老態,就像一位明星倉促忘了染發,露出了白頭來。韋小寶猛地發現,過去那個英姿颯爽的師父蒼老了,“兩鬢斑白,神色甚是憔悴”。
風雨飄搖中,陳近南毫無征兆地向韋小寶說了一番心里話。他“神情郁郁”“滿懷心事”“意興蕭索”,對自己為之奮斗的反清復明的事業失去了信心,對韋小寶說了一句:“唉!大業艱難,也不過做到如何便如何罷了。”
陳近南居然在徒弟面前說出這樣的話來,可見不是大業艱難,簡直是大業無望。
他還突兀地說出了一個“死”——
陳近南走到窗邊,抬頭望天,輕輕說道:“小寶,我聽到這消息之后,就算立即死了,心里也歡喜得緊。”
這是提前埋下了陳近南的結局,也是讓陳近南自己提前預言了自己的命運。
那么,陳近南何以意興蕭索?是什么讓他覺得大業艱難?書上有一段他說的話,給出了部分答案:“小寶,你師父畢生奔波,為的就是圖謀興復明室,眼見日子一天天地過去,百姓對前朝漸漸淡忘,韃子小皇帝施政又很妥善,興復大業越來越渺茫。”
這段話里已經講了幾點原因:一是日子一天天過去,二是百姓對前朝漸漸淡忘,三是韃子小皇帝施政又很妥善。總之就是,時間窗口錯過、民眾無法爭取、敵方沒有破綻,這三樣,哪一樣是陳近南可以徒手改變的?
此外,在這一回里陳近南還說了第四點失望的原因:己方陣營日趨腐朽和昏聵。
他所效忠的對象是臺灣鄭氏。那里的首腦人物缺乏才能和眼光,如韋小寶所說,掌權者太妃是“什么也不懂”,繼承者二公子則是“糊涂沒用,又怕死”“他媽的混賬王八蛋”。一個什么也不懂的加上一個混賬王八蛋,陳近南拔劍四顧,徒勞無功,焉能不意興蕭索,反清復明大業焉能不艱難?
真是李白所謂,“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
四
在金庸精心設計的這一回里,陳近南的蕭索還不只代表他個人,也不只代表天地會。
他的屬性是“俠”,是《鹿鼎記》里最大的一名俠客,也是最后一位俠客,同時,他也是金庸筆下最后登場的一位傳統意義上的俠客。他武功高強,為人端正,仁義禮智信兼備,是一切“俠”的美好品質的集大成者。
而金庸偏偏在這一章里寫他意興蕭索、窮途末路,寫他的事業走入絕境。
陳近南的窮途末路,正宣告了“俠”的窮途末路。事實上,在這一章里共有三位俠客的告別。除了陳近南、吳六奇,還有一位白衣尼,她也是在這一章留下字條、不知所終的。
這一章是俠客的集體謝幕,堪稱俠客之終章。
金庸何以對“俠”的前途如此不抱希望?之前陳近南已經說出了部分原因,時代滾滾向前,民眾無法爭取,在這樣的現實面前,俠已經無可能為。而這一章的后半部分還精心寫了兩個情節,更耐人尋味。
一個是“外國鬼子”南懷仁操演新式大炮,書上還借康熙之口,介紹了之前研究的新式天文歷法,編制《大清時憲歷》的軼事。
另一個是韋小寶率領水師炮轟神龍島,在大炮面前,偌大的神龍教被打得瓦解冰消,毫無還手之力。
金庸提醒我們,歷史已漸漸邁入近代,現代文明已到了門口,俠客更加尷尬,更加無力了。
要退場,就退得徹底。在寫陳近南這最后一尊“俠”的圣象崩塌的時候,金庸眼中當有淚光,但筆下絕無容情。
他把俠的虛弱暴露給你看,少有地披露了他的蒼老和蕭瑟。
之前所有的俠,都絕無蒼老感,亦絕無衰敗感。郭靖、楊過留給我們的都是壯年鼎盛形象。袁士霄、謝煙客、苗人鳳們固然不會衰邁,哪怕張三豐、周伯通等百歲老人也從不曾當真衰邁。
可到了陳近南,卻真真實實讓他蕭瑟給你看了,無力給你看了,好比少年衰朽,美人遲暮,青絲褪去,老年斑冒出,身形佝僂,步履蹣跚。
格外傷人的,是陳近南還渾身帶著一種落伍感和過時感,他的事業被時代拋離,他恪守的教條與眼下的世界格格不入。
他像是一個守衛著古老墓園的衛兵,這園子早已經被人淡忘和拋棄了,他荷戟彷徨,無語地值守著,只等著自己有一天倒下,成為這座墓園的最后一個永眠之人,然后和那無數上古英靈一起,被野草和荊棘吞噬,被歷史的巨輪碾過,只殘余巨大的車轍。
金庸甚至都沒有給陳近南一個體面光彩的死亡。
從前的大俠,幾乎都有一個配得上自己分量的體面死亡。蕭峰之死,六軍辟易,英雄揮淚;洪七公和歐陽鋒之死,在華山之巔縱聲長笑;覺遠大師圓寂于野地,卻也不乏寧靜莊嚴;丁典毒發斃于荒園,但為愛而死,甘之如飴。
唯獨一個陳近南,這個最后的俠客,偏偏讓他稀里糊涂地死于宵小之手。
哪怕是死于施瑯之手,死于馮錫范之手,死于戰陣,死于法場,也都算得上是一代大俠的歸宿。可他卻是被鄭克塽這種爛人背后一刀,就此了賬,不值不當,不明不白。
金庸就是不讓你死得輝煌,他要打消你對“俠”的一切殘留的幻想,告訴你人被歷史碾壓的時候就是這樣不值不當,無聲無息,沒有尊嚴。
五
金庸自己,其實也走過了一個漫長的心路歷程。
此時此刻,已經寫到了最后一部書的他,心情狀態也和當初寫武俠時不一樣了。
金庸起初寫武俠,寫百花錯拳,寫胡家刀法,寫東邪西毒,寫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寫得興致勃勃,像一個孩子,在光怪陸離的世界里游戲。
史航說過一段話:當初在《神雕俠侶》結尾,黃藥師布下二十八宿大陣,天下英雄熱熱鬧鬧會戰襄陽,但凡像個人樣的好漢都聚在一起。那一刻,是金庸作為作者最幸福的時光,是他跟這個世界的蜜月。
的確是這樣。
那時候,金庸還相信人定勝天,相信“俠”有改變格局的偉力。后面就不是了,而是風驟緊,縹緲峰頭云亂。
他筆下漸漸多起來的是人性無解,是個人和歷史之輪猝然碰撞時的無力。理想主義太無力了,降龍掌也好,凝血神爪也罷,通通都無力。
終于時間進入1969年,他寫《鹿鼎記》,他已無法相信“俠”真能解決什么現實問題了。他大概已得出結論:“俠”不能救贖世人,而自得其樂的癲狂世人也根本不需要“俠”的救贖,“俠”其實連自己也救贖不了。
這時候的金庸,佇立在浪漫主義小徑的盡頭,前方沒路,也再不可能返回身,重新去寫那些熱鬧的、樂天的東西,重新去擺一個二十八宿大陣。
他只能卸劍解甲,眼含熱淚,擁抱陳近南,和“俠”拱手揖別。
于是,在恰到好處的《鹿鼎記》第三十四章,一場大風大雨里,金庸安排了陳近南蕭索的身影,以及一曲“寒濤東卷,萬事付空煙”,作為俠的謝幕。
過去的一切俠客,阿青、慕容龍城、無崖子、蕭峰、虛竹、洪七公、黃藥師、陽頂天、張無忌……這一切俠客的身影,最后都重疊化為了陳近南的影子,與我們莊嚴地告別。
六神磊磊,本名王曉磊。知名媒體人,作家。曾任新華社重慶分社記者,長期從事時政、政法報道。2013年開設專欄“六神磊磊讀金庸”,文章廣受歡迎。在金庸小說已然被眾多讀者反復解讀、詮釋的情況下,六神磊磊的金庸解讀仍然脫穎而出,以其犀利、獨到的視角獨樹一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