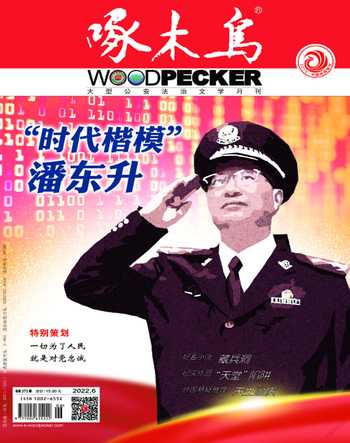72層磚的墻(小小說)
莫小談

“1,2,3,4……”猴子盯著面前的那一堵墻,數墻磚,總共72層磚。再往上是電網,交錯著幾條高壓線。
耳目發現了猴子的異常,轉頭向我報告,說:“猴子有陰謀。”我請耳目坐下說話,他咽了一口唾沫說:“隊長,我懷疑猴子有陰謀,他要越獄。”
“越獄?”我不禁驚出一身冷汗。
“是的,猴子要越獄。”耳目怕我不信,又說,“隊長,猴子每天放風時,都會盯著院墻看,嘴里還不停地數著數。”
“數什么?”
“數墻上的磚。”耳目說,他特意留意了一段時間,并隨著猴子的目光轉換著視角,結合猴子的口型,他斷定是在數墻上的磚層。
我隨即查閱了猴子的檔案——故意傷害罪,刑期兩年半。
猴子傷害的是梁大佐,他的鄰居。梁大佐家建房,將一溜兒院墻壘到猴子家的宅基上,他哪肯讓步,一來二去,兩人就杠上了。族里人出面調停,梁大佐就胡攪蠻纏,前三皇后五帝地往前翻舊賬,把祖上八輩的破事兒都抖落出來,歪理摘下一籮筐。族人們一時也捋不出眉目,只好撂下。難怪,當事人都化骨成灰了,誰還能說得清。
案發當日,梁大佐酒后裝醉,跑在村頭跳腳罵娘。猴子是孝子,聽不得這話,于是沖出去朝梁大佐頭上擂了一拳,耳膜穿孔,是輕傷。梁大佐這回可逮住了理:“我梁某人被猴子開了瓢,以后還咋在溱水河一帶混?”橫豎就那一句話,“不和解,公事公辦,判他幾年是幾年。”
猴子憋著一肚子氣,悻悻地進了監獄。
按說擔這罪名的人不會干出啥大事兒,用“過來人”的話說,“三兩場雪的事兒,打幾個激靈就過去了”。但既然得了線報,作為監區隊長,我還是提起萬分警惕,于是打電話向猴子的村長了解情況。村長說:“猴子是泥瓦匠,常年壘房砌墻,前段時間右腳還在工地上受了傷,平時走路看不出來,就是掏不了大力氣。”村長以為是為猴子減刑,就使勁兒美言,說猴子是個老實人,被捕時說的“出來就給姓梁的放血”那句話是氣話,不能當真。
聽完村長的介紹,我心中大體有了尺寸,但村長口中的“老實人”不能當作排除他預謀越獄的依據,老實人往往辦大事兒,何況他還說過“給姓梁的放血”的話。
我想,是時候會會這個“老實人”了。于是,我把猴子叫到辦公室,開門見山地問他會啥手藝,他嘟噥半晌才說會砌墻。我壓著嗓子,故作深沉地問他會不會爬墻,他不假思索地說:“會,從小就會,村里人誰還不會爬樹翻墻?”
“你是泥瓦匠?”
“是。”
“砌過墻?”
“是。”
“砌墻用磚不?”
“用。”
“一塊磚有多厚?”
“五分半吧。”
“那砌一堵72層磚的墻,有多高?”
“加上沙灰,差不多四米吧。”
“加上電網呢?”我追問他。
猴子好像意識到什么,頭上一下子沁出汗珠。我又問他,想家不?他說想,緊接著就使勁兒搖頭,像撥浪鼓似的:“不,不想,不想家。”
我起身離座,故意在他面前踱步,找一個恰當的時機,抬手指著窗外的高墻問他:“你想沒想過,不走大門,從那里爬墻出去?”猴子急了,他一邊擦汗,一邊不住地賭咒發誓,說自己從沒動過翻墻的念頭,否則天打五雷轟。或許,他認為賭咒是自證清白最好的方式。他終究是個“老實人”,繞了一百圈也沒有卡到正點上,無法證明自己不具備越獄的基礎。其實,我內心早已有了基本的判斷,村長不是說了嗎,猴子的右腳因傷掏不了大力氣,連走遠路都費勁,怎么可能會越獄?但我需要他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為什么每天要數墻磚。
“我不是在數磚。”猴子說,“我是在數天。”
“數天?”
“是的,在數天。”猴子說,他是泥瓦匠,當然對墻磚很敏感,剛轉到我監區的那天,他就發現高墻上的磚共有72層。從那天算起,離他刑滿釋放整720天。“我就天天數磚,每隔十天就用目光在一層磚上刻個印記。”猴子說,等把72層磚全刻完了,他就可以曬大墻外的太陽了。
這次談話使我徹底排除了猴子的“越獄”嫌疑,但也同時發現他的另一個心結,令猴子始終耿耿于懷的還是梁大佐,說他姓梁的侵犯我家宅子,還跳腳罵娘,興他欺負人,就不興我反抗?“蓋在我家的那一堵墻還在,堵心,咽不下這口氣。”猴子說這話時,滿眼仇恨。
從那日起,我覺得如何讓猴子順下這口氣,非常重要。當然,這難免會費一番周折,不過沒關系,我已經交給村長操辦了。具體操辦的細節如何,村長沒說,我也沒有問,只知道猴子出獄時是梁大佐過來接的,他還為猴子準備了一身新行頭,從頭到腳,全套都是新的。猴子起初不要,大步朝前走著,梁大佐就一路小跑緊隨其后,一直哈腰追在他的屁股后面。兩人拐了個彎兒,走出了我的視線。
后來,我曾偶遇過一次猴子,問他現在忙啥呢,他說歲數大了,早干不動泥瓦匠了。聊到健康狀況,他說現在身體不錯,腳傷也慢慢好了。我打趣他,能爬墻不?他咧嘴嘿嘿一笑說:“能爬也沒墻爬了,大佐在我回家之前就把那堵墻拆了,如今兩家小院攏成一個大院落,孫輩們滿院打圈跑,敞亮得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