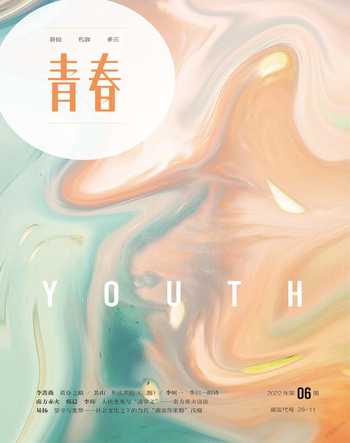守林人
一
窗外的大雨令我回想起我離開家鄉前的最后一個晚上。
那天傍晚,我去在外租房的女友家吃飯。兔子廚藝不精,只會做些清淡的素菜,譬如炒白菜,胡蘿卜炒白菜。餐后,我們在她的房間親熱。由于知道我隔天要走,她較往常更熱烈了些。那期間下起了雨,她的房間拉著窗簾,因此看不到外面的雨勢,聽聲音應該是一場大雨。
之后,我提出想看雨。我們兩人光溜溜赤著腳走到陽臺,活像兩條剛從雨后的泥土里鉆出來的蚯蚓。陽臺的地面上落著一層灰,因為沒有窗簾,除了晾衣服,她很少來這里。好大一場雨,而且看勢頭似乎越來越大,落在樓下自行車車棚的塑料瓦上,簡直像老式電視機天線斷掉之后發出的嘈雜的噪音。
陽臺的窗戶對面是一家賓館,兩棟房子間隔很近,只有五米的距離,沒有窗簾,她不敢過來。我說沒事兒,雨大,對面看不見。我們倚著窗檐看路上的人躲雨,兔子的腳底踩了一層細細的灰塵,這又激起了我的情欲。激烈的雨點零星地濺到兔子的身上,七月的熱空氣像毛毯一樣包裹著我們。
那晚我就睡在她家,火車第二天下午開,去北京的火車,我將要去那里找工作。我既不知道會找到什么樣的工作,也不知道我會去多少年。那晚的雨一直沒停,簡直就像要把我們吞沒了似的。
二
龍仔比我早一個星期去,他找好房子,投了簡歷,等我到了,也好有個落腳的地方。我和他是大學同學,讀同一個專業,他主攻攝像后期。我是個技術盲,大學時代一門心思撲在看書上,幾乎手不釋卷。我們不是一類人,甚至懷著截然不同的信念和喜好,恰好聚在一起四年。
臨近畢業,他問我去哪兒,我說,不知道,要不一起去北京吧,年輕人要去大城市奮斗一把。他說,也行。于是,我們各自回家和親人朋友道別,約定七月中旬在北京見面。
龍仔家里是做生意的,他的奶奶能生,育有九個子女,到了他這一輩,人數又翻了幾倍。他家族里所有的男丁都做拉鏈生意,每個叔叔占據一個沿海城市。父親在威海,他小學的時候父親把家人接了過去,在那里扎根生活。
在決定去北京之后,我問他,為什么不直接回家接替家族的生意呢?他說,還是想出來闖一闖啊,畢竟還是喜歡藝術。他說,他爸給他兩年的時間,能闖出點名堂,可以留在外面,不然就要回家學做生意。我聳聳肩。我既沒有家族,也沒有后路,父母又比較開明,只要自己能養活自己,想去哪里都可以。
我的火車早上到北京。我和龍仔在他租好的房子里碰了面,房子在望京,十三樓,推開窗戶可以看見小區里小學的操場、幾棟三十層的住宅樓、三層的停車場、頂樓被建造成供人散步和晨跑的環形小花園,以及帆船形狀的望京soho大廈。我拍了張照片發給家鄉的兔子,告訴她,這就是我在北京即將展開的新生活。
三
一個星期后,我找到一家小出版社,做圖書的營銷編輯。龍仔去了一家中關村的“格子間公司”,他的老板有好幾家這樣的公司,經常來回跑動,很難見到本人,平時辦公室里只有他和一個美國籍的日本記者。他應聘的攝像師崗位,結果基本沒什么機會出門拍攝,平時就坐在格子間里配字幕。
我去的那家出版社,總社在南方,北京的分社小得可憐,擠在五環處一個辦公樓的十八層,與同層的四五家公司共用一個廁所。此社是個老牌國營出版社,據說二十世紀末輝煌過,之后因為辦公室政治弄得分崩離析,幾乎垮掉,最近幾年才略有復蘇跡象,是因為現任的分社長手腕強硬,辭退了一批等著退休的老干部,招來一些年輕人。我也是年輕人中的一個,只是我進來后才知道,我是社里嘗試招來的第一個應屆生,在公司里年齡最小,倒數第二小的年輕人上個月剛滿三十。
工作大致穩定之后,我打電話給兔子匯報情況,我說:“工作還不錯,老板看了我得獎的那篇書評,覺得我寫得很好,大力贊揚我,給我開了和在這工作五年的人一樣的薪水。”她問我:“做什么工作,寫書評嗎?”我說:“可能順帶著寫一點,但是主要工作不是。”她問我:“主要是干啥?”我說:“圖書營銷。”她說:“營銷和書評寫得好不好有啥關系?”我說:“沒什么關系,老板說是這個崗位空缺著,讓我先補上,以后再給我調。”她嘟囔了一聲,沒再說話了。
我聽出來,她不太開心。我說:“我想你了。”她說:“噢。”我說:“你好好加油,明年爭取存到錢,說服你爸媽,來北京找我。”她沉默了一小會兒,我的聲音像是穿行了格外長的距離,才傳到她的耳朵里。后來她沒有再說話。
掛了電話后,我站在窗臺前抽了支煙。夜色轉深了,除了小學操場和停車場外,其他的樓宇燈火通明。北京的夜晚像一塊不吸水的海綿,黑色無法浸透進來。相比之下,我家鄉的夜晚深沉得多,除了路燈和樓房里幾點零星的光亮外,幾乎一片漆黑。
我想象著那些謎一樣的燈火背后,有誰在做些什么,也想我的未來,我的兔子。這時下起雨來,嘩啦啦越下越大。一會兒工夫,就能聽到街道上的車輪濺起水花的聲音了。我把手臂伸出去,讓雨水順著它往下流。這便是那場令我回想起離開家鄉前的最后一個晚上的大雨。
四
兩個月后,我摸清了這項工作的門道,也開始對它感到厭煩。每天的日子不溫不火,早上八點半掙扎著起床,擠人最多的那趟地鐵,坐四站,中途換乘一次,在公司樓下買一個雞蛋灌餅,帶到辦公室里吃,辦公桌是最普通的工位桌,一坐就是一天,與工廠里的流水線并無太大差異。我一杯接一杯地喝水,每天搔頭抓耳地想著寫什么文章,想不出來時,就去樓層的外置樓梯抽煙。
我在這個樓梯度過了幾乎一小半的工作時間,公司里幾乎都是女生,沒有人抽煙,我常一個人坐在薄薄的鐵樓梯上連抽兩支。那是個逃生梯,四周用鐵板圍起來,鐵板上做成密密麻麻的圓洞,因此四面進風。圓洞盯久了眼花,若想遠眺,需要把臉貼在圓洞上,能看見一片茂密的樹林,是什么樹呢?我不太懂樹木,但可以猜測大概是杉樹類的,四周沒有什么高樓,因此我像是站在荒野中的瞭望塔上,從望遠鏡里觀察。風一吹起,樹木嘩嘩作響,身處十八樓也聽得很清晰。41CA8C5A-C72D-4569-AFAA-F03C7F431FBF
我對樹木有特殊的好感,我家鄉的那座小城,雖不發達,但已經很難見到大片大片的樹木了,每次在電視上看到那些沉默、靜止而長壽的生物齊刷刷站成森林,我就想去傾聽它們,覺得十分美好。
逃生梯上抽煙的人總是很多,看著裝幾乎都是這一層的一家銷售公司的人,大多三五成群,有說有笑地抽煙,活像《志明與春嬌》里的場景。把臉貼在鐵板上看外面的人,據我所見,只有我一個人。
要是工作完成得早,我會和兔子或者龍仔聊聊微信。兔子在一家裝潢精美的咖啡館上班,那是家鄉唯一的一家咖啡館,還沒有像北京的咖啡館一樣,淪為談論工作、見客戶的場所,大家是真的到那里去休閑的,幾個朋友,幾對情侶,在有靠枕的木椅上一坐就是一下午。我去那里陪過兔子幾次,坐在角落里一邊看書,一邊偷瞄她。她穿著亞麻色的工作圍裙,端著圓形的咖啡杯托盤,伴著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爵士樂,在嵌著燈泡的旋轉樓梯和桌子之間周旋,像黑白電影里的窈窕淑女般令人心醉。
這里簡單、純粹、不用動腦。若不是媽媽說,讀了那么多書,怎么能去做服務員,我還真想去這樣的地方上班。
公司五點下班,從不加班,一到點大家都齊刷刷地拎包回家。龍仔的公司離我五站,辦公室因為沒人,所以可以自由進出,我無事可干的時候,會去他公司等他。
五
“真沒趣啊。”龍仔說。他是對著兩臺連屏的臺式電腦說的,但無疑是對我說話。“我會拍會剪會編,卻讓我每天在這里給根本沒人聽的訪談配字幕。你知道嗎,我現在幾乎成了跑腿的了,老板最近要辦公司的手續,要到各個地方去蓋章,他沒時間,就讓我去,我這個星期快把北京跑遍了。”
我本來想說,我倒是希望出去跑腿,我每天坐在辦公室動也不動,像一尊佛。但我還是沒說出口。無趣的事情一旦說出口,就會變得更加無趣。我說:“那我們等會兒去打臺球吧。”“算了,還是不去了。”他說,“累啊,雖然也沒做什么,就是累。累得像一截砍倒在路邊、又被人遺忘的圓木,也不想動,也不想玩,就想躺著,一直躺成煤炭才好。”
等到他配完字幕,已經八點了,我們去樓下的“江同學”買了兩個豬蹄邊走邊啃。那兒是地鐵首發站,人很少,我們靠在長長的空無一人的電梯扶手上想著各自的心事兒,他開口問我:“你說,我們來北京是干嗎來著?”我看了看手機,九月底。才兩個多月,他就問出了這個問題。“來追求夢想的吧,當時好像是這么說的。”
其實我們不是來追求夢想的,因為我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以前覺得,北京文化業發達,機會多,我們來賺錢,來學習。其實,對于一個二流大學的本科畢業生來說,文化產業再發達,機會再多,也與我們沒有關系,這里就只是個很擁擠卻無人交談的城市而已。
龍仔嘆了口氣,說:“我覺得百分之七十北漂一段時間又回家的年輕人,是因為寂寞才走的吧。”寂寞,我羞于說出這個詞,但他說得在理。他說:“你覺得我們現在這個狀態該怎么描述啊?”我想了想,說:“嗯……疲憊又空虛吧。”
“疲憊又空虛,疲憊又空虛。”他把這句話在喉頭來回滾了幾趟,連嘆了三口氣,沒再說話了。
經過小區門口的便利店時,他再一次開口。
“要不國慶過后,我回家做生意,你回去跟兔子結婚吧。”
我打了個哈欠:“說什么呢,你只是累了,回去早點休息,好好睡一覺,明天起來你就不這么想了。”
“可能是吧,但到了晚上又會這么想了。”
“趕緊回房睡覺吧。啥也別干了。”
“嗯,那你也早點睡。”
到了房間門口,我們互道晚安,進了各自的房間。看著他的背影,我仿佛看到一口快干的井,隔一夜水泵又可以搖出一點水來,就是總充盈不起來。
才九點多鐘,離我正常的睡覺時間還有三個小時。我躺在床上看《流動的盛宴》,打游戲,不時去窗邊抽支煙。我沒有早點睡,我知道他也沒有。雖然沒有任何動靜,但我就是知道,龍仔肯定也在自己房間里安靜地做著他自己的毫無意義的事情。也許在和誰聊微信,也許在發呆或者看書,但就是不肯睡覺,如果身體熬得住,甚至希望可以這么一直拖延下去。
六
十月底的時候,我和老板吵了一架。我和他對某本書的解讀意見不合,導致我的推文一直通不過,我幾次據理力爭,發表自己的觀點,都被打回,我一氣之下,轉頭回座位寫了封辭職信,對接了工作——對接時才發現需要對接的東西簡直少得可憐——當天下午就離開了公司。
走的時候,我最后一次去逃生梯抽煙。不知為何,那會兒抽煙的人一個也沒有,我把臉貼在鐵板上,望著樹和云,思考自己要去哪兒。那時北京最舒適的秋天快過去了,樓下的樹林已經半禿,葉落一地。我望著那片樹林,猛然想起小學三年級我們學過的一篇課文《美麗的小興安嶺》。
在哄鬧的課堂上,老師點我起來朗誦這篇課文。“我國東北的小興安嶺,有數不清的紅松、白樺、櫟樹……幾百里連成一片,就像綠色的海洋。春天,樹木抽出新的枝條,長出嫩綠的葉子。山上的積雪融化了,雪水匯成小溪,淙淙地流著。溪里漲滿了春水。小鹿在溪邊散步,它們有的俯下身子喝水,有的側著腦袋欣賞自己映在水里的影子……”
那時的我尚年幼,弱不禁風,留著西瓜頭,從未出過城,每天思考得最多的是,如何開口找媽媽要一塊錢買小賣部里的跳跳糖吃。那時我以為世界到處都是花朵,人生充滿美好和希望,寧靜的人有花草樹木,奮斗的人有高樓大廈,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要不,去小興安嶺做守林人吧。這樣的念頭一起,就像被春風拂過的草般瘋狂生長。我幾乎被感動得不能自已,這是我童年時代的童話里的場景。那時候我突然醒悟,好像世界上不是只有運營、工程師、程序員、會計、項目經理這幾種職業。
我想象在某個偏僻的森林里,有一間圓木砌成的竹筏般的小木屋,留著胡子的我赤裸上身,手拿斧頭,站在門口眺望一片山頭的樹木,枕邊放著封邊磨白的福克納的《八月之光》和兩瓶濃烈的二鍋頭。這里沒有網絡,沒有人和車聲,沒有市場動向和熱點的信息,只有望不見盡頭的樹、蟲子和干爽的風。41CA8C5A-C72D-4569-AFAA-F03C7F431FBF
七
幾天后,我打電話給兔子。
“我在小興安嶺了,你聽。”我把手機舉過頭頂,想讓她聽風的聲音。
“我什么也聽不到,你去小興安嶺旅游去了?”
“我辭職了,來這里做守林人。”
她急急地吞了兩次口水,像是被雞蛋噎到似的:“你有病吧,你要是不想在北京干了,就滾回來,跑去黑龍江干嗎,你騙我的吧,你是不是出軌了?”
“沒有,我只是突發奇想。”我說,“你聽這里的風聲,多清澈,我覺得北京不適合我,我想通了,其實我根本沒什么賺錢的欲望,我就想安安靜靜的,我原本以為這兒連信號都沒有,現在有了,可以打電話,多好,我每天在林子里巡視完,就給你打電話。”
“滾你的。”她哭了。我有點慌,不知道她為什么而哭。我正準備安慰她,話筒那邊有人喊她倒水。她應了一聲,把電話掛了。
我想象她抹了眼淚,紅著眼圈去給人倒水的樣子,有點心疼她。兔子是個典型的小鎮姑娘,沒上多少學,溫柔可愛,有點內向,我多次問她要不要和我一起來北京,她都不愿意。她說,她的父母不會同意的,她自己也不想去,覺得累,適應不了大城市。“我就想安安穩穩地在這兒過一輩子。”她說。
我做不到,想到要在出生的小城活一輩子,生老病死都走不出那條街,我就恐懼得發抖。我的確沒什么賺錢的欲望,但也不是什么安靜的人,我只是想逃避而已。
接下來半個月,我都在給兔子講述小興安嶺的風景。深秋時分,黑龍江已經很冷了,地上的落葉枯得卷起邊來,櫟樹樺樹幾近枯萎,松柏被冷風一吹,綠得油亮。我住在一間山腳下的磚砌平房,給這里的守林員幫忙。我白天去山頂的瞭望塔看守森林,謹防火災,他晚上和我換班。
他家里有一只禿了兩塊毛的花貓,有時我會喂點東西給它吃,多喂幾次,它便與我很親近,我常用軍大衣把它裹在懷里,帶上塔去。塔里可以看到很遠的地方,一片沙沙作響的樹海,刮起風來頂端的樹冠像浪濤一樣浮動,遠處的山頭有七架巨大的風車,給附近的村莊供電。四周沒有比我這兒更高的建筑,我可以一覽眾山小,像兒時數星星一樣徒勞地數著每個山頭的樹木。有時候有鷲和大雁飛過,剛來的時候我分不清,后來守林師傅告訴我,一群飛的是大雁,單只盤旋的是鷲。
白天的小興安嶺平和美麗,可夜晚很難熬。每隔一個星期我們會倒一次班,我看守夜晚。夜班是八點上山,臨近冬天,天黑得很早,我很怕黑,一個人在山路上走,會因為一點動靜就渾身發抖,怕被黑暗中躥出的野獸咬成兩截。半山腰的路中間有一塊柏樹的根莖從地底下突出來,我總是忘記,被絆倒過好幾次,摔在軟軟的泥地里,不怎么疼。
上了塔,除了燈光附近半米,其他地方一片漆黑。那是在城市里從未體會過的黑暗,把手臂伸進那黑暗里,那截軀干像是從身上消失不見了。夜間的風也陰森,穿過樹干,鬼哭狼嚎一般,拍打在瞭望塔的墻壁上,塔仿佛搖晃了起來。有時我覺得我不是在森林里,而是在行駛于太平洋中心的輪船上。
她只是聽著,不再那么激動了,但也不回應。等我說完后,她問我是不是不打算回來了。我說:“我不知道。我在這里應該只是體驗幾個月,然后就回北京。怎么樣,你到底能不能來北京?”她說:“再說吧。掛了。”又補了一句:“你小心點,不要被蟲咬了或者被熊吃了。”
八
掛了電話后,我點了支煙。龍仔說,辦公室里不許抽煙,讓我掐了。他說:“你這樣好嗎,人家這么好一姑娘,你騙她。”我說:“我沒騙她,我只是提前講述未來的生活而已。等我有錢了,我一定會去小興安嶺的。”他說:“等到你有錢,兔子都嫁人了。你到底打算干嗎?”
我不知道。我連去小興安嶺的路線都查好了,但是我沒有錢。我既不想再找工作,也不想回家鄉結婚,每天窩在房間里抽煙,讀沒用的書,或者去龍仔的公司瞎混,編撰小興安嶺的風景講給兔子聽,時不時還找兩張樹林的圖,讓龍仔修一修發給兔子。有時候翻看我們的聊天記錄,我覺得自己真的在守林似的。龍仔幾次給我物色工作,讓我投簡歷試試,我也沒去看,推脫說,明天再投。
一來二去,便入了冬,我一邊告訴兔子,我穿著棉被似的軍大衣瑟縮在瞭望塔里守護光禿禿的森林,一邊坐在有暖氣的房間里抽煙。房間里久不通風的緣故,一股油膩膩的味道。兔子說她辭職了,存了點錢,準備休息到年后再找別的工作。我說:“也好,那你打算在家干嗎?”她說 :“不知道,練練吉他,睡睡覺咯。”我說,那也挺好。
龍仔告訴我,他熬不下去了,打算年后回家繼承家業。他說等他在家賺了錢,給我投資。我說投啥,我什么也不會。
“半年你就回去了,這么快就輸給了現實,鄙視你。”
他笑笑沒說話。
九
三天后,我被電話鈴聲吵醒,迷迷糊糊地摸索著起床。窗外月色柔和,我看了看表,九點十分,我從中午睡到現在。我接了電話,是兔子。
“怎么了?”
“你在干嗎?”
“我剛起床,今天值夜班,馬上就要去山上了,好像起晚了一點,樹林里有點黑,有點嚇人啊。”我一邊說,一邊窸窸窣窣地爬下床,打開臺燈,讓房間亮堂起來。
“沒關系,今天有月光,而且下雪了,照在積雪上還是挺亮的。”
“啊,是啊,下雪了。嗯,你怎么知道啊?這么聰明。”我笑瞇瞇地說。
“因為我現在就在你告訴我的小興安嶺的那個村子的那間屋子前,而屋主告訴我根本沒你這個人。我當然很聰明,我用打工存的錢買的火車票,坐了一天的火車又倒汽車踏著雪來看你,想給你個驚喜,而你就是個騙子!”她語速越來越快。我聽完她的話,感覺心臟在胸腔里沉重地捶動,嘴里干得沙沙作響,不知該如何回應她。
“你要是想逃避我你就直說,我不會逼你跟我結婚,也不會逼你回來,你何必繞這么大一圈騙我?”她的聲音帶著哭腔,我有點慌了。我說:“我沒騙你,我是準備去的。”她開始哭了。我停頓了一會兒,問她:“你這么晚過去,晚上準備住哪兒啊?”話筒里傳來吸氣的聲音,像是要把我從話筒的這一頭吸過去似的。她突然扯大嗓門喊道:“不關你事!”然后掛掉了電話。
放下電話后,我起床喝了口水。九點半,剛剛入夜,北京還很熱鬧,窗外的樓房燈火通明,月光被擋在外面,在空中微弱得像隨時會熄滅的燭火。在小興安嶺,月光應該很亮吧。兔子說很亮就一定很亮,她不會騙我。
我想象著從黑洞似的天空中落下的大雪,密密麻麻地落在樹梢,落在地上,遮住枯葉。我想象著明天清晨,走上瞭望塔,向遠方眺望,一片潔白,空氣像冷冽的泉水般清爽。那是我從未見過的真正的大雪,我想象兔子和我一起登上瞭望塔,在炕上一邊冷得抱成一團,一邊伸手接住完整的雪花。而北京沒有下雪,也沒有下雨,連風也沒起。
我拉上窗簾,躺在床上點了支煙,吸完后又點了一支。在沉寂的夜晚里,香煙總是燃燒得很慢。但夜晚還是很長,要挨到天亮,需要很多很多支煙。不過沒關系,只是吸煙而已,就像呼吸一樣簡單,其他的事情,就留到明天再思考好了。如果明天不想思考,還有明天,還有明天,還有無窮無盡個明天。
作者簡介
李星銳,1995年生,湖北人。作品見于《長江文藝》《特區文學》等刊。
責任編輯 菡萏41CA8C5A-C72D-4569-AFAA-F03C7F431FB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