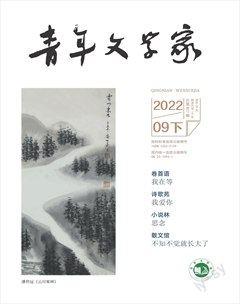當年冬天的打麥場“駕校”
陳福存
前不久,我找老同學玩兒,偶遇中學老校長的兒子。回想起這位講話風趣的老校長,曾因為重視學生自行車安全問題,故意在講“自行車”時使用“臺”這個量詞,即便引發全校師生的嬉笑也不以為意,又想起他曾追在自行車后教閨女學騎車的矯健身影。談話間,我得知老校長已辭世多年了,不由感懷歲月變遷的冷漠無情,時過境遷,世界已經在我們慢慢變老的過程中悄悄改變了。
不知道是因為現在的人聰明了,還是現在的自行車矮小了,或者是現在的年輕人在兒童時騎玩具車就學會騎車了,現今再看不到專門學騎自行車的人了。可是,在我的少年記憶里,學騎自行車是一段熱火朝天的美好回憶。
在我山村老家的屋后,是一大片打麥場,也是孩子們的樂園。在每個忙碌的夏收季節,大人們累得前胸貼后背,黑夜白天連軸轉,將麥地連綿不絕的金黃小麥用鐮刀撂倒,打捆兒運回村,在打麥場晾曬,轱轆碾壓,脫殼風揚,晾干入倉。整整要忙一個多月,之后打麥場里的麥秸垛子就是我們小孩兒的最愛,捉迷藏自不必說,也是我們的蹦跳彈簧床。干凈新鮮的麥秸是那時候的床上必需品,長麥秸編成草墊子鋪在褥子下面的草席上,枕頭里裝滿細軟的新麥秸,睡覺時滿床都是清香的麥子味道。待到冬天,麥秸因做飯燒火越來越少,留出了大片的空地,兒童們玩兒跳繩、丟沙包兒、打拉子、打老栽、跳皮筋兒就有了大戰場,經常有七八群小孩兒一起玩耍,歡笑或吵鬧聲經久不息。
那時候不光農村,城鎮騎自行車的人都不算多,當時比較有身份的人才騎自行車,還有的人經常挽起袖子露出手表,彰顯自己尊貴的地位。有句童謠就反映了當時時髦人的牛氣:“騎洋車的戴手表,沒有媳婦我給你找。”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神州大地,山村面貌也很快煥然一新。打麥場不僅多了打麥機和拖拉機,還少了牛、驢、騾子,少了它們濃重的黑糞味,路上的自行車更是如雨后春筍般多了起來。不光是中年人騎,老人和少年也騎上了,車鈴鐺叮叮當當的聲音經常響遍大街小巷。
春困秋乏夏打盹兒,只有冬天是農閑時節,鄉親們可以在冬天打牌、走親戚、聽梆子柳琴戲,玩把戲雜技的也經常來,所以冬天的山村總是快樂舒緩的。唯獨大雪冰封后的幾天,中午時分,路面泥濘不堪,早晚路滑不好出門,但這也擋不住孩子們在潔白的大地瘋狂地打雪仗。
讓我印象最深的是1985年,我們大隊的打麥場成了風光熱鬧的冬日“駕校”,男女老少都在此學習自行車的騎行技術。先在自行車后座橫綁上一根頂門棍,然后左腳踏在腳踏板上,右腳有節奏地點地劃撥借助地面反作用力前行,反復練習后逐漸加快速度,等完全熟練后再騎上去。膽小的還得需要后面有人扶住后座掌控,后面的人跑步追著,看騎得穩了就偷偷放手,但是往往還是有人仰車翻的尷尬,不過因為冬天都穿著厚棉衣,摔不疼,拍拍塵土自己就爬起來了。圍觀的就打趣:“屁股摔八瓣兒沒有?”那時候的“教練”是資深自行車騎行者,多為長輩,義務教學,經常大聲喊著:“眼看前方,別光低頭瞅地面,提前躲避,小彎拐方向,剎車輕點兒,別一下子踩死,不然會栽倒。”現在想來竟然和汽車駕駛一樣有口訣要領。
個子高的學習有優勢,騎車子不穩要歪時直接兩腿岔開,加上后面有木棍支撐就避免了翻車挨摔。而個子小的則較難學,那時候的自行車都是人貨混載的高大車型,無論“金鹿”“泰山”“飛鴿”都沒有現在的小巧輕盈版,大多都是那種二八大杠式。很多身形矮小的成年人不如十歲小孩兒騎車子溜,小孩兒身高不夠,坐上座位腳夠不到踏板,但是他們善于創新,就不坐車座而是把右腿從車梁下伸到右邊踩踏板,以鐵拐李探海式一起一伏的怪異掏腿招式騎行。這種技術雖然高超,但是應該不算能拿“畢業證”的騎行招式,而我一直用這個招式騎了三年,直到初中二年級才升級為座位騎行。還有一種“肄業證”的騎行招式很雷人,是騎在大梁上的姿勢,不過一般很少有人采用,因為腿短坐座位夠腳踏板還差一小截兒,所以有了類似袋鼠邁步的特技。但該特技對人襠部損害較大,不利于男孩兒發育成長,故而不適宜長途騎行。
還有一些高超的危險騎行技術,比如兩人騎車并行勾肩搭背式、一手拽拖拉機借力式、雙手解放大撒把式、后座長腿弓腰騎車狗熊爬樹式等,這些都不是正規的騎行方式,在我們打麥場“駕校”不公開傳授,只有好事者另請“高明”小班額外專項研修。但是,這種“研究生”級別的騎行有風險,出行需謹慎,出事自負全責。
后來,隨著機械化的普及,打麥場漸漸沒有了以前的風光,面積越來越小,直到前幾年蓋滿了住宅。而自行車也逐漸被更好騎、更省力的電動車代替。回到家鄉,我發現轎車停滿了街巷,只能憑記憶找到當年打麥場游戲的大體位置,往昔的物件難覓蹤跡。現在的農村少了往昔的熱鬧,也讓我更加懷念那令人歡欣的冬日“駕校”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