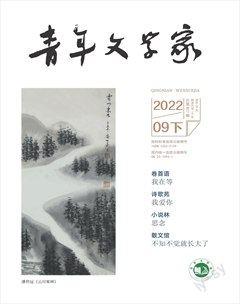心底的那一抹暖
翁中秋
父親喜歡吃肥肉,尤其是那種夾在筷子上,微微顫抖的“活肉”。一口一塊,連肉帶湯一大碗,輕飄飄地下肚。從我有記憶時到他古稀之年,一直都是快樂受用。年少時的我,也是這樣,吃肉厲害,經(jīng)常與父親搶肉吃,記憶猶新。
父親年輕的時候身體單薄,經(jīng)常生病住院。他屬牛,生產(chǎn)隊里的村民叫他“病牦牛”。家里十來畝地的收入,都給了醫(yī)院和村衛(wèi)生室。日子拮據(jù)且無起色,父母見鄰居們都砌房造屋心里著急、焦躁,經(jīng)常唉聲嘆氣。記得那年,父母剛剛忙完秋收。鎮(zhèn)里組織青壯年勞力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將鎮(zhèn)西北部三千畝蘆葦蕩,改造成精養(yǎng)魚塘。家家戶戶都有土方任務,而父親領(lǐng)取了自家的土方任務后,還雄心勃勃地和幾個差不多大的伯父、叔叔們,另外承擔起在上班、做生意的人家沒時間去干的土方任務。他們把土方折現(xiàn)錢托出來,一家可以分七八百塊呢。可以過個肥年,父母心里盤算著,也樂意。父親收拾了大鍬、擔子,帶上母親為他煮熟的雞蛋出門了。
沒過十天,叔叔火急火燎地回家報信。父親生病了,暈倒在工地上,同伴們用掛槳船把他送到鎮(zhèn)里醫(yī)院搶救。幸運的是,父親的身體并無大礙,只是虛脫吃力了,住院一個星期后便回家靜養(yǎng)了。母親精心照顧父親,攙扶他到橋頭、田埂上散步,透氣。在太陽好的時候,母親將草窩子墊上棉絮,讓他在院子里曬太陽。飲食上變著花樣,每隔一天,母親就燉他喜歡的肉湯,湯里時常漂著菜瓢(揚州方言:菜根)、蘿卜、茨菇,滿滿的一搪瓷盆。我小心翼翼地端著送到床頭,或草窩上給父親吃。時常,我用舌尖沾一下湯汁,嘗嘗鮮,肉舍不得沾牙。父親想背著母親分給我和妹妹一半湯肉時,我們兄妹倆都站得遠遠的,想讓父親多吃些,這樣才有營養(yǎng),身體也能早點兒強壯起來。可父親卻把筷子調(diào)過頭來,挑些鹽花放在我們碗里,這樣我們就不可以將肉湯再倒回去,因為父親生病住院時,醫(yī)生囑咐控鹽兩個月。母親知道后,狠狠地瞪了我們一眼。
有了我們兄妹倆的“參戰(zhàn)”,很快便把親戚、鄰居們來看望父親的肋條肉、麥乳精等營養(yǎng)品“殲滅”了。家底的單薄,讓母親慢慢著急了起來。我們兄妹倆自覺許多,父親吃飯的時候我們就躲得遠遠的。有天晚飯時,我躲到奶奶家,正巧奶奶給小叔改善伙食,茨菇燉肉。奶奶盛一小碗,撒上蒜花遞給我。那香味直鉆鼻子,口水汩汩涌上來,我使勁兒咽著口水。舌尖剛剛碰塊肉,腦海里閃出病榻中的父親,已經(jīng)幾天沒有肉沾牙了,身體還是虛弱無力。于是,我縮回舌尖,端著肉碗朝家奔,一手端著肉碗,一手捂著碗口,生怕碗里的肉飛出去。父親盯著我手中那碗熱氣騰騰的茨菇燉肉,半天沒說話,眼睛里有若隱若現(xiàn)的淚花。我們父子商量了半天最后決定,由父親執(zhí)筷夾塊肉送到妹妹嘴里,再夾塊送到我嘴里,然后夾塊放到自己口中,最后我們笑著一起咀嚼人間美味,香!
有天放學回家后,母親把我們兄妹倆趕到廚房里,讓我們先吃晚飯。一碗白湯肉讓我們飽口福,但總是感覺哪里不妥,那肉太油膩了,在喉嚨打轉(zhuǎn),難以下咽,沒有父親碗里的湯肉鮮美。我們納悶兒地看了看母親,她笑了笑,還哄我們多吃肥肉,把湯都喝了。連續(xù)幾天,我嗝了幾天的肉餿味。父親坐在走廊上,吃肉喝湯大快朵頤時,我卻躲得遠遠的,聞到肉味就想吐。父親感到蹊蹺,詢問母親何故。母親微微一笑告訴父親,說我是個肉蒲包,經(jīng)常“搶”肉吃。就討教了鄰居大媽的“好”主意,用糯米熬成濃米湯,與肥肉、白糖燉爛,一粒鹽花不放,再能吃肉的人,一次吃足,以后也決不碰肉了。父親聞聲后連忙責備母親,母親也內(nèi)疚得尬笑,我紅著臉直跺腳。現(xiàn)在細細思忖,那時物質(zhì)匱乏的家,讓母親受了多少煎熬和無奈。
出差回來的爺爺知道情況后,第二天,東方剛剛吐白,一腳跑到三十里外的興化菜場,買了二十多斤厚膘肉和些碎刀肉,讓母親腌好曬干,再熬點兒脂油給父親增加營養(yǎng)。在母親無微不至的調(diào)理下,父親日日見好,扔掉了“病牦牛”的帽子。如今七十三歲的他,一擔兩桶水,還能健步如飛。
那小年夜的中午,干活兒的伯父、叔叔們回來了。他們放下包袱、大鍬和擔子后就來看望父親,同時帶來了一大塊五花肉和父親全額的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