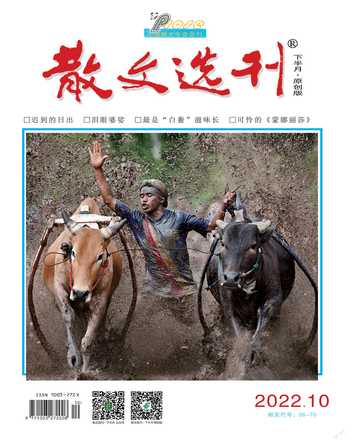珍惜人生中的每一次感動(dòng)
郝大鵬

我出生在中國北方的一個(gè)小城鎮(zhèn)。
三歲那年,父親被下放到一個(gè)最偏遠(yuǎn)的地方去教書,一年只能回兩次家。他每一次臨走時(shí),都會(huì)把我抱起來,久久不愿放下。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盼望父親歸來。我每天都站在父親回家時(shí)出現(xiàn)的街口,翹首等待,盼望他高大而又消瘦的身影出現(xiàn)。那時(shí),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父親回來的第一時(shí)間看到他,然后就飛快地跑上去,喊一聲“爸”。這樣的場景每年都能實(shí)現(xiàn)兩次。每一次父親都是快走兩步,彎下腰,用他的大手把我托起來,在我臉上咬一口,然后兩手夾住我的腰在空中轉(zhuǎn)換一下姿勢(shì),我就順利騎在他的肩頭上。父親笑著,我也笑著,奶奶蹣跚著小腳走出院外瞇著眼笑著,媽媽放下手中的活計(jì)隔著窗也笑著。夕陽掃過我家房檐,把大地染成橘紅色,最后把我和父親疊加的身影拉長,再拉長……這個(gè)場景曾經(jīng)無數(shù)次出現(xiàn)在我的回憶里,出現(xiàn)在我的夢(mèng)中。
大學(xué)畢業(yè)后,我來到現(xiàn)在工作的小縣城。初來乍到,這里沒有親人,沒有朋友,只和一個(gè)大我二十多歲的蒙古族老兄達(dá)木林住在職工宿舍里,大家都稱他老達(dá)。老達(dá)是單位的卡車司機(jī),一個(gè)干了二十多年還沒有轉(zhuǎn)正的臨時(shí)工。單位沒有食堂,我們兩人就用電爐子在寢室做飯吃。每天晚上,我和老達(dá)用聊天打發(fā)時(shí)間。老達(dá)有很豐富的人生經(jīng)歷,他給我講他的故事,我也把我讀過的一些書講給他聽,為了更好地交流,我教他學(xué)漢字,他教我說蒙古語。就這樣,老達(dá)陪我度過了三年的單身生活。
結(jié)婚前一年,老達(dá)幫我在城郊買了一塊宅基地,我準(zhǔn)備蓋房子。我沒有錢,建筑材料都是老達(dá)幫我賒來的,房子的地基石是老達(dá)開著車和我一起從山里運(yùn)來的,那一次往車上搬石頭,我倆的手都磨破了。在老達(dá)的幫助下,房子的墻體一天一天升高,我感覺它不斷壘砌著我對(duì)生活的憧憬和希望。
有一天,砌磚的河沙用完了,因?yàn)榻訚?jì)不上,施工隊(duì)停止施工。我沒有錢雇車,而老達(dá)又去了牧區(qū),幾天以后才能回來。我無助地躺在工地的土堆上睡著了,后來暴雨把我淋醒,已是深夜,才發(fā)現(xiàn)身體四周已是一片汪洋,雨點(diǎn)打在臉上生疼。這時(shí),一柱很強(qiáng)的光照在我身上,那是卡車的大燈發(fā)出來的。“嘿,我是老達(dá),回來幫你拉沙子來了。”老達(dá)的聲音在滾滾的雷聲中那樣清晰可辨。
我想了很多年,直到如今,也不知道老達(dá)怎么能夠那么及時(shí)地出現(xiàn)在夜半風(fēng)雨中。只記得,我們到達(dá)沙場的時(shí)候,已是黎明時(shí)分。雨停了,空氣摻雜著泥土和青草的氣息,山被低垂的云壓低了;不遠(yuǎn)處是一片樹林,雨洗過的樹干在清晨升騰的水汽里顯得更加挺拔蒼勁;水流從山坡上嘩嘩淌泄下來,然后大片散開,又繞過樹林流入草原深處;天地間忽然變得透徹,干凈。朝霞映在老達(dá)的臉上,汗珠從臉上滴下來打在石頭上摔開道道金光,那光里,映射著純潔的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