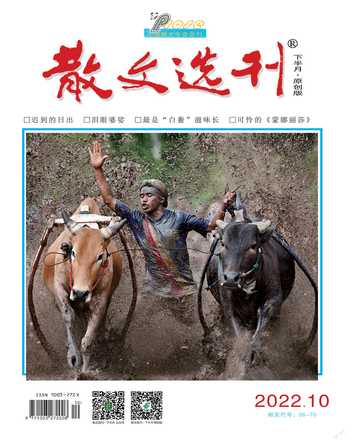四歲,女兒一個人的旅行
洪麗

1998 年,我們舉家南遷,乘坐36 個小時的綠皮火車,從東北來到上海。
剛來上海時的熱情和憧憬,很快被無情的現實擊得粉碎。上海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黃金遍地,唾手可得。為了節省開支,我們全家七口租住在上海的郊區,一套不足六十平方米的公房里。說“家徒四壁”并不為過,房間里除了一張床,沒有任何家具,衣物等都放在紙箱里。兩千多公里的行程,我們只能帶一點兒隨身常用的物品。
人生地不熟,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我就到五公里遠的一家服裝廠,每天騎自行車去上班。老公和哥嫂合開了一家小網吧,二十四小時營業,輪流值班。由于沒有執照,經常被查封,每天營業都戰戰兢兢,收入微薄。婆婆剛退休,一邊要照顧生病臥床不能自理的公公和四歲的女兒,還要買菜燒飯,打理一家人的飲食起居。生活拮據,開銷要精打細算。
網吧離得不遠,就在小區門口臨街的房子里,不需要過馬路,從雜貨店向左拐兩個門面就到了。女兒沒什么像樣的玩具,也沒參加任何興趣班,沒學過任何樂器。除去上幼兒園、待在家里看電視和小朋友在院子里玩耍外,其他時間就待在網吧里。網吧大概是當年女兒唯一的游樂場。
婆婆每次上街買菜也要帶上女兒,把她一個人留在家里不放心。女兒會主動提力所能及的重量,幫奶奶減輕一點兒負擔。天氣炎熱,婆婆提議買支冰激凌。女兒問:“奶奶,你還有錢買菜嗎?”說得婆婆鼻子發酸,心說再怎么苦,也要給孩子買一支。女兒一副小大人的模樣:“奶奶,那你實在要買,就買支五毛錢的棒冰吧。”服裝廠里人手少,工序復雜,趕貨加班是常有的事。我常常下班回來女兒已經睡著,我走的時候她還在睡夢里。我平時也很少有時間去網吧,不知道里面時常煙霧繚繞,二三十平方米的房間里尼古丁濃度高得嗆人。女兒時不時溜去網吧,站在后面偷看大人打游戲。在我還不知道《大富翁》的時候,女兒已經對《仙劍奇俠傳》了如指掌。
我很少有時間陪女兒,從來沒顧及到她的想法,考慮過她的感受,對她的培養和教育更是嚴重缺失。女兒的童年是在婆婆的陪伴中長大的,雖在我身邊,我卻幾乎一無所知。
一個炎熱的午后,我正在廠里上班,婆婆也來廠里做零工,想賺點兒錢補貼家用。門衛大叔把我女兒領到車間。我驚詫地問:“你和誰來的?”
女兒一臉驕傲:“我自己來的。”
“你怎么找得到?”
“我數了,過了六座橋就到了。”
“路上沒碰到人嗎?”
“我遇到了一位老爺爺。老爺爺問我去哪里,我說去找媽媽,老爺爺就走了。”
“為什么要到這里來?怎么不和家里人說一聲。你渴不渴,餓不餓?”
“沒人陪我玩,小朋友都回家了,爸爸在睡覺,奶奶也不在家,我想找媽媽。”女兒被我的聲音嚇到了,怯怯地回答。
眼淚像斷線的珠子,簌簌地滑落,我緊緊抱住滿臉汗水的女兒。哭泣的時候不全是悲傷,有時候是委屈,有時候是心疼,有時候是自責。
從家到工廠將近十里路,女兒只乘車來過一次。天已經黑了,看不清外面的路。對于路癡的我來說,就算大白天也要走上兩個來回才記得住。我騎車都要二十分鐘,以女兒的速度,豈不是要走上兩個鐘頭?
直到幾個小時以后,家里人才發現女兒不見了,慌忙去公園里尋找,小區里、家里、網吧里也找遍了,嗓子都喊啞了,就是不見孩子的蹤影。迫不得已,才抱著最后一線希望打電話給我,怕我擔心還試探地問。我故意不告訴老公,孩子在我這,讓他們多擔心、焦急一會兒,心里的不滿、怨恨實在無處發泄。老公知曉后,在電話里怒吼,說等女兒回去揍她一頓。
事后,我和婆婆常常聊起此事,有種劫后余生的慶幸。剛開始女兒并沒在意,說的次數多了,女兒會驚恐地制止:“你們別說了,我害怕。”
不敢想象,這幾公里路女兒是怎樣走過來的,那是種萬箭穿心的感覺。很多時候,仿佛女兒一個人還孤單地站在歲月里,弱小的身影一直在烈日下踽踽獨行。
她走得實在太慢了,直到今天,還沒走到我的身邊。
美術插圖:知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