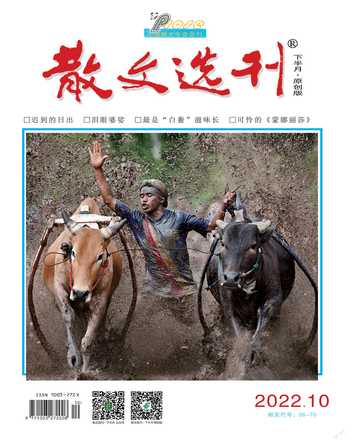秋憶
占麗霞

我想母親大概是喜歡秋的,這樣的判斷基于我腦海中保留和剛剛變為現實的一些關于秋的記憶。比如,她選擇在金秋離世,把生命的絕響留在這個凄美的季節。
有一年,她不知從哪里弄來幾株苗,帶回家種在院子里。她給它們施肥、澆水,但并不修剪,她讓它們自由地長,自由地開花。盡管它們大多松散,花也并不驚艷,但母親特別高興。后來,我在展覽會上看到了其他品種便將其買回家,母親精心侍弄,像照看自己的孩子一般。可我從未問過她為何偏愛菊花,這點疑問現在成了我的一點兒遺憾。
秋天一到,到處又都是滿樹滿枝的桂花,風不吹,它們會在某個早晨落得滿地。母親在鏡子前仔細地梳頭,肩上披著紅底紫花的紗巾,頭發梳理得清清楚楚,花白的碎發正好落在紗巾上,她小心翼翼地撣掉。她看著我從屋里出來。每天在這個點上,我趕著上班。她在鏡子前轉過身:“又這么急,就不知道早起,早餐可別忘了吃喔!”她噘嘴的樣子極其可愛,她微嗔的責備輕巧又使人無法拒絕。而有時,她不看我,認真細致地梳她的頭。
草地上、水溝里落滿了桂花。母親站在桂樹下,手里拿著被單,她高興地沖著我喊:“你牽著被頭,另一角扎在樹上。”她手里拿著竹竿,一邊指揮,一手牢牢攥著另一處被角,竹竿一晃,桂花便紛紛落滿了被單。落在地上的桂花,她一邊打掃一邊惋惜。隔壁的老太太時常隔著柵欄和母親搭話:“為啥你的手那么巧,養的花好,做出來的食物好吃,連樹上結出來的果子都那么甜嘞?我家種啥啥不行。”母親笑著回答:“多施肥呀,來年我給你留顆種子,你再試試,一準行。”
我是母親的幺女,幺女照例是母親最不放心因而得到的關愛也是最多的那一個。因此,父親去世后,母親便和我們住在一起,一晃幾十年過去了。女兒長到23歲時,母親已經快90 歲了,母親發下愿望,如果可以讓她多活三年,看著她親手帶大的外孫女成家那就圓滿了。可惜上天沒有顧念母親的心意。有時候我想,要是上天聽見了母親的心愿該多好。
我曾經常常沉浸在這樣一個夢里:那是一個遙遠而空曠的時空,一條寂靜的長街,我隱約聽見了車的轟鳴,黑煙在繚繞,它孤獨地停滯又奔跑。母親用衣服包著我的頭護我在身下,寒冷的風從四面八方圍擁而來,在揚起的漫天灰土中,故鄉漸漸地遠離。
夢里的長街是我們祖輩生息的地方,長街上有承載著幾代人記憶的老宅子。母親在那成為媳婦,成為母親。有一年,宅子被父親母親賣了,是為了他們的幺女,這是一個蕭瑟的秋天,我總記著他們的堅毅和來回奔波的背影。
“你得成器,你這樣軟弱可怎么行?”母親的憂思總是那樣深。“有您看著,您還擔心什么呢?”“嗯,我還能陪你一輩子嗎?”母親瞪著眼看我。“有你看著,我準能成器。”“那我不得活一百歲呀!”我咧著嘴笑:“一百歲怎么夠!”
母親是民國時生人,她的嚴厲和傳統來自她受過的教育。我說過我的外祖父是當地有名望的教書先生,教會這么一個聰慧的學生自然不難,但封建的禮教和傳統也禁錮了母親的思想,她把心血全用在了家庭,并且放棄了原本美好的工作,自始至終都無怨無悔。
生活在母親的操持下消磨的都是寧靜和安逸,就像屋前的那棵老石榴樹,葉子一遍一遍地黃,又一遍又一遍地綠,看著它落,又看著它生。
院子里變得不再寂靜,老鐵樹開了新葉,綠蕊的海棠正生機勃勃,月季照例開得紛飛。大腹便便的鳥兒,招搖過市,它們在這塊小天地里自由自在地生兒育女。皮襖(我家的狗)經常對于它們的吵鬧頗為不滿,它激動地跑出跑進,母親也無可奈何。
我站在院子里,手里拿著相機,沖著屋子里的母親喊:“您啦,可快著點,我可等著呢!”母親在屋子里回應:“別急,等我換件衣服。”“光線可不等人哦。”院子里的月季正當紅,大朵大朵開得如霞一般耀眼。
母親從屋里出來,她穿一件大紅的薄外套。我說:“媽,你干嗎和花搶鏡頭呀?”母親笑而不答。正如別人評價的那樣,母親確實好看,八十多歲的人啦,皮膚一點不見松弛,她抿著嘴微笑,嘴角上揚,那笑容極輕極淡,都抑制不住地藏在眼睛里,她的可愛和明媚一點兒不輸給花兒。
一大家子人喜歡在這相聚,母親總是最忙的。我們吃著她做的飯,嘗著她做的點心,閑話各自的職業或家常。有時她從廚房里出來,手上的活兒一刻不停,她敏銳地捕捉我們的談話,清晰而自然地參與進來。“ 你們都是‘ 員,都是‘ 師,我也是‘員,我是‘炊事員。”她揚了揚手中的菜,眼睛里都是明亮而溫暖的波光,大家開心的笑聲飛得很遠很遠。
年輕時分家,將正在讀書的小叔子分給母親撫養,母親二話不說當起了他的嫂娘。父親的兄弟姊妹多,母親總盡力周全。親戚你來我往,即使碰到單愛在雞蛋里挑骨頭的人,讓母親傷心難過,母親也不改性情。漸漸受母親的影響,我們也愿意給這個世間多一些溫暖和善良。
母親生性簡樸,極愛干凈,家里總是被她收拾得井井有條,她的東西總是規規整整,絲毫不亂。母親愛看書,書架上有她喜歡的保健醫生和萬年老皇歷。她常用的梳子和頭油放在最顯眼的地方。
我每天趕著時間上班,母親早已等候在院子里,微風揚起她的白發,她的臉紅潤潤的。她一手推著買菜的小車,斜背著零錢包,她歪著腦袋得意地看著我:“我今天約了老朋友先去剪頭發,你帶我們一程。”我著急上班:“那您們可快著點兒,我要遲到了。”母親利索地放好她的東西,簡單的行程竟讓她興奮得像個天真的孩子。
現在,我也常常趕時間,我站在那里,不敢浮想聯翩,眼睛里總是寂寞與惆悵。
不久前,母親的親侄女來消息說,大爺托夢給她了。說,她已經回到了故鄉,和姑爺在一起,一切都很好。我相信這一定是真的!
責任編輯:黃艷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