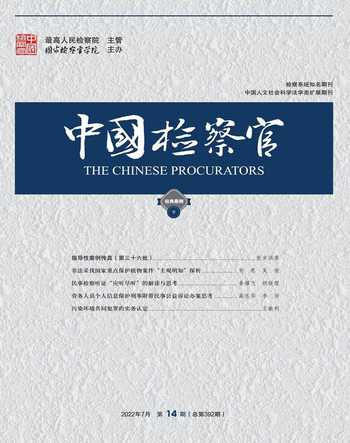復數行為犯中主行為的認定
摘 要:對于復數行為犯的定性,應以復數行為中的主行為性質來認定案件性質。而準確認定復數行為中的主行為,關鍵是從復數行為間的關系入手,分析哪一個行為是主導行為或者支配行為,即哪一個行為在整個犯罪活動中起主導作用和促進作用。誘發或促使行為人產生犯意的行為一般是主行為,將犯意付諸實施的后續行為一般是從行為;在犯罪進程中最難完成的核心行為一般是主行為,較容易完成的輔助行為一般是從行為;最能體現罪刑相適應原則的一般是主行為,明顯導致罪刑不相適應的一般是從行為。
關鍵詞:復數行為 主行為 從行為 罪刑相適應
一、復數行為犯的提出及定性
[案例一]鮑某有一天加班到很晚,臨走時發現隔壁辦公室沒有關門,辦公室內的燈和電風扇也沒有關,鮑某便走進去關電風扇,其在俯身關電風扇時看到辦公桌底下有一張存折,鮑某撿起來一看是同事王某的活期存折,鮑某心想肯定是王某遺失在這里的,他便把存折放進口袋,關上門后離開了。次日鮑某來到銀行,根據他所知道的王某手機尾號和幫王某買機票時掌握的王某身份證號,猜配出存折密碼,取出現金15000元,存入自己名下。(以下簡稱“活期存折案”)
[案例二]閆某伙同楊某,利用某商廈開展民惠龍卡(具有打折、積分功能)積分返券活動的機會,閆某在商廈用本人及他人身份證申請辦理了近10張民惠龍卡,楊某利用曾經在商廈電腦部工作過并掌握密碼的便利,私自進入商廈的計算機系統,向卡內虛加積分80余萬分(積分應由實際消費所得,一定的積分可以兌換一定的禮金券,在商廈可等同于人民幣進行消費),再由閆某持積分卡到前臺找熟人穆某兌換禮金券(兌換的時候應核實身份,核對積分記錄及購物小票)。其間閆某和楊某共兌換禮金券共計人民幣5萬余元并進行消費,后穆某感覺有問題便停止兌換,直至案發。(以下簡稱“積分卡加分案”)
[案例三]李某在網上看到有人出售電腦,便與王某策劃商量了一個方案將這臺電腦搞到手。第二天,李某與出售電腦的張某約好在市物資大樓交易,張某帶著電腦如約來到物資大樓,李某提出要看一下電腦,張某便把電腦交給李某。李某打開電腦包看了一下外形后,提出他一個朋友就在旁邊開了家電腦公司,他要拿給他朋友去看一下質量有沒有問題,張某表示同意,李某便拿著電腦走在前面,張某緊跟在后面。走了幾分鐘后,王某按計劃開著摩托車突然停在李某面前,李某立即跳上車,王某即加大油門,疾馳而去,等張某反應過來,李某、王某早已沒有了蹤影。(以下簡稱“騙奪電腦案”)
刑法分則中,某個條文對某一犯罪客觀構成要件所要求的實行行為不是單一行為而是兩個以上的行為,刑法上稱為復行為犯[1],如高利轉貸罪包括套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和高利轉貸他人兩個實行行為;編造并傳播證券、期貨交易虛假信息罪包括編造和傳播兩個實行行為;丟失槍支不報罪包括丟失槍支和不報告或瞞報兩個實行行為等等。復行為犯的罪名刑法已作明確規定,一般不存在爭議。但在司法實踐中,有一類案件系行為人在一個整體的犯罪故意支配下,先后實施了兩種以上不同性質但緊密關聯的實行行為,應整體評價為一個罪名的犯罪,如上述三個案例。對于這類犯罪,為了與復行為犯相區別,筆者稱之為復數行為犯。對于復數行為犯的定性一直存在較大爭議,筆者認為,對于此類案件的定性,首先要準確認定復數行為犯中的主行為,再以主行為性質確定案件性質。這種案件定性分析方法,可稱為關鍵行為定位法。[2]
二、復數行為犯中復數行為的特征
對于復數行為犯的定性,首先要準確把握和認定復數行為犯中的復數行為。復數行為犯中的“復數行為”主要有三個特征。
第一,復數行為犯在整體上只具備一個犯罪構成。復數行為犯是基于一個犯罪故意支配下,實施了相互關聯的兩個以上實行行為,整體上只具備一個犯罪構成。復數行為犯是實質上的一罪,而不是實質上的數罪、處斷上的一罪,因而不同于牽連犯、吸收犯等罪數形態。具體而言,包含三層含義:一是復數行為是兩個以上的實行行為,不包括教唆、幫助、預備行為;二是這兩個以上行為都是基于一個犯罪故意;三是這兩個以上行為間具有緊密的關聯,常見的關聯如手段與目的、目的與結果等。比如積分卡加分案,就是出于一個犯罪故意(非法占有商場財產的故意),只侵害一個客體(商場財產所有權),但客觀方面實施了私自給商場積分卡加分、使用積分卡兌換購物券、持購物券進行消費等多個實行行為,這些實行行為彼此之間緊密關聯,一環扣一環,環環遞進。這些實行行為結合在一起,從整體上形成一個危害社會的犯罪行為,具備一個犯罪構成要件。
第二,復數行為只是觀念上的不法行為,并非刑法上評價為犯罪的行為。現實生活中,有些犯罪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過一系列的手段才完成犯罪,這個過程中可能有騙、竊、奪、詐等多種成分的行為,這些行為混雜在一起,共同實現一個犯罪故意,即復數行為犯。復數行為犯中的騙、竊、奪、詐等多種成分的行為,只是人們觀念上的騙、竊、奪、詐等不法行為,而不是刑法上被評價為犯罪的詐騙、盜竊、搶奪、敲詐勒索行為。如在騙奪電腦案中,李某、王某實施了系列騙的行為(騙張某來到物資大樓、騙張某將電腦交給自己、騙張某走出大樓)、奪的行為(李某持電腦跳上摩托車,王某疾駛而去),但這個騙、奪都是我們日常生活觀念上的“騙”和“奪”,而不是刑法意義上的“詐騙”和“搶奪”。具體來說,“騙”的行為并非刑法意義上的“詐騙”,因為刑法上的“詐騙”不僅要求行為人有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還要求被害人對財產有處分意思和處分行為,即基于陷入錯誤認識的認識瑕疵而自愿處分財產。而在本案中,張某只是臨時將電腦交到李某手里,而非對電腦的所有權作出處分,張某并不存在自愿交付財產,因而本案的欺騙行為只是我們生活中“欺騙”的概念,不是刑法上的“詐騙”行為。“奪”的行為也并非刑法意義上的“搶奪”,因為刑法上的搶奪是指通過作用于物的暴力,公然奪取他人財物,行為人之前是不占有、控制財物的,通俗地說,刑法上的搶奪是從他人手上奪走財物。而本案中李某跳上摩托車時,已經持有電腦,即已經將電腦“騙”到手,而不是從張某手上暴力奪取過來的。因而這種“奪”的行為也并非刑法上的“搶奪”。本案中“騙”“奪”的行為結合在一起,才是刑法意義上的一個犯罪行為。
第三,復數行為中的主行為也并不是單獨成立犯罪的實行行為。如前所述,復數行為中的任何一個實行行為都不能單獨成立犯罪,而是兩個以上實行行為在整體上具備一個犯罪構成要件。因此,確立復數行為中何者為主行為,是為了根據這個主行為的性質特征,確定復數行為犯在整體上應認定何罪。如在活期存折案中,有日常生活觀念上“撿”(將王某遺忘物撿走)的行為、“盜”(在王某不知情的情況下猜配出王某存折密碼進而將存折內錢取走占為己有)的行為、“騙”(冒充王某或王某委托的取款人,使銀行誤以為鮑某就是王某或王某委托的取款人)的行為。而確定何者為主行為,并不意味著單獨這個行為就構成犯罪,并按照這個行為性質定罪,如認定活期存折案中“撿”的行為是主行為,并不意味著這個行為就是盜竊犯罪行為(因該遺忘物在王某控制范圍內,鮑某“撿”走屬于盜竊),從而認定全案構成盜竊罪。因為鮑某盜走的只是一張存折,屬于財物記載憑證,如果鮑某不知道密碼或者不去猜配密碼,或者即使猜對了密碼但不去銀行取款,存折對他來說也就只是一張廢紙,那么其“撿”的行為不能單獨認定為盜竊他人財物,不屬于刑法上的“盜竊”犯罪行為。
三、如何區分復數行為犯中的主行為和從行為
對于復數犯罪行為,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前面的行為就是主行為,后面的行為就是從行為。[3]主行為的認定標準應該是看哪一種行為對實現行為人的犯罪意圖、非法占有他人財物起了關鍵、決定性或主要的作用,[4]也即哪一種行為在整個犯罪行為中是關鍵行為、主導行為或支配行為。具體而言,體現和表明犯意的行為是主行為,將犯意付諸實施的后續行為是從行為;在犯罪過程中最難完成的核心行為是主行為,較容易完成的行為是從行為;最能體現罪刑相適應原則的是主行為,明顯導致罪刑不相適應的是從行為。
(一)體現和表明犯意的行為是主行為,將犯意付諸實施的后續行為是從行為
具體而言,就是看哪一個行為是體現和表明犯意的行為,這個行為就是主行為,其他將犯意付諸實施的行為或者說實現犯意的行為是主行為的自然延伸,是從行為。
比如活期存折案,有論者認為鮑某行為構成三角詐騙型詐騙罪,因為如果只是盜竊存折而不取款,被害人不會遭受損失,也即造成損失的行為不是盜竊、侵占存折行為,而是取款行為,因此,應根據取款行為的性質定性,而不能根據取得存折的行為定性。[5]也有論者認為這些行為構成普通型詐騙罪,因為猜配他人取款密碼可視為是一種無形偷盜行為,但猜中密碼并不意味著取得了他人存款,行為人支取他人存款,是憑借銀行的信任通過銀行的交付得以實現的,由于銀行的信任是基于一種錯誤的判斷,是行為人隱瞞真相冒用他人名義致銀行誤以為其具有取款合法資格的結果,是典型的冒用詐騙行為,故應認定詐騙罪。[6]筆者認為,在此復數行為犯罪中,“騙”的行為并非主行為,“撿”的行為才是主行為,應根據“撿”的行為即取得存折行為的性質來確定案件的性質。主要理由是:第一,“撿走”活期存折的行為在整個犯罪行為中起了主導作用。在“撿走”活期存折、猜配密碼、取款這三個行為中,“撿走”活期存折的行為是導致被害人損失的關鍵所在,若行為人沒有“撿走”活期存折,后面的系列行為均無從發生。同時,鮑某明知存折就在王某辦公桌底下,王某很容易就能夠發現,卻故意“撿走”,表明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之故意,“撿走”行為直接體現了其犯意,在這種犯意支配下,進而實施后面的猜密碼和取款行為。可以說,行為人“撿走”活期存折對于其實施侵財犯罪起了決定性的促進作用,在整個犯罪行為中起主導作用。第二,行為人“撿走”存折等于實現了對存折記載財產的控制占有。本案中,雖然行為人“撿走”的只是記載財產的支付憑證而不是財產本身,但這個可以即時兌現的活期存折如同一個存有財產的“百寶箱”,存折密碼就如同打開這個“百寶箱”的鑰匙。行為人“撿走”這個活期存折,就等于擁有了對存折記載財產的控制和支配權,只要猜中密碼,就可以打開這個“百寶箱”,進而將他人財產占為己有。因此,行為人最終能夠非法占有他人財產,“撿走”存折的行為至關重要,是起決定性作用的。第三,取款行為只是實現侵財犯意的自然延伸行為。鮑某故意“撿走”存折,表明其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產的故意,接下來的取款行為就是實現這種犯意的必然行為。因此,取款行為是“撿走”存折這一關鍵行為的自然延伸,是行為人實現占有存折記載財產的從行為或者說輔助行為。
確定了本案主行為是“撿”存折行為,本案即應認定為盜竊罪。主要理由是:第一,“撿”的行為在刑法上實質上是“盜竊”行為。前文已述,復數行為犯中的實行行為都是觀念上的不法行為,而非刑法意義上的犯罪行為。本案中行為人鮑某從隔壁辦公室同事王某辦公桌底下“撿走”活期存折,實際上是刑法上的盜竊行為。因為王某的存折就掉落在自己辦公桌底下,沒有脫離王某控制,王某很輕易就能發現,存折并不是王某的“遺忘物”,更非遺失物。鮑某明知存折并未脫離王某控制,仍然在王某控制之下將存折“撿走”,實際上是秘密竊取行為。鮑某竊取王某存折后,通過猜中密碼的方式將存折中財產取出,并占為己有,這是一種將盜竊所得支付憑證兌現的行為,雖然是一種觀念上“欺騙”銀行的不法行為,但實際上是盜竊的事后行為,并不具有刑法評價的意義。因此,根據本案主行為的法律性質,本案應認定為盜竊罪。第二,取款行為也不是刑法上的“詐騙”行為。本案中的取款行為不僅不是復數行為犯中的主行為,而且也不是刑法上的詐騙行為。因為持活期存折取款5萬元以下并不需要出示身份證,也即銀行并不需要驗明取款人真實身份,沒有義務核實取款人是否系存折戶主。即使其他人來取款,銀行也不存在陷入錯誤認識的問題,取款人“詐騙”銀行也就無從談起。第三,本案也不成立所謂的“三角詐騙”。筆者認為“三角詐騙”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對傳統詐騙罪構成要件的這種改造并無必要。“三角詐騙”強調的是被詐騙人并非財產所有權人,其構造是“行為人虛構事實,隱瞞真相——詐騙對象陷入錯誤認識——基于有瑕疵的認識處分了他人的財產——第三人財產權受到損害”。[7]但按照傳統的詐騙罪構造“行為人虛構事實,隱瞞真相——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被害人基于有瑕疵的認識處分財產——行為人取得財產”完全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因為詐騙罪的傳統構造中“被害人基于有瑕疵的認識處分財產”并沒有限定是處分被害人自己所有的財產,當然也包括處分被害人管理、持有、控制下的他人所有的財產。至于最終遭受財產損失的是被害人還是第三人,那是被害人與第三人之間的民事法律關系,刑法上可以在所不問。因此,所謂的“三角詐騙”構成要件與傳統詐騙罪構成要件其實并無二致,客觀方面都要求實施了詐騙行為。而如前所述,本案中的取款行為并非刑法上的“詐騙”行為,自然也就不成立所謂的“三角詐騙”。
再如積分卡加分案,行為人在商場積分卡上私自加分,這就表明行為人具有侵犯商場財產所有權的故意,后面持積分卡換購物券的行為是實現犯意的自然延伸行為、后續行為,持購物券消費更是不具有刑法評價意義的支付憑證兌現行為,因而私自給積分卡加分的行為就是主行為。因此,全案應根據私自給積分卡加分的行為性質定罪(這種私自、秘密加分的行為實質上等同于竊取商場財物,具有盜竊性質),應認定本案成立盜竊罪。
(二)在犯罪進程中最難完成的核心行為是主行為,較容易完成的輔助行為是從行為
具體而言,就是看復數行為中哪一個行為在促使行為人犯罪得逞中的分量最重,或者說看哪一個行為是整個犯罪行為中最難完成的行為,這個最難的行為往往就是最核心的行為,因而應當認定為主行為,其他的輔助行為則應認定為從行為。
如騙奪電腦案,行為人以交易為名,將他人電腦“騙”到自己手上,這個環節的行為是相對容易完成的,而被害人一直跟在行為人身后,電腦并未完全脫離被害人控制范圍,行為人最終能否實現非法占有,關鍵在于跳上摩托車,疾駛而去的行為。因而,行為人最后“奪”的行為是主行為,前面“騙”的行為是準備行為、輔助行為,是從行為。因此,應根據“奪”的行為來定罪,認定全案成立搶奪罪。如果反過來,行為人能夠通過欺騙行為,使被害人完全將電腦交給行為人,行為人獨自離開,在已經完全脫離被害人視線或者控制范圍后,為了避免被害人醒悟后追上來,跳上摩托車,疾駛而去,那么,前面“騙”的行為就是主行為,后面跳上摩托車逃離的行為就是后續行為、保障行為,是從行為。
(三)最能體現罪刑相適應原則的是主行為,明顯導致罪刑不相適應的是從行為
定罪量刑的一般思路是先定罪后量刑,但在疑案分析中,量刑反制定罪理論也是有實踐價值的,該理論的核心觀點是定罪分析處于模棱兩可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存在爭議的各種定罪可能產生的量刑結果來檢驗定罪是否科學、合理。[8]復數行為犯中主行為的認定不同,必然導致案件定性不一,而案件定性不一,量刑也就可能產生較大差異。對此,司法人員可以從不同主行為相對應的案件定性產生的量刑來考察,看是否與行為人的罪行輕重程度及主觀惡性深淺程度相稱,也即是否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的,這一定性相對應的主行為的判斷就是合理、準確的。罪刑相適應的判斷,除了司法人員以司法的專業眼光,從犯罪原因、犯罪情節、犯罪后果、社會危害及行為人的犯罪動機、主觀惡性、犯罪前一貫表現、犯罪后表現等主客觀方面作綜合評判外,還應從常識主義刑法觀角度,考慮刑罰不能違背常識、常情、常理。
如活期存折案,運用量刑反制定罪理論來檢驗案件定性,詐騙罪的立案標準和量刑數額標準均明顯高于盜竊罪,如果認為“騙”的行為是主行為從而認定本案成立詐騙罪,則量刑明顯偏輕,因為行為人明知存折尚在所有權人控制范圍內,并非他人遺忘物更非遺失物,這種情況下仍然“撿”走存折據為己有,在違法性認識上,行為人應當認識到這是在竊取他人財物,其主觀惡性等同于盜竊,故而評價為盜竊罪更能體現罪刑相一致,量刑結果更顯公正,由此也就可以反推而得出結論,應認為“撿”的行為才是主行為從而認定本案成立盜竊罪。
以上復數行為犯中主行為的認定思路僅是筆者的管窺之見。筆者建議“兩高”就此類案件的定性問題發布指導性或典型案例,指導司法人員在辦理此類案件中準確定性,促進司法公正。
*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檢察院檢委會專職委員、三級高級檢察官,全國檢察業務專家[330038]
[1] 參見張明楷:《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91頁。
[2] 參見熊紅文:《公訴實戰技巧(修訂版)》,中國檢察出版社2012年版,第149頁。
[3] 參見張明楷:《單一行為與復數行為的區分》,《人民檢察》2011年第1期。
[4] 參見劉仁文、狄世深、吳孟栓:《私自給商場積分卡加分兌換購物券進行消費應如何處理》,《人民檢察》2006年第20期。
[5] 同前注[3]。
[6] 參見劉一守:《程劍詐騙案——猜配撿拾存折密碼非法提取他人存款行為的定性》,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庭、第二庭編:《刑事審判參考》(總第33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5頁。
[7] 參見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313頁。
[8] 參見梁根林:《量刑反制定罪與刑法基本原則》,《中國檢察官》2019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