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光·建筑·燈火
劉澤曦
人們不停地在建筑物中穿梭。建筑物被認為是“死物”,是“外殼”,卻與人有了絲絲縷縷微妙的聯結。我們開始給它們起名字:“比薩斜塔”“盧浮宮”,這些是公認的;“家”“公司”,這些則是每個人獨有的。興許是覺得名詞太過單調,我們又添上形容詞:“溫馨的家”“冰冷的醫院”,等等。自此,建筑物好像不僅僅是“外殼”了,我們將它當作情感的載體,安心地將情感系在房梁上、融入磚瓦間。
梁思成先生在《為什么研究中國建筑》中寫道:“明清之交,薊城被屠三次,相傳全城人民集中獨樂寺及塔下寺,抵死保護,故城雖屠,而寺無恙,此亦足以表示薊人對寺之愛護也。”獨樂寺對于薊人到底意味著什么? 現在已無法得到確切的回答。薊人大多是貧苦百姓,很可能并不清楚這座寺廟在中國古代建筑史上的地位。私以為他們抵死保護,是因為內心早已將獨樂寺“占為己有”,是把它當作“我們的寺廟”來看待后,激發出了危難時的智勇。他們興許回想起了曾經虔誠的燒香祈禱,孩提時代在寺中躲過的迷藏……對獨樂寺的牽掛情感之濃,竟讓這一群百姓愿意在遭遇屠城時以身軀相護,這足以說明建筑對人民遠遠不是尋常物件那么簡單。
又想起偶然間看到的一則新聞。2021年3月,巴米揚大佛以3D影像的形式在阿富汗巴米揚山谷中重現,當地人激動萬分,甚至淚如雨下。佛像對當地人意味著什么? 信仰、庇佑抑或是神靈?3D影像可以復原其樣貌,卻再也無法復原風吹日曬在大佛身上留下的痕跡,無法復原人們凝視佛像時祈愿和平的目光。巴米揚大佛端坐于山間,靜觀歲月變遷,政權更迭,其本身凝聚的歷史與文化豈能為影像重現?
放眼國外,巴黎圣母院塔樓尖頂遭遇大火,法國巴黎民眾聚集在有八百年歷史的神圣教堂前哭泣、祈禱,為消失的玫瑰窗、飛扶壁而痛心;再觀國內,圓明園被火吞沒,每年數不清的游客來到這里,在僅剩地基的“九州清晏”“曲院風荷”前嘆惋。我們并非專業的建筑家,卻也知曉每一個建筑的消失,都代表著一段不可追溯的歷史。像是一盞長明的“萬年燈”,剎那之間熄滅了光亮,將那段不為人知的小徑掩于黑暗中。普通人對于建筑尚且有如此深的領悟,就不難想象建筑家們面對建筑時的心境了。
《為什么研究中國建筑》不僅有梁思成先生對于自己行程中所見所聞的細致描述,還有很多手工繪制的精美插圖。每一個部件的長寬高,精密計算后的凈荷載甚至能精確到小數點后兩三位,這足以看出梁思成先生對建筑的無比敬畏和熱情。這種熱情使他甘愿放棄原本優渥的生活,和夫人林徽因一起輾轉多地,實地測繪調研古建,即使旅途艱辛、條件簡陋,且結局經常是一無所獲。即使戰火肆虐、城池淪陷,他們最先想到的也是將那些珍貴的手稿藏于最安全的地下庫房,然后才撤離。梁思成先生不僅要向世界證明中國還存在著唐代以前的木構建筑,從而不被西方國家和日本看輕,更要書寫和延續中國建筑史的輝煌。
梁思成先生對建筑的熱愛在《北京——都市計劃的無比杰作》一文中更體現得淋漓盡致。他愛的不是北京城內單個的一殿、一堂、一樓、一塔,而是北京城內的一花一草、一磚一瓦構成的有機整體,他毫不吝嗇地稱贊:“有這樣氣魄的建筑總布局,以這樣規模來處理空間,世界上就沒有第二個!”所以當他目睹北京城市改建,一座座古老城墻轟然倒塌時,他那樣痛心地奔走呼號:“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剝去了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梁思成先生對待古建,就如母親對待孩童,期盼他能歷風霜而不倒,能為社會所用。
建筑師在建筑上傾注的心血,投注的理想,往往超越了簡單的使用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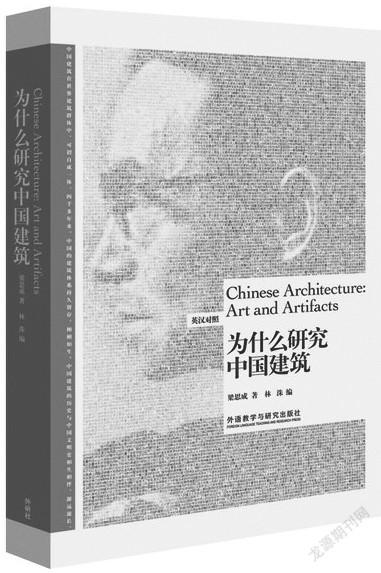
設計師伊勞拉·哈代在巴厘島歷十余載設計建成的竹屋,表現了她幾近“偏執”的環保理念。從父輩開始,哈代一家就致力于建成一座用材絕對環保的小屋。尋竹、加工、制模,過程艱辛,但最難的莫過于讓當地居民搬出鋼筋水泥建造的房屋,住進看起來并不牢固的竹屋。最后,她不僅成功轉變了當地居民的觀念,甚至成立了一個環保組織,一步一步用竹子代替對環境傷害極大的鋼筋混凝土,在巴厘島的山林間,建起一座座環保且宜居的竹屋。竹屋吸引了許多游客參觀,他們在欣賞海島風光的同時,也被造型精美的竹屋吸引。
我家鄉南京市郊的四方當代美術館也匯聚了全球15名頂尖設計師的杰作。主展館由美國著名建筑大師斯蒂文·霍爾親自操刀,筆直的戶外樓梯仿佛通向天空。二層是由竹制黑色混凝土和玻璃構成的順時針折疊的矩形透視空間,從巨大的玻璃窗向前平視,可以看到蒼翠的森林,而向下俯視,則能看到籠罩著微微薄霧的湖區。最妙的還是立于平地向上仰視,不閉合的矩形框住了天上的流云,每一刻都是一幅不同的風景畫。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芬蘭藝術家馬蒂·沙那克塞那豪和皮若·沙那克賽那豪共同設計的別墅“舟泊”,它“停泊”于水邊,湖面上建筑的倒影恰巧是一艘準備出發的小舟。夜晚房內燈光亮起,小舟內也燈火通明,夜晚行舟,隨風起伏,意趣盡現。另外,還有被命名為“馬踏飛燕”的別墅群,由五個小部分組成,像五塊散落的巨石隱于叢林之中,形象地體現出駿馬飛馳的迅疾。這等巧思怎能不讓人為之驚嘆。
四方當代美術館內有精美的建筑群,平常卻人跡罕至。原因是選址偏僻,沒有直達的公共交通,驅車從市中心抵達這里要兩個多小時。但就是這樣偏僻的遠郊為藝術家們提供了寬闊的創作空間,這里依山傍水的優厚條件也為建筑師們提供了獨特的靈感。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美在這里交織,對建筑師而言,建筑是他們理想的實現形式,他們將自己的理念裝進建筑里,等待著探索,欣賞,共鳴,而來參觀的游客也能在這里找到心靈的短暫停靠之處。
相比之下,城市中那些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的同質性則值得警惕。商場那些相同的玻璃櫥窗、相同的頂層塔樓、夜晚相同的燈光設計,人們蝸居其中的相同的小正方形隔間,喧鬧的美食街、服裝店,全面翻新的老式閣樓——放眼中國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我們仿佛對繁華有一種特殊的迷戀,北京的三里屯,上海的外灘商業街,南京的新街口……,擁擠的人潮涌入高檔餐廳、奢侈品店,獲得身份認同和安全感的同時,會不會突然恍惚:我們到底身處哪座城市? 而故宮、圓明園、中山陵、雞鳴寺,北京的豆汁兒,后海胡同里的小吃,南京的鴨血粉絲湯、小籠包,才構成了我們對城市的印象,才讓這座城市有別于其他城市,成為我們心中的“北京”“南京”。
同樣值得警惕的還有那些不合時宜的西式洋樓、西式櫥窗。梁思成先生致力于研究中國建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要提振民族自信心,讓民眾了解中國建筑的歷史是要遠遠長于西方建筑史的,中國建筑史上的精華比起西方也一點兒不遜色。西方有華麗的巴洛克式教堂、尖頂塔樓,東方的江南水鄉也有古色古香的徽派建筑,滇黔一線有獨特的吊腳樓,閩南有造型獨特的民居,黃土高原上有展現古人智慧的窯洞,我們還有全世界最長的長城,最早的石拱橋,最長的石窟……可以說,中國建筑史上群星璀璨,成果豐碩。我們雖然不用拘泥于前人的建造模式,卻應該充分吸收這些模式的精華并加以改造。這樣至少不至于在某地打造的江南水鄉文化旅游景點中,撞見一座巴洛克風格的小樓,上面掛著毛筆寫就的“江南客棧”門匾。此等混搭,大煞風景。若一座城市都被“舶來文化”所“熏陶”,那么走在大街小巷,會讓人誤以為身處異鄉。費孝通先生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前提在于“各美其美”,中國建筑要與世界交流,也要找到屬于自己民族、自己文化的獨特的建筑風格。
建筑對人民的意義,是情感的寄托,是理想的實現,是民族的自信。建筑于我而言,是一盞燈——向內照去,照出建筑師在其上傾注的汗水和心血;向外照去,照出眾生凝視它的千萬種目光;向后照去,照出一段段或美好或坎坷的歷史;向前照去,照亮未來發展的方向。而能被稱為“萬年燈”的建筑,是極少數。它們需要建筑師以赤子之心,精益求精,鑄就經典;需要自然環境的偏愛,助它們遠離山崩地裂,海嘯狂風;需要人民的精心照顧,護它們免于戰火損傷。這樣的“萬年燈”,光亮奪目。歷史的沉淀,自然的偏愛,人民的呵護,為它添上足以萬年不熄的燈油。這樣的“萬年燈”,能夠照亮上下數萬年的時光,照亮一座城市、一個國家。
我衷心希望,有更多像梁思成先生那樣有思想,有堅持,對建筑保有熱愛和初心的建筑師,能建造出代表時代精神的、富有美感的建筑。
我衷心祈愿,在很久很久以后,這個時代的“萬年燈”仍然能夠亮起,能夠講述民族的、人類的歷史,能夠被當作情感的寄存地。愿人們與建筑的聯系能夠更加緊密,人人都來做添“燈油”者,讓“萬年燈”佑“萬戶人”。
(摘自1月19日《中華讀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