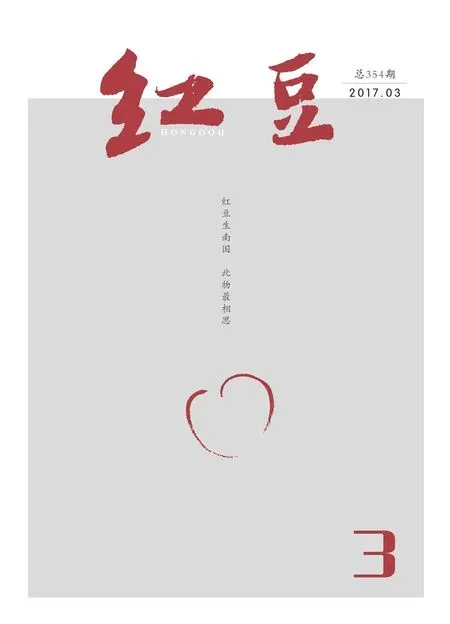詩歌的血液在我體內流淌
由于當詩歌編輯,我的案頭成年累月擺放著大量的詩集和詩歌刊物,其中的大部分詩歌都具有千人一面的雷同表情。這些詩歌的作者在豐富的現實面前選擇了逃離,而轉向個人的內心退守。這一點在女性詩人的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
在這個時代的大多數詩人專心于自己內心隱秘情感表達的時候,我一直走著一條自己的路,而且已經堅定地走了十幾年。從我寫詩的第一天起,我從未盤桓于個人化的抒寫,更多的是對人類命運的整體表達和對宏大的外部現實世界的詩學觀照。
五年前,著名詩人劉西英在讀過我的一首兩百行長詩之后,曾經發出這樣的感慨:“要是詩人們都像田耘這樣寫詩,豈不是要累死自己?”但是我卻始終執著于這種“累”的詩歌寫作方法,我是累并快樂著。
確實,我的詩都比較長,而且很少關注自己,我常常把詩歌的鏡頭投向周遭的世界。那些執著于個體經驗表達的詩人可能無法理解,認為我這樣的宏大敘事是對詩歌的褻瀆,詩人就應該去追求那些浪漫、輕盈和飄逸的東西,就應該去抒寫那些具有最純粹的詩性的東西,例如去寫一座山、一條河、一片云、一朵花。而在我的內心中,“真”與“善”的標準永遠高懸于“美”的標準之上,也就是說,我心目中的好詩不一定是美的,但它一定是真誠的,是能夠直擊人心的。這是我一首詩中的詩句:
請允許我的眼眶再次濕潤。上一次是在
石家莊的詩歌朗誦會上聽黃亞洲的
《大運河放歌》,當朗誦者張敏霞
奔涌的激情遭遇大屏幕上
詩歌原文的波瀾壯闊,當祖國的血液
開始在大運河的血管里汩汩流淌
我的眼淚瞬間就跌落下來
黃亞洲老師的《大運河放歌》,就是我心目中好詩的典范,它飽滿而激情四射,讓讀者心中的情感也呼之欲出。“細節,唯有最真實的細節,才能打動讀者的心弦”,這是我已故的恩師簡明曾經對我說過的話。在我十幾年的詩歌生涯中,我一直秉承這個原則——以細節入詩,拒絕空洞無物的淺表化抒情。
二〇一八年以來,我一直執著于用詩歌寫史,先后完成了《石家莊長歌》《紅色史詩》和《燕趙長歌》三部刻畫歷史的詩集。詩人西川曾說:“歷史之于中國人相當于神話之于希臘人。”這句話表明中國人極為重視歷史。用文字去挽留那些已經逝去和行將逝去的人、事、物,正是文學存在的價值與意義。然而在推崇啟蒙精神與浪漫情懷的朦朧詩潮后,伴隨精英文化的隱身與娛樂文化的勃興,以“新生代”為潮頭,逐漸形成了標榜“活在當下”與“個性表達”的詩歌俗化創作主流。
通過詩歌,我想讓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人重新觸摸到歷史的生活的紋路。我的詩歌常常穿梭于歷史人物和事件中,力圖避免被紛繁復雜的歷史細節所淹沒,不喪失掉自己的聲音,并保留詩歌的意境與意蘊。我的詩不同于一般的抒情詩,我嘗試用組詩的形式,選取地域范圍內的人物,截取不同的生活,對這些人物的生活進行蒙太奇式的剪輯。在敘事過程中,我力圖在生活與詩歌藝術之間形成一種張力。我試圖展示一個隱忍的父親:
此刻,我站在馬路這邊望著對面
一下子就被人群吞沒的
那個瘦小身影,望著
那個沒有他就沒有我的人
瞬間,淚流滿面
我心目中理想的詩應該是這樣的:每一首詩都仿佛萬花筒中變幻的袖珍舞臺,作者則化身為一個冷峻的、反思的寫作者,以詩歌的具象之真摹寫生活的真實,在生活的真實上呈現詩歌的藝術之真。詩中的生活不再是干枯的生活,不再是簡單停留在生活表層上的生活,而是經過藝術加工和思想情感滲透的生活。詩人對時間進行平行、切割或逆轉等處理,給讀者一種時空穿梭或平行時空的錯覺。通過大量的生活細節的呈現,生活中的人和物重新立于詩上,重新開始呼吸。
寧做杜甫,不做李白。在“真”“善”“美”的面前做一道選擇題,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真”和“善”。詩歌的血液在我體內流淌,我的生命因為詩歌充滿溫暖和無限可能。
責任編輯? ?韋毓泉
特邀編輯? ?張? ?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