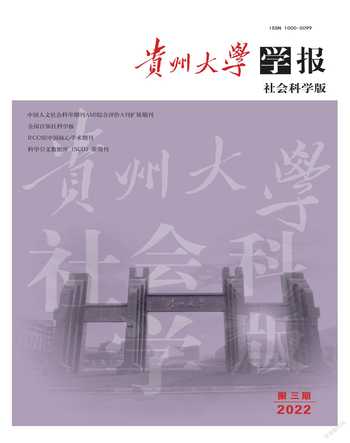論福柯的空間思想
陸 揚(yáng)
(復(fù)旦大學(xué) 中文系,上海 200433)
言及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空間思想,福柯早年的一個(gè)講稿文本《他種空間》在當(dāng)今風(fēng)起云涌的后現(xiàn)代“空間轉(zhuǎn)向”中廣為傳布,并已成為一個(gè)經(jīng)典。雖然這篇講稿的刊布,是在他去世的同年1984年。多年以后,在今日亦成故人的美國人文地理學(xué)家愛德華·索亞(Edward W.Soja)看來,當(dāng)時(shí)福柯已經(jīng)在醞釀?lì)愃朴谒救恕暗谌臻g”那樣的理論體系了。索亞對(duì)福柯的空間思想與列斐伏爾有過一個(gè)比較:
跟列斐伏爾相反,福柯自己的空間理論建構(gòu)從未進(jìn)入高度自覺的細(xì)節(jié),他也很少把自己的空間政治學(xué)轉(zhuǎn)化為明確定義的社會(huì)行動(dòng)綱領(lǐng)。不過我們依然可以說(福柯若經(jīng)提示也會(huì)同意),他的全部著作,從《癲狂與非理智——古典時(shí)期的癲狂史》(1961)到1984年他去世前不久(以及之后)出版的多卷本英譯性史的著作,其核心就是對(duì)空間性進(jìn)行全面的批判的理解。
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本人在1974年出版的標(biāo)志性著作《空間的生產(chǎn)》中,已經(jīng)注意到福柯在《知識(shí)考古學(xué)》里也談到了空間。但列斐伏爾寫作此書時(shí),顯然還未讀到福柯先時(shí)以及后來的空間熱情,并認(rèn)為福柯沒有解釋清楚他所說的空間到底是指什么東西,以及它如何溝通理論領(lǐng)域和實(shí)踐領(lǐng)域。福柯當(dāng)然知道空間是什么。作為讀者,我們反倒納悶,假若列斐伏爾寫作《空間的生產(chǎn)》時(shí),業(yè)已聞知福柯《他種空間》這篇著名講演的內(nèi)容,是不是還會(huì)埋怨福柯談?wù)摽臻g不夠深入?
一、空間的歷史
福柯在1967年3月14日的一次建筑研究會(huì)(Cercle d’études architecturales)上,發(fā)表過一個(gè)題為《他種空間》(Des Espaces Autres)的講演。這個(gè)講演的刊布姍姍來遲,直到福柯本人去世之后的1984年10月,才發(fā)表在《建筑,運(yùn)動(dòng),延續(xù)性》(Architecture,Mouvement,Continuité)雜志的第5期上,后收入《福柯言述集》(Dits et ecrits)第四卷。因?yàn)榘l(fā)表的文本未及經(jīng)作者本人審核,故福柯的正式文集通常不收此文。但在福柯謝世前不久,這個(gè)講演的手稿在柏林的一個(gè)公共場(chǎng)合有過一次展示。由此可見,《他種空間》作為福柯空間思想的代表性著述,其著作權(quán)是不成問題的。
1967年是結(jié)構(gòu)主義方興未艾,或者說是如日中天的年代。所以不奇怪福柯的這個(gè)《他種空間》講演,開篇談?wù)摰囊彩墙Y(jié)構(gòu)主義。福柯說,19世紀(jì)的一大困頓是歷史,發(fā)展與停滯、危及與循環(huán)、過去的不斷積累與世界降溫,諸如此類的主題叫人迷茫。故而,19世紀(jì)的神話資源從根本上說是來自熱力學(xué)第二定律;即是說,能量可以從溫度高的物體傳遞到溫度低的物體上面,但是反過來不能從低向高傳遞。但是今天卻不同,今天的時(shí)代是空間的時(shí)代,其特征是共時(shí)性而不是歷時(shí)性。我們處在一個(gè)并列、遠(yuǎn)近和散布的時(shí)代。我們對(duì)世界的經(jīng)驗(yàn),不復(fù)是時(shí)間串聯(lián)起來的悠長生命,而成為一張用它自己的線索交叉連接起點(diǎn)與點(diǎn)的大網(wǎng)。故而:
結(jié)構(gòu)主義,或者至少集聚在這個(gè)稍許有點(diǎn)籠統(tǒng)的名號(hào)之下的東西,是在可以連接到一根時(shí)間軸線上面的諸多元素之間,建立起一種關(guān)系集合,以使這些元素呈現(xiàn)為并列的、彼此沖突的,又彼此包容的模樣,簡言之,呈現(xiàn)為一種建構(gòu)。事實(shí)上,結(jié)構(gòu)主義并不意味著否定時(shí)間;它認(rèn)真關(guān)系到某種同我們稱之為時(shí)間和歷史的東西打交道的方法。
這是說,空間本身有一段歷史。結(jié)構(gòu)主義雖然奉行共時(shí)性的空間研究方法,但并不意味著排除歷時(shí)性的時(shí)間線索。這以空間出現(xiàn)在我們今天的理論以及各種體系的視野里,并不是新鮮事情。對(duì)此福柯指出,在西方的經(jīng)驗(yàn)里,空間有空間的歷史。回溯歷史,中世紀(jì)就是不同地方的等級(jí)有序的集合,有神圣地方和世俗地方,被保護(hù)的地方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地方,城市地方和鄉(xiāng)村地方等的對(duì)立,所有這些地方都關(guān)系到人們的真實(shí)生活。而在宇宙學(xué)理論里,下面是陸地人間,陸地上面有天國,天國上面還有超級(jí)天國。有些地方的事物已經(jīng)被劇烈移位過,有些地方的事物則天生穩(wěn)穩(wěn)就在那里。而正是所有這些地方的等級(jí)排列、反向排列,以及交叉排列構(gòu)成了我們大體可以叫作中世紀(jì)空間的那東西。簡言之,中世紀(jì)的空間,就是“確認(rèn)方位的空間”(espace de localisation)。
這個(gè)“確認(rèn)方位的空間”,在福柯前一年出版的《詞與物》中,被表述為在中世紀(jì)與文藝復(fù)興之交被新柏拉圖主義復(fù)活的一個(gè)古老概念——“小宇宙”。據(jù)福柯所言,它是將兩個(gè)具有相似性對(duì)象的相互作用,應(yīng)用于所有的自然領(lǐng)域之中。它意味著知識(shí)主體在每個(gè)事物中都能發(fā)現(xiàn)自己的映像,以及對(duì)浩大宇宙的深信不疑。反過來,最高領(lǐng)域中的可見秩序,將同樣反映在地球最深處的黑暗世界中。所以它表明:
存在著一個(gè)巨大的世界,它的四周勾畫了所有被造物的界線;在世界的另一端,存在一個(gè)享有優(yōu)先權(quán)的創(chuàng)造物,它在自己的有限向度內(nèi),產(chǎn)生了有關(guān)天空、星星、山脈、河流和風(fēng)暴的巨大秩序;相似性的相互作用正是在這一基本的類推的有效界線內(nèi)展開的。因這個(gè)事實(shí),從小宇宙到大宇宙的距離無論有多大,但都不可能是無限的。
很顯然,這里以人為小宇宙,對(duì)應(yīng)于自然大宇宙的空間觀里。在福柯看來,它們終究還是有邊界的。用他自己的話說,便是大自然,類似符號(hào)與相似性的相互作用,依據(jù)宇宙的復(fù)制形式,把自身封閉了起來。
福柯認(rèn)為這個(gè)確認(rèn)方位的空間,是始于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因?yàn)橘だ栽馐芷群Φ恼嬲颍辉谟谒l(fā)現(xiàn)或者重新發(fā)現(xiàn)了地球圍繞太陽旋轉(zhuǎn),而在于構(gòu)建了一個(gè)無限的開放空間。在這個(gè)無限的空間里,中世紀(jì)的方位紛紛消解,不復(fù)具有任何意義,而化解成為其運(yùn)動(dòng)中的一個(gè)點(diǎn)。換言之,從伽利略和17世紀(jì)開始,“廣延”(eténdue)替代了方位確認(rèn)。空間由此從中世紀(jì)的方位確認(rèn)轉(zhuǎn)移到近代的擴(kuò)展模式。及至今日,廣延又被“位置”(emplacement)所替代。“位置”可以定義為點(diǎn)與點(diǎn)之間的關(guān)系。而從人口統(tǒng)計(jì)學(xué)的角度來看,人類的位置或者生活空間問題,并不僅僅是探究世界是不是有足夠空間供人類生存,同樣也在于探問人類因素以什么樣的相鄰關(guān)系,怎樣儲(chǔ)存、循環(huán)、標(biāo)簽和分類,方能在特定環(huán)境中達(dá)到特定目的。所以,位置與位置之間的關(guān)系,就是我們今天時(shí)代里的空間形式。這也導(dǎo)致今天時(shí)代的焦慮,何以從根本上關(guān)牽著空間,而遠(yuǎn)勝于關(guān)牽時(shí)間。
問題是,伽利略開啟的世俗空間傳統(tǒng),在福柯看來今天依然有待于開拓。對(duì)此福柯指出,今天我們的生活依然是被一系列根深蒂固的二元對(duì)立所統(tǒng)治,我們的制度和實(shí)踐依然沒有摧毀這些空間。例如: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家庭空間與社會(huì)空間、文化空間與實(shí)用空間、休閑空間與工作空間等,不一而足。對(duì)此,福柯高度推崇哲學(xué)家加斯東·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空間的詩學(xué)》,認(rèn)為巴什拉此書中的現(xiàn)象學(xué)描述可以給予我們?cè)S多啟示。福柯說:
巴什拉的劃時(shí)代著作和現(xiàn)象學(xué)描述教導(dǎo)我們,我們并非生活在一個(gè)同質(zhì)的空洞的空間里;恰恰相反,我們生活的空間也深深浸潤著各種特質(zhì),甚或通盤就是異想天開。我們第一感知的空間、夢(mèng)幻空間和激情空間,各各具有自身的內(nèi)在特質(zhì):有亮麗的、輕盈的、透明的空間,也有晦暗的、粗糲的、蒙障重重的空間;有高高在上的最高空間,也有深深塌陷的泥淖空間;還有涌泉般流動(dòng)不居的空間,以及石頭或水晶般凝結(jié)固定的空間。
但福柯也認(rèn)為,巴什拉的分析對(duì)于思考今日之時(shí)代固然提供了一個(gè)出發(fā)點(diǎn),但主要還是涉及內(nèi)部空間,而他現(xiàn)在同樣希望來談一談外部空間。
福柯所說的外部空間,也就是我們的生活空間。他認(rèn)為在這個(gè)空間里我們的生命、時(shí)間和歷史在不斷遭受侵蝕。這個(gè)空間說到底,本身也是一個(gè)“異質(zhì)空間”(espace hétérogène)。異質(zhì)空間不是真空,不是我們?cè)谄渲锌梢噪S意安置某人某物,可以把它點(diǎn)綴得五光十色的空間。反之,它是一系列關(guān)系,而正是這關(guān)系在界定著我們的交通、街道和運(yùn)動(dòng)。通過這個(gè)關(guān)系群集,我們可以描述咖啡館、影院、海灘這些休閑場(chǎng)所是在什么地方,也可以描繪封閉或半封閉的棲居地,如住宅、臥室、床榻,等等。但是,所有這些場(chǎng)所之間,福柯指出,他最感興趣的是那些在這一大張關(guān)系網(wǎng)里,具有特別屬性的地方,因?yàn)檫@些地方可以質(zhì)疑、抵制,甚至顛覆它們所反映的關(guān)系集群。這些特殊的空間,福柯認(rèn)為主要存在兩種類型:一種聯(lián)系著所有其他空間,那是烏托邦;一種對(duì)立于所有其他空間,那是“異托邦”。
二、異托邦
“異托邦”(hétérotopia)是福柯空間思想的一個(gè)核心概念。所謂異托邦,是相對(duì)烏托邦而言。福柯對(duì)于烏托邦的定義:它是沒有真實(shí)方位的地方。但總體來看,這些地方同社會(huì)的真實(shí)空間多多少少有著曲曲直直的關(guān)系。它們以完美的形式表現(xiàn)社會(huì)本身,或者把社會(huì)顛倒過來,那是反烏托邦。不過說來說去,大凡烏托邦,指的都是非真實(shí)的地方。
但異托邦不同,異托邦是真實(shí)的地方。福柯指出,在每一種文化、每一個(gè)文明里,都有這樣一些確實(shí)存在的真實(shí)地方,它們有時(shí)候就像沒有方位的烏托邦,落實(shí)在了真實(shí)場(chǎng)地,同一文化中的所有其他真實(shí)場(chǎng)景,同時(shí)呈現(xiàn)出來,又同時(shí)彼此沖突和反轉(zhuǎn)。這樣的地方,其實(shí)是在一切地方之外,即便它們?cè)诂F(xiàn)實(shí)中能找到具體方位。這樣一個(gè)歷時(shí)與共時(shí)并存,在又不在的地方,便是福柯的“異托邦”。對(duì)此,福柯做了一個(gè)鏡子的譬喻:
因?yàn)檫@些地方跟它們所反映和言說的場(chǎng)所完全不同,考慮到跟烏托邦的對(duì)比,我將它們稱之為異托邦。我相信在烏托邦和這些完全不同的他種場(chǎng)所,即異托邦之間,還可能有某種混合的、聯(lián)合的經(jīng)驗(yàn),那可能就是鏡子。鏡子說到底是一種烏托邦,因?yàn)樗且粋€(gè)沒有方位的地方。在鏡子里,我在我不在的地方看到自己,那是一個(gè)敞開在平面背后的非真實(shí)的虛擬空間;我就在那里,可是我并不在那里,是一種影子讓我看到了我自己,讓我在我不在場(chǎng)的地方看到自己,這就是鏡子的烏托邦。但是就鏡子存在于真實(shí)世界,就我占據(jù)的位置起到反作用而言,它也是一個(gè)異托邦。
對(duì)此,福柯進(jìn)一步的解釋是,從鏡子出發(fā),我發(fā)現(xiàn)我并不在我所在的地方。鏡子里我的目光從虛擬空間的深處看過來。我在照鏡子,這本身是真實(shí)的,但是鏡子里的我卻是真實(shí)又不真實(shí)的幻相。這面處在真實(shí)與虛擬空間之間的鏡子,在福柯看來,其功能就照出了烏托邦和異托邦的雙重屬性。
那么,異托邦的意義又當(dāng)何論?即是說,在一個(gè)特定社會(huì)中,我們?nèi)绾蝸硐到y(tǒng)研究、分析、解讀這些他種空間呢?福柯提出,圍繞我們生活在其中的這個(gè)異托邦空間,其真真假假的論爭可以稱之為“異托邦學(xué)”。福柯進(jìn)而條分縷析,闡述了異托邦學(xué)和異托邦的六個(gè)原則。
福柯認(rèn)為烏托邦學(xué)的第一原則,就是普天之下任何一種文化,都可以構(gòu)成異托邦。這是說,異托邦無所不在。但即便無所不在,異托邦卻沒有絕對(duì)統(tǒng)一的形式。它形態(tài)各異,不過大體可以歸結(jié)為兩大類型。其一見于原始社會(huì),可名之為危機(jī)異托邦。比如說有一些圣地和禁地,專門留給處在危機(jī)狀態(tài)的人眾,如青少年、處于經(jīng)期的女人、懷孕婦女、老人等。迄至今日,危機(jī)烏托邦已日漸消失,但也有若干剩余,如19世紀(jì)的寄宿學(xué)校,年輕人的兵役服務(wù)等。福柯并舉了“走婚”(voyage de noces)這個(gè)一直到20世紀(jì)中葉依然存在的古老例子,指出女孩子失落貞操,可以發(fā)生在許多“烏有之地”,火車和蜜月旅館就是這一類烏有之地,它們都是沒有地理標(biāo)志的異托邦。
異托邦學(xué)的第二個(gè)原則是同一個(gè)異托邦在社會(huì)歷史中,可以呈現(xiàn)出完全不同的功能。對(duì)此,福柯舉了公墓的例子。墓地當(dāng)然不同于普通的文化空間。但是它跟城邦村莊都有關(guān)系,因?yàn)槊總€(gè)人、每個(gè)家庭都有親人埋葬于斯。福柯指出,在西方文化中公墓事實(shí)上一直存在,但是經(jīng)歷了很大的變化。直到18世紀(jì)末葉,公墓還一直位居城市中心,緊挨著教堂。公墓里也有等級(jí),有骸骨教堂、個(gè)人墳?zāi)梗烫美镞€有墓穴。但是從19世紀(jì)開始,隨著骨灰盒普及大眾,公墓向城市邊緣遷移。這跟擔(dān)憂墓穴傳染疾病的恐懼直接相關(guān)。如是公墓不復(fù)是城市的不朽神圣心臟,反之變身為了“他種城市”,每個(gè)家庭在這里都有一個(gè)幽冥居所。
第三個(gè)原則是指異托邦可以將互不相容的若干空間和場(chǎng)所,并置在同一個(gè)地方。在這一方面,舞臺(tái)和電影院便是例子。舞臺(tái)上互不相干的地點(diǎn)接連展開,影院中我們?cè)谝环蕉S的銀幕上看到了大千世界的三維空間。但這一類異托邦里,最典型的例子是花園。對(duì)此,福柯高度贊賞古代東方花園,指出波斯的傳統(tǒng)花園是一個(gè)神圣空間,它的長方四邊形代表世界的四個(gè)部分,中心有噴泉水池,它較外圍更要神圣,好比世界的肚臍。花園里各種草木匯聚到同一空間,構(gòu)成了一個(gè)微觀宇宙。就此而言,波斯地毯也是花園的復(fù)制品,它將整個(gè)世界的完美符號(hào)聚于一體,是在空間中流動(dòng)的花園。因此,花園就是一個(gè)普世性的幸福異托邦。今天的動(dòng)物園,就是從花園脫胎而出的。
第四個(gè)原則指的是異托邦經(jīng)常聯(lián)系著的時(shí)間的片段。這是說,為了對(duì)稱的緣故,異托邦經(jīng)常走向所謂的“異托時(shí)”(hétérochronies)。對(duì)此,福柯又舉了墓地的例子,他指出,當(dāng)人們同傳統(tǒng)的時(shí)間徹底割斷,異托邦就開始全力以赴了。所以,墓地是異托邦的典型地方,因?yàn)槿松筋^,墓地就伴著這個(gè)古怪的異托“時(shí)”,開始進(jìn)入貌似永恒的另一種時(shí)間。而在我們今天的社會(huì)里,異托邦和異托時(shí)錯(cuò)綜復(fù)雜交合在一起。比如在博物館和圖書館里,異托邦就在無窮無盡地積累時(shí)間,將各個(gè)時(shí)期的文物、文獻(xiàn)和檔案,所有的時(shí)代、所有的形式、所有的趣味,集聚在同一個(gè)空間。福柯指出,這個(gè)無限積累的理念是屬于我們的現(xiàn)代性。不同于博物館和圖書館的永久性,福柯發(fā)現(xiàn)異托邦和異托時(shí)的連接方式還有一種轉(zhuǎn)瞬即逝的形式,那就是節(jié)慶。節(jié)慶的場(chǎng)合通常是在市郊的一片空曠地上,一年一度或一年兩度,三教九流各式人眾匯合過來,摔跤的、耍蛇的、算命的,無所不有。這是為異托邦和異托時(shí)的另一典型景觀。
第五個(gè)原則,異托邦應(yīng)是一個(gè)既開放,又封閉的系統(tǒng),彼此隔絕又彼此滲透。總體來說,異托邦的空間并不像公共空間那樣可以自由出入。進(jìn)入是強(qiáng)制的,如兵營和監(jiān)獄。有一些地方要事先提出申請(qǐng),或者經(jīng)過潔凈儀式,方可入內(nèi),如穆斯林的土耳其浴室。還有一些地方仿佛是敞開大門,誰都可以自由出入這類異托邦空間。然而,那只是幻覺。如巴西過去有些大農(nóng)莊的著名臥室,游人盡可以推門進(jìn)去,睡上一晚。但是,這些臥室跟主人家庭區(qū)域并不聯(lián)通,所以游客到底是過客,并不是主人邀請(qǐng)的貴客。你以為是進(jìn)去了,實(shí)際上還是沒有進(jìn)去。
最后一個(gè)原則是在異托邦跟剩下來所有空間的關(guān)系中,在兩極之間發(fā)揮功能。兩極都旨在創(chuàng)造一個(gè)虛幻空間,可是在這個(gè)虛幻空間里又見出一切真實(shí)空間,它們是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或者反過來說,兩極的功能是意在創(chuàng)造另一個(gè)真實(shí)的空間,一個(gè)完美的、精工細(xì)作的、有條不紊的他種空間,而不似我們自己的空間那樣雜亂無章。所以,它可以作為真實(shí)空間的一種補(bǔ)償。對(duì)此,福柯舉了殖民地的例子。他指出第一波殖民熱潮發(fā)生在17世紀(jì),英國人在美洲建立的新教徒社會(huì),就是絕對(duì)完美的他種空間。與此相似的還有南美洲耶穌會(huì)的殖民地,井井有條堪稱奇跡。如巴拉圭的耶穌會(huì)村莊,就嚴(yán)格按照長方形來布局,矩形的底部是教堂,一邊是學(xué)校,一邊是公墓,教堂前方有一條街道伸出,跟另一條街道十字相交,沿著這兩根軸線,居民各就其位,如是完美演繹了基督的十字架符號(hào)。是以不奇怪,在福柯的《他種空間》這篇講演中,最后的話是:
封閉屋舍和殖民地,是異托邦的兩種極端類型。說到底,我們可以想象船是一種漂流空間,一個(gè)沒有地方的地方,它自給自足,將自己封閉起來,同時(shí)又漂向無限的大海,從港口到港口,從一段航程到另一段航程,從屋舍到屋舍,一直漂到殖民地,尋找它們藏在花園里的珍貴寶藏。這樣想象下來,你就會(huì)懂得從16世紀(jì)到現(xiàn)在,為什么船是我們文明中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偉大工具(今天我不談經(jīng)濟(jì)),而且同時(shí)也是最偉大的想象載體。船是最典型的異托邦。沒有船的文明中夢(mèng)想枯竭,間諜替代冒險(xiǎn),警察替代了海盜。
至此我們發(fā)現(xiàn),福柯談他種空間再是云遮霧罩,終究還是圍繞著以大西洋為中心的海洋文明展開的。烏托邦也好,異托邦也好,大陸文明跟它們沒有關(guān)系。大陸文明在福柯看來,在他的“他種空間”里不值一道。
三、規(guī)訓(xùn)的空間
福柯的《知識(shí)考古學(xué)》在1969年面世,該書的主題之一便是質(zhì)疑歷史研究的連續(xù)性。用福柯本人在該書“引言”中的話說,那些被稱為思想史、科學(xué)史、哲學(xué)史,以及文學(xué)史的學(xué)科,不管它們叫什么名稱,大都業(yè)已偏離傳統(tǒng)史學(xué)家們的研究和方法。在這些學(xué)科中,人們的注意力已經(jīng)從原來描繪成“時(shí)代”或“世紀(jì)”的廣闊單位,轉(zhuǎn)向斷裂現(xiàn)象。故人類思維的連續(xù)性,今天正在受到挑戰(zhàn),反之?dāng)嗬m(xù)性的重要性呼之欲出。就他本人而言,福柯指出,對(duì)于精神病理學(xué)、醫(yī)學(xué)、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這一類傳統(tǒng)學(xué)科,他不會(huì)貿(mào)然深入它們的內(nèi)在形式和潛在矛盾,但是他會(huì)提出問題:
它們根據(jù)什么樣的規(guī)律形成?它們?cè)谑裁礃拥脑捳Z事件基礎(chǔ)上被割裂出來,以及它們最終是否在它們被接受的并且近乎成為制度的個(gè)體性中,不是那些更為穩(wěn)定單位的表層結(jié)果?我接受歷史給我提出的這些整體,只是隨即對(duì)它們表示質(zhì)疑;只是為了解析它們并且想知道是否能合理地對(duì)它們進(jìn)行重新組合;或者是否應(yīng)把它們重建為另一些整體,把它們重新置于一個(gè)更一般的空間,以便在這個(gè)空間中驅(qū)除它們表面的人所熟知的東西,并建立它們的理論。
福柯這里的意思是明確的,那就是他的新歷史主義話語研究是將主要使用空間的方法,放入傳統(tǒng)史學(xué)想當(dāng)然的連續(xù)性形式之中。惟其如此,可望打開一個(gè)更為寬廣的領(lǐng)域,將澄清原始材料即話語空間中的事件群體,作為視為一切批評(píng)行為的先決條件。
福柯1975年出版的《規(guī)訓(xùn)與懲罰:監(jiān)獄的誕生》,被認(rèn)為是受早期馬克思·韋伯(Max Weber)與阿多諾(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等現(xiàn)代性批判家的影響,系統(tǒng)且細(xì)致描寫了現(xiàn)代世界的空間轉(zhuǎn)化譜系。批判的主題固然一如既往,但福柯在此書中表現(xiàn)出來的空間意識(shí),則被認(rèn)為是以身體為中心,通過追溯刑罰體系的變遷,來寫權(quán)力機(jī)制的衍變。酷刑、懲罰、規(guī)訓(xùn)、監(jiān)獄,由此成為該書的四個(gè)典型場(chǎng)景。在該書中,福柯從落筆開始即不厭其詳,細(xì)數(shù)18世紀(jì)以降作為“公共景觀的酷刑”慘不忍睹地撕裂肉體。進(jìn)而表明,西方現(xiàn)代世界形成的歷史,同樣也是一部空間轉(zhuǎn)化的歷史,故必須在權(quán)力、知識(shí)和肉體的關(guān)系之中,來分析現(xiàn)代社會(huì)的轉(zhuǎn)型。
《規(guī)訓(xùn)與懲罰》開篇寫的是公共空間中的公開處決,描述了18世紀(jì)的劊子手如何在廣場(chǎng)上搭起行刑臺(tái),用燒紅的鐵鉗子撕開犯人的胸膛和四肢,用硫磺來燒犯人執(zhí)弒君兇器的右手,再用融化的鉛汁灌入撕裂的傷口,然后四馬分尸。對(duì)此福柯的感想是,作為一種公共景觀的酷刑是消失了,這是事實(shí),即在數(shù)十年間,對(duì)肉體的酷刑和肢解、在臉上和手臂上打烙印、示眾以及暴尸,這些現(xiàn)象終究是消失了。但是懲罰沒有消失:
因此,懲罰將逾益成為刑事程序中最隱蔽的部分。這樣便產(chǎn)生了幾個(gè)后果:它脫離了人們?nèi)粘8惺艿念I(lǐng)域,進(jìn)入抽象意識(shí)的領(lǐng)域;它的效力被視為源于它的必然性,而不是源于可見的強(qiáng)烈程度;受懲罰的確定性,而不是公開懲罰的可怕場(chǎng)面,應(yīng)該能夠阻止犯罪;懲罰的示范力學(xué)改變了懲罰機(jī)制。結(jié)果之一是,司法不再因與其實(shí)踐相連的暴力而承擔(dān)社會(huì)責(zé)任。
至此,我們可以說,福柯下沿的是與他的本國同胞列斐伏爾迥異其趣的另外一個(gè)空間的批評(píng)傳統(tǒng)。誠如福柯《他種空間》和《權(quán)力的地理學(xué)》等文獻(xiàn)中闡述的他種空間與異托邦理念,多被嗣后學(xué)者賦予多元空間的后殖民解讀和性別解讀。從《規(guī)訓(xùn)與懲罰》一書中對(duì)18世紀(jì)中期以來刑罰機(jī)制現(xiàn)代變革的分析,以及對(duì)全景暢視監(jiān)獄機(jī)制下空間、身體、權(quán)力的關(guān)系考察,也都啟發(fā)了我們對(duì)社會(huì)空間與主體認(rèn)同的新認(rèn)知。
福柯的這一思想,直接導(dǎo)致了以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為代表的新歷史主義批評(píng)對(duì)文藝復(fù)興戲劇的重新解讀。格林布拉特本人在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暴風(fēng)雨》中通力破解權(quán)力關(guān)系,讀出普洛斯庇羅對(duì)卡列班的無情殖民,即為一例。福柯的權(quán)力—空間地緣政治學(xué),終而演繹為性取向—性別建構(gòu)的主體性空間對(duì)峙。這一方面,大衛(wèi)·貝爾(David Belle)等人的《繪制欲望:性的地理學(xué)》、羅賓· 朗赫斯特(Robyn Longhurst)的《身體:探索流動(dòng)的邊界》以及琳達(dá)·瓊斯頓(Lynda Johnston)等人的《空間、地方和性:性向地理學(xué)》等一批文獻(xiàn),都可以顯示福柯的影響怎樣在性別和地緣政治的每一層面蔓延。
就規(guī)訓(xùn)與懲罰的主題而言,在福柯看來,歐洲社會(huì)的規(guī)訓(xùn),是從空間的分配起步的。具體來說,為了實(shí)現(xiàn)規(guī)訓(xùn)的目的,需要以下數(shù)種機(jī)制的配合。第一是需要一個(gè)封閉的空間,圈定一個(gè)自我封閉的、有別周圍世界的場(chǎng)所。這方面有對(duì)流浪漢和窮人的“大禁閉”,也有一些更謹(jǐn)慎也更為隱蔽的措施。還有逐漸采用修道院式寄宿制的大學(xué)和中學(xué),以及兵營,它可以約束大軍,使不至擾民,避免駐軍與地方當(dāng)局的沖突。福柯枚舉的統(tǒng)計(jì)數(shù)字是,直到1745年,法國大約有320個(gè)兵營。1775年,兵營內(nèi)的總?cè)藬?shù)達(dá)到20萬人。此外,工廠也逐漸形成大面積的單純而明確的工業(yè)空間。日趨集中的管理模式,便于獲取最大利益,消除偷盜、怠工、動(dòng)亂等不利因素。
第二,有鑒于“封閉”原則在規(guī)訓(xùn)中不可能一勞永逸,第二種機(jī)制是根據(jù)單元就位或者分隔。它意味著規(guī)訓(xùn)空間可以進(jìn)一步細(xì)致化,按需分配,每個(gè)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個(gè)位置上都有一個(gè)人。如是便于監(jiān)督施行,誰到場(chǎng)了,誰缺場(chǎng)了,誰盡力了,誰開小差了,一目了然。這是用紀(jì)律組織起來的一個(gè)可解析的空間。福柯發(fā)現(xiàn)這個(gè)機(jī)制類似修道院的密室,它通常是分格單元式的,適合禁欲主義之需。他并引法國18世紀(jì)警官尼古拉·德拉馬爾(Nicolas Delamare)《論警察》中的描述:“睡覺是死亡的影像,寢室是墓地的影像……盡管寢室是合用的,但是床的排列,幕布的遮擋,使得姑娘起床和就寢都不會(huì)被人看見。”即便如此,福柯認(rèn)為這一方式,也還是顯得粗糙。
第三是按用途分隔出特殊空間。比如陸軍醫(yī)院和海軍醫(yī)院,就有嚴(yán)格的隔離區(qū)域,以防傳染病的流行。每個(gè)病人都被記錄在冊(cè),分床隔離,對(duì)癥處置。隨之形成一種行政空間和政治空間,借此醫(yī)療空間形成了。還有18世紀(jì)末葉出現(xiàn)的工廠,它將人員分配、生產(chǎn)機(jī)制的空間安排,以及其他崗位分配結(jié)合在一起,構(gòu)成的布局是一方面可以統(tǒng)攬全局,一方面可以監(jiān)督到每一個(gè)崗位。工人的體力、敏捷性、熟練性、持久性都?xì)v歷在目。這一規(guī)訓(xùn)空間的形成,故而成為大工業(yè)興起時(shí)期的必然。
第四是教育空間的等級(jí)排列。等級(jí)替代作為統(tǒng)治單位的領(lǐng)土和作為居住單位的地點(diǎn),成為新的規(guī)訓(xùn)空間形式。福柯舉了班級(jí)的例子,他指出在耶穌會(huì)的大學(xué)里,每個(gè)班級(jí)有二三百名學(xué)生,十人一組。這呼應(yīng)了當(dāng)年羅馬和迦太基行伍中的“十人團(tuán)”基本形式。每個(gè)學(xué)生的位置,根據(jù)他作為“十人團(tuán)”中一名戰(zhàn)士的角色來加以確定。從18世紀(jì)開始,“等級(jí)”愈益彰顯,學(xué)生在課堂和校園中的座次和位置、每個(gè)學(xué)生完成各項(xiàng)任務(wù)和考試后的名次、學(xué)生每周每月每年獲得的名次、年齡組的序列、依難度排列的科目序列等,皆排定在等級(jí)空間之中而交替換位。對(duì)此福柯說:
這種系列空間的組織,是基礎(chǔ)教育的重要技術(shù)變動(dòng)之一。它使得傳統(tǒng)體制(每個(gè)學(xué)生受到幾分鐘教師的指導(dǎo),而其他程度不一的學(xué)生無事可做、無人照顧)能夠被取代。它通過逐個(gè)定位使得有可能實(shí)現(xiàn)對(duì)每個(gè)人的監(jiān)督并能使全體人員同時(shí)工作。它組織了一種新的學(xué)徒時(shí)間的體制。它使教育空間既像一個(gè)學(xué)習(xí)機(jī)器,又是一個(gè)監(jiān)督、篩選和獎(jiǎng)勵(lì)機(jī)器。
空間與時(shí)間的因素在這里再度交叉起來,成就為多元并置異托邦的又一種規(guī)訓(xùn)形式。據(jù)福柯自己的解釋,規(guī)訓(xùn)的策略與自然分類法不同,后者是以特征與范疇為基軸,規(guī)訓(xùn)策略則是以單數(shù)和復(fù)數(shù)的關(guān)系為基軸,既對(duì)個(gè)體作特征描述,又對(duì)特定的復(fù)雜對(duì)象加以整理,從而為“細(xì)胞權(quán)力”(cellular power)的微觀物理學(xué)打下了基礎(chǔ)。
福柯認(rèn)為規(guī)訓(xùn)空間的典型,是18至19世紀(jì)英國功利主義哲學(xué)家邊沁(Jeremy Bentham)發(fā)明的全景暢視監(jiān)獄(panopticon)。這類監(jiān)獄的構(gòu)造是在一個(gè)環(huán)形建筑群中心,修建一個(gè)高高的瞭望塔。瞭望塔頂端有一圈大窗戶,面對(duì)包圍著它的環(huán)形建筑。環(huán)形建筑被分隔成一個(gè)個(gè)狹小囚室,每個(gè)囚室都貫穿建筑群的橫切面,佩以兩個(gè)窗戶,一個(gè)朝里跟瞭望塔頂?shù)拇皯粝鄬?duì),一個(gè)朝外用于采光。每個(gè)囚室里關(guān)進(jìn)一個(gè)瘋?cè)恕⒉∪恕⒆锓浮⒐と嘶蛘邔W(xué)生,其一舉一動(dòng),假以跟瞭望塔恰好相反的光源角度,被塔頂?shù)谋O(jiān)視人看得清清楚楚。由于犯人知道自己時(shí)刻暴露在監(jiān)視之下,以至于即便塔頂無人,他們的舉動(dòng)也習(xí)慣成自然,變得規(guī)規(guī)矩矩。福柯認(rèn)為邊沁設(shè)計(jì)的這一全景暢視監(jiān)獄,顛覆了傳統(tǒng)監(jiān)獄的原則,更具體說是推翻了它的三個(gè)基本功能:封閉、黑暗和隱蔽。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種有意識(shí)的和持續(xù)的可見狀態(tài),從而確保權(quán)力自動(dòng)地發(fā)揮作用”。簡言之,權(quán)力不復(fù)體現(xiàn)在個(gè)人身上,而是變相體現(xiàn)在了空間與光的精心安排之上。作為《規(guī)訓(xùn)與懲罰》中被引述最多的這個(gè)全景暢視監(jiān)獄的建筑理念,它不妨說是肉體在空間中的另一種定位,這個(gè)身體為權(quán)力所規(guī)訓(xùn)的定位,可見在福柯看來是無所不在。不僅是監(jiān)獄,醫(yī)院、兵營、工廠和學(xué)校亦然。由是觀之,資本主義的現(xiàn)代性空間,不啻是一個(gè)規(guī)訓(xùn)和懲罰的大監(jiān)獄。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形而上學(xué)》開篇即稱其為人類最高貴感官的視覺,由此也與權(quán)力狼狽為奸,成為了監(jiān)禁與懲罰的幫兇。
美國批評(píng)家菲利普·韋格納(Phillip Wegner)在他題名為《空間批評(píng)》的文章中,認(rèn)為福柯的空間思想是跟列斐伏爾分道揚(yáng)鑣。列斐伏爾關(guān)注現(xiàn)代社會(huì)和現(xiàn)代文化中的空間關(guān)系,福柯則致力于探究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空間轉(zhuǎn)化的歷史譜系,特別是把聚焦的中心轉(zhuǎn)向了身體。如是在福柯筆下,個(gè)人的身體成為公共“劇場(chǎng)”中的主體,承受遠(yuǎn)離日常生活的儀式空間中的嚴(yán)厲懲罰。然而,正因?yàn)檫@一體系變身為了驚心動(dòng)魄的公共景觀,也導(dǎo)致它極不穩(wěn)定,隨時(shí)有可能被顛覆過來。故而:
在這一古老的權(quán)力邏輯中,逐漸滋生出來一個(gè)新的體系,其中每一個(gè)身體發(fā)現(xiàn)自己被定位在“一個(gè)巨大的封閉、復(fù)雜,有等級(jí)森嚴(yán)的結(jié)構(gòu)里”,而屈從于一個(gè)監(jiān)控與操控的連續(xù)體制。一個(gè)福柯名之為“規(guī)訓(xùn)”的整個(gè)運(yùn)作系列——“工具、機(jī)制、程序、應(yīng)用層面、目標(biāo)”——應(yīng)運(yùn)而生,以便生產(chǎn)出“規(guī)范”的主體,同時(shí)標(biāo)記出一個(gè)精心完成的異常行為王國:“如此規(guī)訓(xùn)生產(chǎn)出順從的熟練的身體”,“馴服的”身體。
韋格納上文引號(hào)中的文字,都出自福柯的《規(guī)訓(xùn)與懲罰》。規(guī)訓(xùn)的空間由是觀之,該是福柯謂之“他種空間”的一種資本主義權(quán)力壓迫的空間范式;更具體地說,這是他不厭其詳規(guī)定出的六條原則的“異托邦”的另一種存在形式。誠如烏托邦可以走向它的反面——反烏托邦,異托邦同樣也走向它的真實(shí)存在過的反異托邦。規(guī)訓(xùn)與懲罰的空間,不過是不算姍姍來遲的一個(gè)重要例子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