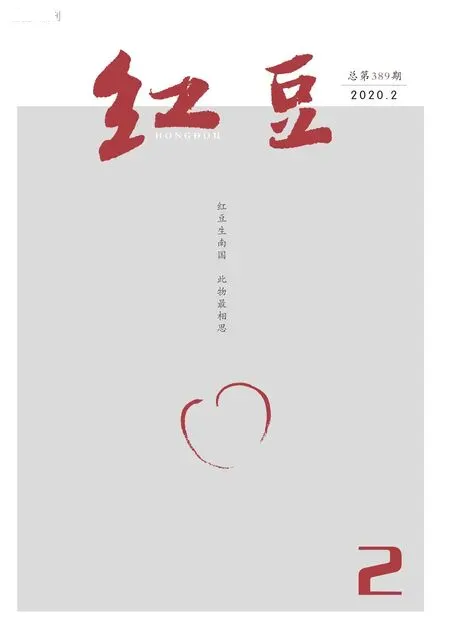我與《紅豆》的故事
莫華杰
我的文學(xué)處女作是在《紅豆》雜志發(fā)表的。這是人生成長的一個(gè)烙印,無論時(shí)間過了多久,每當(dāng)我回憶起二〇一一年的夏天,總有一種歷久彌新的溫暖,使我加倍珍惜如今寫作的日子。
二〇一一年的夏天陽光明媚,點(diǎn)燃了我當(dāng)初的創(chuàng)作激情。我是從這年開始創(chuàng)作純文學(xué)作品的。在此之前,我只是一個(gè)文學(xué)愛好者,參加一些報(bào)紙副刊的征文比賽,并投一些小短文到《大鵬灣》《南葉》《西江月》等打工文學(xué)雜志,以一種自娛自樂的心態(tài),盲目地走在文學(xué)這條小路上——因?yàn)槲疑形凑业酵ㄍ膶W(xué)的康莊大道,直到《紅豆》的出現(xiàn)。
那年夏天,嶺南的天氣跟往年一樣悶熱不堪,我卻以清爽的心情迎接三伏天的到來。夏季來了,改稿會(huì)也就來了,我們得到內(nèi)部消息,將邀請(qǐng)《芙蓉》《紅豆》刊物的編輯來指導(dǎo)會(huì)員寫作。從這一年開始,我所在的長安鎮(zhèn)依靠《長安文學(xué)》內(nèi)刊為陣地,舉辦四季改稿會(huì),請(qǐng)各大刊物的編輯老師來指導(dǎo)會(huì)員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在夏季改稿會(huì),我提交了一篇名為《仿佛有鬼》的中篇小說。在著名作家陳啟文先生的推薦下,《紅豆》編輯韋毓泉老師看中了那篇小說,但是韋老師覺得故事冗長了些,需要修改為短篇。我根據(jù)韋老師提出的寶貴意見,修改了內(nèi)容,調(diào)整了故事,并將標(biāo)題改為《兔子吃蘿卜》,很快就在《紅豆》二〇一一年第十二期發(fā)表出來。
當(dāng)時(shí)的我格外激動(dòng),《紅豆》畢竟是純文學(xué)刊物,也是廣西的老牌名刊,一個(gè)新人能登上這樣的舞臺(tái),那是很榮耀的事情。我期待那一期的《紅豆》快點(diǎn)寄到我手中,以便好好珍藏。第一次在純文學(xué)刊物上亮相,這是我邁入文壇的第一步,意義重大。我甚至恨不得搭輛車子到《紅豆》編輯部去取樣刊,順便拜謝《紅豆》編輯老師們。
偏偏造化弄人,越是期盼越是落空,稿費(fèi)我收到了,就是沒有收到樣刊。我特意打電話去問責(zé)編黃平老師,他又重新給我寄了一次樣刊。然而奇怪的事情又發(fā)生了,居然還是未收到。那時(shí)我在工廠上班,工廠搬遷過兩次,出租房又沒有信箱,寄丟了樣刊也不足為奇,因此也不好意思再找黃平老師要樣刊了。
就這樣,在我高興之余,留下了第一次發(fā)表卻無樣刊的遺憾。為了彌補(bǔ)這個(gè)遺憾,我曾想在各大舊書網(wǎng)上購買那期《紅豆》,卻不曾買到。看來老天爺是有意要讓我留下這個(gè)遺憾,讓我惦念一輩子吧。
近年來,《紅豆》特邀編輯張凱老師多次向我約稿,并介紹我認(rèn)識(shí)其他刊物的編輯,將我的作品推薦出去。我的一篇短篇小說和一篇長達(dá)兩萬五千字的散文又相繼在《紅豆》發(fā)表,都收到了樣刊,倒沒有留下什么遺憾。
《紅豆》對(duì)新人一向是很提攜的,在我所認(rèn)識(shí)的朋友當(dāng)中,尤其是東莞的優(yōu)秀作家,幾乎都在《紅豆》上亮過相。我的朋友圈里面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壇老前輩,在許多大刊發(fā)作品和開專欄,但那些大刊出每期目錄,他都很少點(diǎn)贊,唯獨(dú)《紅豆》每次出目錄,或者有什么作品被選刊轉(zhuǎn)載了,他都要在韋毓泉和張凱兩位老師的朋友圈里點(diǎn)贊。一次我與該前輩喝酒,問及此事,前輩說:“我之所以關(guān)注《紅豆》,給《紅豆》點(diǎn)贊,并不是因?yàn)椤都t豆》發(fā)表我的作品,也不是因?yàn)椤都t豆》辦得好,而是因?yàn)椤都t豆》的編輯老師們都是真性情人。在如今繁雜的文壇,編輯能有辦刊的熱血情懷,能保持人與人的真善美,是很難得的,所以必須點(diǎn)贊。”
前輩的話說出了我們的心聲。《紅豆》的編輯老師除了挖掘好稿、培養(yǎng)文學(xué)青年,還十分愿意與作者成為好朋友。他們不會(huì)因?yàn)樽约菏强锞庉嫞莆罩寮纳鷼⒋髾?quán),而變得不通人情。在《紅豆》的編輯老師看來,文脈薪火相傳,應(yīng)該給予作者溫暖的情懷,讓作者更有寫作的動(dòng)力,而不是讓文學(xué)淪落為一種謀生或出名的工具。
當(dāng)然,即便與《紅豆》的編輯成為朋友,并不意味著在《紅豆》上稿就容易了,相反,條件更嚴(yán)格了。因?yàn)榕笥芽梢詿o話不說,可以坦然地指出作品的不足之處,沒有那么多顧慮。我后來在《紅豆》上發(fā)表短篇小說和散文,編輯經(jīng)常打電話過來跟我交流修改意見,每次都是一兩個(gè)小時(shí),甚至為一小段情節(jié)反復(fù)溝通。也正是這樣,我的作品上了《紅豆》,打磨得愈是飽滿了。張凱老師不僅僅在作者的作品上給予指導(dǎo),他還利用他的人脈資源為長安的作者積極聯(lián)系,讓我們感到《紅豆》人真夠朋友。
從二〇一一年到二〇二一年,十年光陰彈指而過,這些往事仍像昨日一樣歷歷在目。帶有感情的回憶,時(shí)間也就有了溫度,讓我們愈發(fā)珍惜那些過往。阿來老師曾經(jīng)在創(chuàng)作談上說,小說的深度不是思想的深度,而是情感的深度。辦刊也一樣,唯有將情感滲透,與作者的命運(yùn)相連,才能讓作者釋放出靈魂的光彩。
《紅豆》是有感情的刊物,給作者溫暖與美好。我們總是會(huì)想起《相思》中的“紅豆生南國,春來發(fā)幾枝。愿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幾句詩。我們對(duì)《紅豆》除了相思,還有相交、相知、相愛和相守。
感恩相遇,祝《紅豆》越辦越好!
責(zé)任編輯? ?符支宏
特邀編輯? ?張?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