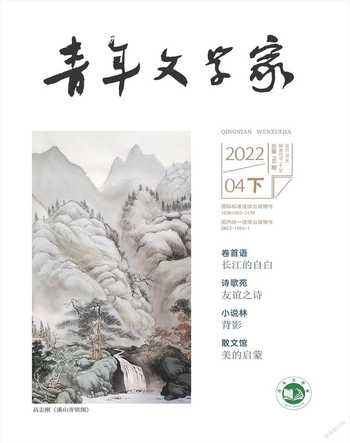淺論《詩經》中的愛情
紀聰聰 孫玉芹 杜甜宇 蔣墨涵 孟慶昉

愛情的表達可以說是《詩經》的精髓所在。歷代對愛情的歌頌層出不窮,《詩經》更是中國愛情詩篇的奠基者,其中的愛情詩燦若星河,有遙望窈窕佳人,苦苦相求的愛情;有執手相濡以沫,共盼白首的愛情;有倚欄望月寄情,翹盼相逢的愛情……他們的感情熱烈、充沛而純粹,不加任何雕飾,所書即所詠,所詠即所感,一字一句皆浸透了情。這些情穿越千年依然真摯感人,當古老的愛情故事與現代的愛情空間碰撞,其中或相似或相異,總令人情不自禁地心生向往。現代的某些因素如紙醉金迷、燈紅酒綠,多多少少摻進了愛情里,沉淀成了雜質,可《詩經》里的愛情回蕩了幾千年,雖在紙上卻在心底,雋永、深邃、真摯,幾千年后人們試圖從中繼續探求愛情的秘密,傳承那亙古如一的真情。本文試圖從《詩經》中的愛情詩出發探索古今的愛情秘籍。
作為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無出其右,是中國詩歌的源頭。孔子評價:“《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其評相當精準,其中詩篇并非陽春白雪,反而是下里巴人,以最質樸、最誠摯、最真誠的語言表達最真實的情感,那種專屬于那個時代及那個時代下人民的古樸熱誠的精神力量,令人不禁如癡如醉。《詩經》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的詩歌,共311篇,其中愛情詩幾乎占了其總詩篇數的1/5,主要收錄在風、雅、頌的“風”中。作為周王朝組織的大規模民間收集詩歌活動收集而來并整合而成的《國風》,可謂代表了各階層的思想與感情,其中的愛情詩不僅具有強烈的現實性,且樸實而生動,仿佛一字一句都穿越千年的長河而風塵不染,并且能夠直抵我們內心深處最真切的情愫,撩撥我們的心弦,令我們的心似被窺探般慌亂。
《詩經》中的愛情詩并非僅僅干枯地訴說情衷,毫無波瀾,其中的愛情故事起承轉合,跌宕起伏,有小心翼翼的暗戀,有驚心動魄的苦戀,有鸞鳳和鳴的相戀,有望穿秋水的思戀,有痛徹心扉的失戀……在這里,有些愛情故事,許是我們曾經歷過的,于是勾起萬千思緒,再與千年前的古人通過一紙漢文、寥寥數語互訴衷腸、秉燭夜談,一見如故;也有我們所不曾歷經的,于是掀起千萬心潮,再與不曾謀面的戀者通過一吟輕嘆、點點情愫探其愛的苦甜咸淡、感同身受。究竟是文字的力量還是愛情的倔強,其實不必深究,更不必細分,于我們而言,情之所起,情之所鐘,一往情深,千百年來其實都是同樣的追求,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離罷了。
現代的天空再不如以往那般清澈空靈,給人的心也多少蒙上了些許雜質塵灰,現代的愛情也被連帶著蒙了些灰。但是總歸不乏向往愛情的人,古今都是一輪月,共寄相思。無論什么樣的光怪陸離、雪月風花迷人眼,總在碰觸到那一卷頁邊泛黃,翻開來還散發著幽幽書墨香的《詩經》時,輕誦其中的愛情詩篇時,感受那背后的愛情故事時,這世界的喧囂就會戛然而止,只留心扉的愛恨嗔癡蕩漾難平,對于愛情的渴望,古今也難異。我們總得相信,再騷亂的外在,都在尋覓著屬于自己的那一份真正的愛。
跟著《詩經》穿堂入庭,探一探這貫穿千古的愛與情,試問愛中意,誰能解情愁?
一、求而不得者
《詩經》的“求而不得”這一類愛情又可以細劃分為兩類:
一類是單相思,“心悅君兮君不知”的愛戀。《詩經》首篇《關雎》,傳頌千年而余音繞梁,便是這樣一類愛情的典型代表。《詩經》以《關雎》開篇,仿佛是愛情以動心開卷。君子遇淑女前,或許對一見鐘情也是嗤之以鼻的,畢竟這樣的愛情顯得輕佻而廉價,好像注定灌了一半以上的“新鮮感”的水分,愛情并不濃稠,又如何求得甜蜜得如膠似漆呢?“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愛情里最大的驚喜就是變故,一朝一夕一瞬,顛覆你對愛情所有的認知。也只一眼而已,君子已淪陷,這一生恐怕都無法想象,自己有一天竟然會羨慕那荇菜,但求淑女一留,得愛人的片刻溫存。吳玲道:“孔老夫子崇尚‘中庸’之德,而《關雎》正是一篇典范之作。一首《關雎》,將愛情最本真的面貌描繪得淋漓盡致,簡單干脆,沒有半點拖泥帶水。”的確,愛情是最蠻不講理的,她任性而偏執,只洲島一遇,驚鴻一瞥,便甘愿受了愛情的枷鎖,日夜輾轉又反側,心里夢里皆是卿,惟愿卿常樂。這一首單戀之歌終是無果了,求而不得,最是煎熬,但是愛情開了卷,波濤滾滾,一發不可收拾,此生惟卿不可。這千年前的愛戀,現在讀來竟仍然令人心動不已,個中情感,讓人錯以為自己便是那心生暗戀難以自拔的君子,其中的沖動、癡迷、渴望、期盼、熱烈,如自己親身經歷一般。《漢廣》《簡兮》《干旄》等多篇都是如此般的單相思。
反觀現代,是否依舊有如此一塵不染的純凈暗戀?是否依舊如此熱烈?是否依舊如此深刻?比起彼時那種質樸得不染一絲雜質的愛戀,現代自然也不乏熱烈的暗戀,但過于泛濫了些,一個人太容易動情,且不論這情之深淺與否,單就動情本身來說,多少摻雜了一些現代的灰塵,快節奏的社會,連愛情都安上了加速器,一眼便認定一生的人或許真是癡人說夢,現代人把“知人知面不知心”發揮到極致,沒有那種只剩下美麗與溫婉的淑女,又哪兒來一見就鐘了一生情的癡人呢?對一人求而不得,換一人再求即可,輾轉反側幾夜難眠,也不至于一生只一人。或許這樣的現代愛情多了些灑脫,多了些靈活,但比之千年前的愛情,總歸是少了些悸動,少了些風韻。
另一類是相戀受阻,寧死不愿屈的哀嘆式愛戀。拿《鄘風·柏舟》來看,這種愛情顯得可悲而可嘆,相戀難相守,心中之苦可見一斑,不僅苦于與戀人不得白首,更苦于親人不能解我情愁,苦苦相逼,愁上加愁。沒有親人支持和祝福的愛情,哪怕得到了白首相依,也終是少了一份幸福,算不得完滿。《柏舟》里的姑娘一嘆三詠,“之死矢靡它”又“之死矢靡慝”,至死也不愿放棄自己認定的愛情,可嘆母親阻撓,可悲母親不理解,可泣上蒼不作美,內心的嗔、骨里的怨無絲毫保留地表達出來,對自由愛情的向往與渴望如此熱烈,可古今最怕一個“孝”字,兩頭難作,可教苦情如何圓滿收場?《鄭風·將仲子》也如是一般,對封建愛情枷鎖的控訴響徹九霄,但問苦情苦的是癡人還是親人?
對比現代,自由作為這個年代的標志,不再是一種追求,而是一種本能。少了這世俗的羈絆,愛情顯得更加肆無忌憚。不必在乎別人的看法,愛情更多的是你情我愿即可,兩個人的愛情,他人不必過多干涉,自由占了上風。這是這個年代之幸,也是愛情之幸,不必哀嘆親人阻撓或老天不公,大膽而奔放地追求自己認定的愛情。但是我們雖享受著自由戀愛的舒暢,卻在這詩中品出更強烈的共通感,痛苦不減千年前。自由雖不再是奢望,但阻撓卻相比千年前更為復雜且坎坷了,物欲橫流的世界,牽絆早已不是親人的不理解,更多縈繞著利益、虛榮的酸臭味。
二、求而即得者
《詩經》中這一類詩歌可謂是甜而不膩。以《邶風·靜女》為例來談,開篇便是癡情小生等候愛戀之人的焦急,這焦急之后卻藏了滿滿要溢出來的甜蜜,那種迫不及待、急不可耐的焦灼感躍然紙上。等待堪堪勾起戀人間的回憶,手中的定情信物惟恐不能鑲進心里。“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多么可愛而又單純的愛戀,清新而傾心。終于待到姑娘歸來,其中欣喜透過這張紙,從每個字中都浸出蜜來。這姑娘豪放而曠達,幾字而已,其形其情躍然紙上,“自牧歸(kuì)荑(tí),洵美且異”,這活潑、機靈的姑娘就立于我們面前,不同于中國傳統姑娘的溫婉羞澀,這樣的率真不造作更令人傾心。曲黎敏道:“在曠野牧場上成長的女人就不同了,她們率真,有著游牧民族的熱情與狂放。她們在愛情和婚戀上主動、熱情、質樸、少算計。她們在追求幸福方面更通透。生命的脆弱與堅強,在草原上,比在農桑園里,表現得更為明顯,那種對生命的憐愛與珍惜的態度,就是草原文化的獨特之處。”擁有這樣一個草原姑娘,怎么會不幸福呢?這種兩情相悅的歡喜,還有《野死有麕》《桑中》等數篇。這一份相戀的甜蜜,我們讀來亦感羨慕,對愛情又多了幾分心馳神往。
再觀現代,這樣的愛情其實并不少見,青春的悸動,羞澀的告白,臉紅心跳的牽手,操場的余暉,拉長的背影相依相偎。原來古今的相戀都有這般沁人心脾的甜蜜。只是難說今人的這份甜蜜保質期有多久,短暫的甜蜜,一次又一次的心動,愛情泛濫了最終只會麻木,我們難以忘卻的,終是最初的那份。初戀何以難以忘懷,不過是因為最初的我們把最純潔、最真誠、最肆無忌憚的愛給予了對方,可現代的初戀自然不似幾千年前《詩經》里的初戀,有走到白頭、至死方休的甜蜜,現代更多的是初戀帶走了我們一切的純潔與美好,連同那些甜蜜一起,半分未曾留下,不復當初。千年前都是最簡單的愛情,千年后卻失了本真,愛情從來不需要華麗的裝飾,一花一草,經彼之手而贈,即為珍寶。
三、得而離別者
《詩經》中的這一類愛情,就味苦了些。得而離別也可以細分為兩類: 一類是情在人不在,這種相離更顯情深。拿《鄭風·出其東門》為引,城東門外美女如云,可都非心上人,既非心上人,如云美色真如云。一生只鐘情于一人,其余皆是過客。但此時心里卻更添思念吧?千萬人潮,車馬喧囂,卻獨獨沒有心系之人的身影,我們似乎更能從這首詩中感到熱烈的思念。欲望是人之常情,可也如毒藥,是愛情的毒,是放縱的藥,這首詩所體現的堅貞也好,思念也罷,確實難能可貴,理學家朱熹也贊道:“是時淫風大行,而其間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謂能自好而不為習俗所移矣。”愛情所求,不過是一生只一人罷了,很多人認為這首詩是述癡情男子對美女不為所動,只愛家中糟糠之妻。其實我私感非也。“美”是一個很主觀的形容詞,“情人眼里出西施”即解。愛情如同戴著有色眼鏡,從來都是不公平的,我有我的心之所向,你有你的心之所屬,我愛到骨子里的人,別人就不再入眼。曲黎敏亦道:“總之,愛,溫暖;欲,奪命;情,多變。人,渴望愛,懼怕欲,煩惱情。把‘心’放對了位置,人的生命就穩定。這首詩里的年輕人就很清楚,世上美女縱有千萬個,而我只愛那一個,她樸素大方又美麗,最關鍵是她懂我心意。”
再觀現代,這個問題其實更為犀利一些。現代的繁華與喧囂,迷了多少人的雙眼,愛情淪為游戲,實在令人唏噓不已。現代人多了一些欲望,多了一些貪婪,穩不了的心,又如何定得了情呢?古今一對比,自知真情可貴。現在的人,多將真情遺落在風月里,真情被分成了很多份,分不過來,也來不及細分,真正完全的鐘情,怕是鳳毛麟角,彌足珍貴。
另一類是人在情終了,這種相離最是傷情。以最著名也是我們最熟悉的怨婦詩《衛風·氓》來看,失戀之苦,彼時最是疼痛,傷了一生,痛了一世。一開始的甜蜜就暗潮洶涌。甜蜜糊住眼,步入婚姻后,卻親眼看著愛人將曾經的愛情埋葬,終究是負了情,負了心,一腔衷情錯付卿。讀來令人淚沾襟,慨嘆愛情的無常與絕情。誰對誰錯終究也是纏綿不清,分離就成了最好的祝福。可女人的離開卻是另一場苦痛的開場,被遺棄的女人,怎能得正眼相待,哪里還配再覓良人呢?身體涼了可以捂熱,可心涼了卻無可奈何。沒有什么能填滿人生的“虛無”,婚姻做不到,愛情也做不到,終其一生,人最終還是要謀求自身的完整和成就。
來觀現代,這種涼心的愛情其實更為常見。2019年,我國綜合平均離婚率為30%左右,個別省份能達到60%,婚姻真的成為愛情的墳墓。其實婚姻與愛情本身并無糾葛,與其說是婚姻葬送了愛情,不如說是愛情的自殺。是否在現代的燈紅酒綠中,更多的人越來越迷茫?對于愛情,難覓良人,可現代人連自己都很難看清。其實并非我們非得向往千年前的那些愛情,暗戀也好,相戀也是,失戀也罷,古今所求,都不過是一生只求一人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