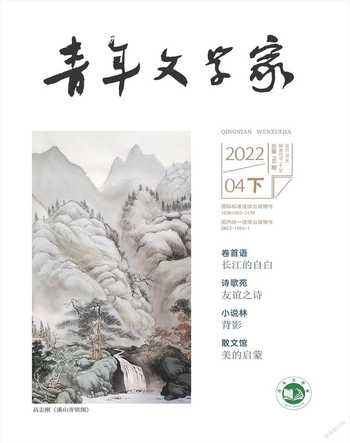論巴金小說(shuō)中的“家庭”書寫
李亞文

“家庭”是巴金小說(shuō)中的一個(gè)重要意象,既是主人公的生活場(chǎng)景,也是主人公的生活方式,亦是人生理想的曲折表達(dá)。“家庭”意象貫穿于巴金的《家》《憩園》與《寒夜》中。作為一個(gè)封建大家庭出身的知識(shí)分子,巴金對(duì)于“家庭”的書寫始終是矛盾的,既存在著眷戀“家庭”的情感,又存在著渴望離開“家庭”的愿望。從三十年代的《家》到四十年代的《憩園》與《寒夜》,從走向崩潰的封建大家庭到以離散收?qǐng)龅男率街R(shí)分子組成的小家庭,“家庭”書寫的背后寄寓著巴金對(duì)理想的生命狀態(tài)的渴慕以及對(duì)現(xiàn)代文明的追求。
一、“家”的不易
無(wú)論是在《家》,還是在《憩園》與《寒夜》中,痛苦始終是一個(gè)無(wú)法回避的話題。在這三部小說(shuō)中,我們看到了三種不同的家庭模式,而這三種不同的家庭模式背后又有其各自難解的問(wèn)題和尷尬的境遇。
(一)大家長(zhǎng)制下的壓迫
《家》作為巴金的早期作品,有較為顯在的個(gè)人經(jīng)驗(yàn)折射。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的巴金,自幼就深感封建家族制對(duì)人性的壓迫,并渴望戰(zhàn)勝這股黑暗的勢(shì)力。
在《家》中,年輕人舉步維艱、處處受限。長(zhǎng)子覺新中學(xué)畢業(yè)后便聽從了父親的命令,與瑞玨成婚,在此之前,他也曾做過(guò)才子佳人的好夢(mèng),但是面對(duì)父親的威嚴(yán),加上其性格本身的軟弱,他不得不放棄繼續(xù)學(xué)業(yè)、放棄與梅表妹成婚的幻想。覺新性格中的怯懦、妥協(xié)是悲劇的基石,但是一味地順從并沒有換來(lái)美好的生活。雖然新婚是甜蜜的,但父親因時(shí)疫過(guò)世后,整個(gè)家族的重?fù)?dān)一下子落在了長(zhǎng)子覺新的身上,壓得他無(wú)法喘息。在兩個(gè)弟弟的眼中,他是“作揖主義”的擁護(hù)者。在家族中,他不僅得不到弟弟們的理解,還深陷于長(zhǎng)輩的紛爭(zhēng)中,唯一理解他的只有妻子瑞玨,但他的妻子最終也淪為了大家族和禮教的犧牲品,于生產(chǎn)之時(shí)命喪城外。最終醒悟過(guò)來(lái)的覺新,意識(shí)到奪去妻子生命的是整個(gè)家族、整個(gè)禮教、整個(gè)制度,但他仍無(wú)力掙脫這些束縛,只能將希望寄托在三弟覺慧身上,幫助他離開了“家”,自己仍留在“家”中掙扎。
(二)新式小家庭對(duì)人性的壓抑
《憩園》與《寒夜》同為巴金二十世紀(jì)四十年代的作品,雖然延續(xù)了巴金對(duì)“家庭”的書寫,但不同于早期作品中將筆觸指向大家族,人到中年的巴金更多地將筆觸深入到知識(shí)分子的小家庭內(nèi)部,家庭中的成員面對(duì)的壓力更多來(lái)自于理想破碎后的內(nèi)心苦悶。由于現(xiàn)代思想與現(xiàn)實(shí)的錯(cuò)位,《憩園》與《寒夜》中的主要人物不得不放下追尋理想人生的腳步,轉(zhuǎn)而直面殘酷的現(xiàn)實(shí)生活,這無(wú)疑加劇了他們的心理扭曲度。在較之《憩園》社會(huì)背景更為復(fù)雜的《寒夜》中,主人公面對(duì)的打擊已經(jīng)不僅僅來(lái)自于小家庭中的重重阻力,更多則來(lái)自于夫妻共同理想破碎后對(duì)人性的考驗(yàn)。
《憩園》中的姚先生和姚太太均為新式知識(shí)分子,尤其是姚太太,她是一位知書達(dá)禮且心思細(xì)膩的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的是一個(gè)近乎完美女主人的角色。她與姚先生通過(guò)介紹成為夫妻后,感情十分要好。但是,作為小虎繼母的她,在家庭中時(shí)常處于一種“失語(yǔ)”的狀態(tài)。盡管她與丈夫感情深厚,但在教育繼子小虎的問(wèn)題上,他們始終無(wú)法達(dá)成共識(shí)。她有心規(guī)勸小虎向?qū)W,卻被小虎的外婆刁難,也得不到丈夫的理解。因此,姚太太的內(nèi)心世界總是苦悶的,有著無(wú)法抵擋的失落和失望,她只能通過(guò)閱讀文學(xué)作品來(lái)寄托內(nèi)心復(fù)雜的感受,渴望在書中尋求到人世間的同情、善良與安慰。
《寒夜》中的汪文宣與曾樹生這對(duì)夫妻,因懷著共同的教育理想而走到了一起,但面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殘酷,他們不得不放棄共同的理想。為維持生計(jì),汪文宣拖著病體每日機(jī)械地重復(fù)著校對(duì)工作,為不和諧的人際關(guān)系和極低的經(jīng)濟(jì)收入而困擾,而曾樹生則是大川銀行的一個(gè)小職員,在上司陳主任的幫助下?lián)鹆思彝ブ薪?jīng)濟(jì)的重?fù)?dān)。小說(shuō)最后,曾樹生選擇與陳主任遠(yuǎn)走蘭州后又回到了重慶,而這時(shí)汪文宣早已在絕望中病逝,兩人的家庭徹底破碎瓦解。
如果說(shuō)《憩園》中的家庭是以女主人姚太太的委曲求全得以維系的話,那么《寒夜》則徹底打碎了這個(gè)家庭圖景。曾樹生是一位思想較姚太太更為進(jìn)步的女性,她既有勇敢追求愛情的勇氣,與汪文宣通過(guò)自由戀愛走到了一起,又有反抗老舊思想的意識(shí),她不認(rèn)可婆婆對(duì)她為維持生計(jì)在外“拋頭露面”的指責(zé),并多次頂撞婆婆,用自己的實(shí)際行動(dòng)表達(dá)對(duì)婆婆這種老舊思想的不滿。在與汪文宣的共同理想破碎后,她雖然同情體弱多病的汪文宣,但因家里的氣氛太過(guò)窒息,為了追求自己未來(lái)的幸福,她毅然決然選擇了離家。
二、“家”的離散
從《家》到《憩園》《寒夜》,我們見證了三個(gè)家庭不同形式的離散,多種人生命運(yùn)的交錯(cuò),集中凸顯了“家庭”這一個(gè)時(shí)空生命單位的復(fù)雜內(nèi)涵。《家》體現(xiàn)出的是舊式家庭中的尊卑觀念、長(zhǎng)幼秩序、家長(zhǎng)威權(quán)、人物的傾軋等問(wèn)題,在《憩園》與《寒夜》中,也并未得到很好的解決。雖然《家》中覺慧的出走是對(duì)大家長(zhǎng)制的有力反抗,但是出走的覺慧是否就擺脫了家庭的困境呢?巴金在《憩園》與《寒夜》中都給出了答案。從《家》到《憩園》與《寒夜》,小說(shuō)中主人公的人生歷程起起伏伏,家庭的紛擾與桎梏并沒有遠(yuǎn)去。
(一)家庭結(jié)構(gòu)的病態(tài)
如前文所言,高家的最高統(tǒng)治者—高老太爺,手握家中人的命運(yùn),把控大小事的走向,也因此釀成了許多悲劇。《家》中的家庭結(jié)構(gòu)是壓迫型的,這種家庭結(jié)構(gòu)使得青年人長(zhǎng)期處于被壓迫的狀態(tài)中,而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提倡民主與科學(xué),這使得家中的青年人們鼓起勇氣來(lái)反抗這不公平的家庭模式。而到《憩園》中,我們看到,新式知識(shí)分子組成的家庭里,也存在著類似的問(wèn)題。在姚先生與姚太太看似平等的夫妻關(guān)系中,依然存在著一方對(duì)另一方的壓制,即使是受過(guò)新式教育的姚太太也無(wú)法幸免。姚太太在憩園中安逸舒適的生活背后,其實(shí)是犧牲自己理想世界的體現(xiàn),姚太太“安居”的選擇背后折射出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對(duì)女性“三從四德”的要求。而在對(duì)繼子小虎的教育問(wèn)題上,姚太太雖屢次勸諫丈夫,但都無(wú)用,反而使得夫妻關(guān)系岌岌可危。我們看到,即使是如姚太太般心懷大愛的知識(shí)女性被禮教制度困于家庭之中時(shí),話語(yǔ)權(quán)也會(huì)逐漸減弱,直到最終失去聲音。同樣,在《寒夜》中,曾樹生也是一個(gè)被家庭束縛住的女性,強(qiáng)勢(shì)的婆婆、懦弱無(wú)能的丈夫、沉默寡言的兒子,使她回到家庭中便感到壓抑與窒息,她是矛盾的。在這樣的家庭壓迫下,曾樹生做出了與姚太太相反的選擇,逃離家庭,與銀行上司陳主任奔赴蘭州。但逃離家庭并不意味著獨(dú)立,她與汪文宣因懷有共同理想組建了家庭,也因共同理想的破滅漸行漸遠(yuǎn),在家庭中,她的經(jīng)濟(jì)能力確實(shí)強(qiáng)于丈夫,但她的成就完全是建立在家庭外另一個(gè)男性的幫扶之下,甚至連逃離家庭也是在陳主任的安排下才得以完成,這種骨子里的依附意識(shí)使她永遠(yuǎn)無(wú)法成為一個(gè)獨(dú)立的個(gè)體。曾樹生作為一個(gè)理想破滅的知識(shí)分子,既有現(xiàn)代女性追求自我的沖動(dòng),渴望獲得理解和自由,渴望遠(yuǎn)離世俗的眼光,同時(shí)又有老舊思想的羈絆,在留下和離開之間搖擺不定,她既難以割舍自己與小家之間的聯(lián)系,又無(wú)法忍受小家對(duì)自己身心的禁錮。她出逃家庭背后的種種復(fù)雜的內(nèi)心感受與行為表現(xiàn)折射出了女性在面對(duì)家庭禁錮時(shí)的兩難境地。
(二)社會(huì)變革的不徹底性
從《家》到《憩園》《寒夜》,小說(shuō)中時(shí)空跨度由二十世紀(jì)二十年代初期延展到四十年代中期,社會(huì)的話語(yǔ)主題也由個(gè)體啟蒙擴(kuò)展到救亡圖存。在《家》中,以覺慧為代表的青年人深受五四精神的影響,渴望走出家庭,渴望反叛大家長(zhǎng)制,但同時(shí)也陷入種種矛盾與糾結(jié)中:他們生活于地主階級(jí)家庭中,對(duì)大家長(zhǎng)制度的反叛同時(shí)也是對(duì)他們從小到大生長(zhǎng)環(huán)境的否定,而這種與原生家庭的完全割裂對(duì)于新青年們來(lái)說(shuō)是極度困難的,因此在《家》這部作品中,我們看到覺新被困在大家族中,成為無(wú)抵抗主義的代表,而覺慧,雖然他看似比覺新激進(jìn)和進(jìn)步,但實(shí)際上他也是一位具有延宕性的人物。覺慧在面對(duì)鳴鳳之死時(shí)的自我剖析揭露了新青年在面對(duì)舊傳統(tǒng)時(shí)左右搖擺的兩難困境,而這種困境一方面來(lái)自于青年本身對(duì)舊式家庭的復(fù)雜情感,另一方面來(lái)源于社會(huì)變革的不徹底性。《憩園》中的萬(wàn)昭華也曾渴望家之外的世界,卻被婚姻困于家庭之中,她既享受夫妻恩愛的安逸生活,也厭倦被困在家庭中的寂寞感。當(dāng)女性解放程度尚未達(dá)到一個(gè)高度時(shí),以個(gè)人之力還無(wú)法擺脫如此角色定位。而在《寒夜》中汪文宣與曾樹生的家庭的解體背后,還有一個(gè)顯著的矛盾便是曾樹生與婆婆之間的關(guān)系。婆婆認(rèn)為兒媳曾樹生的所作所為不符合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對(duì)女性的要求,因此她處處為難兒媳,希望兒媳能夠成為傳統(tǒng)觀念中的好妻子、好母親。巴金通過(guò)對(duì)這兩個(gè)針鋒相對(duì)的女性角色的描寫,在傳統(tǒng)的婚姻方式和新式婚姻的沖突中隱射著社會(huì)變革環(huán)節(jié)中的疏忽,這些客觀存在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導(dǎo)致了曾與汪的小家庭一步步走向了不可挽回的深淵。
三、“家”所寄寓的復(fù)雜情感
巴金筆下的“家”是一個(gè)集合了壓抑與反叛、痛苦與愛戀、腐朽與新生的矛盾綜合體,這些矛盾的書寫很大一部分來(lái)源于他本人的人生經(jīng)歷。我們?cè)谒兰o(jì)四十年代的作品中讀到了巴金努力構(gòu)建知識(shí)分子新式家庭的愿望,但顯而易見,新式家庭的出現(xiàn)并未解決舊式家庭中的問(wèn)題,反而衍生出了新的問(wèn)題。巴金通過(guò)在作品中對(duì)各式家庭的建立,寄寓著自己對(duì)理想生命狀態(tài)的渴慕以及對(duì)現(xiàn)代文明的追求。
(一)對(duì)理想生命狀態(tài)的渴慕
從《家》中以覺新、覺慧為代表的青年們,到《憩園》中的姚太太,再到《寒夜》中的汪文宣與曾樹生,巴金提供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命范式。勇敢離家的覺慧和曾樹生固然有其局限性所在,但其追尋理想生命狀態(tài)的態(tài)度是值得敬佩的,他們一個(gè)沖破了大家長(zhǎng)制的牢籠,尋求光明的前途;一個(gè)叛逃傳統(tǒng)小家庭的束縛,嘗試另一種人生的可能性。同是作為家庭“叛逃者”的巴金,在書寫家庭中此類人物的過(guò)程中,寄寓著個(gè)人對(duì)理想生命狀態(tài)的渴慕。通過(guò)巴金的這三部作品,我們發(fā)現(xiàn)作家以人物對(duì)照的手法表露出了自己理想的生命狀態(tài):在《家》中將覺新的不抵抗主義與覺慧、覺民等人追求自由解放的精神進(jìn)行對(duì)照,在《憩園》中將姚先生的固執(zhí)、自負(fù)與姚太太的溫柔和細(xì)膩進(jìn)行對(duì)照,在《寒夜》中將汪文宣的死氣沉沉與曾樹生的鮮活靈動(dòng)進(jìn)行對(duì)照。通過(guò)這三組人物對(duì)照,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巴金理想的人生狀態(tài)包含著自由解放、平等博愛、個(gè)體獨(dú)立這三大要素,這是他深受五四啟蒙精神的結(jié)果,五四啟蒙精神強(qiáng)調(diào)反傳統(tǒng),追求個(gè)性解放、個(gè)性自由,而這正是巴金筆下部分新式人物所具備的特性,亦是他本人對(duì)理想生命狀態(tài)的認(rèn)知。
(二)對(duì)現(xiàn)代文明的追求
家庭是最小的社會(huì)單位,巴金通過(guò)書寫家庭中的人物、事件,以及上與下觀念的差異,折射出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中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水火不容的局面。家庭同時(shí)也是一個(gè)不同于其他場(chǎng)景的特殊場(chǎng)所,具有隱秘性、私人性的特點(diǎn),家庭中新舊文化碰撞的背后隱蔽著家中青年人最深處的痛苦、矛盾、尷尬的心理狀態(tài)。巴金通過(guò)書寫家庭中新舊文化的差異和沖突,一方面寄寓著個(gè)人對(duì)舊文化的鄙夷與厭棄,另一方面他筆下的主要人物卻又無(wú)法完全割舍自己與這類舊式文化的聯(lián)系:《家》中覺慧對(duì)待鳴鳳雖然有懵懂的愛情卻又始終未將鳴鳳看作一個(gè)獨(dú)立的個(gè)體;《憩園》中姚太太深知自己放棄了人生理想?yún)s又不做任何沖出憩園的努力;《寒夜》中汪文宣作為一個(gè)曾經(jīng)熱衷于教育事業(yè)的知識(shí)分子,卻又處處對(duì)強(qiáng)勢(shì)保守的母親言聽計(jì)從,而曾樹生雖然沖出了家庭的圍困,卻始終沖不出內(nèi)心的藩籬。在巴金書寫家庭的作品中,諸如此類的矛盾如此之多,通過(guò)書寫這類新與舊的沖突,書寫青年人在新與舊中的搖擺與猶豫的心理,實(shí)際上反映的是現(xiàn)代文明取代傳統(tǒng)文明過(guò)程中不得不經(jīng)歷的曲折與坎坷。
“家庭”書寫是巴金小說(shuō)的重要主題之一,通過(guò)家庭這個(gè)小窗口,我們看見了社會(huì)的變革、年輕人的成長(zhǎng)以及思想和精神的掙扎。“家庭”這個(gè)場(chǎng)所不但引發(fā)了青年人對(duì)家庭的全新解讀與定義、個(gè)體在家中的定位的新思考,也詮釋了接受五四思想熏陶的一代知識(shí)分子的思想取向和價(jià)值選擇。通過(guò)閱讀巴金小說(shuō)中的“家庭”書寫,我們得以跟隨巴金回顧幾代青年人對(duì)家的追問(wèn)、懷疑與反思,以及幾代知識(shí)分子重建精神之家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