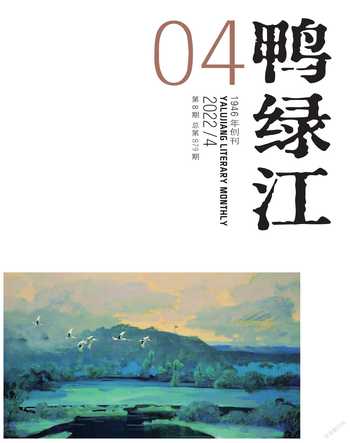清明節的思念
許是因為清明節,前天晚上夢見婆了。
婆去世的時候,我不到5歲。婆在我腦海中的零散記憶,無外乎我惹怒了婆,婆拿著掃帚,一邊蹣跚著一雙小腳攆我,一邊裝怒叫罵。看著婆攆我上氣不接下氣的模樣,我拍著手做著鬼臉故意氣婆:“來些,來些,來攆我啊!”每每巷子里的大爺大媽也來湊熱鬧,他們大笑著慫恿我喊我婆的名字。年少的我在他們的鼓勵下,站在糞堆上,雙手叉腰,大聲地喊著婆的名字。我的叫喊聲讓半條小巷沸騰了,笑聲、調侃聲一片。婆被我的陣勢逗笑了,一屁股坐在碾盤上,笑得上氣不接下氣。看到大人們笑,我更加得意忘形,在大爺大媽的教唆下,繼續挑釁:“來些,哈(壞)老婆,來攆我啊!”婆起身拍了拍土,對著身邊的大爺大媽笑罵:“一個個哈慫,光知道給我娃胡教!”又回過頭,忍住笑對著糞堆上手舞足蹈的我勸說:“我娃乖,再別聽你這些哈慫爺哈慫婆的話,趕緊下來,咱回家,婆給你燙醪糟!”
一聽到醪糟,我在糞堆上安分了許多,但又怕婆騙我,就和婆談了條件:不能騙我,不能回家打我,要給我燙一大碗醪糟。看到婆信誓旦旦,我才下了糞堆,心有余悸地向婆跟前靠攏,嘟著嘴邊磨蹭邊說:“婆,我要喝醪糟!我要喝醪糟!”
在一步之遙時,我被婆一把拽住,婆用笤帚在我屁股上輕輕拍打了兩下,問我:“以后還叫大人名字不?”為了喝醪糟,我回話(道歉)像打盹兒。
婆拽著我朝回走,身后響起一陣笑聲:“娃呀,以后想喝醪糟,就喊婆的名字!”
婆做的醪糟在小鎮很有名。聽媽說,我爺當年孤身一身從富平逃難過來,婆不顧家人反對,嫁給了一貧如洗的爺。為了在小鎮站住腳,爺給人打短工,婆支起了醪糟攤子。爸說,婆做醪糟選最好的米,做出的醪糟又香又甜。誰家媳婦坐月子,買幾斤婆做的醪糟胚子,定會奶水充足;誰家老人病了,喝一碗婆做的醪糟雞蛋,定會神清氣爽。巷子里誰家生孩子,誰家有病人,婆都會記在心里。端一碗醪糟送過去,送的不僅僅是溫暖,更多的是一份鄉情。每每有家境貧寒的人登門,婆都會慷慨贈送,看到對方千恩萬謝,婆總會揮揮手:“客氣啥,誰還沒有個難處?”
貨真價實、童叟無欺是婆醪糟攤子紅火的原因。每天起早貪黑,辛勤勞作,幾年后,爺和婆拆了小土房,蓋起了大瓦房。上梁那天,鄉黨們帶著湊錢買來的鞭炮、帶著镢頭鐵锨前來幫忙。看著燃放的鞭炮,看著一個個忙碌的身影,婆激動得又是倒水又是道謝。“謝啥呢,嬸,這只能說明我嬸的鄉行好啊!”大家伙異口同聲,身后一片爽朗的笑聲。
生活在黃土地上的莊稼人,點滴恩情都會銘記于心。他們能做的就是用淳樸的方式去感恩,用最質樸的語言去感謝。
和婆相處了短短5年,我沒見過婆紅紅火火的醪糟攤子,但我喝過婆做的醪糟。看著婆從黑瓦罐里舀出一勺如羊脂玉般的醪糟放在碗里,在開水的沖擊下,碗底的醪糟歡快地跳著芭蕾,瞬間漂浮在水面。不用放糖,稍稍放涼,只一口,就會甜進心底。那時候,雖說婆不賣醪糟了,但隔三岔五總有人上門求教,婆會和盤托出自己多年做醪糟的經驗。有人打趣,這個瓜老婆,把自己祖傳的秘方都賣了!婆聽了大笑:“又不是啥值錢的東西,難道還要把這醪糟方子背到陰司去?”
和婆唯一的一張合影是我扎著沖天辮,噘著小嘴,一臉不高興。記得那天,婆帶著我和表哥去縣城看望二姑,午飯后,我們一起去照相館。年幼無知的我,面對鏡頭,依舊自顧自地吃著麻餅。在攝影師的提醒下,婆費了很大的口舌才把麻餅從我的手中哄走。看著婆手里攥著的半塊麻餅,我氣得噘著嘴巴,任攝影師怎么逗都無濟于事。
時隔多年,那一幕幕往事仍然歷歷在目。
第二年冬天,婆去世了,爸把合影中的婆單獨洗了一張作為遺照。看著滿屋子忙碌的大人,我問表哥:“婆干啥去了?”表哥哭了:“婆死了。”我繼續問:“死了還能活過來嗎?”表哥默默地搖頭。看著淚流滿面的表哥,我使勁搖著他的胳膊哭喊:“我不要婆死,我不要婆死……”
一眨眼,幾十年過去了。
幾個月前,因為小鎮建新小區,爺和婆的墳再一次被遷。如今,爺和婆的骨灰被安置在幾里外的陵園里。前天回娘家,聽到巷子里幾個嬸子嘆氣:“陵園還是別去了,去了也不讓燒紙!”我接過話茬,笑道:“避免火災,現在都是文明祭奠呢。”
又是清明節,站在樓頂,遙望著陵園的方向,又想婆了。
雖然和婆僅僅相處短短幾年,記憶中也就零星幾個碎片,但那些場景時不時浮現在眼前,每每回味,如婆做的醪糟,又香又甜。
作者簡介:
王寧子,陜西省作家協會會員,《散文選刊》簽約作家,作品散見于各大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