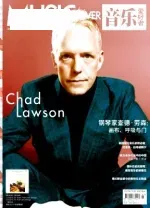守護(hù)美好
宋冉
作曲家蒂埃里·佩庫(kù)(Thierry Pecou,1965- )出生在法國(guó)巴黎附近的一個(gè)小鎮(zhèn),長(zhǎng)大后考入巴黎音樂學(xué)院鋼琴、管弦樂和作曲專業(yè)。成績(jī)優(yōu)異的他獲得了出國(guó)留學(xué)的機(jī)會(huì),先后前往加拿大、俄羅斯、西班牙等國(guó)家進(jìn)行交流學(xué)習(xí),世界各地的風(fēng)土人情激發(fā)了他的創(chuàng)作熱情,不同國(guó)家的文化成為他靈感的源泉。
佩庫(kù)十分關(guān)注自然、動(dòng)物及人文地理等方面的內(nèi)容,先后創(chuàng)作了許多與動(dòng)物相關(guān)的作品,如《無(wú)盡群鳥》(Loiseau innumerable)便是他從鳥類身上獲得靈感創(chuàng)作完成的,而以鯨魚為對(duì)象創(chuàng)作的《關(guān)于物種消失的冥想》(Meditation sur la fin de lespece)則使聽眾置身于廣闊寂靜的海洋中。

許是法國(guó)人天性熱愛自然。在浪漫主義時(shí)期,作曲家圣-桑就創(chuàng)作了著名的《動(dòng)物狂歡節(jié)》,二十世紀(jì)的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創(chuàng)作過交響素描《海》,拉威爾、梅西安等也都或多或少地從自然中獲得靈感,轉(zhuǎn)而進(jìn)行音樂創(chuàng)作。聚焦二十一世紀(jì),作曲家佩庫(kù)延續(xù)了這一傳統(tǒng),創(chuàng)作了多部與自然主題相關(guān)的作品。
從史詩(shī)故事到歌劇
《大地母親:閃閃發(fā)光的世界》(Nahasdzáán in the Glittering World)是一部為自然、動(dòng)物與人文主題而作的室內(nèi)歌劇,由美國(guó)詩(shī)人勞拉·托伊(Laura Tohe,1952— )撰寫劇本,佩庫(kù)作曲。2019年4月23日,該劇于諾曼底魯昂歌劇院完成首演,獲得評(píng)論家和觀眾的廣泛贊揚(yáng)。
該作取材于納瓦霍族的神話故事,以此映射現(xiàn)實(shí)世界中岌岌可危的自然環(huán)境,通過多變的音響效果表現(xiàn)納瓦霍族治療儀式的力量和美感。標(biāo)題中的“Nahasdzáán”一詞在納瓦霍語(yǔ)中是“大地母親”的意思,“閃閃發(fā)光的世界”隱喻的正是我們目前生活的世界。
作品建立在納瓦霍神話傳說之上,由四幕組成,每一幕代表一個(gè)新世界,故事從無(wú)盡黑暗開始,經(jīng)歷了艱難向前、憧憬美好,最后踏上對(duì)抗巨獸的征程。與傳說不同的是,作曲家在最后加入了動(dòng)物的交談組曲,借動(dòng)物之口“談?wù)摗笔澜绲默F(xiàn)狀。故事中共有九個(gè)角色,分別是首次出現(xiàn)在黑色世界的第一個(gè)男人和土狼,藍(lán)色世界里的第一個(gè)女人,黃色世界里的蜘蛛女,白色世界里的雙胞胎兄弟和祖母,烏鴉和老鷹。
第一幕為黑色世界,第一個(gè)男人(男低音)在這一幕中以旁白的身份講述了黑色世界的現(xiàn)狀,他說:“我們像霧一樣漂浮在地球和天空之間。”在第一幕結(jié)尾時(shí),土狼(男高音)以獨(dú)白的形式暗示黑色世界已經(jīng)出現(xiàn)裂痕,隨即需要逃往另一個(gè)世界——藍(lán)色世界。
第二幕為藍(lán)色世界,開篇即第一個(gè)男人的獨(dú)唱,以第一人稱的視角講述到達(dá)新世界的感受,以及透露生活表面美好、實(shí)際丑陋不堪的現(xiàn)實(shí)。伴隨著由電聲鋼琴?gòu)椬嗟念愃歧娐暤囊魳罚谝粋€(gè)女人出場(chǎng)并說道:“我們必須繼續(xù)前進(jìn),我們必須逃離這個(gè)世界。”
在逃到第三幕黃色世界后,蜘蛛女出場(chǎng)。隨后暗示人們不能忘記本來應(yīng)該走的道路。在樂章結(jié)尾時(shí),土狼與蜘蛛女進(jìn)行了對(duì)話,預(yù)示了英雄的母親將要出現(xiàn),她會(huì)帶來優(yōu)美的歌曲、美好的祈禱、完整的地圖,還會(huì)帶來和平。此外,雙胞胎兄弟將會(huì)拯救世界,地球?qū)?huì)變得美好。這是土狼對(duì)于未來世界的預(yù)言。
在第四幕白色世界里,雙胞胎兄弟決定去拯救世界,他們想要尋找父親,從他那里得到武器,以消除世界上的怪物。他們?cè)趯ふ业穆飞嫌龅阶婺福婺钢敢怂麄兦斑M(jìn)的道路。故事到此戛然而止,最后是否走向光明不得而知。歌劇的最后是一段動(dòng)物間的對(duì)話,它們談?wù)撝咨澜绲默F(xiàn)狀,這一世界急切地需要被治療。

作品看似是在講述一個(gè)納瓦霍族的傳統(tǒng)神話故事,實(shí)際上是想通過神話影射目前我們生活的世界正在面臨的危機(jī)。作曲家試圖用納瓦霍族人的歌聲喚醒大眾,將故事作為現(xiàn)實(shí)世界的投影。歌劇的最后唱道:“讓我漫步在美好中吧。讓我們漫步,當(dāng)美好在我們面前。讓我們漫步,當(dāng)美好在我們身后。讓我們漫步,當(dāng)美好在我們頭頂。讓我們漫步,當(dāng)美好在我們之下。”這一內(nèi)容取自納瓦霍族的“夜頌”儀式中,作曲家也許是想通過向神明祈禱來治愈這個(gè)世界。作品的結(jié)尾提到:“生命就在美好中結(jié)束……生命就結(jié)束在美好中。”所以何為世界?世界本應(yīng)美好。
新型儀式性室內(nèi)歌劇
室內(nèi)歌劇(c h a m b e r opera)是佩庫(kù)對(duì)這部作品的定位,但實(shí)際上作品融合了小型管弦樂、聲樂、念白、舞蹈,甚至有動(dòng)物的出現(xiàn),構(gòu)成一個(gè)綜合性的藝術(shù)形式。
這部作品與傳統(tǒng)歌劇的不同之處,首先在于管弦樂隊(duì)。樂隊(duì)并非處于樂池中,而是在舞臺(tái)上。樂隊(duì)的編制精簡(jiǎn),其中加入了色彩樂器。在表演層面,長(zhǎng)笛、薩克斯、單簧管樂手在演奏時(shí)走動(dòng)到舞臺(tái)前方,與動(dòng)物們進(jìn)行互動(dòng)。另外,演唱者減少了在舞臺(tái)上的四處走動(dòng),在固定的位置上進(jìn)行演唱。這部作品沒有傳統(tǒng)“幕”或“樂章”的分隔,而是以故事的層遞作為劃分依據(jù),以器樂演奏來體現(xiàn)音樂的開始與結(jié)束感。相比于其他室內(nèi)歌劇更具有綜合性的特點(diǎn)。除此之外,作曲家還進(jìn)行了一些創(chuàng)新性的突破,比如四位演唱者走到觀眾席,圍繞著觀眾小聲呢喃,仿佛觀眾成了群眾演員,進(jìn)入了納瓦霍族的神話世界中。





作品的另一大亮點(diǎn)是將真實(shí)的動(dòng)物融入到表演中。作曲家將老鷹和狼設(shè)計(jì)在了舞臺(tái)表演中,老鷹通常與舞者一起登場(chǎng),舞者戴上手套,手中拿著飼料吸引老鷹,以便于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老鷹的行動(dòng)。但還是會(huì)有即興性的動(dòng)作發(fā)生,比如老鷹有時(shí)會(huì)脫離舞者的控制,飛到演奏者的頭上。狼在音樂非常靜默時(shí)登場(chǎng),由一位老婦人引上臺(tái),在舞臺(tái)前端踱步幾個(gè)來回之后再下臺(tái)。
冒著動(dòng)物可能會(huì)做出不可控行為的風(fēng)險(xiǎn),作曲家為什么執(zhí)意讓它們上臺(tái)?
之所以選擇這兩種動(dòng)物登臺(tái)是有原因的。在納瓦霍族起源的傳說中,人們用鷹的羽毛召喚出了第一個(gè)男人和第一個(gè)女人。而狼則是納瓦霍族神話中的關(guān)鍵人物,通常出現(xiàn)在神話故事和療愈儀式里。在納瓦霍族神話的所有角色中,狼是最矛盾的,經(jīng)常在將人逗笑和令人恐懼間徘徊。它處于灰色地帶,亦正亦邪。
除了老鷹和狼,作曲家還設(shè)計(jì)了舞者模仿蜘蛛。劇中,兩名舞者以高難度的姿勢(shì)模仿蜘蛛的形態(tài)以及動(dòng)作。蜘蛛在納瓦霍族神話中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它持續(xù)不斷地保護(hù)和幫助人類。在歌劇中,“蜘蛛”幫助了雙胞胎,給了他們能保護(hù)自己的羽毛箍。
動(dòng)物既是故事內(nèi)角色的一部分,也是音樂構(gòu)成的一部分,同時(shí)還是歌劇與現(xiàn)實(shí)連接的橋梁,是一種從舞臺(tái)到自然的回歸。作曲家和腳本作家通過將動(dòng)物引上臺(tái),以舞蹈模仿動(dòng)物的方式,打破了傳統(tǒng)舞臺(tái)和觀眾席的界限,使觀眾不僅是在欣賞一部作品,而是置身于大自然。雖然這部作品是用現(xiàn)代音樂講述本土故事,但并不單純地在講述一個(gè)故事,同時(shí)也在向世人發(fā)出信號(hào),發(fā)出大自然急需治療的吶喊。“小鳥在天空消失的日子,人們還在無(wú)知地歌唱。”佩庫(kù)用歌聲帶我們看到大自然的“無(wú)助”。作曲家用這樣的方式讓觀眾感受到地球正在經(jīng)受的磨難,更是提醒大家,我們沒有處在神話當(dāng)中,無(wú)法拋下現(xiàn)在的世界前往新世界。我們只有一個(gè)地球,如何與自然相處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面向閃閃發(fā)光的世界
劇中的角色從始至終都是為了尋找一個(gè)和諧美好的世界而拋下那個(gè)被摧毀的世界,這些被摧毀的世界本是美好的,丑陋的只是把它們摧毀的邪惡力量罷了。作曲家將史詩(shī)中抽象的邪惡力量具象化,引入了“怪物”這一角色,劇中的雙胞胎兄弟還沒出生就命定成為“怪物殺手”。怪物被殺死之后,故事的結(jié)局并沒有那么美好,世界依舊一團(tuán)糟。“我聽到了伏擊聲,樹木在說它們的根像頭發(fā)一樣從地球的頭皮上拉下來。它們倒下了,它們崩潰了……在火用它的紅色舌頭舔過森林之后……沒有地方可以筑巢。”歌劇雖然是在講述一個(gè)故事,但總是引人深思。作曲家通過一個(gè)結(jié)局并不完美的故事將現(xiàn)實(shí)問題赤裸裸地展示在觀眾面前,他沒有在歌劇中隨意的提供一個(gè)解決方案,而是將問題留給大家深思。

作曲家在廣闊的大地和萬(wàn)千生靈之中汲取到力量,最后以一曲又一曲靈動(dòng)的音樂回饋大自然。在歌劇中他們獵殺怪物以求世界美好,在現(xiàn)實(shí)中的我們應(yīng)當(dāng)做些什么呢?雖然作品以納瓦霍族的前世故事開始,但它隱喻當(dāng)下的真實(shí)遭遇——在全球變暖的時(shí)代,地球母親正在發(fā)生的更大規(guī)模的事情。被有毒氣體、殺害海洋水生動(dòng)物的塑料、倒在地球上的有毒廢料和農(nóng)藥、殺蟲劑等所污染破壞的地球該被如何治愈呢?這是作曲家和編劇想讓我們思考的問題。
我們身處閃閃發(fā)光的世界,大地和天空是我們的依靠,動(dòng)物、植物與我們共同守護(hù)這個(gè)世界。女中音歌唱家克里斯蒂·芬在出演這部歌劇前,認(rèn)為學(xué)習(xí)納瓦霍文化的復(fù)雜神話,以此讓觀眾感受到這種文化的生命力。
對(duì)另一種文化的詳細(xì)了解往往會(huì)增強(qiáng)人們對(duì)該文化的尊重,對(duì)除自身以外的文明保持敬畏之心是非常重要的。神話里的世界可以再創(chuàng)造,但現(xiàn)實(shí)中的世界一旦毀滅便不復(fù)存在,作曲家試圖用納瓦霍族人的歌聲喚醒大眾,將歌劇作為現(xiàn)實(shí)世界的投影。
“文明,曾經(jīng)被西方列強(qiáng)所濫用,來對(duì)非西方國(guó)家采取的歧視性待遇進(jìn)行辯解。”這部作品讓我們認(rèn)識(shí)到,世界并不存在中心,它本身多姿多彩,由不同膚色、不同人種、不同民族共同組成。正如腳本作家勞拉·托伊說:“我們希望讓觀眾思考我們必須為未來做出的選擇,不僅是為了后代,也是為了地球上所有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