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東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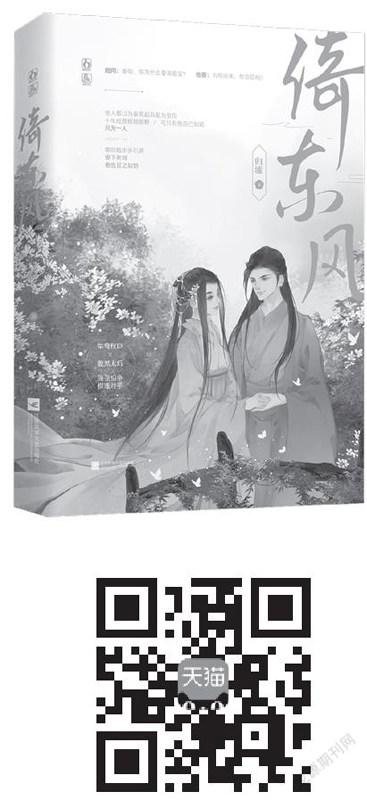
作者簡介:新浪微博:@歸歸歸歸噓
歸墟,南方人。2014年開始發表短篇,作品散見于《花火》《飛魔幻》《愛格》等雜志,擅長寫作文風細膩的古代言情小說,偶爾嘗試輕松風格。
作品簡介:
世人都以為秦荀起兵是為皇位,可只有他自己知道,十年經營,權傾朝野,只為一人。
哪怕她步步引誘,設下死局,他也甘之如飴。
桀驁權臣×腹黑太后,強強相爭,棋逢對手!
(特別聲明:因連載需要,部分情節在連載過程中做了刪改、調整,最終故事情節以實際出版為準!)
正文:
元寧九年臘月十七,雍州紫云渡,黃昏將近,天邊烏云層層疊疊地堆砌著,寒風卷起霜雪,店小二坐在門口,瞅了眼天色,轉身正要進里屋,一陣馬蹄聲由遠及近傳來,為首者身披鴉色大氅,劍眉星目,右頰有道一寸來長的舊疤,儼然是行伍之人。
那一行人勒停馬,每人腰邊都佩著馬刀,神色肅穆。
店小二吃了一驚,忙道:“今夜有雪,小店已經打烊了。”
為首之人翻身下馬,拱手行了一禮:“我與幾位兄弟從北地遠道而來,趕了一天路,不知店家能否提供些飯食?”
店小二張口,上下牙凍得直打戰,掌柜放下賬本走了出來,笑著相迎:“還有炙羊肉和溫酒,客官們不嫌棄的話,便進來歇歇腳。”
入夜后,風雪更密,店小二將馬匹拴好,喂了糧草,小步跑進茶館,抖落一身積雪。
一行人已經在茶館里頭坐下,將兩張木桌拼在一起,一邊烤火取暖,一邊等著上飯,時不時插科打諢兩句。
店小二去后廚晚了些,又挨了掌柜一頓訓,嘟囔著道:“說了關店,是他們非要進來的,七八匹馬要打點,我一個人怎么忙得開?”
掌柜五十來歲,年輕時在北地參過軍,眼力、見識都在他之上,于是斥道:“沒瞧見那些人的佩刀嗎?看形制應該是北地軍中的樣式,這時節趕著入京的貴客,哪里是你我得罪得起的?”
訓完,不放心這個愣頭青獨自應付一屋子人,掌柜便將店小二留在后廚燒火,自己捧著兩大盤炙羊肉出去。
那些人飲了些酒,面色微醺,掌柜送完羊肉便想借口離開,為首之人喚住他:“我有些事,想向掌柜討教。”
他拋來一枚碎銀,掌柜接住,賠笑道:“客官想知道些什么?小店偏僻,消息也不大靈通。”
那人問他:“陛下的病情,掌柜可聽說了?”
“官家陸續病了兩年,這是端國上下都知道的事。不過官家半年前就開始讓東宮監國,傳言說連輔政大臣的人選都定好了,怕是要托孤。”說到這里,掌柜嘆了口氣,“官家仁厚,可惜只有東宮這一位皇子,必定是寵愛的,據說性情養得過于嬌弱了。”
過了小會兒,那人又問:“皇后呢?就沒有關于她的傳聞?”
“小薛后?”掌柜愣了愣,“小薛后性子嫻靜,幾年前入宮受封后一直在御前伺候,與東宮相處融洽,倒是極少聽說這位娘娘的事情。”
他晃了晃杯底的酒,說道:“掌柜這酒釀得不錯,等有空了,我定來討教方子。”
掌柜亦笑:“客官若喜歡,盡管多飲些。”
“還有一件事,想要討教掌柜。”他抬起眸,一雙琥珀色眼瞳在燭火的映照下,越發像是質地上好的琉璃,“凌王與官家一母同胞,東宮年幼,京中可傳過凌王屬意皇位?”
琥珀色眼瞳是北蚩人才有的特征,見他竟生了這般模樣,掌柜不由得驚駭,連舌頭也不利索起來:“妄……妄議天家之事可是要殺頭的,客官莫要多問了。”
他笑了笑,只道:“有勞掌柜。”
掌柜進了后廚,背上冷汗涔涔,他一巴掌扇起倚在灶臺邊烤火的店小二,低聲道:“快些把飯食熱好送過去。”
店小二不明所以,捂著腦袋悶聲哼了幾句,端起托盤出去,那行人已經離去,留了錠銀子在桌上。
他收起銀子,喜不自禁,去后廚稟告掌柜。
掌柜坐在灶膛前烤火,斜倚著墻壁,雙目微合,似是在打盹。他連喚數聲,見掌柜仍無反應,壯著膽子輕輕拍了下。
紙糊的窗戶上不知怎的破了一個洞,北風倒灌進來,掌柜的身子軟軟地倒了下去,心口插著一支弩箭,還在流血。
店小二探過鼻息,隨即連滾帶爬地逃向后院,連銀子掉了,也顧不上撿。
后院的馬匹早就沒了蹤影,一地泥濘雪水,那一行馬蹄依稀是往南去,再過數百里,就是雍州兵營……
第一章·驚變
元寧九年冬月第一場雪,落得比以往要大許多,及至黃昏終于止住,整座宮闕掩于皚皚白雪之下,一眼望去盡是肅殺寒意。
薛縈坐在偏殿里剪燈花,蕭琰服過藥后睡下,承明殿里有醫官和宮人看守,無須她時刻陪在御前。
大概是困得厲害,她竟也無夢無魘地睡了會兒,醒來時外頭廊上點了宮燈,等候在帳外的女官絳珠輕聲說道:“娘娘,方才太子殿下過來了,見娘娘睡著,故在外殿等候,說是等娘娘醒了,一道去承明殿請安。”
薛縈起身,吩咐絳珠:“讓太子入殿等候。”
她匆忙梳洗過,見到蕭鈺,小小的人兒,擁在狐裘里,只露出一張瓷白的面孔,大大的眼睛遮掩在鴉羽似的睫毛之下。他是一個生得精致的孩子,所有見過他的人都這樣說,甚至于,過于女氣了。
蕭鈺向她行禮,見蕭鈺一雙小手凍得通紅,薛縈遞去一個暖爐。他卻沒有接,輕拽了一下薛縈的衣袖,小聲央求道:“若父皇還在歇息,娘娘便不要帶兒臣進去請安,免得擾了父皇清寧。”
明帝蕭琰寬厚仁德,唯獨在養育儲君一事上甚是嚴苛。薛縈不止一次瞧見他怒極時起身,隨手抄起一卷書便敲打蕭鈺,也難怪蕭鈺會怕他父親。
寒風刮過,長廊上掛著的宮燈搖曳起來,薛縈牽過蕭鈺的手,低聲道:“殿下每日都要去請安,今日自然不能例外。”
蕭鈺緊跟在她身后,多半是不太情愿的。
入了承明殿,正逢宮人呈上晚膳,無外乎是一些清淡菜肴和藥粥,薛縈與蕭鈺一道行過禮,于殿下等候。
承明殿的地龍要燒得暖和很多,薛縈站了一會兒竟有點犯困,不多時聽見小黃門過來傳喚太子,當即清醒過來,輕輕拍了一下蕭鈺的小腦袋,道:“去吧!”
君父照例是要考查《治國策》的,蕭鈺記得不熟,磕磕巴巴,還未背到一半就被蕭琰打斷,怒斥幾句,就將他逐了出去。
小黃門奉命將他送回東宮,經過殿下,他復又向薛縈行禮道別,一雙眼眸忍著淚,紅通通的。
薛縈心中默嘆,上前伺候蕭琰用藥,柔聲說道:“殿下年幼,畢竟還只是個九歲的孩子,陛下不宜操之過急。”若是平常,她斷然不敢當著蕭琰的面徑直為蕭鈺求情,可今夜見他委屈至極,心中多少有些不忍。
蕭琰拾起一枚加應子,含在嘴里除去藥湯殘余的苦味,眉頭緊鎖著,卻不說話。
薛縈知曉怕是自己的話觸犯到他,于是笑了笑,又道:“方才是臣妾失禮,臣妾一介婦人,原本不應過問東宮之事。”
“并不是怪你,只是這孩子太不成器,平日太師布置的課業總完成不了,連朕親自督促,也不見起色。”蕭琰道,“你疼愛他,自是好的,可一味勸說不加管束,便是害他。”
薛縈點頭,準備聽他訓斥,蕭琰卻收了怒容,緩和神色,與她說道:“一個月前北蚩南下,寧州又打了場勝仗。年關將近,朕召了寧州刺史秦荀入京領賞,以示嘉獎。”
秦荀這個名字,薛縈從旁人口中聽到過許多遍。
世人最為津津樂道的是元寧五年那一役,北蚩越過邊境攻到寧州城下,秦荀主動請纓,率一小支騎兵從側門出城,繞道偷襲敵方兵營,施計縱火焚了輜重糧草。不料北蚩的右將軍阿渾邪發現異常,率兵追截,秦荀單槍匹馬迎戰,將阿渾邪斬于馬下。那年寧州的冬天提前到來,北蚩被迫退兵,秦荀因此名揚北地,一路晉升,官至寧州刺史。
秦荀常年戍守邊境,執掌二十萬寧州軍,薛縈與他無過多交集,也僅在去年春狩時見過他。
蕭琰對這位寧州刺史一向青睞,數次在朝堂上夸贊他的軍功。
此番蕭琰主動和她談起秦荀,薛縈不知他的用意,只好說道:“臣妾駑鈍,朝堂上的事情,一概是不太清楚的。”
“去年西青山春狩,你與女官走散,是他將你救出,皇后可還記得此事?”蕭琰看著她,目光幽深。
薛縈素來避諱提及這樁舊事,低頭避過他的注視,輕聲道:“臣妾……”
“皇后總是這樣謹慎,鮮少過問朝堂的事,恨不得將自己藏起來。”蕭琰打斷她,“儲君尚未長成,京中不乏對這皇位虎視眈眈者,眼下的局面,皇后心里分明清楚得很。”
他話中之意,指的是與他一母同胞的凌王。
蕭琰膝下只有一位皇子,早早立為儲君,可太子年幼,難以執掌大權,況且前朝便是亡在幼主手中。朝臣們私下多有議論,也不乏公然上書請他改立儲君者,都被他賞了一頓廷杖。
朝臣們背地里的議論倒也算不得什么,更令蕭琰傷神的是,與尚未長成的皇孫相較,太后似乎也更傾向改立次子凌王為儲。
便是在生母的脅迫勸說之下,蕭琰不得不分了些實權給胞弟,雖然之后蕭琰想法子迫使他之藩去了南邊的封地,但他手底下多少有點兵將。現今蕭琰病重,凌王以公務繁忙為由,久未歸京,一番舉動令他起了疑心,便逐漸謀劃起來。
薛縈道:“陛下正值壯年,太子殿下得陛下悉心教養,也無須臣妾為他過多操持。”
蕭琰靠在金絲繡邊的軟枕上,半瞇著眸子,道:“朕覺得乏了,你回含涼殿吧!”
不知何時,雪又下了起來,深及膝蓋。絳珠去傳喚步輦,薛縈立在殿外等候,風卷著雪撲面而來,廊下宮燈不久也覆上一層薄薄霜色。她靜默地望著,便不由得出了神。
直至內侍抬了步輦過來,薛縈才收回心緒,伸手接住一片落雪,對絳珠說道:“你去趟東宮,若殿下還未睡,將他接來含涼殿。”
那雪花很快融化在掌心,涼意絲絲沁入,擴散至四肢百骸。
回到含涼殿,薛縈命宮人添置炭爐,將九支銅制燭臺點上,照得宮室內明亮如晝。待一切準備妥當,絳珠正好攜蕭鈺到了殿外,薛縈屏退宮人,只讓蕭鈺入殿。
蕭鈺有些發蒙,旋即手里被塞了一卷書,正是在承明殿請安時背誦的《治國策》。
薛縈笑意盈盈:“冬夜天黑得早,殿下如果晚間無事,就來含涼殿背書吧!”
之后幾日,太子再去承明殿請安,竟意外地沒有惹怒明帝。
薛縈用白玉調羹輕輕攪動,只盼著湯藥快些涼下來。蕭琰正批閱奏疏,御筆朱批,只稍抬眸便可窺見其中內容,她卻不敢多看。
等他批完奏疏,藥也差不多溫度剛好。薛縈遞上,他一飲而盡,用素絹拭去唇邊藥漬,道:“太子近來表現好了些,想必是你教導了他。”
“臣妾才疏學淺,只能敦促殿下閑暇時多讀些書,將來好為陛下分憂。”薛縈頓了頓,才說,“殿下念書好些年,身邊也沒有伴讀,不過近來和臣妾提起,想討要一個伴讀。聽說是梁大人家的公子,年長他兩歲,是在國子監認識的。”
蕭琰神色冷下幾分,似有不悅:“讓他安心念書,莫要想這些無用的事。”
薛縈本想為他再爭取幾句,瞧見蕭琰的神情,將話咽了下去。
“他似乎從小就喜歡同你親近,有什么事,也極少與朕說。”蕭琰道,“當初許你中宮之位,朕其實是存了私心的。”
薛縈福了福身:“臣妾知曉,日后必定盡力輔佐殿下。”
而后他又問了后宮諸事,蕭琰不喜女色,妃嬪原本就不多。靈毓皇后仙逝以后,他下令遣送走幾位妃嬪,剩下的都安分守己地待在各自宮中,倒是給薛縈打理后宮省去不少麻煩。
略微答過幾句,蕭琰便讓她回去了。
從承明殿出來,回廊下遠遠立著一人,身著絳色官袍,長身玉立,樣貌看起來甚是清俊。
或許是相隔太遠,或者是教漫天風雪遮住了視線,薛縈看不真切他的眉目,便這樣遙遙望了一眼。縱然只是這一剎的相逢,竟也令那人發覺了,向她叩首行了一禮。
她沒有做過多停留,轉身離去,絳珠跟了上來,將她扶上步輦。
“方才給娘娘行禮的人,是大理寺少卿謝懷虛,聽聞陛下召他入宮,是為了商議開春后大赦犯人祈福之事。”絳珠壓低了聲音,同她說道。
薛縈淡淡應了聲,垂下眸:“陛下興許是想為東宮祈福。”
那夜薛縈讓宮人將熏香換成安息香,縱然如此,她睡得依舊不安穩。前塵舊事攜卷風雪一并涌入夢中,恍若又回到了十三歲那年,她與父親從寧州回到京中,入宮拜謁已成為皇后的堂姐。那時堂姐懷孕八月有余,腹部高高隆起,她將手覆了上去,感知到胎動,忍不住發出小小驚呼。
堂姐溫柔地笑著,要她快些定下夫家,只待及笄,便嫁過去。她兩靨緋紅,悄聲告訴堂姐,父親為她許了親,是他的故友謝家,謝家公子幼時與她同窗讀書,算是知根知底的。
而后堂姐難產而亡,薛家遭難,又逢謝家伯伯病故,謝家公子須守滿三年孝才能娶她過門。她滿心歡喜地等待著,卻不承想,等來的竟是天子下旨,命她入宮。
天子心系靈毓皇后,有意立她所出的皇子蕭鈺為儲,召她入宮,實則是為了給蕭鈺尋個品性賢淑的養母。
她父親是不愿意的,但與薛家滿門的前程相比,父親的這點抗爭又算得了什么?
及至后來,謝懷虛考取功名,入京為官,她才又見到他。
那時她立在珠簾后,見他從容叩拜,稱呼她“娘娘”,從此與旁人無異。
入宮數年,她從妃位一路升至皇后,依照天子的旨意,安撫后宮,養育儲君,也許心里早已將他放下,只是寂靜無人時,終究還是會想起這個人、這些事。
蕭琰的病,是在臘八節過后變得嚴重起來。
宮里熬制了臘八粥,蕭琰嘴里苦澀,命小黃門取了半碗。粥已經有點涼了,但他執意要吃,于是小黃門呈上去,結果當夜他就因再度受寒而高熱不退。
薛縈趕去時,承明殿亂成一團,太后和各宮妃嬪皆在,如花似玉的年輕妃嬪們一個個哭得梨花帶雨,而那位呈粥的小黃門已被杖斃于殿外。
蕭琰從昏睡中醒來,聞見哭聲,心中更是煩悶,冷聲斥退妃嬪,留下太后與薛縈。
她以為這對母子有話要說,正要回避,忽被蕭琰喚住。
蕭琰支撐著起身,聲音虛弱,看著太后道:“朕有話要與皇后說,還請母后先去偏殿稍事歇息。”
聽他這樣說,太后不免驚訝,離開前淡淡地掃了薛縈一眼,薛縈佯裝不知,屈身向她見禮。
薛縈取了軟枕給他墊在身后靠著,饒是如此,蕭琰仍有些吃力。
“朕興許熬不過年關了。”他緩緩說道,“太子性情頑劣,這幾年承蒙你的照拂。薛家教出來的女兒定是不會差的。待朕百年之后,望皇后繼續輔佐太子。”
與他相伴數載,兩人之間雖無夫妻情分,現下聽他交代身后事,薛縈心里生出悲戚,點頭應允。
蕭琰繼續說道:“儲君年幼,凌王與朕一母同胞,如今有詔仍不歸京中,私下里許是在謀劃,恐怕太后心里也更偏向那位。如果真到了那時,羽林軍的兵力部署用來護衛宮城定是夠了的,你不必顧慮太多,安然保鈺兒繼位即可。”
薛縈眼中有了水意,道:“臣妾知曉。”
他忽然握住她的手,薛縈愣怔,下意識便要將手抽出,可他使了些力氣壓制住她,道:“朕下旨召你入宮那時,原是知道你已經許了親的。可鈺兒年幼,宮里頭那些妃嬪都想競相誕下皇嗣,朕不放心將他交給別人照看,思來想去,便只有你了。”
薛縈入京時,便做好打算替他蕭家打一輩子長工,掛個虛銜在宮中,撫育小外甥,安分地守著紅墻碧瓦了此一生。
蕭琰這般與她說心里話,倒有點體恤臣下的意味。
她定住心神,道:“在我心里,陛下是大端國的君主,是阿姐的夫婿,我從未想過逾越。”
蕭琰緩緩說道:“日后朝局穩定,待鈺兒親政,你若是想離開,便尋個法子出宮吧,對外就說是病歿了。”
薛縈道:“我從小便沒有母親,兩年前父親也過世了,世間之大,除了陛下賜給我的含涼殿,已無處可去。”
聞言,蕭琰松開手,輕輕拍了下她的肩。
“在我很小的時候,家父常外出游歷,嬤嬤們照顧我并不細致,我害了一場大病,險些丟命。阿姐知道了,將我接去她的院子里照顧,這才好轉起來。在阿姐入宮成為陛下的皇后之前,我都是長在她的身邊。”薛縈抬眸,一雙眼澄澈清亮,“阿姐難產而亡,殿下也是從小沒了母親,我雖不能替代他的生母,但至少,不會容許旁人欺負他。”
蕭琰頓了片刻,才道:“你心底柔善,把鈺兒托付給你,朕很放心。”
更漏聲重重,夜漸深,薛縈想起太后還在外殿等候,許是有話要和蕭琰說,忙收斂好情緒,向蕭琰見禮,退出內殿。經過那座紫檀木山水屏風,她瞧見蕭琰用帕子掩住口鼻猛然咳嗽,像是要把五臟六腑都咳出來。
他斷斷續續病了三年,整個人形銷骨立,如飄零在秋風中的一片枯葉,薛縈明白,他沒有多少時日了。
蕭琰的病牽動著整個后宮,此次他卻命妃嬪們按照位分輪流去御前伺候。眼看除夕臨近,明帝的病未有好轉,一日比一日嚴重起來,太后起先只在永寧宮設了佛龕上香禱祝,后來便提出要去京郊的清音寺為陛下祈福。
清音寺在靈虛山上,這時節無香客前來,山道幾乎被大雪封住,僅有寺里僧人清掃出的一條羊腸小道勉強可以通人。尚未天晴,若此時上山,再遇上一場雪,便要被困在寺里。
得知太后要出宮祈福,薛縈并不詫異,撥了幾位內侍與之同行,以便護衛,并親自打點所需行裝。
即使這樣,她去永寧宮請安,還是不免遭太后奚落。薛縈無視她話里夾槍帶棒之詞,見隨行的宮人物資準備妥當,福了福身便要告退。
太后斜靠在貴妃榻上,擁著狐裘暖爐,聽聞她要走,輕哼一聲:“本宮原本就沒提起要去靈虛山祈福之事,陛下要讓本宮去,本宮只好走這一趟。許是你在他面前提起了什么,才讓他非要趕在風雪天攆走本宮。”
薛縈并不將她的這番指摘放在心里,說道:“近來恐有變故,陛下是擔憂娘娘的安危。靈虛山地處京郊,僻靜幽遠,將娘娘安置在清音寺中,陛下也可放心些,還望娘娘體恤陛下身為人子的一番孝心。”
“京中分明好端端的,哪來的什么變故,定是你在我們母子之間挑撥了什么。”太后的聲調驟然尖銳起來,“他說要納你入宮,我便不同意。偏偏他就跟中了魔似的,非你不可,就跟當初他即位后不顧朝臣反對,立你族姐為后那般。你們姊妹二人都是托生來的狐媚子,這一世專去禍害了他。”
薛縈當即伏跪在地,也不為自己分辯,卻想,太后這般罵她,也算是變著法兒夸了她皮相生得還算不錯吧!
幸而她申斥了幾句,不再繼續往下說,讓宮人扶起薛縈。
罵得久了,她也心累,嘆了聲氣,緩和了語氣問薛縈:“陛下是糊涂了,可皇后當真覺得阿鈺這孩子,能擔此重任?”
薛縈順手撫平下裳的褶皺,笑了一笑,道:“娘娘,這是陛下心中所求,臣妾身為大端的皇后,所能做的,只有竭力助他達成。”
想要保東宮順利繼位,首先就要拔除凌王這一隱患。凌王離京數年,在宮中的耳目早已被蕭琰清理干凈,唯一能與他聯絡的便只有太后。將太后送去靈虛山,一來可以阻斷兩人私下里的書信往來,二來,也是為了防止宮變當真發生,兩軍若是在禁庭之中混戰,恐會傷到太后。
博山爐里投入新的香片,太后躲在裊裊青煙之后,目光有些閃爍:“他答應過本宮,不會傷害手足。”
薛縈道:“陛下應允了娘娘,自然是要做到的。”?次日清晨,太后出宮祈福,薛縈將太后的車駕送走,回到含涼殿,蕭鈺正等著她。
這個時辰,他應該已在國子監念書,薛縈來不及問他緣由,命絳珠去傳步輦,將他交與國子監的徐太師。蕭鈺三步并作兩步上前,抓住她的手,忙道:“父皇昨夜說了,兒臣近來表現尚可,準許兒臣歇息一日。”
聽聞這番說辭,薛縈仍不放心,詢問過他的近侍,這才松了口氣,牽著他一同入殿,喚宮人為他準備些吃食。
“兒臣不餓。”蕭鈺卻將小腦袋搖得跟撥浪鼓似的,顯然有點生氣,小聲道,“娘娘并不信我。”
薛縈起先是擔憂他無端逃學遭父親訓斥,卻沒料到他竟會在意方才那樣一件小事。焐熱了他的一雙小手,薛縈才笑著道:“我近來要煩憂的事有些多,若是怠慢殿下,請殿下恕罪。”
蕭鈺望了望她,似懂非懂的,想了會兒,低下頭道:“我也不是存心要與娘娘置氣。”
言罷,蕭鈺伏在她膝上,專心致志地用指尖描起她裙擺上繡著的花鳥圖樣。
小孩子就是這樣,不將情緒積在心底,可他長至如今歲數,仍不喜刀劍,對女兒家的東西甚是感興趣,未免陰柔了些,這點令薛縈犯難。
她任由思緒飄了很遠,忽聞蕭鈺喚她,聲音悶悶的:“姨母,我聽見照顧我的宮人們說,爹爹快要病死了。”
薛縈吃了一驚,慶幸眼下宮室里只有他們二人,未教旁人聽見。
她伸手將他攬到膝上抱著,低聲道:“不可以這樣喚我。”
蕭鈺掰著小手指頭,道:“可我從小就是這樣喊你的,我有母親,我的母親是靈毓皇后。爹爹說她生下我以后,就離宮遠游去啦!”
薛縈心中沒來由地泛起一縷酸澀,溫柔地道:“阿鈺以后要喚我娘娘,你是儲君,是大端未來的天子,別人私下里說的話,不可輕信。”
“可我一點也不想變得像爹爹那樣,成日忙碌,見了朝臣和各宮娘娘,也總是冷冰冰的。國子監讀書的公子們都有伴讀,偏我沒有。明明梁家小公子已經同意了當我的伴讀,可爹爹就是不允。”他迫切地道,“況且,大端沒有那樣的先例……”
“阿鈺。”薛縈揉了揉他的小腦袋,將他對父親的一腔怨念和控訴打斷,“你是陛下唯一的骨血,總歸是要面對這一切的。”
他霎時紅了鼻頭,細聲細氣地道:“可如果爹爹真的走了,我會害怕的。”
薛縈攬著他,聽見積雪壓斷窗外梧桐木的枝丫,心道:“我也害怕。”
雪天官道泥濘難行,駛出驛館才幾里路,一人一馬身上俱掛滿冰霜,信使緊握韁繩,揚起馬鞭奮力抽下,催促馬匹快行。
如此行了百來里,方才趕到下一處驛館,冒著風雪行路,人與馬匹都已是精疲力竭。信使不敢懈怠,喝了半碗熱湯,帶上炊餅、水囊,換上另一匹良駒復又趕路。
三日后,消息傳至京中,凌王聞悉今上病情加重,已放下手頭事務,啟程趕來。
蕭琰冷笑道:“難得他有這份心,下著大雪,也要千里迢迢從豫州趕來探視兄長。”
起先他屢次下詔,都被凌王以各種事由回絕,現今選在這樣的時機主動回京,難免不讓人生疑。
說完,他便又咳嗽起來,薛縈抬手為他撫背順氣,待氣息平穩,蕭琰道:“去把太子接來。”
現下東宮正在國子監念書,小黃門一去一回便要大半個時辰,薛縈陪他等待,靜默地坐在床邊。他雙眸闔著,呼吸急促,似是吃力得很。
小太子蕭鈺入殿時,腋下還挾著卷書,恭敬地向二人行過禮,立在不遠處,模樣看起來有些拘謹。
蕭琰沖他招手,示意他到自己跟前來。蕭鈺猶疑了一下,才朝他們二人走來,輕聲詢問道:“陛下召兒臣前來,可是有什么事嗎?”
蕭琰問他:“鈺兒近來在讀什么書?”
蕭鈺把書交給近侍,答道:“在學《孟子》里的文章,夫子布置了課業,待兒臣理解熟記了,再請陛下考查。”
“鈺兒以后要做一個仁德的君主,勤政愛民,開創盛世。”蕭琰眼底笑意溫和,撫了撫他頭上梳著的兩個小髻。
小太子將頭重重一點,道:“兒臣謹記陛下的教誨。”
他有些愣怔,分明張口還想與孩子說些話,想了片刻,卻轉首對薛縈道:“朕病得太久,恐把病氣渡給你們母子二人。皇后帶太子出去用午膳,今日不必將他送去國子監了。”
聽到父親這樣說,蕭鈺心中生出一陣小小的雀躍,與薛縈一道往外走去,轉身經過山水屏風,他停下步子,回首望向病榻上的父親,聲音軟軟糯糯:“爹爹的病,何時才能好起來?”
蕭琰笑著道:“等到年后開春,柳樹抽了嫩芽,鹿苑的梅花鹿長出新角,爹爹便能好起來了。”
蕭鈺想了會兒,終于下定決心,鼓起勇氣道:“那等爹爹政務不那么繁忙了,陪我去金明池邊放紙鳶好嗎?爹爹已有好幾年沒有和我去過了。”
望著懵懂無知的幼子,任憑蕭琰平日心腸再硬,此刻終究也變得柔軟。他合起雙掌,捏成小兔形狀:“等來年春暖,爹爹給鈺兒扎一只小兔紙鳶。”
宮燭將影子拉長,投到墻壁上,那小兔搖頭晃腦,憨態可掬,終于逗得蕭鈺展顏。
次日黃昏,蕭琰召集宰相與幾位老臣入宮,及至宮門落鎖,也未見朝臣們所乘的青篷馬車出宮。
睡到四更天,薛縈從夢魘中醒來,驚出一身冷汗。
絳珠擎著盞燭臺走來,以為她夜里口渴要喝水,喚內殿值守的宮娥去端些溫熱的蜂蜜水。薛寧搖頭,問絳珠道:“陛下今日召見的幾位大臣,如今還在宮中嗎?”
絳珠道:“聽承明殿值守的宮人說,陛下晚間時候命內侍收拾出暖閣,讓幾位大人暫時歇下了。”
他這樣著急召朝臣入宮,興許是感知到大限將至,預備欽定顧命大臣臨終托孤了。
薛縈忙披衣起身,吩咐絳珠道:“取面銅鏡來,本宮不放心,要親自去承明殿御前侍奉。”
還未將釵環戴上,外頭便有內侍前來通報,說陛下病情加劇昏迷過去,須請皇后速速趕去承明殿。
薛縈聽后,只來得及隨手撿起兩支素銀簪子斜斜插入發髻。
承明殿內燭火通明,醫官們魚貫進出,見了她,紛紛停下行禮。薛縈心中焦急,詢問內侍,得知小太子已在趕來的路上。
蕭琰依然昏睡著,無轉醒跡象,而先前入宮留宿的大臣們此刻跪在屏風外等候傳召。薛縈沒有流淚,心知這一刻終歸是要到來,無論是蕭琰,還是她,都已做過準備。
太醫提議施金針診治,薛縈清退宮人,讓朝臣們也去外殿候著。金針一枚接一枚刺入頭上穴位,蕭琰仍無反應。薛縈攥著繡帕,掌心滲出細細密密的冷汗,一眨不眨地盯著他。
等了一刻鐘,太醫令取出金針,撩開官袍跪下向她請罪。她的手微微發顫起來,厲聲問道:“還有誰可以使陛下清醒過來?”
太醫們跪了一地,卻無人敢應聲。
薛縈怒道:“養你們有何用?!”
外頭驟然喧嚷,一個小小身子不顧內侍阻攔,徑直沖入內殿,卻被門檻絆了一下,像顆元宵似的滾了進來。
蕭鈺抹了一把臉上的淚,嗚咽著道:“爹爹,爹爹好些了嗎?”
薛縈走去將他抱起,冷靜了些,道:“陛下的病多年未愈,想來你們也盡力了,太醫令留下,余下人等去外殿候著吧!”
到了后半夜,便只有她和蕭鈺以及兩位太醫在內殿守著。蕭琰的氣息一陣急促,過一陣卻又緩和。薛縈為他拭去唇邊的藥漬,一顆心始終懸著。
天色將明,蕭琰終于轉醒,兩頰隱隱透出青灰色。薛縈的心稍稍放下了些,喚宮人請來朝臣,命他們在內殿的那座屏風后等待陛下旨意。
他勉力從被衾下伸出一只手,示意薛縈來他身邊。
薛縈卻只跪在床邊,猶疑片刻,才握住他的手。他嘴唇翕動,嗓音嘶啞:“太子尚未長成,朝政軍務,往后要煩請皇后多加操持。”
她輕聲答道:“臣妾謹記。”
又交代了一些其他的事,他吃力地側過首,望向屏風后。薛縈以為他是在尋找太后周氏,便告訴他太后前幾日去了西青山祈福,已派人出宮報信,要午后才能趕到。
他搖頭,執著地看著那處,薛縈想了想,又道:“陛下是在等凌王嗎?凌王給您遞了奏疏,要來宮中探視您,可豫州地遠,又逢大雪,還得過上三兩日才能抵達京中。”
他的眼瞳開始變得混濁,吐字也含糊起來,依稀是“寧州”二字。薛縈怔了一會兒,忽想起一個月前他曾提起寧州軍又同北蚩打了勝仗,要召刺史秦荀入京。
寧州離京千余里,算算時日,眼下秦荀恐怕還在赴京的路上。
可她不解蕭琰為何要在彌留之際提及這些,柔聲道:“秦將軍應是尚在趕路,陛下定要盡快康復,到時當面嘉賞秦將軍。”
蕭琰動了下眼珠,似乎還有話想說,薛縈湊近,他拼盡所有氣力,將一個紅梨木制成的小匣放到她手里。薛縈明白他的用意,允諾他道:“待日后尋到時機,我定將此物交到殿下手中。”
他闔上雙眸,便又睡了過去,似是疲累至極。
近侍率先發現天子已經沒了氣息,差內侍將備好的白幡懸出去。握著的手再沒有傳遞出半分氣力,可薛縈還是保持方才的姿勢一動不動地跪著。
外頭次第響起哭泣聲,女官絳珠上前攙扶,薛縈才終于松開他漸漸涼去的手,含淚起身,顧視殿內眾人:“取陛下遺詔,宣宰相入殿宣讀。”
元寧九年臘月十九,天子山陵崩,余一幼子,名鈺,是為新帝。
…………
到了午后,長樂宮的靈堂已布置妥當。內侍要將大行皇帝抬入金絲楠木棺槨中安置。蕭鈺守在床邊,不準內侍靠近,渾似一頭發了狂的小獸。
薛縈心中亦是難過,溫聲對他說道:“阿鈺,到娘娘這兒來。”
他嗚嗚咽咽地哭著朝她走來。薛縈矮下身,將他抱去偏殿,安撫了好一會兒才將他哄睡。
見他熟睡,薛縈讓絳珠留守偏殿照看,待他醒后,為他換上朝服和斬衰,自己則先去長樂宮安排諸多事宜。
薛縈沒有傳輦,冒雪行去,寒風刮在臉上跟刀子似的,令她霎時又清醒了幾分。
內侍先前向她稟報了消息,太后的車駕被大雪困在清音寺,要等兩日,才能下山回宮。
京中朝臣今早聞見四十九道喪鐘聲,得悉陛下山陵崩,已陸續入宮,由宰相姚婓率領,前往長樂宮憑吊,并等候新君主持陛下的喪儀。
宮眷們還跪在靈堂哭悼,有兩位娘娘險些暈過去,讓宮人扶到偏殿休息了。
眼下薛縈顧不得其他,向朝臣們公布遺詔內容,扶持蕭鈺順理成章即位,才是最要緊的事。
蕭琰踐祚九年,膝下子嗣單薄,僅有一位皇子,尚不足年歲親政,是故朝臣們對于東宮即位后,由太后薛氏垂簾聽政的安排并無異議。
及至黃昏將近,薛縈才得稍事歇息。絳珠收拾出偏殿供她小憩。她和衣躺下,心緒紛雜,怎么也入不了眠,輾轉起身,詢問伺候的宮人:“殿下現在何處?可是在大行皇帝的梓宮前守著?”
尋了一圈,薛縈才在蓮華樓找到蕭鈺。他立在欄桿旁憑眺遠處,身后只跟了一位小黃門。
薛縈屏退隨行宮人,輕聲問他:“殿下在看什么呢?”
他應聲回首,一張小臉凍得通紅。薛縈把帶來的披風為他裹上,牽起他的手,聽見他低聲道:“這天下,以后當真是我的了嗎?”
她半蹲下身,與他平視,溫柔地注目著他:“殿下不想要嗎?”
“這是爹爹給我的。”蕭鈺看著她,“可本朝開國百年,沒有過女子為帝的先例。”
話音甫落,便教北風吹散,也只有在四下無人的時候,薛縈才敢讓他提起這個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
九年前的鳳儀宮中,靈毓皇后誕下皇長女后驟然離世,陛下悲慟之際,卻做出了一個決定,隱瞞皇女身份,對外宣稱是皇子,并將其立為儲君。
蕭琰將對亡妻的哀思盡數寄托在女兒身上,從此后宮再無皇嗣出生。他甚至不惜違背太祖立下的規矩,執意要將皇位傳給女兒。
待蕭鈺坐穩了這個位子,再將女子身份公開,便是宗親朝臣們,也不好再說什么了。
“這條路興許很艱難,但我會陪著殿下。”薛縈抬手拂去她鬢發間的落雪,“就像殿下的母親當年照拂我那般,照拂殿下。”
蕭鈺吸了吸鼻子,上前抱住薛縈,溫軟的小身子瑟縮著躲進她懷里。
薛縈將她抱起,便要下樓,東南方忽然閃過一瞬光焰,幾乎照亮半邊天際,那是崇寧門的位置。
變故發生在電光石火之間。
須臾,小黃門不顧僭越,跌跌撞撞地爬上樓,顫聲稟道:“殿下,娘娘,凌王……凌王率叛軍入京攻城,還請殿下和娘娘移駕別處。”
凌王私下里與幽州刺史早有往來,策反了他,從幽州借道入京,瞞過蕭琰部下的耳目,提前數日趕到。被策反的幽州軍,加上他從封地帶來的軍士,凌王手底下有四萬余人。
宮中禁衛軍加上羽林衛,合計將近三萬,可守城與之一戰,等候勤王的兵馬趕來救駕。
眼下叛軍盤桓在南邊的幾處宮門外,尚未將北面圍起來。薛縈借蕭鈺之手擬了勤王詔令,蓋上印鑒,讓影衛從北面小門出宮繞行,火速將密信發往京畿周邊數州。
夜色漸深,朝臣們跪在殿下,屏息等候著。長樂宮中靜得可怕,只聞重重更漏聲。
不多時,前方傳回戰報,禁衛軍大統領狄烈臨陣叛變,倒戈攻向了羽林軍。
薛縈攥著座椅的木雕扶手,掌心滲出冷汗,問道:“眼下羽林衛還余多少軍士?”
信使答道:“稟娘娘,羽林衛折損后,僅余萬人。”
殿下傳出竊竊私語,朝臣們競相交頭接耳,為首的宰相姚斐持象笏出列,似是要進言,薛縈搶先道:“諸位都是文臣,與其留在長樂宮,不如隨大行皇帝的梓宮一并遷往春熙殿,等候叛軍伏誅。”
她說這番話原是為了安撫臣下,至于是否真的能在今夜清除叛軍,卻不可知。
朝臣們爭執了小會兒,大半愿隨梓宮遷行,倒是有三兩位年輕臣子選擇留下,言愿為新帝執戟,其中便有謝懷虛。
薛縈抬眸望了他一眼,便起身牽著蕭鈺往內殿去了。
凌王如若攻下皇城,首先定要尋出蕭鈺,或是直接殺了她,或是將她操縱在手里,成為提線傀儡。
一旦凌王發現蕭鈺的女兒身份,等待她的便只有第一種命運。春熙殿只是暫時收容之所,蕭鈺定不能與朝臣們待在一起,須為她尋個安全去處。
薛縈來回踱步,心中焦慮至極,恨不得現下就挖出一個深地洞將她藏好。如此幾番,她終于想起一處,喚來絳珠,低聲與她耳語幾句。
不承想出了岔子,蕭鈺不肯離去,哭著要薛縈與她們一起走。
火光照亮夜空,外頭隱約可以聽見馬蹄金戈聲。薛縈百般勸慰,蕭鈺抽噎著,不愿點頭。
薛縈被逼得沒了法子,抬手摑在她柔嫩的臉頰,力道并不重,但聞清脆一聲響。她別過臉,冷冷道:“護送殿下離開。”
蕭鈺哭出聲來,喧囂的夜里,這樣細弱的哭聲終究太過脆弱無力。
梓宮已被挪走,長樂宮只有兩個宮娥垂手侍立,宮外石階下,那幾位年輕文官正與內侍布置防守之物,依稀可見有火油和弩弓。
薛縈走了出去,夜風裹挾血腥味撲在臉上,寒冷徹骨,那廝殺聲越來越近。
片刻后,一人在她身后拱手行禮,道:“外頭太冷,還請娘娘移步宮中。”
薛縈知道是他來了,卻未轉身,笑著道:“謝大人不應該留下,新君年幼,往后朝政上許多事,還需仰仗忠心的臣子們。”
她不希望謝懷虛死在叛軍刀下,即便年少的歡喜已被時光消磨殆盡,他們之間再無可能,她仍希望他能活著,活著走出困局,日后輔佐蕭鈺。
夜色之中凝著殺意,謝懷虛再度向她行禮:“臣,護送娘娘回宮。”
晚風驟狂,檐下鐵馬相撞,宮燈搖曳不定,踏著一路細碎燭火往前行去,他跟在她的身后默默相送,始終未發一言。他的性子一貫如此,沉穩篤定,知禮,亦守禮。
羽林衛死亡過半,已是強弩之末,小半個時辰后,叛軍很快攻至長樂宮。
在烏泱泱的軍士面前,內侍與幾位文官的抵擋無異于螳臂當車,很快落敗。
凌王下令斬了那些小黃門,將文官們捆在一起,暫不處置。
軍士魚貫入殿,凌王提劍走來,劍尖猶在滴血。
此刻,長樂宮靜得可怕,薛縈聽見自己的那顆心臟怦怦跳動的聲音,佯裝鎮靜,道:“陛下昨日駕崩,梓宮尚未安置,國喪期間,凌王為何迫不及待舉兵入宮?”
說罷,她又逡視一眾將士,揚聲道:“陛下已在遺詔里定下新君人選,諸位又是因何而來?”
凌王朝她拱手行軍禮:“侄兒年幼,恐難以擔此重任,臣身為他的皇叔,須得輔佐他,請娘娘告知太子的下落。”
聽這話的意思,倒是不急于殺了蕭鈺。她緊了緊藏在袖中的匕首,道:“朝中自有股肱之臣,不必勞煩凌王費心。”
凌王蹙眉,似是失了耐性,揮手示意身后副將上前捉拿她。
薛縈后退兩步,取出匕首架在頸間,厲聲說道:“陛下尸骨未寒,你卻無端起兵,逼死皇后,他日天下人皆可討伐你。”
她抱了玉碎的決心,下手又快又狠,雪白的頸上霎時出出一道殷紅的痕,血珠子沁了出來。
以她之死,坐實凌王逼宮謀逆的大罪,倒也不算虧。薛縈凄涼一笑,轉念又想到蕭鈺,一個小丫頭想要坐穩那個位置,將來不知還要吃多少苦頭。
可她再也沒辦法護著蕭鈺了……
一支弩箭攜雷霆之勢破空而來,貫穿她的左肩,薛縈松了匕首,跌坐在地。
凌王唇邊現出譏諷的笑:“臣本就為娘娘想好了去處,不承想娘娘這般著急去見陛下。”
士兵們將一具棺槨抬了上來,那棺槨用上好的金絲楠木制成,雕刻精美,花紋繁復,形制稍遜于天子梓宮。
凌王冷笑,做了個“請”的手勢,他的兩位副將上前抓住她的手腳,把她扔了進去。
后背驀地撞上堅硬的棺底,五臟六腑如被撞碎一般,生生疼了起來,薛縈受不住這陣力道,昏死過去。
醒來時,薛縈身處在密封的棺槨中,四周寂靜無聲,臉頰一片黏膩,是傷口處淌出的血。那支箭還釘在左肩,整只手痛得麻木了。
她不能就這樣被困在棺中,坐以待斃。
薛縈使右手取下發簪,試圖利用鋒利的簪尾鑿穿棺蓋,好讓空氣滲進來。
接連折了兩支銀簪,棺蓋并未受損,僅是內壁多了幾道刻痕。薛縈被困在棺中許久,里頭空氣漸漸稀薄。她有些喘不上氣,神志也變得模糊起來,她不再想這幾日來的經歷,只是放心不下蕭鈺。叛軍破城之際,她才想到去處——把蕭鈺藏在西苑一口枯井中,命女官絳珠與她待在一塊兒貼身保護。
西苑廢棄多年,荒草叢生,那口井位置十分隱蔽,并未記載在宮苑布防圖內,叛軍興許要花三兩日工夫才能找到。
京中告急,禁衛軍叛變,密詔已從京中發出,她用性命賭這兩日內勤王的兵馬盡快趕來,誅滅叛軍,迎回先帝棺槨與新帝。
薛縈死死掐著掌心嫩肉,迫使自己保持清醒。
興許,興許援軍很快便會趕來了……
可京畿周邊屯兵并不多,即便是相離最近的雍州,快馬加鞭趕到也要一日一夜整。
她沒有多少活路了。
約莫過去了一盞茶的工夫,一件重物狠狠撞上棺蓋,薛縈從昏睡中驚醒,緊接著又傳來數次撞擊,像是有人想要開棺。
可棺槨被敲入長釘,封得極死,這個法子沒有奏效,便再沒了動靜。
棺內殘存的空氣即將耗盡,呼吸艱難起來,薛縈抬手拍打棺槨內壁,希冀以此引起外頭的注意,她并不甘心就這樣死去。
不多時,傳來利器劈砍木料的鈍響,棺槨蓋終于裂開一道罅隙,新鮮空氣滲進來,她如一尾瀕死的魚,大口喘息。
發絲教血污浸透,粘連在鬢邊,額頭上俱是冷汗,這模樣實在狼狽得很。
一聲巨響,棺蓋劈開,外頭的火光照進來,有些刺目。薛縈想要抬手去擋,卻見一人,他長了一雙琉璃色的眸子,只一眼,便攝去了她的心神。
這樣異于常人的眼睛,從前她只在一人面上見過。
那人俯身將她從棺中抱出,動作算不上輕柔,厲聲對左右道:“快去尋太醫。”
臉頰貼上冰涼的甲胄,許是長樂宮的火光太過炫目,那一瞬,薛縈以為自己身處夢中。
那人抱著薛縈進了偏殿,尋了處床榻將她放下,便要剝開她的衣裳。薛縈清醒了些,掙扎著抬手去擋:“不,不可以。”
稍有動作,竟又牽扯到左肩傷口,痛得她倒吸一口涼氣。
“再不取出箭鏃,你會血流光死在這里。”那人說完,半跪在她身旁,捉過她一雙細手腕子按住,兩下便用剪子剪開了被血浸泡得發污的衣裳。
偏殿沒有燒地龍,空氣里泛著涼意,左肩大片肌膚裸露,激得她小小地戰栗起來,驚懼羞憤之下,意識復又變得模糊。
那人倒未注意到,將一團布料塞入她的袖口,左手壓制住她的身子,道:“娘娘若是覺得疼,稍后喊出來便是。”
薛縈知曉他的身份,奮力想要掙脫桎梏。他眸色微沉,右手使力,拔除了箭鏃。
血噴濺而出,他騰出雙手用力按壓住。薛縈疼得幾乎昏死過去,整個人似是從水里撈上來的,卻未發出一聲呻吟。
她是薛家的女兒,大端的皇后,怎能教人輕看了去。
少頃,太醫和宮婢趕到,那人起身揩去滿手污血,低聲交代幾句,便匆匆離去了。
薛縈疼昏過去前,只瞧清楚一個背影,身形頎長,披著玄甲。
(未完待續)
下期預告:新帝年幼,朝堂之上波云詭譎,薛縈一方面不得不依仗手握重兵的秦荀,一方面卻又忌憚他。二人的感情也撲朔迷離……下期連載見《花火》2B!
(放立體封和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