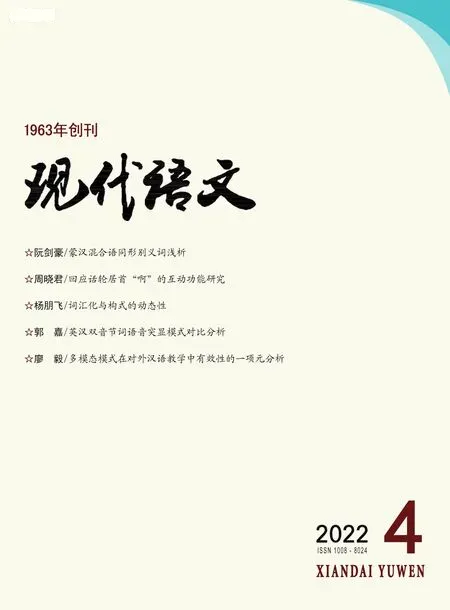清末北京兒歌語音象似修辭的英譯比較研究
牛藝璇


關鍵詞:北京兒歌;語音象似;擬聲詞;英譯策略;《北京兒歌》;《孺子歌圖》
象似性(iconicity)最早由Roman Jacobson提出,指的是語言符號的能指和所指之間具有一種必然的聯系,并且兩者之間的關系是可以論證的,是有理可據的[1](P3)。語音象似(sound iconicity)便是象似性的表現方式之一,指的是借助書面語的視覺效果來傳達某種聽覺效果,在語言使用中的集中體現便是擬聲詞的運用。利用語音象似,能夠加強語言的直觀性、形象性與生動性,在詩歌中使用還能夠進一步增強詩歌的節奏感,是詩歌創作中重要的修辭手段。象似性不僅普遍存在于日常語言的各個層面,而且對于詩歌語言而言,象似性是它的重要規則,并被強調為制約詩歌篇章結構的原則之一[2](P5-21)。兒歌作為一種詩歌,除具有文學性外,還具有一定的音樂性,其音樂性的體現除了詩歌本身的韻律之外,還包括語音象似的運用,具體則表現為擬聲詞的使用。
擬聲詞,又稱“象聲詞”,是指模擬人或事物聲音的詞。它來源于擬聲造詞,是人們按照感知到的各種聲音,利用發音近似的符號進行摹仿而形成的詞語,主要是按照詞語的音義關系予以區分的。漢、英兩種語言在歷史文化背景、語言習慣及審美觀念方面存在差別,因而在擬聲詞的表達方式上也存在著較大的差別[3](P46)。就此而言,擬聲詞的英譯不僅是翻譯過程中的一個難點,同時也可以充分體現譯者的翻譯風格。與其他文體相比,兒歌的目標讀者群體為兒童,它的主體內容大多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人或事物,在創作時使用了較多的擬聲詞。《北京兒歌》[4]與《孺子歌圖》[5]雖然是同一時期的兩部兒歌集,并且有部分兒歌收錄一致,但在擬聲詞的英譯方面卻體現出不同的風格。本文將對兩位譯者擬聲詞英譯的翻譯策略、修辭效果進行深入探討,并在此基礎上,初步窺探兩位譯者的翻譯風格。
一、《北京兒歌》與《孺子歌圖》
《北京兒歌》(Chinese Folklore.Pekingese Rhymes)由威達雷(Baron Guido Vitale,1872—1918)收錄整理而成。威達雷,亦譯為衛太爾、韋大列、威大列。他是晚清意大利外交官,曾于1893—1899年擔任駐華使館翻譯,其間于1896—1897年兼任代辦;1899—1915年任漢文正使[6](P139)。威達雷頗具語言天賦,精通漢語,水平極高。正是由于漢語極為出色,威達雷在1900年被東方學院院長吉拉爾多·德芬蒂斯教授聘為中文教師。
《北京兒歌》,亦譯為《北京童謠》《北京歌唱》《中國民俗》《中國民間傳說》等。該書初版于1896年,由北堂(Pei-T’ang Press)出版發行。《北京兒歌》收錄了北京地區的童謠170首,共235頁,包括封皮、扉頁、前言(Preface)、索引(Indes)、正文(Pekingese Baby-Songs)等;其中,正文主要由三個部分組成,即中文原文、注釋(Notes)與翻譯(Translation)。它是最早由外國人收集、整理、翻譯的北京兒童歌謠集,對中國上一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民俗研究產生過很大影響。早在北京大學歌謠運動時期,威達雷與《北京兒歌》就被時人多次提及。胡適在1922年所作的《北京的平民文學》一文中,曾評價說:“衛太爾男爵是一個有心的人,他在三十年前就能認識到這些歌謠之中有些‘真詩’,他在序里指出十八首來做例,并且說,‘根據在這些歌謠之上,根據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種新的“民族的詩”也許能產生出來呢?’”[7](P323)
《孺子歌圖》(Chinese Mother Goose Rhymes)是由美國傳教士何德蘭(Isaac Taylor Headland,1859—1942)收集整理而成的。何德蘭為美國美以美會傳教士,1888年來華,曾任北京匯文書院文科和神科教習。他與晚清上層社會頗有接觸,多次為光緒進行英文翻譯工作并提供西方書籍。何德蘭十分關注晚清時期中國人的生存狀態及宮廷生活,著述很多,主要有《中國的英雄》(Chinese Heroes)、《慈禧與光緒:中國宮廷中的生存游戲》、《晚清宮廷見聞錄》(Court Life in China)、《中國的新時代:對導致其到來之諸大事件的研究》(China’s new day:A study of events that have led to its coming)、《中國的男孩與女孩》(The Chinese Boy and Girl)、《中國的家庭生活》(Home Life in China)、《中國童謠》(Chinese Rhymes for Children)等。
《孺子歌圖》于1900年由美國紐約的黎威勒公司(Fleming H. Revell Company)出版發行。全書共收錄了138首兒歌,共162頁,包括封皮、百子圖、前言、正文四部分;其中,正文中的每首兒歌均由四個部分組成,即中文原文、英文標題、英文譯文與插圖。何德蘭十分重視北京兒歌的文化價值,并把它們忠實地記錄下來,對保留北京歷史民俗文化作出了貢獻。現代民俗學者常惠曾對《孺子歌圖》大加揄揚:“一本在1900年出版的,共有152首歌謠,是一位美國女士所輯①,不但有中文,還有譯成英文的韻文,而且還有極好的照相,很能把二十年前北京的社會狀態表現出來,這是我最喜歡看的。”[7](P335)
二、北京兒歌中擬聲詞的英譯策略
漢語中擬聲詞自成一類,英語中則沒有獨立的擬聲詞存在,往往由名詞、動詞、副詞等充當。同時,由于中、英文化的不同,對聲音的具體摹擬方式也存在著很大差異。因此,在翻譯過程中,擬聲詞的翻譯可以稱作是一大難點。關于擬聲詞的英譯,張培基曾提出二分法:第一種是漢語原文使用擬聲詞,英譯也用擬聲詞;第二種是漢語原文無擬聲詞,但在英譯時使用擬聲詞。之后,作者又針對各語言之間的復雜情況,指出翻譯中可以創造擬聲詞[8](P12)。胡曙中沿用了張培基的觀點,將擬聲詞翻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保持擬聲詞,第二類是一種語言用擬聲詞、另一種語言不用擬聲詞[9](P373)。李定坤則把擬聲詞翻譯分為四類:一為原文摹聲,譯文也摹聲;二為原文用摹聲詞,譯文不用摹聲詞;三為原文中不用摹聲詞,翻譯時可以運用摹聲詞;四是創造新的摹聲詞[10](P612)。這實際上是對張培基的擬聲詞翻譯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既考慮到擬聲詞的語法意義,也考慮到創造擬聲詞或增加擬聲詞的情況。
通過對《北京兒歌》與《孺子歌圖》中的擬聲詞統計,可以發現,《北京兒歌》中共出現了29個擬聲詞;《孺子歌圖》中則出現了16個擬聲詞。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部分兒歌在《北京兒歌》與《孺子歌圖》均有收錄,因此,共有8個擬聲詞重合。在分析各個擬聲詞所采用的翻譯策略時,我們主要是基于李定坤的擬聲詞翻譯理論,并結合北京兒歌的英譯實際,將擬聲詞翻譯策略分為四類:“對譯”“省略”“補償”和“創新”。
(一)對譯
這里的“對譯”指的是原文摹聲,譯文也摹聲。這一翻譯策略在《北京兒歌》中有3例,在《孺子歌圖》中則只有1例。例如:
(1)咩咩羊/跳花墻(《北京兒歌》)
The bleating small sheep — has jumped over the flowery wall
(2)咩咩羊/跳花墻(《孺子歌圖》)
It jumped the chequered wall,
The bleating little lamb.
(3)干兒①穿著厚底兒鞋/走一步/格登登(《北京兒歌》)
our adopted mother has shoes with a thick sole — at every step — the creaking is heard
例(1)、例(2)中,擬聲詞“咩咩”與“bleating”均作定語,并且所摹擬的聲音基本一致;例(3)中,“creaking”指的是木板等嘎吱作響的聲音,與“格登登”所摹擬的聲音基本相同。這一英譯策略的使用,能夠直接營造出真實的情境,給人一種身臨其境、如聞其聲的感覺。
(二)省略
這里的“省略”指的是原文摹聲,譯文不摹聲。這一翻譯策略在《北京兒歌》中有7例,在《孺子歌圖》中則只有1例。例如:
(4)兩個小鬼溫兒哇溫兒哇吹號兒(《北京兒歌》)
two small devils blow the trumpet
(5)門兒敲得梆梆(《北京兒歌》)
People knock at the door
(6)狗兒汪汪看家(《孺子歌圖》)
The faithful old watch-dog looks after the house
例(4)中,威達雷在翻譯時,直接省去吹號的聲音“溫兒哇”;例(5)中,亦未譯出表示敲門聲的“梆梆”;例(6)中,何德蘭同樣沒有譯出狗吠聲“汪汪”。總的來看,“省略”這一策略的運用,往往會使譯文喪失原文的音樂感與節奏感,尤其是對于兒歌這種本可和曲調歌唱的文本而言。
(三)補償
這里的“補償”,與李定坤所說的“原文沒有摹聲詞,譯文運用摹聲詞”有所不同,它指的是在無法實現擬聲詞對譯的情況下,譯者采用其他方式而進行的說明。我們知道,不同語言之間的擬聲詞系統、聲音特點及它們所承載的文化內涵存在較大差異,漢語系統中的一些擬聲詞,在英語系統中并沒有與之對應的,這時,譯者大多采用譯文補償的策略,對擬聲詞的修辭效果進行彌補。這種翻譯策略在《北京兒歌》中有14例,在《孺子歌圖》中有10例。例如:
(7)楊樹葉兒/嘩啦啦(《北京兒歌》)
The poplar leaves — are stirring
(8)駱駝駱駝噻噻/王八是你哥哥(《北京兒歌》)
Camel, camel, kneel down — a turtle is your older brother
(9)三聲爆竹響叮當(《北京兒歌》)
then three volleys of crackers with a great noise
(10)門兒敲得梆梆(《孺子歌圖》)
Someone is knocking loud at the door
(11)小孩兒在屋里嘎嘎拉拉(《孺子歌圖》)
The baby is crying,
But no one is heeding.
(12)鼓鼕鼕坐大轎(《孺子歌圖》)
Beat the drum, beat the drum,
See, the chair is coming.
例(7)中,譯文通過“stirring(微動)”,來代替楊樹葉兒被風吹動時所發出的嘩啦啦的聲響,即通過標明動作來代替摹聲,例(11)、例(12)均屬于這種情況。例(8)中的擬聲詞“噻噻”本為命令駱駝跪下的指令,譯者直接譯出了指令的內容,即以目的來代替摹聲。例(9)中,爆竹聲“叮當”則被譯為“a great noise”,直接指出“叮當”這一聲音的特征——響聲大,即通過聲音特征來摹聲,例(10)也屬于這種情況。可以說,這一英譯手法的使用,雖然準確地傳達了兒歌的內容,卻同樣失去了兒歌本身所具有的音樂感。
(四)創新
眾所周知,譯者并不是被動的,翻譯也不是一字一句進行對譯的機械操作。也就是說,譯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具有主動性,在符合翻譯的基本規則的前提下,可以進行適當的創新。由于擬聲詞在各個語言系統中并不是完全對應的,因此,常常會出現漢語有而英語中沒有的情況。這時,為了更好地傳達出擬聲詞的修辭效果,有必要創造新的形式。這一翻譯策略在《北京兒歌》中有5例,在《孺子歌圖》中有4例。例如:
(13)走一步/蹋拉拉(《北京兒歌》)
As she advances a step — it sounds t’alalà
(14)大肚子的蝦蟆/哇兒呱哇兒呱的叫(《北京兒歌》)
and the toads with big bellies — cry kurkuà kurkuà
(15)花樹樹嗡嗡嗡(《孺子歌圖》)
A red pepper flower,
Ling, ling, ling.
(16)蝦蟆說什么起來/起來格爾瓜格爾瓜(《孺子歌圖》)
What is he saying there on the rock?
Get up ,get up; ke’rh kua, ke’rh kua.
例(13)中的“蹋拉拉”為走路的聲音;例(14)與例(16)中的擬聲詞“哇兒呱”與“格爾瓜”,摹擬的均是蛤蟆的叫聲;例(15)中的擬聲詞“嗡嗡嗡”,則是無意義的音節,是對兒歌誦唱者所哼唱曲調的文字記錄,并無實際內涵。這幾個擬聲詞的翻譯都是譯者根據聲音特點,選取英語的音素進行組合而創造出來的,生動形象地傳譯出原文的聲音效果,不僅帶給讀者以強烈的現場感,而且保留了兒歌的韻律美。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翻譯策略可能會造成譯文語義理解的困難。
三、《北京兒歌》與《孺子歌圖》英譯比較
通過上文的分析,可以得知,《北京兒歌》《孺子歌圖》在對擬聲詞進行翻譯時,均運用了對譯、省略、補償、創新的翻譯策略,但在具體使用中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具體如表1所示:
上文曾經提及,在《北京兒歌》和《孺子歌圖》所收錄的擬聲詞中,有8個是相同的。通過對這8個擬聲詞翻譯的考察,不僅能夠進一步分析兩位譯者在擬聲詞翻譯方面的特點,還能夠在這一基礎上,窺見兩位譯者的翻譯風格。這8個擬聲詞譯文的比較,具體如表2所示:
之所以會出現上述現象,從本質上來說,它是由兩位譯者的翻譯理念和翻譯宗旨所決定的。威達雷在《北京兒歌》的前言中指出:“After the work of collection, came the work of explanation and translation which was not always easy. The people who spoke the words often were not able to give me light on the difficult points. When pressed by me they suggested something and I picked up what looked more truthlike and reasonable; never did I force or prefer views of my own.”[4](PVII)其中文大意是:“在收集工作結束之后,進行了解釋和翻譯的工作,這些工作并不總是那么容易。傳唱兒歌的人經常無法解釋疑惑點。當我進一步追問時,他們提出了一些看法,我選擇了看起來更真實,更合理的解釋;從來沒有強加或更喜歡我自己的觀點。”何德蘭則指出,他在翻譯時盡可能再現原文的意思,“The child, not the critic, has always been kept in view”[5](P80)。可見,何德蘭的兒歌翻譯始終將兒童放在重要位置,是以此來取悅目的語兒童的,而非評論家。
綜上所述,本文對威達雷《北京兒歌》與何德蘭《孺子歌圖》中的擬聲詞英譯策略進行了分析與描寫。通過擬聲詞英譯策略的比較,可以發現,威達雷傾向于遵照漢語原文來翻譯,何德蘭則更加注重含義的傳達與韻律的一致。需要指出的是,這一結論只是在比較兩位譯者對于擬聲詞翻譯的基礎上得出的,還需通過更加細致的分析予以驗證。兩位譯者的翻譯風格之所以會呈現出這樣的差異,其背后的原因也值得進一步探究。還需指出的是,除了語音象似之外,順序象似、數量象似、對稱象似等,在漢語兒歌中也多有體現,關于它們的翻譯問題也有待學界深入探討。
參考文獻:
[1]沈家煊.句法的象似性問題[J].外語教學與研究, 1993,(1).
[2]Hiraga,M.K.Diagrams and metaphors:Iconic aspects in language[J].Journal of Pragmatics,1994,(1).
[3]彭家玉.漢英擬聲詞異同比較研究[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1999,(4).
[4][意]威達雷.北京兒歌[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5][美]何德蘭.孺子歌圖[M].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6][意]米歇爾·法帝卡.意大利《論壇報》中威達雷關于義和團的報道[A].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清史論叢(2002年號)[C].北京:中國廣播影視出版社,2002.
[7]胡適.北京的平民文學[A].胡適.胡適文存二集卷四[C].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
[8]張培基.英語聲色詞與翻譯[M].北京:商務印書館, 1979.
[9]胡曙中.英漢修辭比較研究[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3.
[10]李定坤.漢英辭格對比與翻譯[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