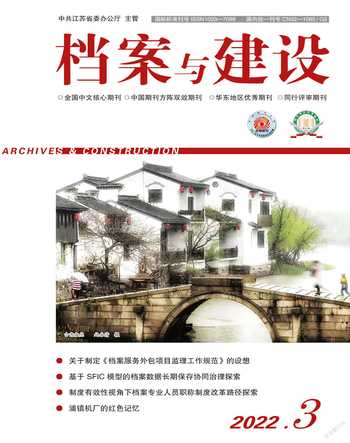信仰與秩序:1935年徐州城隍信仰風波探微
劉晗 王亞民
摘 要:民國時期的徐州,城隍信仰已然融入了民眾的日常生活并形成一種共有習慣,既具有滿足民眾日常需求的工具效用,亦起到了穩定基層秩序的“安全閥”作用。銅山縣基層官員忽視民眾日常生活中精神與物質的雙重需求,違背上級不得“驟行廢除”的指示,做出了燒毀神像之舉,導致官民之間發生嚴重沖突。官府對傳統信仰習俗的改造不應采取激進手段,而應將民眾的基本訴求作為解決問題的核心。
關鍵詞:民國徐州;城隍信仰;官民沖突;基層秩序
囿于階級與思維邏輯的差異,民間城隍信仰常被民國的書寫者以自身經驗出發,冠以“愚昧無知”之名,民國時期徐州地方政府亦是如此。目前,學界對于民眾視域下的研究相對薄弱,故拙文在解讀多種原始文獻的基礎上,從社會文化史角度出發,結合民眾心理與官府行為,力圖就“1935年徐州城隍信仰風波”略加探析,進而揭示其背后的內在邏輯。
一、 城隍信仰習慣的形成與民眾日常生活
徐州城南門外一里(舊城隍街)的城隍廟,相傳為奉祀漢臣紀信之址。至明清時期,城隍已作為國家祭祀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掌控人民,“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為”。[1]
隨著生產力發展,廟會的宗教功能逐漸向商業功能轉移。徐州民眾形成了“有神必拜,拜則成會”的風俗,每逢年關,“聚眾賽會,鑼鼓喧天,鬧市招搖”,[2]游人成千數萬,舞獅雜耍,宗教表演,應有盡有,頗有一番繁華景象。城隍廟周圍的店鋪尤受其利,逐漸形成以城隍廟為中心的商業街道。據調查,在徐海地區90處廟會中,交易買賣與游藝娛樂的比重占61%,而求神拜佛僅有23%,曾經商業對象“大部分不過是城鎮里一般的市民”,[3]而鄉村的定時市集逐漸與廟會相融合,逐漸變成了交易什物之所。由此,廟會成為了緩解農村破產壓力的必要途徑,城隍廟亦演化為民眾日常生活重要的公共空間。
總體看來,城隍廟會被賦予了宗教、商業與娛樂三大功能,在民間信仰根深蒂固、娛樂相對匱乏的民國時期,城隍廟會起到緩解民眾生存精神壓力之作用。在官方與民間的雙重促進之下,城隍神已然深入徐州區域的社會文化之中,幾成當地文化符號。
二、 城隍信仰風波與官方的話語書寫
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思想漸入人心,故而提出“(前清祀典)凡涉于迷信者,應行廢止”。[4]此后,在西學東漸與新思潮的加速傳播下,徹底消除舊信仰、構建新社會成為民初政治的重要議題。民國元年(1912),粵軍在克復徐州后“為破除民眾迷信起見”,即毀除兩廊神像,但城隍“幸未遭及”,事后該廟經過民眾修葺,仍于朔望與會期“香煙繚繞”。[5]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力求破舊立新,“反迷信”亦被規劃進國家制度建構體系之中。南京國民政府聲稱,祀神禮節系“人同獸爭、人同天爭之余毒”,迷信民眾將會“錮蔽其聰明、貽笑于世界”。[6]在地方黨部的積極推動下,各地的破除迷信運動如火如荼。北伐軍二次光復徐州(1928)時,國民黨銅山縣黨部在“破除迷信,彰揚黨義”的旗幟下,分兩路搗毀了該廟,將大殿改為總理紀念堂,余則用作公安局消防隊駐所與教練所之講堂。
1930年,南京國民政府呼吁“在科學昌明時代,城隍實無存在之必要”,[7]飭令各市縣公安局“隨時勸導人民破除迷信”,[8]城隍神亦在被廢之列。表面上,徐州舊時城隍神早已在北伐軍破除迷信聲浪中灰飛煙滅,但城隍廟的主持道士卻暗將神像移至西關的城隍行宮中,并重塑金身。平日有附近民眾組成燒香會,對城隍神進行拜祀。
1935年正月,鄉間民眾“靜極思動”,城隍競賽又在遠近各莊及城廟展開。此次迎神賽會上各種表演及游戲如跑旱船、大頭娃娃舞、舞獅、踩高蹺等層出不窮。有報道稱,此歡鬧場景實乃多年不遇,街市人聲鼎沸,熱鬧非凡,城隍巷內終日“幾無立足之地”。[9]
力主革除封建迷信的銅山縣縣長王公玙聞城隍復活后,驚愕道“竟有人開倒車”,遂以影響治安、關系地方秩序為名,授意騎兵分隊隊長郭玉標封鎖各要道,以隔絕民眾,并令西關鎮長程子良于二月十五日夜[10]實施了燒毀城隍神像的計劃,城隍木像在主持道士“哭天搶地,苦苦哀求”聲中被焚為灰燼。
1928年北伐革命軍破除城隍時,民眾不過“燒香焚銖詛咒”抑或“淚涔涔下”,而無實際之反抗。然而,此次事件發生于正月,民眾恰有余暇,又在奉祀神像與開展廟會的熱情高漲之時,故而民眾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積聚起巨大的反抗動能,這顯然是銅山縣府始料未及的。
民眾對于地方政府的抵抗分為兩個階段,即風潮開始時公開的、有組織的暴力抵抗,游行示威與打砸鎮公所,后期有意無意地制造輿論,實施間接反抗。從“有聲”到“無聲”,反映了民眾在與地方政府博弈時不同的反抗形式。
在第一階段,民眾得知城隍神像被焚后,即組織了數千人的示威運動。保甲長先行辭職,交出甲牌以作抵抗。“保甲長尤為接近民眾,直接影響民眾的地方更多,改造風氣,轉移人心的力量更大”,[11]由此有力地推動了風潮的發展。
隨后,城隍信眾所組成的燒香會“加以擴大”并暗攜武器,試圖與政府對抗,以燒香會為代表的民間宗教組織迅速轉化為抵抗的有生力量。信眾認為政府燒毀城隍神像的行為,“已犯神怒,以后人民生活將更臻困苦”,因而認為政府此舉,實系故意為民“召禍”,[12]漸由信仰對立逐漸上升至官民對立。民眾高呼“城隍能焚,鎮長亦可焚”,[13]隨即沖入鎮長程子良家中,“喝令打倒”,并質問,欲破除迷信緣何鎮長家中仍供奉祖先?遂將程家三代祖龕肆意“滿涂糞污”,以作羞辱。“一時萬眾喧囂,西關一帶,途為之塞”,[14]程子良在護衛之下逃往縣府躲避。
在浩大而激昂的抵制行動中,民眾不斷對縣府進行施壓,要求交出縱火鎮長。同時,各種“迷信游藝”層出不窮,街市一時“鳴炮示威、鑼鼓喧天”,縣府雖然抓捕數人但旋即釋放,萬般無奈之下只得派出軍警維持秩序。民眾不畏強暴,進而提出重塑泥像、“令兩鎮長奉祀,并革其鎮長職”的訴求。
在抵制運動的后期,憚于傳統政治權威,民眾采取分化戰術,即將縣政府與涉事官員相分離,將主要矛頭對準涉事官員,給縣政府留有周旋的余地。其標志是,坊間開始傳聞,程子良于年前向該廟道士借洋二百未遂,此次事件只是出于私心,假借破除迷信而企圖報復。無論該事件是否真實,民眾通過匿名手段施加輿論壓力,借以要求嚴懲“罪魁禍首”鎮長程子良。地方民眾非暴力的反抗形式不僅達到打壓政府之目的,更有效地規避了公開抗爭所受處罰的風險。
此次風潮持續了數日,參與民眾達數萬人,地方仍以破除城隍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為借口,堅稱“系奉省令”“迎神賽會尤在嚴禁之列”,直至縣長王公玙答應對程子良調查處理后,又經“數日疏導,示威群眾方告平息解散”。
作為處理城隍信仰風潮的主要官員,王公玙所載此次事件與之前所述迥然不同。他將此次風潮的發生全然推諉于地方黨政內部“相互傾軋”“壁壘分明”,自稱“兼顧不易,取舍尤難”,直言“此番陽借迎神之名,實含有黨爭意義在內”。[15]
王氏認為民眾之所以暴動,在于西關鎮長程子良在迎神賽會前夕藏匿城隍頭像,民眾以“無頭之神既不可迎,即遷怒于該鎮長”。[16]他指出,1935年春的迎神賽會是有“同志”在其中攛掇,又得到津浦路警備司令王均的支持,程子良“原系某一派系斗士,為敵對者所仇視”,[17]亦反對迎神賽會,因而被“政敵”借刀殺人。
這次風潮的主要處理者是縣長王公玙,“推諉”與“掩飾”不得不說是其世故的表現。他在自述中使用“據傳”“嗣知”等模糊性的字眼,一方面旨在與程子良劃清界限,另一方面則試圖掩飾風潮的某些真相。他在自述中建構了虛擬事實,將風潮的導火索由“燒”改為“藏”,暗示民眾對于“藏”反應強烈,順勢將風潮的責任轉嫁于“愚昧無知”“蠻橫無理”的民眾,試圖掩蓋縣府破除城隍計劃的紕漏以及對城隍信仰風潮帶來的惡劣影響。
三、 城隍風波背后內在邏輯的深層分析
首先,信仰的“社會安全閥”功能失效致使風潮發生。民國時期的徐州地區,“第以連歲天災人禍相逼而至,農民生計困苦極矣”。[18]通常情況下,生活極為困苦的徐州民眾并未“揭竿而起”,而是將“城隍”作為其心靈寄托。此時的城隍信仰已然被賦予了“社會安全閥”之職能,是防止地方社會秩序失范的一道精神屏障,其安全閥功能如若失效,民眾的不可控感隨之出現并加深。從表象看,徐州城隍信仰風波是民俗信仰與政府治理的沖突,但若尋其根本,沖突則是生存壓力與官民矛盾長期積壓的具象化。“土地之集中”“賦稅之畸重”“田賦之增高”“高利貸”“幣值及度量衡之紊亂”“水利的廢弛”“匪患”[19]等等,直接導致徐州地方民眾長期處于壓抑與緊張的狀態,而民眾的精神壓力本可通過城隍信仰活動中的“進香”“祈禱”“賽會”等予以排解。同時,廟會中的農貿活動亦可舒緩民眾物質方面的壓力,一旦內生于民間社會的城隍信仰活動被革除,而外部又無有效渠道予以接替,那么疏解緊張情緒的安全閥門即被阻塞,演化為現實中的民眾風潮。
其次,官方過激的反迷信行為與民間信仰習俗的尖銳對立,導致“除舊布新”無法實現,反而引發劇烈的社會沖突。隨著清王朝的土崩瓦解,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在“反迷信”“現代國家建構”話語下,提出宗教“妨礙國民塑造獨立自主的態度”,然而,民間信仰根植于地方社會文化,與民眾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故而在反迷信運動中受到了來自地方信眾的強大阻力。在數百年歷史中,徐州城隍信仰逐漸臻于一種地方性習俗,官府驟然強力地以“反迷信”方式將其破除,無疑會導致官民沖突,繼而引發社會秩序的混亂。
銅山縣政府破除城隍神廟的過程中,以下幾點值得注意:其一,在破除迷信的政策上,南京國民政府雖然明令取締城隍之地位,但也僅限于“見諸佛經”的虛妄而無歷史淵源的神祇,徐州城隍神以紀信為原型,不在破除之列。其二,在破除迷信的具體實施上,國民黨江蘇省黨部提出緩進的策略,若“驟行廢除,不但啟民眾誤會,亦且易滋糾紛”。[20]其三,在對待民眾的態度上,國民黨中央民運會制定的《民俗改善運動大綱》明確要求,“以誠懇和善之態度糾正民眾不良習俗”,抑或加以勸導,“使其停止或乘機改變其集會之意義”。[21]顯然,銅山縣政府未采取緩進策略與“誠懇和善”的態度,這無疑使民眾陷入了政府“招禍”的錯覺中,是引發城隍信仰風潮的原因之一。
最后,通過透視廟會的宗教職能向商業與娛樂職能的轉變,可以發現徐州城隍廟以及周圍地界已然變為重要的商業空間;再者,“天災之外,同時還有橫征暴斂之軍閥貪官與重租重利之劣紳地主,層層剝削”,[22]徐州民眾通過游藝表演等,已然將其作為轉嫁心理壓力的主要娛樂形式。徐州官府外部強制性的文化改造,不僅阻斷了地方社會文化發展的進程,更與內生的民間信仰相抵牾,弱化了地方政府執政權力的合法性與持續性。
注釋與參考文獻
[1](明)呂本:《明寶訓》(卷四),明萬歷刻本,第14頁。
[2][9]《徐埠破除迷信》,《中央日報》1935年2月20日,第6版。
[3]楊汝熊:《徐海十二縣廟會調查報告》,《教育新路》1933年第23期,第2頁。
[4]《內務教育二部為丁祭事會同通告各省電文》,《臨時政府公報》1912年第32期,第11頁。
[5]莘盫:《粉身碎骨之城隍老爺》,《申報》1928年5月22日,第21版。
[6][7][8]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 第一編 文化(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06、503、514頁。
[10]《新聞報》《時報》言系二月十五日焚毀,《中央日報》及其他言為二月十六日夜焚毀。本文取二月十五夜為焚燒時間。
[11]徐西明等編:《保甲長須知·序》,銅山縣保長訓練所1935年版,第1頁。
[12]悟生:《徐州城隍風潮詳記》,《福爾摩斯》1935年2月27日,第2版。
[13]《徐州西關鎮長焚毀城隍 民眾反對到縣府示威》,《大公報(天津)》1935年2月18日,第4版。
[14]《徐州西關兩鎮長宅被搗》,《申報》1935年2月18日,第3版。
[15][16][17]王公玙:《畸園殘稿》,新文化彩色印書館1984年版,第214頁。
[18]《徐屬農村生活調查》,《中央日報》1932年9月6日,第6版。
[19]吳壽彭:《逗留于農村經濟時代的徐海各屬》,《東方雜志》1930年第27卷第6期,第77頁。
[20]《黨務:打毀神像與破除迷信問題》,《江蘇省政府公報》1928年第64期,第47頁。
[21]《民俗改善運動大綱》,《教育部公報》1934年第6卷第19-20期,第37頁。
[22]潤之:《江浙農民的痛苦及其反抗運動》,《向導》1926年第179期,第18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