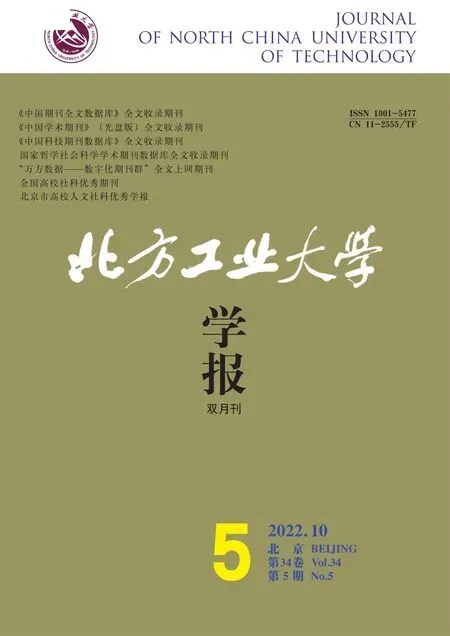正氣沖天地,丹心映雪峰*
——魯迅與馮雪峰
陳漱渝
(北京魯迅博物館,100034,北京)
1942 年,有蘇聯友人向許廣平提出了26 個問題,后來整理成文,題為《研究魯迅文學遺產的幾個問題》,發表于1945 年10 月19 日重慶《新華日報》出版的“魯迅逝世九周年紀念特刊”,后收入許廣平《欣慰的紀念》一書。 其中的第22 個問題是:“在現代中國作家中,誰是被認為先生文學遺產及其手稿最優秀的通人?”許廣平認為這個問題“實在難于回答”,但明確表示:“而自到上海以后,(一九二七至三六年)的十年間,以馮雪峰比較可以算是他的通人。”
1 “先生,你可以這樣做”
魯迅作品問世以來,影響了無數國內外讀者,但能對魯迅施加影響的人,還真是寥寥可數。不過,在魯迅生命的最后10 年,馮雪峰的確對魯迅施加了影響。 他不僅建議魯迅做這樣那樣的工作,而且竟能對魯迅的手稿提出修改意見,甚至代魯迅立言。 許廣平在《魯迅和青年們》一文中有一段真實而生動的描述:
F 說:“你可以這樣這樣的做。”先生說:“不行,這樣我辦不到。”F 又說“先生,你可以做那樣。”先生說:“似乎也不大好。”F 說:“先生,你就試試看吧。”先生說:“姑且試試也可以。”于是韌的比賽,F 目的達到了。
這里所說的F,即指馮雪峰。 魯迅之所以最終接受馮雪峰的意見或建議,不僅因為他“人很質直,是浙東人的老脾氣”,更由于魯迅認為,“站在政治立場上,他是對的”。[1]
嚴格地說,馮雪峰是魯迅的學生。 早在1922年4 月,馮雪峰跟他的詩友就聯名給魯迅寄贈了他們的第一部新詩集《湖畔》。 1925 年春,22 歲的他曾在北京大學旁聽過魯迅講課。 1926 年,他給《莽原》半月刊投寄了一篇譯文,是日本作家森鷗外的短篇小說《花子》,魯迅曾予校改。 同年8月5 日,他曾到北京阜成門內宮門口二條19 號拜訪,想請魯迅幫忙在北新書局出一個小刊物。魯迅當時正準備南下,便告訴他,北新的老板李小峰對此沒有興趣,馮雪峰匆匆告辭,未及深入交談,魯迅連他的名字都沒有記住。
雪峰跟魯迅的親密交往開始于1928 年12月9 日,引薦者是雪峰在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的同學柔石。 柔石跟雪峰等文友曾在1921 年組建了學生文學社團晨光社,1928 年1 月柔石又跟魯迅等人成立了朝花社,以介紹歐洲文學、輸入外國版畫為宗旨,因此就自然而然成了魯迅跟雪峰交往的牽線人。 魯迅跟初相識的人多不愿深談,深化他跟雪峰情感的是那套《科學的藝術論叢書》。 “科學的藝術論”即指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 雪峰原想編輯12—16 種這方面的著作,由他朋友劉吶鷗開辦的水沫書店和沈松泉開辦的光華書店出版。 他跟魯迅、戴望舒等擬定了一個書目,并邀請夏衍、馮乃超、朱鏡我等左翼作家加盟。 但由于種種原因,特別是國民黨當局的查禁,這套書最終只出版了8 種,其中即有魯迅翻譯的《文藝與批評》(盧那察爾斯基)、《文藝政策》(蘇聯文藝政策文件匯集)、《藝術論》(普列漢諾夫)。 馮雪峰翻譯的共4 種:《藝術之社會的基礎》(盧那察爾斯基)、《社會的作家論》(沃洛夫斯基)、《藝術與社會生活》(普列漢諾夫)、《文學評論》(梅林)。 此外還有一種,是蘇汶翻譯的《新藝術論》(波格丹諾夫)。 今天重讀,當然不難發現書中理論的歷史局限,以及譯文的晦澀難懂,但正是這套讀物,為中國左翼作家提供了精神武器,恰如為起義的奴隸竊來了軍火。 在翻譯這套書的過程中,馮雪峰確立了他的唯物史觀,懂得了文藝必須反映現實,并跟人民的革命實踐結合在一起。 魯迅也是在閱讀并譯介這批讀物的過程中,“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并且糾正了他此前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2]
早在跟雪峰交往之前,魯迅結交的文藝青年中有一些就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但他們大多是以個人身份跟魯迅接觸,魯迅也并不一定了解其政治身份。 馮雪峰則不然。 他是1927 年6 月入黨的老黨員,正式跟魯迅聯系之初是中共上海閘北區委所屬第三街道支部(簡稱“文化支部”)的成員。 他跟魯迅等籌辦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以下簡稱“左聯”)及左翼文學刊物都是奉黨組織之命,其直接領導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干事兼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潘漢年。 1931 年2 月,28 歲的雪峰調任“左聯”黨團書記,翌年2 月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書記;同年12 月調任中共中央局宣傳干事,除繼續領導文委之外,還管理一個對外提供宣傳資料的通訊社,直接受張聞天領導。 1933 年6 月,雪峰擔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兼管文委工作,受上海中央局領導,直到1933 年12 月中旬奉調中央蘇區工作。 所以,雪峰名副其實是溝通中國共產黨跟魯迅關系的一座橋梁,雪峰和魯迅之間的關系超越了個人交往的范圍。 1936 年4 月下旬,馮雪峰以中共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從陜北瓦窯堡到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帶給魯迅一幅高50.5 厘米、寬34 厘米的唐卡作為見面禮。 這是長征經過四川彝海鎮時彝族首領小葉丹送給他的,名為“大成就者東必巴”,十分珍貴。 雪峰的直接領導是周恩來和張聞天,所以那時魯迅對于文藝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意見,更是反映了當時陜北中共中央對這一重大政策的認識和意見。 周揚等人提出“國防文學”口號的政策依據,則來自王明主持起草的《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簡稱《八一宣言》),而王明起草《八一宣言》又是根據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并征得了斯大林的同意。[3]在世界各國都面臨的重大歷史轉折關頭,反法西斯是人類共同的首要任務。在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問題上,中國共產黨高層并沒有不同意見,但對于如何結成統一戰線,在政策上一度有不同認識,在策略上也前后作過一些調整,有過從“反蔣抗日”“逼蔣抗日”到改組工農紅軍的階段性變化,因此曾經產生意見分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36 年8 月上旬,中共上海辦事處成立,主要任務是統戰工作和情報工作,潘漢年任主任,雪峰任副主任,主要做黨的組織和文藝界的工作。
雪峰對魯迅后期的思想和創作產生了哪些具體影響呢?
首先,雪峰直接把魯迅推到了左翼文壇盟主的位置。 魯迅在國內外讀者中的深遠影響當然取決于其作品本身,并非人為制造的偶像,但對魯迅的認識有一個不斷深化過程。 中國左翼作家曾對魯迅尊重不夠,甚至發生了后期創造社和太陽社聯手“圍剿”魯迅的情況,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不爭的事實。 直到1928 年9 月25日馮雪峰在文學半月刊《無軌列車》上發表《革命與知識階級》一文,才首次從分析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革命特點的高度,指出在中國的知識階級中,魯迅是在跟封建勢力斗爭方面做得最好的作家。 雖然魯迅一度對這篇文章產生過誤解,雪峰事后也再三反思,說他在此文中將魯迅定性為“同路人”,“是受當時蘇聯幾個機械論者的理論的影響”,但其主要矛頭明明白白是指向后期創造社和太陽社的宗派主義,被當時研究界視為對“革命文學論爭”所作的“很公正的結論”。 沒有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魯迅歷史功績的肯定,左聯的成立就缺乏必要的思想基礎。
左聯的成立并非雪峰的個人動議,而是根據當時中共中央宣傳部干事兼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潘漢年的具體指示。 中共黨史上的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雖然直到1930 年6 月才正式出臺,同年9 月即已終結,但這種“左”傾理論、政策和情緒早在1927 年的“八七會議”上即已冒頭,表現在中國革命處于暫時低潮的歷史條件下仍迫不及待地幻想革命高潮迅速到來。 所以,從1930年3 月—1931 年11 月,左聯基本上成了一個半政黨性的組織。 左聯成立后不久,“社聯”和“劇聯”相繼成立,都屬于“文總”領導。 “文總”將黨的方針政策和決定下達到左聯,通過雪峰跟魯迅商量。 據茅盾回憶,“左聯成員當時要參加示威游行,飛行集會,寫標語,散傳單,到工廠中做鼓動工作,以及幫助工人出墻報,辦夜校等”,唯獨不重視創作。 “左聯成員也像共產黨員那樣編成小組,小組成員還經常變換。”[4]
魯迅對于左聯“左”的理論和做法并不認同。當馮乃超將他起草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理論綱領》請魯迅審閱時,魯迅僅說了一句“這種文章我寫不出來”。 魯迅不僅沒有參加左聯成立初期組織的那些過激的政治活動,而且當時黨的最高領導人李立三希望魯迅發表宣言擁護他的政治主張時,魯迅當場拒絕,那次在上海爵祿飯店的會面成了“各談各的”。 魯迅明確表示:“弄政治宣傳,我到底不行的;但寫點雜文,我比較順手。”左翼成立時盟員大約50 人,其中有為革命獻身的“左聯五烈士”,也有蘇汶(杜衡)、楊村人這樣的政治轉向者,所以魯迅1930 年3 月27 日致章廷謙信中就談到左聯開始的基礎就不大好,其成員“皆茄花色”。 “茄花色”是紹興方言,形容淺紫帶白,表示并不怎么樣。
既然如此,魯迅為何仍然參加左聯并擔任執行委員呢?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舊社會的根柢原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它什么。 并且舊社會還有它使新勢力妥協的好辦法,但它自己是絕不妥協的”。[5]鑒于在肌體老化的中國進行改革的艱難,憑個人之力實難撼動舊社會的根基,必須培養大群的新戰士,充分發揮團體和戰線的力量,進行堅決、持久的斗爭。 這就是魯迅在1930 年代在雪峰等人的推動下不避政治風險參加左聯的原因。 魯迅跟左聯的大多數成員都朝著反帝反封建的同一大目標,但又保持了個人的原則性和獨立性;對內他又跟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劃清了界限。 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二集·〈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說得形象而又深刻:“文學團體不是豆莢,包含在里面的,始終都是豆,大約集成時本已各有不同,后來更各有種種的變化。”[6]
關于魯迅跟左聯的關系,馮雪峰做出了準確的評價:“魯迅先生晚年的主要戰斗都和‘左聯'相關聯,以‘左聯'的成員之一和它的領導者的姿態而進行的。”“在那時候,只要魯迅先生不垮,‘左聯'就不會垮。 只要魯迅先生不退出‘左聯',不放棄領導,‘左聯'的組織和它的活動與斗爭就能夠堅持。”[7]所以,既應該看到魯迅跟左聯的一致性,也應該承認魯迅跟左聯內部錯誤傾向的原則分歧。 不能因為魯迅的獨立性而否定他跟左聯的一致性,甚至提出有“兩個左聯”的新論——一個是“魯迅的左聯”,另一個是“黨的左聯”,而只應說,魯迅后期作品代表了左翼文學的健康方面和主流方面。 恰如不能因為《新青年》陣營既有李大釗,又有胡適,就提出有“兩個《新青年》”,也不能因為魯迅后來跟高長虹反目,就認為有“兩個莽原社”。 左翼作家聯盟的“左翼”二字是魯迅同意加上的,左聯的斗爭大目標是一致的。 馮雪峰的很多意見就代表了中共文化界地下黨的意見。 如果歷史上確實存在著兩個完全對立的左聯,那就無法解釋魯迅為什么會因為左聯在未發表宣言的情況下就自行解散而感到痛心乃至于憤慨!
2 幫魯迅寫文章,改文章
在左聯存在的6 年多當中,魯迅跟馮雪峰有過許多成功的合作。 除開編輯出版《科學的藝術論叢書》之外,雪峰還在魯迅的指導之下編輯過《萌芽月刊》(后改名為《新地月刊》)、《巴爾底山》旬刊、《現代文藝叢書》(共出版4 種)、《前哨》月刊(后改名為《文學導報》半月刊)……最為難得的是,雪峰曾為魯迅校訂譯稿、修改文稿,甚至為魯迅起草文章。
雪峰為魯迅校改譯文的事情見諸魯迅譯文集《文藝政策》的《后記》。 魯迅寫道:“第一,雪峰當編定時,曾給我對比原譯,訂正了幾個錯誤;第二,他又將所譯岡澤秀虎的《以理論為中心的俄國無產階級文學發達史》附在卷末,并將有些字面改從我的譯例,使總覽之后,于這《文藝政策》的來源去脈,更得分明。 這兩點,至少是值得特行聲敘的。”[8]
雪峰為魯迅草擬或筆錄的文章至少有4 篇:一是《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魯迅在左聯成立大會上的講話是即興發言,會前并無講稿,講時亦無記錄。 完全是雪峰根據自己的記憶,增補了魯迅平日談話的內容,整理成文,并經魯迅本人審定的。 這篇文章實際上是左聯的理論綱領和行動綱領,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篇劃時代的文獻。 二是《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寫于1936 年6 月9 日。 對于托洛斯基關于中國革命的論述,以及對中國托洛斯基派的歷史評價,當然有待入進行研究。 但這封復信是魯迅委托雪峰進行處理,并以魯迅本人的名義公開發表的,因此應該跟魯迅的其他作品同樣看待。 三是《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此文系雪峰按照魯迅的立場、態度和多次談話擬稿,并經魯迅本人審定。現已收入《且介亭雜文末編》的《附集》。 《附集》收文21 篇,都是魯迅臨終之前親自放進積稿堆中,準備日后收入他新編的文集。 四是《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此文是魯迅病重期間口授,雪峰筆錄,魯迅再加校改。 有人曾說此文都是雪峰的筆跡,魯迅只改了4 個字。 事實并非如此。 此文手稿現存北京魯迅博物館,在15頁原稿中,有4 頁約1700 多字(主要是批評“四條漢子”的部分)恰恰是魯迅親筆增補的,完全不存在雪峰“勾結胡風,蒙蔽魯迅,打擊周揚,夏衍,分裂左翼文藝界”的問題。 許廣平1957 年8 月14 日在中國作家協會黨組第十七次會議上憤怒地說:“魯迅不同意怎么發表了!? 發表以后魯迅有沒有聲明說這篇文章是雪峰寫的,不是我寫的? ……”
魯迅的文章不僅本人字斟句酌,有時還征詢雪峰的意見。 1932 年10 月10 日,魯迅寫了一篇《論“第三種人”》,對胡秋原向左翼文壇要“創作自由”的做法以及蘇汶自命為“第三種”人提出了批評。 魯迅認為,當時不自由、被查禁的是左翼文學,在壁壘森嚴的階級斗爭中也做不成這種超然世外的“第三種人”。 此文未刊前魯迅征詢雪峰的意見。 雪峰建議在文末添加“怎么辦呢?”這4 個字意在給蘇汶留條后路,望他迷途知返。 魯迅虛心采納了雪峰的意見,因為對于目前并不是敵人者,倘若疾聲厲色,可能會拒人于千里之外。
1936 年9 月5 日,也就是魯迅臨終約一個半月前,寫了一篇雜文《死》,留下了7 條遺囑,征詢雪峰意見。 雪峰提了兩條:一,在“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之后加了一句——“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這就顯得更完整,更具有人情味;二,在“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文學家或美術家”這一句中,加上“空頭”二字,即“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魯迅對“空頭”二字很滿意,笑著說:“這添加得好,只兩個字,就將這些人物刻畫得活靈活現了。 這就是住在上海的好處,看多了這類空頭人物,才能想得到這兩個字。”[9]魯迅修改臨終前不久寫的雜感《半夏小集》,也虛心聽取了雪峰的意見。 比如該文第七則談到他寧愿將自己的血肉喂獅虎鷹隼而一點也不愿給癩皮狗吃,結末一句原為:“但養胖一群癩皮狗,在世界上有什么用?”雪峰認為這樣表述缺乏抒情性,魯迅便欣然改為:“但養胖一群癩皮狗,只會亂鉆,亂叫,可多么討厭!”[10]魯迅幫助青年作家修改文稿的例證很多,但青年作家幫助魯迅捉刀代筆和潤飾文稿的例證實為罕見。
3 魯迅“通人”馮雪峰
在歷時一個多世紀的魯迅研究史上,馮雪峰的地位可謂無人能夠替代,影響可謂無人可以超越。 魯迅生前評論他的文章就已汗牛充棟,但被魯迅本人認可的,除了瞿秋白的《〈魯迅雜感集〉序言》之外,另一篇就是馮雪峰撰寫的《關于魯迅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1936 年7 月中旬,捷克漢學家普實克準備出版他翻譯的《魯迅短篇小說集》捷文版,希望魯迅親自作序,并推薦一篇論述魯迅文學地位的文章。 魯迅感到瞿秋白寫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太長,又專論雜文,便請雪峰趕寫一篇。 同年7 月20 日,雪峰寫了一篇兩千來字的短論《關于魯迅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魯迅審閱時,僅改了幾個錯字,刪去了一兩句,便謄抄付郵了。 魯迅改正的主要之處,是刪去了托爾斯泰和高爾基的名字。 魯迅說:“他們對我的影響是很小的,倒是安得列夫有些影響。”短論中還有一處,指出在中國文學史上,魯迅跟屈原、陶潛、杜甫等同屬一個精神譜系。 魯迅讀后笑道:“這未免過譽了。 如果我們的文豪們一聽到,我又要挨罵幾年了。”此文雖短,但雪峰提出了兩個重要論點:一是認為魯迅10 余本雜文集的社會文化意義,比他的5 本創作(小說、散文詩)更有價值,更為大眾所重視;二是指出“作為一個思想家及社會批評家的地位,在中國,在魯迅自己,都比藝術家的地位偉大得多”。對此,魯迅均未持異議。 因此,雪峰這篇短論,在魯迅研究史上就具有了特殊的意義和地位。
《回憶魯迅》是雪峰奉獻給魯迅愛好者和研究者的一部獨一無二的著作。 此書實際上1946年已開始醞釀,曾在《文匯報·筆會》上發表過一些章節。 1951 年雪峰開始重寫,8 月1 日開始在《新觀察》半月刊上連載,至翌年第8 期續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結集出版,后多次再版,發行量逾10 萬冊。 在這部書中,雪峰以魯迅的學生兼戰友的雙重身份,重點回憶了從1928 年至1936年他跟魯迅的交往,尤其突出了交往中極富政治意義的重大事件,為研究魯迅后期的思想和創作所必讀。 但這部書的寫法尚存在可商榷之處,即作者未將獨家回憶史料與作者本人的理解認識加以必要區分,讀后給人以史料尚可增補而議論可加刪節的感覺。 據唐弢回憶,雪峰在浙江第一師范的同學魏金枝認為此書“有自我炫耀的傾向”。 這使雪峰感到十分詫異,并說:“我給胡喬木同志看過,他沒有說。”[11]
在魯迅研究領域,雪峰還貢獻了很多重要意見,值得后輩研究者認真領會。 在雪峰眼中,魯迅作品在整體上就是一部中華民族的衰落史,是一張中華民族的解剖圖,也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以來的一部血戰史;既顯示了魯迅政治的思想的天才,也顯示了魯迅詩的文學的天才。 魯迅與俄羅斯文學的關系,貫穿其文學活動的始終,這是基于俄羅斯文學的平民性和暴露社會矛盾的深刻性,同時基于魯迅的民族民主革命立場。 但魯迅對域外文化的擇取完全是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向著獨立的文學道路發展,所以他的任何作品都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民族性,從來沒有所謂的異國情調,只有中國文學跟世界文學進步潮流的有機融合。 雪峰認為魯迅思想雖有前后期之分,但他的思想的一貫性表現在催促新的誕生、促使舊的毀滅。 這是辯證法中最主要的一環,在魯迅作品中是一貫表現出來的。
對于魯迅不同體裁的作品,雪峰也進行了相當全面的論述。 他認為,魯迅700 多篇雜文,在中國思想斗爭史上的作用最大,既是民族文學的奇花,也是世界文學的奇花,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和思想史方面占有特殊的地位。 魯迅的小說數量雖說不多,但這些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品奠定了我國現代文學的基石。 魯迅的日記乍看起來似乎寫的多為信札往來、銀錢收付,實際上是研究魯迅的最寶貴和最真實的史料之一,也是屬于人民的重要文獻之一。 所以,早在1951 年,雪峰就通過上海出版公司影印出版了《魯迅日記》手稿。直至臨終前,身罹絕癥的雪峰仍鼎力支持身處逆境的濟南第三中學教師包子衍研讀《魯迅日記》。
在魯迅作品的普及方面,馮雪峰的功績至豐至偉。 普及魯迅的首要工作是出版魯迅的著作,使廣大讀者能通過文本直接跟魯迅進行精神對話、心靈交流。 以雪峰的資歷,新中國成立初期按副部級待遇發放工資;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成立華東軍政委員會,原定雪峰出任文化部長。 雪峰推脫,只出任了上海魯迅著作編刊社的社長兼總編輯。 這個“社”位于上海武進路309 弄12號,成立之初只有4 位編輯,2 名工作人員;辦公用具主要是許廣平留在上海的家具,資料主要靠個人藏書。 就是在這種艱苦的條件下,馮雪峰在1950 年10 月23 日制定了一個《魯迅著作編校和注釋的工作方針和計劃草案》。 1951 年4 月,北京成立了人民文學出版社,雪峰擔任社長和總編輯。 魯迅著作編刊社也由上海遷至北京,成為了人民文學出版社所屬的一個編輯室。
1956 年10 月—1958 年10 月,10 卷本《魯迅全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齊。 全集總體上就是按照雪峰的規劃草案編輯的。 這部《魯迅全集》跟1938 年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所編的20 卷本《魯迅全集》差別有三:一是專收魯迅的創作、評論和文學史著作,以及部分書信,僅增加的佚文就多達106 篇。 《魯迅譯文集》《魯迅輯校古籍》《魯迅科學論著》另行出版。 二是各卷均附注釋,共5 800 余條。 由于魯迅著作博大精深,其注釋也具有百科全書性質,在魯迅著作出版史上是一件開創性的工作。 三是所有作品均經過校勘,訂正了已發現的錯字和標點。 不過,這套全集僅收魯迅書信300 多封,而當時已征集的書信有1 655 封。 個別注釋(尤其是《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題注)有違歷史事實。 但造成上述錯誤的原因文學界已經清楚,不能由雪峰本人承擔責任。
為了幫助一般讀者了解魯迅的生平、思想和著作,雪峰撰寫了大量深入淺出的普及性文章,囊括了魯迅的雜文、日記、譯文、手稿及《野草》中所收的23 篇散文詩。 雪峰撰寫的《魯迅和他少年時候的朋友們》全書僅9 000 余字,1951 年1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1954 年6 月12 日榮獲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兒童文學創作一等獎,總發行量多達45 萬冊,創造了同類作品在出版史上的佳話。 一般讀者如何才能讀懂魯迅作品? 雪峰提出了一個“選擇性閱讀”的建議,即由淺入深、由易到難,先選編魯迅的一些短篇小說,再聯系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去讀他的雜文。 要多精選一些給工人和農民讀的選本,尤其必須有詳細和淺近的注釋。 雪峰的上述建議無疑是切實可行的。
4 毛澤東的支持者馮雪峰
在閱讀馮雪峰回憶魯迅的文章時,筆者曾產生過一種疑惑,那就是雪峰非常強調毛澤東跟魯迅之間相互敬重的感情。 雪峰草擬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公開批駁過中國托派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各派聯合一致抗日”的主張。 魯迅去世之后,毛澤東又被列名為“治喪委員會委員”。 而根據黨史資料,在1935 年1 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是由張聞天代理博古(秦邦憲)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直到1937 年8 月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才擔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書記(亦稱主席)。 1945 年4 月至6 月召開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并載入黨章。1936 年4 月,馮雪峰作為中共中央特派員赴上海,主要是周恩來、張聞天交代的秘密任務,并不是毛澤東。 依據現存資料,可知雪峰一生崇拜的人只有兩個:一個是魯迅,另一個是毛澤東。 雪峰曾經明確跟友人說,在新中國之前他經歷的黨內斗爭中,他始終屬于毛澤東的支持者。
雪峰跟毛澤東的直接接觸,始于1933 年底。當時由于叛徒的出賣,雪峰無法繼續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奉命調往江西瑞金中央蘇區,擔任中央黨校教務主任。 該校校長是張聞天,副校長是董必武。 中央蘇區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在贛閩粵三省創建的革命根據地。 1934 年1 月,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從上海抵達瑞金,將中共蘇區中央局跟中共臨時中央合并,改成中共中央局。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在所謂反“羅明路線”的斗爭中受到批判和打擊。 羅明(1901—1987)當時是中共閩粵贛特委組織部長、福建省委代理書記,擁護和開展游擊戰爭,貫徹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的戰略方針。 博古1945 年5 月3 日在中共七大會議上發言說:“蘇區反對羅明路線,實際是反對毛主席在蘇區的正確路線和作風,這個斗爭擴大到整個中央蘇區和周圍的各個蘇區,有福建的羅明路線,江西的羅明路線,湘贛的羅明路線等等。”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上)一書中寫道:“反‘羅明路線',無論在福建還是在江西,矛頭都是指向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的。”[12]此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在瑞金主持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工作的是博古和項英。 正因為毛澤東當時相對有閑,便有機會跟雪峰聊天,有一回他甚至風趣地說:“今晚約法三章:一不談紅米南瓜,二不談地主惡霸,不談別的,只談魯迅。”當時談話的具體內容唐弢在《追懷雪峰》一文中做出了轉述:
毛澤東告訴雪峰,他很早就讀了魯迅作品。應該讀一讀《阿Q 正傳》。 阿Q 是個落后的農民,缺點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會這個要求是錯誤的。 當雪峰談到他代表“左聯”去請魯迅寫文章時,毛澤東說:“哦,你們還給魯迅出題目! 不出題目豈不比出題目更好嗎?”當談到中央蘇區有人主張請魯迅來擔任“人民教育委員”時,毛澤東搖頭說:“這些人,真的是一點不了解魯迅。”[13]
在中國現代作家中,雪峰是少有的真正走過二萬五千里的“長征干部”。 長征更增進了雪峰對毛澤東的感情。 雪峰跟毛澤東都有煙癮。 毛澤東曾多次派人把自己弄到的紙煙送給雪峰。當瞿秋白就義的噩耗傳來,毛澤東特意通知雪峰,并沉痛地說:“不僅僅是你失去了一個好朋友,我也失去了一個好朋友。”長征期間黨內也有路線之爭。 1935 年7 月,紅軍陸續到達四川松潘縣毛兒蓋藏民區,這時毛澤東跟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已經白熱化。 紅四方面軍原參謀長李特支持張國燾的主張,大肆進行宗派主義活動。 雪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跟李特的宗派主義進行了不調和的斗爭。 1938年,雪峰準備著手撰寫一部50 萬字的小說,書名為《紅進記》,后改題為《盧代之死》,就是反映紅軍從江西蘇區到陜北的那段艱苦征程。 盧代即作品中的主人公,由紅軍戰士成長為一位師長。書中有一段描寫盧代在行軍途中見到毛澤東的文字:“就在這時,他看到更遠的一些地方在一株大的橡樹或榕樹下,有一個巨人在那里散步。 暮色中,還可以看到手上的煙頭一明一滅。 這巨人就是毛澤東。 他對這巨人充滿了敬仰,他知道民族的希望、亞洲的命運都寄托在他身上。 巨人像磁石一樣吸引著他,喚起了他的新的力量,他終于掙扎著回到部隊中來,又追隨巨人繼續長征的路程了。”[14]一目了然,這里描寫的是虛構人物盧代的心理活動,而表達的是雪峰當年的真情實感。
正因為雪峰在當年黨內復雜的路線斗爭中屬于毛澤東的支持者,所以他1936 年4 月下旬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見到魯迅之后,才會重點介紹毛澤東的戰略思想,以及1935 年底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闡述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 雪峰在《回憶魯迅》一書中寫道:“因為那時候(一九三六年),毛澤東同志的天才與思想才開始為黨內大多數人所認識,并逐漸為黨外廣大人民所知道,但許多最重要的著作都還沒有發表,黨內大部分同志在認識上也是以后一步一步深刻起來的,黨外的人在當時真正認識的并不多。”[15]雪峰第對毛澤東的看法,無疑會對魯迅的政治態度產生影響。 關于魯迅送毛澤東一只相當大的金華火腿,以及將《海上述林》(上卷)的皮脊本送毛澤東、藍絨面送周恩來,也都是出于雪峰的提議,因為當時魯迅正有一點錢在雪峰身上。 雪峰本人還買了三五聽白錫包紙煙送給毛澤東,由地下“交通”送到西安再轉交陜北。魯迅去世之后,毛澤東列名于“治喪委員會委員”名單,顯然也是出于雪峰善意的“先斬后奏”。 雖然上海地下黨有渠道跟陜北用秘密電臺溝通,但當時時間上并不允許。 雪峰講得很清楚:“我趕到時,魯迅已斷氣半小時,過了一會兒孫夫人(宋慶齡)也來了,立即在孫夫人參加之下商量治喪委員會名單……當時記者們集中在樓下催得很緊,就把這名單向他們宣布了。”[16]關于魯迅喪事的處理,雪峰事后跟潘漢年商量,再打電話請示了中央。 只是基于當時國民黨當局的新聞管控,除了上海《日日新聞》(晨刊)之外,其他報紙都不敢刊登毛澤東的名字。
還必須提及一件絕對不應該忘卻的往事,那就是雪峰幫助毛澤東將他多年失散的兩個兒子送到蘇聯。 雪峰1936 年5 月到達上海之后,給了董健吾一筆數量相當大的錢,作為岸英兄弟的收養費。 之后雪峰派地下黨員楊承芳跟莫斯科取得聯系,將岸英兄弟護送到莫斯科國際兒童教養院學習。 毛岸英烈士的事跡眾所周知。 毛岸青后來也成了優秀的俄文翻譯家。 被雪峰安排秘密赴陜北的人中,還有丁玲、斯諾、馬海德等知名人士。 馮雪峰的此舉不僅是一般的善舉,而且是對革命事業的一大貢獻。
5 逆境中的馮雪峰
從1954 年開始,雪峰受到了一系列不公正的政治待遇。 首先是批判他主編《文藝報》期間曾用“貴族老爺式的態度”對待李希凡和藍翎,阻礙了對俞平伯《紅樓夢簡論》一文的批判。 但雪峰在1954 年9 月30 日《文藝報》轉載這兩位青年批評家論文的“編者按”中,明確指出他們的觀點“在基本上是正確的”,“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 據當時的親歷者說,當李希凡、藍翎來《文藝報》編輯部時,雪峰非常熱情地接待了他們,臨別時送到大門外,替他們叫了三輪車,還付了車錢。
1954 年12 月31 日,毛澤東將雪峰的雜文《火獄》轉發給中共中央書記處成員及中宣部負責人一閱,“批語”現已收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亦見《毛澤東年譜》第2 卷。 不過“批語”對文章本身未置一詞。 1945 年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還曾贊揚雪峰的《鄉風與市風》《真實之歌》是多年不遇的好作品。 1955 年,雪峰被卷入“胡風事件”,在黨內受到批評,也做過檢討。1957 年6—8 月,中國作協黨組批判并不存在的“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周揚找雪峰說:“批判丁玲、陳企霞,不批判你,群眾是通不過的。”8 月27 日,雪峰被宣布為“文藝界反黨分子”。 但雪峰無論如何也未曾反黨,只因反對投降主義路線跟博古拍過一次桌子。 同年9 月,并無右派言行的雪峰被錯劃為右派。 1958 年2 月,雪峰隨之被開除黨籍。 在開除他黨籍的支部會上,雪峰表示開除決議說的不符合事實,但同時也舉手表示服從,并希望能再回到黨內來。 1961 年,有關方面不允許雪峰完成關于長征的長篇小說,雪峰憤而焚毀積稿。 “文化大革命”期間,雪峰被關進“牛棚”,寫了大量外調材料。 周揚1979 年5 月1 日致樓適夷信中寫道:“他(指雪峰)沒有在‘四人幫'惡毒誹謗我的時機,對我落井投石,把一切錯誤推在我得身上。”1969—1971 年,年近古稀的雪峰被下放到湖北咸寧文化部“五七”干校,參加過田間勞動,也放過鴨子。
在極端艱苦的歲月中,雪峰吟誦過自己《普洛美修士片段》中的詩句:“忍耐是不屈,而憤怒是神圣,頑強簡直是天性! 但這一切都是為了愛……”1975 年2 月,長期患肺氣腫和肺炎的雪峰被確診為肺癌,在首都醫院施行了左上肺全葉切割手術。 1976 年1 月31 日(即農歷丙辰年春節)上午11 時,雪峰在春節的爆竹聲中因肺炎并發癥去世,享年73 歲。 為他擦洗身體時,可以看到他胸前有兩個深深的幾乎穿透著的傷疤,那是在江西上饒集中營坐牢期間留下的。 家屬為他穿上了一身半舊的制服和一雙半新的布鞋。 那制服,是雪峰1951 年率中國作家協會訪問團赴蘇聯參加十月革命節活動時添置的,已經有25年。 臨終前,他曾托人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希望能夠恢復他的黨籍。 這封信當然未能得到回復。 因為姚文元下令“馮雪峰追悼會不能致追悼詞”,他的骨灰盒上只有其子女題寫的三行字:“詩人。 作家。 畢生信仰共產主義。”1979 年2月5 日,雪峰的右派錯案在他逝世3 年之后終于得以改正;4 月4 日,他的黨籍也終于得以恢復。當年11 月17 日,雪峰的真正追悼會在北京西苑飯店大禮堂舉行,參加者有各界人士1 000 余人。葉劍英、鄧小平、陳云、宋慶齡、鄧穎超、王震、胡耀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送了花圈。 胡耀邦還為《回憶雪峰》一書題寫了書名。 時任中宣部副部長朱穆之在悼詞中贊揚馮雪峰“一生忠于黨,忠于人民,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肯定了他在上海從事左翼文化活動期間“傳達了黨中央的各項方針政策,使魯迅加深了對黨中央、毛澤東同志的敬仰和信賴”。 會后有60 余人將其骨灰送至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據《新文學史料》1980 年第1 期記者報道資料,在為雪峰捧骨灰盒的人中有4 個“晚一輩魯迅研究者”,他們是:陳漱渝,朱正,陳早春,包子衍。